想象的共同体增订.pdf
http://www.100md.com
2020年1月29日
 |
| 第1页 |
 |
| 第7页 |
 |
| 第17页 |
 |
| 第24页 |
 |
| 第36页 |
 |
| 第89页 |
参见附件(2296KB,157页)。
想象的共同体,这是一本关于社会民族文化相关的书籍,作者是当前的民族主义理论家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全书一共分为是一个章节带你了解民族主义的特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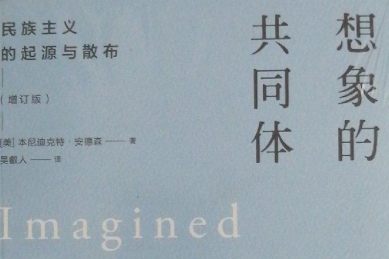
想象的共同体内容提要
是一部在20世纪末探讨民族主义的经典著作。作者本尼迪克特·安德森以“哥白尼精神”独辟蹊径,从民族情感与文化根源来探讨不同民族属性的、 各地的“想象的共同体”,认为这些“想象的共同体” 的崛起主要取决于以下因素;宗教信仰的领土化、古典王朝家族的衰微、时间观念的改变、资本主义与印刷术之间的交互作用、 方言的发展等。本书影响所及几乎横贯所有人文与社会学科,是在理解人类社会诸多现象时不可或缺的指引。
本书自1983年在英语世界问世,到2007年底为止,已经在33个 和地区中,以29种语言出版。也正是这种译本广泛散布的状态,引起作者写作“旅行与交通:论《想象的共同体》的地理传记”的冲动。于是,英国Verso出版社添加此部分内容,出版了新版的《想象的共同体》。本书便以其为底本,增订出版,以飨读者。
想象的共同体作者资料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当代最重要的民族主义理论家。1936年出生于中国云南省昆明市;1941年,为躲避日益升级的中日战争,随全家离开中国。1953年,安德森进入剑桥大学求学,主修西方古典研究与英法文学;1958年远赴康乃尔大学投身乔治·卡欣门下,专攻印尼研究,之后又将研究目光转向其他东南亚国家。1983年,出版民族主义研究经典著作《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一书。除《想象的共同体》外,其他著作还有:《比较的幽灵:民族主义、东南亚与世界》《革命时期的爪哇》《美国殖民时期的泰国政治与文学》和《语言与权力:探索印尼的政治文化》等。
想象的共同体主目录
第二版序
第一章 导论
第二章 文化根源
第三章 民族意识的起源
第四章 欧裔海外移民先驱者
第五章 旧语言,新模型
第六章 官方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
第七章 最后一波
第八章 爱国主义和种族主义
第九章 历史的天使15c
第十章 人口调查、地图、博物馆
第十一章 记忆与遗忘
想象的共同体截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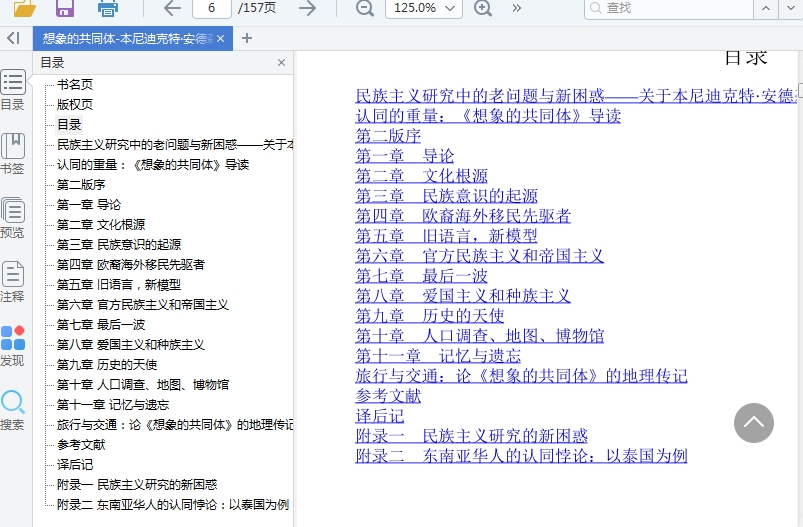

本书仅供个人学习之用,请勿用于商业用途。如 对本书有兴趣,请购买正版书籍。任何对本书籍的修改、加工、传播自负法律 后果。
本书由“行行”整理,如果你不知 道读什么书或者想获得更多免费电子书请加小编微信或QQ:2338856113
小 编也和结交一些喜欢读书的朋友 或者关注小编个人微信公众号名称:幸福的 味道 为了方便书友朋友找
书和看书,小编自己做了一个电子书下载网站,网 站的名称为:周读 网址:www.ireadweek.com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著;吴叡人译.—
增订本.—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
书名原文:Imagined Communities: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ISBN 978-7-208-13849-0
Ⅰ.①想… Ⅱ.①本… ②吴… Ⅲ.①民族主义-研究 Ⅳ.①D091.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125968号
责任编辑 潘丹榕
封面装帧 人马艺术设计·储平
想象的共同体
——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
[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 著
吴叡人 译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 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o)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635×965 116 印张 19.5 插页 4 字数 263,000
2016年8月第1版 2016年8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208-13849-0D·2877
定价 48.00元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First published by Verso 1983
This edition published by Verso 2006
· Benedict Anderson,1983,1991,2006
new material ? Benedict Anderson,2006
Chinese(Simplified Characters only)Trade Paperback
Copyright ? 2016 by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译稿经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企业股份有限公司独家授权想象的共同体 ——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增订版)
[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 著
吴叡人 译
上海他认为他的职责在于逆其惯常之理以爬梳历史。
沃尔特·本雅明,《启蒙之光》 (Illuminations )
如是从所有人种之混合中起始
那异质之物,英格兰人:
在饥渴的强奸之中,愤怒的欲望孕生,在浓妆的不列颠人和苏格兰人之间:
他们繁衍的后裔迅速学会弯弓射箭
把他们的小牝牛套上罗马人的犁:
一个杂种混血的种族于焉出现
没有名字没有民族,没有语言与声名。
在他热烈血管中如今奔流着混合的体液
撒克逊人和丹麦人的交融。
当他们枝叶繁茂的女儿,不辱父母之风
以杂交之欲望接待所有民族。
这令人作呕的一族体内的确包含了嫡传的
精粹的英格兰人之血……
录自丹尼尔·笛福(Daniel Defoe)
《纯正出身的英格兰人》 (The True-Born Englishman )目录
民族主义研究中的老问题与新困惑——关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民族主义研究 汪晖
认同的重量:《想象的共同体》导读
第二版序
第一章 导论
第二章 文化根源
第三章 民族意识的起源
第四章 欧裔海外移民先驱者
第五章 旧语言,新模型
第六章 官方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
第七章 最后一波
第八章 爱国主义和种族主义
第九章 历史的天使
第十章 人口调查、地图、博物馆
第十一章 记忆与遗忘
旅行与交通:论《想象的共同体》的地理传记
参考文献
译后记
附录一 民族主义研究的新困惑
附录二 东南亚华人的认同悖论:以泰国为例如果你不知道读什么书,就关注这个微信号。
微信公众号名称:幸福的味道
加小编微信一起读书
小编微信号:2338856113
【幸福的味道】已提供200个不同类型的书单
1、 历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
2、 每年豆瓣,当当,亚马逊年度图书销售排行榜3、 25岁前一定要读的25本书
4、 有生之年,你一定要看的25部外国纯文学名著
5、 有生之年,你一定要看的20部中国现当代名著
6、 美国亚马逊编辑推荐的一生必读书单100本
7、 30个领域30本不容错过的入门书
8、 这20本书,是各领域的巅峰之作
9、 这7本书,教你如何高效读书
10、 80万书虫力荐的“给五星都不够”的30本书
关注“幸福的味道”微信公众号,即可查看对应书单和得到电子书
也可以在我的网站(周读)www.ireadweek.com 自行下载
更多书单,请关注微信公众号:一种思路民族主义研究中的老问题与新困惑
——关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民族主义研究
汪晖命运
2015年12月13日,朋友传来消息: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教授当日在印度尼西亚辞世。一位在雅加达大学
作研究的年轻人写信说,他前一日还在学校听他演讲,精神矍铄,不能相信他的离去。安德森年届79岁高
龄,虽然事发突然,但并不完全突兀。2013年9月,清华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所邀请他来清华讲学,他
在第一时间回信表示感谢:“能够被您和您在北京的同事们邀请,是我的荣幸。我觉得3月很合适,那个月
中适合您的任何时间都可以。在那个月,我没有承诺其他的旅行安排,而且那是泰国最热的一个月!您的
来信让我想起上次在中国的时间已经是1941年!!!唯一需要警告您的是,77岁的我已经有些脆弱,经常
会感到疲惫……”虽然安德森提及了身体的脆弱和疲惫,但三个惊叹号却强烈地表达了他对即将重访中国的
兴奋之情。
2014年春天,他如约访问北京,虽然常需坐轮椅,但始终兴味盎然,时时冒着雾霾,穿行于街市之
间。除了安排他的演讲之外,我也陪他去国家博物馆等处参观。安德森1936年8月26日出生于中国境内毗邻
东南亚地区的大城市昆明,学术事业起始于他在1967年完成的博士论文《革命时代的爪哇》。1972年,因
与同事合作完成的关于苏哈托政变的研究(撰写于1966年)公开发表,他被拒绝进入印度尼西亚,时间长
达27年(1972—1999年)之久。在此之后,他重新回到祖父、父亲和自己均曾生活过的地区作研究,最终
殁于与自己的国家相隔遥远却又与其人生道路纠缠始终的国度。安德森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夕出生于中
国,在日本军队轰炸昆明的危险时分离开,终于在73年之后再度回到出生的国度,并在这里留下了他的思
考和足迹。冥冥之中,这两个开端与结束交叉重叠,或许就是命运的安排。
在他来访前夕,我们通过邮件商讨两次演讲的题目。我的建议是:首先,从1983年《想象的共同体》
问世至今,在三十余年的时间里,这部书一直是人们讨论和引用的对象,能否请他就三十多年来针对该书
的种种挑战,在清华的讲台上作一个回应?其次,他近年常常住在东南亚地区,观察那里的起伏变化,能
否向中国的听众介绍他的最新研究成果?安德森很快作出回应,并拟定了两个题目,一个是《民族主义研
究的新困惑》,另一个是《东南亚华人的认同悖论:以泰国为例》。想象
安德森所说的“民族主义研究的新困惑”其实是对《想象的共同体》一书的基本论点的延伸性论述。
《想象的共同体》最著名的观点是:民族是一个想象出来的政治意义上的共同体,即它不是许多客观社会
现实的集合,而是一种被想象的创造物。在民族主义研究中,将民族理解为某种想象物并不是安德森的发
明,早于他的研究,厄内斯特·盖尔纳就曾建议“从意愿和文化与政治单位结合的角度来给民族下定义”,即
民族主义造就了民族,而不是相反,从而民族主义热情包含了“文化上富于创造性的、空想的、积极创造的
一面”。 [1] 他们两人也都指出这种想象的、创造性的方面并不等同于说民族主义是一种虚假的、人为的产
物,而是一种新的、被创造的社会事实。这些观点明显受到20世纪60年代以降社会理论、心理分析学说和
意识形态理论的影响。拉康的现实的、想象的和象征的三界说、科里利厄斯·卡斯托里亚迪斯(Cornelius
Castoriadis)在拉康影响下提出的“社会的想象机制”(imaginary institution of societies),以及阿尔都塞的意
识形态理论,都为此后社会理论中各种各样的“想象”论提供了灵感。但对于安德森而言,作为政治共同体
之民族的诞生是与印刷资本主义的发展密切相关的,后者整合各种方言,为小于作为帝国语言(拉丁语)
的新的权力语言的形成提供了可能。较之盖尔纳的解释,安德森的分析更加清晰地突破了民族主义解释中
的社会要素决定论,强化了其形成的能动方面。至于这种能动的解释在多大程度上脱离了社会学决定论,我们稍后再谈。
安德森对民族主义的研究远远超出了欧洲的语境,也不再将民族主义的历史讲述为一个从欧洲向世界
扩散的故事。但我们并不难发现:他的叙述与更早的有关欧洲民族主义的叙述存在某些重合。例如,根据
他的叙述,在欧洲,新教与印刷资本主义的结合促成了取代宗教团体和王朝体系的政治共同体的出现;印
刷资本主义为民族语言的整合与形成提供了条件。这些要素在一些批评者的眼中也正是欧洲中心主义的变
体。这里要强调的是:正是基于这一“在理解世界的方式上”发生了的“根本变化”,安德森对民族主义现象进
行了重新叙述,即有关民族主义的三重分类。不同于那些认为民族主义是从欧洲漫延至世界其他地区的传
统观点,他认为民族主义的第一波是发生在北美殖民地的“克里奥尔民族主义”,或称远程民族主义。这一
民族主义综合了殖民地各阶层的诉求,反抗宗主国的压迫和不平等对待,但在价值上同时汲取了欧洲启蒙
思想。这种对于新的政治共同体的想象是那些去往宗主国的“克里奥尔”官员和当地“克里奥尔”印刷工的创造
物。南北美洲在19世纪兴起的新一波大众性民族主义正是对于这一民族主义版本的回应。第二种民族主义
模式,也是被其他地区民族主义最常复制的模式,是欧洲的语言民族主义,正是通过这语言民族主义的创
造,一种取代帝国的、奴隶制和封建等级制的,即主权的政治共同体诞生了。第三种民族主义即官方民族
主义,即由国家由上至下推进的文化统一与政治统一的进程,通过在交流工具(印刷术)、普及教育和内
政构造等各方面的强制推行,上层统治最终促使包含多样性的和地方性的文化趋于同质化。俄国、晚清中
国的改革都可以算作这一官方民族主义的典范。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民族解放运动的浪潮是民族主义
的“最后一波”,它既是对于官方民族主义的殖民地形式——帝国主义——的反应,也是对先前两波民族主
义浪潮中的大众民族主义(北美与欧洲)的模仿。由此,安德森以民族主义多种形态为介质,描述了一个
不同于从欧洲扩散至其他地区的单线论的多重扩散的全球进程。
《想象的共同体》对民族主义研究的贡献或许可以被归纳为如下几点:首先,它不是用族群、宗教、语言等社会要素解释民族形成,也不是用工业化或一般意义的资本主义说明民族主义的兴起,而是别有新
意地提出印刷资本主义与新的政治共同体形成之间的伴生关系。这为民族形成是一种现代创造过程或想象
过程的论点提供了前提,也为颠倒传统观念中民族与民族主义的衍生关系铺平了道路,即不是民族产生了
民族主义,而是民族主义创造了民族。其次,历来的民族主义研究都将法国大革命的政治原则和欧洲民族
国家的诞生视为一种向全球扩展的体系,并以此为主要视角分析非西方地区的民族主义,而安德森却倒置
了民族主义的历史,即民族主义并不是一种欧洲的产物,恰恰相反,最早的民族主义是发生在北美的“克里
奥尔”民族主义,即一种远程的民族主义。或者说,最早的民族主义是殖民主义全球关系的产物。这一论点
或许源自他在印度尼西亚作研究时所受到的触动,亦即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及其政治进程与欧洲民族主义
之间不可能只是一种由中心区域扩展至其他地区的等级性衍生关系。在有关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的后现
代论述所创造的氛围中,安德森对于殖民地与宗主国、殖民地民族主义(反帝的民族主义)与官方民族主
义的区分,为重新审视20世纪民族运动的历史留下了一个缺口。困惑
《想象的共同体》可能是三十年来有关民族主义的研究中——也是全部社会科学理论中——被征引和
讨论最多的文本之一。在安德森抵达北京后的闲谈中,我问及他对有关《想象的共同体》的质疑和批评的
看法,即哪些观点和商榷是他认为最重要的和值得回应的。他用一种幽默的但显然也是有些骄傲的态度回
答说:绝大部分质疑都是用各自的历史经验对他的理论论述进行修订,至于到底有哪些质疑真正触动了他
的理论预设,他没有举出任何一例。我至今还记得他说这话时的表情。不难想象,他在清华大学所谈的“民
族主义研究的新困惑”与其说是对批评和质疑的回应,毋宁说是对他早期研究的补充和完善。的确,这两场
演讲从不同的方向对《想象的共同体》有关民族和民族主义的定义、历史脉络作了理论的与历史的再阐
释。
这个基本定义就是民族是一个想象出来的政治意义上的共同体,一个被想象的、有限的、享有主权的
共同体。在《想象的共同体》中,安德森解释了为什么这个共同体不是许多客观社会现实的集合,而是一
种被想象的创造物。而在清华的演讲中,他改变了论述的重心,侧重阐述了两个有关这一“想象的共同
体”的问题:第一,作为政治共同体的民族与其他共同体(宗教共同体、族群共同体、家庭等等)相比,究
竟有哪些不同的特征?如何辨识民族主义的情感方式与其他情感方式的联系与区别?第二,《想象的共同
体》所涉及的远程民族主义主要产生于西半球(海地、北美等),那么,在东半球的东南亚和中国,移民
群体与民族认同的关系如何?
他的第一场演讲《民族主义研究的新困惑》主要回答第一个问题,而第二场演讲《东南亚华人的认同
悖论:以泰国为例》则尝试探索第二个问题。在我看来,他所提出的问题很可能不是民族主义研究中的“新
困惑”,而是民族主义研究中尚未展开的老问题。安德森首先不是从定义出发来解释这个问题,而是用某种
人类学的观察来辨识民族主义的认同和情感特征。但是,正如他的印刷资本主义概念很难脱离欧洲民族语
言的形成的历史模型,他对作为政治共同体的民族的独特性的解说也很难脱离欧洲宗教共同体与民族共同
体之间的比较。用他的话说,资本主义、印刷技术和人类语言多样性之间的重合是与一种世俗的政治共同
体的到来同步的。事实上,他的第一场演讲的真正意义在于揭示了他(其实也包括绝大多数西方理论家)
对政治共同体的认识是从政治宗教的联系与区别中展开的,宗教、宗教共同体是思考政治、政治共同体的
基本参照。这是欧洲启蒙运动的遗产。这也让我们更为清楚地了解为什么他在《想象的共同体》中用一种
对于非西方读者难以理解的方式讨论弥赛亚时间与民族主义的空洞、均质的时间之间的关系。如果说《想
象的共同体》对时间的讨论最为抽象和难解,那么,他在清华的演讲却以极为浅显的方式再度通过宗教与
政治之间的关系展开对民族共同体特征的描述:民族共同体和宗教共同体都涉及信念和情感,但两者的区
别是什么?人们像认同宗教一样相信自己的国家是好的,却不会像宗教信徒相信上帝绝对正确那样相信国
家的完美。民族主义的情感表述是:即便我的国家会犯错,但在情感上,不论国家对错,她依旧是我的国
家。这与宗教共同体的信念产生了区别:民族和民族领袖可能犯错,而宗教——如同大多数欧美理论家们
一样,安德森的宗教论述基本上是在一神教的范围内——不会承认信仰和上帝会犯错。这种信念形态的区
分其实也可以被描述为一种世俗信仰与超越信仰之间的区分,即国家——以及他的贤明的或犯错的先人
——始终与我们同在,他们既不上天堂也不下地域,是现世的或历史性的存在(故而可以犯错),而上帝
却在天堂里,他永远正确。正如民族主义运动或民族主义领袖一再诉诸家庭、家族、宗族等等血缘共同体
以表明民族共同体的本质纽带,安德森从另一个角度观察了民族认同与亲缘纽带在情感特征方面的联系和
区别。他比较孩子对母亲行为的羞耻感与民族感情中对于民族行为或状态的羞耻感,不但说明了民族认同
对亲缘关系的模拟,而且也以此论证民族认同与宗教认同的区别。但他的分析集中于某种心理现象的描
述,未能从神学与政治、信仰与意识形态的关系中展开两者的区别和联系,明显地限制了其理论深度。
听到安德森对于羞耻感的讨论,我禁不住联想起美国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中有关原
罪与羞耻的讨论,即西方基督教文明是一种罪感的文化,而日本或东亚是耻感的文化,前者源自超越的视
角,是真正个人主义的,而后者却是在他者注视下的情感方式,是共同体伦理的产物。[20世纪80年代,中国还曾出现过模拟本尼迪克特论述的所谓罪感(欧洲)、耻感(日本)、乐感(中国)的文化模式
论。]本尼迪克特早年研究印第安部落,1927年完成了《文化模式》一书。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对罗
马尼亚、荷兰、德国、泰国等国进行民族性或国民性的研究,他的名作《菊与刀》也是在战争期间由美国
军方支持的研究项目。在这一日后名声大噪的作品中,日本民族性的二重性同样是在“文化模式”的框架下
展开的。与本尼迪克特不同,安德森的论述并未将羞耻感定义为某种独特的文化模式的产物。在他看来,羞耻感是一种现世的共同体关系(民族的、家族的、家庭的……)的普遍的情感特征——既然民族国家可
以犯错,人们对民族国家的情感方式中就必然包含着羞耻的意识,由此,羞耻感成为民族共同体区别于宗
教共同体的一种情感特征。近代中国民族主义运动对中国国民性的批判、美国反越战运动对于美国军事犯
罪的声讨、知识分子痛斥所置身的体制的姿态和唯我独醒的暗示、启蒙者对于未来(尚未出世的孩子们)
的展望均可以从民族主义情感方式的角度加以观察。但是,本尼迪克特与安德森都没有将羞耻感历史化,即有意或无意地遮盖了羞耻感总是在某个他者的注视之下才能发生,羞耻感是历史性权力关系的产物。在
欧美之外的地区,除了西方或内在化了的“西方”,还有谁能够拥有让人羞耻的目光呢?如果从摆脱羞耻感
的角度去观察亚非地区的民族革命,除了让那个目光感到满意之外,我们该从哪里去发现其创造性和自主
性?
安德森在演讲中特别提及民族主义哲学与泛灵论的关系或相似性,实际上是在暗示民族主义与宗教的
关系有些类似于泛灵论与一神教的关系。19世纪欧洲的著作家们——如黑格尔——一再论证:泛灵论是一
种与宗教(一神教)有所重叠但性质不同的东西,东方的佛教、印度教和许多民间信仰都带有泛灵论的特
点;如今安德森在民族主义及其哲学中也看到了类似的东西。正如泛灵论一样,民族主义赋予事物以灵
性,但这种灵性不在超验的世界里,而就在我们的身边,在日常生活的世界内。一个有待回答的问题是:
泛灵论与民族主义究竟存在怎样的思维、情感或历史的关系?如果“东方”是一个泛灵论的世界,那么,东
方民族主义在这个世界的诞生会与一神教世界的民族主义有所区别吗?
政治共同体与亲缘共同体在情感特征和信仰方式上的相似性(俗世的、总是包含羞耻感的、泛灵论的
等等)并不能作为两者相互同一或趋同的证明,恰恰相反,这种情感关联只有在某种状况下才能转化为政
治共同体的形成条件。在《想象的共同体》中,安德森对于印刷资本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关系的分析侧重于
政治共同体形成条件的探索,而在清华演讲中,他集中分析了远程民族主义形成的历史条件。远程民族主
义主要是对移民群体的民族主义及其与宗主国关系的研究,在《想象的共同体》中,这一概念用于对于18
—19世纪美洲民族主义的探讨,其形成的基础条件包括:移民群体、远离母国、与母国的亲缘关系、殖民
地与宗主国的政治关系(认同与反抗)、大规模移民得以可能的航运技术和印刷资本主义的诞生,以及由
这些基础条件而产生出的情感特征。如果说前三项是所有移民群体共同具备的条件,那么,后三项却因
时、因地而发生差异。这也是为什么有些移民群体会转化为新的民族,而另一些移民群体——即便在没有
完全同化于当地社群的条件下——却逐渐疏离于对母国的认同,其族裔认同始终不会上升为独立的民族认
同。在《民族主义研究的新困惑》的末尾,安德森简略地提及了美国《独立宣言》中的修辞,实际上是将
殖民地移民群体对宗主国的反抗和模仿,以及这种反抗和模仿中所包含的屈辱感,作为远程民族主义的政
治特征。
正是从这里,安德森转向了对于远程民族主义的新变化以及东半球移民群体的观察。较之18—19世
纪,当代移民的图景更加复杂,除了从中心地区向边缘区域的移民之外,20世纪移民活动的特征之一是从
边缘区域向中心区域的转移,其民族主义也增加了一些新的特色。安德森举出了在美国的印度锡克教后裔
通过网络参与母国的激进民族主义政治及其心理特征等例子,可惜没有就此展开论述。他聚焦的是东南亚
华人、尤其是泰国华人的认同和情感特征。安德森对于泰国的研究起始于他被禁止进入印度尼西亚之后,1974年他首度进入泰国学习泰语,并与一些卷入反对泰国军事政权的知识分子交往。因此,他的第二次演
讲也可以说是他长期观察的果实。在演讲展开之前,安德森首先声明对于中国的了解不够,有关东南亚华
人的讨论并不是成熟的或完成的作品,但他还是从泰国政治的动荡、尤其是红衫军与黄衫军的斗争及其认
同政治出发,展开其分析。我们可以将他的历史叙述简略地归纳如下:泰国拥有从不同历史时期移居该地
的“华人”,他们分属客家人(红衫军、他信)、福建人(阿披实、黄衫军)、海南人(素帖及其反政府群
体)、潮州人(国王)等等;华人群体由于地域背景、移民时间、阶级或阶层关系等等而发生各种分化组
合。在当前的政治运动中,华人的政治认同与其祖先在母国的出生地有着密切的关系。但他们之间能否构
成一种“华人认同”甚或能否被称为“华人”都是大有疑问的。换句话说,移民及移民群体的形成并不必然产生
远程民族主义,若无其他政治条件,族裔认同或地方认同将无法上升为民族认同,族裔或地方性共同体也
因此不可能上升为政治共同体,亦即民族。这也从相反的方向,说明了民族主义与民族的关系,即如果没
有一种有力的民族主义,即便存在语言、宗教(文化)和族群等社会要素,民族也不可能形成。
在演讲中,安德森主要根据一些片段的笔记展开分析,并未形成完整的论述,但这篇演讲显然提示了
他的思考新方向。在研究东南亚地区的民族主义问题时,安德森一再遭遇海外华人问题。例如,在写作
《比较的幽灵:民族主义、东南亚与世界》一书中有关菲律宾的章节时,他专门研究了“第一个菲律宾
人”何塞·黎刹。他在说明黎刹的身份时,先说他是诗人、小说家、眼科专家、历史学家、医生、好辩的随笔
作家、道德家和政治幻想家,随即提及他的血统,即“1861年他出生于一个混合了华人、日本人、西班牙人和他加禄人血统的富有之家”。但是,菲律宾民族主义并不是一种类似北美的远程民族主义。实际上,安德
森对于菲律宾的研究深受科拉松·阿基诺的“人民革命”的激励,而科拉松·阿基诺也有着华人血统。在安德森
撰写这一节时,他的弟弟、杰出的左翼历史学家佩里·安德森给我写信,请我帮他的哥哥查找一下有无黎刹
著名绝命诗的中文译本。我先前知道鲁迅曾经提及过黎刹及其绝命诗,但经过反复查核,竟然发现该诗有
17种中文译文(大多并不完整),其中最早的、也是不完整的译文的译者是梁启超。我至今不知道梁启超
是从哪种语言将这首诗歌翻译为中文的。没有证据表明梁启超懂西班牙语,他或许是通过日语翻译,但对
比日本译文,梁启超的译笔似乎更加准确。或许,梁启超与菲律宾华侨有关系?这些被称为“东南亚华
人”的人并不是一个作为政治共同体的东南亚华人群体的成员,毋宁说是华人移民分布于各地的后裔,他们
的血缘、地缘关系与北美独立运动迥然有别,并没有出现通过对母国的反抗而产生的政治民族主义。菲律
宾华人后裔的民族主义是在抵抗西班牙殖民主义的过程中形成的,它既不是通过认同母国也不是通过反抗
母国而产生的政治认同。与此略相类似,泰国华人的认同也并未构成远程民族主义的案例。这些例子似乎
从另一方面重复了《想象的共同体》的基本论点:民族—国家不是由宗教、语言、族群等社会要素决定
的,恰恰相反,它是想象的产物。问题
那么,安德森对于民族主义研究新困惑的解说是否完满地或恰当地回应了三十年来围绕或未必围绕他
的早期著作的争议和质疑呢?在回答这一问题之前,或许可以简略地分析对于《想象的共同体》一书的主
要质疑是否构成了真正的质疑。由于讨论纷杂,这里只能检讨两种在我看来较为重要的论点。第一种质疑
可以帕尔塔·查特吉(Partha Chatterjee)为代表。查特吉承认“在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问题的看法上,安德森
的主要贡献是他强调在研究民族运动时,应将意识形态对民族的创造作为中心问题。在这方面他还强调了
现代语言团体对民族的社会创造过程”。但他接着批评说:“安德森不再用这一过程中所固有的各种各样自
相矛盾的政治可能性,而是用社会学决定论来结束他的理论。”就像盖尔纳用“工业社会”的要求论述民族的
起源,安德森用印刷资本主义这一更为精巧的范畴描述民族形成的动态过程。他们都看出了“第三世界民族
主义中深刻的‘模式’特征” [2] 。在安德森的叙述中,尽管民族主义的第一波源自北美,但其模式却来自欧洲
——民族语言共同体、法国大革命提供的政治价值、与工业革命相互适应的政治模式等等。在查特吉看
来,“亚洲和非洲民族主义想象的最有力也最具创造性的部分不是对于西方推销的民族共同体模式的认同,而是对于与这一‘模式’的差异的探求。我们怎么可能忽略这种对于另类模式的寻求而免于将反抗殖民主义的
民族主义化约为一种滑稽的模仿?” [3] 查特吉认为抵抗殖民主义的民族主义包含了两个不同的方面,即物
质的方面和精神的方面。事实上,对于殖民主义的抵抗早在民族运动对于帝国的抵抗之前就已经开始,它
对于西方物质方面的模仿(如同“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所表明的)是与其在精神上寻求自主、独立、区
别于西方模式相互一致的。对于西方的物质模仿越成功,越需要在精神上获取主权性,因此,精神的领域
也是主权的领域,而后者的目标就是确立一个非西方的领域。也只有从这种反殖民民族主义对于差异的寻
求出发,才能发现殖民地民族主义文化(包括文学)的创造性,而不致将这种具有独特性的文学和文化实
践化约为一般的印刷资本主义,即一种在非西方地区进行复制的欧洲模式。
对于安德森的理论的第二种质疑也可以包含对于查特吉的“物质精神”二分论的修订。在查特吉所讨论
的“物质的”或“外在的”领域,如国家机器、科学技术等等方面,是否也存在寻求差异的运动呢?安德森讨论
过中国与苏联的“官方的民族主义”,他甚至也将1979年中越冲突的爆发归结为同一范畴,而拒绝讨论中国
革命曾经提供的既不同于西方路径也并非对苏联模式的简单复制的道路。在具有长久统一的国家传统、以
农业为主又同时拥有久远的独特城市经验、丰富的内外关系模式和半殖民条件的社会里,所有对于外来概
念和模式的运用都内在地包含了差异和独特性。例如,在人民战争条件下,阶级、政党、苏维埃、军队、民族等等范畴不断被使用和复制,但其内涵和相互关系早已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中国与周边国家之间间、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既包含了民族国家间关系的内容,又不可避免地呈现出传统的和不同于欧洲民族
主义的关系及其内容,如政党关系的内容。这种变化并不只是由于历史条件的差异而自然发生的,而是革
命和改良力量根据具体条件进行转化和创造的结果。这一过程甚至对后革命时代的政治共同体也仍然具有
重要的影响力。如果将中国、印度和其他亚非国家的民族运动置于全球民族主义运动和新的区域跨区域关
系的图谱中,民族主义研究中的欧洲模式在多大程度上将被修订甚至彻底改观?
《想象的共同体》将作为政治共同体的民族视为一种晚近的现象,而非宗教、语言、种族等等社会要
素的产物,从而松动了19世纪族裔民族主义所建立起来的民族主义知识,但这一松动同时也被政治分离主
义者用于对分离型民族主义的正当性论证——他们终于找到了一种摆脱种族、语言、宗教、文化的共同性
而“想象”民族的理论。2001年5—6月间,安德森在《新左翼评论》(New Left Review )发表了题为《西方
民族主义与东方民族主义》(Western Nationalism and East Nationalism)一文,“从台湾的角度反思亚欧地区
克里奥尔式的官方的、语言的与远程的民族主义,以及它们对于中国的含义。这里是否存在东方与西方之
间的重大差别?” [4] 这篇文章很可能是在他前一年的台湾演讲的基础上改定的。在广阔的世界范围内,安
德森重新描述各种不同的民族主义,并将“台湾民族主义”解释为最初形态的民族主义的当代版本,即海外
定居群体从帝制母国分离出去的运动。换句话说,他将台湾的分离运动与《想象的共同体》中描述的18世
纪的美国独立运动和19世纪初期拉丁美洲的民族运动放在同一脉络和类型下观察。在他的远程民族主义描
述中,共同的族群、共同的语言、共同的文化都不再是政治共同体的理由,地理的和政治的分离本身已经
为新的民族提供了依据。2000—2001年正值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和首轮政党轮替,分离主义认同政治成为
笼罩台湾政治、形成大众动员的主导氛围。这篇文章对于海外华人、台湾以及主要由华人创建的、区别于
中国的政治共同体新加坡的认同政治的分析,连同《想象的共同体》一书的建构主义之民族观,为台湾分
离主义知识分子提供了理论“灵感”。安德森将许多精力花在用各种细节解构民族与族裔之间的同构关系,以致他的一些有心的或无心的读者——甚至其本人——在分析当代民族主义现象时忘却了他的民族主义分类的政治出发点,即对抵抗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民族主义与官方民族主义的政治区分。从方法论的角度
看,这很可能与他侧重于民族主义的类型分析,而忽略深入的历史脉络的探索有关,其结果是他的颇具新
意的远程民族主义概念无法用于对不同的民族主义或分离主义的政治分析。正如他的弟弟佩里·安德森所
说,台湾与大陆的分离始终源于帝国主义的行动,而非针对帝国的反抗。 [5] 50年的日本殖民历史、战后至
今未脱的美国被保护地地位、冷战时代西方势力遏制社会主义中国的桥头堡、后冷战时代保障美国霸权地
位、遏制中国大陆的新阵地,所有这一切才是台湾分离主义的想象政治的物质基础和先决条件。这是霸权
构造下的分离主义政治,而非抵抗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独立运动。
安德森将意识形态对民族的创造作为中心问题,这一洞见对我们理解当代民族主义和民族分离主义仍
然具有重要的启发。正是意识形态促成相同族群、语言和文化的社会走向分离主义,也正是意识形态危机
成为新型民族主义的动力及契机。然而,相较于社会革命的视角,安德森显然更乐意从民族主义的视角去
观察现代历史。这是他的研究课题决定的,但也是他在两者之间进行辨析的过程中产生的方法。在他的眼
中,胡志明及其领导的越南革命主要是一场民族运动,而非社会革命运动。越南—柬埔寨战争、中国—越
南冲突更是社会主义国家深陷民族主义政治的范例。但是,离开社会革命的视野,亚非地区反帝反殖运动
的具体内涵、政治逻辑和不同命运都难以得到说明。查特吉批评安德森的民族主义理论将殖民地民族主义
视为纯粹衍生性的话语或对西方民族模式的复制,从而忽略了抵抗性民族主义所包含的创造性,这一点也
可以部分地解释他对中国革命及其创造性的忽略。此外,安德森对于作为政治共同体之民族的界定是通过
与非政治共同体的宗教和家族等区别而产生的,那么,如何解释那些并不依赖宗教或至少一神教立国的大
型政治共同体与民族的关系?如何解释王朝制时间与直线时间之间的关系?如何解释现代中国对于长久的
郡县制国家及其文化政治传统的“复制”(也是再造)?在包括《想象的共同体》在内的民族主义研究中,王朝制国家与现代民族国家之间的差异正是第三世界民族主义“衍生性”的证明,即公民权和人民主权都是
对法国革命提供的政治价值和制度模式的借鉴和模仿,但上述历史差异很可能需要另一种理论框架,以便
将民族主义置于新的世界历史的视野之中给予解释。在中国历史中,那种既内在于王朝又超越于具体王朝
的“中国”认同远早于近代民族运动,由这一政治共同体及其相互关系所塑造的区域秩序是否意味着需要找
到新的解释起点?走笔至此,我忽而想到:如果再度将这些问题向安德森提出,他会如何回答呢?我的猜
想是:他依旧会回答说这些问题仍然是“经验性的”,但同时迫不及待地回到东南亚甚至中国的经验中再度
提出他的“新困惑”。
得到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过世的消息后,我致信佩里·安德森表示哀悼和慰问。我在信中告诉佩里,中国
的报刊对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过世和他的生平道路、学术理论有很多报道,这也一定会激发许多研究者
重读其著作的愿望。如今,他的主要著作均有了中文本,或许纪念他的最好方法就是在重新阅读中激发新
的讨论。佩里回信说:是的,对于他的兄长而言,这是最好的纪念。果不其然,上海人民出版社决定重版
《想象的共同体》,潘丹榕编辑嘱咐我为新版写点文字,我因此建议将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清华的两次演
讲作为附录同时刊出,因为这是他对民族主义研究中新困惑的最后解说。我的这篇短文说不上是对他的理
论的全面分析,权作对他73年后重回出生地的纪念吧。
2016年5月11日星期三
————————————————————
注释:
[1] [英]厄内斯特·盖尔纳:《民族与民族主义》,韩红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版,第74页。
[2] [印度]帕尔塔·查特吉:《民族主义思想与殖民地世界:一种衍生的话语?》,范慕尤、杨曦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7年版,第
32页。
[3] Partha Chatterjee,“Whose Imagined Communities?”The Nation and Its Fragments:Colonial and Post-Colonial Historie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3,p.216.
[4] Benedict Anderson:“Western Nationalism and Eastern Nationalism”,New Left Review 9,May-June 2001,31—42.
[5] Perry Anderson:“Stand-Off in Taiwan,”London Review of Books ,Vol.26,Number 11,3 June 2004,12—17.认同的重量:《想象的共同体》 [1] 导读
在这个世界中,我们公正地表现自我;我们尚未形成一致的思想境界,因为这种境界需要直
言的批评、真实的创新以及真正的努力,而我们既未曾创造也未曾经历过这一切。 [2]
——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Said)同情弱小民族的“入戏的观众”
本尼迪克特·R.奥戈尔曼·安德森(Benedict R.O'Gorman Anderson)是一个与异乡和流浪有着深刻宿
缘的人。某种流离失所的因子似乎早早就流淌在爱尔兰裔的安德森家的血液中了,而这样的流离失所又和
大英帝国的盛衰始终相随。 [3] 他的祖父是大英帝国的高级军官,但祖母却来自一个活跃于爱尔兰民族运动
的奥戈尔曼家族(the O'Gormans)。祖父在19世纪后期被派驻槟榔屿(Penang),他的父亲就出生于这个
英属马来亚的殖民地上。在第一年剑桥大学的入学考试失败以后,他的父亲加入了在中国的帝国海关
(Imperial Maritime Customs in China),此后在中国居住将近三十年,成为一个中文流利,事事好奇,十分
热爱中国文化的人。1936年,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出生于云南省昆明市。和大多数其他住在中国的爱尔兰家
庭的小孩不同的是,本尼迪克特和他那位日后同享大名的兄弟——被著名的左派文学理论家特里·伊格尔顿
(Terry Eagleton)誉为“不列颠最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的历史社会学家,《新左翼评论》(New Left
Review )的主编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 [4] ——从小就在一个充满中国风味的家庭环境里成长,而
且他们的保姆还是一位越南女孩。
1941年,安德森家为躲避日益升级的中日战争而举家迁离中国,打算经由美国返回爱尔兰故乡。不料
这个返乡之旅的计划却因太平洋战争的爆发而受阻,安德森家只得暂居美国,等待战争结束。老安德森在
英国驻美情报单位找到了一个中文翻译的职位,本尼迪克特就随着父亲的工作,在加州、丹佛等地开始了
他最初的正式教育。日后,他曾这样深刻地描述这段早期的“流亡”经历的影响:“从那里开始了一连串的疏
离(estrangements)——在美国学校里的英国口音,后来在爱尔兰学校里的美国口音,在英国学校里的爱尔
兰腔——而这一连串的疏离经历使得语言对我而言成为一种获益良多的机会(beneficially problematic)。”
[5]
战争结束,安德森家终于回到爱尔兰,但本尼迪克特从1947年起就在英格兰受教育。1953年,他进入
剑桥大学,主修西方古典研究(Classics Study)与英法文学,奠定了良好的西方语言基础。 [6] 尽管小他两
岁的兄弟佩里在1956年进入牛津大学就读之后很快就成为英国20世纪50年代后期新左派运动的干将,但本
尼迪克特在此时却仍旧只是一个“从未有过任何严肃的政治思想”的20岁青年而已。 [7] 1956年11月的一天,当安德森在剑桥的街道上闲逛时,目睹了一个正在演说批评英法等国入侵苏伊士运河的印度人被一群上流
社会的英国学生攻击,而当他试图阻止这些学生的暴行时,却也和那个印度人同样遭到殴打,连眼镜都被
打落了。这场攻击行动结束后,这群英国学生列队唱起了英国国歌《天佑吾皇》。日后安德森自述当时
他“愤怒至头晕目眩”。这一事件成了安德森的政治启蒙——一种对“帝国的政治”的启蒙,而更重要的是,在
这场政治启蒙的仪式中,他和一个“被殖民者”站在一起接受了帝国的羞辱。 [8] 这个青年时期的经历,深深
影响了他日后批判帝国主义,同情殖民地民族主义的认知与道德立场。
1957年,印尼发生内战,美国中央情报局介入其中。这个新闻事件,立即吸引了刚刚受到“帝国主义压
迫”的政治启蒙的青年安德森的注意。好奇心与新生的政治关怀,促使他在1958年远赴美国的康乃尔大学,投入乔治·卡欣(George Kahin)门下专攻印尼研究。卡欣是美国印尼研究的先驱,“康乃尔现代印尼研究计
划”(Cornell Modern Indonesia Project)的创始人。他聚集了一批顶尖的人才到康乃尔,使这所大学成为美
国东南亚研究的重镇,至今仍声誉不衰。卡欣和其领导下的这批精英——或许我们可以将之称为美国东南
亚研究的“康乃尔学派”——将年轻的安德森引进了一个令人着迷的印尼研究的世界:除了卡欣对他在东南
亚民族主义政治的启蒙之外,第一本印尼文—英文辞典的编纂者、语言学家约翰·埃科尔斯(John Echols)
向他开启了印尼文学之门,而印尼语言文化学者克莱尔·霍尔特(Claire Holt)则带领他认识了独立前的印
尼、爪哇文化,以及荷兰的殖民研究。 [9]
然而对安德森而言,卡欣不但是经师,也是导师(mentor)。作为一个古典意义下的知识分子,卡欣
长期批评战后美国的霸权外交政策,因此,在20世纪50年代曾一度被国务院没收护照。60年代越战加剧,他不但参与反战示威,也将研究重点从印尼扩大到印度支那。这种驱策知识追求的强烈道德关怀,以及对
自己国家恨铁不成钢的爱国主义(patriotism),深深感动了正在成长期的青年安德森。他不仅从他的老师
身上“学到了政治与学术的不可分离” [10] ,也强烈体会到爱国主义的高贵、可敬与合理。日后他在《想象
的共同体》当中所透露的对民族主义相对较积极的态度,除了源于对殖民地民族主义的同情之外,也来自
康乃尔师门的道德熏陶。从1961年到1964年间,安德森在雅加达进行博士论文的田野研究。这段时间,恰好是苏加诺
(Sukarno)总统的威权民粹政权开始衰落前的全盛时期,安德森因此见证到了一个高度政治化、混乱而充
满活力,而且相当自由的印尼的社会与政治。苏加诺那种极具魅力的民粹作风与充满煽动力的反西方民族
主义,使他印象特别深刻。1963年,当苏加诺总统对英国建立马来西亚联邦大发雷霆之际,一群暴民烧毁
了吉隆坡的英国大使馆。当时已经有点“本土化”的安德森刚好住在事发现场附近,他“穿着T恤和纱笼裙,靠在篱笆上”,以一种“爱尔兰人的幸灾乐祸”(Irish Schadenfreude),冷眼旁观这栋烈焰中的建筑。当一位
他认识的暴民领袖特地过来要他不必惊慌时,安德森惊觉原来他根本就不以为自己身在险境。 [11] 也许,在安德森的眼中,印尼人以怒火焚烧帝国领事馆的景象在不知不觉中已经和他在剑桥经历过的那幕小小
的“反帝”行动重叠在一起了吧。
然而安德森绝不只是一个观众而已——他是一个如雷蒙·阿隆(Raymond Aron)一般具有强烈现实关怀
的“入戏的观众”(spectateur engage)。 [12] 1964年,安德森返回美国,当时林登·约翰逊刚连任总统,而美
国国内已逐步走入反对越战的动荡之中。1965年,美国开始大规模轰炸越南,安德森跟随恩师卡欣投入到
反战运动之中。当年9月,印尼军人翁东(Untung)将军发动政变失败,苏哈托(Suharto)将军趁势而起,捏造说翁东为印尼共产党所指使,并大肆屠杀左翼人士。此后苏哈托逐渐架空苏加诺,掌握印尼实权。
1966年1月,安德森与其他两位印尼研究同僚合作完成了一篇分析此次政变的论文。这篇后来被称为“康乃
尔文件”(Cornell Paper)的论文最初只在印尼研究的小圈子内流通,但当年春天却意外流入媒体,引起轩
然大波。由于该文指出翁东将军的流产政变根本与共产党无关,这个论点使苏哈托屠杀左派的行动完全失
去正当性,也同时直接挑战了因此政变而崛起的苏哈托政权的合法性,因此成为安德森在日后(从1972年
到1999年)长达27年被印尼当局禁止入境的主要原因。
1967年,安德森完成其博士论文《革命时期的爪哇》(Java in a Time of Revolution )。 [13] 从1967年
到1972年被驱逐出境为止,他还曾三度回到印尼。在这段时间,由祖国爱尔兰独立斗争的斑斑血史所产生
的同情心,使安德森开始留意越南,并且将越南和印尼这两个同样历经血腥的民族解放斗争才获独立的东
南亚国家联系起来。他极端厌恶华府谈论亚非地区的“低度开发国家”时那种傲慢的口气,也十分同情苏加
诺在面临国家经济危机时,因不满美国的高傲态度而怒喊“Go to hell with your aid!”(去你的援助!)拒绝
美援的处境。安德森日后自述,也许是出于一种“逆转的东方主义”(inverted Orientalism),他和当时大多
数东南亚研究专家都相当同情该地区的民族主义。从一开始,他就认定胡志明与美国的对抗,其根源不是
社会主义,而是民族主义,而苏加诺虽然远不及胡志明,但他被一个由美国撑腰的残酷军事政权推翻,却
使他轻易地“获得了犹如(匈牙利的)柯许特(Kossuth)般的(民族英雄的)悲怆”。 [14]
1972年后,由于不能再进入印尼,安德森逐渐将目光转向其他东南亚国家。1973年,泰国知识分子开
展了一场反军事政权的运动,安德森的数位泰国友人也卷入这场运动之中。于是他在1974年来到泰国,开
始学习泰国的语言,研究当地的文化与政治,并且见证这段激动人心的“曼谷之春”。1979年,美国国会邀
请他为印尼占领下的东帝汶情势作证,由于已被印尼政府“流放”,安德森得以无所顾忌地畅所欲言。以此
次国会作证为契机,他又开始和流亡的东帝汶独立运动人士[他称之为东帝汶的“爱国者们”(patriots)]
交往,并因此涉入全球性的支援东帝汶的运动网络之中。延续当年写“康乃尔文件”那种以知识介入现实的
师门精神,安德森在涉及泰国与东帝汶事务之时,也针对性地写出了一些极具现实性的深刻分析的文字。
[15]
1986年,菲律宾的科拉松·阿基诺那激动的“人民革命”浪潮再次将安德森这个“入戏的观众”卷到这个群
岛之国。继泰国研究之后,他又开始学习塔加洛语和西班牙语,投入菲律宾研究的领域之中。然而此时他
已经不再只是一个热情的区域研究专家——如今他是已成当代民族主义研究经典的《想象的共同体》
(1983)这本书的作者了。“流放”的果实
直接促成他写作《想象的共同体》的原因是1978—1979年间爆发的中国、越南和柬埔寨之间的三角冲
突。这个历史事件令他提出了这个质问:为何民族主义的力量会强大到让三个“国际主义”的社会主义国家
不惜兵戎相见?然而为他完成写作的思想准备的是,1972年被苏哈托“流放”之后他长时间在知识上的尝
试、转变与酝酿。
根据安德森的自述,苏哈托政权对他的“流放”虽然使他无法一如既往地深入印尼社会进行田野研究,却也给他带来几个意想不到的好处。首先,印尼研究的暂时中止使他有机会将目光转移到另一个东南亚国
家——泰国,而泰国这个未经殖民的君主立宪国几乎在每一方面都和经过长期殖民才独立的共和制国家印
尼形成强烈的对比。这两个“个案”(cases)的出现,使原本只埋首于印尼的安德森被迫开始作比较性的思
考,而这样的比较性思考,逐渐使他觉得有必要发展一个架构来理解个案之间的异同。其次,由于已经无
法从事田野的印尼研究,安德森被迫将注意力转移到文字资料,尤其是印尼文学之上。通过研读印尼文
学,特别是伟大的印尼小说家普拉莫底亚·阿南达·托尔(Pramoedya Ananta Toer)的作品,他开始注意到文
学如何可能和“政治的想象”(political imagination)发生关联,以及这个关联中蕴涵的丰富的理论可能。
[16] 就某种意义而言,苏哈托在1972年粗暴地将安德森驱逐出境,反而将他从单一个案的、深陷于具体细
节的“微观式”研究中解放出来,使他得以发展出一个比较的、理论性的以及较宏观的视野。
伟大的知识成就当然绝不会只得之于独裁者的愚昧而已。在1972年以后这段从田野被“放逐”回学院的
时期中,另一个事件更深刻地在安德森的思想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痕,使“比较史”(comparative
history)坚定不移地纳入他的视野当中,这就是来自他的弟弟佩里·安德森及其周边的新左评论集团知识分
子对他的影响。佩里在1974年出版了他的历史社会学杰作两部曲:《从古代通往封建主义之路》(Passages
from Antiquity to Feudalism )和《绝对主义国家的系谱》(Lineages of the Absolutist States )。这两部作品就
时间而言上下涵盖近两千年,就空间而言同时处理欧洲与欧洲以外地区不同社会的变迁,因此本尼迪克特·
安德森称之为“严谨、细致的比较历史研究的模范”确实是当之无愧的。佩里这两部书展现的比较史视野与
社会学理论深度对本尼迪克特有巨大的冲击。佩里这种理论的、比较的和全球性的视野当然也主导了他所
主编的《新左评论》的风格。他所聚集的一批英国的杰出左翼知识分子,如汤姆·奈伦(Tom Nairn)、安东
尼·巴纳特(Anthony Barnett)、朱迪思·赫林(Judith Herrin)等,所写的一篇篇探讨不同国家地区的论文在
评论上并列,创造出一种鲜明的、广阔的国际性视野。与这批博学之士长久相处之余,连严格来说并不那
么左的本尼迪克特也受到鼓舞,希望经由一个“大体上为马克思主义的视角,使我的印尼能够加入世界”。
[17]
融比较史、历史社会学、文本分析与人类学于一炉,安德森最终果然经由《想象的共同体》,把“他的
印尼”送进了“世界”。《想象的共同体》的论证
到底民族(nation)和民族主义(nationalism)是什么?它们的本质是什么?它们在历史上是怎样出现
的,又经历了怎样的变迁?为何它们能够在今天掌握如此深刻的情感上的正当性?在安德森眼中,“民族与
民族主义”的问题构成了支配20世纪的两个重要思潮——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主义——理论的共同缺陷。想要
有效解答这难以捉摸的“民族之谜”,必须扬弃旧教条,以哥白尼精神寻找新的理论典范。安德森写作《想
象的共同体》的目的,就是要提出一个解释上述这些关于民族与民族主义问题的新理论典范。
安德森的研究起点是将民族、民族属性与民族主义视为一种“特殊的文化的人造物”。他在一开头就以
简洁的文字勾勒出本书的论点:
这些人造物之所以在18世纪末被创造出来,其实是从种种各自独立的历史力量复杂的“交
汇”过程中自发地萃取提炼出来的一个结果;然而,一旦被创造出来,它们就会变得“模式化”,在
深浅不一的自觉状态下,它们可以被移植到许多形形色色的社会领域,可以吸纳同样多形形色色
的各种政治和意识形态组合,也可以被这些力量吸收。
在这凝练的文字背后,隐藏着一个非常复杂而细致的论证,以及一幅纵横古今、繁复巨大的历史图
像。
在正式进入论证之前,安德森先为“民族”这个斯芬克斯(sphinx)式的概念提出了一个充满创意的定
义:“它是一种想象的政治共同体——并且,它是被想象为本质上是有限的,同时也享有主权的共同
体。”这个主观主义的定义聪明地回避了寻找民族的“客观特征”的障碍,直指集体认同的“认
知”(cognitive)面向——“想象”不是“捏造”,而是形成任何群体认同所不可或缺的认知过程(cognitive
process),因此“想象的共同体”这个名称指涉的不是什么“虚假意识”的产物,而是一种社会心理学上的“社
会事实”(le fait social)。这个主观认知主义的定义界定了安德森以后整个论证的基调,也就是要探究“民
族”这种特殊的政治想象(认知)成为可能的条件与历史过程。
安德森认为“民族”本质上是一种现代的(modern)想象形式——它源于人类意识在步入现代性
(modernity)过程当中的一次深刻变化。使这种想象成为可能的是两个重要的历史条件。首先是认识论上
的先决条件(epistemological precondition),亦即中世纪以来“人们理解世界的方式”所发生的“根本的变
化”。这种人类意识的变化表现在世界性宗教共同体、王朝以及神谕式的时间观念的没落。只有这三者构成
的“神圣的、层级的、与时间终始的同时性”旧世界观在人类心灵中丧失了霸权地位,人们才有可能开始想
象“民族”这种“世俗的、水平的、横向的”共同体。安德森借用沃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的“同质
的、空洞的时间”(homogenous,empty time)概念来描述新的时间观,并指出18世纪初兴起的两种想象形
式——小说与报纸——“为‘重现’(re-presenting)民族这种想象的共同体提供了技术的手段”,因为它们的
叙述结构呈现出“一个社会学的有机体遵循时历规定之节奏,穿越同质而空洞的时间的想法”,而这恰好是
民族这个“被设想成在历史之中稳定地向下(或向上)运动的坚实的共同体”的准确类比。换言之,对安德
森而言,“民族”这个“想象的共同体”最初而且最主要是通过文字(阅读)来想象的。但与过去在认识论上的
决裂本身不足以说明在诸多可能类型的“水平—世俗”共同体中,为何“民族”会脱颖而出。要“想象民族”,还
需要另一个社会结构上的先决条件,也就是“资本主义、印刷科技与人类语言宿命的多样性这三者的重
合”。这三个因素之间“半偶然的,但却富有爆炸性的相互作用”促成了拉丁文的没落与方言性的“印刷语
言”的兴起,而以个别的印刷方言为基础形成的特殊主义的方言—世俗语言共同体,就是后来“民族”的原
型。
认识论与社会结构上的条件,酝酿了民族共同体的原型,也为现代民族搭好了舞台。以这两个共同的
基本先决条件为论证出发点,安德森接着一步一步地建构了一个关于民族主义如何从美洲最先发生,再一
波一波向欧洲、亚非等地逐步扩散的历史过程的扩散式论证(diffusionist argument)——一种前后关联,但
每一波都必须另作独立解释的复杂论证。
西方主流学界向来以西欧为民族主义的发源地,安德森却讥之为“地方主义”之见,主张18世纪末、19
世纪初在南北美洲的殖民地独立运动才是“第一波”的民族主义。安德森认为,美洲的殖民母国(英国、西
班牙和葡萄牙)对美洲殖民地移民的制度性歧视,使当地欧裔移民(creoles)的社会与政治流动被限定在殖民地的范围之内。他引用人类学家维克多·特纳(Victor Turner)的理论,指出这种歧视与殖民地边界的
重合,为殖民地的欧裔移民创造了一种“受到束缚的朝圣之旅”(cramped pilgrimage)的共同经验——被限
定在个别殖民地的共同领域内体验这种被母国歧视的“旅伴”们于是开始将殖民地想象成他们的祖国,将殖
民地住民想象成他们的“民族”。
“第一波”所创造的“美洲模式”,是一种不以语言为要素的民族主义;然而受到“美洲模式”感染与启发而
在1820年以后出现于欧洲的“第二波”民族主义,却是一种群众性的语言民族主义。安德森对此提出了一
个“多重因素汇聚”(conjunctural)的解释。一方面,美洲(和法国)革命将民族独立与共和革命的模型扩
散到全欧各地。另一方面,16世纪欧洲向全球扩张与“地理大发现”促成了文化多元论在欧洲兴起,而这又
促成了拉丁文之类的古老神圣语言的继续没落。在这场历史运动中,以方言为基础的民族印刷语言和民族
语言的出版业随着(民族)语言学革命趁势而起,而“阅读阶级”则适时出现,成为民族语言出版品的消费
者。由此,民族独立、共和革命与民族语言理念的结合在19世纪前半叶的欧洲孕育了一波民粹主义性格强
烈的语言民族主义。安德森特别提出了“盗版”(piration)——自觉的模仿——的概念来衔接先后出现的民
族主义:作为“第二波”,19世纪欧洲的群众性民族主义因为已有先前美洲与法国的独立民族国家的模型可
供“盗版”,因此在思想和行动上都比“第一波”要更有自觉意识。
“第二波”民族主义在欧洲掀起的滔天巨浪,撞击统治阶级古堡高耸的石墙后所反弹涌现的,就是“第三
波”的民族主义——也就是19世纪中叶以降在欧洲内部出现的所谓“官方民族主义”(official nationalism)。
安德森指出,“官方民族主义”其实是欧洲各王室对第二波群众性民族主义的反动——无力抵挡高涨的民族
主义浪潮的旧统治阶级为了避免被群众力量颠覆,于是干脆收编民族主义原则,并使之与旧的“王朝”原则
结合的一种马基雅维利式的先期(anticipatory)策略。原本只有横向联姻,缺乏明确民族属性的欧洲各王室
竞相“归化”民族,并由此掌握对“民族想象”的诠释权,然后通过由上而下的同化工程,控制群众效忠,巩固
王朝权位。“官方民族主义”的原型是沙皇亚历山大三世时代所推行的“俄罗斯化政策”(Russification),而
反动的马札尔乡绅在1848年革命后推行的马札尔化政策也是一例。另一方面,这些同时也是帝国的王朝又
将这个统治策略应用到海外异民族的殖民地,使被殖民者效忠。最典型的例子是大英帝国殖民官僚马考莱
(Macaulay)在印度推行的英国化政策。这个政策被带入非欧洲地区后,又被幸免于直接征服的少数区域
的统治阶级模仿,如日本明治维新的对内的“官方民族主义”与对殖民地的日本化政策,以及泰国的拉玛六
世的排华民族主义等。
如果“第三波”的“官方民族主义”是对第二波的群众民族主义的反动与模仿,那么“最后一波”,也就是第
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亚非殖民地民族主义,则是对“官方民族主义”的另一面——帝国主义——的反应,以
及对先前百年间先后出现的三波民族主义经验的模仿与“盗版”。安德森从他最熟悉的印尼历史抽绎出一
个“殖民地民族主义”(colonial nationalism)发生的一般性论证。首先,帝国主义的殖民政府利用殖民地
的“俄罗斯化”政策培养了一批通晓双语的殖民地精英。通过共同殖民教育,这些来自不同族群背景的人拥
有了共通的语言,并且有机会接触到欧洲的历史,包括百年来的民族主义的思想、语汇和行动模式。这些
双语精英就是潜在的最初的殖民地民族主义者。另一方面,歧视性的殖民地行政体系与教育体系同时将殖
民地民众的社会政治流动限定在殖民地的范围之内。这个和早期美洲经验类似的“受到束缚的朝圣之旅”,为被殖民者创造了想象民族的领土基础——和18世纪美洲的欧裔移民一样,在20世纪的亚洲和非洲被殖民
者的眼中,殖民地的边界也终于成为“民族”的边界。安德森同时也分析了因条件不足而未能产生“民族想
象”的法属西非和印度支那这两个殖民地,作为反面的比较个案。然而他也提醒我们“最后一波”民族主义的
特征相当复杂,因为它们出现于世界史之中……人们能够以较此前要更复杂得多的方式来“模塑”民族的时
期——它们不仅同时继承了多元的思想与行动可能,也同时继承了前人的进步与反动。
如此,安德森完成了他关于民族主义起源和散布的复杂论证:民族主义以一种和资本主义发展过程类
似的“不平均与合并的发展”(uneven and combined development)方式 [18] ,从美洲到欧洲再到亚非,一波
接着一波先后涌现;它们既属同一场历史巨浪,又相互激荡,各擅胜场。然而为何“民族”竟会在人们心中
激发如此强烈的依恋之情,促使他们前仆后继为之献身呢?安德森认为这是因为“民族”的想象能在人们心
中召唤出一种强烈的历史宿命感。从一开始,“民族”的想象就和种种个人无可选择的事物,如出生地、肤
色等密不可分。更有甚者,想象“民族”最重要的媒介是语言,而语言往往因其起源不易考证,更容易使这
种想象产生一种古老而“自然”的力量。无可选择、生来如此的“宿命”,使人们在“民族”的形象之中感受到一
种真正无私的大我与群体生命的存在。“民族”在人们心中所诱发的感情,主要是一种无私而尊贵的自我牺
牲。因此,安德森极力区分爱国主义与种族主义——对他而言,种族主义的根源不是“民族”的理念,而
是“阶级”的意识形态。在1991年出版的修订版《想象的共同体》当中,安德森在第一版的基础上又收录了两章具有附录性质
的论文。他在“人口调查、地图、博物馆”一章中提出了一个布迪厄式(Bourdieuian)论证 [19] ,试图补充
修正第七章(“最后一波”)关于殖民地民族主义的解释。他指出,殖民地官方民族主义的源头并非19世纪
欧洲王朝国家,而是殖民地政府对殖民地的想象。他举出三种制度(人口调查、地图与博物馆)说明殖民
地政府如何通过制度化(institutionalization)和符码化(codification)的过程将自身对殖民地的想象转移到
殖民地人民身上,并塑造了他们的自我想象。在“记忆与遗忘”一章中,他则探究了历史学与民族主义的密
切关系,指出民族历史的“叙述”(narrative)是建构民族想象不可或缺的一环。连接现代与后现代研究的桥梁
安德森的《想象的共同体》和已故的英国社会人类学家欧内斯特·盖尔纳(Ernest Gellner)所写的《民
族与民族主义》(Nations and Nationalism) 这两本同样在1983年出版的著作如今已是民族主义研究最重要
的两本经典之作了。盖尔纳在《民族与民族主义》中提出的那个标准社会学式的结构功能论论证,无疑已
为侧重实证主义的主流社会科学开出了一条建构民族主义的一般性理论之道。 [20] 那么,我们这本《想象
的共同体》在知识上的贡献又如何呢?
虽然不能在此详细探讨《想象的共同体》,但我们还是愿意提出几点初步的看法。首先,通过复杂而
细致的比较史和历史社会学方法,安德森在相对简短的篇幅内就建构出关于民族主义的一个非常有说服力
的一般性历史论证。 [21] 历史社会学和比较方法是研究民族主义最不可或缺的途径之一,因为几乎所有民
族主义的现象都同时涉及了历史纵深(如特定认同形成过程)以及跨国因素(如帝国主义扩张)。然而这
个研究途径的“操作”非常困难——研究者必须有能力在历史的精确性(accuracy)与理论的简约性
(parsimony)之间取得平衡,并且要有非常杰出的叙事(narrative)技巧,否则一不小心就会像盖尔纳一
样,掉进削(历史之)足适(理论之)履的陷阱之中,或者会变成像另一位多产的当代民族主义理论名家
安东尼·史密斯(Anthony Smith)的纯历史途径那种见树不见林的、琐碎的“民族分类学”。 [22] 安德森则避
开了这两个陷阱。他和兄弟佩里一样擅长运用既有历史研究的成果,并将之与理论性概念结合,然后以惊
人的叙事能力,编织成一个同时观照古今东西的“历史类型”或“因果论证”的文本——谁说社会科学家不需要
文学素养和文字能力?
更重要的是,他个人百科全书式的欧洲史素养与当代东南亚研究权威的背景,以及对东西方多种语言
的掌握能力,使他得以避免包括盖尔纳、史密斯以及霍布斯鲍姆在内的大多数西方民族主义理论家所犯的
那种欧洲中心主义的毛病。安德森的个案提醒我们,“扩散式论证”这种极度困难的论证方式固然不在话
下,即使是最根本的“比较研究”都需要具备相当的知识和语言的条件。
第二,安德森超越一般将民族主义当作一种单纯的政治现象的表层观点,将它与人类深层的意识与世
界观的变化结合起来。他将民族主义放在比政治史或政治思想史更广阔的“文化史”和“社会史”的脉络当中来
理解——民族主义因此不再只是一种意识形态或政治运动,而是一种更复杂深刻的文化现象(或者借用他
自己的话来说,一种“文化的人造物”)。这种颇具人类学精神——或者有点接近法国年鉴学派(Annales)
史学所谓“心态史”(histoire des mentalites)、“历史心理学”(psychologie historique)、“理念的社会
史”(histoire sociale desidees)或“社会—文化史”(histoire socio-culturelle) [23] ——的途径将我们对民族主
义的认识从“社会基础”或“政治动员”的层面扩展到对它的“文化根源”的探求之上。安德森不但没有像一般社
会科学家那样以实证主义式的傲慢(hubris)忽视人类追求“归属感”的需求(因为“不够科学”,或者因为那
是“虚假意识”或“病态”),反而直接面对这个真实而深刻的存在性问题,并在他的架构中为之赋予适当的诠
释与意义。正因如此,他对民族主义的解释就更能掌握到人类行动的深层动机。就某种意义而言,这个途
径间接肯定了德国哲学家赫德(Johann Gottfried von Herder)所说“乡愁是最高贵的痛苦”的箴言。 [24]
第三,《想象的共同体》的论证结合了多重的研究途径,同时兼顾文化与政治、意识与结构,开创了
丰富的研究可能性,因此被北欧学者斯坦·东尼生(Stein Tonnesson)和汉斯·安德洛夫(Hams Antlov)称
为“连接现代与后现代研究途径的桥梁” [25] 。就传统比较政治学与历史社会学的角度而言,这本书最重要
的贡献可能是它关于民族主义的各种“历史类型”以及“民族主义兴起的结构与制度条件”的论证。安德森
的“历史的”(historical)解释和盖尔纳所建构的“非历史的”(a-historical)结构功能论解释恰好成为当代民
族主义理论的两个重要而对立的典范。不过,相对于盖尔纳在主流政治学与政治社会学方面的巨大影响,《想象的共同体》可能对以文化与“意识”(consciousness)为研究对象的社会、人文学科的影响更大。安德
森对宗教、象征(symbol)与意义之诠释(interpretation of meanings)的强烈兴趣,以及“以本地人观
点”(from the native point of view)的倾向清晰地显露了这本书的“人类学精神”。他从现代小说的结构与叙
事技巧以及诗歌的语言中,探讨文学作品如何“重现”(represent)人类对民族共同体的想象的“前卫”尝试,对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兴起于英美文学界的,用解构主义理论、后殖民研究(postcolonial studies)与
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对文学与民族主义关系进行批判性研究的风潮有相当的影响。 [26] 而与文学理
论密切相关的是,安德森运用后现代主义历史哲学家海登·怀特(Hayden White)的理论来解析“民族认同建
构”与“历史叙述”的关系,以及他对殖民地政府(colonial state)角色的观察也在当代后现代主义或后殖民主义史学中留下了印痕。 [27] 最后,安德森所提出的“想象的共同体”的这个主观主义认知的定义对民族主
义的社会心理学研究途径也有不少启发作用。 [28]
当然,像《想象的共同体》这样深具野心的著作势必难逃知识界的检视与争议。例如,安德森视民族
为一种“现代”的想象以及政治与文化建构的产物,这使他在当代西方学界关于民族主义性质与起源时间
的“现代(建构)派对原初派”(modernistconstructivist vs.primordialist)论战中和盖尔纳同被归入“现代
派”,而受到“原初派”的批评。 [29] 而印度裔的美籍中国史专家,芝加哥大学的杜赞奇(Prasenjit Duara)教
授也以中国史为证提出一个与此论战相关的经验批评。杜赞奇认为,早在现代西方民族主义传入中国之
前,中国人早就有类似于“民族”的想象了;对中国而言,崭新的事物不是“民族”这个概念,而是西方的民族
国家体系。 [30] 另外,后殖民研究的先驱理论家夏特吉(Chatterjee)在他那本殖民地民族主义的名著《民
族主义思想和殖民地世界——一个衍生性的议论》(Nationalist Thought and the Colonial World:A
Derivative Discourse) 中则对《想象的共同体》提出了另一种批判:尽管安德森认识到“民族”是一种意识形
态的建构,但他竟然完全忽略了民族主义如何建构“民族”意识形态的具体政治过程。 [31]思想、记忆与认同
最后,对于为何在本书中舍近年来在台湾颇为流行的、“解构”味十足的“国族”一词不用,而将nation依
传统用语译为“民族”,笔者想稍作说明。首先,尽管在经验上nation的形成与“国家”(state)关系极为密
切,但nation一词最初是作为一种理念、政治想象(political vision)或意识形态而出现的,因此本来就带有
很明显的价值意味——从18世纪后半叶开始,经由启蒙时代的思想家和法国大革命的宣传家的如椽大笔,nation一词事实上是和“人民”(peuple,Volk)和“公民”(citoyen)这类字眼一起携手走入现代西方政治语
汇之中的。 [32] 换言之,nation指涉的是一种理想化的“人民全体”或“公民全体”的概念。在此意义上,它
和“国家”是非常不同的东西:nation是(理想化的)人民群体,而“国家”是这个人民群体自我实现的目标或
工具。如果译为“国族”将丧失这个概念中的核心内涵,也就是尊崇“人民”的意识形态。安德森之所以将
nation定义为“想象的共同体”,正是因为这个定义充分掌握到nation作为一种心理的、主观的“远景”(又是一
个“本土”的流行词汇!)的意义。
第二,以服务当权者利益为目的的“国族主义”毕竟只是民族主义复杂历史经验当中的一种类型——所
谓的“官方民族主义”——或者一个可能的组成成分而已,“国族主义”一词不仅遗漏了群众性民族主义这个重
要的范畴,同时也无力描述兼具官方与民粹特征的更复杂的类型。主要基于上述两个理由,笔者决定在本
书采用这两个较能表现出“人民”意识形态这个关键要素的传统词汇。
“民族主义的两面性”的这个评价表明了安德森“介于现代与后现代之间”的政治立场。 [33] 安德森虽然
认为“民族”是一种现代的“文化的人造物”,但他并不认为这个“人造物”是“虚假意识”的产物。“想象的共同
体”不是虚构的共同体,不是政客操纵人民的幻影,而是一种与历史文化变迁相关,根植于人类深层意识的
心理的建构。他同情并尊敬一切反帝、反压迫的民众的民族主义的奋斗,但也清清楚楚地了解这些运动随
时有堕落成反动的“官方民族主义”或者侵略扩张的帝国主义的危险。他写作《想象的共同体》的目的并不
是解构民族认同。正如同他在本书正文前所引用的沃尔特·本雅明的警句“他认为他的职责在于逆其惯常之理
以爬梳历史”所提示的,安德森所关切的“职责”是如何使民族认同“历史化”(historicize)与相对化:民族和
民族主义问题的核心不是“真实与虚构”,而是认识与理解。对他而言,一切既存或曾经出现的民族认同都
是历史的产物,唯有通过客观理解每一个独特的民族认同(包括自我的认同与“他者”的认同)形成的历史
过程与机制,才可能真正摆脱傲慢偏执的民族中心主义,从而寻求共存之道,寻求不同的“想象的共同
体”之间的和平共存之道。
“共同体的追寻”——寻找认同与故乡——是“人类的境况”(human condition)本然的一部分,但就像所
有人类对理想社会的追求一样,这条道路上也遍布着荆棘和引人失足的陷阱。我们必须尽最大的努力,在
情感与理性之间、同情与戒慎之间以及行动与认识之间寻求平衡。不管在这“一切都被允许”的虚无主义年
代里,人类的理性能力受到多么激烈的质疑,理性毕竟是卑微、善变和激情的人类最后的凭借。安德森的
这本《想象的共同体》——这本体现了汉娜·阿伦特所谓海德格尔式的“热情的思考”(passionate thinking)
的著作,就是试图在犬儒与狂热之外寻找认同之路的理性的辛勤劳作。
吴叡人
1999年4月7日午夜于密歇根湖畔斗室
————————————————————
注释:
[1] 本书是根据Benedict Anderson,Imagined Communities: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Revised Edition(London,New York:Verso,1991)的英文原文翻译而成的。翻译过程中,译者也参考了该书1983年出版(初版)的日译本,(べネデクトアンダ一ソ
ン著白石隆,白石さヤ译“想像の共同体一ナショナリズムの起源と流行”,东京:リブロポ一ト ,1987)。
[2] Edward Said,The Politics of Dispossesion:The Struggle for Palestinian Self-Determination 1969—1994,London:Chatto and Windus,1994,p.334.
[3] 本文中关于安德森个人背景的叙述,主要取材于他的两篇带有自述风格的导论文章:他的《语言与权力》(Language and Power,1990)一书的导论,以及他最近一本著作《比较的幽灵》(The Spectre of Comparisons,1998) 的导论。
[4] 佩里·安德森于1938年——也就是本尼迪克特出生后两年——生于伦敦,但出生后不久就被姨妈带到中国。请参见Gregory Elliot,Perry Anderson:The Merciless Laboratory of History ,Minneapolis and London: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99。艾略特的这本书是第一本对佩里·安德森的思想与实践作全面性研究的著作。
[5] Benedict Anderson,Language and Power ,p.2.
[6] 主修西方古典研究意味着必须通晓古希腊文与拉丁文。在西方语言之中,除了希腊文与拉丁文这两种古典语言以及母语英文之外,安
德森至少还精通法文和德文。当他日后投身东南亚研究之后,他至少又先后学会了印尼文、泰文、菲律宾的塔加洛文以及西班牙文。
[7] Benedict Anderson,Language and Power ,p.1.关于佩里·安德森的政治实践,特别是他和英国新左派运动的关系,以及他的历史社
会学理论的讨论,除了前述艾略特的近著《佩里·安德森》(1999)可供参考之外,也可见于Mary Fulbrook and Theda Skocpol,“Destined
Pathways:The Historical Sociology of Perry Anderson,”in Theda Skocpol,ed.,Vision and Method in Historical Sociology ,Cambridge:
Cambridge UP,1984,pp.170—210。
[8] Benedict Anderson,Language and Power ,pp.1—3.
[9] Ibid.,p.3.The Spectre of Comparisons ,p.19.
[10] Benedict Anderson,The Spectre of Comparisons ,pp.18—19.
[11] Benedict Anderson,Language and Power ,p.4.
[12] 笔者在此借用了一本精彩的雷蒙·阿隆访谈录的书名来描述安德森的“实践的观察者”的倾向。请参见James and Marie McIntosh,Raymond Aron,The Committed Observer(Le Spectateur Engage):Interviews with Jean-Louis Missika and Dominique Wolton ,Chicago:Regnery
Gateway,1983。
[13] 这篇论文在1972年以原题出版。请参见Benedict R.Anderson,Java in a Time of Revolution:Occupation and Resistance ,1944—
1946,Ithaca and London: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4] Benedict Anderson,Language and Power ,p.7.关于柯许特的事迹,请参见本书第六章。
[15] 参见安德森的《比较的幽灵》内第二部所收诸文。
[16] Benedict Anderson,Language and Power ,pp.9—10.
[17] Ibid.,p.10.
[18] 虽然安德森和另外两个重要的英国民族主义理论家欧内斯特·盖尔纳(Ernest Gellner)和汤姆·奈伦(Tom Nairn)都在他们的民族主
义理论中使用“不平均与合并的发展”这个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来理解资本主义的历史扩张模式的概念,不过他的用法和后两者有很大的不
同:后两位理论家直接以“不平均与合并的发展”论来解释民族主义(资本主义化或工业化后进地区对来自先进地区剥削的一种反应),但安德
森主要是借用“不平均与合并的发展”来描述民族主义的历史扩张的模式。关于盖尔纳的理论,请参见Ernest Gellner,Nations and Nationalism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3;关于汤姆·奈伦的理论,请参见Tom Nairn,The Break-Up of Britain:Crisis and Neo-Nationalism ,London:
NLB,1977。
[19] 所谓布迪厄式论证指的是法国社会学家皮耶·布迪厄(Pierre Bourdieu)关于社会实践(social practice)如何产生“实体
化”(reification)效果的理论。关于这个理论在民族主义研究中的运用,请参见Rogers Brubaker,Nationalism Reframed:Nationhood and the
National Question in the New Europe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安德森并未引用布迪厄的理论,但他的论点与布迪厄的论证精神
颇为接近,故笔者借用布迪厄之名。
[20] Ernest Gellner,Nations and Nationalism ,Ithaca and London: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3.这本书和《想象的共同体》竟然是在同
一年由同一家出版社出版的!康乃尔大学出版社之中显然潜藏胸有丘壑之士。关于盖尔纳的民族主义在西方社会科学界的讨论,请参见John
A.Hall,ed.,The State of the Nation:Ernest Gellner and the Theory of Nationalism,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9。
[21] 汉斯·科恩(Hans Kohn)的民族主义研究早期经典《民族主义的理念》(The Idea of Nationalism )只写到18世纪末的欧洲就用了七百
多页!请参见Hans Kohn,The Idea of Nationalism:A Study in Its Origins and Background ,Toronto:Collier Books,1944。另一个有类似计划的
作品用了四百多页,但基本上只完成民族主义的分类,无力建构一个系统性的解释。请参见John Breuilly,Nationalism and the State,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5。霍布斯鲍姆的《1780年后的民族与民族主义》(Nations and Nationalism since 1780 )虽然也十分简洁,但该书以历史叙述为主,并未真正提出一个理论性的解释,同时该书还是一本典型的“欧洲中心”观点的作品。请参见E.J.
Hobsbawm,Nations and Nationalism since 1780:Programme,Myth,Realit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22] 安东尼·史密斯非常多产,但比较重要的作品包括《民族主义理论》(Theories of Nationalism, London:Duckworth,1971);《民
族的族群起源》(The Ethnic Origin of Nations, Oxford:Basil Blackwell,1986);以及扼要总结他对民族主义观点的小书《民族认同》
(National Identity, Reno:University of Nevada Press,1991)等。
[23] 关于年鉴学派的研究途径,请参见Roger Chartier,Intellectual History or Sociocultural History?The French Trajectories ,in D.La
Capa & S.L.Kaplan,eds.,Modern European Intellectual History:Reappraisals and New Perspectives, Ithaca and London:Cornell University
Press,pp.13—46。细心的读者可在《想象的共同体》当中看到安德森向年鉴学派致意的痕迹。
[24] 无独有偶的是,安德森所敬重的“新左评论”友人,民族主义研究的前辈,苏格兰的马克思主义者汤姆·奈伦在他最近一本新书中也同
样抨击唯物论和盖尔纳的社会学现代化论都无法解释民族主义这种极度复杂的现象——他甚至提出要回归“人性”(human nature),从人类心理
和生理出发,重新理解民族主义!请参见《民族主义的面相——重新审视贾纳斯》(Faces of Nationalism:Janus Revisited, London:Verso,1997)一书之导论(“On Studying Nationalism”)。
[25] Stein Tonnesson and Hams Antlov,“Asia in Theories of Nationalism and National Identity,”in Stein T?nnesson and Hans Antlov,eds.,Asian Forms of the Nation,Curzon, 1996,p.14.
[26] 关于这方面较早期的研究成果,请参见Homi K.Bhabha,ed.,Nation and Narration ,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1990,特
别是编者洪米·巴巴所写的“导论”和“散播民族——时间、叙事、与现代民族边缘”(Dissemi Nation:Time,Narrative,and the Margins of the
Modern Nation)。这两篇文章是后殖民文学研究关于民族主义的重要论文。
[27] 当代后殖民研究重镇,孟加拉的巴特·夏特吉(Partha Chatterjee)关于殖民地民族主义的名著《民族主义思想与殖民地世界:衍生论
述》(Nationalist Thought and the Colonial World:A Derivative Discourse, 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da Press,1986)和著名的印度裔
中国史专家,芝加哥大学的杜赞奇(Prasenjit Duara)教授的近作《护史退族:现代中国的问题叙事》(Rescuing History from the Nation:
Questioning Narratives of Modern China, Chicago and London: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5)都可以说是在和《想象的共同体》的对
话。
[28] Michael Billig,“Rhetorical Psychology,Ideological Thinking,and Imagining Nationhood,”in Hank Johnston and Bert Klandermans,eds.,Social Movements and Culture, 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95,pp.64—78.[29] 其实这场论战早在1982年就因阿姆斯特朗(J.A.Armstrong)的原初主义论著《民族主义形成之前的民族》(Nations before
Nationalism )的出版而被引发了。不过安德森似乎并未直接参与辩论。后来持续参与论战的主要角色是现代派的盖尔纳和站在折中立场,不过
较偏原初派的安东尼·史密斯。关于这两方意见的一个简明而针锋相对的交换,请参见“The Warwick Debate:The Nation:Real or Imagined”,in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2(3),1996,pp.357—370。
[30] Prasenjit Duara,Rescuring History from the Nation:Questioning Narratives of Modern China ,Chapter 2.
[31] Partha Chatterjee,Nationalist Thought and the Colonial World:A Derivative Discourse ,pp.21—22.
[32] 最重要的两位思想家是法国的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和德国的赫德(Johann Gottfried von Herder),请参见F.M.Barnard,Self-Direction and Political Legitimacy:Rousseau and Herder, Oxford:Clarendon Press,1988。而将卢梭式的公民民族理念应用到法国大革命的
最著名的例子,是谢伊斯(Emmanuel-Joseph Sieves)所写的小册子《何谓第三阶级?》(Qu'est-ce que le Tiers etat ),请参见William H.
Sewell,Jr.,A Rhetoric of Bourgeois Revolution:the Abbe Sieyes and What is the Third Estate? Durham and London:Duke University Press,1994。
[33] 爱尔兰人安德森的这个立场和另一个对后殖民研究有深刻影响的杰出理论家巴勒斯坦人爱德华·萨义德有相近之处。这是一个颇值得
台湾人玩味的政治和知识社会学上的问题。第二版序
有谁会想到那风暴越远离伊甸园就吹得越猛烈呢?
仅仅才过了12年,直接引发我写作《想象的共同体》初稿的那场1978年到1979年在中南半岛的武装冲
突,似乎已经属于另一个时代了。那时,社会主义国家之间更进一步的全面战争的前景始终在我的脑中萦
绕不去。如今这些国家有一半已经加入了天使跟前的那堆残骸了,而剩余的恐怕很快就要追随其后了。幸
存者面临的战争是内战。非常有可能在新世纪开始之时,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会只剩下……共和国
了。
是否这一切多少都应该先预见到呢?在1983年我写道,苏联“不但是19世纪前民族期王朝国家的继承
人,也是21世纪国际主义秩序的先驱”。不过,在追溯摧毁了维也纳、伦敦、君士坦丁堡、巴黎和马德里统
治下的多语言、多族群的庞大帝国的民族主义之爆炸过程后,我却没有能够见到导火线至少已经铺到莫斯
科了。而令人忧郁的安慰是,我们观察到历史似乎比作者更能证明想象的共同体的“逻辑”。
不只是世界已经在过去12年间改变了容貌,民族主义的研究也已经令人震惊地改头换面了——在方
法、规模、深度上,还有纯粹在数量上皆然。仅以英语著作而言,J.A.阿姆斯特朗(J.A.Armstrong)
的《民族主义形成以前的民族》(Nations Before Nationalism ,1982),约翰·布罗伊尔(John Breuilly)的
《民族主义与国家》(Nationalism and the State ,1982),欧内斯特·盖尔纳(Ernest Gellner)的《民族与民
族主义》(Nations and Nationalism ,1983),米洛斯拉夫·罗奇(Miroslav Hroch)的《欧洲民族复兴的社
会先决条件》(Social Preconditions of National Revival in Europe ,1985),安东尼·史密斯(Anthony
Smith)的《民族的族群起源》(The Ethnic Origins of Nations ,1986),P.夏特吉(P.Chatterjee)的
《民族主义思想与殖民地世界》(Nationalist Thought and the Colonial World ,1986),还有埃里克·霍布斯
鲍姆(Eric Hobsbawm)的《1780年后的民族与民族主义》(Nations and Nationalism since 1780,1990)
——只提几本最重要的作品——以其涵盖的历史范围与理论的力量,已经在大体上淘汰了讨论这个主题的
传统文献了。大量研究将研究对象连接到民族主义和民族的史学的、文学的、人类学的、社会学的、女性
主义的和其他的研究领域,其中部分是从这些著作当中发展出来的。 [1]
改写《想象的共同体》,使之符合现实世界与民族主义研究的巨大变化,是一件超过我目前能力范围
的工作。因此,让它大体上保持为一件“未经复原的”特定时期的作品,保留特有的风格、外貌和语气,似
乎是比较好的决定。有两件事让我感到安慰。一方面,社会主义世界的发展,其完整的、最终的结果仍不
甚明朗。另一方面,对我而言,《想象的共同体》所使用的特殊方法和它最关切的问题,似乎还处于较新
的民族主义学术研究的边缘地带——在这个意义上,至少它还未完全被取代。
在第二版中,我只是试着更正我在准备初稿时就应该避免的一些事实、概念和诠释上的错误。这些更
正——也许可以说是依循着1983年版的精神——包括了对第一版的若干更动,以及基本上带有(与本书)
不连续的附录性质的两章新的文字。
在本书当中,我发现了两处翻译上的严重错误:一个是没有实现的承诺,另一处是容易产生误导的加
强语气。因为在1983年的时候,我还无法阅读西班牙文,尽管还有更早的几种译本可用,我却未经深思就
仰赖了利昂·格列罗(Leon Ma.Guerrero)对何赛·黎刹(Jose Rizal)的《社会之癌》(Noli Me Tangere )
的英文译本。直到1990年我才发现格列罗的译本是多么不可思议的错误百出。关于奥托·鲍尔(Otto Bauer)
的《民族问题与社会民主》(Nationalitatenfrage und die Sozialdemocratie )中的一段长而重要的引文,我则
懒惰地仰赖奥斯卡·贾希(Oscar Jaszi)的翻译。直到最近我查阅了原文之后,才发现贾希的政治倾向多么
严重地扭曲了他的译文。至少在两段文字中,我曾经没有信用地承诺要解释为何和其他拉丁美洲国家相比
较,巴西民族主义会发展如此之迟,而且如此特殊。这个版本会尝试去实现这个已被毁弃的誓约。
我最初的计划就是要强调民族主义在新世界的起源。我一直觉得有一种不自觉的地方主义长期地扭曲
了对这个主题的理论化工作。因为习惯了自负地以为现代世界的每个重要东西都起源于欧洲,欧洲的学者
不管是“赞成”还是“反对”民族主义,都很容易把“第二代的”语言民族主义(匈牙利、捷克、波兰等)当作他
们建构模式的起点。我很惊讶地发现,在很多注意到《想象的共同体》一书的作品中,这种欧洲中心的地
方主义仍然继续存在,而且那章讨论美洲起源地的关键文字大体上都被忽略了。不幸的是,除了把第四章
重新命名为“欧裔海外移民先驱者”(Creole Pioneers)之外,我实在找不到更好的“速成的”解决之道了。那两篇“附录”试图要更正第一版中严重的理论缺陷。 [2] 有几位友善的批评家主张说第七章(“最后一
波”)过度简化了早期“第三世界”民族主义建构其模式的过程。此外,那章并未认真处理当地的殖民政府
——不是母国——在设计(styling)这些民族主义的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同时,我逐渐不安地认识到,我
相信对思考民族主义作出了重要的新贡献的那个论证——对时间之理解的改变——明显地缺少了必要的对
等论证:对空间之理解的改变。年轻的泰国历史学家东猜·维尼察古(Tongchai Winichakul)所写的一篇杰
出的博士论文刺激了我去思考地图制作(mapping)对民族主义想象所作的贡献。
“人口调查、地图、博物馆”一章因此分析了19世纪的殖民地政府(及其心态所鼓励的那类政策)如何
在相当不自觉中辩证地创造出最后终于兴起而与之战斗的那些民族主义的基本规则(grammar)的方式。事
实上,或许我们甚至可以说,殖民地政府远在当地的对手出现之前,就在想象这些对手了。人口调查对人
的抽象量化系列化,地图最终将政治空间识别标志化,以及博物馆的“普遍的”、世俗的系谱建构,这三者
以彼此相关的方式,促成了殖民地政府这种想象的形成。
促使我写第二篇“附录”的缘起是,我羞愧地承认在1983年的时候,我完全不了解勒南(Renan)真正所
说过的话,就加以贸然引述:我轻易地把某种事实上全然怪异之事看成了反讽。这个羞辱也迫使我理解
到,我并没有对新出现的什么是民族以及如何将自己想象为古老的民族这个问题,作出任何睿智的解释。
所有那些在大多数学术作品中看起来像是马基雅维利式骗术、资产阶级幻想或者是被发掘出来的历史真相
者,如今却都突然使我觉得是某种更深刻更有趣的东西。假设,在某个历史的关头,“古老”是“崭新”的必然
结果?如果民族主义如我所设想的,是一种激烈变化了的意识形式的表现,那么难道对这个断裂的知觉,以及对较古老的意识的遗忘,民族主义不会创造出它自己的叙述吗?从这个角度来看,大多数19世纪20年
代以后的民族主义思想的那种隔代遗传式的幻想特性看起来就只是一个偶发现象而已;真正重要的是19世
纪20年代以后的民族主义“记忆”和现代传记与自传的内在前提和(写作)惯例之间的结构性的结合。
除了这两篇“附录”可能被证明会有的任何理论上的优点和缺点之外,它们各自都有其司空见惯的限
制。“人口调查、地图、博物馆”的资料全部都引自东南亚。这个区域以某些方式提供了绝佳的建构比较理
论的机会,因为它包含了先前曾被几乎所有帝国主义强权(英国、法国、荷兰、葡萄牙、西班牙和美国)
殖民过的地区,以及从未被殖民过的泰国。然而,即使我的分析对这个区域而言是合理的,但这个分析是
否能被令人信服地应用到全世界各地,尚待观察。在第二篇附录中,我所用到的简要的经验资料几乎完全
是关于我只有很浅认识的西欧和新世界。但我还是必须将焦点放在那里,因为最早传遍了民族主义的失忆
症的土地,就是这些区域。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
1991年2月
————————————————————
注释:
[1] 霍布斯鲍姆就有勇气把这种学术上的爆炸总结为民族主义的时代已经快到尾声了:密涅瓦的猫头鹰(Minerva's owl)总是在黄昏飞
翔。[密涅瓦为罗马神话中司工艺、智慧与战争的女神,“密涅瓦的猫头鹰只在黄昏降临之时才开始它的飞翔”语出黑格尔(G.W.F.
Hegel)的《法哲学原理》(Grundlinien der Philosophie des Recht) (1821)的序言,意指思想只有在现实的历史过程完成之后才会出现。]
[2] 第一篇附录源自为联合国大学世界发展经济学研究所(World Institute for Development Economics Research of the United Nations
University)1989年1月在卡拉奇举办的研讨会所准备的一篇论文。第二篇附录的纲要曾以《叙述民族》(Narrating the Nation)为题发表在1986
年6月13日的《泰晤士报文艺副刊》(The 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 )上。第一章 导论
也许这个现象尚未广受注意,然而,我们正面临马克思主义思想与运动史上一次根本的转型。最近在
越南、柬埔寨和中国之间的战争,就是这个转型最明显的表现。这几场战争具有世界史的重要性,不仅因
为它们是在几个无可置疑的独立革命政权之间最早发生的战争,同时也因为交战各国中没有任何一方尝试
使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观点来为这些战争进行辩护。虽然我们还是可能从“社会帝国主义”或“捍卫社会主
义”之类的角度——这要视个人品味而定——来诠释1969年的中苏边界冲突,以及苏联对德国(1953年)、匈牙利(1956年)、捷克斯洛伐克(1968年)和阿富汗(1980年)等国的军事干预,但是,我猜想,没有
人会真的相信这些术语和中南半岛上发生的事情可以扯上什么关系。
如果说,越南在1978年12月以及1979年1月对柬埔寨的入侵与占领,代表了一个社会主义政权与另一个
社会主义政权之间第一次的大规模传统战争 [1] ,那么中国在1979年2月与越南的冲突则迅速确认了这个先
例。只有那些最深信不疑的人才敢打赌说,在20世纪即将结束的几年里面,如果有任何大规模的国际冲突
爆发,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更不必说较小的社会主义国家了——会站在同一阵线。谁敢保证南斯拉
夫哪一天不会和阿尔巴尼亚打起来?那些企图使红军从东欧驻地撤出的各种团体应该先想一想,1945年以
来,无所不在的红军在多大程度上防止了这个地区的社会主义政权之间爆发武装冲突。
上述的思考,有助于表明一个事实: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生的每一次成功的革命,如中华人民共和
国、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等,都是用民族来自我界定的;通过这样的做法,这些革命扎实地植根于一个从
革命前的过去继承而来的领土与社会空间之中。相反,苏联和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却有一个少见
的共同特性,就是拒绝用民族来为国家命名。这个事实显示,这两国不但是19世纪前民族期王朝国家的继
承人,也是21世纪国际主义秩序的先驱。 [2]
埃里克·霍布斯鲍姆说过:“马克思主义运动和尊奉马克思主义的国家,不论在形式还是实质上都有变成
民族运动和民族政权——也就是转化成民族主义——的倾向。没有任何事实显示这个趋势不会持续下去。”
[3] 在这点上,他是完全正确的。然而,这个倾向并非只发生在社会主义世界之内。联合国几乎年年都接受
新的会员。许多过去被认为已经完全稳固的“老民族”如今却面临境内一些“次”民族主义(sub-nationalisms)
的挑战。这些民族主义运动自然梦想着有这么快乐的一天,他们将要褪去这个“次级”的外衣。事实摆在眼
前:长久以来被预言将要到来的“民族主义时代的终结”,根本还遥遥无期。事实上,民族属性(nation-
ness)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政治生活中最具普遍合法性的价值。
但是,如果事实是清清楚楚的,那么该如何解释这些事实则是一段长期众说纷纭的公案。民族
(nation),民族归属(nationality) (1) ,民族主义(nationalism)——这几个名词涵义之难以界定,早已
众所周知,遑论对之加以分析了。民族主义已经对现代世界产生巨大的影响;然而,与此事实形成明显对
比的是,具有说服力的民族主义理论却屈指可数。休·赛顿-华生(Hugh Seton-Watson),这位关于民族主
义的英文论著中最好、涵盖面最广的一部作品的作者,也是自由主义史学与社会科学的继承人,悲伤地说
道:“我被迫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也就是说,我们根本无法为民族下一个‘科学的’定义;然而,从以前到现
在,这个现象却一直持续存在着。” [4] 汤姆·奈伦(Tom Nairn),《不列颠的崩解》(The Break-up of
Britain) 这部开创性作品的作者,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史学与社会科学传统的传人,作了如此坦白的评
论:“民族主义的理论代表了马克思主义历史性的大失败。” [5] 然而甚至这样的表白也还是有些误导,因为
我们会误以为这段话的含义是,马克思主义确实曾经长期而自觉地追寻一个清晰的民族主义理论,只不过
令人遗憾的是,这个努力失败了。比较准确的说法应该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而言,民族主义已经证明是
一个令人不快的异常现象;并且,正因如此,马克思主义理论常常略过民族主义不提,不愿正视。不然,我们该如何解释马克思在他那篇令人难忘的对1848年革命的阐述当中,竟然没有说明其中那个关键性的形
容词的意义:“当然,每个国家的无产阶级都必须先处理和它自己的(its own)资产阶级之间的关系。” [6]
我们又怎样解释“民族资产阶级”(national bourgeoisie)这个概念被用了一个世纪以上的时间,却没有人认
真地从理论上使“民族”这个形容词的相关性合理化?如果以生产关系来界定,资产阶级明明是一个世界性
的阶级,那么,为什么这个特定部分的资产阶级在理论上是重要的?
本书的目的在于尝试对民族主义这个“异常现象”提出一个比较令人满意的诠释。我觉得,在这个问题
的处理上,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主义的理论都因为陷入一种“晚期托勒密式”的“挽救这个现象”的努力,而变得
苍白无力;我们亟需将理解这个问题的角度,调整到一种富有“哥白尼精神”的方向上。 (2) 我的研究起点
是,民族归属(nationality),或者,有人会倾向于使用能够表现其多重意义的另一字眼,民族的属性(nationness)以及民族主义,是一种特殊类型的文化的人造物(cultural artefacts)。想要适当地理解这些
现象,我们必须审慎思考在历史上它们是怎样出现的,它们的意义怎样在漫长的时间中产生变化,以及为
何今天它们能够掌握如此深刻的情感上的正当性。我将会尝试论证,这些人造物之所以在18世纪末被创造
出来, [7] 其实是从种种各自独立的历史力量复杂的“交汇”过程中自发地萃取提炼出来的一个结果;然而,一旦被创造出来,它们就变得“模式化”(modular),在深浅不一的自觉状态下,它们可以被移植到许多形
形色色的社会领域,可以吸纳同样多形形色色的各种政治和意识形态组合,也可以被这些力量吸收。我也
会试图说明,为什么这些特殊的文化人造物会引发人们如此深沉的依恋之情。概念与定义
在处理上面提出的问题之前,我们似乎应该先简短地考虑一下“民族”这个概念,并且给它下一个可行
的定义。下列三个诡论经常让民族主义的理论家感到恼怒而困惑:(1)民族在历史学家眼中的客观的现代
性相对于民族在民族主义者眼中的主观的古老性;(2)民族归属作为社会文化概念的形式的普遍性——在
现代世界每个人,就像他或她拥有一个性别一样,都能够、应该,并且将会拥有一个民族成员的身份——
相对于民族归属在具体特征上的特殊性,例如,“希腊”民族成员的身份,依照定义本来就是独特的(sui
generis);(3)各种民族主义在“政治上”的力量相对于它们在哲学上的贫困与不统一。换言之,和大多数
其他的主义不同的是,民族主义从未产生它自己的伟大思想家:没有它的霍布斯、托克维尔、马克思或韦
伯。这种“空洞性”很容易让具有世界主义精神和能够使用多种语言的知识分子对民族主义产生某种轻视的
态度。就好像格特鲁德·斯泰因(Gertrude Stein)面对奥克兰(Oakland)的时候,人们会很快下结论说那里
是一个“空无一物的地方”(there is ‘no there there’) (3) 。即使像奈伦这么同情民族主义的学者也还是会如
此写道:“‘民族主义’是现代历史发展中的病态。如同‘神经衰弱’之于个人一样地不可避免;它既带有与神经
衰弱极类似的本质上的暧昧性,也同样有着退化成痴呆症的内在可能性——这个退化可能性乃是根源于世
界上大多数地区所共同面临的无助的两难困境之中(这种痴呆症等于是社会的幼稚病),并且,在多数情
况下是无药可医的。” [8]
有一部分的困难源于,人们虽然不会把“年龄”这个概念当作一个专有名词,他们却常常不自觉地把民
族主义当作专有名词,将它视为一个具有特定专属内容的存在实体,然后把“它”区别为一种意识形态。
(请注意,假如每个人都有年龄,那么“年龄”只不过是一种分析性的表达语汇而已。)我想,如果我们把
民族主义当作像“血缘关系”(kinship)或“宗教”(religion)这类的概念来处理,而不要把它理解为像“自由
主义”或“法西斯主义”之类的意识形态,事情应该会变得比较容易一点。
遵循着人类学的精神,我主张对民族作如下的界定:它是一种想象的政治共同体——并且,它是被想
象为本质上有限的(limited),同时也享有主权的共同体。
它是想象的,因为即使是最小的民族的成员,也不可能认识他们大多数的同胞,和他们相遇,或者甚
至听说过他们,然而,他们相互联结的意象却活在每一位成员的心中。 [9] 当勒南写道“然而,民族的本质
是每个人都会拥有许多共同的事物,而且同时每个人也都遗忘了许多事情” [10] 时,他其实就以一种文雅而
出人意表的方式,指涉了这个想象。当盖尔纳(Gellner)判定“民族主义不是民族自我意识的觉醒:民族主
义发明了原本并不存在的民族” [11] 时,他是带着几分粗暴提出了一个类似的论点。但是,盖尔纳这个表述
的缺点是,他太热切地想指出民族主义其实是伪装在假面具之下,以致他把发明(invention)等同于“捏
造”(fabrication)和“虚假”(falsity),而不是“想象”(imaginging)与“创造”(creation)。在此情形下,他
暗示了有“真实”的共同体存在,而相较于民族,这些真实的共同体享有更优越的地位。事实上,所有比成
员之间有着面对面接触的原始村落更大(或许连这种村落也包括在内)的一切共同体都是想象的。区别不
同的共同体的基础,并非他们的虚假真实性,而是他们被想象的方式。爪哇的村落居民总是知道他们和
从未谋面的人们有所关联,然而这种关联性,就如同可以无限延伸的亲族或侍从(clientship)网络一般,是以特殊主义的方式被想象的。直到不久以前,爪哇语当中还没有能够表示“社会”这个抽象概念的字眼。
今天我们也许会把旧政权时代的法国贵族想成一个阶级;但是他们被想象成一个阶级当然是非常晚近的
事。 [12] 对于“谁是X伯爵?”这样的问题,以往正常的答案不会是“贵族阶级的一员”,而是“X地的领
主”、“Y男爵的伯父”,或者“Z公爵的侍从”。
民族被想象为有限的,因为即使是最大的民族,就算他们或许涵盖了十亿个活生生的人,他们的边
界,纵然是可变的,也还是有限的。没有任何一个民族会把自己想象为等同于全人类。虽然在某些时代,基督徒确实有可能想象地球将成为一个信奉基督教的星球;然而,即使最富于救世主精神的民族主义者也
不会像这些基督徒一样地梦想有朝一日,全人类都会成为他们民族的一员。
民族被想象为拥有主权 ,因为这个概念诞生时,启蒙运动与大革命正在毁坏神谕的、阶层制的皇朝的
合法性。民族发展臻于成熟之时,人类史刚好步入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里,即使是普遍宗教最虔诚的追
随者,也不可避免地被迫要面对生机勃勃的宗教多元主义,并且要面对每一个信仰的本体论主张与它所支
配的领土范围之间也有不一致的现实。民族于是梦想着成为自由的,并且,如果是在上帝管辖下,直接的
自由。衡量这个自由的尺度与象征的就是主权国家。最后,民族被想象为一个共同体,因为尽管在每个民族内部可能存在普遍的不平等与剥削,民族总是
被设想为一种深刻的,平等的同志爱。最终,正是这种友爱关系在过去两个世纪中,驱使数以百万计的人
们甘愿为民族——这个有限的想象——去屠杀或从容赴死。
猛然之间,这些死亡迫使我们直接面对民族主义提出来的核心问题:到底是什么原因使得这种只有短
暂历史(不超过两个世纪)的,缩小了的想象竟然能够激发起如此巨大的牺牲?我相信,只有探究民族主
义的文化根源,我们才有可能开始解答这个问题。
————————————————————
注释:
[1] 我选择用这个论述方式只是想强调战斗的规模和形态,而不是要追究罪责。为了避免可能的误解,我们应该要说1978年12月的入侵源
起,最早可以追溯到1971年的两个革命运动党人之间的武装冲突。在1977年4月之后,最初由柬埔寨人发动,但越南人随即跟进的边界突击行
动的规模和范围逐步扩大,并在1977年12月升级成越南的大规模入侵。然而这些突击行动的目的都不是要推翻敌方政权或占领大片领土,而且
涉及的部队人数也不能和1978年12月所部署的部队相比。关于这场战争的起因的争论思虑最周详的讨论,请参见Stephen P.Heder,“The
Kampuchean-Vietnamese Conflict”,in David W.P.Elliott,ed.,The Third Indochina Conflict ,pp.21—67;Anthony Barnett,“Inter-
Communist Conflicts and Vietnam”,Bulletin of Concerned Asian Scholars ,pp.2—9;and Laura Summers,“In Matters of War and Socialism
Anthony Barnett would Shame and Honour Kampuchea Too Much”,ibid,pp.10—18。
[2] 凡是质疑联合王国在这方面是否称得上和苏联相同的人,都应该问问自己联合王国这个名字到底表示了哪个民族:大不列颠—爱尔兰
民族?
[3] Eric Hobsbawm,“Some Reflection on‘the Break-up of Britain’”,New Left Review ,105(September-October 1977),p.13.
[4] 参见Nations and States ,p.5。
[5] 参见“The Modern Janus”,New Left Review ,94(November-December 1975),p.3。这篇论文被只字未改地收在The Break-up of
Britain ,作为该书的第九章(pp.329—363)。
[6] Karl Marx and Friedrich Engels,The Communist Manifesto .在任何理论的注释当中,“当然”这两个字应该都要在入神的读者眼前闪起
红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62页译文如下:“每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当然首先应该打倒本国的资产阶
级。”——译者注)
[7] 正如艾拉·克米雷能(Aira Kemilainen)所留意到的,学院的民族主义研究的孪生“开国之父”,汉斯·科恩(Hans Kohn)和卡尔顿·海斯
(Carlton Hayes)令人信服地主张应该以这个日期为民族主义之发轫。我相信除了在特定国家的一些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宣传家以外,他们的
结论从未被严重地质疑过。克米雷能也观察到“民族主义”这个词要到19世纪才被广泛而普遍地使用。例如,它并未出现在很多标准的19世纪辞
典当中。虽然亚当·斯密以“‘nations’的财富”(国富论)之名作论,但他只不过把这个名词当作“社会”或“国家”的意思而已。Aira
Kemilainen,Nationalism ,pp.10,33,48—49。
[8] The Break-up of Britain ,p.359.
[9] 参考Seton-Watson,Nations and States ,p.5:“我所能说的就是当一个共同体内部为数众多的一群人认为他们自己形成了一个民族,或者表现得仿佛他们已经形成了一个民族的时候,一个民族就存在了。”
[10] Ernest Renan,“Qu'est-ce qu'une nation”,in Oeuvres Complètes ,1,p.892。他又接着说:“所有法兰西公民都必须已经遗忘圣巴托罗
缪惨案与13世纪发生在南方的屠杀事件。在法国能够提供他们起源于法兰西人证明的家族不到十个……”
[11] Ernest Gellner,Thought and Change ,p.169.
[12] 例如,霍布斯鲍姆为了“修补”这个情况,就说在1789年的时候贵族占全国2300万人口中的40万之多。(参见他的The Age of
Revolution, p.78。)然而我们有可能在旧政权之下想象这幅贵族的统计图像吗?
在本书所讨论的欧洲民族语言发展史的脉络中,vernacular(本意为“某一特定地区的本地语言”),指的是和拉丁文这个跨越地方界限
的“共通语”相对的“地方性”或“区域性”语言,如法语、德语或意大利语等。译者将这个字译为“方言”,纯粹取其“地方语言”的描述性涵义,请
读者勿与语言学上的“方言”(dialect)或汉字日常语汇中的“方言”一词混淆。在语言学上,“方言”(dialects)本意为一个“语言”内部细分出来的
同一语言的变种(variants),并且这些变种之间是可以相互理解的。当一个语言的几个变种方言演化到彼此不能理解时,它们就成为各自独立
的“语言”了。在这个定义下,文艺复兴前后在欧洲发展出来的各种vernaculars(地方语言)应该已经算是“language”,而非“dialect”了。同理,汉文通俗语汇习惯将各地区的地方语言视为在“标准法”位阶下的“方言”的说法,从语言学的角度来看,也是颇成问题的。以中国为例,如果
从“相互可理解性”(intercomprehensibility)的标准来衡量,许多所谓中国的“方言”(如吴语、赣语、粤语、闽北语、闽南语),其实根本是各
自独立的“语言”(language)。所谓“国语”或“普通话”之成为“标准语”,而闽南语、粤语沦为“方言”,并非基于语言学上的理由,而是出于政治
——特别是民族主义——的考虑。——译者注
————————————————————
(1) 根据《牛津英语辞典》(The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nationality一词有下列几个主要意义:(1)民族的特质或性格;(2)民族
主义或民族情感;(3)属于一个特定民族的事实;特定国家(State)的公民或臣民的身份,或者界定这种身份的法律关系,而这种关系涉及
了个人对国家的效忠与国家对个人之保护(国籍);(4)作为一个民族的分别而完整的存在;民族的独立;(5)一个民族;一群潜在的,但
非政治上的民族的人民(people);一个族群团体(ethnic group)。就译者的了解,虽然在通俗语汇或学术论述之中都可以看到上述这几种用
法,但其意义通常需视上下文而定。另外,虽然牛津英语辞典区分了民族(nation)与国家(state)两词的意义,但在通俗语汇上,这两个词经
常被混用。面对此种歧义的语言难局,译者采取根据上下文决定个别单词译法的策略。——译者注
(2) 亚历山大的托勒密(Ptolemy of Alexandria)是公元2世纪的埃及天文学家,他在公元150年左右在著作Almagest 中提出以地球为中心的
宇宙论。托勒密体系必须运用越来越多的数学手段才能解释反常的行星运动,因此沿用到文艺复兴时代时,已经形成一个生硬而负载过重的概
念,但却仍然不能准确地说明或观察行星位置。面对这一困境,波兰天文学家哥白尼(Nicolaus Copernicus,1473—1543)在他的短篇手稿Commentariolus (1514)中提出一个釜底抽薪的解决方案:放弃以地球为中心的预设,重新提出一个以太阳为中心的体系。作者以“晚期托勒
密”来比喻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主义对民族现象的错误理解在面临经验事实愈来愈严重的挑战时,只能用愈来愈复杂而无当的理论来自圆其说;
为今之计,需要以哥白尼的精神,彻底扬弃错误的预设,重新出发。——译者注
(3) “There is no there there”这句话意指“那个地方是人工的,不真实的,缺乏本质的,没有核心的”。这是美国女作家格特鲁德·斯泰因
(Gertrude Stein,1874—1946)在她1937年的作品《每个人的自传》(Everybody's Autobiography )之中描述奥克兰的名句。斯泰因的少女时期
是在北加州的奥克兰和旧金山地区度过的,后来她长住巴黎,视之为其精神上的故乡。在《巴黎,法国》(Paris,France ,1940)一书中,斯
泰因描述法国是她的第二个国家,“它(法国)不是真的(我的国家),但它真的在那里。”(It is not real but it is really there.)试将本句话与
前句作一对比。参见斯泰因:《巴黎,法国》(New York:Liveright,1970),第2页。——译者注第二章 文化根源
没有什么比无名战士的纪念碑和墓园,更能鲜明地表现现代民族主义文化了。这些纪念物之所以被赋
予公开的、仪式性的敬意,恰好是因为它们本来就是被刻意塑造的,或者是根本没人知道到底是哪些人长
眠于其下。这样的事情,是史无前例的。 [1] 你只要想象一下一般民众对于好事者宣称“发现”了某个无名战
士的名字,或是坚持必须在碑中存放一些真正的遗骨时的反应,就可以感受到此事的现代性了。一种奇怪
的,属于当代的亵渎形式!然而,尽管这些墓园之中并没有可以指认的凡人遗骨或者不朽的灵魂,它们却
充塞着幽灵般的民族的想象。 [2] (这也就是为什么许多拥有这种墓园的民族并不觉得有必要指明这些不存
在的英灵属于哪个民族。除了身为德国人、美国人、阿根廷人……之外,他们还有可能属于什么民族?)
如果我们试着去想象,比方说,“无名的马克思主义者之墓”或者“殉难自由主义者衣冠冢”,这类纪念物
的文化意义就会更清楚了。做这种想象有可能不让人感到荒谬吗?毕竟,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主义都不怎么
关心死亡和不朽。然而,民族主义的想象却如此关切死亡与不朽,这正暗示了它和宗教的想象之间有着密
不可分的关系。这种密切关系绝对不是偶然的,所以,如果我们以死亡——这个一切宿命之中最终极的宿
命——作为起点来考察民族主义的文化根源,也许会有所助益。
人会怎么死常常看来是没什么规则可循的,但所有人终究都不免一死。人的生命就充满了这类必然与
偶然的组合。我们全都明白我们体内特定的基因遗传,我们的性别,我们生存的时代,我们种种生理上的
能力,我们的母语等,虽是偶然的,却也是难以改变的。传统的宗教世界观有一个伟大的价值(我们自然
不应将此处所谓的价值和他们在合理化种种支配和剥削体系时所扮演的角色混为一谈),也就是他们对身
处宇宙之内的人、人类作为物种的存在以及生命之偶然性的关心。佛教、基督教或者伊斯兰教在许多不同
的社会中存续了千年以上,这一惊人的事实,证明了这些宗教对于人类苦难的重荷,如疾病、肢体残废、悲伤、衰老和死亡,具有充满想象力的回应能力。为何我生而为盲人?为何我的挚友不幸瘫痪?为何我的
爱女智能不足?宗教企图作出解释。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所有演化论进步论形态的思想体系的一大弱
点,就是对这些问题不耐烦地无言以对。 [3] 同时,宗教思想也以种种不同的方式——通过将宿命转化成生
命的连续性(如业报或原罪等观念),隐讳模糊地暗示不朽的可能。经由此,宗教思想涉及了死者与未降
生者之间的联系,即关于重生的秘密。任何一个曾经经历过他们的子女受孕与诞生的人,都会模糊地领会
到“连续”这个字眼当中同时包含的结合、偶然和宿命。[这里,演化论进步论思想又居于下风了,因为它
对任何连续性的观念抱着近乎赫拉克利特式(Heraclitean) (1) 的厌恶。]
我之所以提出这些似乎有点愚蠢的观点,主要是因为在西欧,18世纪不只标志了民族主义的降生,也
见证了宗教式思考模式的衰颓。这个启蒙运动和理性世俗主义的世纪同时也带来了属于它自己特有的、现
代的黑暗。尽管宗教信仰逐渐退潮,人的受苦——有一部分乃因信仰而生——却并未随之消失。天堂解体
了:所以有什么比命运更没道理的呢?救赎是荒诞不经的:那又为什么非要以另一种形式延续生命不可
呢?因而,这个时代所亟需的是,通过世俗的形式,重新将宿命转化为连续,将偶然转化为意义。在下面
的讨论中我们会知道,很少有东西会比民族这个概念更适于完成这个使命。假设如果民族国家确如公众所
认的,是“新的”而且是“历史的”,则在政治上表现为民族国家的“民族”的身影,总是浮现在遥远不复记忆的
过去之中, [4] 而且,更重要的是,也同时延伸到无限的未来之中,正是民族主义的魔法,将偶然化成命
运。我们或许可以随着德勃艾(Debray)的话说道:“是的,我生而为法国人是相当偶然的;然而,毕竟法
兰西是永恒的。”
我当然不是主张民族主义在18世纪末的出现是宗教世界观的确定性遭侵蚀所“造”成的,我也不是说此
种确定性之受侵蚀本身不需要复杂的解释。我也没有暗示民族主义不知怎样地就在历史过程中“取代”了宗
教。我所主张的是,我们应该将民族主义和一些大的文化体系,而不是被有意识信奉的各种政治意识形
态,联系在一起来加以理解。这些先于民族主义出现的文化体系,在日后既孕育了民族主义,同时也变成
民族主义形成的背景。只有将民族主义和这些文化体系联系在一起,才能真正理解民族主义。
宗教共同体(religious community)和王朝(dynastic realm),是和我们现在的讨论相关的两个文化体
系。就像“民族”在当代的地位一样,这两个文化体系在它们的全盛时期,也都被人们看作是理所当然的参
考架构。因此,一个重要的课题是,我们必须探究为什么这些文化体系会产生不证自明的合理性,而又是
什么样的重要因素导致它们的解体。宗教共同体
很少有什么事情,会比当今世界几个主要宗教所涵盖的地域之广袤,更令人印象深刻了:从摩洛哥到
菲律宾苏禄群岛(Sulu Archipelago)的地区,构成了伊斯兰教共同体;从巴拉圭到日本,尽在基督教世界
的范围之内;而佛教信仰圈,则涵盖了南起斯里兰卡北至朝鲜半岛的广大地域。这几个伟大的神圣文化
(为了本章讨论的目的,也许可以容我再加上“儒教”一项)里都包含有“广大无限的共同体”的概念。然而关
于基督教世界、伊斯兰教世界甚至中国(the middle kingdom)的想象——虽然我们今天把中国想成“中华
(Chinese)之国”,但过去她并不是把自己想象成“中华”,而是“位居中央”(central)之国——之所以可
能,主要还是经由某种神圣的语言与书写文字的媒介。仅以伊斯兰教为例:假如玛昆达纳人
(Maguindanao) (2) 和伯伯尔人(Berbers) (3) 在麦加相遇,他们虽然彼此都不懂对方的语言,无法口头
沟通,却可以理解彼此的文字,因为他们所共有的神圣经典全都是以古典阿拉伯文书写的。就此意义而
言,阿拉伯文正如同中国文字一样,创造了一个符号——而非声音(sounds)——的共同体。(所以今天的
数学语言延续着一个旧传统。罗马尼亚人和泰国人都不知道对方怎么称呼“+”这个符号,但他们都了解这个
符号的意义。)所有伟大而具有古典传统的共同体,都借助某种和超越尘世的权力秩序相联结的神圣语言
为中介,把自己设想为位居宇宙的中心。因此,拉丁文、巴利文、阿拉伯文或中文的扩张范围在理论上是
没有限制的。(事实上,书写文字越死——离口语越远——越好:原则上人人皆可进入纯粹符号的世
界。)
不过这种由神圣语言所结合起来的古典的共同体,具有一种异于现代的民族想象共同体的特征。最关
键的差别在于,较古老的共同体对他们语言的独特的神圣性深具信心,而这种自信则塑造了他们关于认定
共同体成员的一些看法。中国的官人们带着赞许的态度注视着千辛万苦方才学会挥毫书写中国文字的野蛮
人。这些蛮人虽未入文明之室,却总算也登上文明之堂了, [5] 而即使半开化也远胜于蛮貊。这样的态度当
然并非中国人所特有,也不限于古代。比方说,让我们想想下面这段由19世纪初哥伦比亚的自由主义者彼
得罗·费敏·德·瓦加斯(Pedro Fermin de Vargas)所拟的《平蛮策议》:
欲扩张吾人之农业,必先使印第安人西班牙化。彼等之怠惰、愚昧以及对正常应付出之努力
所持之漠然态度,令人思及彼等乃源于一堕落之种族,且距其源头愈远愈形退化……唯今之计,应使印第安人与白人通婚,宣告彼等已无进贡与其他义务,再发给私有土地,使之驯至灭种。 [6]
令人注意的是,这个自由主义者仍然提议用“宣告彼等已无进贡义务”和“发给私有土地”这类手段来让印
第安人“灭种”,而不像随后他在巴西、阿根廷和美国的后继者们一样,干脆用枪炮和细菌来灭绝印第安
人。同样要注意的是和他那屈身以从的残酷并存的一种乐观主义的宇宙论:在受孕于白种人的、“文明
的”精液,并且取得私有财产后,印第安人就和其他所有人一样,终究是可以救赎的。[后来的欧洲帝国主
义者多偏好“纯种的”马来人,廓尔喀人(Gurkhas) (4) 和豪萨族人(Hausas) (5) 胜于“混血种”、“半开化
土人”、“西化的东方绅士”(wog)之类的。费敏的态度和他们是多么不同啊。]
然而,如果神圣而沉默的语言是人们想象昔日那些伟大的世界的共同体的媒介的话,这种幻想的现实
性则系于一个对于当代西方思维而言颇为陌生的理念——符号的非任意性。中文、拉丁文或阿拉伯文的表
意文字是现实的直接流露,而不是任意虚拟的现实表象。关于何者才是适合于大众的语言(拉丁文或方
言)的长期争论,我们都知之甚详。伊斯兰教传统认为,唯有经由那无可替代的真实符号——阿拉伯文,才能接近安拉的真理,因此直到相当晚近,古兰经都还被认为是不可能照原文逐字翻译的(所以也就一直
没有被翻译)。这些古典的共同体从未设想过一个和语言高度分离,而所有语言都只是和它保持等距关系
(所以是可以互换的)符号的世界。事实上,本体论上的真实只能通过一个单一的、拥有特权地位的表象
系统,如教会拉丁文的真理语言(truth-language)、古兰经的阿拉伯文或科举的中文,才能理解。 [7] 而
且,作为所谓“真理语言”,这些表象系统内部带有一种对民族主义而言相当陌生的冲动,也就是朝向“改
宗”(conversion)的冲动。所谓改宗,我指的不是使人接受特定的宗教信条,而是如炼金术般地将之吸收
融合之意。蛮夷化为“中国”,里夫人(Rif) (6) 化为伊斯兰教徒,而伊隆哥人(Ilongo) (7) 则化为基督
徒。人类存有的本性可以经由圣礼而变形。(何妨试将这些耸立天际、傲视一切方言的古老的世界性语言
与湮埋于众方言之间、无人闻问的近代的人造世界语,如世界语或沃卜拉克语 (8) 作一对比。)终究,正是
这种可以经由神圣语言改宗的可能性,才让一个“英格兰人”可以成为教宗(Pope) [8] 而“满族人”得以成为
天子。然而纵然神圣的语言使得“基督教世界”这样的共同体成为可想象的,这些共同体实际的范围及其合理
性,却也不是单凭神圣的文字这一个因素就能解释清楚的。毕竟,能够阅读这些文字的人,只不过是在广
大的文盲之海上露出的数点识字者的小岩礁罢了。 [9] 欲求更完整的解释,我们必须看看文人阶层与其社会
之间的关系。把文人理解为某种神权的科技官僚的想法是错误的。他们所使用的语言,尽管深奥难解,却
完全没有律师或经济学家的术语那种超乎一般社会对现实的观点之外的、堆砌造作的深奥。相反,文人在
一个以神为顶点的宇宙秩序中,构成一个具有战略性地位的阶层。 [10] 关于“社会集团”的一些根本概念,并不是(集团的)界线导向和水平式的,而是向心而阶层式的。我们必须先知道有一个横跨欧洲全域的书
写拉丁文的文人阶级的存在,以及一个人人共有的关于世界的概念——这个概念主张具有双语能力的知识
阶层通过连接方言与拉丁文,同时也连接了尘世与天堂——然后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教皇权在全盛时期竟
然可以如此势焰熏天。(对于被逐出教会的畏惧正反映了这个宇宙论。)
但是,尽管伟大的宗教的想象共同体曾享有崇高的威望,他们的不自觉的整合性,却从中世纪后期开
始稳定地衰退。有种种理由导致了这样的衰退,然而我在此仅欲强调和这些共同体独特的神圣性有直接关
联的两项因素。
首先,是对欧洲以外的世界所进行的探险的影响。这个影响——虽然不限于欧洲,但主要仍发生在欧
洲——“急遽扩大了文化和地理的视野,也因而扩充了人们关于人类可能的生活形式的概念” [11] 。这个过
程,在所有伟大的欧洲人的游记中,早已清晰可察。让我们看看以下这段由威尼斯基督徒马可波罗在13世
纪末所写的,对忽必烈汗(Kublai Khan)饱含敬畏的描述: [12]
大汗在大胜之后,威风凛凛地班师凯旋,返回京城汗八里。这是发生在11月的事,然后大汗
继续在京城住到隔年的2月和3月,正当我们的复活节的时刻。当他得知复活节是我们的主要祭典
之一时,他诏令所有基督徒前来参观,并且令他们随身带来他们的那本含有四福音书的《圣
经》。在恭谨地将《圣经》反复薰香之后,他虔敬地亲吻《圣经》,并且下令所有在场贵族一一
照做。这个仪式是他每逢主要的基督教节庆,如复活节或圣诞节来临时,通常都会遵循的惯例。
此外,每逢撒拉森人(Saracens)(阿拉伯人)、犹太人或者其他偶像教徒的节庆之日,他也依此
惯例,行礼如仪。当他被问及这个举动的动机何在时,他说:“四位伟大的先知,分别受到不同种
类人群的敬拜。基督徒敬耶稣为神;伊斯兰教徒膜拜穆罕默德;犹太人崇敬摩西;偶像教徒则敬
拜所有偶像中最尊崇的索哥蒙巴坎(Sogomombar-kan)(释迦牟尼佛)。我敬爱所有这四位先
知,而且,不管他们之中到底哪一个在天上享有真正至高的地位,我都会向他祈求赐福。”但是从
陛下敬拜这四位神祇的方式观之,明显地,他认为基督徒的信仰至真且至善……
这段记载最引人注意的不是这位蒙古大帝冷静的宗教相对论(那终究还是一种宗教的相对论),而是
马可波罗的态度和语言。即便他是写给他的欧洲基督徒同胞看的,他也从未想过要把忽必烈称为伪善之徒
或者偶像崇拜者。(无疑,这有部分是因为“就臣民的数目、领土的面积和收入的总额而论,他超越了全世
界古往今来所有的君王” [13] 。)而从他不自觉地使用“我们的”(后来又变成“他们的”)这一字眼,以及将
基督徒的信仰描述为“至真”而不只是“真”当中,我们可以察觉到若干“信仰的领土化”(territorialization of
faiths)的种子,它们预示了日后许多民族主义者的语言(“我们的”民族“最好”——在一个竞争的、比较的
场域之中)。
来自波斯的旅行者“里嘉”(Rica)于“1712”年从巴黎写给友人“伊班”(Ibben)的一封信的开头,为我们
提供了一个深富启发性的对照: [14]
教皇是基督徒的头子;他是旧时代的偶像,而现在人们是出于习惯而敬拜他。以往连君主们
都畏惧他,因为他要废除这些君主的王位,就像我们伟大的苏丹要让伊瑞美地亚或乔治亚的国王
退位一样简单。但是现在人们再也不怕他了。他宣称自己是最早的基督徒之一的,一个叫做圣彼
得的人的继承人。这当然是个有钱的世代继承,因为他有庞大的财富,而且控制了一个很大的国
家。
出于一个18世纪的天主教徒之手的这些刻意而复杂的虚构情景,反映出他那位13世纪的前辈天真的写
实主义,然而时至18世纪的此刻,“相对化”和“领土化”已经完全是自觉的,而且是带有政治意图的了。伊朗
宗教政权领袖霍梅尼没有用“大撒旦”之名来称呼异端邪说,甚至也没有用来指某个恶魔般的人物(不起眼
而渺小的卡特总统实在配不上这个头衔),却将之视为一个民族。难道我们不能把这个例子,看作是对这
个正在演化当中的“宗教共同体自觉而带有政治意图的‘相对化’与‘领土化’的”传统,一个吊诡式的透彻阐释
吗?第二个因素是神圣语言自身地位的逐步式微。在论及中世纪的西欧时,布洛克(Bloch)注意到“拉丁
文不仅是教学用的语言,它还是仅有的一个被教授的语言” [15] 。[这第二个“仅”(only)很清楚地显示出
拉丁文的神圣性——所有其他的语言都被认为是不值得教授的。]然而到了16世纪,这种情形已开始急速
改变了。我们无须在此着墨于导致这个改变的种种因素:在后文中我们自会讨论印刷资本主义(print-
capitalism)的无比重要性。我们只要记得这个变化的规模和速度就够了。根据费柏赫(Febvre)和马丁
(Martin)的估计,1500年以前出版的书籍有77%还是用拉丁文写的(然而这也意味着已经有23%的书是以
方言写成的)。 [16] 如果1501年时在巴黎印行的88个版本的书籍当中只有8个版本不是用拉丁文写的,那么
到了1575年之后法文版的书籍就一直占着多数。 [17] 虽然在反宗教改革期间拉丁文曾有短暂的复兴,但拉
丁文的霸权已亡。我们也不只是在谈论是否广泛流行的问题而已。稍后,以一种同样令人晕眩的速度,拉
丁文丧失了作为全欧洲上层知识阶级的语言的地位。17世纪时,霍布斯(Hobbes,1588—1678)因为使用
真理语言写作而享誉欧洲大陆,而莎士比亚(Shakespear,1564—1616)却因以方言写作而声名不闻于英吉
利海峡彼岸。 [18] 如果英语没有在200年后变成最显赫的世界性的——帝国式的语言,莎士比亚果真能幸免
于先前默默无闻的命运吗?同时,在英吉利海峡彼岸的同代文人中,笛卡儿(1596—1650)和帕斯卡
(1623—1662)多以拉丁文书写信简,但伏尔泰(1694—1778)则完全使用方言通信。 [19] “1640年以后,由于以拉丁文写的新书日益减少,而方言著作则与日俱增,出版渐渐不再是一个国际性(原文如此)的事
业了。” [20] 一言以蔽之,拉丁文的衰亡,其实是一个更大的过程,也就是被古老的神圣语言所整合起来的
神圣的共同体逐步分裂、多元化以及领土化的过程的一个例证。王朝
现代人恐怕很难理解曾经有这样一个世界,在那里大多数的人唯一想象得到的“政治”体系似乎只有王
朝而已。因为“真正的”(serious)君主制本质上存在于一个和所有与现代的政治生活有关的概念相交会的位
置上。王权把所有事物环绕在一个至高的中心四周,并将它们组织起来。它的合法性源于神授,而非民众
——毕竟,民众只是臣民(subjects),不是公民(citizens)。在现代概念中,国家主权在一个法定疆域内
的每平方厘米的土地上所发生的效力,是完全、平整而且均匀的。但是在比较古老的想象里面,由于国家
是以中心(center)来界定的,国家与国家之间的边界是交错模糊的,而且主权也颇有相互渗透重叠之处。
[21] 因而,很吊诡的是,前现代的帝国与王国竟能够轻易地维系他们对极度多样而异质,并且经常是居住
在不相连的领土上的臣民的长期统治。 [22]
我们同时也要记得,这些古老的君主制国家,不只通过战争,也靠一种和今日所实行的颇不相同的“性
的政治”来进行扩张。经由垂直性的法则,王朝之间的联姻把多种多样的民众聚合到新的顶点之下。就此而
言,哈布斯堡王室是个中典范。诚如那收场的戏文所云:“让别人去战斗吧!汝,幸运的奥地利结婚去
吧!”(Bella gerant alii tu felix Austria nube! (9) )以下是一段稍作简化了的哈布斯堡家族后期君主拥有的
头衔: [23]
奥地利皇帝;匈牙利,波希米亚,达尔马提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加利西亚,罗德美
利亚,与伊利里亚之王;耶路撒冷等地之王;奥地利大公;托斯卡纳与克拉科夫大公;洛林,萨
尔茨堡,史地利亚,卡林西亚,卡尼奥拉,与布科维纳公爵;特兰西瓦尼亚大公,摩拉维亚边境
伯爵;上下西里西亚,摩德纳,帕尔马,皮亚琴察,与瓜斯地拉,奥斯维茨和萨托,泰申,福里
奥,拉古萨,与扎拉大公;哈布斯堡与蒂洛尔,基堡,哥兹,格拉地斯卡伯爵;特兰托与布利琛
公爵;上下洛斯茨与伊斯的利亚边境伯爵;霍恩姆斯,费尔得克奇,布莱根茨,索能堡等地之伯
爵;的里雅斯特领主,卡塔罗与温地斯马克领主;伏伊伏丁那与塞尔维亚大公……
诚如贾希(Jászi)公允的观察,这个头衔“不是没有滑稽的一面……这是哈布斯堡家族无数次联姻、讨
价还价和掠夺的记录”。
在一夫多妻为宗教所认可的世界里,复杂的多层妻妾体制对于王朝的整合具有关键的重要性。事实
上,可否容我说,王室血统的威望除了源自神命之外,经常也来自异族通婚(miscegenation)呢? [24] 因
为,这种血缘的混合是统治地位的表现。从11世纪以来(如果在此之前真的有过的话)就再也没有一个“英
格兰的”王朝统治过伦敦。这是一个典型的例证。而我们又该把波旁王室(the Bourbons)派给哪一个“民
族”呢? [25]
然而,17世纪时,由于某些无须在此细究的因素,神圣君主自然而然产生的正当性在西欧开始慢慢衰
退。1649年,查尔斯·斯图亚特(Charles Stuart)在现代世界的第一场革命中被斩首,而在17世纪50年代,这个重要的欧洲国家的统治者不是国王,而是一个平民出身的监国(Protector)。但即使在诗人波普
(Pope)和爱迪生(Addison)的时代,安·斯图亚特(Anne Stuart)仍然在使用以皇族之手触摸病人的方式
为人治病。在启蒙运动时代的法国,直到旧政权瓦解前夕,波旁王室的路易十五和路易十六也都还在做这
种事情。 [26] 然而1789年以后,统治者就得要声嘶力竭而且自觉地辩护他们的合法性了,而在此过程
中,“君主制”(monarchy)变成了一个半规范化的模式。天皇和天子变成了“皇帝”。在边远的泰国,拉玛五
世(Rama V)[Chulalongkorn(朱拉隆功)]把他的子侄送到圣彼得堡、伦敦和柏林的宫廷里去学习这个
世界性的模式的机微奥妙。1887年,他将法定长子继承的必要原则予以制度化,从而将泰国带入“与西欧
诸‘文明的’君主制国家并列”之境。 [27] 这个新体制在1910年,把一个在早先的旧制下当然会被略过的古怪
的同性恋者送上了王位。不过,在他的加冕典礼上,来自英国、俄国、希腊、瑞典、丹麦甚至日本等国的
代表出席,等于宣示了各君主国对他登基为拉玛六世的认可。 [28]
迟至1914年,君主制国家还是世界政治体系成员中的多数,然而,正如我们将在下面仔细探究的,早
在旧的正当性原则无声无息地消亡之际,很多君主早已在探求“民族的”标志了。尽管腓特烈大帝(1749—
1786年在位)的军队中还有为数众多的“外国人”,他的侄孙腓特烈·威廉三世(1797—1840年在位)的军
队,在沙恩霍斯特(Scharnhorst)、格耐斯瑙(Gneisenau)和克劳塞维茨(Clausewitz)等人 (10) 了不起的
改革之后,已经彻底地变成“普鲁士的国民军”了。 [29]对时间的理解
然而,我们也不应该目光短浅地认为民族的想象共同体就真是从宗教共同体和王朝之中孕育,然后再
取而代之而已。在神圣的共同体、语言和血统衰退的同时,人们理解世界的方式,正在发生根本的变化。
这个变化,才是让“思考”民族这个行为变得可能的最重要因素。
要想感觉一下这个变化,我们如果去看看那些神圣共同体怎样在视觉上被表现出来,像中世纪教堂里
的浮雕和彩绘玻璃,或早期意大利和佛兰芒(Flemish)巨匠的画作,当会获益良多。这些视觉表现的代表
性特征是,它们和“现代服装”之间具有某种容易令人误解的相似性。那些遵循星辰的指引来到耶稣诞生的
马槽的牧羊人竟然有着伯根地农民的五官。童贞玛丽长得像塔斯卡尼商人的女儿。在很多画作当中,出现
在画面上的委托创作主顾穿着全套市民阶级或贵族的行头,满怀赞叹地跪在牧羊人的身边。显然,我们今
天看似不协调的事物在中世纪的宗教敬拜者眼中却是完全自然的。我们所面对的,是一个几乎完全以视觉
和听觉来表现对现实的想象的世界。基督教世界需要经由无数个特殊的事物,像是这面浮雕,那片窗户,这篇祷文,那个故事,这出道德剧,那个圣者或殉教者的遗骨等,才形成其普遍性的形式。尽管横跨全欧
熟悉拉丁文的知识阶层是建构基督教想象的一个重要成分,然而以较个别而具体的视、听觉创造物当作向
不识字的民众传播教义的媒介的做法,也同等重要。就算听过那个谦逊的教区教士讲道的街坊民众人人都
对他的家世和弱点了如指掌,他也还是他的教众和上帝之间的直接媒介。这种宇宙普遍性(cosmic-
universal)原则和现世特殊性(mundane-particular)原则的并立,意味着不管基督教世界可能有多广阔,或
者人们觉得它有多广阔,事实上它是以种种特殊的面貌,针对不同的地域共同体如斯瓦比亚(Swabia)或
安达卢西亚(Andalusia)等,以这些共同体自身的形象呈现出来的。以现代美术馆那种“回复原貌”的精
神,把童贞玛丽画得像闪族人,或穿着“第一世纪”的服装,中世纪基督徒对这种事情是无法想象的。中世
纪的基督教教义并没有历史是一条无尽的因果锁链这样的观念,也没有过去与现在断然二分的想法。 [30]
据布洛克的考察,当时的人认为既然基督的二次降临随时会到来,他们必然已经接近时间的尽头了——诚
如保罗所言,“主降临之日将如黑夜之窃贼般悄然到来”。无怪乎伟大的12世纪编年史家弗来兴主教奥托
(Bishop Otto of Freising)会反复陈说“被置于时间尽头之我等”。布洛克下结论说,中世纪的人“从献身冥思
之日起,他们的思绪就远离这样的念头,即年轻而富有活力的人类种族拥有久远未来的前景” [31] 。
奥尔巴哈(Auerbach)为这种形式的意识,描绘了一幅令人难忘的图像: [32]
如果像以撒(Issac)(圣经中亚伯拉罕之子,被其父献祭给上帝)的牺牲这样的事件,被诠
释为预示了基督的牺牲,因而前者仿佛像是宣告且承诺了后者的发生,而后者则“成就了”前者,那么,在两个相互没有时间或因果关联的事件之间,某种关联就被建立起来了——而这个关联是
无法用理性在水平的次元上建立起来的……只有两个事件都被垂直地联系到唯一能够如此规划历
史并且提供理解历史之钥的神谕,才有可能确立这个关联……此时此地不再只是尘世事件之链的
一环而已,它同时是一个始终存在,并且终将在未来被完成的事物;而且,严格说来,在上帝眼
中,它是某种永恒的、无时不在的,以及在已支离破碎的尘世领域中被完成的事物。
他正确地强调出像同时性(simultaneity)这样的概念对我们而言是全然陌生的。这个概念把时间看成
很接近本雅明所说的“弥赛亚时间”,一种过去和未来汇聚于瞬息即逝的现在的同时性。 [33] 在这种看待事
物的观点中,“其时”(meanwhile)一词是不可能具有真正的意义的。
我们自己的同时性概念,是在一段漫长的时间里逐渐成形的,而它的出现当然和世俗科学的发展有关
——虽然这两者之间究竟如何相关仍有待深入探讨。但因为这个概念是这么重要,如果不对它作充分的思
考,我们势必难以究明民族主义那隐微而不易辩识的起源。最后终于取代了中世纪的与“时间并进的同时
性”概念的,再借用本雅明的话,是一种“同质的、空洞的时间”的观念。在此观念中,同时性是横向的,与
时间交错的;标示它的不是预兆与成就,而是由时钟与日历所测量的,时间上的一致(temporal
coincidence)。 [34]
如果我们思考一下两种最初兴起于18世纪欧洲的想象形式——小说与报纸——的基本结构,就能够明
白何以这个转型对于民族的想象共同体的诞生会是如此重要了。 [35] 因为这两种形式为“重现”民族这种想
象的共同体,提供了技术上的手段。首先来考察旧式小说的结构,一种从巴尔扎克的杰作到所有同代的三流廉价小说都共有的典型结构。
很清楚,它是一种以“同质的、空洞的时间”来表现同时性的设计,或者说是对“其时”这两个字的一种复杂注
解。为了说明起见,让我举一部单纯的小说情节里面的一段为例。在这段情节中,某男子(A)有妻(B)
与情妇(C),而这个情妇又有一情人(D)。我们也许可以为这段情节想象出一个如下的时间表:
要注意在这个时序中A和D从未碰面,而事实上如果C很精明,这两人可能根本不知道彼此的存在。
[36] 那么A和D到底有什么关系?有两个互补的概念。第一,他们都身处“社会”(如西撒克斯、卢卑克、洛
杉矶)之中。因为这些社会有着如此坚实稳定存在的社会学实体,其成员(A和D)因此甚至可 ......
本书由“行行”整理,如果你不知 道读什么书或者想获得更多免费电子书请加小编微信或QQ:2338856113
小 编也和结交一些喜欢读书的朋友 或者关注小编个人微信公众号名称:幸福的 味道 为了方便书友朋友找
书和看书,小编自己做了一个电子书下载网站,网 站的名称为:周读 网址:www.ireadweek.com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著;吴叡人译.—
增订本.—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
书名原文:Imagined Communities: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ISBN 978-7-208-13849-0
Ⅰ.①想… Ⅱ.①本… ②吴… Ⅲ.①民族主义-研究 Ⅳ.①D091.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125968号
责任编辑 潘丹榕
封面装帧 人马艺术设计·储平
想象的共同体
——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
[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 著
吴叡人 译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 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o)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635×965 116 印张 19.5 插页 4 字数 263,000
2016年8月第1版 2016年8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208-13849-0D·2877
定价 48.00元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First published by Verso 1983
This edition published by Verso 2006
· Benedict Anderson,1983,1991,2006
new material ? Benedict Anderson,2006
Chinese(Simplified Characters only)Trade Paperback
Copyright ? 2016 by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译稿经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企业股份有限公司独家授权想象的共同体 ——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增订版)
[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 著
吴叡人 译
上海他认为他的职责在于逆其惯常之理以爬梳历史。
沃尔特·本雅明,《启蒙之光》 (Illuminations )
如是从所有人种之混合中起始
那异质之物,英格兰人:
在饥渴的强奸之中,愤怒的欲望孕生,在浓妆的不列颠人和苏格兰人之间:
他们繁衍的后裔迅速学会弯弓射箭
把他们的小牝牛套上罗马人的犁:
一个杂种混血的种族于焉出现
没有名字没有民族,没有语言与声名。
在他热烈血管中如今奔流着混合的体液
撒克逊人和丹麦人的交融。
当他们枝叶繁茂的女儿,不辱父母之风
以杂交之欲望接待所有民族。
这令人作呕的一族体内的确包含了嫡传的
精粹的英格兰人之血……
录自丹尼尔·笛福(Daniel Defoe)
《纯正出身的英格兰人》 (The True-Born Englishman )目录
民族主义研究中的老问题与新困惑——关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民族主义研究 汪晖
认同的重量:《想象的共同体》导读
第二版序
第一章 导论
第二章 文化根源
第三章 民族意识的起源
第四章 欧裔海外移民先驱者
第五章 旧语言,新模型
第六章 官方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
第七章 最后一波
第八章 爱国主义和种族主义
第九章 历史的天使
第十章 人口调查、地图、博物馆
第十一章 记忆与遗忘
旅行与交通:论《想象的共同体》的地理传记
参考文献
译后记
附录一 民族主义研究的新困惑
附录二 东南亚华人的认同悖论:以泰国为例如果你不知道读什么书,就关注这个微信号。
微信公众号名称:幸福的味道
加小编微信一起读书
小编微信号:2338856113
【幸福的味道】已提供200个不同类型的书单
1、 历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
2、 每年豆瓣,当当,亚马逊年度图书销售排行榜3、 25岁前一定要读的25本书
4、 有生之年,你一定要看的25部外国纯文学名著
5、 有生之年,你一定要看的20部中国现当代名著
6、 美国亚马逊编辑推荐的一生必读书单100本
7、 30个领域30本不容错过的入门书
8、 这20本书,是各领域的巅峰之作
9、 这7本书,教你如何高效读书
10、 80万书虫力荐的“给五星都不够”的30本书
关注“幸福的味道”微信公众号,即可查看对应书单和得到电子书
也可以在我的网站(周读)www.ireadweek.com 自行下载
更多书单,请关注微信公众号:一种思路民族主义研究中的老问题与新困惑
——关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民族主义研究
汪晖命运
2015年12月13日,朋友传来消息: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教授当日在印度尼西亚辞世。一位在雅加达大学
作研究的年轻人写信说,他前一日还在学校听他演讲,精神矍铄,不能相信他的离去。安德森年届79岁高
龄,虽然事发突然,但并不完全突兀。2013年9月,清华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所邀请他来清华讲学,他
在第一时间回信表示感谢:“能够被您和您在北京的同事们邀请,是我的荣幸。我觉得3月很合适,那个月
中适合您的任何时间都可以。在那个月,我没有承诺其他的旅行安排,而且那是泰国最热的一个月!您的
来信让我想起上次在中国的时间已经是1941年!!!唯一需要警告您的是,77岁的我已经有些脆弱,经常
会感到疲惫……”虽然安德森提及了身体的脆弱和疲惫,但三个惊叹号却强烈地表达了他对即将重访中国的
兴奋之情。
2014年春天,他如约访问北京,虽然常需坐轮椅,但始终兴味盎然,时时冒着雾霾,穿行于街市之
间。除了安排他的演讲之外,我也陪他去国家博物馆等处参观。安德森1936年8月26日出生于中国境内毗邻
东南亚地区的大城市昆明,学术事业起始于他在1967年完成的博士论文《革命时代的爪哇》。1972年,因
与同事合作完成的关于苏哈托政变的研究(撰写于1966年)公开发表,他被拒绝进入印度尼西亚,时间长
达27年(1972—1999年)之久。在此之后,他重新回到祖父、父亲和自己均曾生活过的地区作研究,最终
殁于与自己的国家相隔遥远却又与其人生道路纠缠始终的国度。安德森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夕出生于中
国,在日本军队轰炸昆明的危险时分离开,终于在73年之后再度回到出生的国度,并在这里留下了他的思
考和足迹。冥冥之中,这两个开端与结束交叉重叠,或许就是命运的安排。
在他来访前夕,我们通过邮件商讨两次演讲的题目。我的建议是:首先,从1983年《想象的共同体》
问世至今,在三十余年的时间里,这部书一直是人们讨论和引用的对象,能否请他就三十多年来针对该书
的种种挑战,在清华的讲台上作一个回应?其次,他近年常常住在东南亚地区,观察那里的起伏变化,能
否向中国的听众介绍他的最新研究成果?安德森很快作出回应,并拟定了两个题目,一个是《民族主义研
究的新困惑》,另一个是《东南亚华人的认同悖论:以泰国为例》。想象
安德森所说的“民族主义研究的新困惑”其实是对《想象的共同体》一书的基本论点的延伸性论述。
《想象的共同体》最著名的观点是:民族是一个想象出来的政治意义上的共同体,即它不是许多客观社会
现实的集合,而是一种被想象的创造物。在民族主义研究中,将民族理解为某种想象物并不是安德森的发
明,早于他的研究,厄内斯特·盖尔纳就曾建议“从意愿和文化与政治单位结合的角度来给民族下定义”,即
民族主义造就了民族,而不是相反,从而民族主义热情包含了“文化上富于创造性的、空想的、积极创造的
一面”。 [1] 他们两人也都指出这种想象的、创造性的方面并不等同于说民族主义是一种虚假的、人为的产
物,而是一种新的、被创造的社会事实。这些观点明显受到20世纪60年代以降社会理论、心理分析学说和
意识形态理论的影响。拉康的现实的、想象的和象征的三界说、科里利厄斯·卡斯托里亚迪斯(Cornelius
Castoriadis)在拉康影响下提出的“社会的想象机制”(imaginary institution of societies),以及阿尔都塞的意
识形态理论,都为此后社会理论中各种各样的“想象”论提供了灵感。但对于安德森而言,作为政治共同体
之民族的诞生是与印刷资本主义的发展密切相关的,后者整合各种方言,为小于作为帝国语言(拉丁语)
的新的权力语言的形成提供了可能。较之盖尔纳的解释,安德森的分析更加清晰地突破了民族主义解释中
的社会要素决定论,强化了其形成的能动方面。至于这种能动的解释在多大程度上脱离了社会学决定论,我们稍后再谈。
安德森对民族主义的研究远远超出了欧洲的语境,也不再将民族主义的历史讲述为一个从欧洲向世界
扩散的故事。但我们并不难发现:他的叙述与更早的有关欧洲民族主义的叙述存在某些重合。例如,根据
他的叙述,在欧洲,新教与印刷资本主义的结合促成了取代宗教团体和王朝体系的政治共同体的出现;印
刷资本主义为民族语言的整合与形成提供了条件。这些要素在一些批评者的眼中也正是欧洲中心主义的变
体。这里要强调的是:正是基于这一“在理解世界的方式上”发生了的“根本变化”,安德森对民族主义现象进
行了重新叙述,即有关民族主义的三重分类。不同于那些认为民族主义是从欧洲漫延至世界其他地区的传
统观点,他认为民族主义的第一波是发生在北美殖民地的“克里奥尔民族主义”,或称远程民族主义。这一
民族主义综合了殖民地各阶层的诉求,反抗宗主国的压迫和不平等对待,但在价值上同时汲取了欧洲启蒙
思想。这种对于新的政治共同体的想象是那些去往宗主国的“克里奥尔”官员和当地“克里奥尔”印刷工的创造
物。南北美洲在19世纪兴起的新一波大众性民族主义正是对于这一民族主义版本的回应。第二种民族主义
模式,也是被其他地区民族主义最常复制的模式,是欧洲的语言民族主义,正是通过这语言民族主义的创
造,一种取代帝国的、奴隶制和封建等级制的,即主权的政治共同体诞生了。第三种民族主义即官方民族
主义,即由国家由上至下推进的文化统一与政治统一的进程,通过在交流工具(印刷术)、普及教育和内
政构造等各方面的强制推行,上层统治最终促使包含多样性的和地方性的文化趋于同质化。俄国、晚清中
国的改革都可以算作这一官方民族主义的典范。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民族解放运动的浪潮是民族主义
的“最后一波”,它既是对于官方民族主义的殖民地形式——帝国主义——的反应,也是对先前两波民族主
义浪潮中的大众民族主义(北美与欧洲)的模仿。由此,安德森以民族主义多种形态为介质,描述了一个
不同于从欧洲扩散至其他地区的单线论的多重扩散的全球进程。
《想象的共同体》对民族主义研究的贡献或许可以被归纳为如下几点:首先,它不是用族群、宗教、语言等社会要素解释民族形成,也不是用工业化或一般意义的资本主义说明民族主义的兴起,而是别有新
意地提出印刷资本主义与新的政治共同体形成之间的伴生关系。这为民族形成是一种现代创造过程或想象
过程的论点提供了前提,也为颠倒传统观念中民族与民族主义的衍生关系铺平了道路,即不是民族产生了
民族主义,而是民族主义创造了民族。其次,历来的民族主义研究都将法国大革命的政治原则和欧洲民族
国家的诞生视为一种向全球扩展的体系,并以此为主要视角分析非西方地区的民族主义,而安德森却倒置
了民族主义的历史,即民族主义并不是一种欧洲的产物,恰恰相反,最早的民族主义是发生在北美的“克里
奥尔”民族主义,即一种远程的民族主义。或者说,最早的民族主义是殖民主义全球关系的产物。这一论点
或许源自他在印度尼西亚作研究时所受到的触动,亦即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及其政治进程与欧洲民族主义
之间不可能只是一种由中心区域扩展至其他地区的等级性衍生关系。在有关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的后现
代论述所创造的氛围中,安德森对于殖民地与宗主国、殖民地民族主义(反帝的民族主义)与官方民族主
义的区分,为重新审视20世纪民族运动的历史留下了一个缺口。困惑
《想象的共同体》可能是三十年来有关民族主义的研究中——也是全部社会科学理论中——被征引和
讨论最多的文本之一。在安德森抵达北京后的闲谈中,我问及他对有关《想象的共同体》的质疑和批评的
看法,即哪些观点和商榷是他认为最重要的和值得回应的。他用一种幽默的但显然也是有些骄傲的态度回
答说:绝大部分质疑都是用各自的历史经验对他的理论论述进行修订,至于到底有哪些质疑真正触动了他
的理论预设,他没有举出任何一例。我至今还记得他说这话时的表情。不难想象,他在清华大学所谈的“民
族主义研究的新困惑”与其说是对批评和质疑的回应,毋宁说是对他早期研究的补充和完善。的确,这两场
演讲从不同的方向对《想象的共同体》有关民族和民族主义的定义、历史脉络作了理论的与历史的再阐
释。
这个基本定义就是民族是一个想象出来的政治意义上的共同体,一个被想象的、有限的、享有主权的
共同体。在《想象的共同体》中,安德森解释了为什么这个共同体不是许多客观社会现实的集合,而是一
种被想象的创造物。而在清华的演讲中,他改变了论述的重心,侧重阐述了两个有关这一“想象的共同
体”的问题:第一,作为政治共同体的民族与其他共同体(宗教共同体、族群共同体、家庭等等)相比,究
竟有哪些不同的特征?如何辨识民族主义的情感方式与其他情感方式的联系与区别?第二,《想象的共同
体》所涉及的远程民族主义主要产生于西半球(海地、北美等),那么,在东半球的东南亚和中国,移民
群体与民族认同的关系如何?
他的第一场演讲《民族主义研究的新困惑》主要回答第一个问题,而第二场演讲《东南亚华人的认同
悖论:以泰国为例》则尝试探索第二个问题。在我看来,他所提出的问题很可能不是民族主义研究中的“新
困惑”,而是民族主义研究中尚未展开的老问题。安德森首先不是从定义出发来解释这个问题,而是用某种
人类学的观察来辨识民族主义的认同和情感特征。但是,正如他的印刷资本主义概念很难脱离欧洲民族语
言的形成的历史模型,他对作为政治共同体的民族的独特性的解说也很难脱离欧洲宗教共同体与民族共同
体之间的比较。用他的话说,资本主义、印刷技术和人类语言多样性之间的重合是与一种世俗的政治共同
体的到来同步的。事实上,他的第一场演讲的真正意义在于揭示了他(其实也包括绝大多数西方理论家)
对政治共同体的认识是从政治宗教的联系与区别中展开的,宗教、宗教共同体是思考政治、政治共同体的
基本参照。这是欧洲启蒙运动的遗产。这也让我们更为清楚地了解为什么他在《想象的共同体》中用一种
对于非西方读者难以理解的方式讨论弥赛亚时间与民族主义的空洞、均质的时间之间的关系。如果说《想
象的共同体》对时间的讨论最为抽象和难解,那么,他在清华的演讲却以极为浅显的方式再度通过宗教与
政治之间的关系展开对民族共同体特征的描述:民族共同体和宗教共同体都涉及信念和情感,但两者的区
别是什么?人们像认同宗教一样相信自己的国家是好的,却不会像宗教信徒相信上帝绝对正确那样相信国
家的完美。民族主义的情感表述是:即便我的国家会犯错,但在情感上,不论国家对错,她依旧是我的国
家。这与宗教共同体的信念产生了区别:民族和民族领袖可能犯错,而宗教——如同大多数欧美理论家们
一样,安德森的宗教论述基本上是在一神教的范围内——不会承认信仰和上帝会犯错。这种信念形态的区
分其实也可以被描述为一种世俗信仰与超越信仰之间的区分,即国家——以及他的贤明的或犯错的先人
——始终与我们同在,他们既不上天堂也不下地域,是现世的或历史性的存在(故而可以犯错),而上帝
却在天堂里,他永远正确。正如民族主义运动或民族主义领袖一再诉诸家庭、家族、宗族等等血缘共同体
以表明民族共同体的本质纽带,安德森从另一个角度观察了民族认同与亲缘纽带在情感特征方面的联系和
区别。他比较孩子对母亲行为的羞耻感与民族感情中对于民族行为或状态的羞耻感,不但说明了民族认同
对亲缘关系的模拟,而且也以此论证民族认同与宗教认同的区别。但他的分析集中于某种心理现象的描
述,未能从神学与政治、信仰与意识形态的关系中展开两者的区别和联系,明显地限制了其理论深度。
听到安德森对于羞耻感的讨论,我禁不住联想起美国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中有关原
罪与羞耻的讨论,即西方基督教文明是一种罪感的文化,而日本或东亚是耻感的文化,前者源自超越的视
角,是真正个人主义的,而后者却是在他者注视下的情感方式,是共同体伦理的产物。[20世纪80年代,中国还曾出现过模拟本尼迪克特论述的所谓罪感(欧洲)、耻感(日本)、乐感(中国)的文化模式
论。]本尼迪克特早年研究印第安部落,1927年完成了《文化模式》一书。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对罗
马尼亚、荷兰、德国、泰国等国进行民族性或国民性的研究,他的名作《菊与刀》也是在战争期间由美国
军方支持的研究项目。在这一日后名声大噪的作品中,日本民族性的二重性同样是在“文化模式”的框架下
展开的。与本尼迪克特不同,安德森的论述并未将羞耻感定义为某种独特的文化模式的产物。在他看来,羞耻感是一种现世的共同体关系(民族的、家族的、家庭的……)的普遍的情感特征——既然民族国家可
以犯错,人们对民族国家的情感方式中就必然包含着羞耻的意识,由此,羞耻感成为民族共同体区别于宗
教共同体的一种情感特征。近代中国民族主义运动对中国国民性的批判、美国反越战运动对于美国军事犯
罪的声讨、知识分子痛斥所置身的体制的姿态和唯我独醒的暗示、启蒙者对于未来(尚未出世的孩子们)
的展望均可以从民族主义情感方式的角度加以观察。但是,本尼迪克特与安德森都没有将羞耻感历史化,即有意或无意地遮盖了羞耻感总是在某个他者的注视之下才能发生,羞耻感是历史性权力关系的产物。在
欧美之外的地区,除了西方或内在化了的“西方”,还有谁能够拥有让人羞耻的目光呢?如果从摆脱羞耻感
的角度去观察亚非地区的民族革命,除了让那个目光感到满意之外,我们该从哪里去发现其创造性和自主
性?
安德森在演讲中特别提及民族主义哲学与泛灵论的关系或相似性,实际上是在暗示民族主义与宗教的
关系有些类似于泛灵论与一神教的关系。19世纪欧洲的著作家们——如黑格尔——一再论证:泛灵论是一
种与宗教(一神教)有所重叠但性质不同的东西,东方的佛教、印度教和许多民间信仰都带有泛灵论的特
点;如今安德森在民族主义及其哲学中也看到了类似的东西。正如泛灵论一样,民族主义赋予事物以灵
性,但这种灵性不在超验的世界里,而就在我们的身边,在日常生活的世界内。一个有待回答的问题是:
泛灵论与民族主义究竟存在怎样的思维、情感或历史的关系?如果“东方”是一个泛灵论的世界,那么,东
方民族主义在这个世界的诞生会与一神教世界的民族主义有所区别吗?
政治共同体与亲缘共同体在情感特征和信仰方式上的相似性(俗世的、总是包含羞耻感的、泛灵论的
等等)并不能作为两者相互同一或趋同的证明,恰恰相反,这种情感关联只有在某种状况下才能转化为政
治共同体的形成条件。在《想象的共同体》中,安德森对于印刷资本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关系的分析侧重于
政治共同体形成条件的探索,而在清华演讲中,他集中分析了远程民族主义形成的历史条件。远程民族主
义主要是对移民群体的民族主义及其与宗主国关系的研究,在《想象的共同体》中,这一概念用于对于18
—19世纪美洲民族主义的探讨,其形成的基础条件包括:移民群体、远离母国、与母国的亲缘关系、殖民
地与宗主国的政治关系(认同与反抗)、大规模移民得以可能的航运技术和印刷资本主义的诞生,以及由
这些基础条件而产生出的情感特征。如果说前三项是所有移民群体共同具备的条件,那么,后三项却因
时、因地而发生差异。这也是为什么有些移民群体会转化为新的民族,而另一些移民群体——即便在没有
完全同化于当地社群的条件下——却逐渐疏离于对母国的认同,其族裔认同始终不会上升为独立的民族认
同。在《民族主义研究的新困惑》的末尾,安德森简略地提及了美国《独立宣言》中的修辞,实际上是将
殖民地移民群体对宗主国的反抗和模仿,以及这种反抗和模仿中所包含的屈辱感,作为远程民族主义的政
治特征。
正是从这里,安德森转向了对于远程民族主义的新变化以及东半球移民群体的观察。较之18—19世
纪,当代移民的图景更加复杂,除了从中心地区向边缘区域的移民之外,20世纪移民活动的特征之一是从
边缘区域向中心区域的转移,其民族主义也增加了一些新的特色。安德森举出了在美国的印度锡克教后裔
通过网络参与母国的激进民族主义政治及其心理特征等例子,可惜没有就此展开论述。他聚焦的是东南亚
华人、尤其是泰国华人的认同和情感特征。安德森对于泰国的研究起始于他被禁止进入印度尼西亚之后,1974年他首度进入泰国学习泰语,并与一些卷入反对泰国军事政权的知识分子交往。因此,他的第二次演
讲也可以说是他长期观察的果实。在演讲展开之前,安德森首先声明对于中国的了解不够,有关东南亚华
人的讨论并不是成熟的或完成的作品,但他还是从泰国政治的动荡、尤其是红衫军与黄衫军的斗争及其认
同政治出发,展开其分析。我们可以将他的历史叙述简略地归纳如下:泰国拥有从不同历史时期移居该地
的“华人”,他们分属客家人(红衫军、他信)、福建人(阿披实、黄衫军)、海南人(素帖及其反政府群
体)、潮州人(国王)等等;华人群体由于地域背景、移民时间、阶级或阶层关系等等而发生各种分化组
合。在当前的政治运动中,华人的政治认同与其祖先在母国的出生地有着密切的关系。但他们之间能否构
成一种“华人认同”甚或能否被称为“华人”都是大有疑问的。换句话说,移民及移民群体的形成并不必然产生
远程民族主义,若无其他政治条件,族裔认同或地方认同将无法上升为民族认同,族裔或地方性共同体也
因此不可能上升为政治共同体,亦即民族。这也从相反的方向,说明了民族主义与民族的关系,即如果没
有一种有力的民族主义,即便存在语言、宗教(文化)和族群等社会要素,民族也不可能形成。
在演讲中,安德森主要根据一些片段的笔记展开分析,并未形成完整的论述,但这篇演讲显然提示了
他的思考新方向。在研究东南亚地区的民族主义问题时,安德森一再遭遇海外华人问题。例如,在写作
《比较的幽灵:民族主义、东南亚与世界》一书中有关菲律宾的章节时,他专门研究了“第一个菲律宾
人”何塞·黎刹。他在说明黎刹的身份时,先说他是诗人、小说家、眼科专家、历史学家、医生、好辩的随笔
作家、道德家和政治幻想家,随即提及他的血统,即“1861年他出生于一个混合了华人、日本人、西班牙人和他加禄人血统的富有之家”。但是,菲律宾民族主义并不是一种类似北美的远程民族主义。实际上,安德
森对于菲律宾的研究深受科拉松·阿基诺的“人民革命”的激励,而科拉松·阿基诺也有着华人血统。在安德森
撰写这一节时,他的弟弟、杰出的左翼历史学家佩里·安德森给我写信,请我帮他的哥哥查找一下有无黎刹
著名绝命诗的中文译本。我先前知道鲁迅曾经提及过黎刹及其绝命诗,但经过反复查核,竟然发现该诗有
17种中文译文(大多并不完整),其中最早的、也是不完整的译文的译者是梁启超。我至今不知道梁启超
是从哪种语言将这首诗歌翻译为中文的。没有证据表明梁启超懂西班牙语,他或许是通过日语翻译,但对
比日本译文,梁启超的译笔似乎更加准确。或许,梁启超与菲律宾华侨有关系?这些被称为“东南亚华
人”的人并不是一个作为政治共同体的东南亚华人群体的成员,毋宁说是华人移民分布于各地的后裔,他们
的血缘、地缘关系与北美独立运动迥然有别,并没有出现通过对母国的反抗而产生的政治民族主义。菲律
宾华人后裔的民族主义是在抵抗西班牙殖民主义的过程中形成的,它既不是通过认同母国也不是通过反抗
母国而产生的政治认同。与此略相类似,泰国华人的认同也并未构成远程民族主义的案例。这些例子似乎
从另一方面重复了《想象的共同体》的基本论点:民族—国家不是由宗教、语言、族群等社会要素决定
的,恰恰相反,它是想象的产物。问题
那么,安德森对于民族主义研究新困惑的解说是否完满地或恰当地回应了三十年来围绕或未必围绕他
的早期著作的争议和质疑呢?在回答这一问题之前,或许可以简略地分析对于《想象的共同体》一书的主
要质疑是否构成了真正的质疑。由于讨论纷杂,这里只能检讨两种在我看来较为重要的论点。第一种质疑
可以帕尔塔·查特吉(Partha Chatterjee)为代表。查特吉承认“在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问题的看法上,安德森
的主要贡献是他强调在研究民族运动时,应将意识形态对民族的创造作为中心问题。在这方面他还强调了
现代语言团体对民族的社会创造过程”。但他接着批评说:“安德森不再用这一过程中所固有的各种各样自
相矛盾的政治可能性,而是用社会学决定论来结束他的理论。”就像盖尔纳用“工业社会”的要求论述民族的
起源,安德森用印刷资本主义这一更为精巧的范畴描述民族形成的动态过程。他们都看出了“第三世界民族
主义中深刻的‘模式’特征” [2] 。在安德森的叙述中,尽管民族主义的第一波源自北美,但其模式却来自欧洲
——民族语言共同体、法国大革命提供的政治价值、与工业革命相互适应的政治模式等等。在查特吉看
来,“亚洲和非洲民族主义想象的最有力也最具创造性的部分不是对于西方推销的民族共同体模式的认同,而是对于与这一‘模式’的差异的探求。我们怎么可能忽略这种对于另类模式的寻求而免于将反抗殖民主义的
民族主义化约为一种滑稽的模仿?” [3] 查特吉认为抵抗殖民主义的民族主义包含了两个不同的方面,即物
质的方面和精神的方面。事实上,对于殖民主义的抵抗早在民族运动对于帝国的抵抗之前就已经开始,它
对于西方物质方面的模仿(如同“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所表明的)是与其在精神上寻求自主、独立、区
别于西方模式相互一致的。对于西方的物质模仿越成功,越需要在精神上获取主权性,因此,精神的领域
也是主权的领域,而后者的目标就是确立一个非西方的领域。也只有从这种反殖民民族主义对于差异的寻
求出发,才能发现殖民地民族主义文化(包括文学)的创造性,而不致将这种具有独特性的文学和文化实
践化约为一般的印刷资本主义,即一种在非西方地区进行复制的欧洲模式。
对于安德森的理论的第二种质疑也可以包含对于查特吉的“物质精神”二分论的修订。在查特吉所讨论
的“物质的”或“外在的”领域,如国家机器、科学技术等等方面,是否也存在寻求差异的运动呢?安德森讨论
过中国与苏联的“官方的民族主义”,他甚至也将1979年中越冲突的爆发归结为同一范畴,而拒绝讨论中国
革命曾经提供的既不同于西方路径也并非对苏联模式的简单复制的道路。在具有长久统一的国家传统、以
农业为主又同时拥有久远的独特城市经验、丰富的内外关系模式和半殖民条件的社会里,所有对于外来概
念和模式的运用都内在地包含了差异和独特性。例如,在人民战争条件下,阶级、政党、苏维埃、军队、民族等等范畴不断被使用和复制,但其内涵和相互关系早已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中国与周边国家之间间、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既包含了民族国家间关系的内容,又不可避免地呈现出传统的和不同于欧洲民族
主义的关系及其内容,如政党关系的内容。这种变化并不只是由于历史条件的差异而自然发生的,而是革
命和改良力量根据具体条件进行转化和创造的结果。这一过程甚至对后革命时代的政治共同体也仍然具有
重要的影响力。如果将中国、印度和其他亚非国家的民族运动置于全球民族主义运动和新的区域跨区域关
系的图谱中,民族主义研究中的欧洲模式在多大程度上将被修订甚至彻底改观?
《想象的共同体》将作为政治共同体的民族视为一种晚近的现象,而非宗教、语言、种族等等社会要
素的产物,从而松动了19世纪族裔民族主义所建立起来的民族主义知识,但这一松动同时也被政治分离主
义者用于对分离型民族主义的正当性论证——他们终于找到了一种摆脱种族、语言、宗教、文化的共同性
而“想象”民族的理论。2001年5—6月间,安德森在《新左翼评论》(New Left Review )发表了题为《西方
民族主义与东方民族主义》(Western Nationalism and East Nationalism)一文,“从台湾的角度反思亚欧地区
克里奥尔式的官方的、语言的与远程的民族主义,以及它们对于中国的含义。这里是否存在东方与西方之
间的重大差别?” [4] 这篇文章很可能是在他前一年的台湾演讲的基础上改定的。在广阔的世界范围内,安
德森重新描述各种不同的民族主义,并将“台湾民族主义”解释为最初形态的民族主义的当代版本,即海外
定居群体从帝制母国分离出去的运动。换句话说,他将台湾的分离运动与《想象的共同体》中描述的18世
纪的美国独立运动和19世纪初期拉丁美洲的民族运动放在同一脉络和类型下观察。在他的远程民族主义描
述中,共同的族群、共同的语言、共同的文化都不再是政治共同体的理由,地理的和政治的分离本身已经
为新的民族提供了依据。2000—2001年正值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和首轮政党轮替,分离主义认同政治成为
笼罩台湾政治、形成大众动员的主导氛围。这篇文章对于海外华人、台湾以及主要由华人创建的、区别于
中国的政治共同体新加坡的认同政治的分析,连同《想象的共同体》一书的建构主义之民族观,为台湾分
离主义知识分子提供了理论“灵感”。安德森将许多精力花在用各种细节解构民族与族裔之间的同构关系,以致他的一些有心的或无心的读者——甚至其本人——在分析当代民族主义现象时忘却了他的民族主义分类的政治出发点,即对抵抗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民族主义与官方民族主义的政治区分。从方法论的角度
看,这很可能与他侧重于民族主义的类型分析,而忽略深入的历史脉络的探索有关,其结果是他的颇具新
意的远程民族主义概念无法用于对不同的民族主义或分离主义的政治分析。正如他的弟弟佩里·安德森所
说,台湾与大陆的分离始终源于帝国主义的行动,而非针对帝国的反抗。 [5] 50年的日本殖民历史、战后至
今未脱的美国被保护地地位、冷战时代西方势力遏制社会主义中国的桥头堡、后冷战时代保障美国霸权地
位、遏制中国大陆的新阵地,所有这一切才是台湾分离主义的想象政治的物质基础和先决条件。这是霸权
构造下的分离主义政治,而非抵抗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独立运动。
安德森将意识形态对民族的创造作为中心问题,这一洞见对我们理解当代民族主义和民族分离主义仍
然具有重要的启发。正是意识形态促成相同族群、语言和文化的社会走向分离主义,也正是意识形态危机
成为新型民族主义的动力及契机。然而,相较于社会革命的视角,安德森显然更乐意从民族主义的视角去
观察现代历史。这是他的研究课题决定的,但也是他在两者之间进行辨析的过程中产生的方法。在他的眼
中,胡志明及其领导的越南革命主要是一场民族运动,而非社会革命运动。越南—柬埔寨战争、中国—越
南冲突更是社会主义国家深陷民族主义政治的范例。但是,离开社会革命的视野,亚非地区反帝反殖运动
的具体内涵、政治逻辑和不同命运都难以得到说明。查特吉批评安德森的民族主义理论将殖民地民族主义
视为纯粹衍生性的话语或对西方民族模式的复制,从而忽略了抵抗性民族主义所包含的创造性,这一点也
可以部分地解释他对中国革命及其创造性的忽略。此外,安德森对于作为政治共同体之民族的界定是通过
与非政治共同体的宗教和家族等区别而产生的,那么,如何解释那些并不依赖宗教或至少一神教立国的大
型政治共同体与民族的关系?如何解释王朝制时间与直线时间之间的关系?如何解释现代中国对于长久的
郡县制国家及其文化政治传统的“复制”(也是再造)?在包括《想象的共同体》在内的民族主义研究中,王朝制国家与现代民族国家之间的差异正是第三世界民族主义“衍生性”的证明,即公民权和人民主权都是
对法国革命提供的政治价值和制度模式的借鉴和模仿,但上述历史差异很可能需要另一种理论框架,以便
将民族主义置于新的世界历史的视野之中给予解释。在中国历史中,那种既内在于王朝又超越于具体王朝
的“中国”认同远早于近代民族运动,由这一政治共同体及其相互关系所塑造的区域秩序是否意味着需要找
到新的解释起点?走笔至此,我忽而想到:如果再度将这些问题向安德森提出,他会如何回答呢?我的猜
想是:他依旧会回答说这些问题仍然是“经验性的”,但同时迫不及待地回到东南亚甚至中国的经验中再度
提出他的“新困惑”。
得到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过世的消息后,我致信佩里·安德森表示哀悼和慰问。我在信中告诉佩里,中国
的报刊对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过世和他的生平道路、学术理论有很多报道,这也一定会激发许多研究者
重读其著作的愿望。如今,他的主要著作均有了中文本,或许纪念他的最好方法就是在重新阅读中激发新
的讨论。佩里回信说:是的,对于他的兄长而言,这是最好的纪念。果不其然,上海人民出版社决定重版
《想象的共同体》,潘丹榕编辑嘱咐我为新版写点文字,我因此建议将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清华的两次演
讲作为附录同时刊出,因为这是他对民族主义研究中新困惑的最后解说。我的这篇短文说不上是对他的理
论的全面分析,权作对他73年后重回出生地的纪念吧。
2016年5月11日星期三
————————————————————
注释:
[1] [英]厄内斯特·盖尔纳:《民族与民族主义》,韩红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版,第74页。
[2] [印度]帕尔塔·查特吉:《民族主义思想与殖民地世界:一种衍生的话语?》,范慕尤、杨曦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7年版,第
32页。
[3] Partha Chatterjee,“Whose Imagined Communities?”The Nation and Its Fragments:Colonial and Post-Colonial Historie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3,p.216.
[4] Benedict Anderson:“Western Nationalism and Eastern Nationalism”,New Left Review 9,May-June 2001,31—42.
[5] Perry Anderson:“Stand-Off in Taiwan,”London Review of Books ,Vol.26,Number 11,3 June 2004,12—17.认同的重量:《想象的共同体》 [1] 导读
在这个世界中,我们公正地表现自我;我们尚未形成一致的思想境界,因为这种境界需要直
言的批评、真实的创新以及真正的努力,而我们既未曾创造也未曾经历过这一切。 [2]
——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Said)同情弱小民族的“入戏的观众”
本尼迪克特·R.奥戈尔曼·安德森(Benedict R.O'Gorman Anderson)是一个与异乡和流浪有着深刻宿
缘的人。某种流离失所的因子似乎早早就流淌在爱尔兰裔的安德森家的血液中了,而这样的流离失所又和
大英帝国的盛衰始终相随。 [3] 他的祖父是大英帝国的高级军官,但祖母却来自一个活跃于爱尔兰民族运动
的奥戈尔曼家族(the O'Gormans)。祖父在19世纪后期被派驻槟榔屿(Penang),他的父亲就出生于这个
英属马来亚的殖民地上。在第一年剑桥大学的入学考试失败以后,他的父亲加入了在中国的帝国海关
(Imperial Maritime Customs in China),此后在中国居住将近三十年,成为一个中文流利,事事好奇,十分
热爱中国文化的人。1936年,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出生于云南省昆明市。和大多数其他住在中国的爱尔兰家
庭的小孩不同的是,本尼迪克特和他那位日后同享大名的兄弟——被著名的左派文学理论家特里·伊格尔顿
(Terry Eagleton)誉为“不列颠最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的历史社会学家,《新左翼评论》(New Left
Review )的主编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 [4] ——从小就在一个充满中国风味的家庭环境里成长,而
且他们的保姆还是一位越南女孩。
1941年,安德森家为躲避日益升级的中日战争而举家迁离中国,打算经由美国返回爱尔兰故乡。不料
这个返乡之旅的计划却因太平洋战争的爆发而受阻,安德森家只得暂居美国,等待战争结束。老安德森在
英国驻美情报单位找到了一个中文翻译的职位,本尼迪克特就随着父亲的工作,在加州、丹佛等地开始了
他最初的正式教育。日后,他曾这样深刻地描述这段早期的“流亡”经历的影响:“从那里开始了一连串的疏
离(estrangements)——在美国学校里的英国口音,后来在爱尔兰学校里的美国口音,在英国学校里的爱尔
兰腔——而这一连串的疏离经历使得语言对我而言成为一种获益良多的机会(beneficially problematic)。”
[5]
战争结束,安德森家终于回到爱尔兰,但本尼迪克特从1947年起就在英格兰受教育。1953年,他进入
剑桥大学,主修西方古典研究(Classics Study)与英法文学,奠定了良好的西方语言基础。 [6] 尽管小他两
岁的兄弟佩里在1956年进入牛津大学就读之后很快就成为英国20世纪50年代后期新左派运动的干将,但本
尼迪克特在此时却仍旧只是一个“从未有过任何严肃的政治思想”的20岁青年而已。 [7] 1956年11月的一天,当安德森在剑桥的街道上闲逛时,目睹了一个正在演说批评英法等国入侵苏伊士运河的印度人被一群上流
社会的英国学生攻击,而当他试图阻止这些学生的暴行时,却也和那个印度人同样遭到殴打,连眼镜都被
打落了。这场攻击行动结束后,这群英国学生列队唱起了英国国歌《天佑吾皇》。日后安德森自述当时
他“愤怒至头晕目眩”。这一事件成了安德森的政治启蒙——一种对“帝国的政治”的启蒙,而更重要的是,在
这场政治启蒙的仪式中,他和一个“被殖民者”站在一起接受了帝国的羞辱。 [8] 这个青年时期的经历,深深
影响了他日后批判帝国主义,同情殖民地民族主义的认知与道德立场。
1957年,印尼发生内战,美国中央情报局介入其中。这个新闻事件,立即吸引了刚刚受到“帝国主义压
迫”的政治启蒙的青年安德森的注意。好奇心与新生的政治关怀,促使他在1958年远赴美国的康乃尔大学,投入乔治·卡欣(George Kahin)门下专攻印尼研究。卡欣是美国印尼研究的先驱,“康乃尔现代印尼研究计
划”(Cornell Modern Indonesia Project)的创始人。他聚集了一批顶尖的人才到康乃尔,使这所大学成为美
国东南亚研究的重镇,至今仍声誉不衰。卡欣和其领导下的这批精英——或许我们可以将之称为美国东南
亚研究的“康乃尔学派”——将年轻的安德森引进了一个令人着迷的印尼研究的世界:除了卡欣对他在东南
亚民族主义政治的启蒙之外,第一本印尼文—英文辞典的编纂者、语言学家约翰·埃科尔斯(John Echols)
向他开启了印尼文学之门,而印尼语言文化学者克莱尔·霍尔特(Claire Holt)则带领他认识了独立前的印
尼、爪哇文化,以及荷兰的殖民研究。 [9]
然而对安德森而言,卡欣不但是经师,也是导师(mentor)。作为一个古典意义下的知识分子,卡欣
长期批评战后美国的霸权外交政策,因此,在20世纪50年代曾一度被国务院没收护照。60年代越战加剧,他不但参与反战示威,也将研究重点从印尼扩大到印度支那。这种驱策知识追求的强烈道德关怀,以及对
自己国家恨铁不成钢的爱国主义(patriotism),深深感动了正在成长期的青年安德森。他不仅从他的老师
身上“学到了政治与学术的不可分离” [10] ,也强烈体会到爱国主义的高贵、可敬与合理。日后他在《想象
的共同体》当中所透露的对民族主义相对较积极的态度,除了源于对殖民地民族主义的同情之外,也来自
康乃尔师门的道德熏陶。从1961年到1964年间,安德森在雅加达进行博士论文的田野研究。这段时间,恰好是苏加诺
(Sukarno)总统的威权民粹政权开始衰落前的全盛时期,安德森因此见证到了一个高度政治化、混乱而充
满活力,而且相当自由的印尼的社会与政治。苏加诺那种极具魅力的民粹作风与充满煽动力的反西方民族
主义,使他印象特别深刻。1963年,当苏加诺总统对英国建立马来西亚联邦大发雷霆之际,一群暴民烧毁
了吉隆坡的英国大使馆。当时已经有点“本土化”的安德森刚好住在事发现场附近,他“穿着T恤和纱笼裙,靠在篱笆上”,以一种“爱尔兰人的幸灾乐祸”(Irish Schadenfreude),冷眼旁观这栋烈焰中的建筑。当一位
他认识的暴民领袖特地过来要他不必惊慌时,安德森惊觉原来他根本就不以为自己身在险境。 [11] 也许,在安德森的眼中,印尼人以怒火焚烧帝国领事馆的景象在不知不觉中已经和他在剑桥经历过的那幕小小
的“反帝”行动重叠在一起了吧。
然而安德森绝不只是一个观众而已——他是一个如雷蒙·阿隆(Raymond Aron)一般具有强烈现实关怀
的“入戏的观众”(spectateur engage)。 [12] 1964年,安德森返回美国,当时林登·约翰逊刚连任总统,而美
国国内已逐步走入反对越战的动荡之中。1965年,美国开始大规模轰炸越南,安德森跟随恩师卡欣投入到
反战运动之中。当年9月,印尼军人翁东(Untung)将军发动政变失败,苏哈托(Suharto)将军趁势而起,捏造说翁东为印尼共产党所指使,并大肆屠杀左翼人士。此后苏哈托逐渐架空苏加诺,掌握印尼实权。
1966年1月,安德森与其他两位印尼研究同僚合作完成了一篇分析此次政变的论文。这篇后来被称为“康乃
尔文件”(Cornell Paper)的论文最初只在印尼研究的小圈子内流通,但当年春天却意外流入媒体,引起轩
然大波。由于该文指出翁东将军的流产政变根本与共产党无关,这个论点使苏哈托屠杀左派的行动完全失
去正当性,也同时直接挑战了因此政变而崛起的苏哈托政权的合法性,因此成为安德森在日后(从1972年
到1999年)长达27年被印尼当局禁止入境的主要原因。
1967年,安德森完成其博士论文《革命时期的爪哇》(Java in a Time of Revolution )。 [13] 从1967年
到1972年被驱逐出境为止,他还曾三度回到印尼。在这段时间,由祖国爱尔兰独立斗争的斑斑血史所产生
的同情心,使安德森开始留意越南,并且将越南和印尼这两个同样历经血腥的民族解放斗争才获独立的东
南亚国家联系起来。他极端厌恶华府谈论亚非地区的“低度开发国家”时那种傲慢的口气,也十分同情苏加
诺在面临国家经济危机时,因不满美国的高傲态度而怒喊“Go to hell with your aid!”(去你的援助!)拒绝
美援的处境。安德森日后自述,也许是出于一种“逆转的东方主义”(inverted Orientalism),他和当时大多
数东南亚研究专家都相当同情该地区的民族主义。从一开始,他就认定胡志明与美国的对抗,其根源不是
社会主义,而是民族主义,而苏加诺虽然远不及胡志明,但他被一个由美国撑腰的残酷军事政权推翻,却
使他轻易地“获得了犹如(匈牙利的)柯许特(Kossuth)般的(民族英雄的)悲怆”。 [14]
1972年后,由于不能再进入印尼,安德森逐渐将目光转向其他东南亚国家。1973年,泰国知识分子开
展了一场反军事政权的运动,安德森的数位泰国友人也卷入这场运动之中。于是他在1974年来到泰国,开
始学习泰国的语言,研究当地的文化与政治,并且见证这段激动人心的“曼谷之春”。1979年,美国国会邀
请他为印尼占领下的东帝汶情势作证,由于已被印尼政府“流放”,安德森得以无所顾忌地畅所欲言。以此
次国会作证为契机,他又开始和流亡的东帝汶独立运动人士[他称之为东帝汶的“爱国者们”(patriots)]
交往,并因此涉入全球性的支援东帝汶的运动网络之中。延续当年写“康乃尔文件”那种以知识介入现实的
师门精神,安德森在涉及泰国与东帝汶事务之时,也针对性地写出了一些极具现实性的深刻分析的文字。
[15]
1986年,菲律宾的科拉松·阿基诺那激动的“人民革命”浪潮再次将安德森这个“入戏的观众”卷到这个群
岛之国。继泰国研究之后,他又开始学习塔加洛语和西班牙语,投入菲律宾研究的领域之中。然而此时他
已经不再只是一个热情的区域研究专家——如今他是已成当代民族主义研究经典的《想象的共同体》
(1983)这本书的作者了。“流放”的果实
直接促成他写作《想象的共同体》的原因是1978—1979年间爆发的中国、越南和柬埔寨之间的三角冲
突。这个历史事件令他提出了这个质问:为何民族主义的力量会强大到让三个“国际主义”的社会主义国家
不惜兵戎相见?然而为他完成写作的思想准备的是,1972年被苏哈托“流放”之后他长时间在知识上的尝
试、转变与酝酿。
根据安德森的自述,苏哈托政权对他的“流放”虽然使他无法一如既往地深入印尼社会进行田野研究,却也给他带来几个意想不到的好处。首先,印尼研究的暂时中止使他有机会将目光转移到另一个东南亚国
家——泰国,而泰国这个未经殖民的君主立宪国几乎在每一方面都和经过长期殖民才独立的共和制国家印
尼形成强烈的对比。这两个“个案”(cases)的出现,使原本只埋首于印尼的安德森被迫开始作比较性的思
考,而这样的比较性思考,逐渐使他觉得有必要发展一个架构来理解个案之间的异同。其次,由于已经无
法从事田野的印尼研究,安德森被迫将注意力转移到文字资料,尤其是印尼文学之上。通过研读印尼文
学,特别是伟大的印尼小说家普拉莫底亚·阿南达·托尔(Pramoedya Ananta Toer)的作品,他开始注意到文
学如何可能和“政治的想象”(political imagination)发生关联,以及这个关联中蕴涵的丰富的理论可能。
[16] 就某种意义而言,苏哈托在1972年粗暴地将安德森驱逐出境,反而将他从单一个案的、深陷于具体细
节的“微观式”研究中解放出来,使他得以发展出一个比较的、理论性的以及较宏观的视野。
伟大的知识成就当然绝不会只得之于独裁者的愚昧而已。在1972年以后这段从田野被“放逐”回学院的
时期中,另一个事件更深刻地在安德森的思想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痕,使“比较史”(comparative
history)坚定不移地纳入他的视野当中,这就是来自他的弟弟佩里·安德森及其周边的新左评论集团知识分
子对他的影响。佩里在1974年出版了他的历史社会学杰作两部曲:《从古代通往封建主义之路》(Passages
from Antiquity to Feudalism )和《绝对主义国家的系谱》(Lineages of the Absolutist States )。这两部作品就
时间而言上下涵盖近两千年,就空间而言同时处理欧洲与欧洲以外地区不同社会的变迁,因此本尼迪克特·
安德森称之为“严谨、细致的比较历史研究的模范”确实是当之无愧的。佩里这两部书展现的比较史视野与
社会学理论深度对本尼迪克特有巨大的冲击。佩里这种理论的、比较的和全球性的视野当然也主导了他所
主编的《新左评论》的风格。他所聚集的一批英国的杰出左翼知识分子,如汤姆·奈伦(Tom Nairn)、安东
尼·巴纳特(Anthony Barnett)、朱迪思·赫林(Judith Herrin)等,所写的一篇篇探讨不同国家地区的论文在
评论上并列,创造出一种鲜明的、广阔的国际性视野。与这批博学之士长久相处之余,连严格来说并不那
么左的本尼迪克特也受到鼓舞,希望经由一个“大体上为马克思主义的视角,使我的印尼能够加入世界”。
[17]
融比较史、历史社会学、文本分析与人类学于一炉,安德森最终果然经由《想象的共同体》,把“他的
印尼”送进了“世界”。《想象的共同体》的论证
到底民族(nation)和民族主义(nationalism)是什么?它们的本质是什么?它们在历史上是怎样出现
的,又经历了怎样的变迁?为何它们能够在今天掌握如此深刻的情感上的正当性?在安德森眼中,“民族与
民族主义”的问题构成了支配20世纪的两个重要思潮——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主义——理论的共同缺陷。想要
有效解答这难以捉摸的“民族之谜”,必须扬弃旧教条,以哥白尼精神寻找新的理论典范。安德森写作《想
象的共同体》的目的,就是要提出一个解释上述这些关于民族与民族主义问题的新理论典范。
安德森的研究起点是将民族、民族属性与民族主义视为一种“特殊的文化的人造物”。他在一开头就以
简洁的文字勾勒出本书的论点:
这些人造物之所以在18世纪末被创造出来,其实是从种种各自独立的历史力量复杂的“交
汇”过程中自发地萃取提炼出来的一个结果;然而,一旦被创造出来,它们就会变得“模式化”,在
深浅不一的自觉状态下,它们可以被移植到许多形形色色的社会领域,可以吸纳同样多形形色色
的各种政治和意识形态组合,也可以被这些力量吸收。
在这凝练的文字背后,隐藏着一个非常复杂而细致的论证,以及一幅纵横古今、繁复巨大的历史图
像。
在正式进入论证之前,安德森先为“民族”这个斯芬克斯(sphinx)式的概念提出了一个充满创意的定
义:“它是一种想象的政治共同体——并且,它是被想象为本质上是有限的,同时也享有主权的共同
体。”这个主观主义的定义聪明地回避了寻找民族的“客观特征”的障碍,直指集体认同的“认
知”(cognitive)面向——“想象”不是“捏造”,而是形成任何群体认同所不可或缺的认知过程(cognitive
process),因此“想象的共同体”这个名称指涉的不是什么“虚假意识”的产物,而是一种社会心理学上的“社
会事实”(le fait social)。这个主观认知主义的定义界定了安德森以后整个论证的基调,也就是要探究“民
族”这种特殊的政治想象(认知)成为可能的条件与历史过程。
安德森认为“民族”本质上是一种现代的(modern)想象形式——它源于人类意识在步入现代性
(modernity)过程当中的一次深刻变化。使这种想象成为可能的是两个重要的历史条件。首先是认识论上
的先决条件(epistemological precondition),亦即中世纪以来“人们理解世界的方式”所发生的“根本的变
化”。这种人类意识的变化表现在世界性宗教共同体、王朝以及神谕式的时间观念的没落。只有这三者构成
的“神圣的、层级的、与时间终始的同时性”旧世界观在人类心灵中丧失了霸权地位,人们才有可能开始想
象“民族”这种“世俗的、水平的、横向的”共同体。安德森借用沃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的“同质
的、空洞的时间”(homogenous,empty time)概念来描述新的时间观,并指出18世纪初兴起的两种想象形
式——小说与报纸——“为‘重现’(re-presenting)民族这种想象的共同体提供了技术的手段”,因为它们的
叙述结构呈现出“一个社会学的有机体遵循时历规定之节奏,穿越同质而空洞的时间的想法”,而这恰好是
民族这个“被设想成在历史之中稳定地向下(或向上)运动的坚实的共同体”的准确类比。换言之,对安德
森而言,“民族”这个“想象的共同体”最初而且最主要是通过文字(阅读)来想象的。但与过去在认识论上的
决裂本身不足以说明在诸多可能类型的“水平—世俗”共同体中,为何“民族”会脱颖而出。要“想象民族”,还
需要另一个社会结构上的先决条件,也就是“资本主义、印刷科技与人类语言宿命的多样性这三者的重
合”。这三个因素之间“半偶然的,但却富有爆炸性的相互作用”促成了拉丁文的没落与方言性的“印刷语
言”的兴起,而以个别的印刷方言为基础形成的特殊主义的方言—世俗语言共同体,就是后来“民族”的原
型。
认识论与社会结构上的条件,酝酿了民族共同体的原型,也为现代民族搭好了舞台。以这两个共同的
基本先决条件为论证出发点,安德森接着一步一步地建构了一个关于民族主义如何从美洲最先发生,再一
波一波向欧洲、亚非等地逐步扩散的历史过程的扩散式论证(diffusionist argument)——一种前后关联,但
每一波都必须另作独立解释的复杂论证。
西方主流学界向来以西欧为民族主义的发源地,安德森却讥之为“地方主义”之见,主张18世纪末、19
世纪初在南北美洲的殖民地独立运动才是“第一波”的民族主义。安德森认为,美洲的殖民母国(英国、西
班牙和葡萄牙)对美洲殖民地移民的制度性歧视,使当地欧裔移民(creoles)的社会与政治流动被限定在殖民地的范围之内。他引用人类学家维克多·特纳(Victor Turner)的理论,指出这种歧视与殖民地边界的
重合,为殖民地的欧裔移民创造了一种“受到束缚的朝圣之旅”(cramped pilgrimage)的共同经验——被限
定在个别殖民地的共同领域内体验这种被母国歧视的“旅伴”们于是开始将殖民地想象成他们的祖国,将殖
民地住民想象成他们的“民族”。
“第一波”所创造的“美洲模式”,是一种不以语言为要素的民族主义;然而受到“美洲模式”感染与启发而
在1820年以后出现于欧洲的“第二波”民族主义,却是一种群众性的语言民族主义。安德森对此提出了一
个“多重因素汇聚”(conjunctural)的解释。一方面,美洲(和法国)革命将民族独立与共和革命的模型扩
散到全欧各地。另一方面,16世纪欧洲向全球扩张与“地理大发现”促成了文化多元论在欧洲兴起,而这又
促成了拉丁文之类的古老神圣语言的继续没落。在这场历史运动中,以方言为基础的民族印刷语言和民族
语言的出版业随着(民族)语言学革命趁势而起,而“阅读阶级”则适时出现,成为民族语言出版品的消费
者。由此,民族独立、共和革命与民族语言理念的结合在19世纪前半叶的欧洲孕育了一波民粹主义性格强
烈的语言民族主义。安德森特别提出了“盗版”(piration)——自觉的模仿——的概念来衔接先后出现的民
族主义:作为“第二波”,19世纪欧洲的群众性民族主义因为已有先前美洲与法国的独立民族国家的模型可
供“盗版”,因此在思想和行动上都比“第一波”要更有自觉意识。
“第二波”民族主义在欧洲掀起的滔天巨浪,撞击统治阶级古堡高耸的石墙后所反弹涌现的,就是“第三
波”的民族主义——也就是19世纪中叶以降在欧洲内部出现的所谓“官方民族主义”(official nationalism)。
安德森指出,“官方民族主义”其实是欧洲各王室对第二波群众性民族主义的反动——无力抵挡高涨的民族
主义浪潮的旧统治阶级为了避免被群众力量颠覆,于是干脆收编民族主义原则,并使之与旧的“王朝”原则
结合的一种马基雅维利式的先期(anticipatory)策略。原本只有横向联姻,缺乏明确民族属性的欧洲各王室
竞相“归化”民族,并由此掌握对“民族想象”的诠释权,然后通过由上而下的同化工程,控制群众效忠,巩固
王朝权位。“官方民族主义”的原型是沙皇亚历山大三世时代所推行的“俄罗斯化政策”(Russification),而
反动的马札尔乡绅在1848年革命后推行的马札尔化政策也是一例。另一方面,这些同时也是帝国的王朝又
将这个统治策略应用到海外异民族的殖民地,使被殖民者效忠。最典型的例子是大英帝国殖民官僚马考莱
(Macaulay)在印度推行的英国化政策。这个政策被带入非欧洲地区后,又被幸免于直接征服的少数区域
的统治阶级模仿,如日本明治维新的对内的“官方民族主义”与对殖民地的日本化政策,以及泰国的拉玛六
世的排华民族主义等。
如果“第三波”的“官方民族主义”是对第二波的群众民族主义的反动与模仿,那么“最后一波”,也就是第
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亚非殖民地民族主义,则是对“官方民族主义”的另一面——帝国主义——的反应,以
及对先前百年间先后出现的三波民族主义经验的模仿与“盗版”。安德森从他最熟悉的印尼历史抽绎出一
个“殖民地民族主义”(colonial nationalism)发生的一般性论证。首先,帝国主义的殖民政府利用殖民地
的“俄罗斯化”政策培养了一批通晓双语的殖民地精英。通过共同殖民教育,这些来自不同族群背景的人拥
有了共通的语言,并且有机会接触到欧洲的历史,包括百年来的民族主义的思想、语汇和行动模式。这些
双语精英就是潜在的最初的殖民地民族主义者。另一方面,歧视性的殖民地行政体系与教育体系同时将殖
民地民众的社会政治流动限定在殖民地的范围之内。这个和早期美洲经验类似的“受到束缚的朝圣之旅”,为被殖民者创造了想象民族的领土基础——和18世纪美洲的欧裔移民一样,在20世纪的亚洲和非洲被殖民
者的眼中,殖民地的边界也终于成为“民族”的边界。安德森同时也分析了因条件不足而未能产生“民族想
象”的法属西非和印度支那这两个殖民地,作为反面的比较个案。然而他也提醒我们“最后一波”民族主义的
特征相当复杂,因为它们出现于世界史之中……人们能够以较此前要更复杂得多的方式来“模塑”民族的时
期——它们不仅同时继承了多元的思想与行动可能,也同时继承了前人的进步与反动。
如此,安德森完成了他关于民族主义起源和散布的复杂论证:民族主义以一种和资本主义发展过程类
似的“不平均与合并的发展”(uneven and combined development)方式 [18] ,从美洲到欧洲再到亚非,一波
接着一波先后涌现;它们既属同一场历史巨浪,又相互激荡,各擅胜场。然而为何“民族”竟会在人们心中
激发如此强烈的依恋之情,促使他们前仆后继为之献身呢?安德森认为这是因为“民族”的想象能在人们心
中召唤出一种强烈的历史宿命感。从一开始,“民族”的想象就和种种个人无可选择的事物,如出生地、肤
色等密不可分。更有甚者,想象“民族”最重要的媒介是语言,而语言往往因其起源不易考证,更容易使这
种想象产生一种古老而“自然”的力量。无可选择、生来如此的“宿命”,使人们在“民族”的形象之中感受到一
种真正无私的大我与群体生命的存在。“民族”在人们心中所诱发的感情,主要是一种无私而尊贵的自我牺
牲。因此,安德森极力区分爱国主义与种族主义——对他而言,种族主义的根源不是“民族”的理念,而
是“阶级”的意识形态。在1991年出版的修订版《想象的共同体》当中,安德森在第一版的基础上又收录了两章具有附录性质
的论文。他在“人口调查、地图、博物馆”一章中提出了一个布迪厄式(Bourdieuian)论证 [19] ,试图补充
修正第七章(“最后一波”)关于殖民地民族主义的解释。他指出,殖民地官方民族主义的源头并非19世纪
欧洲王朝国家,而是殖民地政府对殖民地的想象。他举出三种制度(人口调查、地图与博物馆)说明殖民
地政府如何通过制度化(institutionalization)和符码化(codification)的过程将自身对殖民地的想象转移到
殖民地人民身上,并塑造了他们的自我想象。在“记忆与遗忘”一章中,他则探究了历史学与民族主义的密
切关系,指出民族历史的“叙述”(narrative)是建构民族想象不可或缺的一环。连接现代与后现代研究的桥梁
安德森的《想象的共同体》和已故的英国社会人类学家欧内斯特·盖尔纳(Ernest Gellner)所写的《民
族与民族主义》(Nations and Nationalism) 这两本同样在1983年出版的著作如今已是民族主义研究最重要
的两本经典之作了。盖尔纳在《民族与民族主义》中提出的那个标准社会学式的结构功能论论证,无疑已
为侧重实证主义的主流社会科学开出了一条建构民族主义的一般性理论之道。 [20] 那么,我们这本《想象
的共同体》在知识上的贡献又如何呢?
虽然不能在此详细探讨《想象的共同体》,但我们还是愿意提出几点初步的看法。首先,通过复杂而
细致的比较史和历史社会学方法,安德森在相对简短的篇幅内就建构出关于民族主义的一个非常有说服力
的一般性历史论证。 [21] 历史社会学和比较方法是研究民族主义最不可或缺的途径之一,因为几乎所有民
族主义的现象都同时涉及了历史纵深(如特定认同形成过程)以及跨国因素(如帝国主义扩张)。然而这
个研究途径的“操作”非常困难——研究者必须有能力在历史的精确性(accuracy)与理论的简约性
(parsimony)之间取得平衡,并且要有非常杰出的叙事(narrative)技巧,否则一不小心就会像盖尔纳一
样,掉进削(历史之)足适(理论之)履的陷阱之中,或者会变成像另一位多产的当代民族主义理论名家
安东尼·史密斯(Anthony Smith)的纯历史途径那种见树不见林的、琐碎的“民族分类学”。 [22] 安德森则避
开了这两个陷阱。他和兄弟佩里一样擅长运用既有历史研究的成果,并将之与理论性概念结合,然后以惊
人的叙事能力,编织成一个同时观照古今东西的“历史类型”或“因果论证”的文本——谁说社会科学家不需要
文学素养和文字能力?
更重要的是,他个人百科全书式的欧洲史素养与当代东南亚研究权威的背景,以及对东西方多种语言
的掌握能力,使他得以避免包括盖尔纳、史密斯以及霍布斯鲍姆在内的大多数西方民族主义理论家所犯的
那种欧洲中心主义的毛病。安德森的个案提醒我们,“扩散式论证”这种极度困难的论证方式固然不在话
下,即使是最根本的“比较研究”都需要具备相当的知识和语言的条件。
第二,安德森超越一般将民族主义当作一种单纯的政治现象的表层观点,将它与人类深层的意识与世
界观的变化结合起来。他将民族主义放在比政治史或政治思想史更广阔的“文化史”和“社会史”的脉络当中来
理解——民族主义因此不再只是一种意识形态或政治运动,而是一种更复杂深刻的文化现象(或者借用他
自己的话来说,一种“文化的人造物”)。这种颇具人类学精神——或者有点接近法国年鉴学派(Annales)
史学所谓“心态史”(histoire des mentalites)、“历史心理学”(psychologie historique)、“理念的社会
史”(histoire sociale desidees)或“社会—文化史”(histoire socio-culturelle) [23] ——的途径将我们对民族主
义的认识从“社会基础”或“政治动员”的层面扩展到对它的“文化根源”的探求之上。安德森不但没有像一般社
会科学家那样以实证主义式的傲慢(hubris)忽视人类追求“归属感”的需求(因为“不够科学”,或者因为那
是“虚假意识”或“病态”),反而直接面对这个真实而深刻的存在性问题,并在他的架构中为之赋予适当的诠
释与意义。正因如此,他对民族主义的解释就更能掌握到人类行动的深层动机。就某种意义而言,这个途
径间接肯定了德国哲学家赫德(Johann Gottfried von Herder)所说“乡愁是最高贵的痛苦”的箴言。 [24]
第三,《想象的共同体》的论证结合了多重的研究途径,同时兼顾文化与政治、意识与结构,开创了
丰富的研究可能性,因此被北欧学者斯坦·东尼生(Stein Tonnesson)和汉斯·安德洛夫(Hams Antlov)称
为“连接现代与后现代研究途径的桥梁” [25] 。就传统比较政治学与历史社会学的角度而言,这本书最重要
的贡献可能是它关于民族主义的各种“历史类型”以及“民族主义兴起的结构与制度条件”的论证。安德森
的“历史的”(historical)解释和盖尔纳所建构的“非历史的”(a-historical)结构功能论解释恰好成为当代民
族主义理论的两个重要而对立的典范。不过,相对于盖尔纳在主流政治学与政治社会学方面的巨大影响,《想象的共同体》可能对以文化与“意识”(consciousness)为研究对象的社会、人文学科的影响更大。安德
森对宗教、象征(symbol)与意义之诠释(interpretation of meanings)的强烈兴趣,以及“以本地人观
点”(from the native point of view)的倾向清晰地显露了这本书的“人类学精神”。他从现代小说的结构与叙
事技巧以及诗歌的语言中,探讨文学作品如何“重现”(represent)人类对民族共同体的想象的“前卫”尝试,对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兴起于英美文学界的,用解构主义理论、后殖民研究(postcolonial studies)与
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对文学与民族主义关系进行批判性研究的风潮有相当的影响。 [26] 而与文学理
论密切相关的是,安德森运用后现代主义历史哲学家海登·怀特(Hayden White)的理论来解析“民族认同建
构”与“历史叙述”的关系,以及他对殖民地政府(colonial state)角色的观察也在当代后现代主义或后殖民主义史学中留下了印痕。 [27] 最后,安德森所提出的“想象的共同体”的这个主观主义认知的定义对民族主
义的社会心理学研究途径也有不少启发作用。 [28]
当然,像《想象的共同体》这样深具野心的著作势必难逃知识界的检视与争议。例如,安德森视民族
为一种“现代”的想象以及政治与文化建构的产物,这使他在当代西方学界关于民族主义性质与起源时间
的“现代(建构)派对原初派”(modernistconstructivist vs.primordialist)论战中和盖尔纳同被归入“现代
派”,而受到“原初派”的批评。 [29] 而印度裔的美籍中国史专家,芝加哥大学的杜赞奇(Prasenjit Duara)教
授也以中国史为证提出一个与此论战相关的经验批评。杜赞奇认为,早在现代西方民族主义传入中国之
前,中国人早就有类似于“民族”的想象了;对中国而言,崭新的事物不是“民族”这个概念,而是西方的民族
国家体系。 [30] 另外,后殖民研究的先驱理论家夏特吉(Chatterjee)在他那本殖民地民族主义的名著《民
族主义思想和殖民地世界——一个衍生性的议论》(Nationalist Thought and the Colonial World:A
Derivative Discourse) 中则对《想象的共同体》提出了另一种批判:尽管安德森认识到“民族”是一种意识形
态的建构,但他竟然完全忽略了民族主义如何建构“民族”意识形态的具体政治过程。 [31]思想、记忆与认同
最后,对于为何在本书中舍近年来在台湾颇为流行的、“解构”味十足的“国族”一词不用,而将nation依
传统用语译为“民族”,笔者想稍作说明。首先,尽管在经验上nation的形成与“国家”(state)关系极为密
切,但nation一词最初是作为一种理念、政治想象(political vision)或意识形态而出现的,因此本来就带有
很明显的价值意味——从18世纪后半叶开始,经由启蒙时代的思想家和法国大革命的宣传家的如椽大笔,nation一词事实上是和“人民”(peuple,Volk)和“公民”(citoyen)这类字眼一起携手走入现代西方政治语
汇之中的。 [32] 换言之,nation指涉的是一种理想化的“人民全体”或“公民全体”的概念。在此意义上,它
和“国家”是非常不同的东西:nation是(理想化的)人民群体,而“国家”是这个人民群体自我实现的目标或
工具。如果译为“国族”将丧失这个概念中的核心内涵,也就是尊崇“人民”的意识形态。安德森之所以将
nation定义为“想象的共同体”,正是因为这个定义充分掌握到nation作为一种心理的、主观的“远景”(又是一
个“本土”的流行词汇!)的意义。
第二,以服务当权者利益为目的的“国族主义”毕竟只是民族主义复杂历史经验当中的一种类型——所
谓的“官方民族主义”——或者一个可能的组成成分而已,“国族主义”一词不仅遗漏了群众性民族主义这个重
要的范畴,同时也无力描述兼具官方与民粹特征的更复杂的类型。主要基于上述两个理由,笔者决定在本
书采用这两个较能表现出“人民”意识形态这个关键要素的传统词汇。
“民族主义的两面性”的这个评价表明了安德森“介于现代与后现代之间”的政治立场。 [33] 安德森虽然
认为“民族”是一种现代的“文化的人造物”,但他并不认为这个“人造物”是“虚假意识”的产物。“想象的共同
体”不是虚构的共同体,不是政客操纵人民的幻影,而是一种与历史文化变迁相关,根植于人类深层意识的
心理的建构。他同情并尊敬一切反帝、反压迫的民众的民族主义的奋斗,但也清清楚楚地了解这些运动随
时有堕落成反动的“官方民族主义”或者侵略扩张的帝国主义的危险。他写作《想象的共同体》的目的并不
是解构民族认同。正如同他在本书正文前所引用的沃尔特·本雅明的警句“他认为他的职责在于逆其惯常之理
以爬梳历史”所提示的,安德森所关切的“职责”是如何使民族认同“历史化”(historicize)与相对化:民族和
民族主义问题的核心不是“真实与虚构”,而是认识与理解。对他而言,一切既存或曾经出现的民族认同都
是历史的产物,唯有通过客观理解每一个独特的民族认同(包括自我的认同与“他者”的认同)形成的历史
过程与机制,才可能真正摆脱傲慢偏执的民族中心主义,从而寻求共存之道,寻求不同的“想象的共同
体”之间的和平共存之道。
“共同体的追寻”——寻找认同与故乡——是“人类的境况”(human condition)本然的一部分,但就像所
有人类对理想社会的追求一样,这条道路上也遍布着荆棘和引人失足的陷阱。我们必须尽最大的努力,在
情感与理性之间、同情与戒慎之间以及行动与认识之间寻求平衡。不管在这“一切都被允许”的虚无主义年
代里,人类的理性能力受到多么激烈的质疑,理性毕竟是卑微、善变和激情的人类最后的凭借。安德森的
这本《想象的共同体》——这本体现了汉娜·阿伦特所谓海德格尔式的“热情的思考”(passionate thinking)
的著作,就是试图在犬儒与狂热之外寻找认同之路的理性的辛勤劳作。
吴叡人
1999年4月7日午夜于密歇根湖畔斗室
————————————————————
注释:
[1] 本书是根据Benedict Anderson,Imagined Communities: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Revised Edition(London,New York:Verso,1991)的英文原文翻译而成的。翻译过程中,译者也参考了该书1983年出版(初版)的日译本,(べネデクトアンダ一ソ
ン著白石隆,白石さヤ译“想像の共同体一ナショナリズムの起源と流行”,东京:リブロポ一ト ,1987)。
[2] Edward Said,The Politics of Dispossesion:The Struggle for Palestinian Self-Determination 1969—1994,London:Chatto and Windus,1994,p.334.
[3] 本文中关于安德森个人背景的叙述,主要取材于他的两篇带有自述风格的导论文章:他的《语言与权力》(Language and Power,1990)一书的导论,以及他最近一本著作《比较的幽灵》(The Spectre of Comparisons,1998) 的导论。
[4] 佩里·安德森于1938年——也就是本尼迪克特出生后两年——生于伦敦,但出生后不久就被姨妈带到中国。请参见Gregory Elliot,Perry Anderson:The Merciless Laboratory of History ,Minneapolis and London: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99。艾略特的这本书是第一本对佩里·安德森的思想与实践作全面性研究的著作。
[5] Benedict Anderson,Language and Power ,p.2.
[6] 主修西方古典研究意味着必须通晓古希腊文与拉丁文。在西方语言之中,除了希腊文与拉丁文这两种古典语言以及母语英文之外,安
德森至少还精通法文和德文。当他日后投身东南亚研究之后,他至少又先后学会了印尼文、泰文、菲律宾的塔加洛文以及西班牙文。
[7] Benedict Anderson,Language and Power ,p.1.关于佩里·安德森的政治实践,特别是他和英国新左派运动的关系,以及他的历史社
会学理论的讨论,除了前述艾略特的近著《佩里·安德森》(1999)可供参考之外,也可见于Mary Fulbrook and Theda Skocpol,“Destined
Pathways:The Historical Sociology of Perry Anderson,”in Theda Skocpol,ed.,Vision and Method in Historical Sociology ,Cambridge:
Cambridge UP,1984,pp.170—210。
[8] Benedict Anderson,Language and Power ,pp.1—3.
[9] Ibid.,p.3.The Spectre of Comparisons ,p.19.
[10] Benedict Anderson,The Spectre of Comparisons ,pp.18—19.
[11] Benedict Anderson,Language and Power ,p.4.
[12] 笔者在此借用了一本精彩的雷蒙·阿隆访谈录的书名来描述安德森的“实践的观察者”的倾向。请参见James and Marie McIntosh,Raymond Aron,The Committed Observer(Le Spectateur Engage):Interviews with Jean-Louis Missika and Dominique Wolton ,Chicago:Regnery
Gateway,1983。
[13] 这篇论文在1972年以原题出版。请参见Benedict R.Anderson,Java in a Time of Revolution:Occupation and Resistance ,1944—
1946,Ithaca and London: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4] Benedict Anderson,Language and Power ,p.7.关于柯许特的事迹,请参见本书第六章。
[15] 参见安德森的《比较的幽灵》内第二部所收诸文。
[16] Benedict Anderson,Language and Power ,pp.9—10.
[17] Ibid.,p.10.
[18] 虽然安德森和另外两个重要的英国民族主义理论家欧内斯特·盖尔纳(Ernest Gellner)和汤姆·奈伦(Tom Nairn)都在他们的民族主
义理论中使用“不平均与合并的发展”这个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来理解资本主义的历史扩张模式的概念,不过他的用法和后两者有很大的不
同:后两位理论家直接以“不平均与合并的发展”论来解释民族主义(资本主义化或工业化后进地区对来自先进地区剥削的一种反应),但安德
森主要是借用“不平均与合并的发展”来描述民族主义的历史扩张的模式。关于盖尔纳的理论,请参见Ernest Gellner,Nations and Nationalism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3;关于汤姆·奈伦的理论,请参见Tom Nairn,The Break-Up of Britain:Crisis and Neo-Nationalism ,London:
NLB,1977。
[19] 所谓布迪厄式论证指的是法国社会学家皮耶·布迪厄(Pierre Bourdieu)关于社会实践(social practice)如何产生“实体
化”(reification)效果的理论。关于这个理论在民族主义研究中的运用,请参见Rogers Brubaker,Nationalism Reframed:Nationhood and the
National Question in the New Europe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安德森并未引用布迪厄的理论,但他的论点与布迪厄的论证精神
颇为接近,故笔者借用布迪厄之名。
[20] Ernest Gellner,Nations and Nationalism ,Ithaca and London: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3.这本书和《想象的共同体》竟然是在同
一年由同一家出版社出版的!康乃尔大学出版社之中显然潜藏胸有丘壑之士。关于盖尔纳的民族主义在西方社会科学界的讨论,请参见John
A.Hall,ed.,The State of the Nation:Ernest Gellner and the Theory of Nationalism,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9。
[21] 汉斯·科恩(Hans Kohn)的民族主义研究早期经典《民族主义的理念》(The Idea of Nationalism )只写到18世纪末的欧洲就用了七百
多页!请参见Hans Kohn,The Idea of Nationalism:A Study in Its Origins and Background ,Toronto:Collier Books,1944。另一个有类似计划的
作品用了四百多页,但基本上只完成民族主义的分类,无力建构一个系统性的解释。请参见John Breuilly,Nationalism and the State,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5。霍布斯鲍姆的《1780年后的民族与民族主义》(Nations and Nationalism since 1780 )虽然也十分简洁,但该书以历史叙述为主,并未真正提出一个理论性的解释,同时该书还是一本典型的“欧洲中心”观点的作品。请参见E.J.
Hobsbawm,Nations and Nationalism since 1780:Programme,Myth,Realit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22] 安东尼·史密斯非常多产,但比较重要的作品包括《民族主义理论》(Theories of Nationalism, London:Duckworth,1971);《民
族的族群起源》(The Ethnic Origin of Nations, Oxford:Basil Blackwell,1986);以及扼要总结他对民族主义观点的小书《民族认同》
(National Identity, Reno:University of Nevada Press,1991)等。
[23] 关于年鉴学派的研究途径,请参见Roger Chartier,Intellectual History or Sociocultural History?The French Trajectories ,in D.La
Capa & S.L.Kaplan,eds.,Modern European Intellectual History:Reappraisals and New Perspectives, Ithaca and London:Cornell University
Press,pp.13—46。细心的读者可在《想象的共同体》当中看到安德森向年鉴学派致意的痕迹。
[24] 无独有偶的是,安德森所敬重的“新左评论”友人,民族主义研究的前辈,苏格兰的马克思主义者汤姆·奈伦在他最近一本新书中也同
样抨击唯物论和盖尔纳的社会学现代化论都无法解释民族主义这种极度复杂的现象——他甚至提出要回归“人性”(human nature),从人类心理
和生理出发,重新理解民族主义!请参见《民族主义的面相——重新审视贾纳斯》(Faces of Nationalism:Janus Revisited, London:Verso,1997)一书之导论(“On Studying Nationalism”)。
[25] Stein Tonnesson and Hams Antlov,“Asia in Theories of Nationalism and National Identity,”in Stein T?nnesson and Hans Antlov,eds.,Asian Forms of the Nation,Curzon, 1996,p.14.
[26] 关于这方面较早期的研究成果,请参见Homi K.Bhabha,ed.,Nation and Narration ,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1990,特
别是编者洪米·巴巴所写的“导论”和“散播民族——时间、叙事、与现代民族边缘”(Dissemi Nation:Time,Narrative,and the Margins of the
Modern Nation)。这两篇文章是后殖民文学研究关于民族主义的重要论文。
[27] 当代后殖民研究重镇,孟加拉的巴特·夏特吉(Partha Chatterjee)关于殖民地民族主义的名著《民族主义思想与殖民地世界:衍生论
述》(Nationalist Thought and the Colonial World:A Derivative Discourse, 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da Press,1986)和著名的印度裔
中国史专家,芝加哥大学的杜赞奇(Prasenjit Duara)教授的近作《护史退族:现代中国的问题叙事》(Rescuing History from the Nation:
Questioning Narratives of Modern China, Chicago and London: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5)都可以说是在和《想象的共同体》的对
话。
[28] Michael Billig,“Rhetorical Psychology,Ideological Thinking,and Imagining Nationhood,”in Hank Johnston and Bert Klandermans,eds.,Social Movements and Culture, 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95,pp.64—78.[29] 其实这场论战早在1982年就因阿姆斯特朗(J.A.Armstrong)的原初主义论著《民族主义形成之前的民族》(Nations before
Nationalism )的出版而被引发了。不过安德森似乎并未直接参与辩论。后来持续参与论战的主要角色是现代派的盖尔纳和站在折中立场,不过
较偏原初派的安东尼·史密斯。关于这两方意见的一个简明而针锋相对的交换,请参见“The Warwick Debate:The Nation:Real or Imagined”,in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2(3),1996,pp.357—370。
[30] Prasenjit Duara,Rescuring History from the Nation:Questioning Narratives of Modern China ,Chapter 2.
[31] Partha Chatterjee,Nationalist Thought and the Colonial World:A Derivative Discourse ,pp.21—22.
[32] 最重要的两位思想家是法国的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和德国的赫德(Johann Gottfried von Herder),请参见F.M.Barnard,Self-Direction and Political Legitimacy:Rousseau and Herder, Oxford:Clarendon Press,1988。而将卢梭式的公民民族理念应用到法国大革命的
最著名的例子,是谢伊斯(Emmanuel-Joseph Sieves)所写的小册子《何谓第三阶级?》(Qu'est-ce que le Tiers etat ),请参见William H.
Sewell,Jr.,A Rhetoric of Bourgeois Revolution:the Abbe Sieyes and What is the Third Estate? Durham and London:Duke University Press,1994。
[33] 爱尔兰人安德森的这个立场和另一个对后殖民研究有深刻影响的杰出理论家巴勒斯坦人爱德华·萨义德有相近之处。这是一个颇值得
台湾人玩味的政治和知识社会学上的问题。第二版序
有谁会想到那风暴越远离伊甸园就吹得越猛烈呢?
仅仅才过了12年,直接引发我写作《想象的共同体》初稿的那场1978年到1979年在中南半岛的武装冲
突,似乎已经属于另一个时代了。那时,社会主义国家之间更进一步的全面战争的前景始终在我的脑中萦
绕不去。如今这些国家有一半已经加入了天使跟前的那堆残骸了,而剩余的恐怕很快就要追随其后了。幸
存者面临的战争是内战。非常有可能在新世纪开始之时,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会只剩下……共和国
了。
是否这一切多少都应该先预见到呢?在1983年我写道,苏联“不但是19世纪前民族期王朝国家的继承
人,也是21世纪国际主义秩序的先驱”。不过,在追溯摧毁了维也纳、伦敦、君士坦丁堡、巴黎和马德里统
治下的多语言、多族群的庞大帝国的民族主义之爆炸过程后,我却没有能够见到导火线至少已经铺到莫斯
科了。而令人忧郁的安慰是,我们观察到历史似乎比作者更能证明想象的共同体的“逻辑”。
不只是世界已经在过去12年间改变了容貌,民族主义的研究也已经令人震惊地改头换面了——在方
法、规模、深度上,还有纯粹在数量上皆然。仅以英语著作而言,J.A.阿姆斯特朗(J.A.Armstrong)
的《民族主义形成以前的民族》(Nations Before Nationalism ,1982),约翰·布罗伊尔(John Breuilly)的
《民族主义与国家》(Nationalism and the State ,1982),欧内斯特·盖尔纳(Ernest Gellner)的《民族与民
族主义》(Nations and Nationalism ,1983),米洛斯拉夫·罗奇(Miroslav Hroch)的《欧洲民族复兴的社
会先决条件》(Social Preconditions of National Revival in Europe ,1985),安东尼·史密斯(Anthony
Smith)的《民族的族群起源》(The Ethnic Origins of Nations ,1986),P.夏特吉(P.Chatterjee)的
《民族主义思想与殖民地世界》(Nationalist Thought and the Colonial World ,1986),还有埃里克·霍布斯
鲍姆(Eric Hobsbawm)的《1780年后的民族与民族主义》(Nations and Nationalism since 1780,1990)
——只提几本最重要的作品——以其涵盖的历史范围与理论的力量,已经在大体上淘汰了讨论这个主题的
传统文献了。大量研究将研究对象连接到民族主义和民族的史学的、文学的、人类学的、社会学的、女性
主义的和其他的研究领域,其中部分是从这些著作当中发展出来的。 [1]
改写《想象的共同体》,使之符合现实世界与民族主义研究的巨大变化,是一件超过我目前能力范围
的工作。因此,让它大体上保持为一件“未经复原的”特定时期的作品,保留特有的风格、外貌和语气,似
乎是比较好的决定。有两件事让我感到安慰。一方面,社会主义世界的发展,其完整的、最终的结果仍不
甚明朗。另一方面,对我而言,《想象的共同体》所使用的特殊方法和它最关切的问题,似乎还处于较新
的民族主义学术研究的边缘地带——在这个意义上,至少它还未完全被取代。
在第二版中,我只是试着更正我在准备初稿时就应该避免的一些事实、概念和诠释上的错误。这些更
正——也许可以说是依循着1983年版的精神——包括了对第一版的若干更动,以及基本上带有(与本书)
不连续的附录性质的两章新的文字。
在本书当中,我发现了两处翻译上的严重错误:一个是没有实现的承诺,另一处是容易产生误导的加
强语气。因为在1983年的时候,我还无法阅读西班牙文,尽管还有更早的几种译本可用,我却未经深思就
仰赖了利昂·格列罗(Leon Ma.Guerrero)对何赛·黎刹(Jose Rizal)的《社会之癌》(Noli Me Tangere )
的英文译本。直到1990年我才发现格列罗的译本是多么不可思议的错误百出。关于奥托·鲍尔(Otto Bauer)
的《民族问题与社会民主》(Nationalitatenfrage und die Sozialdemocratie )中的一段长而重要的引文,我则
懒惰地仰赖奥斯卡·贾希(Oscar Jaszi)的翻译。直到最近我查阅了原文之后,才发现贾希的政治倾向多么
严重地扭曲了他的译文。至少在两段文字中,我曾经没有信用地承诺要解释为何和其他拉丁美洲国家相比
较,巴西民族主义会发展如此之迟,而且如此特殊。这个版本会尝试去实现这个已被毁弃的誓约。
我最初的计划就是要强调民族主义在新世界的起源。我一直觉得有一种不自觉的地方主义长期地扭曲
了对这个主题的理论化工作。因为习惯了自负地以为现代世界的每个重要东西都起源于欧洲,欧洲的学者
不管是“赞成”还是“反对”民族主义,都很容易把“第二代的”语言民族主义(匈牙利、捷克、波兰等)当作他
们建构模式的起点。我很惊讶地发现,在很多注意到《想象的共同体》一书的作品中,这种欧洲中心的地
方主义仍然继续存在,而且那章讨论美洲起源地的关键文字大体上都被忽略了。不幸的是,除了把第四章
重新命名为“欧裔海外移民先驱者”(Creole Pioneers)之外,我实在找不到更好的“速成的”解决之道了。那两篇“附录”试图要更正第一版中严重的理论缺陷。 [2] 有几位友善的批评家主张说第七章(“最后一
波”)过度简化了早期“第三世界”民族主义建构其模式的过程。此外,那章并未认真处理当地的殖民政府
——不是母国——在设计(styling)这些民族主义的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同时,我逐渐不安地认识到,我
相信对思考民族主义作出了重要的新贡献的那个论证——对时间之理解的改变——明显地缺少了必要的对
等论证:对空间之理解的改变。年轻的泰国历史学家东猜·维尼察古(Tongchai Winichakul)所写的一篇杰
出的博士论文刺激了我去思考地图制作(mapping)对民族主义想象所作的贡献。
“人口调查、地图、博物馆”一章因此分析了19世纪的殖民地政府(及其心态所鼓励的那类政策)如何
在相当不自觉中辩证地创造出最后终于兴起而与之战斗的那些民族主义的基本规则(grammar)的方式。事
实上,或许我们甚至可以说,殖民地政府远在当地的对手出现之前,就在想象这些对手了。人口调查对人
的抽象量化系列化,地图最终将政治空间识别标志化,以及博物馆的“普遍的”、世俗的系谱建构,这三者
以彼此相关的方式,促成了殖民地政府这种想象的形成。
促使我写第二篇“附录”的缘起是,我羞愧地承认在1983年的时候,我完全不了解勒南(Renan)真正所
说过的话,就加以贸然引述:我轻易地把某种事实上全然怪异之事看成了反讽。这个羞辱也迫使我理解
到,我并没有对新出现的什么是民族以及如何将自己想象为古老的民族这个问题,作出任何睿智的解释。
所有那些在大多数学术作品中看起来像是马基雅维利式骗术、资产阶级幻想或者是被发掘出来的历史真相
者,如今却都突然使我觉得是某种更深刻更有趣的东西。假设,在某个历史的关头,“古老”是“崭新”的必然
结果?如果民族主义如我所设想的,是一种激烈变化了的意识形式的表现,那么难道对这个断裂的知觉,以及对较古老的意识的遗忘,民族主义不会创造出它自己的叙述吗?从这个角度来看,大多数19世纪20年
代以后的民族主义思想的那种隔代遗传式的幻想特性看起来就只是一个偶发现象而已;真正重要的是19世
纪20年代以后的民族主义“记忆”和现代传记与自传的内在前提和(写作)惯例之间的结构性的结合。
除了这两篇“附录”可能被证明会有的任何理论上的优点和缺点之外,它们各自都有其司空见惯的限
制。“人口调查、地图、博物馆”的资料全部都引自东南亚。这个区域以某些方式提供了绝佳的建构比较理
论的机会,因为它包含了先前曾被几乎所有帝国主义强权(英国、法国、荷兰、葡萄牙、西班牙和美国)
殖民过的地区,以及从未被殖民过的泰国。然而,即使我的分析对这个区域而言是合理的,但这个分析是
否能被令人信服地应用到全世界各地,尚待观察。在第二篇附录中,我所用到的简要的经验资料几乎完全
是关于我只有很浅认识的西欧和新世界。但我还是必须将焦点放在那里,因为最早传遍了民族主义的失忆
症的土地,就是这些区域。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
1991年2月
————————————————————
注释:
[1] 霍布斯鲍姆就有勇气把这种学术上的爆炸总结为民族主义的时代已经快到尾声了:密涅瓦的猫头鹰(Minerva's owl)总是在黄昏飞
翔。[密涅瓦为罗马神话中司工艺、智慧与战争的女神,“密涅瓦的猫头鹰只在黄昏降临之时才开始它的飞翔”语出黑格尔(G.W.F.
Hegel)的《法哲学原理》(Grundlinien der Philosophie des Recht) (1821)的序言,意指思想只有在现实的历史过程完成之后才会出现。]
[2] 第一篇附录源自为联合国大学世界发展经济学研究所(World Institute for Development Economics Research of the United Nations
University)1989年1月在卡拉奇举办的研讨会所准备的一篇论文。第二篇附录的纲要曾以《叙述民族》(Narrating the Nation)为题发表在1986
年6月13日的《泰晤士报文艺副刊》(The 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 )上。第一章 导论
也许这个现象尚未广受注意,然而,我们正面临马克思主义思想与运动史上一次根本的转型。最近在
越南、柬埔寨和中国之间的战争,就是这个转型最明显的表现。这几场战争具有世界史的重要性,不仅因
为它们是在几个无可置疑的独立革命政权之间最早发生的战争,同时也因为交战各国中没有任何一方尝试
使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观点来为这些战争进行辩护。虽然我们还是可能从“社会帝国主义”或“捍卫社会主
义”之类的角度——这要视个人品味而定——来诠释1969年的中苏边界冲突,以及苏联对德国(1953年)、匈牙利(1956年)、捷克斯洛伐克(1968年)和阿富汗(1980年)等国的军事干预,但是,我猜想,没有
人会真的相信这些术语和中南半岛上发生的事情可以扯上什么关系。
如果说,越南在1978年12月以及1979年1月对柬埔寨的入侵与占领,代表了一个社会主义政权与另一个
社会主义政权之间第一次的大规模传统战争 [1] ,那么中国在1979年2月与越南的冲突则迅速确认了这个先
例。只有那些最深信不疑的人才敢打赌说,在20世纪即将结束的几年里面,如果有任何大规模的国际冲突
爆发,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更不必说较小的社会主义国家了——会站在同一阵线。谁敢保证南斯拉
夫哪一天不会和阿尔巴尼亚打起来?那些企图使红军从东欧驻地撤出的各种团体应该先想一想,1945年以
来,无所不在的红军在多大程度上防止了这个地区的社会主义政权之间爆发武装冲突。
上述的思考,有助于表明一个事实: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生的每一次成功的革命,如中华人民共和
国、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等,都是用民族来自我界定的;通过这样的做法,这些革命扎实地植根于一个从
革命前的过去继承而来的领土与社会空间之中。相反,苏联和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却有一个少见
的共同特性,就是拒绝用民族来为国家命名。这个事实显示,这两国不但是19世纪前民族期王朝国家的继
承人,也是21世纪国际主义秩序的先驱。 [2]
埃里克·霍布斯鲍姆说过:“马克思主义运动和尊奉马克思主义的国家,不论在形式还是实质上都有变成
民族运动和民族政权——也就是转化成民族主义——的倾向。没有任何事实显示这个趋势不会持续下去。”
[3] 在这点上,他是完全正确的。然而,这个倾向并非只发生在社会主义世界之内。联合国几乎年年都接受
新的会员。许多过去被认为已经完全稳固的“老民族”如今却面临境内一些“次”民族主义(sub-nationalisms)
的挑战。这些民族主义运动自然梦想着有这么快乐的一天,他们将要褪去这个“次级”的外衣。事实摆在眼
前:长久以来被预言将要到来的“民族主义时代的终结”,根本还遥遥无期。事实上,民族属性(nation-
ness)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政治生活中最具普遍合法性的价值。
但是,如果事实是清清楚楚的,那么该如何解释这些事实则是一段长期众说纷纭的公案。民族
(nation),民族归属(nationality) (1) ,民族主义(nationalism)——这几个名词涵义之难以界定,早已
众所周知,遑论对之加以分析了。民族主义已经对现代世界产生巨大的影响;然而,与此事实形成明显对
比的是,具有说服力的民族主义理论却屈指可数。休·赛顿-华生(Hugh Seton-Watson),这位关于民族主
义的英文论著中最好、涵盖面最广的一部作品的作者,也是自由主义史学与社会科学的继承人,悲伤地说
道:“我被迫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也就是说,我们根本无法为民族下一个‘科学的’定义;然而,从以前到现
在,这个现象却一直持续存在着。” [4] 汤姆·奈伦(Tom Nairn),《不列颠的崩解》(The Break-up of
Britain) 这部开创性作品的作者,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史学与社会科学传统的传人,作了如此坦白的评
论:“民族主义的理论代表了马克思主义历史性的大失败。” [5] 然而甚至这样的表白也还是有些误导,因为
我们会误以为这段话的含义是,马克思主义确实曾经长期而自觉地追寻一个清晰的民族主义理论,只不过
令人遗憾的是,这个努力失败了。比较准确的说法应该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而言,民族主义已经证明是
一个令人不快的异常现象;并且,正因如此,马克思主义理论常常略过民族主义不提,不愿正视。不然,我们该如何解释马克思在他那篇令人难忘的对1848年革命的阐述当中,竟然没有说明其中那个关键性的形
容词的意义:“当然,每个国家的无产阶级都必须先处理和它自己的(its own)资产阶级之间的关系。” [6]
我们又怎样解释“民族资产阶级”(national bourgeoisie)这个概念被用了一个世纪以上的时间,却没有人认
真地从理论上使“民族”这个形容词的相关性合理化?如果以生产关系来界定,资产阶级明明是一个世界性
的阶级,那么,为什么这个特定部分的资产阶级在理论上是重要的?
本书的目的在于尝试对民族主义这个“异常现象”提出一个比较令人满意的诠释。我觉得,在这个问题
的处理上,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主义的理论都因为陷入一种“晚期托勒密式”的“挽救这个现象”的努力,而变得
苍白无力;我们亟需将理解这个问题的角度,调整到一种富有“哥白尼精神”的方向上。 (2) 我的研究起点
是,民族归属(nationality),或者,有人会倾向于使用能够表现其多重意义的另一字眼,民族的属性(nationness)以及民族主义,是一种特殊类型的文化的人造物(cultural artefacts)。想要适当地理解这些
现象,我们必须审慎思考在历史上它们是怎样出现的,它们的意义怎样在漫长的时间中产生变化,以及为
何今天它们能够掌握如此深刻的情感上的正当性。我将会尝试论证,这些人造物之所以在18世纪末被创造
出来, [7] 其实是从种种各自独立的历史力量复杂的“交汇”过程中自发地萃取提炼出来的一个结果;然而,一旦被创造出来,它们就变得“模式化”(modular),在深浅不一的自觉状态下,它们可以被移植到许多形
形色色的社会领域,可以吸纳同样多形形色色的各种政治和意识形态组合,也可以被这些力量吸收。我也
会试图说明,为什么这些特殊的文化人造物会引发人们如此深沉的依恋之情。概念与定义
在处理上面提出的问题之前,我们似乎应该先简短地考虑一下“民族”这个概念,并且给它下一个可行
的定义。下列三个诡论经常让民族主义的理论家感到恼怒而困惑:(1)民族在历史学家眼中的客观的现代
性相对于民族在民族主义者眼中的主观的古老性;(2)民族归属作为社会文化概念的形式的普遍性——在
现代世界每个人,就像他或她拥有一个性别一样,都能够、应该,并且将会拥有一个民族成员的身份——
相对于民族归属在具体特征上的特殊性,例如,“希腊”民族成员的身份,依照定义本来就是独特的(sui
generis);(3)各种民族主义在“政治上”的力量相对于它们在哲学上的贫困与不统一。换言之,和大多数
其他的主义不同的是,民族主义从未产生它自己的伟大思想家:没有它的霍布斯、托克维尔、马克思或韦
伯。这种“空洞性”很容易让具有世界主义精神和能够使用多种语言的知识分子对民族主义产生某种轻视的
态度。就好像格特鲁德·斯泰因(Gertrude Stein)面对奥克兰(Oakland)的时候,人们会很快下结论说那里
是一个“空无一物的地方”(there is ‘no there there’) (3) 。即使像奈伦这么同情民族主义的学者也还是会如
此写道:“‘民族主义’是现代历史发展中的病态。如同‘神经衰弱’之于个人一样地不可避免;它既带有与神经
衰弱极类似的本质上的暧昧性,也同样有着退化成痴呆症的内在可能性——这个退化可能性乃是根源于世
界上大多数地区所共同面临的无助的两难困境之中(这种痴呆症等于是社会的幼稚病),并且,在多数情
况下是无药可医的。” [8]
有一部分的困难源于,人们虽然不会把“年龄”这个概念当作一个专有名词,他们却常常不自觉地把民
族主义当作专有名词,将它视为一个具有特定专属内容的存在实体,然后把“它”区别为一种意识形态。
(请注意,假如每个人都有年龄,那么“年龄”只不过是一种分析性的表达语汇而已。)我想,如果我们把
民族主义当作像“血缘关系”(kinship)或“宗教”(religion)这类的概念来处理,而不要把它理解为像“自由
主义”或“法西斯主义”之类的意识形态,事情应该会变得比较容易一点。
遵循着人类学的精神,我主张对民族作如下的界定:它是一种想象的政治共同体——并且,它是被想
象为本质上有限的(limited),同时也享有主权的共同体。
它是想象的,因为即使是最小的民族的成员,也不可能认识他们大多数的同胞,和他们相遇,或者甚
至听说过他们,然而,他们相互联结的意象却活在每一位成员的心中。 [9] 当勒南写道“然而,民族的本质
是每个人都会拥有许多共同的事物,而且同时每个人也都遗忘了许多事情” [10] 时,他其实就以一种文雅而
出人意表的方式,指涉了这个想象。当盖尔纳(Gellner)判定“民族主义不是民族自我意识的觉醒:民族主
义发明了原本并不存在的民族” [11] 时,他是带着几分粗暴提出了一个类似的论点。但是,盖尔纳这个表述
的缺点是,他太热切地想指出民族主义其实是伪装在假面具之下,以致他把发明(invention)等同于“捏
造”(fabrication)和“虚假”(falsity),而不是“想象”(imaginging)与“创造”(creation)。在此情形下,他
暗示了有“真实”的共同体存在,而相较于民族,这些真实的共同体享有更优越的地位。事实上,所有比成
员之间有着面对面接触的原始村落更大(或许连这种村落也包括在内)的一切共同体都是想象的。区别不
同的共同体的基础,并非他们的虚假真实性,而是他们被想象的方式。爪哇的村落居民总是知道他们和
从未谋面的人们有所关联,然而这种关联性,就如同可以无限延伸的亲族或侍从(clientship)网络一般,是以特殊主义的方式被想象的。直到不久以前,爪哇语当中还没有能够表示“社会”这个抽象概念的字眼。
今天我们也许会把旧政权时代的法国贵族想成一个阶级;但是他们被想象成一个阶级当然是非常晚近的
事。 [12] 对于“谁是X伯爵?”这样的问题,以往正常的答案不会是“贵族阶级的一员”,而是“X地的领
主”、“Y男爵的伯父”,或者“Z公爵的侍从”。
民族被想象为有限的,因为即使是最大的民族,就算他们或许涵盖了十亿个活生生的人,他们的边
界,纵然是可变的,也还是有限的。没有任何一个民族会把自己想象为等同于全人类。虽然在某些时代,基督徒确实有可能想象地球将成为一个信奉基督教的星球;然而,即使最富于救世主精神的民族主义者也
不会像这些基督徒一样地梦想有朝一日,全人类都会成为他们民族的一员。
民族被想象为拥有主权 ,因为这个概念诞生时,启蒙运动与大革命正在毁坏神谕的、阶层制的皇朝的
合法性。民族发展臻于成熟之时,人类史刚好步入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里,即使是普遍宗教最虔诚的追
随者,也不可避免地被迫要面对生机勃勃的宗教多元主义,并且要面对每一个信仰的本体论主张与它所支
配的领土范围之间也有不一致的现实。民族于是梦想着成为自由的,并且,如果是在上帝管辖下,直接的
自由。衡量这个自由的尺度与象征的就是主权国家。最后,民族被想象为一个共同体,因为尽管在每个民族内部可能存在普遍的不平等与剥削,民族总是
被设想为一种深刻的,平等的同志爱。最终,正是这种友爱关系在过去两个世纪中,驱使数以百万计的人
们甘愿为民族——这个有限的想象——去屠杀或从容赴死。
猛然之间,这些死亡迫使我们直接面对民族主义提出来的核心问题:到底是什么原因使得这种只有短
暂历史(不超过两个世纪)的,缩小了的想象竟然能够激发起如此巨大的牺牲?我相信,只有探究民族主
义的文化根源,我们才有可能开始解答这个问题。
————————————————————
注释:
[1] 我选择用这个论述方式只是想强调战斗的规模和形态,而不是要追究罪责。为了避免可能的误解,我们应该要说1978年12月的入侵源
起,最早可以追溯到1971年的两个革命运动党人之间的武装冲突。在1977年4月之后,最初由柬埔寨人发动,但越南人随即跟进的边界突击行
动的规模和范围逐步扩大,并在1977年12月升级成越南的大规模入侵。然而这些突击行动的目的都不是要推翻敌方政权或占领大片领土,而且
涉及的部队人数也不能和1978年12月所部署的部队相比。关于这场战争的起因的争论思虑最周详的讨论,请参见Stephen P.Heder,“The
Kampuchean-Vietnamese Conflict”,in David W.P.Elliott,ed.,The Third Indochina Conflict ,pp.21—67;Anthony Barnett,“Inter-
Communist Conflicts and Vietnam”,Bulletin of Concerned Asian Scholars ,pp.2—9;and Laura Summers,“In Matters of War and Socialism
Anthony Barnett would Shame and Honour Kampuchea Too Much”,ibid,pp.10—18。
[2] 凡是质疑联合王国在这方面是否称得上和苏联相同的人,都应该问问自己联合王国这个名字到底表示了哪个民族:大不列颠—爱尔兰
民族?
[3] Eric Hobsbawm,“Some Reflection on‘the Break-up of Britain’”,New Left Review ,105(September-October 1977),p.13.
[4] 参见Nations and States ,p.5。
[5] 参见“The Modern Janus”,New Left Review ,94(November-December 1975),p.3。这篇论文被只字未改地收在The Break-up of
Britain ,作为该书的第九章(pp.329—363)。
[6] Karl Marx and Friedrich Engels,The Communist Manifesto .在任何理论的注释当中,“当然”这两个字应该都要在入神的读者眼前闪起
红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62页译文如下:“每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当然首先应该打倒本国的资产阶
级。”——译者注)
[7] 正如艾拉·克米雷能(Aira Kemilainen)所留意到的,学院的民族主义研究的孪生“开国之父”,汉斯·科恩(Hans Kohn)和卡尔顿·海斯
(Carlton Hayes)令人信服地主张应该以这个日期为民族主义之发轫。我相信除了在特定国家的一些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宣传家以外,他们的
结论从未被严重地质疑过。克米雷能也观察到“民族主义”这个词要到19世纪才被广泛而普遍地使用。例如,它并未出现在很多标准的19世纪辞
典当中。虽然亚当·斯密以“‘nations’的财富”(国富论)之名作论,但他只不过把这个名词当作“社会”或“国家”的意思而已。Aira
Kemilainen,Nationalism ,pp.10,33,48—49。
[8] The Break-up of Britain ,p.359.
[9] 参考Seton-Watson,Nations and States ,p.5:“我所能说的就是当一个共同体内部为数众多的一群人认为他们自己形成了一个民族,或者表现得仿佛他们已经形成了一个民族的时候,一个民族就存在了。”
[10] Ernest Renan,“Qu'est-ce qu'une nation”,in Oeuvres Complètes ,1,p.892。他又接着说:“所有法兰西公民都必须已经遗忘圣巴托罗
缪惨案与13世纪发生在南方的屠杀事件。在法国能够提供他们起源于法兰西人证明的家族不到十个……”
[11] Ernest Gellner,Thought and Change ,p.169.
[12] 例如,霍布斯鲍姆为了“修补”这个情况,就说在1789年的时候贵族占全国2300万人口中的40万之多。(参见他的The Age of
Revolution, p.78。)然而我们有可能在旧政权之下想象这幅贵族的统计图像吗?
在本书所讨论的欧洲民族语言发展史的脉络中,vernacular(本意为“某一特定地区的本地语言”),指的是和拉丁文这个跨越地方界限
的“共通语”相对的“地方性”或“区域性”语言,如法语、德语或意大利语等。译者将这个字译为“方言”,纯粹取其“地方语言”的描述性涵义,请
读者勿与语言学上的“方言”(dialect)或汉字日常语汇中的“方言”一词混淆。在语言学上,“方言”(dialects)本意为一个“语言”内部细分出来的
同一语言的变种(variants),并且这些变种之间是可以相互理解的。当一个语言的几个变种方言演化到彼此不能理解时,它们就成为各自独立
的“语言”了。在这个定义下,文艺复兴前后在欧洲发展出来的各种vernaculars(地方语言)应该已经算是“language”,而非“dialect”了。同理,汉文通俗语汇习惯将各地区的地方语言视为在“标准法”位阶下的“方言”的说法,从语言学的角度来看,也是颇成问题的。以中国为例,如果
从“相互可理解性”(intercomprehensibility)的标准来衡量,许多所谓中国的“方言”(如吴语、赣语、粤语、闽北语、闽南语),其实根本是各
自独立的“语言”(language)。所谓“国语”或“普通话”之成为“标准语”,而闽南语、粤语沦为“方言”,并非基于语言学上的理由,而是出于政治
——特别是民族主义——的考虑。——译者注
————————————————————
(1) 根据《牛津英语辞典》(The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nationality一词有下列几个主要意义:(1)民族的特质或性格;(2)民族
主义或民族情感;(3)属于一个特定民族的事实;特定国家(State)的公民或臣民的身份,或者界定这种身份的法律关系,而这种关系涉及
了个人对国家的效忠与国家对个人之保护(国籍);(4)作为一个民族的分别而完整的存在;民族的独立;(5)一个民族;一群潜在的,但
非政治上的民族的人民(people);一个族群团体(ethnic group)。就译者的了解,虽然在通俗语汇或学术论述之中都可以看到上述这几种用
法,但其意义通常需视上下文而定。另外,虽然牛津英语辞典区分了民族(nation)与国家(state)两词的意义,但在通俗语汇上,这两个词经
常被混用。面对此种歧义的语言难局,译者采取根据上下文决定个别单词译法的策略。——译者注
(2) 亚历山大的托勒密(Ptolemy of Alexandria)是公元2世纪的埃及天文学家,他在公元150年左右在著作Almagest 中提出以地球为中心的
宇宙论。托勒密体系必须运用越来越多的数学手段才能解释反常的行星运动,因此沿用到文艺复兴时代时,已经形成一个生硬而负载过重的概
念,但却仍然不能准确地说明或观察行星位置。面对这一困境,波兰天文学家哥白尼(Nicolaus Copernicus,1473—1543)在他的短篇手稿Commentariolus (1514)中提出一个釜底抽薪的解决方案:放弃以地球为中心的预设,重新提出一个以太阳为中心的体系。作者以“晚期托勒
密”来比喻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主义对民族现象的错误理解在面临经验事实愈来愈严重的挑战时,只能用愈来愈复杂而无当的理论来自圆其说;
为今之计,需要以哥白尼的精神,彻底扬弃错误的预设,重新出发。——译者注
(3) “There is no there there”这句话意指“那个地方是人工的,不真实的,缺乏本质的,没有核心的”。这是美国女作家格特鲁德·斯泰因
(Gertrude Stein,1874—1946)在她1937年的作品《每个人的自传》(Everybody's Autobiography )之中描述奥克兰的名句。斯泰因的少女时期
是在北加州的奥克兰和旧金山地区度过的,后来她长住巴黎,视之为其精神上的故乡。在《巴黎,法国》(Paris,France ,1940)一书中,斯
泰因描述法国是她的第二个国家,“它(法国)不是真的(我的国家),但它真的在那里。”(It is not real but it is really there.)试将本句话与
前句作一对比。参见斯泰因:《巴黎,法国》(New York:Liveright,1970),第2页。——译者注第二章 文化根源
没有什么比无名战士的纪念碑和墓园,更能鲜明地表现现代民族主义文化了。这些纪念物之所以被赋
予公开的、仪式性的敬意,恰好是因为它们本来就是被刻意塑造的,或者是根本没人知道到底是哪些人长
眠于其下。这样的事情,是史无前例的。 [1] 你只要想象一下一般民众对于好事者宣称“发现”了某个无名战
士的名字,或是坚持必须在碑中存放一些真正的遗骨时的反应,就可以感受到此事的现代性了。一种奇怪
的,属于当代的亵渎形式!然而,尽管这些墓园之中并没有可以指认的凡人遗骨或者不朽的灵魂,它们却
充塞着幽灵般的民族的想象。 [2] (这也就是为什么许多拥有这种墓园的民族并不觉得有必要指明这些不存
在的英灵属于哪个民族。除了身为德国人、美国人、阿根廷人……之外,他们还有可能属于什么民族?)
如果我们试着去想象,比方说,“无名的马克思主义者之墓”或者“殉难自由主义者衣冠冢”,这类纪念物
的文化意义就会更清楚了。做这种想象有可能不让人感到荒谬吗?毕竟,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主义都不怎么
关心死亡和不朽。然而,民族主义的想象却如此关切死亡与不朽,这正暗示了它和宗教的想象之间有着密
不可分的关系。这种密切关系绝对不是偶然的,所以,如果我们以死亡——这个一切宿命之中最终极的宿
命——作为起点来考察民族主义的文化根源,也许会有所助益。
人会怎么死常常看来是没什么规则可循的,但所有人终究都不免一死。人的生命就充满了这类必然与
偶然的组合。我们全都明白我们体内特定的基因遗传,我们的性别,我们生存的时代,我们种种生理上的
能力,我们的母语等,虽是偶然的,却也是难以改变的。传统的宗教世界观有一个伟大的价值(我们自然
不应将此处所谓的价值和他们在合理化种种支配和剥削体系时所扮演的角色混为一谈),也就是他们对身
处宇宙之内的人、人类作为物种的存在以及生命之偶然性的关心。佛教、基督教或者伊斯兰教在许多不同
的社会中存续了千年以上,这一惊人的事实,证明了这些宗教对于人类苦难的重荷,如疾病、肢体残废、悲伤、衰老和死亡,具有充满想象力的回应能力。为何我生而为盲人?为何我的挚友不幸瘫痪?为何我的
爱女智能不足?宗教企图作出解释。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所有演化论进步论形态的思想体系的一大弱
点,就是对这些问题不耐烦地无言以对。 [3] 同时,宗教思想也以种种不同的方式——通过将宿命转化成生
命的连续性(如业报或原罪等观念),隐讳模糊地暗示不朽的可能。经由此,宗教思想涉及了死者与未降
生者之间的联系,即关于重生的秘密。任何一个曾经经历过他们的子女受孕与诞生的人,都会模糊地领会
到“连续”这个字眼当中同时包含的结合、偶然和宿命。[这里,演化论进步论思想又居于下风了,因为它
对任何连续性的观念抱着近乎赫拉克利特式(Heraclitean) (1) 的厌恶。]
我之所以提出这些似乎有点愚蠢的观点,主要是因为在西欧,18世纪不只标志了民族主义的降生,也
见证了宗教式思考模式的衰颓。这个启蒙运动和理性世俗主义的世纪同时也带来了属于它自己特有的、现
代的黑暗。尽管宗教信仰逐渐退潮,人的受苦——有一部分乃因信仰而生——却并未随之消失。天堂解体
了:所以有什么比命运更没道理的呢?救赎是荒诞不经的:那又为什么非要以另一种形式延续生命不可
呢?因而,这个时代所亟需的是,通过世俗的形式,重新将宿命转化为连续,将偶然转化为意义。在下面
的讨论中我们会知道,很少有东西会比民族这个概念更适于完成这个使命。假设如果民族国家确如公众所
认的,是“新的”而且是“历史的”,则在政治上表现为民族国家的“民族”的身影,总是浮现在遥远不复记忆的
过去之中, [4] 而且,更重要的是,也同时延伸到无限的未来之中,正是民族主义的魔法,将偶然化成命
运。我们或许可以随着德勃艾(Debray)的话说道:“是的,我生而为法国人是相当偶然的;然而,毕竟法
兰西是永恒的。”
我当然不是主张民族主义在18世纪末的出现是宗教世界观的确定性遭侵蚀所“造”成的,我也不是说此
种确定性之受侵蚀本身不需要复杂的解释。我也没有暗示民族主义不知怎样地就在历史过程中“取代”了宗
教。我所主张的是,我们应该将民族主义和一些大的文化体系,而不是被有意识信奉的各种政治意识形
态,联系在一起来加以理解。这些先于民族主义出现的文化体系,在日后既孕育了民族主义,同时也变成
民族主义形成的背景。只有将民族主义和这些文化体系联系在一起,才能真正理解民族主义。
宗教共同体(religious community)和王朝(dynastic realm),是和我们现在的讨论相关的两个文化体
系。就像“民族”在当代的地位一样,这两个文化体系在它们的全盛时期,也都被人们看作是理所当然的参
考架构。因此,一个重要的课题是,我们必须探究为什么这些文化体系会产生不证自明的合理性,而又是
什么样的重要因素导致它们的解体。宗教共同体
很少有什么事情,会比当今世界几个主要宗教所涵盖的地域之广袤,更令人印象深刻了:从摩洛哥到
菲律宾苏禄群岛(Sulu Archipelago)的地区,构成了伊斯兰教共同体;从巴拉圭到日本,尽在基督教世界
的范围之内;而佛教信仰圈,则涵盖了南起斯里兰卡北至朝鲜半岛的广大地域。这几个伟大的神圣文化
(为了本章讨论的目的,也许可以容我再加上“儒教”一项)里都包含有“广大无限的共同体”的概念。然而关
于基督教世界、伊斯兰教世界甚至中国(the middle kingdom)的想象——虽然我们今天把中国想成“中华
(Chinese)之国”,但过去她并不是把自己想象成“中华”,而是“位居中央”(central)之国——之所以可
能,主要还是经由某种神圣的语言与书写文字的媒介。仅以伊斯兰教为例:假如玛昆达纳人
(Maguindanao) (2) 和伯伯尔人(Berbers) (3) 在麦加相遇,他们虽然彼此都不懂对方的语言,无法口头
沟通,却可以理解彼此的文字,因为他们所共有的神圣经典全都是以古典阿拉伯文书写的。就此意义而
言,阿拉伯文正如同中国文字一样,创造了一个符号——而非声音(sounds)——的共同体。(所以今天的
数学语言延续着一个旧传统。罗马尼亚人和泰国人都不知道对方怎么称呼“+”这个符号,但他们都了解这个
符号的意义。)所有伟大而具有古典传统的共同体,都借助某种和超越尘世的权力秩序相联结的神圣语言
为中介,把自己设想为位居宇宙的中心。因此,拉丁文、巴利文、阿拉伯文或中文的扩张范围在理论上是
没有限制的。(事实上,书写文字越死——离口语越远——越好:原则上人人皆可进入纯粹符号的世
界。)
不过这种由神圣语言所结合起来的古典的共同体,具有一种异于现代的民族想象共同体的特征。最关
键的差别在于,较古老的共同体对他们语言的独特的神圣性深具信心,而这种自信则塑造了他们关于认定
共同体成员的一些看法。中国的官人们带着赞许的态度注视着千辛万苦方才学会挥毫书写中国文字的野蛮
人。这些蛮人虽未入文明之室,却总算也登上文明之堂了, [5] 而即使半开化也远胜于蛮貊。这样的态度当
然并非中国人所特有,也不限于古代。比方说,让我们想想下面这段由19世纪初哥伦比亚的自由主义者彼
得罗·费敏·德·瓦加斯(Pedro Fermin de Vargas)所拟的《平蛮策议》:
欲扩张吾人之农业,必先使印第安人西班牙化。彼等之怠惰、愚昧以及对正常应付出之努力
所持之漠然态度,令人思及彼等乃源于一堕落之种族,且距其源头愈远愈形退化……唯今之计,应使印第安人与白人通婚,宣告彼等已无进贡与其他义务,再发给私有土地,使之驯至灭种。 [6]
令人注意的是,这个自由主义者仍然提议用“宣告彼等已无进贡义务”和“发给私有土地”这类手段来让印
第安人“灭种”,而不像随后他在巴西、阿根廷和美国的后继者们一样,干脆用枪炮和细菌来灭绝印第安
人。同样要注意的是和他那屈身以从的残酷并存的一种乐观主义的宇宙论:在受孕于白种人的、“文明
的”精液,并且取得私有财产后,印第安人就和其他所有人一样,终究是可以救赎的。[后来的欧洲帝国主
义者多偏好“纯种的”马来人,廓尔喀人(Gurkhas) (4) 和豪萨族人(Hausas) (5) 胜于“混血种”、“半开化
土人”、“西化的东方绅士”(wog)之类的。费敏的态度和他们是多么不同啊。]
然而,如果神圣而沉默的语言是人们想象昔日那些伟大的世界的共同体的媒介的话,这种幻想的现实
性则系于一个对于当代西方思维而言颇为陌生的理念——符号的非任意性。中文、拉丁文或阿拉伯文的表
意文字是现实的直接流露,而不是任意虚拟的现实表象。关于何者才是适合于大众的语言(拉丁文或方
言)的长期争论,我们都知之甚详。伊斯兰教传统认为,唯有经由那无可替代的真实符号——阿拉伯文,才能接近安拉的真理,因此直到相当晚近,古兰经都还被认为是不可能照原文逐字翻译的(所以也就一直
没有被翻译)。这些古典的共同体从未设想过一个和语言高度分离,而所有语言都只是和它保持等距关系
(所以是可以互换的)符号的世界。事实上,本体论上的真实只能通过一个单一的、拥有特权地位的表象
系统,如教会拉丁文的真理语言(truth-language)、古兰经的阿拉伯文或科举的中文,才能理解。 [7] 而
且,作为所谓“真理语言”,这些表象系统内部带有一种对民族主义而言相当陌生的冲动,也就是朝向“改
宗”(conversion)的冲动。所谓改宗,我指的不是使人接受特定的宗教信条,而是如炼金术般地将之吸收
融合之意。蛮夷化为“中国”,里夫人(Rif) (6) 化为伊斯兰教徒,而伊隆哥人(Ilongo) (7) 则化为基督
徒。人类存有的本性可以经由圣礼而变形。(何妨试将这些耸立天际、傲视一切方言的古老的世界性语言
与湮埋于众方言之间、无人闻问的近代的人造世界语,如世界语或沃卜拉克语 (8) 作一对比。)终究,正是
这种可以经由神圣语言改宗的可能性,才让一个“英格兰人”可以成为教宗(Pope) [8] 而“满族人”得以成为
天子。然而纵然神圣的语言使得“基督教世界”这样的共同体成为可想象的,这些共同体实际的范围及其合理
性,却也不是单凭神圣的文字这一个因素就能解释清楚的。毕竟,能够阅读这些文字的人,只不过是在广
大的文盲之海上露出的数点识字者的小岩礁罢了。 [9] 欲求更完整的解释,我们必须看看文人阶层与其社会
之间的关系。把文人理解为某种神权的科技官僚的想法是错误的。他们所使用的语言,尽管深奥难解,却
完全没有律师或经济学家的术语那种超乎一般社会对现实的观点之外的、堆砌造作的深奥。相反,文人在
一个以神为顶点的宇宙秩序中,构成一个具有战略性地位的阶层。 [10] 关于“社会集团”的一些根本概念,并不是(集团的)界线导向和水平式的,而是向心而阶层式的。我们必须先知道有一个横跨欧洲全域的书
写拉丁文的文人阶级的存在,以及一个人人共有的关于世界的概念——这个概念主张具有双语能力的知识
阶层通过连接方言与拉丁文,同时也连接了尘世与天堂——然后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教皇权在全盛时期竟
然可以如此势焰熏天。(对于被逐出教会的畏惧正反映了这个宇宙论。)
但是,尽管伟大的宗教的想象共同体曾享有崇高的威望,他们的不自觉的整合性,却从中世纪后期开
始稳定地衰退。有种种理由导致了这样的衰退,然而我在此仅欲强调和这些共同体独特的神圣性有直接关
联的两项因素。
首先,是对欧洲以外的世界所进行的探险的影响。这个影响——虽然不限于欧洲,但主要仍发生在欧
洲——“急遽扩大了文化和地理的视野,也因而扩充了人们关于人类可能的生活形式的概念” [11] 。这个过
程,在所有伟大的欧洲人的游记中,早已清晰可察。让我们看看以下这段由威尼斯基督徒马可波罗在13世
纪末所写的,对忽必烈汗(Kublai Khan)饱含敬畏的描述: [12]
大汗在大胜之后,威风凛凛地班师凯旋,返回京城汗八里。这是发生在11月的事,然后大汗
继续在京城住到隔年的2月和3月,正当我们的复活节的时刻。当他得知复活节是我们的主要祭典
之一时,他诏令所有基督徒前来参观,并且令他们随身带来他们的那本含有四福音书的《圣
经》。在恭谨地将《圣经》反复薰香之后,他虔敬地亲吻《圣经》,并且下令所有在场贵族一一
照做。这个仪式是他每逢主要的基督教节庆,如复活节或圣诞节来临时,通常都会遵循的惯例。
此外,每逢撒拉森人(Saracens)(阿拉伯人)、犹太人或者其他偶像教徒的节庆之日,他也依此
惯例,行礼如仪。当他被问及这个举动的动机何在时,他说:“四位伟大的先知,分别受到不同种
类人群的敬拜。基督徒敬耶稣为神;伊斯兰教徒膜拜穆罕默德;犹太人崇敬摩西;偶像教徒则敬
拜所有偶像中最尊崇的索哥蒙巴坎(Sogomombar-kan)(释迦牟尼佛)。我敬爱所有这四位先
知,而且,不管他们之中到底哪一个在天上享有真正至高的地位,我都会向他祈求赐福。”但是从
陛下敬拜这四位神祇的方式观之,明显地,他认为基督徒的信仰至真且至善……
这段记载最引人注意的不是这位蒙古大帝冷静的宗教相对论(那终究还是一种宗教的相对论),而是
马可波罗的态度和语言。即便他是写给他的欧洲基督徒同胞看的,他也从未想过要把忽必烈称为伪善之徒
或者偶像崇拜者。(无疑,这有部分是因为“就臣民的数目、领土的面积和收入的总额而论,他超越了全世
界古往今来所有的君王” [13] 。)而从他不自觉地使用“我们的”(后来又变成“他们的”)这一字眼,以及将
基督徒的信仰描述为“至真”而不只是“真”当中,我们可以察觉到若干“信仰的领土化”(territorialization of
faiths)的种子,它们预示了日后许多民族主义者的语言(“我们的”民族“最好”——在一个竞争的、比较的
场域之中)。
来自波斯的旅行者“里嘉”(Rica)于“1712”年从巴黎写给友人“伊班”(Ibben)的一封信的开头,为我们
提供了一个深富启发性的对照: [14]
教皇是基督徒的头子;他是旧时代的偶像,而现在人们是出于习惯而敬拜他。以往连君主们
都畏惧他,因为他要废除这些君主的王位,就像我们伟大的苏丹要让伊瑞美地亚或乔治亚的国王
退位一样简单。但是现在人们再也不怕他了。他宣称自己是最早的基督徒之一的,一个叫做圣彼
得的人的继承人。这当然是个有钱的世代继承,因为他有庞大的财富,而且控制了一个很大的国
家。
出于一个18世纪的天主教徒之手的这些刻意而复杂的虚构情景,反映出他那位13世纪的前辈天真的写
实主义,然而时至18世纪的此刻,“相对化”和“领土化”已经完全是自觉的,而且是带有政治意图的了。伊朗
宗教政权领袖霍梅尼没有用“大撒旦”之名来称呼异端邪说,甚至也没有用来指某个恶魔般的人物(不起眼
而渺小的卡特总统实在配不上这个头衔),却将之视为一个民族。难道我们不能把这个例子,看作是对这
个正在演化当中的“宗教共同体自觉而带有政治意图的‘相对化’与‘领土化’的”传统,一个吊诡式的透彻阐释
吗?第二个因素是神圣语言自身地位的逐步式微。在论及中世纪的西欧时,布洛克(Bloch)注意到“拉丁
文不仅是教学用的语言,它还是仅有的一个被教授的语言” [15] 。[这第二个“仅”(only)很清楚地显示出
拉丁文的神圣性——所有其他的语言都被认为是不值得教授的。]然而到了16世纪,这种情形已开始急速
改变了。我们无须在此着墨于导致这个改变的种种因素:在后文中我们自会讨论印刷资本主义(print-
capitalism)的无比重要性。我们只要记得这个变化的规模和速度就够了。根据费柏赫(Febvre)和马丁
(Martin)的估计,1500年以前出版的书籍有77%还是用拉丁文写的(然而这也意味着已经有23%的书是以
方言写成的)。 [16] 如果1501年时在巴黎印行的88个版本的书籍当中只有8个版本不是用拉丁文写的,那么
到了1575年之后法文版的书籍就一直占着多数。 [17] 虽然在反宗教改革期间拉丁文曾有短暂的复兴,但拉
丁文的霸权已亡。我们也不只是在谈论是否广泛流行的问题而已。稍后,以一种同样令人晕眩的速度,拉
丁文丧失了作为全欧洲上层知识阶级的语言的地位。17世纪时,霍布斯(Hobbes,1588—1678)因为使用
真理语言写作而享誉欧洲大陆,而莎士比亚(Shakespear,1564—1616)却因以方言写作而声名不闻于英吉
利海峡彼岸。 [18] 如果英语没有在200年后变成最显赫的世界性的——帝国式的语言,莎士比亚果真能幸免
于先前默默无闻的命运吗?同时,在英吉利海峡彼岸的同代文人中,笛卡儿(1596—1650)和帕斯卡
(1623—1662)多以拉丁文书写信简,但伏尔泰(1694—1778)则完全使用方言通信。 [19] “1640年以后,由于以拉丁文写的新书日益减少,而方言著作则与日俱增,出版渐渐不再是一个国际性(原文如此)的事
业了。” [20] 一言以蔽之,拉丁文的衰亡,其实是一个更大的过程,也就是被古老的神圣语言所整合起来的
神圣的共同体逐步分裂、多元化以及领土化的过程的一个例证。王朝
现代人恐怕很难理解曾经有这样一个世界,在那里大多数的人唯一想象得到的“政治”体系似乎只有王
朝而已。因为“真正的”(serious)君主制本质上存在于一个和所有与现代的政治生活有关的概念相交会的位
置上。王权把所有事物环绕在一个至高的中心四周,并将它们组织起来。它的合法性源于神授,而非民众
——毕竟,民众只是臣民(subjects),不是公民(citizens)。在现代概念中,国家主权在一个法定疆域内
的每平方厘米的土地上所发生的效力,是完全、平整而且均匀的。但是在比较古老的想象里面,由于国家
是以中心(center)来界定的,国家与国家之间的边界是交错模糊的,而且主权也颇有相互渗透重叠之处。
[21] 因而,很吊诡的是,前现代的帝国与王国竟能够轻易地维系他们对极度多样而异质,并且经常是居住
在不相连的领土上的臣民的长期统治。 [22]
我们同时也要记得,这些古老的君主制国家,不只通过战争,也靠一种和今日所实行的颇不相同的“性
的政治”来进行扩张。经由垂直性的法则,王朝之间的联姻把多种多样的民众聚合到新的顶点之下。就此而
言,哈布斯堡王室是个中典范。诚如那收场的戏文所云:“让别人去战斗吧!汝,幸运的奥地利结婚去
吧!”(Bella gerant alii tu felix Austria nube! (9) )以下是一段稍作简化了的哈布斯堡家族后期君主拥有的
头衔: [23]
奥地利皇帝;匈牙利,波希米亚,达尔马提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加利西亚,罗德美
利亚,与伊利里亚之王;耶路撒冷等地之王;奥地利大公;托斯卡纳与克拉科夫大公;洛林,萨
尔茨堡,史地利亚,卡林西亚,卡尼奥拉,与布科维纳公爵;特兰西瓦尼亚大公,摩拉维亚边境
伯爵;上下西里西亚,摩德纳,帕尔马,皮亚琴察,与瓜斯地拉,奥斯维茨和萨托,泰申,福里
奥,拉古萨,与扎拉大公;哈布斯堡与蒂洛尔,基堡,哥兹,格拉地斯卡伯爵;特兰托与布利琛
公爵;上下洛斯茨与伊斯的利亚边境伯爵;霍恩姆斯,费尔得克奇,布莱根茨,索能堡等地之伯
爵;的里雅斯特领主,卡塔罗与温地斯马克领主;伏伊伏丁那与塞尔维亚大公……
诚如贾希(Jászi)公允的观察,这个头衔“不是没有滑稽的一面……这是哈布斯堡家族无数次联姻、讨
价还价和掠夺的记录”。
在一夫多妻为宗教所认可的世界里,复杂的多层妻妾体制对于王朝的整合具有关键的重要性。事实
上,可否容我说,王室血统的威望除了源自神命之外,经常也来自异族通婚(miscegenation)呢? [24] 因
为,这种血缘的混合是统治地位的表现。从11世纪以来(如果在此之前真的有过的话)就再也没有一个“英
格兰的”王朝统治过伦敦。这是一个典型的例证。而我们又该把波旁王室(the Bourbons)派给哪一个“民
族”呢? [25]
然而,17世纪时,由于某些无须在此细究的因素,神圣君主自然而然产生的正当性在西欧开始慢慢衰
退。1649年,查尔斯·斯图亚特(Charles Stuart)在现代世界的第一场革命中被斩首,而在17世纪50年代,这个重要的欧洲国家的统治者不是国王,而是一个平民出身的监国(Protector)。但即使在诗人波普
(Pope)和爱迪生(Addison)的时代,安·斯图亚特(Anne Stuart)仍然在使用以皇族之手触摸病人的方式
为人治病。在启蒙运动时代的法国,直到旧政权瓦解前夕,波旁王室的路易十五和路易十六也都还在做这
种事情。 [26] 然而1789年以后,统治者就得要声嘶力竭而且自觉地辩护他们的合法性了,而在此过程
中,“君主制”(monarchy)变成了一个半规范化的模式。天皇和天子变成了“皇帝”。在边远的泰国,拉玛五
世(Rama V)[Chulalongkorn(朱拉隆功)]把他的子侄送到圣彼得堡、伦敦和柏林的宫廷里去学习这个
世界性的模式的机微奥妙。1887年,他将法定长子继承的必要原则予以制度化,从而将泰国带入“与西欧
诸‘文明的’君主制国家并列”之境。 [27] 这个新体制在1910年,把一个在早先的旧制下当然会被略过的古怪
的同性恋者送上了王位。不过,在他的加冕典礼上,来自英国、俄国、希腊、瑞典、丹麦甚至日本等国的
代表出席,等于宣示了各君主国对他登基为拉玛六世的认可。 [28]
迟至1914年,君主制国家还是世界政治体系成员中的多数,然而,正如我们将在下面仔细探究的,早
在旧的正当性原则无声无息地消亡之际,很多君主早已在探求“民族的”标志了。尽管腓特烈大帝(1749—
1786年在位)的军队中还有为数众多的“外国人”,他的侄孙腓特烈·威廉三世(1797—1840年在位)的军
队,在沙恩霍斯特(Scharnhorst)、格耐斯瑙(Gneisenau)和克劳塞维茨(Clausewitz)等人 (10) 了不起的
改革之后,已经彻底地变成“普鲁士的国民军”了。 [29]对时间的理解
然而,我们也不应该目光短浅地认为民族的想象共同体就真是从宗教共同体和王朝之中孕育,然后再
取而代之而已。在神圣的共同体、语言和血统衰退的同时,人们理解世界的方式,正在发生根本的变化。
这个变化,才是让“思考”民族这个行为变得可能的最重要因素。
要想感觉一下这个变化,我们如果去看看那些神圣共同体怎样在视觉上被表现出来,像中世纪教堂里
的浮雕和彩绘玻璃,或早期意大利和佛兰芒(Flemish)巨匠的画作,当会获益良多。这些视觉表现的代表
性特征是,它们和“现代服装”之间具有某种容易令人误解的相似性。那些遵循星辰的指引来到耶稣诞生的
马槽的牧羊人竟然有着伯根地农民的五官。童贞玛丽长得像塔斯卡尼商人的女儿。在很多画作当中,出现
在画面上的委托创作主顾穿着全套市民阶级或贵族的行头,满怀赞叹地跪在牧羊人的身边。显然,我们今
天看似不协调的事物在中世纪的宗教敬拜者眼中却是完全自然的。我们所面对的,是一个几乎完全以视觉
和听觉来表现对现实的想象的世界。基督教世界需要经由无数个特殊的事物,像是这面浮雕,那片窗户,这篇祷文,那个故事,这出道德剧,那个圣者或殉教者的遗骨等,才形成其普遍性的形式。尽管横跨全欧
熟悉拉丁文的知识阶层是建构基督教想象的一个重要成分,然而以较个别而具体的视、听觉创造物当作向
不识字的民众传播教义的媒介的做法,也同等重要。就算听过那个谦逊的教区教士讲道的街坊民众人人都
对他的家世和弱点了如指掌,他也还是他的教众和上帝之间的直接媒介。这种宇宙普遍性(cosmic-
universal)原则和现世特殊性(mundane-particular)原则的并立,意味着不管基督教世界可能有多广阔,或
者人们觉得它有多广阔,事实上它是以种种特殊的面貌,针对不同的地域共同体如斯瓦比亚(Swabia)或
安达卢西亚(Andalusia)等,以这些共同体自身的形象呈现出来的。以现代美术馆那种“回复原貌”的精
神,把童贞玛丽画得像闪族人,或穿着“第一世纪”的服装,中世纪基督徒对这种事情是无法想象的。中世
纪的基督教教义并没有历史是一条无尽的因果锁链这样的观念,也没有过去与现在断然二分的想法。 [30]
据布洛克的考察,当时的人认为既然基督的二次降临随时会到来,他们必然已经接近时间的尽头了——诚
如保罗所言,“主降临之日将如黑夜之窃贼般悄然到来”。无怪乎伟大的12世纪编年史家弗来兴主教奥托
(Bishop Otto of Freising)会反复陈说“被置于时间尽头之我等”。布洛克下结论说,中世纪的人“从献身冥思
之日起,他们的思绪就远离这样的念头,即年轻而富有活力的人类种族拥有久远未来的前景” [31] 。
奥尔巴哈(Auerbach)为这种形式的意识,描绘了一幅令人难忘的图像: [32]
如果像以撒(Issac)(圣经中亚伯拉罕之子,被其父献祭给上帝)的牺牲这样的事件,被诠
释为预示了基督的牺牲,因而前者仿佛像是宣告且承诺了后者的发生,而后者则“成就了”前者,那么,在两个相互没有时间或因果关联的事件之间,某种关联就被建立起来了——而这个关联是
无法用理性在水平的次元上建立起来的……只有两个事件都被垂直地联系到唯一能够如此规划历
史并且提供理解历史之钥的神谕,才有可能确立这个关联……此时此地不再只是尘世事件之链的
一环而已,它同时是一个始终存在,并且终将在未来被完成的事物;而且,严格说来,在上帝眼
中,它是某种永恒的、无时不在的,以及在已支离破碎的尘世领域中被完成的事物。
他正确地强调出像同时性(simultaneity)这样的概念对我们而言是全然陌生的。这个概念把时间看成
很接近本雅明所说的“弥赛亚时间”,一种过去和未来汇聚于瞬息即逝的现在的同时性。 [33] 在这种看待事
物的观点中,“其时”(meanwhile)一词是不可能具有真正的意义的。
我们自己的同时性概念,是在一段漫长的时间里逐渐成形的,而它的出现当然和世俗科学的发展有关
——虽然这两者之间究竟如何相关仍有待深入探讨。但因为这个概念是这么重要,如果不对它作充分的思
考,我们势必难以究明民族主义那隐微而不易辩识的起源。最后终于取代了中世纪的与“时间并进的同时
性”概念的,再借用本雅明的话,是一种“同质的、空洞的时间”的观念。在此观念中,同时性是横向的,与
时间交错的;标示它的不是预兆与成就,而是由时钟与日历所测量的,时间上的一致(temporal
coincidence)。 [34]
如果我们思考一下两种最初兴起于18世纪欧洲的想象形式——小说与报纸——的基本结构,就能够明
白何以这个转型对于民族的想象共同体的诞生会是如此重要了。 [35] 因为这两种形式为“重现”民族这种想
象的共同体,提供了技术上的手段。首先来考察旧式小说的结构,一种从巴尔扎克的杰作到所有同代的三流廉价小说都共有的典型结构。
很清楚,它是一种以“同质的、空洞的时间”来表现同时性的设计,或者说是对“其时”这两个字的一种复杂注
解。为了说明起见,让我举一部单纯的小说情节里面的一段为例。在这段情节中,某男子(A)有妻(B)
与情妇(C),而这个情妇又有一情人(D)。我们也许可以为这段情节想象出一个如下的时间表:
要注意在这个时序中A和D从未碰面,而事实上如果C很精明,这两人可能根本不知道彼此的存在。
[36] 那么A和D到底有什么关系?有两个互补的概念。第一,他们都身处“社会”(如西撒克斯、卢卑克、洛
杉矶)之中。因为这些社会有着如此坚实稳定存在的社会学实体,其成员(A和D)因此甚至可 ......
您现在查看是摘要介绍页, 详见PDF附件(2296KB,15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