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逻辑.pdf
http://www.100md.com
2020年2月11日
 |
| 第1页 |
 |
| 第10页 |
 |
| 第16页 |
 |
| 第29页 |
 |
| 第33页 |
 |
| 第101页 |
参见附件(6842KB,304页)。
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逻辑是作家阿夫纳奥弗尔写的关于诺贝尔奖的书籍,主要讲述了诺贝尔奖的起源,发展历程,它的设立目的,设计了很多的经济学理论和经济学行为。

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逻辑内容提要
《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逻辑》以诺贝尔经济学奖为主题展开论述,聚焦于阐述和反思这一奖项的起源与影响力。这本书在撰写过程中参阅了之前从未公开过的瑞典国家银行档案,考察了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历史,剖析了自该奖项颁发以来的经济学说发展历程,尤其是内洽其中的社会民主主义与市场自由主义之间的博弈,并基于此对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及其影响力进行了特色的分析。
这本书尖锐地指出,设立诺贝尔经济学奖,其目的是试图利用“诺贝尔”的品牌光环来提升银行的以及市场友好型经济理论的威望,并以此来影响瑞典和其他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实践。它反思了瑞典、欧洲和美国的市场自由主义者与社会民主主义者在此过程中所做的斗争,通过这些犀利视角对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可以说,这本书地描述了经济学理论照进现实世界的后果。而付诸经济实践,也许才是对某一项经济学理论大的褒奖。
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逻辑作者信息
阿夫纳奥弗尔,牛津大学经济史,万灵学院名誉院士,英国科学院院士。
加布里埃尔索德伯格,瑞典乌普萨拉大学经济史研究员。
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逻辑章节预览
第一章 假想机器
第二章 “经济科学”奖
第三章 痛苦之源: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金融与社会民主
第四章 瑞典央行捐赠了一个诺奖
第五章 经济学有政治偏见吗
第六章 个人声誉
第七章 诺贝尔经济学与社会民主
第八章 将模型引入决策:阿瑟?林德贝克与瑞典社会民主主义
第九章 究竟是瑞典僵化症还是假性僵化症?20世纪80年代的瑞典
第十章 真正的危机:不是工作激励而是失控的信贷
第十一章 在斯堪的纳维亚之外:对市场腐败的华盛顿共识
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逻辑截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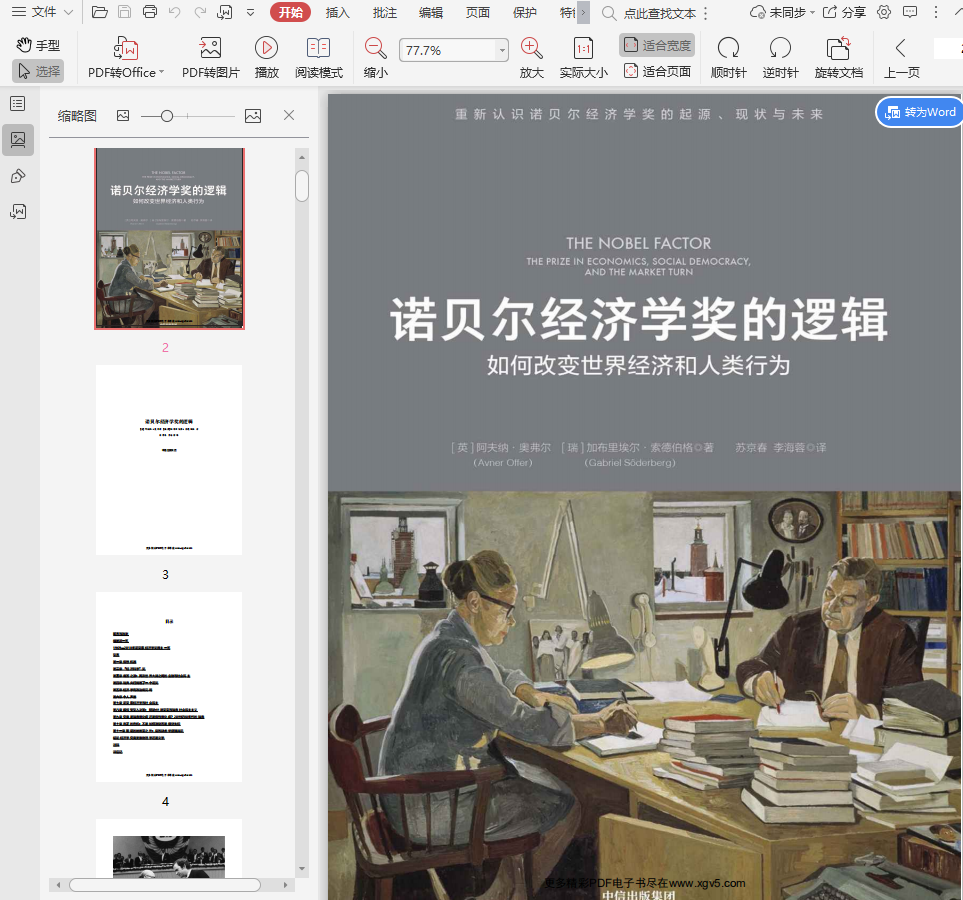

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逻辑
[英]阿夫纳·奥弗尔 [瑞典]加布里埃尔·索德伯格 著
苏京春 李海蓉 译
中信出版集团
目录
前言与致谢
缩略词一览
1969—201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一览
引言
第一章 假想机器
第二章 “经济科学”奖
第三章 痛苦之源: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金融与社会民主
第四章 瑞典央行捐赠了一个诺奖
第五章 经济学有政治偏见吗
第六章 个人声誉
第七章 诺贝尔经济学与社会民主
第八章 将模型引入决策:阿瑟·林德贝克与瑞典社会民主主义
第九章 究竟是瑞典僵化症还是假性僵化症?20世纪80年代的瑞典
第十章 真正的危机:不是如何激励而是信贷失控
第十一章 斯堪的纳维亚之外:腐败肆虐华盛顿共识
结论 经济学究竟更像物理学还是文学
注释
译后记
1976年12月10日,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从瑞典国王卡尔十六世·古斯塔夫(Carl XVI
Gustaf)手中接过诺贝尔经济学奖
我坚信:
有道理的事,说一遍即可;
没道理的事,说千遍亦无用。
——威廉·哈兹里特(William Hazlitt)
《席间闲谈》(又名《关于人物及风格的新评论》,1822年)
(Table Talk or Original Essays on Men and Manners )
前言与致谢
1970年左右,时代气息突变。在西方富裕社会,持续20年之久的充分就业与
富足被艰苦岁月与劳苦之身取代。那些基于经济学说主张对市场进行调控和刺激
的论证无法解释这场“市场变革”(market turn)。那么,经济学说是如何发
挥作用的,都能发挥什么作用呢?诺贝尔经济学奖(1969年第一次颁发)很合时
宜地给出了不同时代经济学说的定位。诺贝尔经济学奖为新古典经济学和社会民
主主义这两个不断发展的学说之间产生的冲突提供了一定的参考,而这两个学说
竞相影响着战后若干年社会的形成。瑞典创立了诺贝尔奖,而其自身是社会民主
的一个原型。这个国家也只是长篇故事中的一个篇章,实际上社会民主主义对我
们的影响更为广泛。表面上,这两个学说泾渭分明,实际上,它们相克相生,尽
管这并不意味着这两个学说结合后会更完美。
本书开门见山地阐述了诺贝尔奖项的故事,从第二章第一部分的介绍开始,而后在第四章和第六章进一步做了叙述。第三章则深入探讨了两次世界大战之间
的历史根源。
在进入正文之前,我们首先要致谢为本书提供帮助的人。因为这个选题,他
们之间形成了一种非正式的公私合作伙伴关系。我们的母校——乌普萨拉大学和
牛津大学,以及牛津大学万灵学院,在教学和管理方面给予了我们很大的支持。
乌普萨拉大学和万灵学院为我们提供了非常好的工作地点以及良好的合作条件,牛津大学纳菲尔德学院则提供了非常丰富的图书馆资源,学校里的同事甚至乐于
将我们的一些日常工作纳入他们规定性的研究任务当中。这些大学都诚挚地配合
了由利华休姆信托基金和新经济思维研究所(INET)资助的研究机会,这两个机
构(起源于80年前)都是由慷慨的资本家创建的。牛津大学历史学院和万灵学院
也为我们的一些特殊需求提供了小额资助。此书完稿于加布里埃尔接管瑞典银行
之前,所以书中使用的数据均不含其任职期间的数据。
在瑞典,阿瑟·林德贝克(Assar Lindbeck)教授与阿夫纳·奥弗尔进行了
为期一天的全方位访问,该议程还得到进一步延伸,增加了令人颇受鼓舞的晚宴
环节。约尔根·韦布尔(J?rgen Weibull)教授促成了这次访问活动,并且通过
敏锐决策推动了晚宴的实现。在瑞典,我们还与拉尔斯·马格努松(Lars
Magnusson)教授、杰肯·米达尔(Janken Myrdal)教授和彼得·诺贝尔
(Peter Nobel)教授进行了对话。在此向他们致谢。
萨缪尔·比约克(Samuel Bjork)参与了第六章的写作。他为巴斯模型提出
了一个新的运算法则,并且使用了我们收集到的数据来估计巴斯曲线。菲利普·
米卢斯基(Philip Mirowski)也曾与我们合作,但是因观点相左而离开了。他
尖锐直白的建议对本书产生了应有的影响,这也使我们的合作结束得更加温和。
同事和朋友们都给予了我们帮助、倾听与回应。克里斯托弗·拉格奎斯特
(Christopher Lagerqvist)建立了牛津-乌普萨拉实验室,这一实验室首次把
我们凑在了一起。研讨会和会议论文得以在四大洲的12个国家举行和发表。在此
一并感谢对我们的邀请、尖锐的评论以及所到之处、所见之人、所思所得共同形
成的丰富经历。我们的朋友和同事(包括三个研究助手,在此也一并提及)阅读
了本书的相应章节,并且对本书的观点进行了研讨,他们包括圣达斯·埃里
(Sundas Ali)、托尼·阿特金森(Tony Atkinson)、萨缪尔·比约克、莎拉
·卡罗(Sarah Caro)、文森特·克劳福德(Vincent Crawford)、保罗·大卫
(Paul David)、詹姆斯·芬斯克(James Fenske)、塔玛·弗兰克(Tamar
Frankel)、蒂姆·罗尼格(Tim Leunig)、约翰内斯·林德沃(Johannes
Lindvall,他做的贡献远远超过其职责范围)、孟苗(Meng Miao)、菲利普·
米卢斯基、汤姆·尼古拉斯(Tom Nicholas)、亨利·欧胜(Henry
Ohlsson)、安德鲁·斯科特(Andrew Scott)、克劳迪奥·索普兰泽蒂
(Claudio Sopranzetti)、戴维·斯图克勒(David Stuckler)和朱丽亚·特
威格(Julia Twigg)。完整稿由帕梅拉·克莱米特(Pamela Clemit)、沙米姆
·甘米奇(Shamim Gammage)、麦克斯·哈里斯(Max Harris)和罗梅什·瓦提
林根(Romesh Vaitilingam)审读,他们纠正了我们的很多错误,这使我们受益
颇丰。书中如果存在错误都是我们自己的责任。出版社的两个审稿人付出了大量
劳动并提供了大力支持。他们的贡献使我们想表达的观点更加精确。沙米姆·甘
米奇为我们提供了出色的技术支持。莎拉·卡罗和汉娜·保罗(Hannah Paul,为出版社工作)给予了我们大量鼓励、包容和指导。
在此,加布里埃尔对妻子毛(Mao)表示感谢,并对即将长大且开始学习阅
读的女儿小李李(little Li)同样表达感激之情。阿夫纳也向妻子利亚
(Leah)表示感谢,感谢她几十年来的合作、支持、勤勉以及其给予的独到见
解。
缩略词一览
AEA: 美国经济协会
ATP: 瑞典补充养老金制度
BIS: 国际清算银行
DSGE: 动态随机一般均衡
ESO: 公共经济学研究专家组
FOREX: 外汇
GDP: 国内生产总值(经济产出的国内度量,不考虑海外资产的产出)
IMF: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UI: 工业经济与社会研究所,斯德哥尔摩;目前叫工业经济研究所
LDC: 欠发达国家
LIBOR: 伦敦同业拆借利率(英国基准金融市场利率)
LO: 瑞典体力劳动者工会联合会
MCE: 市场出清均衡
NBER: (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
NCM: 新古典宏观经济学
NPW: 诺贝尔奖得主
OECD: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PPP: 购买力平价(相关经济体中可比较商品价格所决定的汇率)
SAF: 瑞典雇主联合会
SAP: 瑞典社会民主工人党
SNS: 商业和政策研究中心,斯德哥尔摩
TCO: 瑞典非体力劳动者工会联合会
VAR: 向量自回归(一种广泛应用数据的一致性但不是明确检验理论模型
的统计学估计方法)
WashCon: 华盛顿共识
1969—201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一览
1969: 拉格纳·弗里希(Ragnar Frisch)
简·丁伯根(Jan Tinbergen)
1970: 保罗·A.萨缪尔森(Paul A.Samuelson)
1971: 西蒙·库兹涅茨(Simon Kuznets)
1972: 约翰·R.希克斯(John R.Hicks)
肯尼斯·J.阿罗(Kenneth J.Arrow)
1973: 华西里·列昂惕夫(Wassily Leontief)
1974: 纲纳·缪达尔(Gunnar Myrdal)
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冯·哈耶克(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
1975: 列奥尼德·康托罗维奇(Leonid Vitaliyevich Kantorovich)
佳林·C.库普曼斯(Tjalling C.Koopmans)
1976: 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
1977: 詹姆斯·E.米德(James E.Meade)
贝蒂·俄林(Bertil Ohlin)
1978: 赫伯特·A.西蒙(Herbert A.Simon)
1979: 阿瑟·刘易斯爵士(Sir Arthur Lewis)
西奥多·W.舒尔茨(Theodore W.Schultz)
1980: 劳伦斯·R.克莱因(Lawrence R.Klein)
1981: 詹姆斯·托宾(James Tobin)
1982: 乔治·J.斯蒂格勒(George J.Stigler)
1983: 罗拉尔·德布鲁(Gerard Debreu)
1984: 理查德·斯通(Richard Stone)
1985: 弗兰科·莫迪利安尼(Franco Modigliani)
1986: 小詹姆斯·M.布坎南(James M.Buchanan Jr.)
1987: 罗伯特·M.索洛(Rober M.Solow)
1988: 莫里斯·阿莱斯(Maurice Allais)
1989: 特里夫·哈维默(Trygve Haavelmo)
1990: 哈里·M.马科维茨(Harry M.Markowitz)
默顿·H.米勒(Merton H.Miller)
威廉·F.夏普(William F.Sharpe)
1991: 罗纳德·H.科斯(Ronald H.Coase)
1992: 加里·S.贝克(Gary S.Becker)
1993: 罗伯特·W.福格尔(Robert W.Fogel)
道格拉斯·C.诺斯(Douglass C.North)
1994: 约翰·C.海萨尼(John C.Harsanyi)
小约翰·F.纳什(John F.Nash Jr.)
莱因哈德·泽尔腾(Reinhard Selten)
1995: 小罗伯特·E.卢卡斯(Robert E.Lucus Jr.)
1996: 詹姆斯·A.莫里斯(James A.Mirrlees)
威廉·维克里(William Vickrey)
1997: 罗伯特·C.默顿(Robert C.Merton)
迈伦·S.斯科尔斯(Myron S.Scholes)
1998: 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
1999: 罗伯特·A.门德尔(Robert A.Mundell)
2000: 詹姆斯·J.赫克曼(James J.Heckman)
丹尼尔·L.麦克法登(Daniel L.McFadden)
2001: 乔治·A.阿克洛夫(George A.Akerlof)
A.迈克尔·斯彭斯(A.Michael Spence)
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Joseph E.Stiglitz)
2002: 丹尼尔·卡尼曼(Daniel Kahneman)
弗农·L.史密斯(Vernon L.Smith)
2003: 罗伯特·F.恩格尔三世(Robert F.EngleⅢ)
克莱夫·W.J.格兰杰(Clive W.J.Granger)
2004: 芬恩·E.基德兰德(Finn E.Kydland)
爱德华·C.普雷斯科特(Edward C.Prescott)
2005: 罗伯特·J.奥曼(Robert J.Aumann)
托马斯·C.谢林(Thomas C.Schelling)
2006: 埃德蒙·S.费尔普斯(Edmund S.Phelps)
2007: 莱昂尼德·赫维奇(Leonid Hurwicz)
埃里克·S.马斯金(Eric S.Maskin)
罗杰·B.迈尔森(Roger B.Myerson)
2008: 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
2009: 埃莉诺·奥斯特罗姆(Elinor Ostrom)
奥利弗·E.威廉姆森(Oliver E.Williamson)
2010: 彼得·A.戴蒙德(Peter A.Diamond)
戴尔·T.莫滕森(Dale T.Mortensen)
克里斯托弗·A.皮萨里德斯(Christopher A.Pissarides)
2011: 托马斯·J.萨金特(Thomas J.Sargent)
克里斯托弗·A.西姆斯(Christopher A.Sims)
2012: 埃尔文·E.罗斯(Alvin E.Roth)
罗伊德·S.沙普利(Lloyd S.Shapley)
2013: 尤金·F.法玛(Eugene F.Fama)
拉尔斯·皮特·汉森(Lars Peter Hansen)
罗伯特·J.席勒(Robert J.Shiller)
2014: 让·梯若尔(Jean Tirole)
2015: 安格斯·迪顿(Angus Deaton)
2016: 奥利弗·哈特(Oliver Hart)
本特·霍姆斯特罗姆(Bengt Holmstrom)
2017: 理查德·泰勒(Richard Thaler)
2018: 保罗·罗默(Paul Romer)
威廉·诺德豪斯(William Nordhaus)
引言
在学术圈中,经济学家是为数不多的愿意阐述应该如何管理社会的群体之
一。他们很少有统一的声音,但这并没有减少他们的信心。不管是疑惑还是尊
敬,社会大众都对经济学家信心满满。而经济学家真正知道些什么,他们是怎么
知道这些的?他们的权威性来自何方,在多大程度上能得以证明呢?经济学说的
创建虽然通常带有理论推导的性质,但它的影响力是巨大的和实实在在的。自20
世纪70年代以来,经济学说的创建紧随重大历史趋势,这一趋势就是我们提出
的“市场转向”:它是市场自由主义不断崛起的过程,(像经济学一样)也是将购
买和销售奉为人际关系和社会组织准则的一场政治和社会运动。经济学到底能
给“市场转向”提供多好的理论证明呢?与过往相比,它究竟是不是一种进步呢?
公正世界理论
1969年12月10日晚上,在宏伟的斯德哥尔摩音乐大厅,当物理学、化学、医
学、文学奖项桂冠都被摘取之后,荷兰经济学家简·丁伯根被第一次授予“纪念阿
尔弗雷德·诺贝尔(Alfred Nobel)经济学奖”。其他领域的诺贝尔奖项都是从1901
年开始每年颁发一次的。阿尔弗雷德·诺贝尔虽然是一位多产的发明家和天才的商
人,但他并没有创立经济学奖项。在一封信中,他写道自己“满心憎恨商业”,他
把自己定位为社会民主主义者。 [1]
在颁奖仪式上,经济学家丁伯根被安排与其
他领域的获奖者分开而立。在文学奖得主——爱尔兰前卫剧作家、小说家和诗人
——萨缪尔·贝克特(Samuel Beckett)获得颁奖之后才颁发经济学奖项。尽管经
济学现在仍然很难有一定之规,但总体看来还是比贝克特所在的文学领域好一
些。那么经济学究竟是更像物理学还是更像文学呢?大多数获得诺贝尔奖的经济
学家都选择忽略这一问题,所以它一直遗留至今。
在进行寻求所谓“效率”这一实践利益的社会活动时,利益是什么,以及为谁
争取这种利益,通常并不明晰。然而,一旦经济学不能持续践行这一社会活动,它的有效性就会降低。经济政策会影响个人与国家的生计和福利,还会广泛影响
金融与商业利益。基于此,经济学家的观点应该具有某种特殊的权威性,这一点
跟其他专家群体相比显著不同:他们应当是有理有据的顾问,公正而客观。他们
应该独立于部门和个人利益诉求之外,也应该独立于来自宗教制裁或个人意志这
样的哲学范畴诉求之外。在这里,我不得不提到一个经济学家通常不会意识到的
事实:他们在研究中往往将个人观点作为首要考虑因素,然而在提出对策时又会
忽略这一点。
经济学包括许多学说和主张,这些学说和主张之间并不总是协调一致的。经
济学的目的是给社会现实提供一个简化但正确的解释。它的权威性是双重的:一
方面在于理论本身必须引人注目,另一方面在于理论能够经受观察与结果的检
验。经济理论的魅力就在于它每天要将与直觉相冲突的事实进行简化处理,与此
同时还要给混乱的现实建立秩序。有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经济学理论很难被人
们掌握,但很容易被人们相信。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方法论者(赞扬经济
学方法和研究目的的学者)将关注重点和很多努力都放在了理论的内在有效性
上,特别是关注这些理论究竟如何联系在一起并且产生作用。 [2]
关注这一课题
的主要原因是,许多经济理论既不是来源于实践,也不是来源于实验结果。
维多利亚时代的生物学家托马斯·赫胥黎(Thomas Huxley)曾在1870年说
道:“科学的巨大不幸在于美丽的猜想被丑陋的现实扼杀。”冒着不合时宜的风
险,我们与现今的方法论者分道扬镳,而力求回到更简单的时代。在那时,理论
如果想要被认定为正确,就必须与发生的事实相一致。将理论与现实对证并不是
一件简单且容易办到的事情,我们也不想以此来冒犯那些提出相关理论的作者,但我们当中有人亲自进行了尝试,将乔治·阿克洛夫的柠檬市场经济理论(这一理
论因在2001年获得诺贝尔奖而得到认可)与历史上的二手车市场进行了对比。
[3]
不难发现,在这个理论当中,有一个关键的理论基础是错误的。若像这个理
论阐述的那样,其先天就是不可检验的,它的一些假设不是必然的,这与现实不
符。而我们坚持现实的理由是,理论不仅应当涉及如何理解世界(这是所谓认识
论)或者说世界是如何形成的(这是所谓存在论),还应当涉及生活如何运转。
也就是说,理论还应当具有“规范”的特性。许多因素都会牵扯到部分人的利益或
导致部分人的苦难,而针对这些问题,经济学是否都有能力去面对并解决呢?可
能也正是因为如此,我们才必须要不停地追问:“经济学正确吗?真的有用吗?”
[4]
而其他学科可以不需要证明这些问题就可以坦然地存在:委托和精神上的信
仰不需要得到外界客观事实的证实。统治阶层经常会抵触观点和证据。官员、神
职人员、先知以及领导者不会总是屈服于实验结果,但是欧洲和美国的启蒙运动
者却以批判的观点和证据探索了现实。我们认为,科学就应该遵循这种方法。而
经济学,如果想要寻求同样的社会尊重,也应该遵循一样的研究方法。
经济学到底建立了什么样的“规范”?其研究开始于最大化“财富”或者说“福
利”这样值得赞赏的原则。然而,福利被定义为个人想要得到的东西。这就是所谓
的“方法论中的个体论”原则。当一个人能够获得更多他想得到的东西,而没有剥
削别人的财富时,我们就说发生了社会进步,即所谓的“帕累托改进”[Pareto
improvement,这是以意大利经济学家维尔弗雷多·帕累托(Vilfredo Pareto)的名
字命名的]。在社会不存在懒惰现象的情况下,如果没人损失,就没人获取。我们
通过交易达到这样的社会状态:人们卖出他们不那么需要的物品(包括劳动
力),同时买入他们更需要的物品。每个人都有可以用于出售的东西。如果每个
人可以自由交换,那么整个系统就可以实现良性均衡,即所谓“帕累托效
率”(Pareto efficient)。这种状态在18世纪就是亚当·斯密期盼的在“看不见的
手”的作用下所达到的状态。 [5]
在这样的系统中,每个人都可以获得与所能出售物品相对等的价值,所得即
应得。这样的理想市场状态,岂不是与一个更广泛的学说直接关联在一起了!这
个学说叫作“公正世界理论”。这一概念虽然来源于社会心理学,但是在此以另一
种不同的内涵得到了应用。 [6]
“公正世界理论”非常简单:它认为每个人都获得
了自己应得的东西。即使西班牙宗教法庭烧死了异教徒,那也是因为他们罪有应
得。即使苏联的农民挨饿或者被驱逐,那也是他们应得的下场。同样,纳粹分子
和犹太人所为和所遭遇的,也都各有理由。“公正世界理论”无处不在,带有政
治、宗教、种族、性别和文化含义。这个理论荒诞地认为世间所有的痛苦都有其
合理性。
而市场自由主义就是这样一种意义上的“公正世界理论”。1976年的诺贝尔奖
得主米尔顿·弗里德曼就曾写道:在自由市场社会中,可以直接证明国民收入分配
合理性的原则,就是要让每个人按照他生产的产品,以及他拥有的工具生产的产
品,来分配其所得到的财富。 [7]
换言之,每个人都得到了他应该得到的。财富
和能力的初始禀赋分配以及相应的市场产出这两者(正如弗里德曼所说)在学理
上都应当各得其所。他认为,自由市场经济不仅是有效率的,而且是公正的,它
体现了一种无法违背的自然秩序。个体规范给予了市场经济社会当中存在的不平
等以及经济困难现象一个看似合理的解释。这是19世纪古典自由主义倡导的自由
放任观点的突出表现。虽然不是每个经济学家都接受自由放任所秉承的伦理价值
观点,但在经济建模过程中,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这一假设是普遍存在的。
市场自由主义十分激进。如果你天真地认为个体的自利行为真的能够让集体
福利最大化,那么就表示你间接承认了任何形式的集体行为都很可能损害福利或
者减少福利。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20世纪70年代以来,许多与政策有关的经济
分析实际上都以此为出发点。这是一个相当反直觉的结论,而实际情况真的是这
样吗?诺贝尔奖的重要作用之一在此呼之欲出,那就是提供公正的科学验证。自
利或者说市场出清这种“看不见的手”的理论,与我们所做的许多有组织的社会改
进活动的努力方向并不一致,特别是在社会民主问题上,这一冲突更加明显。
社会民主对经济学的挑战
19世纪后三分之一时段,贸易集团和社会民主党派有所发展并抵制了这一预
先假设。 [8]
他们的活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首先在澳大利亚的政府中产生了
影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又开始在欧洲的西北部产生影响。社会民主(在本
书中我们这样称呼这种社会实践)跟那一时代的经济学相比有不同的优先考虑顺
序。在经济理论中,行为是由独立自主的个人支配的。在社会民主问题中,基本
的行为冲动不是为了获得个人满足而是出于义务,基本的活动单位不是个体而是
群体、家庭、阶级和国家。初始目标并不是获取私利的满足,而是获得安全感。
更明确地说,是处理生命周期中的偶然问题。相较于经济理论中激发行动的个人
渴望而言,社会民主是受到如何处理依赖关系这样的社会问题支配的。
在生命周期中,每个人都要经历自己不能供养自己的时间段。在最初为人母
阶段、幼年以及孩童阶段、受教育阶段、生病阶段、失业阶段、残疾阶段以及老
年阶段,生活成本都是非常高而且非常消耗时间的。 [9]
在处于依赖状态的时
候,除了可以要求人权之外,我们没有可以用于出售的产品来讨价还价,我们没
有可以立足的能力,在谋划人生上也没有远见和能力。“福利”问题就是解决如何
在整个生命周期中将资源从生产者手中转移到具有依赖关系的人手中。在美国南
北战争的年代,失业问题几乎威胁着每一个从事手工劳动的家庭,因为失业会使
其丧失赖以生存的基础。
社会民主和市场经济学说之间的区别很容易描述,即如何处理不确定性问
题。对每个个体而言,依赖的时机和程度是不确定的。然而从总体上说,社会作
为一个整体,互相依赖的程度是众所周知的,其未来的情况也是可以精准预测
的。在社会民主问题上,可以互相支持,从一代人向另一代人的横向转移,从生
产者向受赡养者的转移,都是通过税收实现的。在这样一个社会保险系统中,受
赡养者的风险是储存在一个池子当中的。有多少财富可供转移是由纳税人和接受
者之间的政治平衡决定的。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每个人都做出贡献并从中受
益。 [10]
相比于弗里德曼,在社会民主学说中(也称为“公正世界理论”),每个
人都各得其所。这就把福利来源的权利扩展到了整个国家和政府。在瑞典,社会
民主被认定为“人们的家”,其领导人这样说道:
家的基础是共同性和相互性。一个好的家庭不会有特权,也没有人受轻
视,家长对待自己的子女和继子女都是一样的。没有人会轻视他人,也没有
人会利用他人来获得好处……在好的家庭中你会看到平等、同情、合作和互
助友爱。 [11]
社会民主甚至更注重性别平等,它并不关注市场,而是更加关注家人和家
庭。在诺贝尔奖项设立30年之后,才有一位女性——埃莉诺·奥斯特罗姆,获得了
诺贝尔经济学奖,她是迄今为止唯一一位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女性。
相较而言,在经济学问题上,风险是由每个独立个体导致的。每个人从年轻
时开始不断支付保险费并不断存款,从而将自己的财务索偿权安全地转移到养老
问题实际发生的未来。证券和其他商品一样,每个人按照各自能承受的限度,在
金融市场上以保险和储蓄的形式购买。风险由保险公司和银行储备在资金池中。
每个人按照商业合同的规定来享受保险。
在未来获取利益的方式上,两种学说是不同的。但是,在两种学说之间还有
重叠:对生产而言,两者都依赖私人所有权和管理,并且通过市场进行分工,或
多或少都有竞争性;两者也都依赖政府,从而寻求一系列公共产品和集体产品,如国防和公路。
工人诉求、贸易联盟、社会主义、土地改革运动以及社会民主等社会现象,都需要有一个智慧而合理的解释,而维多利亚晚期的经济学说就解决了这一问
题。 [12]
自由经济学家主张维持现存的财产秩序及其不平等性。在西欧、北美和
澳大利亚,社会民主最终战胜了法西斯主义,建立了福利国家,在战后的30年中
保卫了资本主义结构并主导了政策。它使经济增长更可持续,并使财富分配更加
平等。为了实现这一点,它必须挑战新古典经济学的假设,有时候甚至要摒弃这
些假设。
与正统经济学中一切自由这一竞争性思想相较而言,社会民主党派在战后欧
洲(英语国家)建立了一系列的共同意志:
建立用于供给养老需求的集体保险,由政府规范和管理,通过渐进式
税收实现。
通过租赁控制、新建房屋、抵押机构、公共或者集体所有权来实现高
质量可负担房屋的供给。
提供更好的中等和高等水平的教育,支持科学研究,开展文化和体育
活动,有计划地使用土地,修建公路和铁路。
在一些扩展公共服务和国有企业领域建立混合经济,但是仍然保持对
生产和分配管理的私人所有权。
对弱势群体要进行特殊关注。 [13]
美国也实行了很多这类方案,即使不能提供全民健康权利保障,至少也会向
老人及贫困人群提供这种保障。
这些服务看上去都非常昂贵:由政府管理,从税收中支付,在欧洲西北部,政府在这方面的支出在20世纪70年代末甚至占到GDP的40%~50%。但是选民认
为:总体而言,对纳税人来说,这一支出带来的好处是大于成本的。 [14]
它将购
买力从消费旺盛的年份推迟到了真正有需要的年份。赚钱的人帮助那些暂时需要
供养的人:母亲、儿童、学生、失业者、残疾人、病患以及年迈的老人。反过
来,有生产能力的人也期盼当自己处于人生中需要被赡养的阶段时也能够得到这
些帮助。税收是渐进式的,所以那些富有的人就会缴纳更多的税,相应地从税收
中得到的更少。在福利较高并且是全民享有福利的情况下(即所有人可以均等享
有),那些收入较低的人相应地受益更多。 [15]
发达国家的这种不平等在中世纪
时期达到了最低水平。
竞争观
将第二次世界大战归结为是美国南北战争期间传统经济学失败的结果,并不
牵强。 [16]
在1944年,战势依然肆虐,两家媒体报道了两位经济学家提出的对未
来的不同看法,这两位经济学家在30年后的同一天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一是
《战后瑞典劳工计划》(The Postwar Programme of Swedish Labour ),由当时瑞
典执政的社会民主党发表,其合著者是经济学家纲纳·缪达尔[他的画像还在我们
的夹克衫里,画像里还有他的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妻子阿尔瓦(Alva)]。 [17]
二是《通往奴役之路》(The Road to Serfdom ),由哈耶克所著,在英国发表。
[18]
瑞典的社会民主党于1932年执政,它使瑞典远离战争。 [19]
它于1944年提出
的项目计划是其社会抱负达到顶峰的表现。它谴责内战经济学容忍了失业和贫
穷,战争甚至刺激了处于中立的瑞典生产资源的流动,而瑞典本来应该是一个世
界和平的典范。27项具体的挑战体现在三个大的方面:“充分就业”(这是社会安
全的主要保障),“公平分配和更高的生活水平”(这意味着从资本到劳动力的重
新分配),“更高的生产效率和提升的工业时代的民主性”(确立了经济增长的目
标)。这是瑞典社会民主党最突出的特点:纲纳·缪达尔的创新之处在于他提出了
所有人的安全和平等也具有生产性这一观点。 [20]
由于精神问题和社交能力的不
足可能导致有些人不能工作,而热衷于改革对这些人是缺乏同情心的,这是改革
的负面问题。 [21]
不论怎样,整体来看,这对传统经济思想来说也是一种清晰
的、适度的且带有民主性的挑战。 [22]
在哈耶克看来(他是在伦敦经济学院任职的奥地利籍教授),社会民主是“通
往奴役之路”的第一站,它甚至会开启专政之路。但这本专著也容易让人对理解他
的观点产生偏激:哈耶克实际上认可那些对社会保险及其他方面的政府干预。他
一方面对社会民主的“社会”方面感到不安,另一方面也对“民主”的一面表现得比
较谨慎。自由作为专政的对立面,并不一定会引发民主,还必须避免多数人的暴
政。 [23]
“我宁愿暂时牺牲..民主,如果是在自由实现之前必须这么做的话。”他
于1981年在智利接受访问的时候这样说道。 [24]
《通往奴役之路》在英国引起了轰动,当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这本书之
后,美国的反响更是热烈。 [25]
它的发行量巨大,在《读者文摘》(Reader.s
Digest )中发表的缩编本的发行量超过100万册。在畅销周刊《看》(Look )上
发表的卡通版本也获得了通用汽车和通用电气的免费资助发行。卡通版本省略了
关于社会保险的章节。此书还被迅速翻译成瑞典语,在瑞典成为反对社会民主的
一个焦点问题,而社会民主党候选人对权力的把握在瑞典从来都不是很稳固。
[26]
哈耶克关于社会民主的滑坡理论曾经被荒诞地歪曲:在世界上没有哪一个社
会比北欧福利国家更加远离奴役境况。政府高度干预的混合经济很多年来都保持
了政治自由和经济自由,然而自由体制和极权体制却都未达到这种状态。 [27]
但
是随后哈耶克不断否定经济学的科学地位,一直到后来其发表诺贝尔奖获奖演说
时都是如此。
哈耶克当时在英国已经被约翰·梅纳德·凯恩斯边缘化,但是在美国却被奉为
名人。他将他在文学和财政方面的成功转化成政治方案。1947年由商业基金会出
资,在瑞士朝圣山酒店举办了一场经济学家、记者和商人的聚会。经过几天的深
思熟虑,这些参会者发起成立了朝圣山学社。从那年开始,在美国基金会的资助
下,社团定期在舒适的大酒店召开聚会,从而成为抵制社会民主的思想焦点。
[28]
在大概20年的时间里,这一社团由哈耶克掌管,由他来审核所有的新成员。
第一次聚会邀请了一些欧洲和美国的持有反劳工立场的主要知识分子,其中包括
几位未来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哈耶克、米尔顿·弗里德曼、乔治·斯蒂格勒、贝蒂·
俄林和莫里斯·阿莱斯(虽然后两位学者拒绝了邀请)。 [29]
另外一位参加者,哲学家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即《开放社会及其敌人》(The Open Society
and its Enemies ,1945年)的作者,甚至提出应该向外部批评家开放社团会议,但是遭到了哈耶克的拒绝。 [30]
“自由”并不等于开放的思想。
多年以后,米尔顿·弗里德曼向社团的官方历史学家马克斯·哈特维尔(Max
Hartwell)这样描述社团的发展进程:
在朝圣山学社成立会议上我们所预计的对自由社会的威胁,与经过干预
时期后所凸显出来的对自由社会的威胁有很大不同。起初我们担心的只是中
央计划经济和广泛国有化问题,而新的威胁是经过福利国家和重新分配而发
生作用的。很不幸,这种威胁没有消失,而仅仅是改变了特性而已。尽管如
此,我仍然相信在解释所谓的自由主义重现这一问题时将这个变化指出来还
是非常重要的。就像多年以前由国际妇女服装工人联合会制作的音乐剧《坐
立不安》(Pins and Needles )中的一首歌的歌词写的那样,“向前一步,向后两步,这就是我们的进步之路”。 [31]
这句歌词颇具讽刺意味(它也恰是列宁手册的标题)。 [32]
这部音乐剧源自
纽约犹太移民文化,而弗里德曼也诞生于这种文化当中。该音乐剧是由国际妇女
服装工人联合会的成员创作和制作,演员阵容中有剪刀工、粗缝工和缝纫机操作
员,1937—1940年,这部音乐剧在美国百老汇表演了1 000次以上,甚至在富兰克
林·D.罗斯福当政期间还在白宫进行了演出。弗里德曼在1985年写这封信的时候,虽然相当悲观地再次引用了这句音乐剧中的歌词,但这种表达成为朝圣山学社颇
具渐进主义色彩的漫长发展中极富幽默感的一笔。朝圣山学社最终获得了巨大的
成功,这种成功绝非仅仅体现在其八个成员都荣获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还包括在
此过程中其获得的巨大声誉。
理论及其成效
诺贝尔奖可以证明经济学建立的理论有相当深厚的理论储备。的确,只有一
小部分经济学家加入了朝圣山学社或者说支持其目标,但是其中最著名的部分成
员是诺贝尔奖得主。市场自由主义的支配地位几乎就是诺贝尔奖项设立的时间。
我们可以这样描述:1967年12月,米尔顿·弗里德曼做了美国经济学会会长致辞。
[33]
其所传达的信息相当具有鼓动性:与社会民主相关的凯恩斯经济政策使失业
和通货膨胀不再处于困境。在接下来的7年里,弗里德曼成为所有经济学家中被
引用得最多的经济学家之一,暂时超过了亚当·斯密,而后者此前一直是被引用次
数最多的经济学家。 [34]
这次演讲标志着在两个学说之间由来已久的历史博弈过
程中的一次变化。一方面,社会民主化是一场致力于减少大多数人的不安全和不
平等的政治运动,其方式是通过渐进式的税收来提供健康、教育以及避免生命周
期中的不确定性。另一方面,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学说(作为更广泛的新自由化和
市场自由化的社会运动学说)却用于毁灭这些改革。在接下来的几十年,新自由
主义(学说)以及市场自由化(运动)做了许多事情来反转战后福利国家,然而
对西方社会的大多数人来说,繁荣和前途一直持平甚至出现下降。但也就是在这
几十年当中,一定程度上因为新自由者所倡导的全球化,世界范围内的繁荣有所
增长。印度和巴西等虽没有屈从于市场自由化指令,但实际上也跟随日本、中国
台湾、韩国和新加坡这些先驱经济体渗透进了西方市场。 [35]
社会民主化背后并没有经济学那样巨大的智力团队。 [36]
在诺贝尔奖得主当
中,只有纲纳·缪达尔可以被看成是直接的倡导者(虽然在我们所处的时代,大约
有一半的诺贝尔奖得主倾向于社会民主主义,并且总体来说在经济学家当中占到
一个更高的比例)。 [37]
虽然没有许多学说理论,但是其实际的成功跟市场自由
化的成功一样显著。如图0.1所示,在处于主导地位的经济与发展合作组织国家当
中,大约30%的收入用于社会保险以及社会政策,并且由中央政府进行分配(底
部曲线)。1990—2008年,这一比例仍然处于上升状态。社会保险这一考虑因素
在选民中比重新分配问题更加受欢迎。 [38]
美国定期选举保守人士担任政府要
职,但是在对社会保险这样一个更小的部门进行的私有化尝试到目前为止是失败
的。原因就在于,对社会保险而言,社会民主主义方法更有效率, [39]
但是并不
安全。社会民主主义就其劳动观点来看与市场自由化直接发生冲突。对市场自由
化而言,工作像其他商品一样,可以随意购买和销售。“随意”(at will)是美国现
在的就业学说,允许工人在任何时候没有任何理由就被解雇(除非受到合同保
护)。对大多数人而言,这是极度不安全感的根源,因为家庭负债(如抵押贷款
的月供和孩子的教育支出)被锁定到未来很远的时间,工作让人有尊严、让人有
奋斗的目标。至少在美国,医疗保障普遍与就业联系在一起。在今天的欧洲市场
自由化进程中,“劳动市场弹性”很大,寻求与美国的“随意”就业学说相接轨。
图0.1 社会支出占政府支出的百分比和政府支出占GDP的百分比(1990-2008年)
资料来源:OECD, “按目的地国政府支出” (2014年)
注:GTE表示政府支出总额,SOC表示社会支出(健康、教育和社会支出保险 福利)GDP表示国内生产总
值。
2008年,金融市场必须由政府出手救市来避免更加荒唐的局面,这是无论是
社会民主人士还是市场自由主义者都不曾预见的政府干预的福利。但这么做并没
有得到任何赞同。相反,市场自由主义者将出现的赤字看作一种可能击垮福利国
家的星星之火,就像一个将要溺死的人只顾着跟他的妻子一起逃生,却任由身边
的求助者溺死一样。这样的故事在此书完结的时候还在继续。
我们要讨论的话题既不是针对单个诺贝尔奖获得者所获得的成功,也不是简
单地将诺贝尔经济学奖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实际上,我们采用了几种方式来
研究。 [40]
一套学说怎样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成功地激发了政策,实际上反映的是
经济学的世俗力量。而经济学说更容易从外部观察,比如从学说的使用者那里得
以反映,而并不是更多地由其创始人去主动评论。那些将经济学说用于政策制定
的人实际上很少精通经济学精髓思想。同样,对那些受到经济学说影响的人而
言,他们的观点,也就是我们采用的观点,也一样不是精通经济学的人表达的观
点。
本书的主旨
经济学通过构建简单的经济行为模型并将其集中体现在政策中来发生作用。
将个人的逐利性这一前提与社会和谐结合在一起实在是一项野心勃勃的事业,以
至于无论是客观分析还是经验判断都毫无争议地宣告这种尝试的失败。为摆脱这
些弱点,芝加哥学派的经济学家提出,盈利公司应该取代福利国家,这与政治上
的新右派观点是一致的。对于一种宣扬合理性的学说而言,诺贝尔奖是一个十分
反常的现象,是一个戏法,是单方面授予的一个奖项,就像赠予礼物一样。讽刺
的是,这样的一个戏法反而被看作是科学,甚至摇身一变成为一种权威。自然科
学家认为理论必须跟证据相符。然而在经济学研究中,因为实证上的失败,方法
论者已经不再对经济学做这种要求。许多实干家已经得出了相反的结论,并对核
心的学说提出了相反的意见。抽象理论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就达到了顶峰,然
而,在实验室里、实践中和自然科学实验中都出现了新的“经验转向”,几乎没有
提及市场出清理论。好几个诺贝尔奖得主也都对核心学说提出了疑问。
诺贝尔经济学奖起源于瑞典社会主义和商业精英之间的冲突,在西方社会更
广泛地存在于阶级冲突的当地化表现中。瑞典在“一战”中是中立国,具备丰富的
能力和自然资源禀赋,在战争中,很容易地转向了社会主义。在欧洲大多数国家
中,债务负担的挑战在国内和国际危机时刻达到顶点。1945年之后,瑞典执政的
社会民主党将住房和充分就业放在首位,而中央银行出于价格稳定的考虑,抵制
这一做法。政府扼杀了银行,于是银行寻求出路来坚持自己的主张。恰逢此时,诺贝尔经济学奖在1968年得到中央银行的捐赠,而当时社会民主主义的成功处于
巅峰。
经济学有政治偏见吗?我们可以用诺贝尔奖得主在学科中的引用统计和观点
纵览来研究这一问题。这一奖项的管理人(一个经济学家小组)努力保持左派和
右派之间的机制平衡,但是从总体上来说,在学科内部还是更倾向于观点天平的
右派,这是因为倾向于社会民主价值观的经济学家人数较左派多出了一两位。诺
贝尔奖评定委员会通过选出游戏顶端的学者而获得可信度。当然也有例外,比如
哈耶克,他在获奖前本来默默无闻,但是得奖使他的论文引用量得到飙升。委员
会也阻止过几位被高频引用的学者,其中至少有两位是基于意识形态的基础而进
行研究的。19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50年代是诺贝尔奖的第一个历史阶段,市场出
清的均衡经济学与古典自由主义的低税准则是一致的。社会民主主义在战后的成
功挑战了这一模型。经济学弹指之间就对此做出了回应,它用恶意动机假设代替
了协调假设这一研究基石。它基于效率挑战了社会民主主义,但是这一反转让实
践付出了代价。协调主义学说使制定理想的政策成为可能。而恶意假设使产出难
以确定。唯利是图不再带来最好的产出结果。经济学的权威被无形地破坏了。与
此同时,恶意假设又助长了恶意的发展。
在瑞典,社会民主主义受到一些与阿瑟·林德贝克教授有关系的经济学家的直
接挑战,林德贝克教授管理着诺贝尔奖项。林德贝克关于社会民主无效性的论断
并没有说服力。他警告的经济危机确实发生了,但不是以他预期的原因引发的。
这场危机是由金融管制的过于宽松导致的,而林德贝克和其他市场自由经济学家
对此观点持支持态度。当被邀请进一个右倾政府来制定政策的时候,林德贝克并
没有因此感到不安,他开出了一个收缩劳动津贴的药方。他的改革方案被部分执
行,但是它们的关联性受到质疑。尽管存在市场自由主义,但是瑞典的社会民主
主义还是可以适应的,它成功地经历了政府中各党派的变更和去工业化这一社会
变革。
在斯堪的纳维亚以外,有利于市场运行的改革受到在华盛顿得到支持的国际
金融机构的推行。“华盛顿共识”将信用扩展到发展中国家,但它以有利于商业发
展的宽松管制为前提条件。但这么做导致了一个预期之外的后果,那些借款国家
腐败盛行,而后这一后果又蔓延到居于核心的西方经济体,现在这一现象已经非
常普遍。这一难以捉摸的问题,使经济学宣称的种族中立遭到强烈谴责。这证明
了一点,即学说中的种族中立会导致更高昂的经济和社会成本。
总之,经济学的影响力与其作为哲学、一门科学学说以及一套政策的缺点相
比并不匹配。“看不见的手”是一项神秘的定律,但它反复失灵,到现在影响变小
了。另外,经济学有一套实证办法并取得了成功,有其技术上甚至科学上的可信
度所能解释的领域。这表明了一些权威的丧失,但并不是完全丧失。经济学并不
比其他的权威来源更有优势,但与其相比也不是更具劣势;它只是应该被看作许
多声音中的一种而已。从这一角度来讲,它更像是社会民主主义。诺贝尔奖评定
委员会认为经济学并不仅仅是一个孤立的包罗万象的思想体系,它要承认经济实
践的事实,诺贝尔奖评定委员会就可以一直保持这一奖项的可信度。社会民主主
义提供了一种解决办法,这种办法在实效上更具成功性,分析上更具连贯性,经
济上更具有效性,道德上更具吸引力,并且理论上更适度。
[1] Ahlqvist et al.,‘Falkst Pris i Nobels Namn’[‘False Prize in Nobel.s Name’](2001);Nobel,‘Alfred
Bernhard Nobel’(2001),260.
[2] Kincaid,Oxford Handbook of the Philosophy of Economics(2009);M?ki,Philosophy of
Economics(2012).
[3] Akerlof,‘The Market for Lemons’(1970);Offer,‘The Markup for Lemons’(2007).
[4] As per Blaug,‘Why I Am Not a Constructivist’(1994),118-119.
[5] Offer,‘Self-Interest,Sympathy,and the Invisible Hand’(2012).
[6] Rubin,‘Who Believes in a Just World?’(1975);Lerner,Belief in a Just World(1980).
[7] Friedman,Capitalism and Freedom(1962),161-162.
[8] Deane,‘Scope and Method of Economic Science’(1983).
[9] Offer,‘Economy of Obligation’(2012).
[10] Hills,Good Times,Bad Times(2014).
[11] Per Albin Hansson,Swedish Parliament,Andra Kammarens Protokoll Nr 14-19[Second Chamber
Debates],no.3,28 January1928,11.
[12] Deane,‘Scope and Method of Economic Science’(1983);Mirowski,Effort-less Economy of
Science(2004),chs.13-14;Gaffney and Harrison,Corrup-tion of Economics(1994).
[13] For Norway and Sweden,Sejersted,Age of Social Democracy(2011).
[14] Lindert,Growing Public(2004),II;Hills,Good Times,Bad Times(2015).
[15] Rothstein and Steinmo,‘Social Democracy in Crisis?’(2013),99.
[16] Chapter 3,below.
[17] Landsorganisationen,Postwar Programme of Swedish Labour(1946,originally published 1944).
[18] Hayek,Road to Serfdom(1944).
[19] Berman,The Social Democratic Moment(1998).
[20] Andersson,Between Growth and Security(2006),ch.2.
[21] Andersson,ibid.,ch.3;Myrdal,Nation and Family(1941),ch.6(revision of Alva and Gunnar
Myrdal,Kris i Befolkningsfr?gan[1934]).
[22] Landsorganisationen,Postwar Programme of Swedish Labour(1946),3-5.
[23] Burgin,Great Persuasion(2012),116-120,esp.119.
[24] Caldwell and Montes,‘Friedrich Hayek and His Visits to Chile’(2014),47.
[25] S?derberg et al.,‘Hayek in Citations’(2013),66-67.
[26] Lewin,Planhush?llningsdebatten(1967),267-273.
[27] Alves and Meadowcroft,‘Hayek.s Slippery Slope’(2014).
[28] Mont Pèlerin Society Papers,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Stanford Univer-sity,and
Liberaalarchief,Ghent;Hartwell,HistoryoftheMontPèlerinSoci-ety(1995);Walpen,Die offenen Feinde
und ihre Gesellschaft(2004);Mi-rowski and Plehwe,The Roadfrom Mont Pèlerin(2009);Burgin,The
Great Persuasion(2012),ch.3.
[29] Allais did so later.
[30] Burgin,The Great Persuasion(2012),95.
[31] Friedman to Max Hartwell,10 July 1985,Hoover Institution,Friedman Pa-pers,200-10.
[32] Lenin,One Step Forward,Two Steps Back(19041947).
[33] Friedman,‘The Role of Monetary Policy’(1968).
[34] See figure 6.9,below.Kenneth Arrow also overtook Smith for a few years.
[35] Alpert,The Age of Oversupply(2013);Lin,Demystifying the Chinese Economy(2011);
Wade,Governing the Market(1990);and chapter 11,below.
[36] Myrdal,Kris i Befolkningsfr?gan(1934);Crosland,Future of Socialism(1936);Korpi and
Palme,‘The Paradox of Redistribution’(1988);Esping-Andersson,Three Worlds of Welfare
Capitalism(1990);Rothstein,Just Institutions Matter(1998);Barr,Economics of the Welfare
State(2012).
[37] Below,chapter 5,figure 5.2.
[38] Taylor-Gooby,Double Crisis ofthe Welfare State(2013).
[39] Offer,‘Economy of Obligation’(2012).
[40] Grüske,Die Nobelpreistr?ger der?konomischen Wissenschaft(1994);McCarty,The Nobel
Laureates(2001);Vane and Mulhearn,The Nobel Memorial Laureates in Economics(2006);Breit,Lives ofthe Laureates(2009);Horn,Roads to Wis-dom(2009);Karier,Intellectual Capital(2010);
Klein et al.,‘Ideological Pro-files of the Nobel Laureates’(2013);Ghosh,‘Beautiful Minds’(2015).
第一章
假想机器
提到经济学家,我们通常都认为他们是为世界代言的清高群体,但实际上绝
大多数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都与世俗脱不了干系。“经济著作大部分都以推测为
主,都是对可能性世界的不确定探索。” [1]
大约一半的诺贝尔奖得主都主要致力
于学说框架、假想机器或者简单说就是“模型”的构建。这一术语其实可以与“模型
飞机”这种表述联系起来理解,但又不像模型飞机,因为经济学模型大部分都停留
在纸面上,通常以数学方程的形式存在,但是也有类似于机械上的那种可以构建
的经济模型。比如,菲利普斯的国民收入模拟液压计算机(Phillips MO-NIAC)
就可以模仿经济中的货币循环,它通过在玻璃管道中注入带颜色的水和可控制的
阀门,从而实现对政策选择的模拟。 [2]
模型的构建
英国的牛津市有一个巨大而美丽的开放空间,叫作港口草地,距离城中心很
近。因为是公有财产所以它没有被开发,这违背了市场准则。周末,这里往往会
吸引一些航模爱好者,这些航模一整天都在头顶发出声响。然而经济模型却几乎
不能被带到港口草地上去,也不可能飞行。想要离开它们的设计者去知晓它们真
正的适航能力有多好,是相当困难的。
港口草地市郊还有一座令人辛酸的纪念碑(见图1·1),它是为了纪念1912年
在那里坠机的两位优秀的飞行员。这座纪念碑凸显了科学与经济学模型之间的差
别。小型侦察机飞行器预示着真正的进步,而英国第一次有动力的飞行仅仅发生
在那次坠机事故的四年以前。这种革新是冒着生命危险来检验的,而不只是靠纸
面上的推测。它不仅需要钱来推动,还需要合作和竞争,由政府参与执行,并且
在特定的地点完成,以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但是在主流的或者新古典的经济学
中,模型并不在特定的时间和地点存在。如果这些模型被否定,那也不是靠实践
经验来否定,而是被其他经济学家所否定。 [3]
这还不是问题的终结。用琼·罗宾
逊(Joan Robinson,她是有资格获得诺贝尔奖的,但并未获奖)的话来说:“在一
个学科中,如果没有发现能够被广泛认可的某种可以证明的错误,那么该学说就
会长期存在。” [4]
经济模型并不容易设计,它需要跟一系列的制约条件相协调,包括已经存在
的信念、政策和政治导向、一些更大的理论、内部一致性、数学技术、程序化的
事实(例如生产者、消费者、税收),以及与真实世界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行类
比。 [5]
经济模型还需要由实证观察来证实:它必须像飞行模型那样,能
够“飞”起来。 [6]
图1.1 牛津伍尔弗科特(Wolvercote)公墓的航空纪念碑
资料来源:照片由阿夫纳(Avner)提供。
两个已有的知识点是经济学学说的核心思想:“学说个人主义”和“看不见的
手”。 [7]
经济活动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私人逐利的驱动,它会累积到一个很有效率
的状态(均衡),在这一状态下,供给等于需求,所有的市场达到出清状态。亚
当·斯密在经济学说中只提到过一次“看不见的手”这一概念。他并没有说明“看不
见的手”是如何起作用的,虽然他确实举了一个非常完美的例子, [8]
但它依然只
是一种猜想、一种信念。 [9]
想要证明均衡的有效性,想要从数学上证明其存
在,这种探究已经有很长的历史了。 [10]
我们可以跳过亚当·斯密之后的一个世
纪,从1874年的莱昂·瓦尔拉斯(Leon Walras)开始研究。他描述了这样一种经
济状态:所有价格都可以通过一种想象中的拍卖达到均衡水平,在拍卖中不会有
卖不出去的剩余产品。1881年的弗朗西斯·埃奇沃思(Francis Edgeworth)和1906
年的帕累托不约而同地阐述道,当贸易双方交换商品的时候,如果能够成交,那
么就能分享与自身讨价还价能力相匹配的所有可以得到的利益(这就是已经在前
文中提到的“帕累托改进”)。埃奇沃思还拿出理由说明即使有无数交易者,那么
均衡点也会是唯一的。 [11]
20世纪30年代一个更具包容性的思想——“福利经济学”被提出。它证实在市
场交易中达到“效率”所要具备的条件,即所有商品都能卖出去。简言之,这个条
件证明了一个更大范围的均衡性:当两种投入(即劳动力和机器)结合到生产中
的时候,所有生产者都可以得到同样产出,即产出值唯一。当价格下跌时,消费
者买得更多;当成本上升时,生产者就会提高所售产品的价格,需求和供给会收
敛在一个均衡点。换句话说,在下一次购买或者销售中,采用的“边际价格”,对
所有销售者和购买者都是一样的(就像开篇所举的两个交易者的例子),这样就
会满足效率需求,从而使所有产品都能销售出去。这种边际价格准则有时被看作
经济学的第三个核心理论。而这些限制性的一致性假设与目前所出现的任何经济
实践都是不相符的。事实上,经济学理论对于供给者之间是如何竞争的这一问
题,阐述得都不是很清晰(尤其对于没有价格差异的产品而言)。 [12]
真实世界
中并不存在这样的理想状态,所以经济学家的研究必须对其进行假想。
1954年,肯尼斯·阿罗、吉拉德·德布鲁和莱昂内尔·麦肯齐(Lionel
Mckenzie)分别宣称由瓦尔拉斯(还有埃奇沃思、帕累托和其他经济学家提到
的)所提出的单一均衡点是可以通过数学办法求得的。“一般均衡”[general
equilibrium,可简称为“阿罗-德布鲁均衡”]存在的证据被奉为经济学的神明之物,它揭示了市场魔力的秘密。 [13]
但是需要十分苛刻的条件,即没有任何一个交易
者能够影响市场价格(完全竞争),一般均衡才能真正发挥作用。最重要的是,要存在完全市场,也就是每一个消费者和生产者在任何时间及任何天气情况下
(无论是雨天还是晴天)都知道全部商品的全部价格,而且所有的商品(无论是
现货还是存货)都能全部实现交易。没有规模经济效应,在工厂中,单个工人尽
可能多地进行生产。一般均衡情况不考虑政府、货币、财政、垄断、合作、期望
以及随时间而出现的各种变化,也不涉及失业、分配和不平等。一般均衡也不讨
论如何实现这种均衡状态或者接下来会发生什么。这种假设虽然不符合任何客观
现实。这一模型告诉我们这样一种均衡在数学分析上不是不可能(它是“存在
的”),并且与可利用资源的充分使用具有一致性(“帕累托效率”)。但是这样的
平衡在数学意义上是否存在(稳定性属性),到目前为止仍然是一个疑问。 [14]
阿罗的合作者弗兰克·哈恩(Frank Hahn)认为完全市场假设完全是虚构的,阿罗
补充说:“一个这样的系统不可能存在。” [15]
哈恩又前进了一步,他认为一般均
衡的存在条件是极其苛刻的,因而一般均衡点也经常用来反驳“看不见的手”这一
说法,因为它们不存在。 [16]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认为完全信息和完全市场状态
始终不能实现(二者都不可能),所以均衡就不可能处于帕累托最优状态。 [17]
一个模型飞机在飞行中不断地在引力和浮力之间找平衡。当模型坠落在地的
时候,它获得了更稳定的均衡。类似的,在经济学中,均衡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
题。它看上去跟事实经验相符,特别是对那些境况相对富裕的人更是如此。桌上
有食物,银行里有金钱,商店里也是琳琅满目,汽车停在车道上。一个学期接着
一个学期,然后进入暑假,还有海外会议,事情看上去不断变好。但是实际上,在其他地方,还存在焦虑、失业、债务、疾病、离婚、长时间无趣工作、痛苦、歧视、精神错乱、监狱、战争和死亡。而市场如果需要所有刺激因素来激发那些
神秘力量,那我们就不能去阻止这些事情发生。如果你不喜欢它,你可以选择主
动远离它。那些内战中想要脱离贫困和不安全境遇的无产者,对均衡概念是没有
兴趣的。
在经济建模上,自利和均衡是优先考虑的因素,而他们把实际需要建立模型
的问题当作前提条件。二者都不是事实发生的。埃奇沃思和帕累托指出,两个自
利的当事人进行交换的时候将不会发生任何浪费,这是对潜在市场效率具有启蒙
意义的分析。 [18]
但是在接下来的几十年中,自利和均衡这两个优先考虑因素提
出了自身对经济模型精确的需求,好像它们本身自带了一些可贵品质一样。就像
苏联的指令性经济那样,新古典经济模型也体现了设计者的梦想和价值。在模型
中,自利是一个优点,像模型假定的那样,对自私实现了自证。在新古典模型
中,财产所有者可以实现自我满足而不必考虑那些拥有较少资源的人。如果经济
学家可以将模型展示(或制造)出来、用以与现实进行匹配,就已经很好了。如
果模型完全是正确的,那么社会不就是多余的了么。
模型如何发挥作用
经济模型通过类比,从而拓展到真实世界中。芝加哥模型的建立者罗伯特·卢
卡斯认为,模型构建的目的是从我们对一种情况的已知出发进行类比,进而分析
我们希望知道的另外一种极其不同的情况。 [19]
真实 世界将融入模型所示范的
完美标准中。但是模型与现实相比还是相当简化的。在某一必要方面,X就
像Y一样。它以两种方式之一来工作:要么其他条件不变(所有因素保持相
等),要么进行必要的更改。它不是一个现实中的模型,而是对它的抽象。在现
实中,X从来不等于Y,所以对于现实没有吸引力。没有什么观察和 测量能够表
明模型与现实的类比是错误的。卢卡斯写道,某一个人认为有说服力的类比,他
的邻居可能并不认同, [20]
这意味着没有什么客观的选择标准。
在经济论述中,一个模型仅需要证明其具有内部一致性。这个主题重现在卢
卡斯模型中,例如:
一个“理论”不是关于实际经济行为假设的一个集合,而是为了建立平
行或者类比系统的一套精确假设——一个机械的、模仿的经济。从这个观点
来看,一个“好的”模型不一定比一个糟糕的模型更“真实”,但是能够更
好地模仿现实。当然,通过“更好地模仿”所表现出来的东西将由一个人希
望回答的特定问题决定。 [21]
换句话说,模型不会像现实一样工作,但是可以模仿一些特定方面或产出。
这些听上去貌似十分可信,但是值得思考的是,既然在这样一个简单的维度上起
了作用(实际上经常不是这样),那又怎么可能在一个实际的有所发展的具有复
杂内容的历史经济中得到验证呢?
类比也是诗人的写作手法,就像诗歌中的隐喻一样,模型会引起美丽的联
想,虽然并不真实。 [22]
同样,经济模型通常跟直觉相反,但导致了认知的极度
震撼。把经济模型看成飞机模型就是一种隐喻。然而,经济模型远比机械模型复
杂得多。当参数变化之后,某些情况就可能出现(有某种特定的概率)。但是经
济模型并不能展示出遗漏某种因素会带来的后果,也不能说明有哪些因素被遗漏
了。这样的模型所得出的政策工具也几乎不可依赖。 [23]
相反,如果它是一门完
善的科学,即使在表述上多么具有学术性,也可以有力地支持和解释社会与经济
所赖以存在的技术(交通、通信、能源和健康)在日常生活中产生的必然影响。
模型要构建在合理的基础上。模型并不要求实验上的有效性,但实际上却应
该如此。数学家和博弈论学家约翰·冯·诺依曼(John von Neumann)在1955年写
道,模型可以独立存在,但是仅可以通过观察和经验有效性来证明其正确性。
科学家不解释,甚至几乎从不解释模型,他们的主要工作就是构建模
型。数学构想就是通过模型来表达,附加一些特定的语言表述,来描述观察
到的现象。这样一种数学构想的正确性是纯粹而精确的,从而让人们期待它
能起作用。 [24]
好的经济模型是反直觉的,并且要具备极强的说服力。英国经济学家大卫·李
嘉图(David Ricardo,1776—1823年)为模型构建提供了一个不朽的模板。他的
比较优势理论假设存在两个国家,每个国家生产两种产品,在这种情况下,即使
一个国家生产每种商品都是最便宜的,在两个国家进行贸易也是互利的。这一观
点发表于1817年,在今天的教材中依然存在,它奠定了自由贸易政策的基础。这
样有说服力的模型是不容易构建的。做这样一种反直觉的假设,并将这些假设融
入模型中而得出有意义的结论,非常需要天赋。这一点就足以成为有潜力的诺贝
尔经济学奖候选人进入候选池的屏障。外部有效性的现实检验,是最后也是最苛
刻的要求,还经常被遗漏。将模型与观察到的现实进行匹配的困难还有一个,那
就是没有现实能够完全符合模型。完全竞争这种只存在于想象中的模型,从来不
能被观察到,所以这一模型也就谈不上失败。这种不能匹配完全的现实情况曾经
被称为“涅槃谬误”。 [25]
但是对于市场自由主义者而言,“涅槃经济学”使任何真
实经济看上去都很糟糕,特别是对战后若干年中那些高税率的社会民主主义国家
所达成的共识。
李嘉图恶习
新飞机模型往往在风道中被测试:计算问题本身是不可依赖的,必须亲自试
验才行。从风道发展成一个实际可以工作的航线之间,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但
是经济模型很少因为实验而被拒绝。再以李嘉图为例,他是一个英雄形象的缩
影。除了比较优势理论之外,他还设计了其他令人信服的模型,这些模型表明,从长期来看,劳动工资会下降至仅够维持生活水平的状态,此外(单独在其他模
型中提出的),稳定的价格需要有货币黄金储备才能够实现。考虑这些模型的基
础,结论是不可避免的。这些模型运用了维多利亚时代的世界观,但是历史经验
将其抛在身后,今天这些观点不再正确。李嘉图的战略被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称为“李嘉图恶习”。
李嘉图的兴趣是要获得一个直接而且具有实际意义的清晰结论。为了实
现这一点,他将整个系统切割成若干部分,然后又尽可能地将其捆绑成大的
部分,最后将其冷藏——这样许多尽可能多的问题就成为“固定的”和“既
定的”。然后他将一个简单假设堆砌在另一个简单假设的基础之上,直到通
过这些假设将每个问题都妥善地安排好。他建立了简单的单向关系,以致到
最后他所期待的结果出现同义反复。例如,一个著名的李嘉图理论就是利润
由小麦的价格决定。在他的隐性假设下,这不仅是真实的而且是不容置疑
的,事实上不论问题大小,李嘉图的逻辑都是如此。利润不可能由其他因素
决定,因为其他因素都已经“既定”了,即固定不变。它是如此完美的理
论,以致从来没有人反驳或提出异议。这种将特定结论应用于解决实际问题
的习惯,我们应该称其为“李嘉图恶习”。 [26]
罗伯特·卢卡斯跟李嘉图一样善于运用模型。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他
是新自由主义构建模型领域的领军人物。他对于如何构建模型及模型能起什么作
用非常清楚。对卢卡斯而言,经济学仅是类似于机器构建的学科。“在经济思想上
的进步意味着构建越来越完美的抽象模拟模型并不是对于世界的更好的可表达性
的观察。” [27]
模型在计算机程序中得以精确体现。“我们的任务就是要编写
FORTRAN(公式翻译器)程序,这种程序把特殊的经济政策规则看成‘输入’,随
后以统计结果形成‘产出’,这些统计结果以时间序列描述我们关心的经济运行特
征,而按照我们的预期,这些经济运行特征是由这些政策产生的。” [28]
我们普遍认为,1945年之后出现的高增长、社会保险充分和巨大消费的经济
黄金时期应该归功于凯恩斯政策的实行,该政策允许政府来管理私人和公共需求
从而确保充分就业和较低的通货膨胀。 [29]
卢卡斯的项目,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是新自由主义的芝加哥学院及其分支学院发起的项目之一,它认为凯恩斯政策干
预是无效甚至是徒劳的。其他的研究项目有米尔顿·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它提倡
以一个不变的速度来提高货币供给量从而匹配真实GDP的期望增长率,进而获得
价格稳定。这是不可能起作用的,甚至会被认为是错误的。 [30]
在其他学说中,同负盛名的科斯定理(芝加哥学派喜欢这么说)认为资产的
初始分配并不重要,因为(在一个充满摩擦和冲突的世界中)市场交换会将其转
换成巨大的生产力。相反,罗纳德·科斯自己却希望经济摩擦会阻止这种情况。
[31]
乔治·斯蒂格勒的“管制经济学”认为管制对于有管制的行业是最有效的,对公
共行业无效;相关的“公共选择理论”(詹姆斯·布坎南及其他人提出)假定公务人
员仅受自我利益的驱使。 [32]
1995年,这些研究成果均被授予诺贝尔经济学奖。
爱德华·普雷斯科特、芬恩·基德兰德和托马斯·萨金特都曾与卢卡斯一起工作,后
来也都获得了诺贝尔奖。尤金·法玛在2013年因金融有效市场学说而获得诺贝尔
奖。 [33]
还没有获奖的是罗伯特·巴罗(Robert Barro),他提出了“李嘉图等价定
理”,这一模型源于李嘉图的思想。它认为用于增加需求的政府支出,会因为谨慎
的消费者在预期未来税收的情况下减少支出的行为而被抵销。政策重点在于政府
不会带来任何不同(即政策无效性),这意味着社会民主主义和凯恩斯管理政策
会完全无效。发展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阿尔伯特·赫希曼(Albert Hirschman)已
经提出,自法国大革命以来,改革的无效已经成为政治保守派的三个持久的比喻
之一,这就将芝加哥学派也置于政治保守派这一血统之中了。 [34]
理性预期
在这些学说中,从经济学家引用的情况来看,理性预期宏观经济学是最不歪
曲事实的,是最以经验为主的,到目前为止也是最成功的。这一学说在宏观经济
学领域有持续的影响力,在意识形态和方法论研究领域也被芝加哥市场学派的奠
基人和自由思想的“新凯恩斯学者”广泛应用。这是一个模型化方法:假设个体市
场参与者基于所有可以获得的公共信息形成对未来价格水平的预期。“形成他们的
预期”是指在分析可获得的信息时,公共成员被认为正在使用经济学家自己的统计
模型,而无论这些模型在技术上是多么难以实现。这使他们至少能够在平均水平
上对未来价格进行正确的预期。然后他们的利己选择从总体上决定经济进程
(即“宏观经济学”)。这一学说是一次分析上的巨大成就,被认为困难到足以使
其获得好几次诺贝尔奖。但是即使在它已经被理解和形成之前,它的应用也不是
每个人都可以胜任的。
现在考虑一个类似的系统:安提凯希拉装置(Antikythera mechanism)是一
个神秘的机械设计,它的残骸于1901年在地中海上的一艘古船残骸中被发现。在
对它进行了一个多世纪的研究之后,它被破译并重新组装成一个复杂的钟表装
置,有很多齿轮,能够成功预测月食及五大行星的星空位置。 [35]
这个模拟计算
装置,比19世纪之前的任何装置都要复杂,很显然是在公元前2世纪完成的,然
而其设计可以追溯到公元前3世纪位于锡拉丘兹的阿基米德。
经济学家与安提凯希拉装置的构造者共用同一个假设,即经济有一个类似于
在天体之间存在的潜在规律。在发表诺贝尔获奖演说时,莫里斯·阿莱斯这样说
道:
首先,任何科学存在的前提是要有规则存在的,这些规则可以被分析和
预测。在天体技术的研究上尤其如此。对于许多经济现象而言,这样的道理
同样适用。实际上,对于经济现象的全盘分析说明:适用于实体科学的那些
显而易见的规则,同样存在于经济现象之中。这就是为什么经济学也是一门
科学,以及为什么适用于实体科学的那些普遍规则和方法也同样适用于这门
科学。 [36]
但是跟安提凯希拉装置不同的是,经济学家的机器不是实体的。它是一种想
象中的构造,从来不会沿着路面翻滚,也不会在跑道上着陆,而且不会预测月
食,即使失败也不容易被发现。这种机器只存在于想象之中,但是对不同的学者
而言是如此不同。在理性预期理论中,经济学家的机器也出现在经济中的每个个
体的头脑之中。用托马斯·萨金特(理性预期学派的发起人之一)的话说就
是:“在模型中的所有当事人,计量经济学家和上帝都共同分享同一个模型。”
[37]
上帝和其他人所做的假设是当前价格紧紧围绕着金融及其他资产的真正价值
而波动。资产价格是对未来现金流入的以现值表现的索偿权,所以真实的价值意
味着这些未来收入及经济的未来进程都是事先决定的,也就是可知的,这样就没
有不确定性(有一些说法体现了不确定性,但是这些表达缺乏“理性”)。每个个
体都掌握所有的数据,都能使用最好的经济模型。这样一来,资产价格就是“正确
的”,市场价格的均衡点就代表了资源的最佳分配;换句话说,它是合理的。任何
价格偏离都是随机的,错误会互相抵消。这是“看不见的手”作用下的完美结果。
做出这些假设的一个理由就是要基于“微观基础”,即个人的逐利性,来将经
济理解为一个整体(宏观经济学)。这种要求激发了方法论的个体论研究,这一
学说认为逐利的个体是经济的唯一推动者。更有帮助的是,这一学说使经济学家
可以把从个人选择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非常完善的微观经济学用于分析经济整体。
然而这种理由也是有疑问的。首先,所谓的微观基础是不可验证的,是我们并不
确定了解的,而仅仅是我们深信而已。行为经济学认为真实的个体会对逐利性规
则出现系统性(但并不是一致性)的偏离,但是这一点被忽略了。即使一个人将
个体选择作为基础性的,但是模型实际上并不是简单累加个体选择,更不要说驱
使个体做出这些行为的预期了。这种研究是很困难的,因为人们在偏好上是如此
不同,没有人会确切知道其他人在想什么。20世纪70年代的一个理论结果表明,通过这种加总而得到唯一的一般均衡点是不可能的,也就是“一切皆有可能定
理”。 [38]
所以“微观基础”方法就相当于仅仅假设(或主张)所有的市场参与者
把自己看成具备了相同的资产和偏好禀赋的单独个体而进行活动,他们被看成典
型的代理人,然后用微观经济学方法被模型化。但是如果他们在各个方面都相
同,那么他们之间为什么还要进行贸易呢?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远离实际情
况。
微观基础在科学上被认为极其严密,所以在方法上是具备约束力的。但是规
则是武断的:为什么减少只是对个体,而不是对他们的心理、生物、化学和物理
学?为什么将总和归功于个体选择?为什么不选择其他方法?甚至在微观经济学
理论中,市场都是由社会规则和传统统治的,而且依赖于语言和计算方法这样的
社会媒体存在。经历了好几个时代后,微观基础的规则已经渐渐消亡,从未被任
何接近于严格的事实所证实。 [39]
只要从个人选择到宏观经济的真实加总不可
行, [40]
它就不能被看成是基础的需求。鼓吹(有时候甚至是锁定)其他变通做
法绝不仅仅是一种口号。但是卢卡斯模型要起作用的话,这就是非常必要的一种
办法。
对微观基础也可以进行不同的分析,即可以用研究个人行为的经济学方法对
宏观经济问题进行分析。这就是微观基础的要求条件被真正理解的原因。这相当
于将目的性和合理性融入经济总量(例如,一个有“代表性的消费者”)的研究之
中,并且假设这一具有想象力的个体的选择在整个时期内能够生产出最好可能的
(均衡)产品。如果世界真是如此,那么这将是一个研究经济总量的好方法。
[41]
把事情想象成这样,就是超现实主义的了。那就是一种假装有知识的做法。
[42]
20世纪80年代早期,数学证明显示,一个人以上的理性预期将在内部产生不
一致性,理性个体的不同预期想要汇聚成一个正确预期,每个个体需要知道其他
个体是如何预期的。就像批评家(未来的获奖者)说的那样:理性预期的“猜
想”就像上帝无所不知的“猜想”一样。寻找证据几乎没有任何意义。 [43]
尽管存在这些问题,有两个原因使模型仍然很有吸引力。首先,他们是非常
传统的:他们将经济学非常标准的动机性假设延展开来,而且使宏观经济现实从
下至上的模型化成为可能。保罗·克鲁格曼这样解释:如果仅有一个方法极为合
理,那就会有无穷多的方法是不合理的,你应该如何选择呢? [44]
这不是完全正
确的:这种完美的合理性仅在世界处于稳定状态并且可知的情况下才起作用。一
些假设可以放松,但是人们通过工作所发现的已经存在的未来(遍历性假设),这一假设是不能放松的。 [45]
期望能够被证明是正确的这一假设如果不存在的
话,模型化就会非常困难,而宏观经济学家就是要将观察到的规则简化成一般规
则(对我们自己而言,这实际上是一个正确的程序)。卢卡斯很有名的批评论断
就是,实证的凯恩斯模型(与劳伦斯·克莱因有关)对过去到未来进行了推断,而
没有考虑逐利的参与者按照理性预期做事会有导致颠覆的潜在风险(卢卡斯批
判)。但是没有信息是来自未来的。理性预期以过去和现在的信息为基础。假设
每个人都一定能够使用这些信息就太牵强了,而且这一点已经被反复证明是错误
的(将在下一部分中说明)。卢卡斯批判原则上是正确的(虽然这是卢卡斯批判
的那些模型构建者所期望的)。如果每个人都可以获得充分信息并且可以随意获
取,那么这一现象就必须被重视。但是卢卡斯批判的实证效果已经被发现是很差
甚至是不能成立的,如果人们意识到自己已经严重偏离了理想的话,对此就不会
感到吃惊。 [46]
然而这已经成为宏观经济学的标杆。
理性预期假设为政策提供了合理性。政府做出稳定价格的承诺并不可信。为
了克服这个问题,货币政策被移交给中央银行来制定,中央银行是游离于政治之
外的,其目标是要把通货膨胀限制在一个非常小的范围内(一般是2%)。一旦通
货膨胀有所抬头,中央银行就会在经济运行中采用更高的利率,这样就可以通过
失业来控制工资水平。 [47]
理性预期理论是一种“看不见的手”的理论,它也认为
市场不能被改善。任何政府干预手段都可能被预期到并且被市场参与者抵消。如
果干预是有效的,那么它会导致经济偏离自然和理想的状态,从而发生“扭曲”。
所以干预是无效的,甚至是有害而无益的,但是在通货膨胀目标实现上是一个例
外。这一学说显然与商业利益和富人在价格稳定、纳税更少、更少受到管制方面
的利益是一致的。理性预期是一个很保守的理论:中央银行运用这一理论要求工
资要受到管制,但对房产和股票价格却不这样要求。
我们很容易忘记约瑟夫·斯蒂格利茨说过的话:“‘看不见的手’必须作为一种信
仰,而不是一种科学命题。” [48]
理性预期政策标准(像大多数“看不见的手”的
论述)在已经确认的知识中是找不到的:它们仅反映了理论家的偏好和优先考虑
因素。这些是被看作前提条件的。这种观点与抽象推理并不矛盾,但是与其当局
在政策制定上所宣称的是矛盾的。
它是真实的吗
卢卡斯在20世纪80年代被质疑:“你是跟随真理的吗?”他这样回答:“是的,但是我不知道在我们的经济中真理是指什么。我们正在设计模拟人类的机器人,在我们所能获得的资料上,存在一些实际限制。” [49]
这样脆弱的构造即使在发
明者自己看来都是经受不住检验的。这种看似庄严的知识和永恒稳定的模型被持
续不断地修复,从而遭到了破坏,而这种修复通常也是为了解决该模型与经济现
实之间很差的适应性。卢卡斯摒弃了用货币流通紊乱来驱动经济周期模型的努
力。托马斯·萨金特是理性预期的发起者之一。他的一个学生在萨金特的著作中已
经罗列了“关于理性预期理论兴起的十个故事”。每个模型都是为了解决之前模型
中出现的一些问题。 [50]
这些“故事”不总是彼此吻合的,这反映出这一理论的一些内容的偶然性特
点。萨金特因为推理的严谨而闻名。这种范例中缺乏的是对事实的尊重。而萨金
特对此非常公正。经验检验与理性预期是不一致的,所以经验参数与所谓“校
准”程序中出现的模型是不一致的。在这一模型中所产生的周期与真实世界的参数
是一致的,这些参数是从稳定“深入”的微观经济学偏好(例如工作与闲暇)、技
术变量和已经被卢卡斯否定的极具实证经验特点的宏观经济学中得到的。如果这
些周期可以匹配,不是任何特殊的历史周期,而是真实历史周期的“二阶矩”,也
就是它的一般形态,经常是去趋势化的而且脱离于稳定期间的,那么这就可以被
看作是一种成就。即使这并不容易管理,但是也可以被判断是已经失败的。 [51]
这并不令人吃惊——例如,偏好和技术都是不变的,甚至除了进行假设之外,都
是很容易识别的。萨金特还流露过这样的思想:
校准对于理论能达到什么目标而言,也不是完全值得信赖的,因为如果
你没有充分信任你的模型,而仅仅是使用它,那就意味着你认为你的模型是
部分有误的或是不完全正确的,或者如果你相信其他人的模型和数据比你自
己的更合理。在我的记忆中,鲍勃·卢卡斯(Bob Lucas)和爱德华·普雷斯
科特起初对于理性预期计量经济学都是很热情的。毕竟它唤起了我们自己对
于高标准的追求,我们因为凯恩斯主义者没有做到这一点而进行过批评。但
是在对理性预期模型进行了大概五年的检验之后,我想起鲍勃·卢卡斯和普
雷斯科特都曾经告诉我这些检验导致太多很好的模型被否定。校准的目的在
于忽略你自己模型中的一些概率含义而保持其他的一些概率含义。总之,直
接承认你自己的模型虽然并不正确,但是仍然值得作为一个数量政策分析工
具的载体,而校准的目的,就是起到这样的平衡作用。 [52]
对比而言,当萨金特写经济历史的时候,他在很大程度上省去了对模型的引
用。 [53]
对卢卡斯而言,繁荣、萧条、失业和复苏的周期都完全不构成政策挑战,而
只是在均衡之前的一种摇摆,但是这些对凯恩斯而言就是一个挑战,并且在一定
程度上驱动了社会民主党派的行动。在卢卡斯模型中,政策干预因为个人知识经
济的运行(理性预期)而被击败,并将运用这些知识避免对于自己利益所产生的
负面效应。只有个人能有预期,并且自己对此感兴趣。真实的微观基础解释将从
个人选择中推断而来,但是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并不知道关于实际选择的任何情
况。它在“代理人模型”中起作用,也就是经济作为一个整体被模型化为仅由一个
或者两个个体构成。一旦这些形成了飞跃,就很可能构建一个长期的均衡模型,这是一种“真正的商业周期”,在这种周期中波动起源于外部惊喜(或者“震
动”)。“均衡”由一个简单的代理消费者构成,他从一个单一的代理公司购买并为
这个公司工作。阿罗-德布鲁一般均衡点被期待要提升经济效率,尽管这一理论自
身缺乏现实性。 [54]
阿罗-德布鲁仅适用于存在许多代理人的大的经济体的情
况,这是一种恒定的静态的结果,没有给冲击和摇摆留下任何空间。 [55]
甚至在
转换到一个连续均衡状态时,它仍然需要具备完全的一致性(完全市场)。在只
有两个代理人的情况下,市场几乎不可能达到“一般”均衡。
另外一些跟麻省理工学院、哈佛大学、伯克利加州大学和斯坦福大学的顶级
学术机构有联系的理性预期经济学家(相对于芝加哥和明尼苏达大学的“淡水”派
而言,他们被称为“盐水”经济学家)通过向模型中注入冲突和干扰因素对模型进
行了修改。这些“新凯恩斯”模型越来越精致。终于在2000年左右,新古典宏观经
济学和新凯恩斯主义的各个分支结合在一起,形成了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其
目的是将更多的现实融入内部临时均衡模型。这些模型超出了校准范畴而应用了
更多的传统统计推理方法,并且将参数从真实数据中分离出来(“估计值”)。得
到的模型运用于越来越多的实证数据检验,这种真实数据的使用确实在提升预测
的准确性上起到了一些作用。 [56]
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开始统治宏观经济学研
究,各国中央银行开始运用和求助于这个模型。 [57]
吸引力在于理性和均衡的传
统基础,但是这些非现实性的基础限制了它们的可依赖性和精确性。这些理论的
大部分也意味着市场相比于政策是被优先考虑的一个因素。他们预测的质量至多
可以跟统计外推技术的结果相提并论,统计外推技术根本不做任何经济理论假
设,实际上这两种方法现在经常被结合使用。 [58]
这些模型经过30年的完善,依
然在实证环节上表现得很糟糕。实干家对此深有体会。尽管中央银行广泛部署,但他们仍然不是核心决策框架的一部分,也没有为“黄金时间”做好充分准备。
[59]
他们没有预测到2008年的金融危机,其重要原因在于他们一向不考虑金融部
门。现代宏观经济学运用先验世界观点来比对数据,从而证明一致性。 [60]
尽管
陷入了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的大规模应用,但是中央银行没有抛弃凯恩斯主义
起源的巨大统计模型,它众所周知的缺点唤起了卢卡斯革命。对比而言,如果私
人的钱处于危险之中,那么商业几乎绝对依赖统计模型所做的描述性预测,并且
完全不会使用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除非有时候会尽力模仿中央银行的决策。
[61]
理性预期模型的指数可以追溯到米尔顿·弗里德曼的方法论的论述中,其中说
道,只要模型做出了好的预期,分析所依赖的现实就不重要。 [62]
然而,好的预
测不能被看成理性预期。它的实证数据很少,为了把它代入有实证证据的任何平
行排列都必须进行复杂的扭曲操作。与安提凯希拉所做的比较就说这么多。 [63]
古代希腊的机械装置是基于错误的地心说宇宙论的(这对米尔顿·弗里德曼而言不
是一个问题),但是相对于任务的重要性和前提条件的非现实性而言,它做出了
相当多的预测。理性预期模型与安提凯希拉装置一样都具备非现实主义的特性,但不像古希腊的机械装置那样,理性预期模型所做的预测是非常糟糕的。
新古典宏观经济学与社会民主
假定有两个积极的代理人、近乎完美的预测,以及不朽的生命,那么按照新
古典经济学的说法,就不必存在社会保险。它是一种没有政府、金钱和社会的经
济体。没有公众,就没有公共产品的概念。也许这就是它如此流行的原因。在
1957年米尔顿·弗里德曼提出的“永久收入”假设中提到了消费者通过借入和储蓄来
调整收入的波动,在这一假设中,就部分运用了上述假设。因为生命无限,所以
不存在退休问题。两年之前,凯恩斯主义阵营的弗兰科·莫迪利安尼提出的更现实
的生命周期理论还认为至少退休问题是会发生的。 [64]
同时,进行了一些某种程
度不同的假设(工人及退休的人的代际交叠),保罗·萨缪尔森做出了一个模型,这一模型认为社会保险是必要的,至少是有用的。这三个模型都从假设中获取结
论(很有智慧),并且强调在社会民主主义和市场自由化之间的争论(仍然发生
着)中模型的容忍度。这些研究成果都被授予了诺贝尔经济学奖。
卢卡斯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满足了反直觉意识、理论连贯性、可理解的比
喻、有说服力的类比、数学技术、程序化的事实和政策及政治上的正确性等建模
条件。1981年,卢卡斯得意地说:“总体来看,我认为一个声称理解了飞行原理的
人是很有可能造出可以飞行的机器的,理解商业循环就意味着创造商业循环的能
力,这两个问题几乎是相同的。” [65]
那些飞机也是如此。然而要注意的是不能
仅仅声称控制了商业周期(这不一定是必然的),而是要构建一个可信服的实物
模型。
到目前为止,与现实发生冲突是一种收获。在所有条件满足之后,最后一个
条件,实证有效性的检验问题就可能是一件尴尬的事情。在标准的计量经济学
中,一个偶然的模型力图包括所有相关的变量,估计程序使用现实生活中的原始
数据来发现其重要性及重要的程度。这个程序必须是描述性的。如果匹配结果非
常糟糕,那么模型将被拒绝。它还会遇到严重的问题(见第二章)。校准的新古
典宏观经济学程序不必满足这样一个检验:它预先选择匹配数据,估计结果仍然
很糟糕。
弗兰克·哈恩是一位受人尊敬的建模家,他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这样谈及新古
典宏观经济学:
我一直认为竞争一般均衡分析是像一个飞机工程师能造出来的实体模型
一样。最近这些年我的兴趣很大程度上在于发现许多经济学家不把实体模型
当作一架真正可以飞行的飞机,政治家、银行家和所有的时事评论者都来争
夺座位。这一次全世界的理论家都意识到这样的实体模型是不可能飞起来
的,因为它忽略了真实世界中很重要的方面,这种认知将促使一些激进的设
计产生。而且,无论在哪个阶段,实体模型都是完整的。 [66]
卢卡斯并没有被吓住。他在1988年芝加哥大学毕业大会上致辞的时候,以一
种宗教权威的口吻进行了演讲。从一个想象的问题开始,他对毕业生这样说道:
我们需要将我们自己从历史经验中解放出来,从而找到我们的社会可以
比过去运转得更好的方法……我们没发现想象和思想的王国其实是一种对实
际和现实的替代,或者说是一种退而求其次的做法。相反,它是我们所能找
到的认真思考现实世界的唯一道路。 [67]
这种假想的现实原则一直被坚持作为一种政策指导。2003年,卢卡斯又一次
将主席致辞递交美国经济学会。它是一次结束历史的演说,或者说更像是宣告宏
观经济学的完结的演说:“遏制萧条的核心问题已经解决。” [68]
这是他研究方法
的原理,即衰退并不重要:商业周期的上升和下降是宏观经济调整的最好路径。
所以寻求稳定性不会有什么实质性收获,但是更具竞争力的市场(特别是劳动力
市场)将能极大地提升消费。
仅仅五年之后,经济危机发生了。卢卡斯之前预测经济会永久呈现3%的增
长。 [69]
他的信心来自哪里呢?它是基于几个模型的,所有的模型都是“一个良
好的增长模型的变形,在这个模型中消费者(可能是一个无限存在的动态生命
体,也可能是几代人的更迭)会在长期中将消费效用和闲暇最大化,公司会最大
化利润,市场将持续出清”。 [70]
换句话说,是一个良好的、消费者的、公司的
模型。这样的模型很难构建,而且不容易理解。但它不可能真正起作用——它们
仅仅是模型。在李嘉图飞跃中,卢卡斯抛弃了这些不实用的观点。这个政策天生
是无效的(这是他自己的核心信条)在这里被遗忘了。
对神坛上的卢卡斯而言,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模型为再分配这一机制激进上升
的市场自由化进程提供了合理的解释:废除了对资本的征税,对于收入征收统一
税,将福利国家私有化。将资本收入税收削减为零(用其他税收来覆盖支出)是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模型获得的一个喜人结果,这一变革为
美国和英国在接下来的十年中从资本获得退税收入提供了正当理由(这一理论曾
经受到挑战)。 [71]
来自“滴漏效应”的经济增长将给消费带来7.5%~15%的增
长。在另外一个例子中,财政上的更高税收只需要用更短的工作时间来负担。对
劳动和消费(工作中更长的工时)采用较低的美国式税率的那些法国家庭而
言,“稳态福利增益”相当于消费增长大约20%的水平。这些都来自单一个体模型
中闲暇和工作之间权衡的不稳定结果。 [72]
用这些额外收入,法国人就能购买政府当前提供的物品。他说:“可以考虑一
下小学教育或者日托,这些目前都是由‘扭曲税收’进行财政支持的。” [73]
倾听
者都是默认有效市场不是一个假设而是一个既定的事实,虽然这样的市场并不存
在。另一个假设是法国工人就他们上交的税收而言得不到任何回报,因此他们不
能在私人市场的柜台上进行购买。与卢卡斯观点相反的是,有人可以指出由法国
人的税收提供的社会保险以及自由教育比市场消费增长20%更有意义(甚至从金
融术语来看),对于那些低收入人群的意义就更大了。
美国市场健康服务相较于欧洲社会民主党提供的这些服务来说,前者的价格
是后者的两倍,而且有效性更差。欧洲退休金则慷慨得多。 [74]
在华丽的表达背
后,卢卡斯忘记了这样一个事实,即法国人也必须工作更长时间,才能换取政府
已经提供的物品。此后,他又表达了对于下降分布的厌恶:“在已经出现的对健康
经济学发展有害的趋势中,最引人注意而且我认为最有害的趋势就是把注意力放
在分配上面。” [75]
增长分布的非相关性即使应用卢卡斯自己的方法,对于美国
的情况而言也已经表明是错误的,那么对于一个之前30年大多数人都未能从经济
增长中获益的国家来说,情况就更不令人吃惊了。 [76]
再次重申我们的观
点,“典型代理人”模型给政策提供了一个非常差的保证。
它究竟是什么
新古典宏观经济学与人文科学中的后现代主义运动在历史上同时发生。 [77]
后现代主义的具体时间不容易确定。如果它有核心思想,那么它的核心思想就是
拒绝把观察和测量、原因和效应的分析作为有效性的标准。对它与经济学的联
系,以前就有过研究。它一直致力于博弈论、非对称信息、行为及女权主义经济
学领域的不可预测论的逆势问题研究。 [78]
从后现代主义的观点来看,经济学的
错误在于理性和均衡的“现代主义的元叙事”问题,以及以一种符合逻辑的科学解
释的欧洲启蒙运动的信仰问题。在一系列的学术和娱乐书籍中,经济学家和历史
学家戴尔得丽·麦克洛斯基(Deirdre McCloskey)将经典的文学传统用于她的经济
演讲,她将经济演讲看作一种不可预测但充满新思想的对话,而且是对有说服力
的研究的一种无尽追求。这一点从她出色的口才中可以看出来。 [79]
说服力作为经济观点讨论的目的是符合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家的想法的。但是
用克里斯托弗·西姆斯的话来说,“面对骗子的时候我们有心软的这种风险”。 [80]
没有事实,说服力从何而来?我们又在讨论什么?探求说服力大概就是想要证明
自己是正确的一种努力。事实对于推理、学习、合作和签约来说都是非常必要
的。事实不会每时每刻都出现,但是当它缺席的时候,我们所知道的一切就都是
一种可以唤起我们觉醒的认知。
与后现代主义的相似不是新古典学说的边缘问题,而恰恰是核心问题。像后
现代主义一样,新古典宏观经济学不再让事实进入个人的幻想,对后现代主义在
高低文化水平之间的平衡也是认可的。在对社会和普通商品不给予任何空间这一
点上,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比后现代主义走得更远。像后现代主义一样,新古典宏
观经济学对于集体愿望也保持中立态度,而集体愿望促使社会民主党派认识到有
其他人的存在,而且其他人有特殊的需求,并且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义务是可以互
相起作用的。
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是反现实主义的:“社会理论不像热力学,它被谴责一直处
于不可检验状态,而且一直局限于思想领域。” [81]
脱离了现实主义的束缚使卢
卡斯能够迷惑他的读者。一方面,它认为失业是一种自愿选择,这是一种思想实
验(在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学派中没有其他的实验)。 [82]
另一方面,还有少数人
表面上看起来是认同要信赖社会保险的。 [83]
总而言之,他自己的猜想就是“效
率要求对失业的人进行补贴,因此又会提升平均失业水平”(他在芬兰这样一个北
欧福利国家做的演讲)。 [84]
读者抓破脑袋来思考和解决这些冲突,并且渗透这
些深奥的模型,这些模型对于激烈的社会变革是持赞同态度的,模型当中的大多
数思想(表面上如此)都是符合富人利益的。
但是我们也可以持怀疑态度。模型的先决条件从来未被满足,那就没有理由
认为其他事情会保持均等(其他条件不变),或者要做任何必要的改变(必要的
变更)。因果和推理就会被搁置起来。 [85]
这会带来令人振奋的局面,但是当就
政策问题发声的时候,卢卡斯恰恰是滥用职权的人。两个“理性代理人”经济模型
不是建立在微观经济基础之上的。而且在模型中,缺乏严格的阿罗-德布鲁条件
(在现实世界中是不可能被满足的)的竞争经济并不被认为比其他经济更有效
率,甚至在帕累托均衡的有限意义上也是如此。 [86]
但是回头讨论是无用的,作为一门学说,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在普遍意义上来
讲更像经济学,与批评家的相处并不融洽,甚至在学派内部都存在不融洽的情
况。 [87]
卢卡斯对批评家一直不是很礼貌,他把对手凯恩斯学派的学者描述成绝
望的“头盖骨卡嗒卡嗒”。 [88]
一般来说,经济学家会被其他学派(和非正统的实
践者)看成是居高临下的而且疏远的。这一点在引用方式上已经得到确认了——
对比其他学派,经济学家很少从外界引用,当他们做这样的引用时,大多数人利
用的都是像财政、统计学和商业领域的知识,而且所合作的人也都是同意他们观
点的人。 [89]
这就不可能形成坚定的不同意见。这意味着外界的人不可能有资格
来判断,甚至当他们自己的利益处于紧要关头的时候也是如此(经常是正确的,但是在标准的经济假设上是存在争议的)。然而它可能使人对于看上去未得到保
证的主张感到不满,这就可能陷于一种一般的错误,即把行为归因于处理手段而
不是环境。 [90]
在这样的情况下,冷淡不是一种集体特性的缺点,而更可能是为
了引起对学说世界观的一种关注。经济学说是理性主义的。他们的逻辑推理来源
于可以自证合理性的事物,所以他们是抵制证据的,因此(对经济学家而言)他
们违背常识或者认为与现实不一致是无关紧要的。 [91]
如果基础条件不可以共
享,那么就没有意义开展讨论。
不尊重现实和推理也是各个时代中右翼倾向的共同特点。它会导致将卢卡斯
的表现(还包括用于质疑社会民主主义的理性预期和典型代理人战略)看成一
种“agnotology”的实践——agnotology最初是为那些否定烟草和癌症之间关系的人
杜撰出来的术语,这些人还否认全球变暖、否定药物试验管制和否定2008年金融
危机之后采取的“一般商业模式”。 [92]
它代表了看上去非常诚实的理论观点,但
是缺乏令人信服的证据,而且意图散布混乱和怀疑。 [93]
如果这些意图不能接近
真实情况,而是寻求一种原因,那么这种无条理就是有意义的。像布什进军伊拉
克,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家看起来也在“制造他们自己的现实”。 [94]
这在短时间可
能是有效的。鉴于我们对芝加哥学派以外的很多学派的巨大专业认可度,甚至在
政治思想上彼此互为对手的人也如此认可,那我们其实可以承认我们自己的混乱
和游移不定。领军的经济学家也有跟我们一样的困惑。 [95]
对于理论化这一问题是不可能有任何反对意见的。如果学者希望探讨不朽
的、一致的、能够预知而且是只有一个个体存在的经济情况的数学含义的话,那
为什么不呢?约翰·希克斯曾经这样写道:
太多的经济理论之所以被研究,其实除了学术上的吸引力之外,并没有
更好的理由:它只是一个好的游戏而已。我们没有理由对此感到羞愧,因为
对于数学的许多分支而言也同样如此。 [96]
诚然,它可以繁荣很久,但这样的模型对于反对集体行动而言并不能提供任
何保证,或者我们可以说(其自身)对于任何其他政策这样的模型都是如此。
经济学的内部纠纷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并不认同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实际上(在第五章我们可
以看到),相反的情况更接近事实。诺贝尔奖评定委员会也有所犹豫。在诺贝尔
经济学奖得主中,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学派的经济学家已经被明确地否定了,否定
这一学派的经济学家有肯尼斯·阿罗、詹姆斯·托宾、弗兰科·莫迪利安尼、罗伯特·
索洛、弗农·史密斯(在他的诺贝尔获奖演说中)、埃德蒙·费尔普斯、保罗·克鲁
格曼、克里斯托弗·西姆斯,当然还可能有其他人。 [97]
索洛曾经写道:“宏观社
会已经对其自身进行了夸张的欺诈,对其学生也是如此。” [98]
在关于2008年金
融危机的一次国会听证会上,这位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学家对于新古典宏观经济学
给予了粗鲁的回应:
他们想当然地认为整个经济可以被看成是一个单一的、一致的个体或者
一个朝代,他能够执行一套按照理性设计好的长期的计划,只是偶尔被预期
之外的震动扰乱一下,但是可以以一种理性的、一致的办法调整自身。我认
为这幅图画是不可能通过嗅诊测试的。这一思想的主角宣称对自己的社会地
位负责,宣称这一理论是建立在我们对于宏观经济行为的了解之上的,但是
实际上我认为这种宣称是虚伪的。 [99]
模型化是不可逃避的,在经济学中模型是一种飞行器。我们在本书第六章也
使用数学模型来描述和解释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著名的理论轨迹。索洛的双重
因素经济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增长模型(资本和劳动)是接近于典型代理人模型
的,虽然它并不假定资本和劳动的总和有其自身隐含的含义。但是模型没有独立
的权威性。为了证明政策的正确性,模型必须考虑一些真实的购买行为。数学
家、物理学家和博学家冯·诺依曼因为说了这样的话而闻名:“当你甚至不知道你
正在讨论什么的时候,再精确都是没有意义的。” [100]
决策制定者就像现在的作者一样,必须凭信任来相信这些专家。他们不是模
型构建者。如何决定听谁的?政策不能单一地依赖模型,它在设计上并不像喷气
式飞机那样精确,它的表现也不容易测量。收集信息、开展研究、写作论文、咨
询机构,同样还有偏见、歧视、忠诚和配偶问题。模型仅是所有混合问题的一部
分而已。最成功的因素能够进入政策制定的考虑之中,成为“初始模型”,这些因
素必须是被深信不疑的,政策制定者认为专家懂得这些问题,虽然并不确定如何
知道及为什么。那些应用政策的人很少能够将模型拆分,或者自己来进行平衡。
有说服力的模型的单一存在有一些证明价值,这是独立于证明之外的。模型是很
难被检验的,并且不确认性被忽略了。所以这就是诺贝尔奖的权威品质的重要性
所在。奖项的魅力和权威的有效性就是我们下一章要谈的内容。
[1] McCloskey,‘Economics Science:A Search through the Hyperspace of As-sumptions’(1991),11.
[2] Morgan,The World in the Model(2012),ch.5.
[3] ‘Neoclassical’:The economics of Adam Smith,David Ricardo and John Stuart Mill(classical
economics,c.1770-1870)reckoned economic value by the cost of
production.Its‘neoclassical’successors(from the 1870s onwards,including W.S.Jevons,Vilfredo Pareto,Alfred Marshall,Paul Samuelson)measured it by willingness to pay.
[4] Robinson,Economic Philosophy(1962),79.On her entitlement to the prize,see 136-137,below.
[5] Boumans,‘Built-in Justification’(1999),93.
[6] In substantive agreement with Syll,On the Use and Misuse of Theories and Models(2015).
[7] Introduction,above,3.
[8] Smith,‘Digression Concerning the Corn Trade’,Wealth of Nations(17761976),IV.5.b 1-9,524
-528.
[9] Offer,‘Self-interest,Sympathy and the Invisible Hand’(2012).
[10] Precursors,Ingrao and Israel,The Invisible Hand(1990),chs.2-3.
[11] Creedy,‘Some Recent Interpretations’(1980);Humphrey,‘Early History of the Box
Diagram’(1996).
[12] Blaug,Economic Theory in Retrospect(1997),570-595.
[13] Historical survey and analysis,Ingrao and Israel,The Invisible Hand(1990).
[14] Rizvi,‘The Sonnenschein-Mantel-Debreu Results’(2006);Fisher,‘The Stability of General
Equilibrium’(2011).
[15] Hahn,‘Reflections on the Invisible Hand’(19821984),121;Arrow,‘Ra-tionality of Self and
Others in an Economic-System’(1986),S393.
[16] Hahn,‘On the Notion of Equilibrium in Economics’(19731984),52.
[17] Stiglitz,Whither Socialism(1994),ch.2.
[18] Humphrey,‘Early History of the Box Diagram’(1996).
[19] Lucas,‘What Economists Do’(1988),5.
[20] Ibid.,5.
[21] Lucas,‘Methods and Problems in Business Cycle Theory’(1980),697.
[22] McCloskey,‘Economic Science:A Search through the Hyperspace of Assump-tions’(1991),13;King,The Microfoundations Delusion(2012),ch.2.
[23] For example,Tovar,‘DSGE Models and Central Banks’(2008),18.
[24] von Neumann,‘Method in the Physical Sciences’(1955),492.
[25] Demsetz,‘Information and Efficiency’(1969),1.
[26] Schumpeter,History of Economic Analysis(1954),472-473.
[27] Lucas,‘Methods and Problems’(1980),700;Lucas,Lectures on Economic Growth(2002),21.
[28] Lucas,‘Methods and Problems’(1980),709;FORTRAN is a formerly per-vasive computer
coding language.
[29] Forder,Macroeconomics and the Phillips Curve Myth(2014),argues that ne-oliberal critics
misrepresented Keynesian policies.
[30] Modigliani,‘The Monetarist Controversy Revisited’(19881997);Mayer,‘The Twilight of the
Monetarist Debate’(1990).
[31] Coase,‘The Institutional Structure of Production’,Nobel Lecture 1991.Nobel Lectures(delivered by
NPWs usually a day or two after the prize ceremony)are cited henceforth with title and year.They are available
at http:www.no-belprize.orgnobel_prizeseconomic-scienceslaureatesindex.html,and are mostly reprinted
in an irregular series of variously edited volumes entitled Eco-nomic Sciences with dates.
[32] McLean,Public Choice(1980);Mueller,Public Choice III(2003).
[33] Fox,The Myth ofthe Rational Market(2009).
[34] Hirschman,Rhetoric of Reaction(1991),74.
[35] Freeth,The Antikythera Mechanism(2008);Freeth et al.,‘Calendars with Olympiad
Display’(2008);Marchant,Decoding the Heavens(2008);Freeth,‘Decoding an Ancient
Computer’(2009).
[36] Allais,‘An Outline of My Main Contributions’,Nobel Lecture 1988,243.
[37] Evans and Honkapohja,‘An Interview with Thomas Sargent’(2005),566.
[38] Kirman,‘Whom and What Does the Representative Individual Represent?’ (1992);Rizvi,‘The
Sonnenschein-Mantel-Debreu Results after Thirty Years’(2006).
[39] Kirman,‘Whom or What Does the Representative Individual Represent?’(1992);Hartley,The
Representative Agent(1997);Kincaid,Individualism and the Unity of Science(1997);Hoover,Methodology of Empirical Macro-economics(2001),ch.3;Duarte,Microfoundations
Considered(2012);Janssen,Microfoundations(2012);King,The Microfoundations
Delusion(2012);Syll,Use and Misuse of Theories and Models(2015),ch.3.
[40] Hoover,The New Classical Microeconomics(1998),224-230,241-244.
[41] Hahn,‘Macroeconomics and General Equilibrium’(2003),206.
[42] Caballero,‘Macroeconomics after the Crisis’(2010),89.
[43] Frydman and Phelps,‘Introduction’(1983),26;Frydman,‘Towards an Un-derstanding of
Market Processes’(1982);Arrow,‘Rationality of Self and Others’(1986),S393.
[44] Macfarquar,‘The Deflationist’(2010).
[45] Davidson,‘Reality and Economic Theory’(1996).
[46] Favero and Hendry,‘Testing the Lucas Critique’(1992);Ericsson and Irons,‘The Lucas Critique
in Practice’(1995);Linde,‘Testing for the Lucas Critique’(2001);Hendry,‘Forecast Failures,Expectations Formation and the Lucas Critique’(2002).
[47] Grimes,‘Four Lectures on Central Banking’(2014),4-37.
[48] Stiglitz,‘The Invisible Hand and Modern Welfare Economics’(1991),35.
[49] Klamer,The New Classical Macroeconomics(1984),49.
[50] Sent,Evolving Rationality of Rational Expectations(1998),1-11.
[51] Watson,‘Measures of Fit for Calibrated Models’(1993);Hoover,‘Facts and
Artifacts’(1995);Hansen and Heckman,‘Empirical Foundations of Calibration’(1996);Carlaw and
Lipsey,‘Does History Matter?’(2012).
[52] Evans and Honkapohja,‘Interview with Thomas Sargent’,568-569.
[53] Sargent and Velde,The Big Problem of Small Change(2002).
[54] Lucas,‘Methods and Problems in Business Cycle Theory’(1980),701.
[55] Hahn,‘General Equilibrium Theory’(19811984),79.
[56] Woodford,Interest and Prices(2003);Smets and Wouters,‘Estimated Dy-namic Stochastic
General Equilibrium’(2003).
[57] Chari,‘Statement of V.V.Chari’(2010),32.
[58] Gürkaynak et al.,‘Do DSGE Forecast More Accurately’(2013).
[59] Tovar,‘DSGE Models and Central Banks’(2008),quotes,2,18;Schorf-heide,‘Estimation
and Evaluation of DSGE Models’(2011).
[60] Marchionatti and Sella,‘Is Neo-Walrasian Macroeconomics a Dead End?’(2015),27.
[61] Bachman,‘What Economic Forecasters Really Do’(1996);Smith,‘The Most Damning Criticism
of DSGE’(2014),including comments by Daniel Bachman;Dou,‘Macroeconomic Models’(2015).
[62] Friedman,‘The Methodology of Positive Economics’(1953).
[63] Ball,‘Intertemporal Substitutions’(1990),706,lists several earlier empirical failures;Pollock
and Suyderhoud,‘An Empirical Window on Rational Expec-tation Formation’(1992);Carter and
Maddock,Rational Expectations(1984),141-143;Lovell,‘Tests of the Rational Expectations
Hypothesis’(1986);Obstfeld and Rogoff,Foundations of International Macroeconomics(1996),625,cited in Frydman and Goldberg(below),28-29;Estrella and Fuhrer,‘Dynamic
Inconsistencies’(2002);Frydman and Goldberg,Beyond Mechanical Markets(2005),ch.5.
[64] Modigliani,‘Life-Cycle,Individual Thrift and the Wealth of Nations’,Nobel Lecture 1985.
[65] Lucas,Studies in Business-Cycle Theory(1981),8.
[66] Hahn,‘Review of Beenstock’(1981),1036.
[67] Lucas,‘What Economists Do’(1988).
[68] Lucas,‘Macroeconomic Priorities’(2003).
[69] Klamer,The New Classical Macroeconomics(1984),52.
[70] Lucas,‘Macroeconomic Priorities’(2003),2.
[71] Straub and Werning,‘Positive Long Run Capital Taxation:Chamley-Judd Revisited’(2014).
[72] Lucas,‘Macroeconomic Priorities’(2003),1-2;‘Dubious’,see Hansen and
Heckman,‘Empirical Foundations of Calibration’(1996),100.
[73] Lucas,‘Macroeconomic Priorities’(2003),1-2.
[74] Offer,‘Economy of Obligation’(2012);Offer,‘A Warrant for Pain’(2012).
[75] Lucas,‘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Past and Future’(2014).
[76] Córdoba and Verdier,‘Lucas vs.Lucas:On Inequality and Growth’(2007).
[77] Rosenau,Post-Modernism and the Social Sciences(1992);Blaug,‘Why IAm Not a
Constructivist’(1994),130.
[78] Heap,‘Post-Modernity and New Conceptions of Rationality’(1993);Cul-lenberg et al.,Postmodernism,Economics and Knowledge(2001);Amariglio and Ruccio,Postmodern Moments in
Modern Economics(2003).
[79] McCloskey,The Rhetoric of Economics(1985);Knowledge and Persuasion in
Economics(1994).
[80] Sims,‘Macroeconomics and Methodology’(1996),110;Athreya,Big Ideas in
Macroeconomics(2015),13-14.
[81] Varoufakis,‘Deconstructing Homo Economicus?’(2012),393.
[82] Lucas,Models of Business Cycles(1987),section V.
[83] For example,Lucas,ibid.,31,61,105.
[84] Ibid.,69.
[85] See also Arrow,‘Rationality of Self and Others’(1986),S390.
[86] Lipsey and Lancaster,‘The General Theory of Second Best’(1956);Buiter,‘The Economics of
Dr Pangloss’(1980),45.
[87] Kapeller,‘Some Critical Notes’(2010),332-334;Francis,‘The Rise and Fall of Debate in
Economics’(2014);Fourcade et al.,‘The Superiority of Economists’(2015).
[88] Lucas,‘Methods and Problems’(1980),698;Lucas,‘Macroeconomic Prior-ities’(2003),1;also Klamer,The New Classical Macroeconomics(1984),50-51;Mankiw,‘The Reincarnation of
Keynesian Economics’(1991),1.
[89] Fourcade et al.,‘The Superiority of Economics’(2015).
[90] Nisbett and Ross,Human Inference(1980),30-32.
[91] Carter and Maddox,Rational Choice(1984),142.
[92] Proctor,Cancer Wars(1995),8;Proctor and Schiebinger,Agnotology:The Making and
Unmaking of Ignorance(2008);Pinto,‘Tensions in Agnotology’(2015).
[93] Mirowski,Never Let a Serious Crisis Go to Waste(2013),ch.4;Krugman,‘What They Say
versus What They Mean’(2013).
[94] Suskind,‘Faith,Certainty and the Presidency of George W.Bush’(2004).
[95] For example,Robert Clower and David Colander,in Snowdon and Vane,Conversations with
Leading Economists(1999),188-189,212,214-215;Caballero,‘Macroeconomics after the
Crisis’(2010).
[96] Hicks,Causality in Economics(1979),viii.
[97] Phelps,Frydman and Phelps,‘Introduction’(1983);Tobin,see Klamer,Conversations with
Economists(1984),110-111;Arrow,‘Rationality of Selfand Others’(1986),S393;Modigliani,see
Hirschman,Rhetoric of Reaction(1991),74;Hahn and Solow,A Critical Essay on Modern
Macroeconomic Theory(1995);Sims,‘Macroeconomics and Methodology’(1996);Sims,‘Comment
on Del Negro,Schorfheide,Smets and Wouters’(2006),2;Krugman,‘How Did Economists Get It So
Wrong?’(2009).
[98] Solow,‘Reflections on the Survey’(2007),235;also Solow,‘The State of
Macroeconomics’(2008).
[99] Solow,in US Congress,‘Building a Science of Economics for the Real World’(2010),12;also
Solow,‘Dumb and Dumber in Macroeconomics’(20032009).
[100] Wikiquotes,‘Talk:John von Neumann’(2015).
第二章
“经济科学”奖
在动荡的世界中,阿尔弗雷德·诺贝尔在1895年授予的这些奖项就像一盏盏拥
有不朽价值的明灯一样,始终散发着耀眼的光辉。这些奖项表彰的是人类为了寻
求真理所做出的努力、付出的真诚以及取得的成功,这是一个可以让人奠定地位
的荣誉。1968年,瑞典中央银行说服诺贝尔基金会增加了一个经济学奖项,这一
奖项与科学、文学及和平奖项拥有完全平等的地位。以这样一种微不足道的投
资,就将诺贝尔奖的权威光环轻松扩展到了经济学领域。这种行为实际上就像拿
阿尔弗雷德·诺贝尔本人做了一次颇具价值的创业运动一样。而正如诺贝尔本人是
炸药的发明者那样,诺贝尔经济学奖同样既蕴藏着正面的力量,也蕴藏着负面的
力量。对于经济学是否能够被称为一门科学这个问题我们应当如何认定?科学方
法论专家、实践主义经济学家以及诺贝尔奖获得者对此给出了截然不同的答案。
而当我们站在审视经济学政策建议的层面来看待经济学说的时候,这个问题就显
得尤为重要。
诺贝尔奖是一种仪式和象征
在自然科学领域,诺贝尔奖是最高荣誉。它站在金钱之上的原因就是它的奖
金丰厚。它有可信度方面的质疑也是因为它会授予得奖者一笔意外之财,尽管这
笔钱对于中央银行而言可能只是一笔小钱,但是对于全世界的学者而言可能是一
笔巨款。 [1]
但是金钱本身并不足以构成诺贝尔奖地位的全部。卡托研究所的米
尔顿·弗里德曼奖(在2002年奖金达到50万美元)就不具备同样的标志性意义,能
够给予几乎等额奖金的沃尔夫奖或者巴尔扎恩奖也不具备这样的意义。但颇具讽
刺意味的是,对于一个(大多数情况下)颁发给理性运用的奖项而言,它自身却
是一个相当陈旧的仪式,这种反差具有不可思议的魔力,反而可以给人带来卓越
的光环。一位钦佩者在1976年给米尔顿·弗里德曼的信中写道:“我出于简单而自
私的理由为你的获奖感到高兴,因为我可以对我的孩子说我曾经跟摘得诺贝尔奖
桂冠的人握过手。” [2]
弗里德曼回忆道:
诺贝尔奖会把获奖人变成一个其所属领域的专家,并且会吸引来自世界
各地的杂志和电视台的记者和摄影师。我自己就已经被问及从普通感冒的治
愈到一封约翰·F.肯尼迪(John F.Kennedy)签字的信件的市场价值的所有
问题。毫无疑问,这种关注不仅是奉承性的,而且是毁灭性的。 [3]
这种魔力还以另外一种方式起作用:瑞典皇家法庭(另一种古代遗物)沐浴
在奖项的光辉之中。
这一奖项赞美思想的力量。在知识所授予的洞察力和它所带来的优势上,思
想的力量是很难界定的。对大自然的控制最初可能创造了诺贝尔的财富。诺贝尔
将不稳定的爆炸性硝化甘油制造成可以储存、运输并且可以安全触碰的炸药。他
发明的无烟火药因为可以隐藏炮火的来源,从而加重了战争的危险性。后来在英
国又被进一步发展成线状无烟火药,它给两次世界大战和无数更小规模的冲突提
供了火药。如果这一发明曾经获得了诺贝尔奖的话,那么其他人就会因为只发明
烈性不那么强的爆炸物而不能获奖。诺贝尔的创新是不需要证实的:这些炸药伴
随一声声巨响炸开,利润滚滚而来。科学方面的成功很少有这样的结局和确定
性,而且一般是超出普通人控制范围的。诺贝尔奖已经将公众的注意力转移到一
些不那么显著的成就上,并且赋予获奖人金钱和名望。
智力奖项是碎片化结构上的启蒙装置,在这一结构中,每个层级都是复制较
低层级的成果。在认知梯子的每一节上,从小学开始,都由各种认知和选择进行
了标记。考试、毕业、穿毕业礼服以及获得学位,都标志着学术进展上的不同阶
段,学生会为这些活动做各种准备。在梯子上升的过程中,路是越来越窄的。每
所大学都有精英教授,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科学和投稿机构。庄严的图书馆有各
种论文,有一些已经有三个世纪那样古老了,这些论文当时被投递出去都是为了
得到权威认证和学术团体授予的各种奖项的。
在成立之初,诺贝尔奖是最新的、最令人兴奋的现存的学术奖励。 [4]
伟大
的国际性的颁奖活动发出一系列奖牌。维多利亚时代晚期是爱国主义盛行的时
期,各种奖项不仅使奖项得主获得荣耀,也令奖项得主的祖国以及颁发奖项的人
都获得荣耀。在1896年的雅典奥林匹克运动会上,0.1秒之差就能区别出金牌、银
牌和铜牌。这自然让人想到诺贝尔奖发出一个金牌就好像也对获奖等级进行了区
分一样。
哈耶克因为在1974年10月14日获得诺贝尔奖而受到关注。12月6日,他的孩
子、女婿和妻子陪同他来到斯德哥尔摩。接下来一周,外交部官员一直陪同他。
之后的三天,他参加了如旋风一样的记者招待会、官方午宴和晚宴。在10日上
午,他预演了获奖仪式。 [5]
(所谓的)诺贝尔音乐节在同一天的下午4点开始。
在黑暗寒冷的北欧冬季,这次活动是一年之中的“瑞典的社交活动事件”,也是一
次令人眩目的迎接圣诞的活动。 [6]
所有领域的诺贝尔奖得主,男士都要身穿黑色燕尾服(一种带长尾的礼
服),系白色领带,然后由各种旗帜打头阵,在一队学生的簇拥下,走进庄严的
斯德哥尔摩音乐大厅。学生们穿着无尾礼服(女士则穿黑色长袍),头戴白色尖
顶海军帽,身披蓝黄相间的绶带,蓝色和黄色是瑞典国旗的配色。大喇叭里传出
像国王一样的声音,宣布奖项和获奖者。然后上百个显赫人物继续前往斯德哥尔
摩蓝色城市大厅,并在那里待三个小时。他们会一起参加皇家宴会、家庭聚会以
及和学生共同庆祝等一系列活动。 [7]
餐点已经由年会的主厨秘密预定好,模拟
宴会也已经提前一个月进行过预演。为了保持温馨的瑞典宴会传统,通常会有学
生合唱团用歌声来给晚宴增色。在之后几年中,逐渐加入了管弦乐队的表演,发
展到20世纪90年代,这一娱乐庆典似乎已经成为一出“小型戏剧”了。与此同时,整个国家民众都能在电视上观看这一庆典活动。整个现场会穿插着干杯和短暂的
演讲,最后在维也纳华尔兹的舞曲中结束。 [8]
在获奖后的第二天,哈耶克发表
了传统的诺贝尔获奖演说。而两周之后,他在给诺贝尔基金会主席写信时说
道:“我们慢慢地从美丽的斯德哥尔摩之梦中苏醒过来,回到了日常的生活之中..”
[9]
与他共同获奖的经济学家纲纳·缪达尔持有的是社会民主主义观点,他选择将
奖金捐献出去,但是哈耶克没有这样做,我只能将此理解为这笔奖金缓解了哈耶
克所憎恨的他对福利国家的依赖(因为高昂的医疗费用)。 [10]
对米尔顿·弗里德曼而言,这一奖项掀起了一股庆祝狂潮,每一次庆祝,他都
进行了私人答谢。其中有来自三个著名的以色列社会民主党人士的贺词,第一个
就是集体区居民[(埃胡德·阿弗里尔(Ehud Avriel)、什洛莫·埃韦尼利
(Sholomo Avineri)、迈克尔·布鲁诺(Michael Bruno)]。 [11]
来自经济事务研
究所(英国的新自由主义思想智库)的拉尔夫·哈里斯(Ralph Harris)和阿瑟·塞
尔登(Arthur Seldon)发来贺电,“我们很高兴你没有像哈耶克跟缪达尔一样,与
约翰·加尔布雷思(John Galbraith)分享这一奖项”。英国著名经济记者塞缪尔·布
里坦(Samuel Brittan)曾经非常矛盾地写道:“这一奖项让我们的心跟随我们所
看到的英国并没有走智利道路的事实。”[1975年5月,弗里德曼曾给哈里斯写信
说:“罗丝(Rose)和我在智利度过了非常美妙的一周..我担心智利就是未来英国
的样子。”]
[12]
而思想上的对手肯尼斯·阿罗则明确保证这一奖项已经被他摘取
了。 [13]
“自由党”主席爱德华·克兰三世(Edward CraneⅢ)作为一名密友
说:“因为你和哈耶克这三年的努力,自由市场总算是变得非常可观了。” [14]
哲
学家卡尔·波普尔在写给弗里德曼的信中说:“对于朝圣山学社而言,这是多么令
人振奋的消息啊!它的两任主席都摘得了诺贝尔桂冠!” [15]
这一程序已成定式。 [16]
决定谁能获奖的权威都身处声誉卓著的学术机构之
中:瑞典皇家科学院、瑞典学院和卡罗林斯卡医学院。和平奖是一个例外,它由
挪威议会颁发。文学奖由瑞典文学院颁发。而瑞典皇家科学院则是经济学奖的管
理机构,对奖项的提名记录有保密50年的规则,但是其设有三个公开账户、一个
资料库和三个会谈,以此来看似公开地提供相关信息。 [17]
要知道,其他诺贝尔
奖项均是由五位专家构成的永久委员会来履行排名和推荐候选人这项职责的。每
年秋季,诺贝尔经济学奖就开始进行提名(次年2月1日截止),那些有资格提名
他人的人有的来自瑞典皇家科学院,有的是北欧国家某些大学的经济学教授,也
有曾经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奖人,还有经济学奖评委会的成员。每年秋季,评委会会寄出符合要求的候选人名单,然后评委会将选出几百名被多次推荐的候
选人,并委任海外评审专家来筛选候选人,评委会整个夏天都会收到来自四面八
方的推荐信。最终候选人名单会提交给各位院士,然后提交到所有学术成员的全
体会议上,经历两轮会议讨论之后再确定最佳人选。最后通过秘密投票来选出得
票最高的候选人。可见,没有提名就没有评选,有时候评选就像一场战争。列夫·
托尔斯泰(Leo Tolstoy)在1901年没有获得文学奖提名,于是就拒绝以后被考虑
提名。 [18]
同样被错过的还有安东·契诃夫(Anton Chekhov)、约瑟夫·康拉德
(Joseph Conrad)、托马斯·哈代(Thomas Hardy)、亨利克·易卜生(Henrik
Ibsen)、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詹姆斯·乔伊斯(James Joyce)、马塞尔·
普罗斯特(Marcel Proust)、奥古斯特·斯特林堡(August Strindberg)、弗吉尼亚
·伍尔芙(Virginia Wolf)、爱弥尔·佐拉(Emile Zola),还有许多获奖者并不出
名,而那些特别出色的反而几乎被人遗忘了。
国家学术机构一般由资深或者年长的学者组成。论资排辈与革新带来的破坏
性潜力是不相称的。科学共和国(The Republic of Science)有一个不成文的规
矩,那就是实质研究比地位更重要,而且每个人的声音都要能被听到。在自然科
学领域,这对诺贝尔奖评定委员会来说是一个挑战。 [19]
瑞典很少处于研究的最
前沿,学者有时候发现跟随前沿脚步是非常艰难的。专家并不比他们所支持的观
点水平更高,甚至至多就是旗鼓相当。像化学家斯凡特·阿伦尼斯(Svante
Arrhenius)和物理学家卡尔·威廉·奥森(Carl Wilhelm Oseen)这样非凡的人物渐
渐掌管了委员会。一个反常规的做法就是他们会阻止当年某个奖项的颁发,节省
下来的钱转给瑞典研究基金,有时候也会转化成委员会成员的隐形利益。一个简
单被征求意见的提名就可能胜过被外界大量提名的候选人。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在
1905年就公开发表了三篇划时代的论文,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这三篇
论文已经非常著名了,但是他错过了好几次得奖机会,最终在1922年因为一篇并
不是他最重要的论文而得奖,这篇论文对于委员会中反对相对论的人来说更容易
接受。
还有一些天才很晚才被大家认识,一些人甚至在机会到来之前就已经去世
了,而少数几个因为做出的是共同发现,所以也错过了得奖机会。北欧的候选人
面临的障碍可能比较小。提名委员会的决定(它做了绝大部分工作)可能在自然
或社会科学分组中,或者全体委员讨论时被推翻。尽管有一些瑕疵,并且经常遭
到怀疑和询问,这一奖项仍然保持很高的地位。全世界都知道 ......
[英]阿夫纳·奥弗尔 [瑞典]加布里埃尔·索德伯格 著
苏京春 李海蓉 译
中信出版集团
目录
前言与致谢
缩略词一览
1969—201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一览
引言
第一章 假想机器
第二章 “经济科学”奖
第三章 痛苦之源: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金融与社会民主
第四章 瑞典央行捐赠了一个诺奖
第五章 经济学有政治偏见吗
第六章 个人声誉
第七章 诺贝尔经济学与社会民主
第八章 将模型引入决策:阿瑟·林德贝克与瑞典社会民主主义
第九章 究竟是瑞典僵化症还是假性僵化症?20世纪80年代的瑞典
第十章 真正的危机:不是如何激励而是信贷失控
第十一章 斯堪的纳维亚之外:腐败肆虐华盛顿共识
结论 经济学究竟更像物理学还是文学
注释
译后记
1976年12月10日,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从瑞典国王卡尔十六世·古斯塔夫(Carl XVI
Gustaf)手中接过诺贝尔经济学奖
我坚信:
有道理的事,说一遍即可;
没道理的事,说千遍亦无用。
——威廉·哈兹里特(William Hazlitt)
《席间闲谈》(又名《关于人物及风格的新评论》,1822年)
(Table Talk or Original Essays on Men and Manners )
前言与致谢
1970年左右,时代气息突变。在西方富裕社会,持续20年之久的充分就业与
富足被艰苦岁月与劳苦之身取代。那些基于经济学说主张对市场进行调控和刺激
的论证无法解释这场“市场变革”(market turn)。那么,经济学说是如何发
挥作用的,都能发挥什么作用呢?诺贝尔经济学奖(1969年第一次颁发)很合时
宜地给出了不同时代经济学说的定位。诺贝尔经济学奖为新古典经济学和社会民
主主义这两个不断发展的学说之间产生的冲突提供了一定的参考,而这两个学说
竞相影响着战后若干年社会的形成。瑞典创立了诺贝尔奖,而其自身是社会民主
的一个原型。这个国家也只是长篇故事中的一个篇章,实际上社会民主主义对我
们的影响更为广泛。表面上,这两个学说泾渭分明,实际上,它们相克相生,尽
管这并不意味着这两个学说结合后会更完美。
本书开门见山地阐述了诺贝尔奖项的故事,从第二章第一部分的介绍开始,而后在第四章和第六章进一步做了叙述。第三章则深入探讨了两次世界大战之间
的历史根源。
在进入正文之前,我们首先要致谢为本书提供帮助的人。因为这个选题,他
们之间形成了一种非正式的公私合作伙伴关系。我们的母校——乌普萨拉大学和
牛津大学,以及牛津大学万灵学院,在教学和管理方面给予了我们很大的支持。
乌普萨拉大学和万灵学院为我们提供了非常好的工作地点以及良好的合作条件,牛津大学纳菲尔德学院则提供了非常丰富的图书馆资源,学校里的同事甚至乐于
将我们的一些日常工作纳入他们规定性的研究任务当中。这些大学都诚挚地配合
了由利华休姆信托基金和新经济思维研究所(INET)资助的研究机会,这两个机
构(起源于80年前)都是由慷慨的资本家创建的。牛津大学历史学院和万灵学院
也为我们的一些特殊需求提供了小额资助。此书完稿于加布里埃尔接管瑞典银行
之前,所以书中使用的数据均不含其任职期间的数据。
在瑞典,阿瑟·林德贝克(Assar Lindbeck)教授与阿夫纳·奥弗尔进行了
为期一天的全方位访问,该议程还得到进一步延伸,增加了令人颇受鼓舞的晚宴
环节。约尔根·韦布尔(J?rgen Weibull)教授促成了这次访问活动,并且通过
敏锐决策推动了晚宴的实现。在瑞典,我们还与拉尔斯·马格努松(Lars
Magnusson)教授、杰肯·米达尔(Janken Myrdal)教授和彼得·诺贝尔
(Peter Nobel)教授进行了对话。在此向他们致谢。
萨缪尔·比约克(Samuel Bjork)参与了第六章的写作。他为巴斯模型提出
了一个新的运算法则,并且使用了我们收集到的数据来估计巴斯曲线。菲利普·
米卢斯基(Philip Mirowski)也曾与我们合作,但是因观点相左而离开了。他
尖锐直白的建议对本书产生了应有的影响,这也使我们的合作结束得更加温和。
同事和朋友们都给予了我们帮助、倾听与回应。克里斯托弗·拉格奎斯特
(Christopher Lagerqvist)建立了牛津-乌普萨拉实验室,这一实验室首次把
我们凑在了一起。研讨会和会议论文得以在四大洲的12个国家举行和发表。在此
一并感谢对我们的邀请、尖锐的评论以及所到之处、所见之人、所思所得共同形
成的丰富经历。我们的朋友和同事(包括三个研究助手,在此也一并提及)阅读
了本书的相应章节,并且对本书的观点进行了研讨,他们包括圣达斯·埃里
(Sundas Ali)、托尼·阿特金森(Tony Atkinson)、萨缪尔·比约克、莎拉
·卡罗(Sarah Caro)、文森特·克劳福德(Vincent Crawford)、保罗·大卫
(Paul David)、詹姆斯·芬斯克(James Fenske)、塔玛·弗兰克(Tamar
Frankel)、蒂姆·罗尼格(Tim Leunig)、约翰内斯·林德沃(Johannes
Lindvall,他做的贡献远远超过其职责范围)、孟苗(Meng Miao)、菲利普·
米卢斯基、汤姆·尼古拉斯(Tom Nicholas)、亨利·欧胜(Henry
Ohlsson)、安德鲁·斯科特(Andrew Scott)、克劳迪奥·索普兰泽蒂
(Claudio Sopranzetti)、戴维·斯图克勒(David Stuckler)和朱丽亚·特
威格(Julia Twigg)。完整稿由帕梅拉·克莱米特(Pamela Clemit)、沙米姆
·甘米奇(Shamim Gammage)、麦克斯·哈里斯(Max Harris)和罗梅什·瓦提
林根(Romesh Vaitilingam)审读,他们纠正了我们的很多错误,这使我们受益
颇丰。书中如果存在错误都是我们自己的责任。出版社的两个审稿人付出了大量
劳动并提供了大力支持。他们的贡献使我们想表达的观点更加精确。沙米姆·甘
米奇为我们提供了出色的技术支持。莎拉·卡罗和汉娜·保罗(Hannah Paul,为出版社工作)给予了我们大量鼓励、包容和指导。
在此,加布里埃尔对妻子毛(Mao)表示感谢,并对即将长大且开始学习阅
读的女儿小李李(little Li)同样表达感激之情。阿夫纳也向妻子利亚
(Leah)表示感谢,感谢她几十年来的合作、支持、勤勉以及其给予的独到见
解。
缩略词一览
AEA: 美国经济协会
ATP: 瑞典补充养老金制度
BIS: 国际清算银行
DSGE: 动态随机一般均衡
ESO: 公共经济学研究专家组
FOREX: 外汇
GDP: 国内生产总值(经济产出的国内度量,不考虑海外资产的产出)
IMF: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UI: 工业经济与社会研究所,斯德哥尔摩;目前叫工业经济研究所
LDC: 欠发达国家
LIBOR: 伦敦同业拆借利率(英国基准金融市场利率)
LO: 瑞典体力劳动者工会联合会
MCE: 市场出清均衡
NBER: (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
NCM: 新古典宏观经济学
NPW: 诺贝尔奖得主
OECD: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PPP: 购买力平价(相关经济体中可比较商品价格所决定的汇率)
SAF: 瑞典雇主联合会
SAP: 瑞典社会民主工人党
SNS: 商业和政策研究中心,斯德哥尔摩
TCO: 瑞典非体力劳动者工会联合会
VAR: 向量自回归(一种广泛应用数据的一致性但不是明确检验理论模型
的统计学估计方法)
WashCon: 华盛顿共识
1969—201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一览
1969: 拉格纳·弗里希(Ragnar Frisch)
简·丁伯根(Jan Tinbergen)
1970: 保罗·A.萨缪尔森(Paul A.Samuelson)
1971: 西蒙·库兹涅茨(Simon Kuznets)
1972: 约翰·R.希克斯(John R.Hicks)
肯尼斯·J.阿罗(Kenneth J.Arrow)
1973: 华西里·列昂惕夫(Wassily Leontief)
1974: 纲纳·缪达尔(Gunnar Myrdal)
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冯·哈耶克(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
1975: 列奥尼德·康托罗维奇(Leonid Vitaliyevich Kantorovich)
佳林·C.库普曼斯(Tjalling C.Koopmans)
1976: 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
1977: 詹姆斯·E.米德(James E.Meade)
贝蒂·俄林(Bertil Ohlin)
1978: 赫伯特·A.西蒙(Herbert A.Simon)
1979: 阿瑟·刘易斯爵士(Sir Arthur Lewis)
西奥多·W.舒尔茨(Theodore W.Schultz)
1980: 劳伦斯·R.克莱因(Lawrence R.Klein)
1981: 詹姆斯·托宾(James Tobin)
1982: 乔治·J.斯蒂格勒(George J.Stigler)
1983: 罗拉尔·德布鲁(Gerard Debreu)
1984: 理查德·斯通(Richard Stone)
1985: 弗兰科·莫迪利安尼(Franco Modigliani)
1986: 小詹姆斯·M.布坎南(James M.Buchanan Jr.)
1987: 罗伯特·M.索洛(Rober M.Solow)
1988: 莫里斯·阿莱斯(Maurice Allais)
1989: 特里夫·哈维默(Trygve Haavelmo)
1990: 哈里·M.马科维茨(Harry M.Markowitz)
默顿·H.米勒(Merton H.Miller)
威廉·F.夏普(William F.Sharpe)
1991: 罗纳德·H.科斯(Ronald H.Coase)
1992: 加里·S.贝克(Gary S.Becker)
1993: 罗伯特·W.福格尔(Robert W.Fogel)
道格拉斯·C.诺斯(Douglass C.North)
1994: 约翰·C.海萨尼(John C.Harsanyi)
小约翰·F.纳什(John F.Nash Jr.)
莱因哈德·泽尔腾(Reinhard Selten)
1995: 小罗伯特·E.卢卡斯(Robert E.Lucus Jr.)
1996: 詹姆斯·A.莫里斯(James A.Mirrlees)
威廉·维克里(William Vickrey)
1997: 罗伯特·C.默顿(Robert C.Merton)
迈伦·S.斯科尔斯(Myron S.Scholes)
1998: 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
1999: 罗伯特·A.门德尔(Robert A.Mundell)
2000: 詹姆斯·J.赫克曼(James J.Heckman)
丹尼尔·L.麦克法登(Daniel L.McFadden)
2001: 乔治·A.阿克洛夫(George A.Akerlof)
A.迈克尔·斯彭斯(A.Michael Spence)
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Joseph E.Stiglitz)
2002: 丹尼尔·卡尼曼(Daniel Kahneman)
弗农·L.史密斯(Vernon L.Smith)
2003: 罗伯特·F.恩格尔三世(Robert F.EngleⅢ)
克莱夫·W.J.格兰杰(Clive W.J.Granger)
2004: 芬恩·E.基德兰德(Finn E.Kydland)
爱德华·C.普雷斯科特(Edward C.Prescott)
2005: 罗伯特·J.奥曼(Robert J.Aumann)
托马斯·C.谢林(Thomas C.Schelling)
2006: 埃德蒙·S.费尔普斯(Edmund S.Phelps)
2007: 莱昂尼德·赫维奇(Leonid Hurwicz)
埃里克·S.马斯金(Eric S.Maskin)
罗杰·B.迈尔森(Roger B.Myerson)
2008: 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
2009: 埃莉诺·奥斯特罗姆(Elinor Ostrom)
奥利弗·E.威廉姆森(Oliver E.Williamson)
2010: 彼得·A.戴蒙德(Peter A.Diamond)
戴尔·T.莫滕森(Dale T.Mortensen)
克里斯托弗·A.皮萨里德斯(Christopher A.Pissarides)
2011: 托马斯·J.萨金特(Thomas J.Sargent)
克里斯托弗·A.西姆斯(Christopher A.Sims)
2012: 埃尔文·E.罗斯(Alvin E.Roth)
罗伊德·S.沙普利(Lloyd S.Shapley)
2013: 尤金·F.法玛(Eugene F.Fama)
拉尔斯·皮特·汉森(Lars Peter Hansen)
罗伯特·J.席勒(Robert J.Shiller)
2014: 让·梯若尔(Jean Tirole)
2015: 安格斯·迪顿(Angus Deaton)
2016: 奥利弗·哈特(Oliver Hart)
本特·霍姆斯特罗姆(Bengt Holmstrom)
2017: 理查德·泰勒(Richard Thaler)
2018: 保罗·罗默(Paul Romer)
威廉·诺德豪斯(William Nordhaus)
引言
在学术圈中,经济学家是为数不多的愿意阐述应该如何管理社会的群体之
一。他们很少有统一的声音,但这并没有减少他们的信心。不管是疑惑还是尊
敬,社会大众都对经济学家信心满满。而经济学家真正知道些什么,他们是怎么
知道这些的?他们的权威性来自何方,在多大程度上能得以证明呢?经济学说的
创建虽然通常带有理论推导的性质,但它的影响力是巨大的和实实在在的。自20
世纪70年代以来,经济学说的创建紧随重大历史趋势,这一趋势就是我们提出
的“市场转向”:它是市场自由主义不断崛起的过程,(像经济学一样)也是将购
买和销售奉为人际关系和社会组织准则的一场政治和社会运动。经济学到底能
给“市场转向”提供多好的理论证明呢?与过往相比,它究竟是不是一种进步呢?
公正世界理论
1969年12月10日晚上,在宏伟的斯德哥尔摩音乐大厅,当物理学、化学、医
学、文学奖项桂冠都被摘取之后,荷兰经济学家简·丁伯根被第一次授予“纪念阿
尔弗雷德·诺贝尔(Alfred Nobel)经济学奖”。其他领域的诺贝尔奖项都是从1901
年开始每年颁发一次的。阿尔弗雷德·诺贝尔虽然是一位多产的发明家和天才的商
人,但他并没有创立经济学奖项。在一封信中,他写道自己“满心憎恨商业”,他
把自己定位为社会民主主义者。 [1]
在颁奖仪式上,经济学家丁伯根被安排与其
他领域的获奖者分开而立。在文学奖得主——爱尔兰前卫剧作家、小说家和诗人
——萨缪尔·贝克特(Samuel Beckett)获得颁奖之后才颁发经济学奖项。尽管经
济学现在仍然很难有一定之规,但总体看来还是比贝克特所在的文学领域好一
些。那么经济学究竟是更像物理学还是更像文学呢?大多数获得诺贝尔奖的经济
学家都选择忽略这一问题,所以它一直遗留至今。
在进行寻求所谓“效率”这一实践利益的社会活动时,利益是什么,以及为谁
争取这种利益,通常并不明晰。然而,一旦经济学不能持续践行这一社会活动,它的有效性就会降低。经济政策会影响个人与国家的生计和福利,还会广泛影响
金融与商业利益。基于此,经济学家的观点应该具有某种特殊的权威性,这一点
跟其他专家群体相比显著不同:他们应当是有理有据的顾问,公正而客观。他们
应该独立于部门和个人利益诉求之外,也应该独立于来自宗教制裁或个人意志这
样的哲学范畴诉求之外。在这里,我不得不提到一个经济学家通常不会意识到的
事实:他们在研究中往往将个人观点作为首要考虑因素,然而在提出对策时又会
忽略这一点。
经济学包括许多学说和主张,这些学说和主张之间并不总是协调一致的。经
济学的目的是给社会现实提供一个简化但正确的解释。它的权威性是双重的:一
方面在于理论本身必须引人注目,另一方面在于理论能够经受观察与结果的检
验。经济理论的魅力就在于它每天要将与直觉相冲突的事实进行简化处理,与此
同时还要给混乱的现实建立秩序。有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经济学理论很难被人
们掌握,但很容易被人们相信。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方法论者(赞扬经济
学方法和研究目的的学者)将关注重点和很多努力都放在了理论的内在有效性
上,特别是关注这些理论究竟如何联系在一起并且产生作用。 [2]
关注这一课题
的主要原因是,许多经济理论既不是来源于实践,也不是来源于实验结果。
维多利亚时代的生物学家托马斯·赫胥黎(Thomas Huxley)曾在1870年说
道:“科学的巨大不幸在于美丽的猜想被丑陋的现实扼杀。”冒着不合时宜的风
险,我们与现今的方法论者分道扬镳,而力求回到更简单的时代。在那时,理论
如果想要被认定为正确,就必须与发生的事实相一致。将理论与现实对证并不是
一件简单且容易办到的事情,我们也不想以此来冒犯那些提出相关理论的作者,但我们当中有人亲自进行了尝试,将乔治·阿克洛夫的柠檬市场经济理论(这一理
论因在2001年获得诺贝尔奖而得到认可)与历史上的二手车市场进行了对比。
[3]
不难发现,在这个理论当中,有一个关键的理论基础是错误的。若像这个理
论阐述的那样,其先天就是不可检验的,它的一些假设不是必然的,这与现实不
符。而我们坚持现实的理由是,理论不仅应当涉及如何理解世界(这是所谓认识
论)或者说世界是如何形成的(这是所谓存在论),还应当涉及生活如何运转。
也就是说,理论还应当具有“规范”的特性。许多因素都会牵扯到部分人的利益或
导致部分人的苦难,而针对这些问题,经济学是否都有能力去面对并解决呢?可
能也正是因为如此,我们才必须要不停地追问:“经济学正确吗?真的有用吗?”
[4]
而其他学科可以不需要证明这些问题就可以坦然地存在:委托和精神上的信
仰不需要得到外界客观事实的证实。统治阶层经常会抵触观点和证据。官员、神
职人员、先知以及领导者不会总是屈服于实验结果,但是欧洲和美国的启蒙运动
者却以批判的观点和证据探索了现实。我们认为,科学就应该遵循这种方法。而
经济学,如果想要寻求同样的社会尊重,也应该遵循一样的研究方法。
经济学到底建立了什么样的“规范”?其研究开始于最大化“财富”或者说“福
利”这样值得赞赏的原则。然而,福利被定义为个人想要得到的东西。这就是所谓
的“方法论中的个体论”原则。当一个人能够获得更多他想得到的东西,而没有剥
削别人的财富时,我们就说发生了社会进步,即所谓的“帕累托改进”[Pareto
improvement,这是以意大利经济学家维尔弗雷多·帕累托(Vilfredo Pareto)的名
字命名的]。在社会不存在懒惰现象的情况下,如果没人损失,就没人获取。我们
通过交易达到这样的社会状态:人们卖出他们不那么需要的物品(包括劳动
力),同时买入他们更需要的物品。每个人都有可以用于出售的东西。如果每个
人可以自由交换,那么整个系统就可以实现良性均衡,即所谓“帕累托效
率”(Pareto efficient)。这种状态在18世纪就是亚当·斯密期盼的在“看不见的
手”的作用下所达到的状态。 [5]
在这样的系统中,每个人都可以获得与所能出售物品相对等的价值,所得即
应得。这样的理想市场状态,岂不是与一个更广泛的学说直接关联在一起了!这
个学说叫作“公正世界理论”。这一概念虽然来源于社会心理学,但是在此以另一
种不同的内涵得到了应用。 [6]
“公正世界理论”非常简单:它认为每个人都获得
了自己应得的东西。即使西班牙宗教法庭烧死了异教徒,那也是因为他们罪有应
得。即使苏联的农民挨饿或者被驱逐,那也是他们应得的下场。同样,纳粹分子
和犹太人所为和所遭遇的,也都各有理由。“公正世界理论”无处不在,带有政
治、宗教、种族、性别和文化含义。这个理论荒诞地认为世间所有的痛苦都有其
合理性。
而市场自由主义就是这样一种意义上的“公正世界理论”。1976年的诺贝尔奖
得主米尔顿·弗里德曼就曾写道:在自由市场社会中,可以直接证明国民收入分配
合理性的原则,就是要让每个人按照他生产的产品,以及他拥有的工具生产的产
品,来分配其所得到的财富。 [7]
换言之,每个人都得到了他应该得到的。财富
和能力的初始禀赋分配以及相应的市场产出这两者(正如弗里德曼所说)在学理
上都应当各得其所。他认为,自由市场经济不仅是有效率的,而且是公正的,它
体现了一种无法违背的自然秩序。个体规范给予了市场经济社会当中存在的不平
等以及经济困难现象一个看似合理的解释。这是19世纪古典自由主义倡导的自由
放任观点的突出表现。虽然不是每个经济学家都接受自由放任所秉承的伦理价值
观点,但在经济建模过程中,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这一假设是普遍存在的。
市场自由主义十分激进。如果你天真地认为个体的自利行为真的能够让集体
福利最大化,那么就表示你间接承认了任何形式的集体行为都很可能损害福利或
者减少福利。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20世纪70年代以来,许多与政策有关的经济
分析实际上都以此为出发点。这是一个相当反直觉的结论,而实际情况真的是这
样吗?诺贝尔奖的重要作用之一在此呼之欲出,那就是提供公正的科学验证。自
利或者说市场出清这种“看不见的手”的理论,与我们所做的许多有组织的社会改
进活动的努力方向并不一致,特别是在社会民主问题上,这一冲突更加明显。
社会民主对经济学的挑战
19世纪后三分之一时段,贸易集团和社会民主党派有所发展并抵制了这一预
先假设。 [8]
他们的活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首先在澳大利亚的政府中产生了
影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又开始在欧洲的西北部产生影响。社会民主(在本
书中我们这样称呼这种社会实践)跟那一时代的经济学相比有不同的优先考虑顺
序。在经济理论中,行为是由独立自主的个人支配的。在社会民主问题中,基本
的行为冲动不是为了获得个人满足而是出于义务,基本的活动单位不是个体而是
群体、家庭、阶级和国家。初始目标并不是获取私利的满足,而是获得安全感。
更明确地说,是处理生命周期中的偶然问题。相较于经济理论中激发行动的个人
渴望而言,社会民主是受到如何处理依赖关系这样的社会问题支配的。
在生命周期中,每个人都要经历自己不能供养自己的时间段。在最初为人母
阶段、幼年以及孩童阶段、受教育阶段、生病阶段、失业阶段、残疾阶段以及老
年阶段,生活成本都是非常高而且非常消耗时间的。 [9]
在处于依赖状态的时
候,除了可以要求人权之外,我们没有可以用于出售的产品来讨价还价,我们没
有可以立足的能力,在谋划人生上也没有远见和能力。“福利”问题就是解决如何
在整个生命周期中将资源从生产者手中转移到具有依赖关系的人手中。在美国南
北战争的年代,失业问题几乎威胁着每一个从事手工劳动的家庭,因为失业会使
其丧失赖以生存的基础。
社会民主和市场经济学说之间的区别很容易描述,即如何处理不确定性问
题。对每个个体而言,依赖的时机和程度是不确定的。然而从总体上说,社会作
为一个整体,互相依赖的程度是众所周知的,其未来的情况也是可以精准预测
的。在社会民主问题上,可以互相支持,从一代人向另一代人的横向转移,从生
产者向受赡养者的转移,都是通过税收实现的。在这样一个社会保险系统中,受
赡养者的风险是储存在一个池子当中的。有多少财富可供转移是由纳税人和接受
者之间的政治平衡决定的。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每个人都做出贡献并从中受
益。 [10]
相比于弗里德曼,在社会民主学说中(也称为“公正世界理论”),每个
人都各得其所。这就把福利来源的权利扩展到了整个国家和政府。在瑞典,社会
民主被认定为“人们的家”,其领导人这样说道:
家的基础是共同性和相互性。一个好的家庭不会有特权,也没有人受轻
视,家长对待自己的子女和继子女都是一样的。没有人会轻视他人,也没有
人会利用他人来获得好处……在好的家庭中你会看到平等、同情、合作和互
助友爱。 [11]
社会民主甚至更注重性别平等,它并不关注市场,而是更加关注家人和家
庭。在诺贝尔奖项设立30年之后,才有一位女性——埃莉诺·奥斯特罗姆,获得了
诺贝尔经济学奖,她是迄今为止唯一一位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女性。
相较而言,在经济学问题上,风险是由每个独立个体导致的。每个人从年轻
时开始不断支付保险费并不断存款,从而将自己的财务索偿权安全地转移到养老
问题实际发生的未来。证券和其他商品一样,每个人按照各自能承受的限度,在
金融市场上以保险和储蓄的形式购买。风险由保险公司和银行储备在资金池中。
每个人按照商业合同的规定来享受保险。
在未来获取利益的方式上,两种学说是不同的。但是,在两种学说之间还有
重叠:对生产而言,两者都依赖私人所有权和管理,并且通过市场进行分工,或
多或少都有竞争性;两者也都依赖政府,从而寻求一系列公共产品和集体产品,如国防和公路。
工人诉求、贸易联盟、社会主义、土地改革运动以及社会民主等社会现象,都需要有一个智慧而合理的解释,而维多利亚晚期的经济学说就解决了这一问
题。 [12]
自由经济学家主张维持现存的财产秩序及其不平等性。在西欧、北美和
澳大利亚,社会民主最终战胜了法西斯主义,建立了福利国家,在战后的30年中
保卫了资本主义结构并主导了政策。它使经济增长更可持续,并使财富分配更加
平等。为了实现这一点,它必须挑战新古典经济学的假设,有时候甚至要摒弃这
些假设。
与正统经济学中一切自由这一竞争性思想相较而言,社会民主党派在战后欧
洲(英语国家)建立了一系列的共同意志:
建立用于供给养老需求的集体保险,由政府规范和管理,通过渐进式
税收实现。
通过租赁控制、新建房屋、抵押机构、公共或者集体所有权来实现高
质量可负担房屋的供给。
提供更好的中等和高等水平的教育,支持科学研究,开展文化和体育
活动,有计划地使用土地,修建公路和铁路。
在一些扩展公共服务和国有企业领域建立混合经济,但是仍然保持对
生产和分配管理的私人所有权。
对弱势群体要进行特殊关注。 [13]
美国也实行了很多这类方案,即使不能提供全民健康权利保障,至少也会向
老人及贫困人群提供这种保障。
这些服务看上去都非常昂贵:由政府管理,从税收中支付,在欧洲西北部,政府在这方面的支出在20世纪70年代末甚至占到GDP的40%~50%。但是选民认
为:总体而言,对纳税人来说,这一支出带来的好处是大于成本的。 [14]
它将购
买力从消费旺盛的年份推迟到了真正有需要的年份。赚钱的人帮助那些暂时需要
供养的人:母亲、儿童、学生、失业者、残疾人、病患以及年迈的老人。反过
来,有生产能力的人也期盼当自己处于人生中需要被赡养的阶段时也能够得到这
些帮助。税收是渐进式的,所以那些富有的人就会缴纳更多的税,相应地从税收
中得到的更少。在福利较高并且是全民享有福利的情况下(即所有人可以均等享
有),那些收入较低的人相应地受益更多。 [15]
发达国家的这种不平等在中世纪
时期达到了最低水平。
竞争观
将第二次世界大战归结为是美国南北战争期间传统经济学失败的结果,并不
牵强。 [16]
在1944年,战势依然肆虐,两家媒体报道了两位经济学家提出的对未
来的不同看法,这两位经济学家在30年后的同一天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一是
《战后瑞典劳工计划》(The Postwar Programme of Swedish Labour ),由当时瑞
典执政的社会民主党发表,其合著者是经济学家纲纳·缪达尔[他的画像还在我们
的夹克衫里,画像里还有他的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妻子阿尔瓦(Alva)]。 [17]
二是《通往奴役之路》(The Road to Serfdom ),由哈耶克所著,在英国发表。
[18]
瑞典的社会民主党于1932年执政,它使瑞典远离战争。 [19]
它于1944年提出
的项目计划是其社会抱负达到顶峰的表现。它谴责内战经济学容忍了失业和贫
穷,战争甚至刺激了处于中立的瑞典生产资源的流动,而瑞典本来应该是一个世
界和平的典范。27项具体的挑战体现在三个大的方面:“充分就业”(这是社会安
全的主要保障),“公平分配和更高的生活水平”(这意味着从资本到劳动力的重
新分配),“更高的生产效率和提升的工业时代的民主性”(确立了经济增长的目
标)。这是瑞典社会民主党最突出的特点:纲纳·缪达尔的创新之处在于他提出了
所有人的安全和平等也具有生产性这一观点。 [20]
由于精神问题和社交能力的不
足可能导致有些人不能工作,而热衷于改革对这些人是缺乏同情心的,这是改革
的负面问题。 [21]
不论怎样,整体来看,这对传统经济思想来说也是一种清晰
的、适度的且带有民主性的挑战。 [22]
在哈耶克看来(他是在伦敦经济学院任职的奥地利籍教授),社会民主是“通
往奴役之路”的第一站,它甚至会开启专政之路。但这本专著也容易让人对理解他
的观点产生偏激:哈耶克实际上认可那些对社会保险及其他方面的政府干预。他
一方面对社会民主的“社会”方面感到不安,另一方面也对“民主”的一面表现得比
较谨慎。自由作为专政的对立面,并不一定会引发民主,还必须避免多数人的暴
政。 [23]
“我宁愿暂时牺牲..民主,如果是在自由实现之前必须这么做的话。”他
于1981年在智利接受访问的时候这样说道。 [24]
《通往奴役之路》在英国引起了轰动,当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这本书之
后,美国的反响更是热烈。 [25]
它的发行量巨大,在《读者文摘》(Reader.s
Digest )中发表的缩编本的发行量超过100万册。在畅销周刊《看》(Look )上
发表的卡通版本也获得了通用汽车和通用电气的免费资助发行。卡通版本省略了
关于社会保险的章节。此书还被迅速翻译成瑞典语,在瑞典成为反对社会民主的
一个焦点问题,而社会民主党候选人对权力的把握在瑞典从来都不是很稳固。
[26]
哈耶克关于社会民主的滑坡理论曾经被荒诞地歪曲:在世界上没有哪一个社
会比北欧福利国家更加远离奴役境况。政府高度干预的混合经济很多年来都保持
了政治自由和经济自由,然而自由体制和极权体制却都未达到这种状态。 [27]
但
是随后哈耶克不断否定经济学的科学地位,一直到后来其发表诺贝尔奖获奖演说
时都是如此。
哈耶克当时在英国已经被约翰·梅纳德·凯恩斯边缘化,但是在美国却被奉为
名人。他将他在文学和财政方面的成功转化成政治方案。1947年由商业基金会出
资,在瑞士朝圣山酒店举办了一场经济学家、记者和商人的聚会。经过几天的深
思熟虑,这些参会者发起成立了朝圣山学社。从那年开始,在美国基金会的资助
下,社团定期在舒适的大酒店召开聚会,从而成为抵制社会民主的思想焦点。
[28]
在大概20年的时间里,这一社团由哈耶克掌管,由他来审核所有的新成员。
第一次聚会邀请了一些欧洲和美国的持有反劳工立场的主要知识分子,其中包括
几位未来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哈耶克、米尔顿·弗里德曼、乔治·斯蒂格勒、贝蒂·
俄林和莫里斯·阿莱斯(虽然后两位学者拒绝了邀请)。 [29]
另外一位参加者,哲学家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即《开放社会及其敌人》(The Open Society
and its Enemies ,1945年)的作者,甚至提出应该向外部批评家开放社团会议,但是遭到了哈耶克的拒绝。 [30]
“自由”并不等于开放的思想。
多年以后,米尔顿·弗里德曼向社团的官方历史学家马克斯·哈特维尔(Max
Hartwell)这样描述社团的发展进程:
在朝圣山学社成立会议上我们所预计的对自由社会的威胁,与经过干预
时期后所凸显出来的对自由社会的威胁有很大不同。起初我们担心的只是中
央计划经济和广泛国有化问题,而新的威胁是经过福利国家和重新分配而发
生作用的。很不幸,这种威胁没有消失,而仅仅是改变了特性而已。尽管如
此,我仍然相信在解释所谓的自由主义重现这一问题时将这个变化指出来还
是非常重要的。就像多年以前由国际妇女服装工人联合会制作的音乐剧《坐
立不安》(Pins and Needles )中的一首歌的歌词写的那样,“向前一步,向后两步,这就是我们的进步之路”。 [31]
这句歌词颇具讽刺意味(它也恰是列宁手册的标题)。 [32]
这部音乐剧源自
纽约犹太移民文化,而弗里德曼也诞生于这种文化当中。该音乐剧是由国际妇女
服装工人联合会的成员创作和制作,演员阵容中有剪刀工、粗缝工和缝纫机操作
员,1937—1940年,这部音乐剧在美国百老汇表演了1 000次以上,甚至在富兰克
林·D.罗斯福当政期间还在白宫进行了演出。弗里德曼在1985年写这封信的时候,虽然相当悲观地再次引用了这句音乐剧中的歌词,但这种表达成为朝圣山学社颇
具渐进主义色彩的漫长发展中极富幽默感的一笔。朝圣山学社最终获得了巨大的
成功,这种成功绝非仅仅体现在其八个成员都荣获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还包括在
此过程中其获得的巨大声誉。
理论及其成效
诺贝尔奖可以证明经济学建立的理论有相当深厚的理论储备。的确,只有一
小部分经济学家加入了朝圣山学社或者说支持其目标,但是其中最著名的部分成
员是诺贝尔奖得主。市场自由主义的支配地位几乎就是诺贝尔奖项设立的时间。
我们可以这样描述:1967年12月,米尔顿·弗里德曼做了美国经济学会会长致辞。
[33]
其所传达的信息相当具有鼓动性:与社会民主相关的凯恩斯经济政策使失业
和通货膨胀不再处于困境。在接下来的7年里,弗里德曼成为所有经济学家中被
引用得最多的经济学家之一,暂时超过了亚当·斯密,而后者此前一直是被引用次
数最多的经济学家。 [34]
这次演讲标志着在两个学说之间由来已久的历史博弈过
程中的一次变化。一方面,社会民主化是一场致力于减少大多数人的不安全和不
平等的政治运动,其方式是通过渐进式的税收来提供健康、教育以及避免生命周
期中的不确定性。另一方面,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学说(作为更广泛的新自由化和
市场自由化的社会运动学说)却用于毁灭这些改革。在接下来的几十年,新自由
主义(学说)以及市场自由化(运动)做了许多事情来反转战后福利国家,然而
对西方社会的大多数人来说,繁荣和前途一直持平甚至出现下降。但也就是在这
几十年当中,一定程度上因为新自由者所倡导的全球化,世界范围内的繁荣有所
增长。印度和巴西等虽没有屈从于市场自由化指令,但实际上也跟随日本、中国
台湾、韩国和新加坡这些先驱经济体渗透进了西方市场。 [35]
社会民主化背后并没有经济学那样巨大的智力团队。 [36]
在诺贝尔奖得主当
中,只有纲纳·缪达尔可以被看成是直接的倡导者(虽然在我们所处的时代,大约
有一半的诺贝尔奖得主倾向于社会民主主义,并且总体来说在经济学家当中占到
一个更高的比例)。 [37]
虽然没有许多学说理论,但是其实际的成功跟市场自由
化的成功一样显著。如图0.1所示,在处于主导地位的经济与发展合作组织国家当
中,大约30%的收入用于社会保险以及社会政策,并且由中央政府进行分配(底
部曲线)。1990—2008年,这一比例仍然处于上升状态。社会保险这一考虑因素
在选民中比重新分配问题更加受欢迎。 [38]
美国定期选举保守人士担任政府要
职,但是在对社会保险这样一个更小的部门进行的私有化尝试到目前为止是失败
的。原因就在于,对社会保险而言,社会民主主义方法更有效率, [39]
但是并不
安全。社会民主主义就其劳动观点来看与市场自由化直接发生冲突。对市场自由
化而言,工作像其他商品一样,可以随意购买和销售。“随意”(at will)是美国现
在的就业学说,允许工人在任何时候没有任何理由就被解雇(除非受到合同保
护)。对大多数人而言,这是极度不安全感的根源,因为家庭负债(如抵押贷款
的月供和孩子的教育支出)被锁定到未来很远的时间,工作让人有尊严、让人有
奋斗的目标。至少在美国,医疗保障普遍与就业联系在一起。在今天的欧洲市场
自由化进程中,“劳动市场弹性”很大,寻求与美国的“随意”就业学说相接轨。
图0.1 社会支出占政府支出的百分比和政府支出占GDP的百分比(1990-2008年)
资料来源:OECD, “按目的地国政府支出” (2014年)
注:GTE表示政府支出总额,SOC表示社会支出(健康、教育和社会支出保险 福利)GDP表示国内生产总
值。
2008年,金融市场必须由政府出手救市来避免更加荒唐的局面,这是无论是
社会民主人士还是市场自由主义者都不曾预见的政府干预的福利。但这么做并没
有得到任何赞同。相反,市场自由主义者将出现的赤字看作一种可能击垮福利国
家的星星之火,就像一个将要溺死的人只顾着跟他的妻子一起逃生,却任由身边
的求助者溺死一样。这样的故事在此书完结的时候还在继续。
我们要讨论的话题既不是针对单个诺贝尔奖获得者所获得的成功,也不是简
单地将诺贝尔经济学奖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实际上,我们采用了几种方式来
研究。 [40]
一套学说怎样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成功地激发了政策,实际上反映的是
经济学的世俗力量。而经济学说更容易从外部观察,比如从学说的使用者那里得
以反映,而并不是更多地由其创始人去主动评论。那些将经济学说用于政策制定
的人实际上很少精通经济学精髓思想。同样,对那些受到经济学说影响的人而
言,他们的观点,也就是我们采用的观点,也一样不是精通经济学的人表达的观
点。
本书的主旨
经济学通过构建简单的经济行为模型并将其集中体现在政策中来发生作用。
将个人的逐利性这一前提与社会和谐结合在一起实在是一项野心勃勃的事业,以
至于无论是客观分析还是经验判断都毫无争议地宣告这种尝试的失败。为摆脱这
些弱点,芝加哥学派的经济学家提出,盈利公司应该取代福利国家,这与政治上
的新右派观点是一致的。对于一种宣扬合理性的学说而言,诺贝尔奖是一个十分
反常的现象,是一个戏法,是单方面授予的一个奖项,就像赠予礼物一样。讽刺
的是,这样的一个戏法反而被看作是科学,甚至摇身一变成为一种权威。自然科
学家认为理论必须跟证据相符。然而在经济学研究中,因为实证上的失败,方法
论者已经不再对经济学做这种要求。许多实干家已经得出了相反的结论,并对核
心的学说提出了相反的意见。抽象理论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就达到了顶峰,然
而,在实验室里、实践中和自然科学实验中都出现了新的“经验转向”,几乎没有
提及市场出清理论。好几个诺贝尔奖得主也都对核心学说提出了疑问。
诺贝尔经济学奖起源于瑞典社会主义和商业精英之间的冲突,在西方社会更
广泛地存在于阶级冲突的当地化表现中。瑞典在“一战”中是中立国,具备丰富的
能力和自然资源禀赋,在战争中,很容易地转向了社会主义。在欧洲大多数国家
中,债务负担的挑战在国内和国际危机时刻达到顶点。1945年之后,瑞典执政的
社会民主党将住房和充分就业放在首位,而中央银行出于价格稳定的考虑,抵制
这一做法。政府扼杀了银行,于是银行寻求出路来坚持自己的主张。恰逢此时,诺贝尔经济学奖在1968年得到中央银行的捐赠,而当时社会民主主义的成功处于
巅峰。
经济学有政治偏见吗?我们可以用诺贝尔奖得主在学科中的引用统计和观点
纵览来研究这一问题。这一奖项的管理人(一个经济学家小组)努力保持左派和
右派之间的机制平衡,但是从总体上来说,在学科内部还是更倾向于观点天平的
右派,这是因为倾向于社会民主价值观的经济学家人数较左派多出了一两位。诺
贝尔奖评定委员会通过选出游戏顶端的学者而获得可信度。当然也有例外,比如
哈耶克,他在获奖前本来默默无闻,但是得奖使他的论文引用量得到飙升。委员
会也阻止过几位被高频引用的学者,其中至少有两位是基于意识形态的基础而进
行研究的。19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50年代是诺贝尔奖的第一个历史阶段,市场出
清的均衡经济学与古典自由主义的低税准则是一致的。社会民主主义在战后的成
功挑战了这一模型。经济学弹指之间就对此做出了回应,它用恶意动机假设代替
了协调假设这一研究基石。它基于效率挑战了社会民主主义,但是这一反转让实
践付出了代价。协调主义学说使制定理想的政策成为可能。而恶意假设使产出难
以确定。唯利是图不再带来最好的产出结果。经济学的权威被无形地破坏了。与
此同时,恶意假设又助长了恶意的发展。
在瑞典,社会民主主义受到一些与阿瑟·林德贝克教授有关系的经济学家的直
接挑战,林德贝克教授管理着诺贝尔奖项。林德贝克关于社会民主无效性的论断
并没有说服力。他警告的经济危机确实发生了,但不是以他预期的原因引发的。
这场危机是由金融管制的过于宽松导致的,而林德贝克和其他市场自由经济学家
对此观点持支持态度。当被邀请进一个右倾政府来制定政策的时候,林德贝克并
没有因此感到不安,他开出了一个收缩劳动津贴的药方。他的改革方案被部分执
行,但是它们的关联性受到质疑。尽管存在市场自由主义,但是瑞典的社会民主
主义还是可以适应的,它成功地经历了政府中各党派的变更和去工业化这一社会
变革。
在斯堪的纳维亚以外,有利于市场运行的改革受到在华盛顿得到支持的国际
金融机构的推行。“华盛顿共识”将信用扩展到发展中国家,但它以有利于商业发
展的宽松管制为前提条件。但这么做导致了一个预期之外的后果,那些借款国家
腐败盛行,而后这一后果又蔓延到居于核心的西方经济体,现在这一现象已经非
常普遍。这一难以捉摸的问题,使经济学宣称的种族中立遭到强烈谴责。这证明
了一点,即学说中的种族中立会导致更高昂的经济和社会成本。
总之,经济学的影响力与其作为哲学、一门科学学说以及一套政策的缺点相
比并不匹配。“看不见的手”是一项神秘的定律,但它反复失灵,到现在影响变小
了。另外,经济学有一套实证办法并取得了成功,有其技术上甚至科学上的可信
度所能解释的领域。这表明了一些权威的丧失,但并不是完全丧失。经济学并不
比其他的权威来源更有优势,但与其相比也不是更具劣势;它只是应该被看作许
多声音中的一种而已。从这一角度来讲,它更像是社会民主主义。诺贝尔奖评定
委员会认为经济学并不仅仅是一个孤立的包罗万象的思想体系,它要承认经济实
践的事实,诺贝尔奖评定委员会就可以一直保持这一奖项的可信度。社会民主主
义提供了一种解决办法,这种办法在实效上更具成功性,分析上更具连贯性,经
济上更具有效性,道德上更具吸引力,并且理论上更适度。
[1] Ahlqvist et al.,‘Falkst Pris i Nobels Namn’[‘False Prize in Nobel.s Name’](2001);Nobel,‘Alfred
Bernhard Nobel’(2001),260.
[2] Kincaid,Oxford Handbook of the Philosophy of Economics(2009);M?ki,Philosophy of
Economics(2012).
[3] Akerlof,‘The Market for Lemons’(1970);Offer,‘The Markup for Lemons’(2007).
[4] As per Blaug,‘Why I Am Not a Constructivist’(1994),118-119.
[5] Offer,‘Self-Interest,Sympathy,and the Invisible Hand’(2012).
[6] Rubin,‘Who Believes in a Just World?’(1975);Lerner,Belief in a Just World(1980).
[7] Friedman,Capitalism and Freedom(1962),161-162.
[8] Deane,‘Scope and Method of Economic Science’(1983).
[9] Offer,‘Economy of Obligation’(2012).
[10] Hills,Good Times,Bad Times(2014).
[11] Per Albin Hansson,Swedish Parliament,Andra Kammarens Protokoll Nr 14-19[Second Chamber
Debates],no.3,28 January1928,11.
[12] Deane,‘Scope and Method of Economic Science’(1983);Mirowski,Effort-less Economy of
Science(2004),chs.13-14;Gaffney and Harrison,Corrup-tion of Economics(1994).
[13] For Norway and Sweden,Sejersted,Age of Social Democracy(2011).
[14] Lindert,Growing Public(2004),II;Hills,Good Times,Bad Times(2015).
[15] Rothstein and Steinmo,‘Social Democracy in Crisis?’(2013),99.
[16] Chapter 3,below.
[17] Landsorganisationen,Postwar Programme of Swedish Labour(1946,originally published 1944).
[18] Hayek,Road to Serfdom(1944).
[19] Berman,The Social Democratic Moment(1998).
[20] Andersson,Between Growth and Security(2006),ch.2.
[21] Andersson,ibid.,ch.3;Myrdal,Nation and Family(1941),ch.6(revision of Alva and Gunnar
Myrdal,Kris i Befolkningsfr?gan[1934]).
[22] Landsorganisationen,Postwar Programme of Swedish Labour(1946),3-5.
[23] Burgin,Great Persuasion(2012),116-120,esp.119.
[24] Caldwell and Montes,‘Friedrich Hayek and His Visits to Chile’(2014),47.
[25] S?derberg et al.,‘Hayek in Citations’(2013),66-67.
[26] Lewin,Planhush?llningsdebatten(1967),267-273.
[27] Alves and Meadowcroft,‘Hayek.s Slippery Slope’(2014).
[28] Mont Pèlerin Society Papers,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Stanford Univer-sity,and
Liberaalarchief,Ghent;Hartwell,HistoryoftheMontPèlerinSoci-ety(1995);Walpen,Die offenen Feinde
und ihre Gesellschaft(2004);Mi-rowski and Plehwe,The Roadfrom Mont Pèlerin(2009);Burgin,The
Great Persuasion(2012),ch.3.
[29] Allais did so later.
[30] Burgin,The Great Persuasion(2012),95.
[31] Friedman to Max Hartwell,10 July 1985,Hoover Institution,Friedman Pa-pers,200-10.
[32] Lenin,One Step Forward,Two Steps Back(19041947).
[33] Friedman,‘The Role of Monetary Policy’(1968).
[34] See figure 6.9,below.Kenneth Arrow also overtook Smith for a few years.
[35] Alpert,The Age of Oversupply(2013);Lin,Demystifying the Chinese Economy(2011);
Wade,Governing the Market(1990);and chapter 11,below.
[36] Myrdal,Kris i Befolkningsfr?gan(1934);Crosland,Future of Socialism(1936);Korpi and
Palme,‘The Paradox of Redistribution’(1988);Esping-Andersson,Three Worlds of Welfare
Capitalism(1990);Rothstein,Just Institutions Matter(1998);Barr,Economics of the Welfare
State(2012).
[37] Below,chapter 5,figure 5.2.
[38] Taylor-Gooby,Double Crisis ofthe Welfare State(2013).
[39] Offer,‘Economy of Obligation’(2012).
[40] Grüske,Die Nobelpreistr?ger der?konomischen Wissenschaft(1994);McCarty,The Nobel
Laureates(2001);Vane and Mulhearn,The Nobel Memorial Laureates in Economics(2006);Breit,Lives ofthe Laureates(2009);Horn,Roads to Wis-dom(2009);Karier,Intellectual Capital(2010);
Klein et al.,‘Ideological Pro-files of the Nobel Laureates’(2013);Ghosh,‘Beautiful Minds’(2015).
第一章
假想机器
提到经济学家,我们通常都认为他们是为世界代言的清高群体,但实际上绝
大多数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都与世俗脱不了干系。“经济著作大部分都以推测为
主,都是对可能性世界的不确定探索。” [1]
大约一半的诺贝尔奖得主都主要致力
于学说框架、假想机器或者简单说就是“模型”的构建。这一术语其实可以与“模型
飞机”这种表述联系起来理解,但又不像模型飞机,因为经济学模型大部分都停留
在纸面上,通常以数学方程的形式存在,但是也有类似于机械上的那种可以构建
的经济模型。比如,菲利普斯的国民收入模拟液压计算机(Phillips MO-NIAC)
就可以模仿经济中的货币循环,它通过在玻璃管道中注入带颜色的水和可控制的
阀门,从而实现对政策选择的模拟。 [2]
模型的构建
英国的牛津市有一个巨大而美丽的开放空间,叫作港口草地,距离城中心很
近。因为是公有财产所以它没有被开发,这违背了市场准则。周末,这里往往会
吸引一些航模爱好者,这些航模一整天都在头顶发出声响。然而经济模型却几乎
不能被带到港口草地上去,也不可能飞行。想要离开它们的设计者去知晓它们真
正的适航能力有多好,是相当困难的。
港口草地市郊还有一座令人辛酸的纪念碑(见图1·1),它是为了纪念1912年
在那里坠机的两位优秀的飞行员。这座纪念碑凸显了科学与经济学模型之间的差
别。小型侦察机飞行器预示着真正的进步,而英国第一次有动力的飞行仅仅发生
在那次坠机事故的四年以前。这种革新是冒着生命危险来检验的,而不只是靠纸
面上的推测。它不仅需要钱来推动,还需要合作和竞争,由政府参与执行,并且
在特定的地点完成,以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但是在主流的或者新古典的经济学
中,模型并不在特定的时间和地点存在。如果这些模型被否定,那也不是靠实践
经验来否定,而是被其他经济学家所否定。 [3]
这还不是问题的终结。用琼·罗宾
逊(Joan Robinson,她是有资格获得诺贝尔奖的,但并未获奖)的话来说:“在一
个学科中,如果没有发现能够被广泛认可的某种可以证明的错误,那么该学说就
会长期存在。” [4]
经济模型并不容易设计,它需要跟一系列的制约条件相协调,包括已经存在
的信念、政策和政治导向、一些更大的理论、内部一致性、数学技术、程序化的
事实(例如生产者、消费者、税收),以及与真实世界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行类
比。 [5]
经济模型还需要由实证观察来证实:它必须像飞行模型那样,能
够“飞”起来。 [6]
图1.1 牛津伍尔弗科特(Wolvercote)公墓的航空纪念碑
资料来源:照片由阿夫纳(Avner)提供。
两个已有的知识点是经济学学说的核心思想:“学说个人主义”和“看不见的
手”。 [7]
经济活动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私人逐利的驱动,它会累积到一个很有效率
的状态(均衡),在这一状态下,供给等于需求,所有的市场达到出清状态。亚
当·斯密在经济学说中只提到过一次“看不见的手”这一概念。他并没有说明“看不
见的手”是如何起作用的,虽然他确实举了一个非常完美的例子, [8]
但它依然只
是一种猜想、一种信念。 [9]
想要证明均衡的有效性,想要从数学上证明其存
在,这种探究已经有很长的历史了。 [10]
我们可以跳过亚当·斯密之后的一个世
纪,从1874年的莱昂·瓦尔拉斯(Leon Walras)开始研究。他描述了这样一种经
济状态:所有价格都可以通过一种想象中的拍卖达到均衡水平,在拍卖中不会有
卖不出去的剩余产品。1881年的弗朗西斯·埃奇沃思(Francis Edgeworth)和1906
年的帕累托不约而同地阐述道,当贸易双方交换商品的时候,如果能够成交,那
么就能分享与自身讨价还价能力相匹配的所有可以得到的利益(这就是已经在前
文中提到的“帕累托改进”)。埃奇沃思还拿出理由说明即使有无数交易者,那么
均衡点也会是唯一的。 [11]
20世纪30年代一个更具包容性的思想——“福利经济学”被提出。它证实在市
场交易中达到“效率”所要具备的条件,即所有商品都能卖出去。简言之,这个条
件证明了一个更大范围的均衡性:当两种投入(即劳动力和机器)结合到生产中
的时候,所有生产者都可以得到同样产出,即产出值唯一。当价格下跌时,消费
者买得更多;当成本上升时,生产者就会提高所售产品的价格,需求和供给会收
敛在一个均衡点。换句话说,在下一次购买或者销售中,采用的“边际价格”,对
所有销售者和购买者都是一样的(就像开篇所举的两个交易者的例子),这样就
会满足效率需求,从而使所有产品都能销售出去。这种边际价格准则有时被看作
经济学的第三个核心理论。而这些限制性的一致性假设与目前所出现的任何经济
实践都是不相符的。事实上,经济学理论对于供给者之间是如何竞争的这一问
题,阐述得都不是很清晰(尤其对于没有价格差异的产品而言)。 [12]
真实世界
中并不存在这样的理想状态,所以经济学家的研究必须对其进行假想。
1954年,肯尼斯·阿罗、吉拉德·德布鲁和莱昂内尔·麦肯齐(Lionel
Mckenzie)分别宣称由瓦尔拉斯(还有埃奇沃思、帕累托和其他经济学家提到
的)所提出的单一均衡点是可以通过数学办法求得的。“一般均衡”[general
equilibrium,可简称为“阿罗-德布鲁均衡”]存在的证据被奉为经济学的神明之物,它揭示了市场魔力的秘密。 [13]
但是需要十分苛刻的条件,即没有任何一个交易
者能够影响市场价格(完全竞争),一般均衡才能真正发挥作用。最重要的是,要存在完全市场,也就是每一个消费者和生产者在任何时间及任何天气情况下
(无论是雨天还是晴天)都知道全部商品的全部价格,而且所有的商品(无论是
现货还是存货)都能全部实现交易。没有规模经济效应,在工厂中,单个工人尽
可能多地进行生产。一般均衡情况不考虑政府、货币、财政、垄断、合作、期望
以及随时间而出现的各种变化,也不涉及失业、分配和不平等。一般均衡也不讨
论如何实现这种均衡状态或者接下来会发生什么。这种假设虽然不符合任何客观
现实。这一模型告诉我们这样一种均衡在数学分析上不是不可能(它是“存在
的”),并且与可利用资源的充分使用具有一致性(“帕累托效率”)。但是这样的
平衡在数学意义上是否存在(稳定性属性),到目前为止仍然是一个疑问。 [14]
阿罗的合作者弗兰克·哈恩(Frank Hahn)认为完全市场假设完全是虚构的,阿罗
补充说:“一个这样的系统不可能存在。” [15]
哈恩又前进了一步,他认为一般均
衡的存在条件是极其苛刻的,因而一般均衡点也经常用来反驳“看不见的手”这一
说法,因为它们不存在。 [16]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认为完全信息和完全市场状态
始终不能实现(二者都不可能),所以均衡就不可能处于帕累托最优状态。 [17]
一个模型飞机在飞行中不断地在引力和浮力之间找平衡。当模型坠落在地的
时候,它获得了更稳定的均衡。类似的,在经济学中,均衡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
题。它看上去跟事实经验相符,特别是对那些境况相对富裕的人更是如此。桌上
有食物,银行里有金钱,商店里也是琳琅满目,汽车停在车道上。一个学期接着
一个学期,然后进入暑假,还有海外会议,事情看上去不断变好。但是实际上,在其他地方,还存在焦虑、失业、债务、疾病、离婚、长时间无趣工作、痛苦、歧视、精神错乱、监狱、战争和死亡。而市场如果需要所有刺激因素来激发那些
神秘力量,那我们就不能去阻止这些事情发生。如果你不喜欢它,你可以选择主
动远离它。那些内战中想要脱离贫困和不安全境遇的无产者,对均衡概念是没有
兴趣的。
在经济建模上,自利和均衡是优先考虑的因素,而他们把实际需要建立模型
的问题当作前提条件。二者都不是事实发生的。埃奇沃思和帕累托指出,两个自
利的当事人进行交换的时候将不会发生任何浪费,这是对潜在市场效率具有启蒙
意义的分析。 [18]
但是在接下来的几十年中,自利和均衡这两个优先考虑因素提
出了自身对经济模型精确的需求,好像它们本身自带了一些可贵品质一样。就像
苏联的指令性经济那样,新古典经济模型也体现了设计者的梦想和价值。在模型
中,自利是一个优点,像模型假定的那样,对自私实现了自证。在新古典模型
中,财产所有者可以实现自我满足而不必考虑那些拥有较少资源的人。如果经济
学家可以将模型展示(或制造)出来、用以与现实进行匹配,就已经很好了。如
果模型完全是正确的,那么社会不就是多余的了么。
模型如何发挥作用
经济模型通过类比,从而拓展到真实世界中。芝加哥模型的建立者罗伯特·卢
卡斯认为,模型构建的目的是从我们对一种情况的已知出发进行类比,进而分析
我们希望知道的另外一种极其不同的情况。 [19]
真实 世界将融入模型所示范的
完美标准中。但是模型与现实相比还是相当简化的。在某一必要方面,X就
像Y一样。它以两种方式之一来工作:要么其他条件不变(所有因素保持相
等),要么进行必要的更改。它不是一个现实中的模型,而是对它的抽象。在现
实中,X从来不等于Y,所以对于现实没有吸引力。没有什么观察和 测量能够表
明模型与现实的类比是错误的。卢卡斯写道,某一个人认为有说服力的类比,他
的邻居可能并不认同, [20]
这意味着没有什么客观的选择标准。
在经济论述中,一个模型仅需要证明其具有内部一致性。这个主题重现在卢
卡斯模型中,例如:
一个“理论”不是关于实际经济行为假设的一个集合,而是为了建立平
行或者类比系统的一套精确假设——一个机械的、模仿的经济。从这个观点
来看,一个“好的”模型不一定比一个糟糕的模型更“真实”,但是能够更
好地模仿现实。当然,通过“更好地模仿”所表现出来的东西将由一个人希
望回答的特定问题决定。 [21]
换句话说,模型不会像现实一样工作,但是可以模仿一些特定方面或产出。
这些听上去貌似十分可信,但是值得思考的是,既然在这样一个简单的维度上起
了作用(实际上经常不是这样),那又怎么可能在一个实际的有所发展的具有复
杂内容的历史经济中得到验证呢?
类比也是诗人的写作手法,就像诗歌中的隐喻一样,模型会引起美丽的联
想,虽然并不真实。 [22]
同样,经济模型通常跟直觉相反,但导致了认知的极度
震撼。把经济模型看成飞机模型就是一种隐喻。然而,经济模型远比机械模型复
杂得多。当参数变化之后,某些情况就可能出现(有某种特定的概率)。但是经
济模型并不能展示出遗漏某种因素会带来的后果,也不能说明有哪些因素被遗漏
了。这样的模型所得出的政策工具也几乎不可依赖。 [23]
相反,如果它是一门完
善的科学,即使在表述上多么具有学术性,也可以有力地支持和解释社会与经济
所赖以存在的技术(交通、通信、能源和健康)在日常生活中产生的必然影响。
模型要构建在合理的基础上。模型并不要求实验上的有效性,但实际上却应
该如此。数学家和博弈论学家约翰·冯·诺依曼(John von Neumann)在1955年写
道,模型可以独立存在,但是仅可以通过观察和经验有效性来证明其正确性。
科学家不解释,甚至几乎从不解释模型,他们的主要工作就是构建模
型。数学构想就是通过模型来表达,附加一些特定的语言表述,来描述观察
到的现象。这样一种数学构想的正确性是纯粹而精确的,从而让人们期待它
能起作用。 [24]
好的经济模型是反直觉的,并且要具备极强的说服力。英国经济学家大卫·李
嘉图(David Ricardo,1776—1823年)为模型构建提供了一个不朽的模板。他的
比较优势理论假设存在两个国家,每个国家生产两种产品,在这种情况下,即使
一个国家生产每种商品都是最便宜的,在两个国家进行贸易也是互利的。这一观
点发表于1817年,在今天的教材中依然存在,它奠定了自由贸易政策的基础。这
样有说服力的模型是不容易构建的。做这样一种反直觉的假设,并将这些假设融
入模型中而得出有意义的结论,非常需要天赋。这一点就足以成为有潜力的诺贝
尔经济学奖候选人进入候选池的屏障。外部有效性的现实检验,是最后也是最苛
刻的要求,还经常被遗漏。将模型与观察到的现实进行匹配的困难还有一个,那
就是没有现实能够完全符合模型。完全竞争这种只存在于想象中的模型,从来不
能被观察到,所以这一模型也就谈不上失败。这种不能匹配完全的现实情况曾经
被称为“涅槃谬误”。 [25]
但是对于市场自由主义者而言,“涅槃经济学”使任何真
实经济看上去都很糟糕,特别是对战后若干年中那些高税率的社会民主主义国家
所达成的共识。
李嘉图恶习
新飞机模型往往在风道中被测试:计算问题本身是不可依赖的,必须亲自试
验才行。从风道发展成一个实际可以工作的航线之间,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但
是经济模型很少因为实验而被拒绝。再以李嘉图为例,他是一个英雄形象的缩
影。除了比较优势理论之外,他还设计了其他令人信服的模型,这些模型表明,从长期来看,劳动工资会下降至仅够维持生活水平的状态,此外(单独在其他模
型中提出的),稳定的价格需要有货币黄金储备才能够实现。考虑这些模型的基
础,结论是不可避免的。这些模型运用了维多利亚时代的世界观,但是历史经验
将其抛在身后,今天这些观点不再正确。李嘉图的战略被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称为“李嘉图恶习”。
李嘉图的兴趣是要获得一个直接而且具有实际意义的清晰结论。为了实
现这一点,他将整个系统切割成若干部分,然后又尽可能地将其捆绑成大的
部分,最后将其冷藏——这样许多尽可能多的问题就成为“固定的”和“既
定的”。然后他将一个简单假设堆砌在另一个简单假设的基础之上,直到通
过这些假设将每个问题都妥善地安排好。他建立了简单的单向关系,以致到
最后他所期待的结果出现同义反复。例如,一个著名的李嘉图理论就是利润
由小麦的价格决定。在他的隐性假设下,这不仅是真实的而且是不容置疑
的,事实上不论问题大小,李嘉图的逻辑都是如此。利润不可能由其他因素
决定,因为其他因素都已经“既定”了,即固定不变。它是如此完美的理
论,以致从来没有人反驳或提出异议。这种将特定结论应用于解决实际问题
的习惯,我们应该称其为“李嘉图恶习”。 [26]
罗伯特·卢卡斯跟李嘉图一样善于运用模型。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他
是新自由主义构建模型领域的领军人物。他对于如何构建模型及模型能起什么作
用非常清楚。对卢卡斯而言,经济学仅是类似于机器构建的学科。“在经济思想上
的进步意味着构建越来越完美的抽象模拟模型并不是对于世界的更好的可表达性
的观察。” [27]
模型在计算机程序中得以精确体现。“我们的任务就是要编写
FORTRAN(公式翻译器)程序,这种程序把特殊的经济政策规则看成‘输入’,随
后以统计结果形成‘产出’,这些统计结果以时间序列描述我们关心的经济运行特
征,而按照我们的预期,这些经济运行特征是由这些政策产生的。” [28]
我们普遍认为,1945年之后出现的高增长、社会保险充分和巨大消费的经济
黄金时期应该归功于凯恩斯政策的实行,该政策允许政府来管理私人和公共需求
从而确保充分就业和较低的通货膨胀。 [29]
卢卡斯的项目,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是新自由主义的芝加哥学院及其分支学院发起的项目之一,它认为凯恩斯政策干
预是无效甚至是徒劳的。其他的研究项目有米尔顿·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它提倡
以一个不变的速度来提高货币供给量从而匹配真实GDP的期望增长率,进而获得
价格稳定。这是不可能起作用的,甚至会被认为是错误的。 [30]
在其他学说中,同负盛名的科斯定理(芝加哥学派喜欢这么说)认为资产的
初始分配并不重要,因为(在一个充满摩擦和冲突的世界中)市场交换会将其转
换成巨大的生产力。相反,罗纳德·科斯自己却希望经济摩擦会阻止这种情况。
[31]
乔治·斯蒂格勒的“管制经济学”认为管制对于有管制的行业是最有效的,对公
共行业无效;相关的“公共选择理论”(詹姆斯·布坎南及其他人提出)假定公务人
员仅受自我利益的驱使。 [32]
1995年,这些研究成果均被授予诺贝尔经济学奖。
爱德华·普雷斯科特、芬恩·基德兰德和托马斯·萨金特都曾与卢卡斯一起工作,后
来也都获得了诺贝尔奖。尤金·法玛在2013年因金融有效市场学说而获得诺贝尔
奖。 [33]
还没有获奖的是罗伯特·巴罗(Robert Barro),他提出了“李嘉图等价定
理”,这一模型源于李嘉图的思想。它认为用于增加需求的政府支出,会因为谨慎
的消费者在预期未来税收的情况下减少支出的行为而被抵销。政策重点在于政府
不会带来任何不同(即政策无效性),这意味着社会民主主义和凯恩斯管理政策
会完全无效。发展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阿尔伯特·赫希曼(Albert Hirschman)已
经提出,自法国大革命以来,改革的无效已经成为政治保守派的三个持久的比喻
之一,这就将芝加哥学派也置于政治保守派这一血统之中了。 [34]
理性预期
在这些学说中,从经济学家引用的情况来看,理性预期宏观经济学是最不歪
曲事实的,是最以经验为主的,到目前为止也是最成功的。这一学说在宏观经济
学领域有持续的影响力,在意识形态和方法论研究领域也被芝加哥市场学派的奠
基人和自由思想的“新凯恩斯学者”广泛应用。这是一个模型化方法:假设个体市
场参与者基于所有可以获得的公共信息形成对未来价格水平的预期。“形成他们的
预期”是指在分析可获得的信息时,公共成员被认为正在使用经济学家自己的统计
模型,而无论这些模型在技术上是多么难以实现。这使他们至少能够在平均水平
上对未来价格进行正确的预期。然后他们的利己选择从总体上决定经济进程
(即“宏观经济学”)。这一学说是一次分析上的巨大成就,被认为困难到足以使
其获得好几次诺贝尔奖。但是即使在它已经被理解和形成之前,它的应用也不是
每个人都可以胜任的。
现在考虑一个类似的系统:安提凯希拉装置(Antikythera mechanism)是一
个神秘的机械设计,它的残骸于1901年在地中海上的一艘古船残骸中被发现。在
对它进行了一个多世纪的研究之后,它被破译并重新组装成一个复杂的钟表装
置,有很多齿轮,能够成功预测月食及五大行星的星空位置。 [35]
这个模拟计算
装置,比19世纪之前的任何装置都要复杂,很显然是在公元前2世纪完成的,然
而其设计可以追溯到公元前3世纪位于锡拉丘兹的阿基米德。
经济学家与安提凯希拉装置的构造者共用同一个假设,即经济有一个类似于
在天体之间存在的潜在规律。在发表诺贝尔获奖演说时,莫里斯·阿莱斯这样说
道:
首先,任何科学存在的前提是要有规则存在的,这些规则可以被分析和
预测。在天体技术的研究上尤其如此。对于许多经济现象而言,这样的道理
同样适用。实际上,对于经济现象的全盘分析说明:适用于实体科学的那些
显而易见的规则,同样存在于经济现象之中。这就是为什么经济学也是一门
科学,以及为什么适用于实体科学的那些普遍规则和方法也同样适用于这门
科学。 [36]
但是跟安提凯希拉装置不同的是,经济学家的机器不是实体的。它是一种想
象中的构造,从来不会沿着路面翻滚,也不会在跑道上着陆,而且不会预测月
食,即使失败也不容易被发现。这种机器只存在于想象之中,但是对不同的学者
而言是如此不同。在理性预期理论中,经济学家的机器也出现在经济中的每个个
体的头脑之中。用托马斯·萨金特(理性预期学派的发起人之一)的话说就
是:“在模型中的所有当事人,计量经济学家和上帝都共同分享同一个模型。”
[37]
上帝和其他人所做的假设是当前价格紧紧围绕着金融及其他资产的真正价值
而波动。资产价格是对未来现金流入的以现值表现的索偿权,所以真实的价值意
味着这些未来收入及经济的未来进程都是事先决定的,也就是可知的,这样就没
有不确定性(有一些说法体现了不确定性,但是这些表达缺乏“理性”)。每个个
体都掌握所有的数据,都能使用最好的经济模型。这样一来,资产价格就是“正确
的”,市场价格的均衡点就代表了资源的最佳分配;换句话说,它是合理的。任何
价格偏离都是随机的,错误会互相抵消。这是“看不见的手”作用下的完美结果。
做出这些假设的一个理由就是要基于“微观基础”,即个人的逐利性,来将经
济理解为一个整体(宏观经济学)。这种要求激发了方法论的个体论研究,这一
学说认为逐利的个体是经济的唯一推动者。更有帮助的是,这一学说使经济学家
可以把从个人选择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非常完善的微观经济学用于分析经济整体。
然而这种理由也是有疑问的。首先,所谓的微观基础是不可验证的,是我们并不
确定了解的,而仅仅是我们深信而已。行为经济学认为真实的个体会对逐利性规
则出现系统性(但并不是一致性)的偏离,但是这一点被忽略了。即使一个人将
个体选择作为基础性的,但是模型实际上并不是简单累加个体选择,更不要说驱
使个体做出这些行为的预期了。这种研究是很困难的,因为人们在偏好上是如此
不同,没有人会确切知道其他人在想什么。20世纪70年代的一个理论结果表明,通过这种加总而得到唯一的一般均衡点是不可能的,也就是“一切皆有可能定
理”。 [38]
所以“微观基础”方法就相当于仅仅假设(或主张)所有的市场参与者
把自己看成具备了相同的资产和偏好禀赋的单独个体而进行活动,他们被看成典
型的代理人,然后用微观经济学方法被模型化。但是如果他们在各个方面都相
同,那么他们之间为什么还要进行贸易呢?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远离实际情
况。
微观基础在科学上被认为极其严密,所以在方法上是具备约束力的。但是规
则是武断的:为什么减少只是对个体,而不是对他们的心理、生物、化学和物理
学?为什么将总和归功于个体选择?为什么不选择其他方法?甚至在微观经济学
理论中,市场都是由社会规则和传统统治的,而且依赖于语言和计算方法这样的
社会媒体存在。经历了好几个时代后,微观基础的规则已经渐渐消亡,从未被任
何接近于严格的事实所证实。 [39]
只要从个人选择到宏观经济的真实加总不可
行, [40]
它就不能被看成是基础的需求。鼓吹(有时候甚至是锁定)其他变通做
法绝不仅仅是一种口号。但是卢卡斯模型要起作用的话,这就是非常必要的一种
办法。
对微观基础也可以进行不同的分析,即可以用研究个人行为的经济学方法对
宏观经济问题进行分析。这就是微观基础的要求条件被真正理解的原因。这相当
于将目的性和合理性融入经济总量(例如,一个有“代表性的消费者”)的研究之
中,并且假设这一具有想象力的个体的选择在整个时期内能够生产出最好可能的
(均衡)产品。如果世界真是如此,那么这将是一个研究经济总量的好方法。
[41]
把事情想象成这样,就是超现实主义的了。那就是一种假装有知识的做法。
[42]
20世纪80年代早期,数学证明显示,一个人以上的理性预期将在内部产生不
一致性,理性个体的不同预期想要汇聚成一个正确预期,每个个体需要知道其他
个体是如何预期的。就像批评家(未来的获奖者)说的那样:理性预期的“猜
想”就像上帝无所不知的“猜想”一样。寻找证据几乎没有任何意义。 [43]
尽管存在这些问题,有两个原因使模型仍然很有吸引力。首先,他们是非常
传统的:他们将经济学非常标准的动机性假设延展开来,而且使宏观经济现实从
下至上的模型化成为可能。保罗·克鲁格曼这样解释:如果仅有一个方法极为合
理,那就会有无穷多的方法是不合理的,你应该如何选择呢? [44]
这不是完全正
确的:这种完美的合理性仅在世界处于稳定状态并且可知的情况下才起作用。一
些假设可以放松,但是人们通过工作所发现的已经存在的未来(遍历性假设),这一假设是不能放松的。 [45]
期望能够被证明是正确的这一假设如果不存在的
话,模型化就会非常困难,而宏观经济学家就是要将观察到的规则简化成一般规
则(对我们自己而言,这实际上是一个正确的程序)。卢卡斯很有名的批评论断
就是,实证的凯恩斯模型(与劳伦斯·克莱因有关)对过去到未来进行了推断,而
没有考虑逐利的参与者按照理性预期做事会有导致颠覆的潜在风险(卢卡斯批
判)。但是没有信息是来自未来的。理性预期以过去和现在的信息为基础。假设
每个人都一定能够使用这些信息就太牵强了,而且这一点已经被反复证明是错误
的(将在下一部分中说明)。卢卡斯批判原则上是正确的(虽然这是卢卡斯批判
的那些模型构建者所期望的)。如果每个人都可以获得充分信息并且可以随意获
取,那么这一现象就必须被重视。但是卢卡斯批判的实证效果已经被发现是很差
甚至是不能成立的,如果人们意识到自己已经严重偏离了理想的话,对此就不会
感到吃惊。 [46]
然而这已经成为宏观经济学的标杆。
理性预期假设为政策提供了合理性。政府做出稳定价格的承诺并不可信。为
了克服这个问题,货币政策被移交给中央银行来制定,中央银行是游离于政治之
外的,其目标是要把通货膨胀限制在一个非常小的范围内(一般是2%)。一旦通
货膨胀有所抬头,中央银行就会在经济运行中采用更高的利率,这样就可以通过
失业来控制工资水平。 [47]
理性预期理论是一种“看不见的手”的理论,它也认为
市场不能被改善。任何政府干预手段都可能被预期到并且被市场参与者抵消。如
果干预是有效的,那么它会导致经济偏离自然和理想的状态,从而发生“扭曲”。
所以干预是无效的,甚至是有害而无益的,但是在通货膨胀目标实现上是一个例
外。这一学说显然与商业利益和富人在价格稳定、纳税更少、更少受到管制方面
的利益是一致的。理性预期是一个很保守的理论:中央银行运用这一理论要求工
资要受到管制,但对房产和股票价格却不这样要求。
我们很容易忘记约瑟夫·斯蒂格利茨说过的话:“‘看不见的手’必须作为一种信
仰,而不是一种科学命题。” [48]
理性预期政策标准(像大多数“看不见的手”的
论述)在已经确认的知识中是找不到的:它们仅反映了理论家的偏好和优先考虑
因素。这些是被看作前提条件的。这种观点与抽象推理并不矛盾,但是与其当局
在政策制定上所宣称的是矛盾的。
它是真实的吗
卢卡斯在20世纪80年代被质疑:“你是跟随真理的吗?”他这样回答:“是的,但是我不知道在我们的经济中真理是指什么。我们正在设计模拟人类的机器人,在我们所能获得的资料上,存在一些实际限制。” [49]
这样脆弱的构造即使在发
明者自己看来都是经受不住检验的。这种看似庄严的知识和永恒稳定的模型被持
续不断地修复,从而遭到了破坏,而这种修复通常也是为了解决该模型与经济现
实之间很差的适应性。卢卡斯摒弃了用货币流通紊乱来驱动经济周期模型的努
力。托马斯·萨金特是理性预期的发起者之一。他的一个学生在萨金特的著作中已
经罗列了“关于理性预期理论兴起的十个故事”。每个模型都是为了解决之前模型
中出现的一些问题。 [50]
这些“故事”不总是彼此吻合的,这反映出这一理论的一些内容的偶然性特
点。萨金特因为推理的严谨而闻名。这种范例中缺乏的是对事实的尊重。而萨金
特对此非常公正。经验检验与理性预期是不一致的,所以经验参数与所谓“校
准”程序中出现的模型是不一致的。在这一模型中所产生的周期与真实世界的参数
是一致的,这些参数是从稳定“深入”的微观经济学偏好(例如工作与闲暇)、技
术变量和已经被卢卡斯否定的极具实证经验特点的宏观经济学中得到的。如果这
些周期可以匹配,不是任何特殊的历史周期,而是真实历史周期的“二阶矩”,也
就是它的一般形态,经常是去趋势化的而且脱离于稳定期间的,那么这就可以被
看作是一种成就。即使这并不容易管理,但是也可以被判断是已经失败的。 [51]
这并不令人吃惊——例如,偏好和技术都是不变的,甚至除了进行假设之外,都
是很容易识别的。萨金特还流露过这样的思想:
校准对于理论能达到什么目标而言,也不是完全值得信赖的,因为如果
你没有充分信任你的模型,而仅仅是使用它,那就意味着你认为你的模型是
部分有误的或是不完全正确的,或者如果你相信其他人的模型和数据比你自
己的更合理。在我的记忆中,鲍勃·卢卡斯(Bob Lucas)和爱德华·普雷斯
科特起初对于理性预期计量经济学都是很热情的。毕竟它唤起了我们自己对
于高标准的追求,我们因为凯恩斯主义者没有做到这一点而进行过批评。但
是在对理性预期模型进行了大概五年的检验之后,我想起鲍勃·卢卡斯和普
雷斯科特都曾经告诉我这些检验导致太多很好的模型被否定。校准的目的在
于忽略你自己模型中的一些概率含义而保持其他的一些概率含义。总之,直
接承认你自己的模型虽然并不正确,但是仍然值得作为一个数量政策分析工
具的载体,而校准的目的,就是起到这样的平衡作用。 [52]
对比而言,当萨金特写经济历史的时候,他在很大程度上省去了对模型的引
用。 [53]
对卢卡斯而言,繁荣、萧条、失业和复苏的周期都完全不构成政策挑战,而
只是在均衡之前的一种摇摆,但是这些对凯恩斯而言就是一个挑战,并且在一定
程度上驱动了社会民主党派的行动。在卢卡斯模型中,政策干预因为个人知识经
济的运行(理性预期)而被击败,并将运用这些知识避免对于自己利益所产生的
负面效应。只有个人能有预期,并且自己对此感兴趣。真实的微观基础解释将从
个人选择中推断而来,但是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并不知道关于实际选择的任何情
况。它在“代理人模型”中起作用,也就是经济作为一个整体被模型化为仅由一个
或者两个个体构成。一旦这些形成了飞跃,就很可能构建一个长期的均衡模型,这是一种“真正的商业周期”,在这种周期中波动起源于外部惊喜(或者“震
动”)。“均衡”由一个简单的代理消费者构成,他从一个单一的代理公司购买并为
这个公司工作。阿罗-德布鲁一般均衡点被期待要提升经济效率,尽管这一理论自
身缺乏现实性。 [54]
阿罗-德布鲁仅适用于存在许多代理人的大的经济体的情
况,这是一种恒定的静态的结果,没有给冲击和摇摆留下任何空间。 [55]
甚至在
转换到一个连续均衡状态时,它仍然需要具备完全的一致性(完全市场)。在只
有两个代理人的情况下,市场几乎不可能达到“一般”均衡。
另外一些跟麻省理工学院、哈佛大学、伯克利加州大学和斯坦福大学的顶级
学术机构有联系的理性预期经济学家(相对于芝加哥和明尼苏达大学的“淡水”派
而言,他们被称为“盐水”经济学家)通过向模型中注入冲突和干扰因素对模型进
行了修改。这些“新凯恩斯”模型越来越精致。终于在2000年左右,新古典宏观经
济学和新凯恩斯主义的各个分支结合在一起,形成了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其
目的是将更多的现实融入内部临时均衡模型。这些模型超出了校准范畴而应用了
更多的传统统计推理方法,并且将参数从真实数据中分离出来(“估计值”)。得
到的模型运用于越来越多的实证数据检验,这种真实数据的使用确实在提升预测
的准确性上起到了一些作用。 [56]
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开始统治宏观经济学研
究,各国中央银行开始运用和求助于这个模型。 [57]
吸引力在于理性和均衡的传
统基础,但是这些非现实性的基础限制了它们的可依赖性和精确性。这些理论的
大部分也意味着市场相比于政策是被优先考虑的一个因素。他们预测的质量至多
可以跟统计外推技术的结果相提并论,统计外推技术根本不做任何经济理论假
设,实际上这两种方法现在经常被结合使用。 [58]
这些模型经过30年的完善,依
然在实证环节上表现得很糟糕。实干家对此深有体会。尽管中央银行广泛部署,但他们仍然不是核心决策框架的一部分,也没有为“黄金时间”做好充分准备。
[59]
他们没有预测到2008年的金融危机,其重要原因在于他们一向不考虑金融部
门。现代宏观经济学运用先验世界观点来比对数据,从而证明一致性。 [60]
尽管
陷入了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的大规模应用,但是中央银行没有抛弃凯恩斯主义
起源的巨大统计模型,它众所周知的缺点唤起了卢卡斯革命。对比而言,如果私
人的钱处于危险之中,那么商业几乎绝对依赖统计模型所做的描述性预测,并且
完全不会使用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除非有时候会尽力模仿中央银行的决策。
[61]
理性预期模型的指数可以追溯到米尔顿·弗里德曼的方法论的论述中,其中说
道,只要模型做出了好的预期,分析所依赖的现实就不重要。 [62]
然而,好的预
测不能被看成理性预期。它的实证数据很少,为了把它代入有实证证据的任何平
行排列都必须进行复杂的扭曲操作。与安提凯希拉所做的比较就说这么多。 [63]
古代希腊的机械装置是基于错误的地心说宇宙论的(这对米尔顿·弗里德曼而言不
是一个问题),但是相对于任务的重要性和前提条件的非现实性而言,它做出了
相当多的预测。理性预期模型与安提凯希拉装置一样都具备非现实主义的特性,但不像古希腊的机械装置那样,理性预期模型所做的预测是非常糟糕的。
新古典宏观经济学与社会民主
假定有两个积极的代理人、近乎完美的预测,以及不朽的生命,那么按照新
古典经济学的说法,就不必存在社会保险。它是一种没有政府、金钱和社会的经
济体。没有公众,就没有公共产品的概念。也许这就是它如此流行的原因。在
1957年米尔顿·弗里德曼提出的“永久收入”假设中提到了消费者通过借入和储蓄来
调整收入的波动,在这一假设中,就部分运用了上述假设。因为生命无限,所以
不存在退休问题。两年之前,凯恩斯主义阵营的弗兰科·莫迪利安尼提出的更现实
的生命周期理论还认为至少退休问题是会发生的。 [64]
同时,进行了一些某种程
度不同的假设(工人及退休的人的代际交叠),保罗·萨缪尔森做出了一个模型,这一模型认为社会保险是必要的,至少是有用的。这三个模型都从假设中获取结
论(很有智慧),并且强调在社会民主主义和市场自由化之间的争论(仍然发生
着)中模型的容忍度。这些研究成果都被授予了诺贝尔经济学奖。
卢卡斯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满足了反直觉意识、理论连贯性、可理解的比
喻、有说服力的类比、数学技术、程序化的事实和政策及政治上的正确性等建模
条件。1981年,卢卡斯得意地说:“总体来看,我认为一个声称理解了飞行原理的
人是很有可能造出可以飞行的机器的,理解商业循环就意味着创造商业循环的能
力,这两个问题几乎是相同的。” [65]
那些飞机也是如此。然而要注意的是不能
仅仅声称控制了商业周期(这不一定是必然的),而是要构建一个可信服的实物
模型。
到目前为止,与现实发生冲突是一种收获。在所有条件满足之后,最后一个
条件,实证有效性的检验问题就可能是一件尴尬的事情。在标准的计量经济学
中,一个偶然的模型力图包括所有相关的变量,估计程序使用现实生活中的原始
数据来发现其重要性及重要的程度。这个程序必须是描述性的。如果匹配结果非
常糟糕,那么模型将被拒绝。它还会遇到严重的问题(见第二章)。校准的新古
典宏观经济学程序不必满足这样一个检验:它预先选择匹配数据,估计结果仍然
很糟糕。
弗兰克·哈恩是一位受人尊敬的建模家,他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这样谈及新古
典宏观经济学:
我一直认为竞争一般均衡分析是像一个飞机工程师能造出来的实体模型
一样。最近这些年我的兴趣很大程度上在于发现许多经济学家不把实体模型
当作一架真正可以飞行的飞机,政治家、银行家和所有的时事评论者都来争
夺座位。这一次全世界的理论家都意识到这样的实体模型是不可能飞起来
的,因为它忽略了真实世界中很重要的方面,这种认知将促使一些激进的设
计产生。而且,无论在哪个阶段,实体模型都是完整的。 [66]
卢卡斯并没有被吓住。他在1988年芝加哥大学毕业大会上致辞的时候,以一
种宗教权威的口吻进行了演讲。从一个想象的问题开始,他对毕业生这样说道:
我们需要将我们自己从历史经验中解放出来,从而找到我们的社会可以
比过去运转得更好的方法……我们没发现想象和思想的王国其实是一种对实
际和现实的替代,或者说是一种退而求其次的做法。相反,它是我们所能找
到的认真思考现实世界的唯一道路。 [67]
这种假想的现实原则一直被坚持作为一种政策指导。2003年,卢卡斯又一次
将主席致辞递交美国经济学会。它是一次结束历史的演说,或者说更像是宣告宏
观经济学的完结的演说:“遏制萧条的核心问题已经解决。” [68]
这是他研究方法
的原理,即衰退并不重要:商业周期的上升和下降是宏观经济调整的最好路径。
所以寻求稳定性不会有什么实质性收获,但是更具竞争力的市场(特别是劳动力
市场)将能极大地提升消费。
仅仅五年之后,经济危机发生了。卢卡斯之前预测经济会永久呈现3%的增
长。 [69]
他的信心来自哪里呢?它是基于几个模型的,所有的模型都是“一个良
好的增长模型的变形,在这个模型中消费者(可能是一个无限存在的动态生命
体,也可能是几代人的更迭)会在长期中将消费效用和闲暇最大化,公司会最大
化利润,市场将持续出清”。 [70]
换句话说,是一个良好的、消费者的、公司的
模型。这样的模型很难构建,而且不容易理解。但它不可能真正起作用——它们
仅仅是模型。在李嘉图飞跃中,卢卡斯抛弃了这些不实用的观点。这个政策天生
是无效的(这是他自己的核心信条)在这里被遗忘了。
对神坛上的卢卡斯而言,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模型为再分配这一机制激进上升
的市场自由化进程提供了合理的解释:废除了对资本的征税,对于收入征收统一
税,将福利国家私有化。将资本收入税收削减为零(用其他税收来覆盖支出)是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模型获得的一个喜人结果,这一变革为
美国和英国在接下来的十年中从资本获得退税收入提供了正当理由(这一理论曾
经受到挑战)。 [71]
来自“滴漏效应”的经济增长将给消费带来7.5%~15%的增
长。在另外一个例子中,财政上的更高税收只需要用更短的工作时间来负担。对
劳动和消费(工作中更长的工时)采用较低的美国式税率的那些法国家庭而
言,“稳态福利增益”相当于消费增长大约20%的水平。这些都来自单一个体模型
中闲暇和工作之间权衡的不稳定结果。 [72]
用这些额外收入,法国人就能购买政府当前提供的物品。他说:“可以考虑一
下小学教育或者日托,这些目前都是由‘扭曲税收’进行财政支持的。” [73]
倾听
者都是默认有效市场不是一个假设而是一个既定的事实,虽然这样的市场并不存
在。另一个假设是法国工人就他们上交的税收而言得不到任何回报,因此他们不
能在私人市场的柜台上进行购买。与卢卡斯观点相反的是,有人可以指出由法国
人的税收提供的社会保险以及自由教育比市场消费增长20%更有意义(甚至从金
融术语来看),对于那些低收入人群的意义就更大了。
美国市场健康服务相较于欧洲社会民主党提供的这些服务来说,前者的价格
是后者的两倍,而且有效性更差。欧洲退休金则慷慨得多。 [74]
在华丽的表达背
后,卢卡斯忘记了这样一个事实,即法国人也必须工作更长时间,才能换取政府
已经提供的物品。此后,他又表达了对于下降分布的厌恶:“在已经出现的对健康
经济学发展有害的趋势中,最引人注意而且我认为最有害的趋势就是把注意力放
在分配上面。” [75]
增长分布的非相关性即使应用卢卡斯自己的方法,对于美国
的情况而言也已经表明是错误的,那么对于一个之前30年大多数人都未能从经济
增长中获益的国家来说,情况就更不令人吃惊了。 [76]
再次重申我们的观
点,“典型代理人”模型给政策提供了一个非常差的保证。
它究竟是什么
新古典宏观经济学与人文科学中的后现代主义运动在历史上同时发生。 [77]
后现代主义的具体时间不容易确定。如果它有核心思想,那么它的核心思想就是
拒绝把观察和测量、原因和效应的分析作为有效性的标准。对它与经济学的联
系,以前就有过研究。它一直致力于博弈论、非对称信息、行为及女权主义经济
学领域的不可预测论的逆势问题研究。 [78]
从后现代主义的观点来看,经济学的
错误在于理性和均衡的“现代主义的元叙事”问题,以及以一种符合逻辑的科学解
释的欧洲启蒙运动的信仰问题。在一系列的学术和娱乐书籍中,经济学家和历史
学家戴尔得丽·麦克洛斯基(Deirdre McCloskey)将经典的文学传统用于她的经济
演讲,她将经济演讲看作一种不可预测但充满新思想的对话,而且是对有说服力
的研究的一种无尽追求。这一点从她出色的口才中可以看出来。 [79]
说服力作为经济观点讨论的目的是符合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家的想法的。但是
用克里斯托弗·西姆斯的话来说,“面对骗子的时候我们有心软的这种风险”。 [80]
没有事实,说服力从何而来?我们又在讨论什么?探求说服力大概就是想要证明
自己是正确的一种努力。事实对于推理、学习、合作和签约来说都是非常必要
的。事实不会每时每刻都出现,但是当它缺席的时候,我们所知道的一切就都是
一种可以唤起我们觉醒的认知。
与后现代主义的相似不是新古典学说的边缘问题,而恰恰是核心问题。像后
现代主义一样,新古典宏观经济学不再让事实进入个人的幻想,对后现代主义在
高低文化水平之间的平衡也是认可的。在对社会和普通商品不给予任何空间这一
点上,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比后现代主义走得更远。像后现代主义一样,新古典宏
观经济学对于集体愿望也保持中立态度,而集体愿望促使社会民主党派认识到有
其他人的存在,而且其他人有特殊的需求,并且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义务是可以互
相起作用的。
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是反现实主义的:“社会理论不像热力学,它被谴责一直处
于不可检验状态,而且一直局限于思想领域。” [81]
脱离了现实主义的束缚使卢
卡斯能够迷惑他的读者。一方面,它认为失业是一种自愿选择,这是一种思想实
验(在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学派中没有其他的实验)。 [82]
另一方面,还有少数人
表面上看起来是认同要信赖社会保险的。 [83]
总而言之,他自己的猜想就是“效
率要求对失业的人进行补贴,因此又会提升平均失业水平”(他在芬兰这样一个北
欧福利国家做的演讲)。 [84]
读者抓破脑袋来思考和解决这些冲突,并且渗透这
些深奥的模型,这些模型对于激烈的社会变革是持赞同态度的,模型当中的大多
数思想(表面上如此)都是符合富人利益的。
但是我们也可以持怀疑态度。模型的先决条件从来未被满足,那就没有理由
认为其他事情会保持均等(其他条件不变),或者要做任何必要的改变(必要的
变更)。因果和推理就会被搁置起来。 [85]
这会带来令人振奋的局面,但是当就
政策问题发声的时候,卢卡斯恰恰是滥用职权的人。两个“理性代理人”经济模型
不是建立在微观经济基础之上的。而且在模型中,缺乏严格的阿罗-德布鲁条件
(在现实世界中是不可能被满足的)的竞争经济并不被认为比其他经济更有效
率,甚至在帕累托均衡的有限意义上也是如此。 [86]
但是回头讨论是无用的,作为一门学说,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在普遍意义上来
讲更像经济学,与批评家的相处并不融洽,甚至在学派内部都存在不融洽的情
况。 [87]
卢卡斯对批评家一直不是很礼貌,他把对手凯恩斯学派的学者描述成绝
望的“头盖骨卡嗒卡嗒”。 [88]
一般来说,经济学家会被其他学派(和非正统的实
践者)看成是居高临下的而且疏远的。这一点在引用方式上已经得到确认了——
对比其他学派,经济学家很少从外界引用,当他们做这样的引用时,大多数人利
用的都是像财政、统计学和商业领域的知识,而且所合作的人也都是同意他们观
点的人。 [89]
这就不可能形成坚定的不同意见。这意味着外界的人不可能有资格
来判断,甚至当他们自己的利益处于紧要关头的时候也是如此(经常是正确的,但是在标准的经济假设上是存在争议的)。然而它可能使人对于看上去未得到保
证的主张感到不满,这就可能陷于一种一般的错误,即把行为归因于处理手段而
不是环境。 [90]
在这样的情况下,冷淡不是一种集体特性的缺点,而更可能是为
了引起对学说世界观的一种关注。经济学说是理性主义的。他们的逻辑推理来源
于可以自证合理性的事物,所以他们是抵制证据的,因此(对经济学家而言)他
们违背常识或者认为与现实不一致是无关紧要的。 [91]
如果基础条件不可以共
享,那么就没有意义开展讨论。
不尊重现实和推理也是各个时代中右翼倾向的共同特点。它会导致将卢卡斯
的表现(还包括用于质疑社会民主主义的理性预期和典型代理人战略)看成一
种“agnotology”的实践——agnotology最初是为那些否定烟草和癌症之间关系的人
杜撰出来的术语,这些人还否认全球变暖、否定药物试验管制和否定2008年金融
危机之后采取的“一般商业模式”。 [92]
它代表了看上去非常诚实的理论观点,但
是缺乏令人信服的证据,而且意图散布混乱和怀疑。 [93]
如果这些意图不能接近
真实情况,而是寻求一种原因,那么这种无条理就是有意义的。像布什进军伊拉
克,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家看起来也在“制造他们自己的现实”。 [94]
这在短时间可
能是有效的。鉴于我们对芝加哥学派以外的很多学派的巨大专业认可度,甚至在
政治思想上彼此互为对手的人也如此认可,那我们其实可以承认我们自己的混乱
和游移不定。领军的经济学家也有跟我们一样的困惑。 [95]
对于理论化这一问题是不可能有任何反对意见的。如果学者希望探讨不朽
的、一致的、能够预知而且是只有一个个体存在的经济情况的数学含义的话,那
为什么不呢?约翰·希克斯曾经这样写道:
太多的经济理论之所以被研究,其实除了学术上的吸引力之外,并没有
更好的理由:它只是一个好的游戏而已。我们没有理由对此感到羞愧,因为
对于数学的许多分支而言也同样如此。 [96]
诚然,它可以繁荣很久,但这样的模型对于反对集体行动而言并不能提供任
何保证,或者我们可以说(其自身)对于任何其他政策这样的模型都是如此。
经济学的内部纠纷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并不认同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实际上(在第五章我们可
以看到),相反的情况更接近事实。诺贝尔奖评定委员会也有所犹豫。在诺贝尔
经济学奖得主中,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学派的经济学家已经被明确地否定了,否定
这一学派的经济学家有肯尼斯·阿罗、詹姆斯·托宾、弗兰科·莫迪利安尼、罗伯特·
索洛、弗农·史密斯(在他的诺贝尔获奖演说中)、埃德蒙·费尔普斯、保罗·克鲁
格曼、克里斯托弗·西姆斯,当然还可能有其他人。 [97]
索洛曾经写道:“宏观社
会已经对其自身进行了夸张的欺诈,对其学生也是如此。” [98]
在关于2008年金
融危机的一次国会听证会上,这位凯恩斯主义的经济学家对于新古典宏观经济学
给予了粗鲁的回应:
他们想当然地认为整个经济可以被看成是一个单一的、一致的个体或者
一个朝代,他能够执行一套按照理性设计好的长期的计划,只是偶尔被预期
之外的震动扰乱一下,但是可以以一种理性的、一致的办法调整自身。我认
为这幅图画是不可能通过嗅诊测试的。这一思想的主角宣称对自己的社会地
位负责,宣称这一理论是建立在我们对于宏观经济行为的了解之上的,但是
实际上我认为这种宣称是虚伪的。 [99]
模型化是不可逃避的,在经济学中模型是一种飞行器。我们在本书第六章也
使用数学模型来描述和解释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著名的理论轨迹。索洛的双重
因素经济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增长模型(资本和劳动)是接近于典型代理人模型
的,虽然它并不假定资本和劳动的总和有其自身隐含的含义。但是模型没有独立
的权威性。为了证明政策的正确性,模型必须考虑一些真实的购买行为。数学
家、物理学家和博学家冯·诺依曼因为说了这样的话而闻名:“当你甚至不知道你
正在讨论什么的时候,再精确都是没有意义的。” [100]
决策制定者就像现在的作者一样,必须凭信任来相信这些专家。他们不是模
型构建者。如何决定听谁的?政策不能单一地依赖模型,它在设计上并不像喷气
式飞机那样精确,它的表现也不容易测量。收集信息、开展研究、写作论文、咨
询机构,同样还有偏见、歧视、忠诚和配偶问题。模型仅是所有混合问题的一部
分而已。最成功的因素能够进入政策制定的考虑之中,成为“初始模型”,这些因
素必须是被深信不疑的,政策制定者认为专家懂得这些问题,虽然并不确定如何
知道及为什么。那些应用政策的人很少能够将模型拆分,或者自己来进行平衡。
有说服力的模型的单一存在有一些证明价值,这是独立于证明之外的。模型是很
难被检验的,并且不确认性被忽略了。所以这就是诺贝尔奖的权威品质的重要性
所在。奖项的魅力和权威的有效性就是我们下一章要谈的内容。
[1] McCloskey,‘Economics Science:A Search through the Hyperspace of As-sumptions’(1991),11.
[2] Morgan,The World in the Model(2012),ch.5.
[3] ‘Neoclassical’:The economics of Adam Smith,David Ricardo and John Stuart Mill(classical
economics,c.1770-1870)reckoned economic value by the cost of
production.Its‘neoclassical’successors(from the 1870s onwards,including W.S.Jevons,Vilfredo Pareto,Alfred Marshall,Paul Samuelson)measured it by willingness to pay.
[4] Robinson,Economic Philosophy(1962),79.On her entitlement to the prize,see 136-137,below.
[5] Boumans,‘Built-in Justification’(1999),93.
[6] In substantive agreement with Syll,On the Use and Misuse of Theories and Models(2015).
[7] Introduction,above,3.
[8] Smith,‘Digression Concerning the Corn Trade’,Wealth of Nations(17761976),IV.5.b 1-9,524
-528.
[9] Offer,‘Self-interest,Sympathy and the Invisible Hand’(2012).
[10] Precursors,Ingrao and Israel,The Invisible Hand(1990),chs.2-3.
[11] Creedy,‘Some Recent Interpretations’(1980);Humphrey,‘Early History of the Box
Diagram’(1996).
[12] Blaug,Economic Theory in Retrospect(1997),570-595.
[13] Historical survey and analysis,Ingrao and Israel,The Invisible Hand(1990).
[14] Rizvi,‘The Sonnenschein-Mantel-Debreu Results’(2006);Fisher,‘The Stability of General
Equilibrium’(2011).
[15] Hahn,‘Reflections on the Invisible Hand’(19821984),121;Arrow,‘Ra-tionality of Self and
Others in an Economic-System’(1986),S393.
[16] Hahn,‘On the Notion of Equilibrium in Economics’(19731984),52.
[17] Stiglitz,Whither Socialism(1994),ch.2.
[18] Humphrey,‘Early History of the Box Diagram’(1996).
[19] Lucas,‘What Economists Do’(1988),5.
[20] Ibid.,5.
[21] Lucas,‘Methods and Problems in Business Cycle Theory’(1980),697.
[22] McCloskey,‘Economic Science:A Search through the Hyperspace of Assump-tions’(1991),13;King,The Microfoundations Delusion(2012),ch.2.
[23] For example,Tovar,‘DSGE Models and Central Banks’(2008),18.
[24] von Neumann,‘Method in the Physical Sciences’(1955),492.
[25] Demsetz,‘Information and Efficiency’(1969),1.
[26] Schumpeter,History of Economic Analysis(1954),472-473.
[27] Lucas,‘Methods and Problems’(1980),700;Lucas,Lectures on Economic Growth(2002),21.
[28] Lucas,‘Methods and Problems’(1980),709;FORTRAN is a formerly per-vasive computer
coding language.
[29] Forder,Macroeconomics and the Phillips Curve Myth(2014),argues that ne-oliberal critics
misrepresented Keynesian policies.
[30] Modigliani,‘The Monetarist Controversy Revisited’(19881997);Mayer,‘The Twilight of the
Monetarist Debate’(1990).
[31] Coase,‘The Institutional Structure of Production’,Nobel Lecture 1991.Nobel Lectures(delivered by
NPWs usually a day or two after the prize ceremony)are cited henceforth with title and year.They are available
at http:www.no-belprize.orgnobel_prizeseconomic-scienceslaureatesindex.html,and are mostly reprinted
in an irregular series of variously edited volumes entitled Eco-nomic Sciences with dates.
[32] McLean,Public Choice(1980);Mueller,Public Choice III(2003).
[33] Fox,The Myth ofthe Rational Market(2009).
[34] Hirschman,Rhetoric of Reaction(1991),74.
[35] Freeth,The Antikythera Mechanism(2008);Freeth et al.,‘Calendars with Olympiad
Display’(2008);Marchant,Decoding the Heavens(2008);Freeth,‘Decoding an Ancient
Computer’(2009).
[36] Allais,‘An Outline of My Main Contributions’,Nobel Lecture 1988,243.
[37] Evans and Honkapohja,‘An Interview with Thomas Sargent’(2005),566.
[38] Kirman,‘Whom and What Does the Representative Individual Represent?’ (1992);Rizvi,‘The
Sonnenschein-Mantel-Debreu Results after Thirty Years’(2006).
[39] Kirman,‘Whom or What Does the Representative Individual Represent?’(1992);Hartley,The
Representative Agent(1997);Kincaid,Individualism and the Unity of Science(1997);Hoover,Methodology of Empirical Macro-economics(2001),ch.3;Duarte,Microfoundations
Considered(2012);Janssen,Microfoundations(2012);King,The Microfoundations
Delusion(2012);Syll,Use and Misuse of Theories and Models(2015),ch.3.
[40] Hoover,The New Classical Microeconomics(1998),224-230,241-244.
[41] Hahn,‘Macroeconomics and General Equilibrium’(2003),206.
[42] Caballero,‘Macroeconomics after the Crisis’(2010),89.
[43] Frydman and Phelps,‘Introduction’(1983),26;Frydman,‘Towards an Un-derstanding of
Market Processes’(1982);Arrow,‘Rationality of Self and Others’(1986),S393.
[44] Macfarquar,‘The Deflationist’(2010).
[45] Davidson,‘Reality and Economic Theory’(1996).
[46] Favero and Hendry,‘Testing the Lucas Critique’(1992);Ericsson and Irons,‘The Lucas Critique
in Practice’(1995);Linde,‘Testing for the Lucas Critique’(2001);Hendry,‘Forecast Failures,Expectations Formation and the Lucas Critique’(2002).
[47] Grimes,‘Four Lectures on Central Banking’(2014),4-37.
[48] Stiglitz,‘The Invisible Hand and Modern Welfare Economics’(1991),35.
[49] Klamer,The New Classical Macroeconomics(1984),49.
[50] Sent,Evolving Rationality of Rational Expectations(1998),1-11.
[51] Watson,‘Measures of Fit for Calibrated Models’(1993);Hoover,‘Facts and
Artifacts’(1995);Hansen and Heckman,‘Empirical Foundations of Calibration’(1996);Carlaw and
Lipsey,‘Does History Matter?’(2012).
[52] Evans and Honkapohja,‘Interview with Thomas Sargent’,568-569.
[53] Sargent and Velde,The Big Problem of Small Change(2002).
[54] Lucas,‘Methods and Problems in Business Cycle Theory’(1980),701.
[55] Hahn,‘General Equilibrium Theory’(19811984),79.
[56] Woodford,Interest and Prices(2003);Smets and Wouters,‘Estimated Dy-namic Stochastic
General Equilibrium’(2003).
[57] Chari,‘Statement of V.V.Chari’(2010),32.
[58] Gürkaynak et al.,‘Do DSGE Forecast More Accurately’(2013).
[59] Tovar,‘DSGE Models and Central Banks’(2008),quotes,2,18;Schorf-heide,‘Estimation
and Evaluation of DSGE Models’(2011).
[60] Marchionatti and Sella,‘Is Neo-Walrasian Macroeconomics a Dead End?’(2015),27.
[61] Bachman,‘What Economic Forecasters Really Do’(1996);Smith,‘The Most Damning Criticism
of DSGE’(2014),including comments by Daniel Bachman;Dou,‘Macroeconomic Models’(2015).
[62] Friedman,‘The Methodology of Positive Economics’(1953).
[63] Ball,‘Intertemporal Substitutions’(1990),706,lists several earlier empirical failures;Pollock
and Suyderhoud,‘An Empirical Window on Rational Expec-tation Formation’(1992);Carter and
Maddock,Rational Expectations(1984),141-143;Lovell,‘Tests of the Rational Expectations
Hypothesis’(1986);Obstfeld and Rogoff,Foundations of International Macroeconomics(1996),625,cited in Frydman and Goldberg(below),28-29;Estrella and Fuhrer,‘Dynamic
Inconsistencies’(2002);Frydman and Goldberg,Beyond Mechanical Markets(2005),ch.5.
[64] Modigliani,‘Life-Cycle,Individual Thrift and the Wealth of Nations’,Nobel Lecture 1985.
[65] Lucas,Studies in Business-Cycle Theory(1981),8.
[66] Hahn,‘Review of Beenstock’(1981),1036.
[67] Lucas,‘What Economists Do’(1988).
[68] Lucas,‘Macroeconomic Priorities’(2003).
[69] Klamer,The New Classical Macroeconomics(1984),52.
[70] Lucas,‘Macroeconomic Priorities’(2003),2.
[71] Straub and Werning,‘Positive Long Run Capital Taxation:Chamley-Judd Revisited’(2014).
[72] Lucas,‘Macroeconomic Priorities’(2003),1-2;‘Dubious’,see Hansen and
Heckman,‘Empirical Foundations of Calibration’(1996),100.
[73] Lucas,‘Macroeconomic Priorities’(2003),1-2.
[74] Offer,‘Economy of Obligation’(2012);Offer,‘A Warrant for Pain’(2012).
[75] Lucas,‘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Past and Future’(2014).
[76] Córdoba and Verdier,‘Lucas vs.Lucas:On Inequality and Growth’(2007).
[77] Rosenau,Post-Modernism and the Social Sciences(1992);Blaug,‘Why IAm Not a
Constructivist’(1994),130.
[78] Heap,‘Post-Modernity and New Conceptions of Rationality’(1993);Cul-lenberg et al.,Postmodernism,Economics and Knowledge(2001);Amariglio and Ruccio,Postmodern Moments in
Modern Economics(2003).
[79] McCloskey,The Rhetoric of Economics(1985);Knowledge and Persuasion in
Economics(1994).
[80] Sims,‘Macroeconomics and Methodology’(1996),110;Athreya,Big Ideas in
Macroeconomics(2015),13-14.
[81] Varoufakis,‘Deconstructing Homo Economicus?’(2012),393.
[82] Lucas,Models of Business Cycles(1987),section V.
[83] For example,Lucas,ibid.,31,61,105.
[84] Ibid.,69.
[85] See also Arrow,‘Rationality of Self and Others’(1986),S390.
[86] Lipsey and Lancaster,‘The General Theory of Second Best’(1956);Buiter,‘The Economics of
Dr Pangloss’(1980),45.
[87] Kapeller,‘Some Critical Notes’(2010),332-334;Francis,‘The Rise and Fall of Debate in
Economics’(2014);Fourcade et al.,‘The Superiority of Economists’(2015).
[88] Lucas,‘Methods and Problems’(1980),698;Lucas,‘Macroeconomic Prior-ities’(2003),1;also Klamer,The New Classical Macroeconomics(1984),50-51;Mankiw,‘The Reincarnation of
Keynesian Economics’(1991),1.
[89] Fourcade et al.,‘The Superiority of Economics’(2015).
[90] Nisbett and Ross,Human Inference(1980),30-32.
[91] Carter and Maddox,Rational Choice(1984),142.
[92] Proctor,Cancer Wars(1995),8;Proctor and Schiebinger,Agnotology:The Making and
Unmaking of Ignorance(2008);Pinto,‘Tensions in Agnotology’(2015).
[93] Mirowski,Never Let a Serious Crisis Go to Waste(2013),ch.4;Krugman,‘What They Say
versus What They Mean’(2013).
[94] Suskind,‘Faith,Certainty and the Presidency of George W.Bush’(2004).
[95] For example,Robert Clower and David Colander,in Snowdon and Vane,Conversations with
Leading Economists(1999),188-189,212,214-215;Caballero,‘Macroeconomics after the
Crisis’(2010).
[96] Hicks,Causality in Economics(1979),viii.
[97] Phelps,Frydman and Phelps,‘Introduction’(1983);Tobin,see Klamer,Conversations with
Economists(1984),110-111;Arrow,‘Rationality of Selfand Others’(1986),S393;Modigliani,see
Hirschman,Rhetoric of Reaction(1991),74;Hahn and Solow,A Critical Essay on Modern
Macroeconomic Theory(1995);Sims,‘Macroeconomics and Methodology’(1996);Sims,‘Comment
on Del Negro,Schorfheide,Smets and Wouters’(2006),2;Krugman,‘How Did Economists Get It So
Wrong?’(2009).
[98] Solow,‘Reflections on the Survey’(2007),235;also Solow,‘The State of
Macroeconomics’(2008).
[99] Solow,in US Congress,‘Building a Science of Economics for the Real World’(2010),12;also
Solow,‘Dumb and Dumber in Macroeconomics’(20032009).
[100] Wikiquotes,‘Talk:John von Neumann’(2015).
第二章
“经济科学”奖
在动荡的世界中,阿尔弗雷德·诺贝尔在1895年授予的这些奖项就像一盏盏拥
有不朽价值的明灯一样,始终散发着耀眼的光辉。这些奖项表彰的是人类为了寻
求真理所做出的努力、付出的真诚以及取得的成功,这是一个可以让人奠定地位
的荣誉。1968年,瑞典中央银行说服诺贝尔基金会增加了一个经济学奖项,这一
奖项与科学、文学及和平奖项拥有完全平等的地位。以这样一种微不足道的投
资,就将诺贝尔奖的权威光环轻松扩展到了经济学领域。这种行为实际上就像拿
阿尔弗雷德·诺贝尔本人做了一次颇具价值的创业运动一样。而正如诺贝尔本人是
炸药的发明者那样,诺贝尔经济学奖同样既蕴藏着正面的力量,也蕴藏着负面的
力量。对于经济学是否能够被称为一门科学这个问题我们应当如何认定?科学方
法论专家、实践主义经济学家以及诺贝尔奖获得者对此给出了截然不同的答案。
而当我们站在审视经济学政策建议的层面来看待经济学说的时候,这个问题就显
得尤为重要。
诺贝尔奖是一种仪式和象征
在自然科学领域,诺贝尔奖是最高荣誉。它站在金钱之上的原因就是它的奖
金丰厚。它有可信度方面的质疑也是因为它会授予得奖者一笔意外之财,尽管这
笔钱对于中央银行而言可能只是一笔小钱,但是对于全世界的学者而言可能是一
笔巨款。 [1]
但是金钱本身并不足以构成诺贝尔奖地位的全部。卡托研究所的米
尔顿·弗里德曼奖(在2002年奖金达到50万美元)就不具备同样的标志性意义,能
够给予几乎等额奖金的沃尔夫奖或者巴尔扎恩奖也不具备这样的意义。但颇具讽
刺意味的是,对于一个(大多数情况下)颁发给理性运用的奖项而言,它自身却
是一个相当陈旧的仪式,这种反差具有不可思议的魔力,反而可以给人带来卓越
的光环。一位钦佩者在1976年给米尔顿·弗里德曼的信中写道:“我出于简单而自
私的理由为你的获奖感到高兴,因为我可以对我的孩子说我曾经跟摘得诺贝尔奖
桂冠的人握过手。” [2]
弗里德曼回忆道:
诺贝尔奖会把获奖人变成一个其所属领域的专家,并且会吸引来自世界
各地的杂志和电视台的记者和摄影师。我自己就已经被问及从普通感冒的治
愈到一封约翰·F.肯尼迪(John F.Kennedy)签字的信件的市场价值的所有
问题。毫无疑问,这种关注不仅是奉承性的,而且是毁灭性的。 [3]
这种魔力还以另外一种方式起作用:瑞典皇家法庭(另一种古代遗物)沐浴
在奖项的光辉之中。
这一奖项赞美思想的力量。在知识所授予的洞察力和它所带来的优势上,思
想的力量是很难界定的。对大自然的控制最初可能创造了诺贝尔的财富。诺贝尔
将不稳定的爆炸性硝化甘油制造成可以储存、运输并且可以安全触碰的炸药。他
发明的无烟火药因为可以隐藏炮火的来源,从而加重了战争的危险性。后来在英
国又被进一步发展成线状无烟火药,它给两次世界大战和无数更小规模的冲突提
供了火药。如果这一发明曾经获得了诺贝尔奖的话,那么其他人就会因为只发明
烈性不那么强的爆炸物而不能获奖。诺贝尔的创新是不需要证实的:这些炸药伴
随一声声巨响炸开,利润滚滚而来。科学方面的成功很少有这样的结局和确定
性,而且一般是超出普通人控制范围的。诺贝尔奖已经将公众的注意力转移到一
些不那么显著的成就上,并且赋予获奖人金钱和名望。
智力奖项是碎片化结构上的启蒙装置,在这一结构中,每个层级都是复制较
低层级的成果。在认知梯子的每一节上,从小学开始,都由各种认知和选择进行
了标记。考试、毕业、穿毕业礼服以及获得学位,都标志着学术进展上的不同阶
段,学生会为这些活动做各种准备。在梯子上升的过程中,路是越来越窄的。每
所大学都有精英教授,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科学和投稿机构。庄严的图书馆有各
种论文,有一些已经有三个世纪那样古老了,这些论文当时被投递出去都是为了
得到权威认证和学术团体授予的各种奖项的。
在成立之初,诺贝尔奖是最新的、最令人兴奋的现存的学术奖励。 [4]
伟大
的国际性的颁奖活动发出一系列奖牌。维多利亚时代晚期是爱国主义盛行的时
期,各种奖项不仅使奖项得主获得荣耀,也令奖项得主的祖国以及颁发奖项的人
都获得荣耀。在1896年的雅典奥林匹克运动会上,0.1秒之差就能区别出金牌、银
牌和铜牌。这自然让人想到诺贝尔奖发出一个金牌就好像也对获奖等级进行了区
分一样。
哈耶克因为在1974年10月14日获得诺贝尔奖而受到关注。12月6日,他的孩
子、女婿和妻子陪同他来到斯德哥尔摩。接下来一周,外交部官员一直陪同他。
之后的三天,他参加了如旋风一样的记者招待会、官方午宴和晚宴。在10日上
午,他预演了获奖仪式。 [5]
(所谓的)诺贝尔音乐节在同一天的下午4点开始。
在黑暗寒冷的北欧冬季,这次活动是一年之中的“瑞典的社交活动事件”,也是一
次令人眩目的迎接圣诞的活动。 [6]
所有领域的诺贝尔奖得主,男士都要身穿黑色燕尾服(一种带长尾的礼
服),系白色领带,然后由各种旗帜打头阵,在一队学生的簇拥下,走进庄严的
斯德哥尔摩音乐大厅。学生们穿着无尾礼服(女士则穿黑色长袍),头戴白色尖
顶海军帽,身披蓝黄相间的绶带,蓝色和黄色是瑞典国旗的配色。大喇叭里传出
像国王一样的声音,宣布奖项和获奖者。然后上百个显赫人物继续前往斯德哥尔
摩蓝色城市大厅,并在那里待三个小时。他们会一起参加皇家宴会、家庭聚会以
及和学生共同庆祝等一系列活动。 [7]
餐点已经由年会的主厨秘密预定好,模拟
宴会也已经提前一个月进行过预演。为了保持温馨的瑞典宴会传统,通常会有学
生合唱团用歌声来给晚宴增色。在之后几年中,逐渐加入了管弦乐队的表演,发
展到20世纪90年代,这一娱乐庆典似乎已经成为一出“小型戏剧”了。与此同时,整个国家民众都能在电视上观看这一庆典活动。整个现场会穿插着干杯和短暂的
演讲,最后在维也纳华尔兹的舞曲中结束。 [8]
在获奖后的第二天,哈耶克发表
了传统的诺贝尔获奖演说。而两周之后,他在给诺贝尔基金会主席写信时说
道:“我们慢慢地从美丽的斯德哥尔摩之梦中苏醒过来,回到了日常的生活之中..”
[9]
与他共同获奖的经济学家纲纳·缪达尔持有的是社会民主主义观点,他选择将
奖金捐献出去,但是哈耶克没有这样做,我只能将此理解为这笔奖金缓解了哈耶
克所憎恨的他对福利国家的依赖(因为高昂的医疗费用)。 [10]
对米尔顿·弗里德曼而言,这一奖项掀起了一股庆祝狂潮,每一次庆祝,他都
进行了私人答谢。其中有来自三个著名的以色列社会民主党人士的贺词,第一个
就是集体区居民[(埃胡德·阿弗里尔(Ehud Avriel)、什洛莫·埃韦尼利
(Sholomo Avineri)、迈克尔·布鲁诺(Michael Bruno)]。 [11]
来自经济事务研
究所(英国的新自由主义思想智库)的拉尔夫·哈里斯(Ralph Harris)和阿瑟·塞
尔登(Arthur Seldon)发来贺电,“我们很高兴你没有像哈耶克跟缪达尔一样,与
约翰·加尔布雷思(John Galbraith)分享这一奖项”。英国著名经济记者塞缪尔·布
里坦(Samuel Brittan)曾经非常矛盾地写道:“这一奖项让我们的心跟随我们所
看到的英国并没有走智利道路的事实。”[1975年5月,弗里德曼曾给哈里斯写信
说:“罗丝(Rose)和我在智利度过了非常美妙的一周..我担心智利就是未来英国
的样子。”]
[12]
而思想上的对手肯尼斯·阿罗则明确保证这一奖项已经被他摘取
了。 [13]
“自由党”主席爱德华·克兰三世(Edward CraneⅢ)作为一名密友
说:“因为你和哈耶克这三年的努力,自由市场总算是变得非常可观了。” [14]
哲
学家卡尔·波普尔在写给弗里德曼的信中说:“对于朝圣山学社而言,这是多么令
人振奋的消息啊!它的两任主席都摘得了诺贝尔桂冠!” [15]
这一程序已成定式。 [16]
决定谁能获奖的权威都身处声誉卓著的学术机构之
中:瑞典皇家科学院、瑞典学院和卡罗林斯卡医学院。和平奖是一个例外,它由
挪威议会颁发。文学奖由瑞典文学院颁发。而瑞典皇家科学院则是经济学奖的管
理机构,对奖项的提名记录有保密50年的规则,但是其设有三个公开账户、一个
资料库和三个会谈,以此来看似公开地提供相关信息。 [17]
要知道,其他诺贝尔
奖项均是由五位专家构成的永久委员会来履行排名和推荐候选人这项职责的。每
年秋季,诺贝尔经济学奖就开始进行提名(次年2月1日截止),那些有资格提名
他人的人有的来自瑞典皇家科学院,有的是北欧国家某些大学的经济学教授,也
有曾经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奖人,还有经济学奖评委会的成员。每年秋季,评委会会寄出符合要求的候选人名单,然后评委会将选出几百名被多次推荐的候
选人,并委任海外评审专家来筛选候选人,评委会整个夏天都会收到来自四面八
方的推荐信。最终候选人名单会提交给各位院士,然后提交到所有学术成员的全
体会议上,经历两轮会议讨论之后再确定最佳人选。最后通过秘密投票来选出得
票最高的候选人。可见,没有提名就没有评选,有时候评选就像一场战争。列夫·
托尔斯泰(Leo Tolstoy)在1901年没有获得文学奖提名,于是就拒绝以后被考虑
提名。 [18]
同样被错过的还有安东·契诃夫(Anton Chekhov)、约瑟夫·康拉德
(Joseph Conrad)、托马斯·哈代(Thomas Hardy)、亨利克·易卜生(Henrik
Ibsen)、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詹姆斯·乔伊斯(James Joyce)、马塞尔·
普罗斯特(Marcel Proust)、奥古斯特·斯特林堡(August Strindberg)、弗吉尼亚
·伍尔芙(Virginia Wolf)、爱弥尔·佐拉(Emile Zola),还有许多获奖者并不出
名,而那些特别出色的反而几乎被人遗忘了。
国家学术机构一般由资深或者年长的学者组成。论资排辈与革新带来的破坏
性潜力是不相称的。科学共和国(The Republic of Science)有一个不成文的规
矩,那就是实质研究比地位更重要,而且每个人的声音都要能被听到。在自然科
学领域,这对诺贝尔奖评定委员会来说是一个挑战。 [19]
瑞典很少处于研究的最
前沿,学者有时候发现跟随前沿脚步是非常艰难的。专家并不比他们所支持的观
点水平更高,甚至至多就是旗鼓相当。像化学家斯凡特·阿伦尼斯(Svante
Arrhenius)和物理学家卡尔·威廉·奥森(Carl Wilhelm Oseen)这样非凡的人物渐
渐掌管了委员会。一个反常规的做法就是他们会阻止当年某个奖项的颁发,节省
下来的钱转给瑞典研究基金,有时候也会转化成委员会成员的隐形利益。一个简
单被征求意见的提名就可能胜过被外界大量提名的候选人。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在
1905年就公开发表了三篇划时代的论文,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这三篇
论文已经非常著名了,但是他错过了好几次得奖机会,最终在1922年因为一篇并
不是他最重要的论文而得奖,这篇论文对于委员会中反对相对论的人来说更容易
接受。
还有一些天才很晚才被大家认识,一些人甚至在机会到来之前就已经去世
了,而少数几个因为做出的是共同发现,所以也错过了得奖机会。北欧的候选人
面临的障碍可能比较小。提名委员会的决定(它做了绝大部分工作)可能在自然
或社会科学分组中,或者全体委员讨论时被推翻。尽管有一些瑕疵,并且经常遭
到怀疑和询问,这一奖项仍然保持很高的地位。全世界都知道 ......
您现在查看是摘要介绍页, 详见PDF附件(6842KB,30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