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知盈余.pdf
http://www.100md.com
2020年2月13日
 |
| 第1页 |
 |
| 第7页 |
 |
| 第12页 |
 |
| 第26页 |
 |
| 第49页 |
 |
| 第114页 |
参见附件(3215KB,184页)。
认知盈余是作家克莱·舍基写的关于时间管理的书籍,作者通过研究发现美国人光花在看电视上的娱乐时间就非常的多,如果人类将这种平庸时间拿来创造更加有意义的事情,那么也会变得更加卓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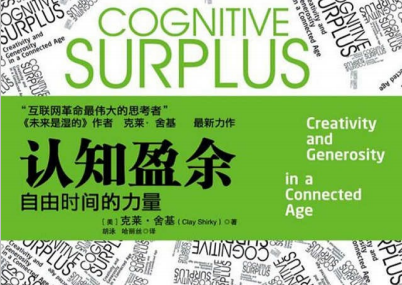
认知盈余内容简介
克莱·舍基说,美国人一年花在看电视上的时间大约2000亿个小时,而这几乎是2000个维基百科项目一年所需要的时间。如果我们将每个人的自由时间看成一个集合体,一种认知盈余,那么,这种盈余会有多大?我们已经忘记了我们的自由时间始终属于我们自己,我们可以凭自己的意愿来消费它们,创造它们和分享它们,我们可以通过积累将平庸变成卓越。
认知盈余作者信息
克莱·舍基,被誉为“互联网革命最伟大的思考者”、“新文化最敏锐的观察者”,从事有关互联网的社会和经济影响的写作、教学与咨询,特别关注社会网络和技术网络的交叉地带。目前在纽约大学的互动电信项目中任教,其咨询客户包括诺基亚、宝洁、BBC、美国海军和乐高公司等。多年来,在《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哈佛商业评论》、《连线》和《IEEE计算机》等报刊上发表文章,广受读者追捧,并经常在技术会议上充当主题演讲者。
认知盈余读者评价
《认知盈余》应该归类进社会化知识管理,和个人品牌、时间管理也都沾点边。相对于国外,目前国内拥有自由时间并且能够形成力量的人,还不普遍,但这是大势所趋,因为科技和时代裹挟我们前进。拥有自由时间而想要改进,或者还在无意义消耗(比如天天把日常生活刷进微博),都应该好好读读这书。
认知盈余截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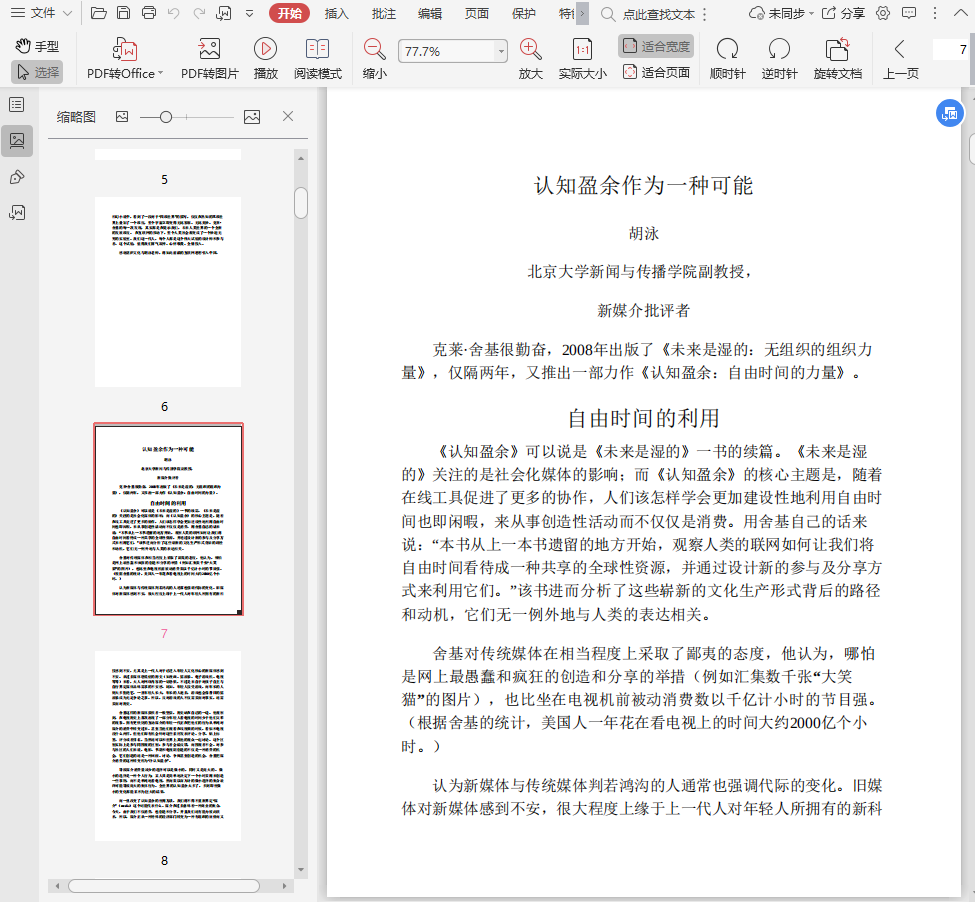
本书纸版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于 2012年1月出版
作者授权湛庐文化(Cheers Publishing)作中国大陆(地区)电子
版发行(限简体中文)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书名:认知盈余
著者:(美)克莱·舍基
字数:159 000
电子书定价:29.99美元
Cognitive surplus: creativity and generosity in a connected age by Clay
Shirky.
Copyright ? Clay Shirky,2010互联网新时代的晨光
马化腾
腾讯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
最近有幸读了两本克莱·舍基的书。第一本是《未来是湿的》,相
信大家都知道。
《认知盈余》是第二本。作者不愧为“互联网革命最伟大的思考
者”,他对互联网给人类所带来的行为举止以及文化的变迁洞若观火。
这两本著作一脉相承,它们所探讨的是这样几个问题:
随着全球用户接触互联网的门槛变得越来越低,互联网用户数量变得更加庞大,它们将形
成什么样的社会形态?我们该如何顺应这种变化?而作为互联网的从业者们,又该如何从中寻
找自己的机会?
克莱·舍基应该是一个坚定的“分享主义”倡导者。如果说,《未来
是湿的》告诉我们世界正在进入一个分享的世界,人人都在享受分享所
带来的“红利”,那么《认知盈余》便是在进一步阐述,我们得以分享的
资源禀赋。
任何时候,人们都不缺乏分享的欲望,为什么克莱·舍基会把它作
为一个重点问题来研究?这得益于互联网所带来的技术革命,用通俗的
话来说,就是“天时、地利、人和”。
首先是天时。 互联网的高速运算、处理能力,让每个从业者得以
高效、快速地完成自己的工作。这意味着,每个人可以享受更多工作之
外的时间;
其次是地利。 通讯成本的下降、带宽的增加,让用户接触互联网的成本变得更加低廉。网络不再是少数精英群体的专利,它像水和电一
样,成了生活的必需品;
最后是人和。 接触成本的降低,不可避免地使得互联网用户呈现
爆发式增长,网民和现实生活中的人群,二者的边界变得越来越模糊。
正如克莱·舍基所言,“对网络的传统看法认为它是一个独立的空间,一
个有别于现实世界的虚拟空间……而现在,越来越多的人使用电脑和智
能手机,虚拟信息空间的整个概念都在退化。”
网络世界越来越接近现实世界,意味着基于这个概念建立起来的互
联网商业模式将要被重新架构。
我曾经说过,不管已经出现了多少大公司,人类依然处于互联网时
代的黎明时分,微微的晨光还照不亮太远的路。在这个行当里,不管一
家公司的赢利状况有多么喜人,也随时面临被甩出发展潮流的风险。
发展潮流的漩涡正在席卷我们,网络正在发生演变。过去,我们可
以把网络解读为一种精英享用的新兴工具,它向用户提供的是一个接触
传统精英文化的更加便捷的通道,也就是说互联网是内容的传递者而不
是生产者;现在则不同,每个人都可以成为内容的生产者,互联网作为
一个社会形态的元素,正在为社会源源不断地输出新的内容、制造新的
话题。
“认知盈余”是新时代网民赋予互联网从业者最大的红利之一。 什
么是“认知盈余”,克莱·舍基给出的定义很简单,就是受过教育,并拥
有自由支配时间的人,他们有丰富的知识背景,同时有强烈的分享欲
望,这些人的时间汇聚在一起,产生巨大的社会效应。可以说,facebook、twitter以及维基百科的成功,都是“认知盈余”的功劳。在中
国,微博的兴起,同样有赖于它。参与分享的网民数量越来越多,力量越来越强大,互联网产业也随
之迎来“核聚变”,原来我们所熟知的商业模式,随时可能成为泡影。每
一个从业者必须认识到,如果你不能学会主动迎接,不对这种网民自由
参与分享的精神保持敬畏之心,你就会被炸得粉碎。
一个新的互联网时代即将到来。这将是一个鼓励分享、平台崛起的
时代。靠单一产品赢得用户的时代已经过去、渠道为王的传统思维不再
吃香。在新的时代,如果还背着这些包袱,那就等于给波音787装了一
个拖拉机的马达,想飞也飞不起来。如何铸造一个供更多合作伙伴共
同创造、供用户自由选择的平台,才是互联网新时代从业者需要思考
的问题。 这个新时代,不再信奉传统的弱肉强食般的“丛林法则”,它
更崇尚的是“天空法则”。所谓“天高任鸟飞”,所有的人在同一天空下,但生存的维度并不完全重合,麻雀有麻雀的天空,老鹰也有老鹰的天
空。决定能否成功、有多大成功的,是自己发现需求、主动创造分享平
台的能力。
在这个平台上,用户将是内容的主导者、分享的提供者。每个用
户的知识贡献、内容分享,是这个平台赖以成功、赖以繁荣的重要保
障, “少数人使用廉价的工具,投入很少的时间和金钱,就能在社会中
开拓出足够的集体善意,创造出五年前没人能够想象的资源”。任何有
意打破这种保障的行为,都将受到市场的惩罚。
从去年年底开始,我就一直在思考,如何能将腾讯打造成一个供更
多合作伙伴自由创业、供更多用户自由分享的开放平台。这是一个“摸
着石头过河”的过程,它需要腾讯内外都改变心态,用更加开放的大脑
去迎接变革。这段时间以来,我们已经拥有了一些经验,也总结了很多
教训。无论如何,我相信,这是一条正确的道路。我也相信,坚持走下
去,互联网新时代的晨光就在不远的前方。
最后想说的一点感慨是:互联网真是个神奇的东西。我最近在一部科幻小说中,看到了一段对于“四维世界”的描写,仅仅在熟知的三维世
界上叠加了一个维度,整个宇宙立即变得无比寥廓、无比美妙。克莱·
舍基的每一次发现,其实都是在提示我们,未来人类世界的一个全新
的发展维度。 在互联网的推动下,整个人类社会都变成了一个妙趣无
穷的实验室。我们这一代人,每个人都是这个伟大试验的设计师和参与
者。这个试验,值得我们屏气凝神、心怀敬畏、全情投入。
感谢湛庐文化与胡泳老师,将如此前沿的互联网思想引入中国。认知盈余作为一种可能
胡泳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新媒介批评者
克莱·舍基很勤奋,2008年出版了《未来是湿的:无组织的组织力
量》,仅隔两年,又推出一部力作《认知盈余:自由时间的力量》。
自由时间的利用
《认知盈余》可以说是《未来是湿的》一书的续篇。《未来是湿
的》关注的是社会化媒体的影响;而《认知盈余》的核心主题是,随着
在线工具促进了更多的协作,人们该怎样学会更加建设性地利用自由时
间也即闲暇,来从事创造性活动而不仅仅是消费。用舍基自己的话来
说:“本书从上一本书遗留的地方开始,观察人类的联网如何让我们将
自由时间看待成一种共享的全球性资源,并通过设计新的参与及分享方
式来利用它们。”该书进而分析了这些崭新的文化生产形式背后的路径
和动机,它们无一例外地与人类的表达相关。
舍基对传统媒体在相当程度上采取了鄙夷的态度,他认为,哪怕
是网上最愚蠢和疯狂的创造和分享的举措(例如汇集数千张“大笑
猫”的图片),也比坐在电视机前被动消费数以千亿计小时的节目强。
(根据舍基的统计,美国人一年花在看电视上的时间大约2000亿个小
时。)
认为新媒体与传统媒体判若鸿沟的人通常也强调代际的变化。旧媒
体对新媒体感到不安,很大程度上缘于上一代人对年轻人所拥有的新科技感到不安,尤其是上一代人对于已进入年轻人文化核心的新媒体感到
不安。从过去媒体恐慌症的历史(如漫画、摇滚乐、电子游戏机、电视
等等)来看,大人对网络内容的一切恐惧,不过是来自于对孩子自主与
自行界定媒体品味需求的不安感。比如,年轻人接受游戏,而年长的人
则大多拒绝它。一旦年轻人长大,年长的人逝去,游戏也会像昔日的摇
滚乐成为无足争论之事。所以,反对游戏的人不仅需要面对事实,还需
要面对历史。
舍基这样的新媒体鼓吹者一般坚信,历史站在自己的一边。他观察
到,在电视历史上首次出现了一部分年轻人看电视的时间少于他们父辈
的现象。拥有更快捷的互动媒介的年轻一代正在把他们的行为从单纯对
媒介的消费中转变过来。甚至当他们观看在线视频的时候,看似和电视
没什么两样,但他们却有机会针对这些素材发表评论、分享、贴上标
签、评分或者排名,当然还可以和世界上其他的观众一起讨论。这个区
别实际上是参与同围观的区别:参与者会给反馈,而围观者不会。对参
与社区的人们来说,电影、书籍和电视剧创造的不仅是一种消费的机
会,它们创造的还是一种回应、讨论、争辩甚至创造的机会。舍基把媒
介消费的这种转变称为“净认知盈余”。
导致媒介消费量减少的选择可以是微小的,同时又是庞大的。 微
小的选择是一种个人行为;某人只是简单地决定下一个小时要用来创造
一些事物,而不是单纯地看电视。然而数以百万计的微小选择的集合最
终可能导致庞大的集体行为。全世界的认知盈余太多了,多到即使微
小的变化都能累积为巨大的结果。
而一旦改变了认知盈余的使用方法,我们将不得不重新界定“媒
介”(media)这个词能代表什么。媒介在过去意味着一种商业的集合,今天,由于我们不仅消费,也创造和分享,并且我们还有能力彼此联
系,所以,媒介正从一种特殊的经济部门转变为一种有组织的廉价而又全球适用的分享工具。
舍基最爱讲的故事是一个四岁小姑娘的轶事。他在公开演讲中提过
这个故事,在本书中它也出现了,甚至成为本书最后一章的标题:“寻
找鼠标,世界是‘闲’的”。
这个故事是这样的:舍基的一位朋友和他四岁的女儿一起看DVD。电影放到一半时,小姑
娘毫无征兆地从沙发上跳起来跑到电视机屏幕背后去。他的这位朋友以为她想看看电影里的演
员是不是真的躲在屏幕背后,但是这并不是小姑娘要找的。小姑娘围着屏幕后面的电线绕来绕
去。她爸爸问:“你在做什么?”小姑娘从屏幕后方探出头来说,“找鼠标。”
这个故事可以再一次看出舍基对年轻人使用新媒体的方式寄予的厚
望:年轻人足以开始吸收身处的文化,但是对其文化的前身却知之甚
少,所以完全不必受过去的媒介文化的污染。
消费、创造与分享
关掉电视的人干什么呢?年轻人越来越多地用电脑、手机和其他联
网设备取代电视。这并非简单的硬件转移,而是用户习惯的重大迁移:
人们现在可以一起做很多更有用、更好玩的事情了。
舍基在书中列举了大量协同行动的例子,比如维基百科的编纂就是他最爱引证的证据之
一,还有些例子听上去颇有些匪夷所思:在韩国民众持续抗议进口美国牛肉的事件当中,一群
某个韩国男孩乐队组合的少女粉丝通过在网上的松散联系,竟然几乎迫使政府下台。
对旧媒体、旧机构做事方式的憎厌、对新技术的拥抱以及对下一代
年轻人的期许,所有这些混合起来,导致舍基倾向于讲述从电视中解放
的社会革命故事的一半:在《认知盈余》,以及在更早的著作《未来是
湿的》里面,舍基笔下的几乎所有网络集体行动都是积极的,每个人似
乎都在使用互联网令我们这个世界变得更加美好。对于这样的论证方
式,那些反技术决定论者当然也会乐于举出成打的例子,证明数字科技
在生活品质的创造上,其摧毁能力大于贡献能力。舍基的另外一个问题是,他低估了文化消费的价值。在网络上创造
愚蠢的东西的价值,果真高于阅读一本复杂的侦探小说的价值吗?是不
是只要是创造就拥有了某种神圣性,而只要是消费就显示了低级智慧?
美国文化批评家史蒂文·约翰逊在他2005年出版的著作《坏事变好事》
(Everything Bad Is Good for You )中,曾以游戏和电视剧为例,直接向
下述说法发起挑战:大众文化是一种致人愚蠢的东西。
例如,约翰逊争辩说,情节简单、黑白分明的电视剧早已失去市
场,今天再看《豪门恩怨》,我们会十分惊异于它的天真做作。现在的
电视剧叙述线索纷繁错乱,人物暧昧难明,常常含有需要观众主动填补
的隐喻空间,要靠观众自行猜测人物与事件、人物与人物之间的关系。
甚至连真人秀节目都在调动观众的预测性想象。在这种情况下,电视也
和游戏一样,向人们提出了更高的认知能力上的要求。由此,大众文化
使现代人变得聪明了,而不是相反。
约翰逊的结论很难说是证据充足的,但同样应该指出,那些关于大
众文化消费对大众的头脑充满损害性的责难,也并不完全站得住脚。舍
基低估了创造性生产的质量问题——平庸是创造性生产的供应增加所必
然带来的副作用。由此,我们是不是可以确定,消费一些伟大的文化产
品,要胜于创造另一只“大笑猫”?
在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舍基犯了其他媒介消费的批判者(比如说波
兹曼)所易犯的同样毛病:我们不需要引用德里达的观点也可以知道,文本阅读本身就是一个创造性行为,我们必须不断地向字句的模糊性之
中注入意义。头脑在这里并不是简单地被浪费;我们要怀疑舍基对于创
造的定义:并不是只有我们的想法结晶为物理的或者可见的剩余物才算
是创造。况且,在我们真正创造出任何有意义的产物之前,我们必得经
历一个消费和吸收的过程,并对我们所消费和吸收的进行思考。这也就
是尼采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所言,我们必须先变成啜饮一切水的骆驼,才会成为狮子。
当然,只要舍基不把他对媒介和认知盈余的观察弄得那么两极化,这些批评其实也是无的放矢的。舍基正确地指出,人们使用媒介具有三
种目的:消费、创造与分享。20世纪的媒介作为一种单一事件发展着:
消费。但眼下我们正在越来越多地创造和分享媒介,这是件值得大书特
书的事情。不过,消费的行为并不会全然消失,而是会继续扮演重要作
用。第1章 当自由时间累积成认知盈余
美国人一年花在看电视上的时间约为2000亿个小时,这几乎是2000
个维基百科项目每年所需要的时间。想象一下,如果我们将全世界受教
育公民的自由时间看成一个集合体,一种认知盈余,那么,这种盈余会
有多大?我们已经忘记了我们的自由时间始终是属于我们自己的,我们
可以凭借自己的意愿来消费它们,我们可以通过累积将平庸变成优秀,而真正的鸿沟在于什么都不做和做点儿什么。
庞大的选择是一种集体行为,是数以百万计的微小选择的集合。全
世界的认知盈余太多了,多到即使微小的变化都能累积成巨大的后果。
20世纪,社会生活的原子化使我们远离了参与文化,以至于当它回
归时,我们需要用“参与文化”这样一个词汇来描述它。
将我们的关注点拓展到包括创造和分享,并不需要通过个人行为的
大幅度转变来使结果发生巨大变化。
18世纪20年代,整个伦敦正忙着把自己灌得酩酊大醉。整个城市都
陷入了对杜松子酒的狂热之中,这种现象的出现很大程度上是由那些从
农村来城市找工作的人所推动的。杜松子酒具有不少吸引人的特质:酿
造它的谷物在当地就能买到;它的包装比啤酒更有型;它比进口葡萄酒
便宜得多。因此杜松子酒成为了这些深深地承受着新城市生活压力的新
兴人群的一种麻醉剂,生活压力催生了一系列新的行为举止,包括对杜
松子酒的狂热。
卖杜松子酒的手推车在伦敦街头随处可见;如果你买不起一整杯的
话,你可以买一块被酒浸泡过的抹布;如果你醉了,需要睡一觉来解
酒,会有价格低廉的小旅馆按钟点出租草席供你休息,而这门生意也相当兴旺。对于那些突然陷入一种陌生而又缺乏人情味的生活的人来说,杜松子酒就像一种社会润滑剂,使他们不至于彻底崩溃。杜松子酒能让
它的消费者一点一点地崩溃。这是一种城市规模的集体性酗酒。
对杜松子酒的狂热确有其事:在18世纪初,杜松子酒的消费突飞猛
进,甚至当啤酒和葡萄酒销量不佳时依然如此。这也是一种认知的转
变。英格兰的权贵们对他们在伦敦街头看到的景象越来越警觉了。人口
数量以一种史无前例的速率增长,可以预见随之而来的一系列生活环
境、公共卫生以及各种犯罪问题的不断滋长。尤其让他们感到不安的
是,伦敦的妇女也开始沉溺于酒精,她们经常聚在那些有男有女的杜松
子酒廊里,用自己的行为来肯定杜松子酒对社会规范的腐蚀作用。
人们为什么会喝杜松子酒并不难理解,它兼具口感好与容易让人喝
醉两种特点,是一种迷人的混合物,尤其是在一个清醒节制被高估的混
乱世界里。在早年的工业社会中,饮用杜松子酒为涌入城市、尤其是集
中在伦敦的人群提供了一种应对机制。工业化使伦敦成为了人口流入最
多的城市。从17世纪中叶到18世纪中叶,伦敦人口的增幅达到英国全境
人口增幅的2.5倍;到1750年,每10个英国人中就有1个住在伦敦,这个
比例在一个世纪以前是25∶1。
工业化不仅创造了新的工作方式,还创造了新的生活方式,因为人
口重置破坏了乡村生活所共有的古老习惯,而大量人口涌入也使新的人
口密度破坏了旧有的城市生活模式。为了恢复工业化前的社会规范,从
18世纪20年代末起,议会开始查封杜松子酒。此后历经30余年,议会通
过了一条又一条法律来禁止生产、消费和销售杜松子酒。委婉地说,这
种策略没有见效,结果却演变成了一场长达30年之久的猫捉老鼠游戏。
现实往往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议会禁止“调味烈酒”,于是酿酒商便不再在酒浆中加入杜松子。销售杜松子酒被宣布为非
法,妇女们便将卖酒用的酒瓶藏在裙子底下。还有一些深具企业家精神的小贩创造了一种名叫“喵咪咪”的橱柜,它被放置在街边,顾客可以随意接近。只要顾客知道密码,把钱交给里面
的卖主,就能买到一小杯杜松子酒。
平息这种狂热的并不是任何一套法律。杜松子酒的消费被视为一个
亟待解决的问题,然而事实上它作为表象反映出了一个真正的问题——
戏剧性的社会变革,以及旧有城市模式在适应这种变化时表现出的乏
力。帮助平息对杜松子酒的狂热的,正是围绕着伦敦令人难以置信的社
会密度产生的新城市现状进行的社会重建。这种重建最终将伦敦变成了
大家公认的最早一批现代化城市之一。当谈论起“工业化社会”时,我们
所说的很多制度事实上都是应工业化的环境而生,而非由工业化本身造
成的。互助型社会使除开家族和宗教关系外的人们也能共同处理风险。
集中的人口促使咖啡馆以及后来的餐馆遍地开花。政党也开始招募城市
中的穷人,并将响应他们的人提名为候选人。只有在城市密度不再被视
为危机,而仅仅被当做一个事实甚至机会时,才会出现上述这些变化。
造成杜松子酒大量消费的原因,有一半是人们想通过麻痹自己来抵
御对城市生活的恐惧,而这种消费开始回落,是因为新的社会结构减轻
了这种恐惧。人口数量和社会总财富的增长使创造新的社会制度成为
可能。和丧失理智的群众不同,新社会的建筑师们察觉到,工业化的
副产品——某种公民盈余(civic surplus)出现了。
那我们呢?我们在历史上的代际变迁又是怎样的呢?那一部分仍时
常被我们称做“工业化社会”的全球人口,事实上早已转变成后工业化形
态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了农村人口流失、城市化发展以及郊区人
口密度增长的趋势,辅以在几乎所有人群中都不断提高的教育水平,标
志着愿意思考和谈话、而不是生产或运输物料的人数的空前增加。在这
样的转变过程中,我们的“杜松子酒”,一种虽饱受批评却能让我们在由
一个社会转变为另一个社会的过程中放轻松的润滑剂,会是什么呢?
答案是情景喜剧(sitcom)。看喜剧,或者肥皂剧(soap opera)、古装剧(costume drama)以及电视上播出的各种娱乐节目,侵吞了发达
国家公民的大量自由时间。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持续增长的国内生产总值、教育水平以及人
均寿命迫使工业化社会去努力解决一个全国性的、之前从未遇到过的问
题,那就是自由时间 。受教育人群可支配的自由时间不断累积并激
增,究其原因,一是受教育人群自身数量飞涨,二是人们寿命越来越长
但工作时间却越来越短。(有部分人口在20世纪40年代前便经历了教育
和自由时间的急剧上升,但当时这种趋势仅发生在城市地区,并且大萧
条推翻了很多当时的潮流,无论涉及到教育还是下班后的时间。)这一
改变还削弱了传统消磨时间的方式,而这种削弱是郊区化的产物——远
离城市,远离邻里,不断更换工作,不断搬家。战后美国每年积累的自
由时间总计有数十亿小时之多,但是人们野炊的频率和保龄球社团的数
量却开始出现倒退。我们究竟用这些时间做什么去了?大多数情况下,我们在看电视。
我们看《我爱露西》(I Love Lucy )
[1]
,看《盖里甘的岛》(Gilligan's Island )
[2]
,看
《马尔柯姆的一家》(Malcolm in the Middle )
[3]
,看《绝望的主妇》(Desperate Housewives)
[4]。我们有太多有待消磨的自由时间,但能消磨这些时间的趣事却太少,以至于每个发达国
家的公民都开始看电视,好像这是一种义务似的。很快看电视就消耗掉了我们最大部分的自由
时间:全世界的人们平均每周花在看电视上的时间超过20小时。
在媒介史上,只有广播和电视一样做到过无处不在,并且很多时
候,收听广播都伴随着其他活动,比如工作或者旅行。而通常情况下,对大多数人来讲,看电视就是他们在从事的活动。因为电视同时调动视
觉和听觉,甚至只是稍微关注一下的人都会挪不开步子。作为消费的先
决条件,电视把人们粘在了椅子和沙发上。
情景喜剧就是我们的杜松子酒,是在面对社会变迁危机时的一种能
够无限扩张的反应。通过饮用杜松子酒的行为,不难解释为什么人们会
看电视节目——有一部分确实不错。令人难以解释的是,收看电视节目是怎么一步一步成为每一个发达国家市民的第二职业的。药理学家会
说:“过量成毒药。”适量摄入酒精和咖啡因都没问题,可过量就会致
命。同样,电视的问题也不在于节目的内容,而在于节目的量:对于个
人以及整个文化的影响都取决于量。我们不仅收看好节目和烂节目,其
实我们什么都看——情景喜剧、肥皂剧、电视导购节目(infomercial)
以及家庭购物节目。人们往往在关心当时正在播放什么节目之前就已经
决定要看电视。关键并不在于我们看什么,而在于我们一生会看多长时
间,是一个又一个小时,日复一日,还是年复一年。某个出生于1960年
的人到目前为止已经看了约5万小时的电视节目,而且很有可能在他离
世之前还会再看3万小时。
这种状况并非美国独有。20世纪50年代以来,任何一个GDP持续增
长的国家都无一例外地面临人类事务的重新排序。整个发达国家社会做
得最多的三件事,分别是工作、睡觉和看电视。尽管已经有相当多的证
据表明看电视过多是造成人们不快乐的原因之一,但现实依然如故。
2007年,在由《经济心理学》杂志(Journal of Economic Psychology )发起的一项《看电视
让我们变快乐了吗?》(Does Watching TV Make Us Happy? )的让人如梦方醒的研究中,行为
经济学家布鲁诺·弗雷(Bruno Frey)、克里斯蒂娜·贝尼希(Christine Benesch)和阿洛伊斯·斯
塔策(Alois Stutzer)断定,不仅不快乐的人群比快乐的人群看更多电视,而且人们常常会为了
看电视而把其他活动推到一边,而那些活动虽然并非即刻愉悦人心,但却能提供长久的满足
感。从另一方面来说,花过多时间来看电视和不断增长的物质欲以及焦虑感存在着联系。
对于看过多电视可能对身体有害的思考一直被人提及。近半个世纪
以来,媒介批评家们面对电视给社会带来的影响不断地绞着他们的双
手,连手掌心都快搓破了。从牛顿·米诺(Newton Minow)
[5]
称电视
为“茫茫荒原”(vast wasteland)的著名论述,到“傻瓜盒子”(idiot
box)或“蠢材显像管”(boob tube)等绰号,再到罗纳德·达尔(Ronald
Dahl)在《查理和巧克力工厂》(Charlie and the Chocolate Factory )
中对痴迷于电视的迈克·蒂维(Mike Teavee)的缺德描述。
[6]
尽管说了
那么多刻薄话,他们的抱怨却从来都没起作用——在过去50年中,人们用于看电视的平均时间每年都在增长。我们已经了解了电视对人们快乐
程度的影响,这些了解起初只是道听途说,后来有数十年心理学方面的
研究做支持,但仍然没有阻碍人们看电视时间的增长,这一活动仍然主
宰着我们的休闲时间。为什么会这样呢?
议会的反对并没有减少人们对杜松子酒的消费,出于同样的原因,急剧增长的电视观看本身也并不是问题,它只是问题的一种反映形式。
人类是社会性动物,但自由时间的激增和某种社会资产的稳步减少趋
于一致,这种社会资产便是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与依靠。 线索之一便
是,观察电视收看时间的急速增长是如何导致其他活动,尤其是社交活
动被取代的。正如吉伯·福尔斯(Jib Fowles)在《为何观看》(Why
Viewers Watch )一书中所解释的,“看电视主要替代了三项活动:其他
娱乐、社交,以及睡眠。”一种叫做“社交替代假说”(social surrogacy
hypothesis)的理论认为,电视的消极作用之一是,它减少了人与人之
间接触的时间。
社交替代分为两部分。福尔斯陈述了第一部分——我们已经看了太
多电视,以至于取代了我们消磨时间的其他方式,包括和家人及朋友在
一起的时间;另一部分则是荧幕上的人物组成了一群想象中的朋友。来
自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的心理学家杰伊·德里克(Jaye Derrick)、希拉·加布里埃尔(Shira Gabriel),以及来自迈阿密大学的库尔特·胡根
伯格(Kurt Hugenberg)共同研究得出,当人们感觉孤独时,会转台到
自己喜欢的电视节目,收看这些节目会让他们感到不那么孤独。这种转
移解释了电视是如何成为最受拥戴的可选活动的,甚至当收看时间多到
和不愉快密切相关并诱发不快时依然如此:不管看电视有什么坏处,反
正总比感觉自己很孤独要好,即使事实上你确实是孤独的。因为看电视
是一件可以独立完成的事情,而且电视在缓解人们孤独感的同时,恰好
具备能够流行起来的特性,尤其是当社会由人口稠密的城市和联系紧密
的乡村走向通勤工作和频繁迁移造成的相对断裂时。只要家里有一台电视机,那人们即使想要多看一个小时也不需要付出额外的代价。
于是看电视创造了某种单调的重复工作(treadmill)。路易吉诺·布
鲁尼(Luiginao Bruni)和卢卡·斯坦卡(Luca Stanca)在《经济行为与
组织》杂志(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and Organization )中一篇
《独自观看》(Watching Alone )的论文中指出,看电视在通过单独活
动推掉社交活动的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马可·桂(Marco Gui)
和卢卡·斯坦卡在他们2009年的论文《看电视,满足感和幸福感》
(Television Viewing, Satisfaction and Happiness )中也提到了相同的现
象:电视在提高人们的实利主义和物欲方面起着重要作用,因而能导致
个体低估人际关系给生活带来满足感的相对重要性,也因此导致了人们
过多地从事产生收益的活动而对关系活动投入不足。将“对关系活动投
入不足”这句干巴巴的经济学术语译成通俗语言,就是指花很少时间来
陪家人和朋友。 正是由于看太多的电视使我们将更多的精力转而投入
到物质满足上,因此花在社交方面的时间就减少了。
我真正弄明白人们为何决定把最大部分的自由时间花在对单一媒介
的消费上,是在2008年我写的一本关于社会化媒体的书《未来是湿的》
(Here Comes Everybody )
[7]
出版以后。当时一位电视制片人在试图决
定是否让我在她的节目上讨论这本书时问我:“你认为目前社会化媒体
有哪些有趣的用处?”
我向她提起了维基百科,一部经协作完成的百科全书,我还向她提
及了维基百科上关于冥王星的文章。
早在2006年,冥王星就被从太阳系行星俱乐部中剔除了——天文学家认定它和其他行星很
不一样,因此他们计划对行星进行重新定义,以将冥王星排除在外。此事件引发了对维基百科
上冥王星这一词条的编辑高峰。考虑到冥王星地位的改变,人们频繁地对该词条进行编辑修
改。最热衷于此事的一小组编辑人员,在如何最贴切描述冥王星地位的改变这一问题上,并未
达成一致。他们更新了关于冥王星的词条——从章节到句子,甚至到词语的选择都互相较劲,最终把文章的本质内容从“冥王星是太阳系第九大行星”改成了“冥王星是一颗位于太阳系边缘,形状不规则,围绕不规则轨道旋转的石头”。我原以为那位制片人和我会开始一个关于知识的社会结构、权力的
本质或者任何一个谈到维基百科都经常会引出的话题。但是,她没有提
到任何此类问题。相反,她叹息道:“人们哪儿来的时间?”听到这些,我立刻插话说:“别人可以问,但是做电视这一行的人绝对不能问这样
的问题。你应该清楚那些时间是从哪儿来的。”她知道,因为她供职于
一个在过去50年中消磨掉公民大量自由时间的行业。
想象一下,如果我们将全世界受教育公民的自由时间看成一个集
合体,一种认知盈余(cognitive surplus),那么,这种盈余会有多
大? 为了算清这笔账,需要一个计量单位,那么就让我们从维基百科
开始吧。
设想将所有人花在维基百科上的时间总数作为一种计量单位——将对每一篇文章的每一处
编辑,对每一次编辑的讨论,包括用维基百科上现有的任何一种语言完成的,时间统统加起
来,截至我跟电视制片人说话的那一刻,大概代表了一亿个小时的人类思考。
马丁·瓦滕伯格(Martin Wattenberg),一位致力于研究维基百科的
IBM研究员,帮助我得到了这一数据。虽然他用的是“在信封背面涂涂
画画”的粗略算法,但在数量级方面是正确无误的。显然,累计达一亿
小时的思考时间已经很多了,然而和我们花在电视上的时间相比,这些
时间仍是小巫见大巫。
美国人一年花在看电视上的时间大约是2000亿个小时。这几乎是
2000个维基百科项目每年所需要的时间,甚至这个时间的一个零头都无
比庞大:每周末我们都会花大约1亿小时仅仅用来看电视。这是很大一
部分盈余。那些提出“人们哪儿来的时间”花在维基百科上的人没有意识
到,相比我们全部所拥有的自由时间的总和而言,维基百科项目所占用
的时间是多么微不足道。这是一个不平凡的时代,因为我们现在可以
把自由时间当做一种普遍的社会资产,用于大型的共同创造的项目,而不是一组仅供个人消磨的一连串时间。一开始社会完全不知道应该如何处理任何盈余——这也正是为什么
这些时间会成为盈余的原因所在。大多数情况下,当余下一块很大规模
的自由时间时(每年数以十亿计甚至数以万亿计小时),我们便会将它
消磨在看电视上,因为我们认为以这种方式来消磨这部分时间比现有其
他可供选择的方式要好。当然,我们也可以在室外玩耍,读书看报,或
者和朋友一起搞音乐创作。但大多数情况下我们不会那么做,因为和简
单地坐下看电视相比,那些活动的门槛太高。发达国家的生活中包含了
太多消极参与:我们在工作中是办公室寄生虫,在家又成了沙发土
豆。 如果认定比起其他事情来,我们更想做消极参与者,那么这种状
态就很容易解释。这种现实在过去数十年中似乎合情合理。很多证据支
持这一观点,而反对之声并不多。
然而现在,在电视历史上首次出现了一部分年轻人看电视的时间少
于他们父辈的现象。一些针对中学生、宽带用户和YouTube用户的研究
已经注意到了这种变化,并且基本的观察结果总是一致的:拥有更快捷
的互动媒介的年轻一代正在把他们的行为从单纯对媒介的消费中转变过
来。甚至当他们观看在线视频的时候,这种行为看似和看电视没什么两
样,但他们却有机会针对这些素材发表评论、分享、贴上标签、评分或
者排名,当然还可以和世界上其他的观众一起讨论。
丹·希尔(Dan Hill)在一篇被广泛转载的网络文章《为什么〈迷失〉
[8]
会成为一种新媒
介》中指出,这部电视剧的观众不仅仅是观众——他们协同创造了一部围绕此剧的内容汇编,叫做“迷失百科”(Lostpedia) ——真的,除此之外还能叫什么呢。换句话说,甚至当他们看电
视的时候,很多互联网用户都会参与进来,而这种和参与相关的行为同消极的消费行为之间存
在着某种区别。
导致电视消费量减少的选择可以是微小的,同时也可以是庞大的。
微小的选择是一种个人行为,一个人只是简单地决定下一个小时是用来
和朋友聊天、玩游戏还是创造一些事物,而不再是单纯地看电视。庞大
的选择则是一种集体行为,是数以百万计的微小选择的集合。整个人
群中不断累积的对参与态度的转变,使得维基百科的产生成为可能。这种对自由时间的使用选择使得电视行业为之震惊,因为“看电视是消
磨时光的最好办法,这一曾经为观众所认可的观念”,已经作为社会的
一种不变特征存在了很久。一位研究协同工作的英国学者查理·利德比
特(Charlie Leadbeater)在报告中指出,一位电视主管人员最近告诉
他,年轻人的分享行为会随着他们长大而逐渐消失,因为工作会耗费他
们太多的精力,以至于在他们回家后的空闲时间里除了“瘫在电视机
前”什么都不想做。轻信“这种行为过去稳定,因此将来也会稳定”是错
误的——这不仅仅错误,而且构成了一种特殊的错误。
奶昔错误
麦当劳想提高奶昔销量,因此雇用了一些研究员来弄清楚顾客最关
注奶昔的哪种特质。是要做得更稠?更甜?还是更凉?几乎所有研究员
关注的都是产品。然而其中一个叫杰拉德·博斯特尔(Gerald Berstell)
的研究员却选择了忽略奶昔本身,对顾客进行研究。
他每天坐在麦当劳里长达18个小时,观察都有哪些人在什么时候买奶昔。最终,他得出了
一个令人惊讶的发现:很多奶昔都是在早上被销售出去的——奇怪,显然在早上8点时喝奶昔并
不适合火腿、鸡蛋这样的早餐样式。博斯特尔还从早上购买奶昔的人群的行为中得出了三条其
他线索,买家通常独自一人,除了奶昔外他们几乎不买任何其他食物,他们从不在店里喝奶
昔。
显然这些早餐喝奶昔的人都是上班族,他们打算在开车上班途中
喝。这些行为实际上显而易见,但其他研究人员却忽略了,因为它们不
符合有关奶昔和早餐的正常思维。博斯特尔和他的同事们在发表于《哈
佛商业评论》的一篇《为你的产品找到正确的角色》(Finding the Right
Job for Your Product )的文章中指出,理解到底发生了什么事的关键是
停止孤立地观察产品,并放弃对早餐的传统理解。取而代之的是,博斯
特尔关注着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顾客早上8点钟购买奶昔的目的是什
么?”如果你想在开车的时候进食,就必须选一些可以用一只手吃的东
西。它不能太烫,不能溅得到处都是,也不能太油腻。同时它必须可
口,并且需要花一些时间来吃完。没有一种传统早餐符合这些诉求,因
此那些顾客会购买奶昔来取而代之,不再顾及刻板的早餐传统。
除了博斯特尔外,所有研究人员都忽略了这一事实。他们犯了两种
错误,我们可以称之为“奶昔错误”(milkshake mistakes)。
第一种错误是主要关注产品本身,认为对于产品来讲每个要点都存
在于产品的属性中,没有顾及到顾客想让它扮演怎样的角色,即他们购
买奶昔的目的是什么。
第二种错误是对人们早餐常吃食物种类的观念过于狭隘,仿佛所有
习惯都是根深蒂固的传统,而不是累积起来的偶然事件一样。当顾客需
要食物来起一些非传统的作用时——在他们早晨上班的路途中作为填饱
肚子的东西和娱乐,那么不管是奶昔本身还是早餐的历史就都不重要
了,顾客并不是为了这些原因而购买奶昔的。
联想到媒体,我们也面临同样的问题。当我们谈起网络和短信的作
用时,我们很容易犯奶昔错误,我们只会关注工具本身。我这么说是根
据我的自身经验,20世纪90年代我开展了大量关于电脑和互联网性能的
研究,却很少考虑到其实是人类的欲望塑造了它们。
新媒体工具的社会化应用令人惊叹,究其原因,一部分在于这些应
用方式的可能性并不固有存在于工具本身之中。从便携式收音机到个人
电脑,整整一代人在个人技术的伴随下成长起来,因此他们会把新的媒
体工具纳为己用也并不奇怪。然而,人们对社会科技的使用却很少由工
具本身来决定。当我们使用网络时,最重要的是我们获得了同他人联
系的接口。我们想和别人联系在一起,这是一种电视无法替代的诉
求,但实际上我们可以通过使用社会化媒体来满足它。我们很容易设想,当今的世界反映了某种对社会的理想表达,所有
背离这种神圣传统的事情都是骇人听闻和不正当的。尽管互联网已经出
现了40年,万维网技术也已出现了20年,社会中以往喜欢将大量自由时
间用于消费的个体成员开始主动创造并分享事物,但仍有很多人对此感
到惊讶。和以往相比,这种创造并分享的行为的确令人惊讶。然而媒介
的单纯消费从来都不是一个神圣的传统,它们仅仅是一连串偶然事件的
累积,当人们使用新的传播工具能达到旧有媒体无法完成的目标时,它
们就失效了。
举例来说,一种叫做Ushahidi
[9]
的服务平台被开发出来,用于帮助
肯尼亚居民对发生种族暴力进行预警。
2007年12月,一次极具争议的选举使得支持和反对姆瓦伊·齐贝吉(Mwai Kibaki)总统的
双方陷入针锋相对的境地。一位名叫奥赖·奥科罗(Ory Okolloh)的肯尼亚政治活跃人士,在自
己的博客上记录了一次由于肯尼亚政府禁止主流媒体报道而引发的暴力冲突。而后她请读者将
他们所见证的暴力,通过电子邮件或者在她的博客上发表评论的形式传递出来。
事实证明这种方式非常受欢迎,她的博客“肯尼亚博学者”(Kenyan
Pundit)成为第一人称报道的一个重要来源。人们对此事的关注度不断
上升,以至于短短数日后奥科罗的博客便再也无法承受如此庞大的信息
量。于是她设想了一种服务平台,并把它命名为“Ushahidi”,这个平台
可以自动收集群众的报道(她曾经是手动收集的),并且能在地图上实
时显示报道中冲突发生的地点。她在博客中流露出了这个想法,引起了
程序员埃里克·赫斯曼(Erik Hersman)和大卫·考比亚(David Kobia)
的兴趣。他们三人进行了一次电话会议,仔细讨论了如何使这种服务平
台有效运作。三天后,第一版Ushahidi平台问世了。
肯尼亚选举后,人们通常只能发现发生在他们身边的暴力冲突。因
为没有社会资源,人们无法确认出事地点,无法了解到底发生了什么,也无法知道如何提供援助。我们通常依靠政府或者专业媒体来获得集体
暴乱方面的信息,但在2008年初的肯尼亚,鉴于党派狂热和审查机制,专业媒体不会报道这些内容,而政府对此也不愿意报道任何消息。
Ushahidi的开发被用于收集那些可用但分散的信息,将所有个人观
察所得的碎片编织成一幅全国性的画面。即使公众想了解的信息存在于
政府的某些机构,但由于Ushahidi的信息是由市民们提供的点点滴滴经
过重现所绘制出来的,因此它们比权威部门的信息更容易获得。这个项
目虽从网页开始起步,但Ushahidi的开发人员很快便增加了可以通过手
机短信来上传信息的功能,此时报道的信息流才真正开始不停地涌入。
在Ushahidi启动了数月后,哈佛大学肯尼迪政治学院做了一次分析。通
过对比Ushahidi和主流媒体提供的数据,他们认为Ushahidi在报道暴力
冲突的发生、冲突后的抗议以及非死亡暴力事件方面做得更好,并且报
道范围也更大——涵盖了广阔的地理区域,包括农村地区。
所有这些信息都是有用的——全世界的政府在被关注时都显得对公
民不那么极端,同时,肯尼亚的非政府组织通过对这些数据的使用来锁
定人道主义救援对象。但这仅仅是一个开始。在意识到这个网站的潜力
后,创立者们决定将Ushahidi变成一个平台,任何人都能设立自己的服
务并通过短信来收集、定位信息。这个想法使充分利用大量集体信息变
得容易,并且从最初的肯尼亚开始向别国传播开去。自从它在2008年首
次亮相以来,Ushahidi已经被用于追踪刚果国内类似的暴力事件,用于
监督印度和墨西哥的投票点及预防投票者作弊,用于报道数个东非国家
的重要药品供应量,还曾用于海地和智利地震后的伤员搜救工作。
少数人使用廉价的工具,投入很少时间和金钱,就能在社会中开拓
出足够多的集体善意,创造出5年前没人能够想象的资源。和许多有意
义的故事一样,Ushahidi的故事教会了我们几个不同的道理:
人们想做一些事情来让世界变得更美好;当他们受到邀请时愿意伸
出援手;在尝试新事物时,使用简单灵活的工具可以排除很多困难;如
果你想充分利用认知盈余,不必拥有一台高级的电脑,一部手机就足够了。然而这个故事教给我们最重要的道理之一是:一旦你弄明白如何通
过一种让他人在意的方式来充分利用认知盈余,那么他人也会复制你
的技术,一而再再而三地传遍世界。
为帮助困境中痛苦的人们而设计出来的Ushahidi网站是伟大的,然
而并非所有的传播工具都被如此大量地使用。事实上,大多数情况都并
非如此。每个人都看得到像Ushahidi或维基百科这样杰出的项目,然
而,与它们相对应的,存在着无数的做完即废的一次性工作,这些工作
投入极少,除了成为低俗笑话,也起不到更积极的作用。
眼下最标准的例子就是“大笑猫”(lolcat),一张可爱的猫咪图片会因为被加上一个可爱的
标题而显得更可爱。“猫配标题”这种做法的理想效果是能让观众大声笑出来,因此在“猫”前面
加上“大笑”二字。
收集这类图片最多的是一家名叫ICanHasCheezburg的网站,它是以它最初的图像来命名
的:一只灰色的猫张着嘴,狂躁地瞪着眼睛,配以“我能吃奶酪三明治吗?”的标题(“大笑
猫”的糟糕拼写让它声名狼藉)。ICanHasCheezburg网站拥有超过3000幅“大笑猫”的图片,比
如“我今天过得不爽”、“我偷了你一些吃的,谢谢,再见”以及“强盗猫刚吃了你的玉米煎饼”。
每个标题下都跟着数以百计也以“大笑猫”口吻写的评论。我们现在已经远离了Ushahidi。
“大笑猫”的诞生过程可以被提名为最愚蠢的创造行为。当然也会有
其他候选者,但“大笑猫”无疑是其中最全面的案例之一。成型很快,也
不需要什么技术含量,一张“大笑猫”图片所拥有的社会价值仅仅和一个
坐上去就发出放屁声的垫子相当,它的文化寿命如同蜉蝣一般短暂。任
何看到“大笑猫”的人都会在第一时间得到一条与之相关联的信息:你也
能玩这个游戏。由于“大笑猫”被创造得如此轻而易举,因此谁都可以在
一只可爱的猫咪图片旁加上一个笨拙的标题(狗、大颊鼠或海象——在
ICanhasCheezburg网站上,大家在浪费时间方面是平等的),然后和全
世界分享这一创造。
“大笑猫”图片虽然不能说话,但它们内部却存在着种种统一的准
则,从“标题要按照发音来拼写”到“字母要用无衬线字体”。就连愚蠢的深度也得加以规定,换句话说,某些方式创造出的“大笑猫”是错误的,而另一些方式创造出的“大笑猫”是正确的,也就是说,这其中存在着一
定的质量标准,甚至制约。无论这个世界对下一只“大笑猫”的需求有多
小,“你也能玩这个游戏”的信息相对我们所习惯的媒介来说体现出了一
种变化。再愚蠢的创造也是一种创造。
很多针对“大笑猫”的反对之声都着眼于它有多么愚蠢:就算你的猫
让人笑死,也没有多大的意义。就创造的范围来说,平庸和优秀之间确
实有着天壤之别。然而,不管怎样,平庸仍然处在创造的范围内,你可
以通过累积将平庸变成优秀。真正的鸿沟在于什么都不做和做点儿什么
之间,而创造“大笑猫”的人已经跨过了这道坎。
只要媒介的假定目的是允许普通人消费那些经专业创造而成的素
材,那么经业余创造的素材的增值便显得难以理解。业余创造的素材显
得很不专业——例如“大笑猫”就是卡通网络的一种低质量替代品。但是
在这一整段时间里,如果我们使用媒介的目的不仅仅是让它提供专业内
容呢?如果我们一直以来总是既想生产又想消费,但是没有人给我们这
样的机会呢?“你也可以玩这个游戏”中蕴含的愉悦并不仅仅存在于创
造,它同样存在于分享中。 “用户生成的内容”(user-generated
content)这个当前用于描述业余者的创造行动的词组所阐述的其实不仅
仅是个人行为,更是一种社会行为。“大笑猫”不仅仅是由用户生成的,它更是被用户分享的东西。事实上,分享才是愉悦的来源——没有人创
造一只“大笑猫”的目的是为了给自己留着。
20世纪,社会生活的原子化使我们远离了参与文化,以至于当它回
归时,我们需要用“参与文化”(participatory culture)这样一个词汇来描
述它。在20世纪之前,我们并没有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词组来形容参与文
化。这实际上是一种同义反复,文化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便是参与——聚
会、活动和表演,除了这些地方,文化还能从哪儿来呢?和别人一起创造并分享某样事物,这一简单的举动至少代表了对某种旧有文化模型
的回应,而这种文化模型现在正披着科技的外衣。
只要你接受了人们实际上很喜欢创造并分享事物这个观点,不管分
享的内容有多笨拙,完成得有多糟糕,并且能够理解“让彼此都能欢
笑”和“付钱让别人做一些让我们发笑的事情”是两种不同行为的话,那
么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卡通网络就成了“大笑猫”的一种低质量替代品
了。
多即是不同
当人们在调查一种像维基百科、Ushahidi或者“大笑猫”这样的新兴
文化产物时,要回答“人们哪儿来的时间”这样的问题出人意料地简单。
我们总能抽出时间来做我们感兴趣的事情,因为那些事情吸引着我
们,而这些时间是从争取每周40小时工作制的斗争中得来的。在19世纪
末为谋求更好的工作环境而进行的抗议活动中,有一句很受欢迎的工人
口号是这样说的:“8小时工作,8小时睡觉,8小时做我们想做的
事!”一个多世纪后的今天,对无组织时间显见而具体的利用已经成为
了工业化廉价商品的一部分。 然而在过去50年中,我们却把这来之不
易的时间的大部分都花在了一项简单的活动上,这种行为普遍到连我们
自己都已经忘记了我们的空闲时间始终属于我们自己,我们可以凭自己
的意愿来消费它们。
“人们哪儿来的时间”,问这样问题的人通常并不是在寻求答案。这
个问题很浮夸,说明问问题的人认为某些特定的行为很愚蠢。
在我和前面那位电视制片人的谈话中,我也提到了《魔兽世界》(World of Warcraft ),一款基于包括骑士、精灵和恶魔在内的魔幻设定的网络游戏。《魔兽世界》中的很多挑战都非
常困难,因为它们很难被单个玩家征服。相反,玩家们需要组织在一起形成公会,即一种由很
多成员构成的复杂的虚拟社会结构。在我描述这些公会和需要其成员们完成的任务时,我知道
那位制片人是怎样看待魔兽世界玩家的:成年男女蹲在地下室里扮演精灵?都是些失败者。答案显而易见:他们至少在做一些事情。你看过《盖里甘的岛》中
的这样一个情节吗?人们就快离开那个岛的时候盖里甘陷入了混乱,于
是他们没走成。这个情节我在成长的过程中看过很多遍。每次看到这个
时长为半小时的情节时,我都没有在分享照片、上传视频或者在一个邮
件列表上对话。
对此我曾经有一个不变的借口——那些事情中没有一件是我小时候
就能做的,那时候我能做的就是每年花数千小时在《盖里甘的岛》、《帕特里奇一家》(The Patridge Family )
[10]
和《霹雳娇娃》
(Charlie's Angels )
[11]
上。不管你认为蹲在地下室里扮精灵有多可
怜,我都可以以自身经验来告诉你:蹲在地下室里纠结金杰(Ginger)
和玛丽·安(Mary Ann)
[12]
谁更可爱更糟糕。
戴夫·希基(David Hickey),一位反传统的艺术历史学家和文化批
评家,在1997年写了一篇《和打酱油者搞浪漫》(Romancing the Looky-
Loos )的文章,他在文中讨论了各种各样的音乐听众。这篇文章的标题
来自于他父亲,身为音乐家的父亲把一群仅仅去消费的特殊听众叫
做“打酱油的人”(looky-loos)
[13]。要做一个打酱油的人首先得去参加
一场活动,尤其是现场活动,但他们和你在电视上盲目地收看这个活动
的效果一样:
他们在门口买票入场,但对活动没有做出任何贡献——没有给予活动任何肯定或否定,让
你可以与之结伴或者反对他们。
而参与者却不一样。参与是一种行为,它让你觉得自己的出席很
重要,让你在看到或听到某些东西时觉得自己的回应也是活动的一部
分。 希基引用了音乐家韦纶·詹宁斯(Waylon Jennings)在讨论为懂得
参与的听众演奏是怎样一种感觉时说的一段话:
他们从小酒吧里发现了你,因为他们知道你在做什么,于是你便觉得自己是在为他们演
奏。而且如果你做错了,你马上就会知道。参与者会给反馈,而围观者不会。即使在活动结束后,参与行为还
能进行得如火如荼——对整个社团的人来说,电影、书籍和电视剧创造
的不仅是一种消费的机会。它们创造的还是一种回应、讨论、争辩甚至
创造的机会。
20世纪的媒介作为一种单一事件发展着,这种单一事件就是消费。
在那个时代,鼓舞媒介的问题是:“如果我们生产得更多,你会消费得
更多吗?”人们对于这个问题的普遍回答曾经是“是”,因为人们平均每
年都会消费更多的电视资源。但实际上媒介就像铁人三项运动,由三种
不同的活动组成:人们喜欢消费,但他们也喜欢创造和分享。 我们总
是喜欢所有这三种活动,但直到最近为止,电视媒介依然只回报其中的
一种。
电视是不平衡的,如果我拥有一个电视台,而你拥有一台电视机,那么我可以跟你说话,但你却无法跟我说话。相反,电话却是平衡的。
如果你购买了消费手段,那么你也自动获得了创造手段。当你购买电话
时,没有人会问你只用来收听还是也会用来打电话这样的问题,参与行
为固有地存在于电话中。对于电脑来说也一样,当你买了一台可以消费
数字内容的机器时,你同时也购买了一台可以创造内容的机器。此外,你还能和你的朋友分享这些素材,你可以告诉他们你消费、创造和分享
的事物。这些并不是它的附加特性,而是基本要素中的一部分。
日积月累的迹象表明,如果你为人们提供了创造和分享的机会,那
么他们有时会和你辩论,即使他们此前从没有过那样的举动,即使他们
对此并不像专业人士那样精通。这并不能说明我们将停止盲目地看电
视,它仅仅说明了消费已经不是我们利用媒介的唯一方式。对于我们每
年消耗的一万亿小时的空闲时间来说,任何转变——不管多么微小,都可能是很大一部分时间。
将我们的关注点拓展到包括创造和分享在内,并不需要通过个人行为的大幅度转变来使结果发生巨大变化。全世界的认知盈余太多了,多
到即使微小的变化都能累积成巨大的后果。
试想一下,99%的事物都和原先一样,人们仍像以前那样消费着99%的电视资源,但那些
时间中的1%发生了变化,开始被用于创造和分享。相关人群每年仍然会花多达一万亿小时的时
间来看电视,而这些时间中的1%就比每年用于维基百科的时间的一百倍还多。
规模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因为盈余需要能够被累积起来。对于像
Ushahidi这样的工作,人们必须同心协力贡献自己的空余时间来创造认
知盈余,而不仅仅是完成一系列微不足道而又彼此分离的个人行为。
累积规模一部分和受教育人群如何利用空闲时间有关,另一部分则取决
于累积行为本身,和人们越来越多地在单一的分享型媒介空间内彼此互
联有关。2010年,全球通过互联网联系到一起的人口即将超过20亿,手
机用户更是早已突破了30亿。因为全世界大概有45亿成年人(全球人口
约30%的年龄在15岁以下),所以我们生活在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中
——对大多数居民来说,作为全球范围内互动组织的一部分已经变得再
正常不过。
规模能区分大小盈余作用之间的不同。我第一次发现这个原理是在
30年前。那时父母为了给我过16岁生日,送我去纽约城找我的堂兄。我
的反应和你们眼中被扔进那种环境的中西部孩子很像,我心中充满了对
高楼、人群和喧闹的敬畏。但是除了那些大事以外,我还注意到了一件
小事——切片比萨,它改变了我对于可能性的观念。
我曾经在我家乡一家叫做肯氏的比萨店里打工。在那儿我认识到了这样一个道理:顾客要
比萨,你做比萨,20分钟后你把比萨交到顾客手上。这个过程很简单,也可预测。但是切片比
萨却完全不同。你不可能知道谁会要一角,因此你要提前把馅饼做好,因为顾客的全部要求就
是在20分钟之内进来拿了切片比萨后走人,而且他们拿的只是一小角比萨,而不是一整块。
在我16岁时,那个启发了我的切片比萨,它所蕴涵的意义是:当群
体足够大时,不可预知的可以变得可预知。 如今任何一天你都不必知
道谁会来买比萨,只需要确定一定会有人来买就行。一旦对于需求的确定开始远离个人顾客,而向集体顾客回流,那么崭新的行为种类便成为
可能。如果我16岁那年有更多的流动资金,那我也会在观察雇出租车和
等公交车两种行为的过程中发现同样的原理。更普遍的是,一个事件
发生的可能性就是它可能发生的次数和频率的或然率。 在我长大的地
方,顾客在下午3点购买一小片切片比萨的可能性太低,因此我们不会
冒险提前做好一整张比萨。而在34号大街和第六大道的拐角处,你就可
以做上一整张比萨来等待生意上门。任何人类活动,无论看上去多么
不可能,在人群中发生的可能性都会增加。规模较大的盈余和小盈余
就是不同。
物理学家菲利普·安德森(Philip Anderson)说过:“多即不
同。”(More is different.) 当你把某样东西累积了很多时,它就会以新
的形式来表现,而我们新的媒介工具正在以一种空前的规模累积我们创
造和分享的个人能力。想想下面这个问题,其答案在近年来发生了戏剧
性的变化:一个拿着相机的人遭遇一件全球性大事件的可能性有多大?
如果你从一个自我中心的角度阐述这个问题,那就是,我能遇到这
件事的概率有多大?这种概率很小,小到让人难以察觉,并且从个人角
度来推断的话,总体概率似乎也很小。
我们认识新的媒介工具所带来的文化变革非常艰难的原因之一就在
于,我们惯于以自我为中心(egocentric)看待事物,而这是错误的路
径。一个拿着相机的人遭遇一件全球性大事的可能性,仅仅和事件目击
者人数以及他们中带着相机的比例有关。第一个数字会根据事件不同展
开上下浮动,而第二个数字——带着相机的人,从2000年的数百万人上
升到如今的超过十亿人。照相机现在已经被植入了手机中,因而提升了
随时会携带相机的人数。我们已经多次看到这种新情况产生的作用:
2005年伦敦地铁恐怖袭击事件、2006年泰国政变、2008年奥克兰警察杀死黑人奥斯卡·格兰
特(Oscar Grant)案,以及2009年伊朗大选后出现的动荡局面——所有这些和数不清的更多事件都被相机拍了下来,并上传到网上让更多人看到。一个拿着相机的人遭遇一件全球性大事的
可能性,很快就变成了一个事件会有目击者看到的可能性。
规模上的变化意味着曾经不可能的事情变成了可能,曾经不太可能
的事情变成了肯定。我们曾经依靠专业的摄影记者来记录那些事件,而
现在我们越来越多地成为了彼此的基础设施。用这种方式来看待分享或
许比较冷血——我们越来越多地通过陌生人随机决定分享的内容来了解
世界,但即使这样也是对人类有好处的。正如库尔特·冯内古特(Kurt
Vonnegut)在《泰坦的海妖》(The Sirens of Titans )中借主角之口说
出的:“人身上发生的最糟糕的事就是,他们对任何人和任何事都没有
用处。”我们融合认知盈余的方式会让这种命运不太可能马上到来。
我们正在越来越多地创造和分享媒介,因此我们不得不重新学
习“媒介”这个词代表着什么。
“媒介”(media),简单而言就是任何传播中的中间层,无论它如字母表般久远还是像手机
般现代。最直接并相对中庸的定义则是,过去数十年中另外一种来自于媒介消费模式的概念:
媒介涉及到商业的集合,从报纸杂志到广播电视,媒介用特殊的方式来创造素材、用特殊的方
式来赚钱。
如果我们仅仅使用媒介来指代这些商业形式和素材,这个词汇就会
变成一个时代错误,而妨碍当今发生的事情。我们平衡消费与创造和
分享的能力以及彼此联系的能力,正在把人们对媒介的认识从一种特
殊的经济部门,转变为一种有组织的廉价而又全球适用的分享工具。
认知盈余,一种全新的资源
在这本书中,我讲述了随着全世界累积的自由时间不断聚集而产生
的新资源。使我们有权使用这种资源的最重要的两个转变已经产生——
全球受教育人口累积起来的每年超过一万亿小时的自由时间,以及公
共媒介的发明和扩散, 它使得以前被排除在外的普通市民能够利用自
由时间从事自己喜欢或关心的活动。这两个事实适用于本书中所有的故事,从Ushahidi这样的富有启发性的分享到像“大笑猫”那样仅供自娱自
乐的活动。认识到这两种变化,认识到它们和20世纪媒介的不同,仅仅
是理解今天会发生什么和明天可能发生什么的开始。
我在之前写的《未来是湿的》一书中,讲述了社会化媒体历史性的
崛起,以及随之产生的群体行为环境的改变。本书从上一本书遗留的
地方开始,观察人类的联网如何让我们将自由时间看成一种共享的全
球性资源,并通过设计新的参与及分享方式来利用它们。 我们的认知
盈余只是一种可能,它自身并不代表任何事物,也做不了任何事情。为
了了解我们能利用这一新资源来做什么,我们不仅要了解那些可以利用
它的活动种类,而且要知道如何以及在哪里利用它们。
当警察想要了解某人是否会采取特殊行动时,他们会寻找一些手
段、动机或机会。手段和动机是指怎样和为什么要采取这种特殊行动,而机会指的是在哪里行动以及和谁一起行动。人们有能力、动机和机会
来利用不断累积的自由时间做一些事情吗?对这些问题的积极回答能帮
助建立人和行动之间的联系。把这个问题放大来阐述的话,手段、动机
和机会能帮助解释社会上出现的新行为。了解一件因为我们的认知盈余
而变得可能的事情,意味着理解我们累积自由时间的方式,利用这种新
型资源的动机以及我们事实上正在彼此创造的机会的本质。在接下来的
三章中,我将具体阐述怎样和为什么要利用认知盈余,以及在认知盈余
背后存在着什么。
尽管花了这些篇幅,我仍然没有描述我们可以利用认知盈余来做
什么,因为我们只有通过集体才能去做事情,这是一个社会性问题,而不仅仅是个人的事。 要想从共享的自由时间和才能中得到任何东
西,我们必须彼此协作,因此利用认知盈余并不仅仅是个人喜好的堆
积。不同用户群体的文化对成员间的互相期待以及成员如何一起工作的
影响巨大。文化会决定我们从认知盈余中获得的价值中有多少仅仅是公用的(communal),被参与者所欣赏,但对整体社会没太多用处,而有多少是公民的(civic)。 (你可以把“公用”和“公民”的对比看做
是“大笑猫”和“Ushahidi”的对比。)在第2章第4章阐述完手段、动机和
机会后,我将会讲述用户文化的问题以及公用价值和公民价值的对比。
最后一章作为全书推理性最强的一章,具体阐述了我们从对认知盈
余的成功利用中获得的经验,这些经验能够指引我们,因为更多的认知
盈余正在以更重要的方式被利用着。尽管由于社会系统的复杂性,尤其
是在包含了不同的主动参与者的情况下,这些经验不能被简单地当成药
方使用,但它们可以作为一种导轨(guide rail)来帮助你的新项目避免
面临某些特定的困境。
从过去孤立的时间和才能中脱颖而出的认知盈余,仅仅是一种原材
料。要从中获得价值,我们必须让它变得有用或者能利用它做一些事
情。我们大家并不仅仅是认知盈余的来源,也是设计它的使用方式的
人,这种设计是通过参与,以及当我们以新的方式联系在一起时对彼此
的期待而展开的。
[1] 《我爱露西》是一部美国黑白电视情景喜剧,由CBS从1951年10月15日到1957年5月6日播放。它是美国20世纪
50年代最著名的情景喜剧系列,至今还被认为是最精彩的电视节目之一,被频繁重播。——译者注
[2] 《盖里甘的岛》是美国20世纪60年代的著名情景喜剧,由CBS从1964年9月26日到1967年9月4日播放。——译者
注
[3] 《马尔柯姆的一家》是福克斯电视网播出的电视喜剧,从2000年1月9日到2006年5月14日播放,该剧曾获得多个
奖项。——译者注
[4] 《绝望的主妇》描写了一个虚构的美国小镇上一群妇女的生活,在表面光鲜的郊区社区中,充满了秘密和罪
行。自从该电视剧于2004年10月3日在ABC首播以来,收获了无数奖项,首播季吸引了2100万观众,在2007年,它成为
全世界最流行的电视剧之一,观众达1.2亿。2010年,它成为全球观看人数最多的系列剧集,在68个国家和地区中平均
拥有5100万观众。它也是2010年美国收益第三大的电视剧,每半小时创收274万美元。——译者注
[5] 牛顿·米诺(1926—) ,美国律师,曾任联邦通信委员会主席。——译者注
[6] 《查理和巧克力工厂》是英国作家罗纳德·达尔于1964年出版的童书,描写了查理·贝克特和其他4个孩子在一家
巧克力工厂中的冒险。其中一个叫做迈克·蒂维的孩子因为爱看电视,做了很多蠢事。——译者注
[7] 本书中文版已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译者注
[8] 《迷失》(Lost ),ABC于2004—2010年播放的电视连续剧,共有六季,曾获得多个奖项。——译者注[9] Ushahidi,斯瓦西里语,意为“目击”或者“证明”。
[10] 《帕特里奇一家》是ABC播出的美国电视剧,描写一个丧偶的母亲和她的5个孩子如何走上音乐道路的故事。
播放时间是1970年9月25日到1974年8月31日。——译者注
[11] 《霹雳娇娃》是一部关于三位女私家侦探的电视连续剧,是比较早地让妇女扮演传统上男人占据的角色的作品
之一。它从1976—1981年一直在ABC播放,是美国20世纪70年代最成功的电视剧之一。——译者注
[12] 《盖里甘的岛》中的两个女性角色,就好比中文语境中的红玫瑰与白玫瑰。——译者注
[13] “looky-loos”是一个人造词,用来指只围观、不参与的人,故用中文新词“打酱油者”译之。——译者注第2章 工具赋予的可能性
当韩国民众在首尔市中心展开轰轰烈烈的示威游行时,谁也不会想
到,在游行中,一半以上的参与者,竟然都是十几岁的小女孩儿。是什
么让这些年幼到连选举权都没有的小姑娘接连数周,夜以继日地在公园
里抗议?……对认知盈余的利用使人们得以用更慷慨、更公开、更加社
会化的方式来表现自己。现在,除了时间,我们还拥有任由我们支配的
工具,并不是我们的工具塑造了我们的行为,但是工具赋予了行为发生
的可能。
新的媒体形式囊括了经济学的转变,这种转变很大程度上为我们所
见的慷慨、公开、有创造力的行为提供了便捷的方式。
原本只能在单向公共媒体(如书籍和电影)和双向个人媒体(如电
话)间进行的选择,如今扩展出了第三个选项:从个人到公众的可延展
的双向媒体操作。
旧世界已经让位于一个全新的世界,在这里,大多数形式的交流,不管是公开的还是私下的,都以某种形式可为任何人所用。
早在2003年,美国多个牛肉源被发现带有疯牛病菌(学名“牛海绵
状脑病”),其后韩国便禁止从美国进口牛肉。除少数的特殊情况外,这项禁令一直持续了5年。一直以来韩国就是美国的第三大牛肉出口市
场,因此这项禁令成为了两国政府间的敏感问题。最终,在2008年4
月,韩国总统李明博和美国总统乔治·布什就重新开放韩国对美国的牛
肉市场问题进行了磋商,并以此作为两国更为广泛的自由贸易协议的试
行。表面上看来,这项自由贸易协议结束了此前的禁令,但那是在韩国
民众参与进来之前。当年5月,美国牛肉重返韩国市场的消息一经披露,韩国民众就在
贯穿首尔市中心的绿化带——清溪川公园举行了公开抗议。抗议以烛光
守夜的形式开始,大量民众聚集在公园过夜。此次抗议具有一些与众不
同的特点,其一是持续时间长:抗议并没有逐渐趋于平息,反而持续了
数个星期;其二是抗议的涉及面广:尽管示威开始的时候规模很小,但
随后人数增加到了数千人,最终达到上万人。截至6月初,此次抗议已
成为韩国自1987年争取恢复民主选举以来最大规模的抗议示威。大量民
众对清溪川公园的长时间占据破坏了大片绿地。
然而,最不同寻常的却是参与抗议的民众本身,这里所指的不是民
众的数量,而是他们的构成。此前韩国的抗议游行大多是由政党或工会
组织的。但在针对疯牛病的抗议中,一半以上的参与者(包括初期的组
织者)都是青少年,特别是十几岁的小女孩儿。
这些“烛光女孩”年纪太小而没有选举权,她们不是任何政党的成员,而且她们中的大多数
人在此之前也没有参与过任何公众性的政治活动。这些人的参与使守夜行动成为韩国首例家庭
式抗议:在长达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很多人举家出现在公园里,他们甚至经常带着婴幼儿。无
论哪个国家的政府在调查威胁国家安全的可能因素时,都不会担心十几岁的小女孩儿。那她们
究竟来自哪里呢?
这些女孩一直都存在——毕竟,她们是韩国的公民,只是此前她们
没有被大批地动员起来。民主国家既培养也依赖公民的知足常乐。当一
个国家的公民足够满意而不出现在街上游行的时候,这样的民主国家是
正常运行的;而一旦公民上街示威,那么就意味着这个国家有什么地方
做的不对了。由此看来,小女孩儿们的参与着实是个问题:是什么令这
些年幼到连选举权都没有的小姑娘接连数周,夜以继日地出现在公园里
抗议呢?
韩国政府曾试图指责一些政治外围团体和试图挑衅的组织蓄意破坏
韩美之间的关系,然而此次抗议游行的规模如此之大,持续时间如此之
久,很快便令政府之前的解释显得空洞无力。这些孩子是怎么变得如此激进的?南加州大学的文化人类学家伊藤瑞子(Mimi Ito),一位致力
于研究青少年行为和通信技术之间的交叉关系的学者,引用一名13岁烛
光女孩的话解释了小姑娘参加抗议的动机,她说:“是因为东方神起
(Dong Bang Shin Ki,DBSK)我才来这儿的。”
东方神起既不是一个政党组织也不是一个热衷于政治活动的团体。东方神起只是一个男子
乐团(意为“上帝从东方升起”),各地的男子乐团都有这样一个习惯,乐队中的每一名成员都
象征着一种不同的类型:金俊秀浪漫可爱;沈昌珉高大英俊、健硕黝黑,等等。他们俊朗潇
洒,大多对政治漠不关心,也鲜有对外交政策的言论发表,就连抗议性的音乐作品都没有发表
过。然而他们却是韩国女孩儿们的重要注意力焦点。
当韩国市场重新向美国牛肉打开大门时,拥有近百万用户的乐队粉
丝网站“仙后座”(Cassiopeia)的公告版面上发布了禁令被取消的消
息,很多抗议者便是率先由此得知此事的。
“是因为东方神起我才来这儿的”和“是东方神起让我来这儿的”并不
是一回事。东方神起从未真正建议任何公共甚至政治活动。但他们的网
站或多或少向这些小女孩们提供了一个可以随心所欲讨论包括政治在内
的所有问题的平台。她们开始焦虑,事实上是接二连三的为围绕着重新
开放韩国市场可能造成的健康和政治问题而感到焦虑。女孩儿们对李明
博政府辱没国家尊严、危害民众健康的妥协行为惊恐万分,心怀愤懑,于是她们聚集在一起,决定要对此采取些行动。
东方神起的网站为成百上千的韩国年轻人聚集在一起提供了一个平
台,也提供了一个理由。在这个平台上,发生在校园或咖啡店里的原本
稍纵即逝的对话获得了两种此前只有专业的媒体制作人才能拥有的特
质:可及性和永久性。可及性的意思是一个人写的东西可以被一群人读
懂,而永久性是指给出的作品一直存在。当人们接触了网络之后,可及
性和永久性都会增加,而韩国是世界上人与人联系最为紧密的国家。首
尔居民利用电脑和移动电话上网的质量、速度和范围的平均水平均好于
伦敦、巴黎和纽约居民。诸如Pop Seoul 和K-Popped 这样的八卦娱乐媒体报道东方神起的时
候,从未曾询问过读者对政府食品进口政策的看法。同前面提到的两个
八卦网站一样,东方神起的公告板也不是一种特定的政治环境,但与八
卦网站不同的是,这些公告板也不是完全无关政治的。它们由其参与者
塑造,具有参与者所赋予的特征。主流韩国媒体报道牛肉禁令的解除,一小部分专业媒体制作者将此消息传达给一大批彼此不太搭界的业余媒
体用户(这是20世纪广播媒介和印刷媒介的常态)。与之不同的是,无
论什么时候东方神起的粉丝在“仙后座”上发布消息,不管是金俊秀剪了
新发型还是韩国政府的进口政策有变,都会像韩国报纸上的文章一样被
广泛公开地传播开来,远比电视上的消息更加唾手可得——因为网络上
的东西总比电视上的东西更容易被分享。此外,这些零星而业余的媒体
用户不是沉默的消费者,而是喧闹的制造者,他们本身就可以按照自己
的意愿对各种消息做出反应和转载。在针对疯牛病的抗议事件中,联合
起来的韩国民众们一个比一个激进,既使是13岁的孩子也不例外。
韩国对美国牛肉的政策究竟应当如何,很多人对此其实不甚了了。
但是李明博总统对协议做出的改变令韩国民众感到不安,他们本期望政
府在更改决议时可以顾及自己的利益,然而政府却没有这么做。当因年
幼而没有选举权的孩子们出现在街道上反对政府政策时,这一举动着实
撼动了政府——此前政府习惯于享受缺乏公众监督的高度的行事自由。
在这次围绕食品安全(当然,随着抗议的进行,教育政策和居民身份问
题也被一并提了出来)这样的街头巷尾热点问题的大规模抗议事件中,李明博政府的声望大打折扣。2008年2月李明博是以接近75%的支持率
进入内阁的,然而,仅在5月一个月,其支持率便骤然跌至不到20%。
到了6月,抗议仍然没有结束,李明博政府终于决定让抗议者适可而止了,于是下令警察镇
压抗议游行——警察饶有兴致地开始了行动。一时间,网络上到处充斥着警察用水炮和警棍袭
击并无暴力行为的抗议人群的景象;成千上万的观众在线观看警察踢打十几岁小姑娘头的视
频。镇压与李氏政府的初衷大相径庭。一时间,公众对韩国警察的谴责之声四起,甚至蔓延到
国际社会,亚洲人权委员会(Asian Human Rights Commission)等组织都开始着手调查此事。
由于暴力镇压,抗议得到了更多的关注,规模也更加壮大。6月10日是20世纪80年代韩国军国主义政府结束,重新恢复民主制
的纪念日。在临近2008年6月10日时,针对疯牛病的示威活动呈现出一
种全面的反政府抗议的趋势。无奈之下,李明博总统在电视上为没有充
分征询民众意见就取消美国牛肉进口的禁令而向全体国民道歉。至此,抗议活动结束了。他不得不迫使所有内阁成员辞职,重新议定从美国进
口牛肉的限制协议,从整体上向国民解释攸关自由贸易协议的究竟是什
么。他对民众说道:“此前我以为,在我任期满一年之前我若不对政策
做出些挑战就不能称之为胜任,因此,当选总统后,我有些操之过
急。”
李明博总统的一系列举措起作用了。虽然仍有人对李明博和李氏政
府及其某些政策不满意,但听到总统承认自己未直接向公众征求意见是
错误的,看见总统向采用极端手段镇压抗议的内阁直接开火,民众的不
满情绪大大缓解。尽管耗费了大量的政治资本,李明博仍旧取得了部分
胜利,而公园里的抗议者同样也赢得了一些东西。民众渴望在重要问题
上有话语权,如果正常渠道无法实现,那么像东方神起的公告板这样的
地方总能提供给大家他们想要的协调行动。
首尔的普通居民使用了一种对“从前作为受众的人们”(The People
Formerly Known as the Audience)既不鼓励沉默也不禁止发声的交流媒
体,这个说法是我纽约大学的同事杰·罗森(Jay Rosen)最喜欢用的。
我们习惯了依赖媒体将信息传达给我们:电视里的人告诉我们,由于恐
惧疯牛病,韩国政府禁止美国牛肉进口,同样也是电视里的人告诉我
们,牛肉禁令解除了。
然而,在韩国此次抗议期间,媒体不再仅仅是信息的来源,而同时
开始成为协调的核心力量。参加广场上抗议的孩子们使用东方神起公告
板,也使用Daum、Naver、Cyworld和其他一些门户网站的在线聊天室
进行对话。他们还通过手机发送图像和文字信息,不仅为了传播信息和发表言论,也为了依靠这些信息和言论采取行动——无论是在网上还是
在现实中。就因为这样做,这些孩子们改变了韩国政府的运行环境。
对网络的传统看法大多认为,它是一个独立的空间,一个有别于现
实世界的虚拟信息空间,是历史的一种偶然。追溯到当初网民数量还很
少的时候,我们日常生活中认识的大部分人还都不在这少数的网民中。
而现在,越来越多的人使用电脑和智能手机,虚拟信息空间的整个概念
都在退化。我们的社会化媒体工具不是现实生活的一个选项,而是它的
一部分,尤其是社会化媒体已经日益成为现实世界中应对突发事件的协
调工具时,就像在清溪川公园里所显示的那样。
这种与日俱增的公众参与所带来的的长期影响将会怎样,现在还不
十分清楚。韩国总统的任期是五年一届,所以李明博再也不用面对选
民。另外,韩国政府强势推行上网实名制
[1]。(值得注意的是,这项规
定只适用于月访问者超过10万人次的网站,这无疑给该规定增添了政治
意味。)政府试图将百姓带回到我们称之为知足常乐的状态。就这样,政府和人民之间的竞争开始成为一场军备竞赛,但这场竞赛的参与者是
崭新的阶层。当十几岁的小姑娘们无须专业的组织和组织者发起,就能
帮忙组织一场令政府焦躁异常的抗议时,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领
域。正如伊藤瑞子所形容的:
他们参与抗议大多并非立足于他们日常生活的具体条件,而是源于他们共享同一媒体而凝
结成的团结力量。尽管孩子们在网上所做的很多事都被看做是琐碎而无关紧要的,但正是这些
事练就了他们相互团结、相互交流的能力,最终,他们动员起来。从口袋妖怪(Pokemon)
[2]
到大量的政治抗议,不是独特的媒体表达形式,而是如何将这种媒体表述和社会行为绑定在一
起,造就了这独一无二的历史性时刻,也造就了当今崛起的一代。
关注数字媒体的人通常会担心面对面的交流方式会没落,但是在首
尔,世界上有线网络和无线网络最为发达的地方,数字媒体的影响却恰
恰相反。数字工具对于协调人类交往和现实世界活动至关重要。认为媒
体是相对隔离于“现实世界”之外的领域的传统观念,将不再适用于类似于针对疯牛病抗议的情况,事实上,也不适用于人们利用社会化媒体安
排现实活动的多种方式。不仅社会化媒体在崭新的族群——也就是我
们的手中有了新的一面,当沟通工具掌握在新的族群手中时,也会呈
现出新的特点。
新方法,解决老问题
交通问题,尤其是上下班高峰时段的交通问题,是现在亟待以社会
方式解决的现实问题。上下班都要历尽一番周折,更有千百万的人一周
有5天都要忍受这样的折磨。乍看之下这个问题似乎和媒体毫无关联,但有效解决交通拥堵的重要方法之一就是合伙搭车(carpooling),合
伙搭车的关键并不在于汽车本身,而在于协调。合伙用车并不需要新
车,需要的仅仅是现有汽车的最新消息。
PickupPal.com是众多新消息渠道之一,它是一个为协调路线相同的司机和乘客而设计的合
伙搭车网站。司机提供报价,如果乘客同意的话,系统就会让司机和乘客彼此联系。就像任何
一份一句话商业计划书一样,有太多的细节藏在后面,大到如何找出相近路线、相同时间以达
成一宗可接受的组合,小到如何在最少泄露个人信息的前提下让司机和乘客相互联系。
PickupPal同样面临着规模的问题——当司机和乘客的数量处于某一
临界数字以下时,系统很难运行,当然超过临界数字越多则越好。同样
是使用该系统的两个人,一个三次中配对成功了一次,另一个十次中配
对成功了九次,这两者对该系统的认可程度一定截然不同。三中一是备
选方案,而十中九则变成了常规。解决PickupPal规模问题的最基本方法
是从社交可能性较高的地方着手,再向其周边扩展。由于该系统对大城
市周边通勤最有效,与PickupPal合作的是可以向员工或成员发布拼车信
息(该策略亦能协助增强使用者之间的信任感)的公司和组织。
PickupPal同样整合了像facebook这样的现有社交工具,以便尽可能容易
地找到合适的拼车伙伴。上述这些策略非常有效:到2009年底,PickupPal.com已经拥有了107个国家的超过140000的用户。
PickupPal提供的服务和我们所知的认知盈余大致相似。当每个人都
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解决上下班高峰的拥堵问题时,办法只能是每个人
买辆车自己开。然而这样的“解决方式”无疑只能使问题雪上加霜。一旦
我们把上下班高峰问题当做协调问题来看,我们便能想到不仅是一两个而且是一大堆解决办法。在合伙用车的情景中,马路上的汽车数量会演
变成一种机会,因为每一辆有空位的汽车都有可能找到同路人。
PickupPal将过剩的汽车和驾驶员重新整合,把他们当做潜在的共享资
源。只要能使用允许群组交流的媒体,人们就可以依赖司机和乘客间的
信息变化寻求解决交通问题的新方法,此一方法使人人都能受益。
对大多数人都有益,却未见得对公交公司也有益。2008年5月,位
于安大略湖区的汽车公司Trentway-Wagar聘请了一位私家侦探来使用
PickupPal。侦探确认了PickupPal的运营方式如广告所述,并以书面文字
陈述了他支付司机60美元搭车到蒙特利尔的事实。凭借这一证据,Trentway-Wagar向安大略公路交通管理局(Ontario Highway Transport
Board, OHTB)请愿,要求关闭PickupPal网站,理由是PickupPal以帮助
协调司机和乘客的名义启动,但它运作得太好了,已经不像一个合伙搭
车网站了。Trentway-Wagar引用了《安大略公用机动车条例》(Ontario
Public Vehicles Act )第11章,其中规定合伙搭车只能发生在家庭和工作
两种情况下(学校和医院除外),并须在政府规定的线路内;同时,每
天的司机必须是同一个人;此外,汽油和途中的开支应按周支付。
Trentway-Wagar主张鉴于合伙用车曾经很不方便,因此应当一如既
往地“不便”,一旦这种“不便”消失,就应当有法令重新介入。奇怪的
是,一个机构在担负起协助解决某一社会问题责任的同时,亦扮演着保
护该问题的角色,因为这种机构的存在是以社会对其管理行为的持续需
求为前提的。公交公司提供着至关重要的服务——公共交通运输,然而
它们亦放纵自己去限制竞争,阻止把旅客从一个地方送到另一个地方的
替代性方式,就像Trentway-Wagar所做的那样。
安大略公路交通管理局支持Trentway-Wagar公交车公司的诉讼,下
令禁止PickupPal在安大略的营运。PickupPal就此事进行了抗辩,但在听
证会上失败了。然而公众开始关注此事,在油价飙升、重视环境、财政缩减的年代,几乎没有人站在Trentway-Wagar一边。从在线请愿书到T
恤销售,公众从各种渠道的回应都传递着同一个信息:保护PickupPal。
人们对于无法享受PickupPal网络服务所带来的不便进行的讨论激烈
到令政府无法回避。在Trentway-Wagar赢得了短暂几周的胜利之后,安
大略立法机关修改了公用机动车条例的相关规定,使PickupPal重新合法
化。
PickupPal主要从以下几方面利用社会化媒体:
首先,PickupPal能够迅速为其用户提供充足的信息以解决现实生活中的问题。PickupPal无
法在缺少令潜在司机和乘客共享其各自路线的信息交流媒介的条件下独立存在。
其次,它创造了集合价值(aggregate value)——用户越多,匹配的可能性就越大。原有的
逻辑,如电视逻辑,仅仅把观众当做个体的集合,每个个体都无法为彼此创造真正的价值。而
数字媒体的逻辑则不同,它承认这些从前作为受众的人们每天都可以为彼此创造价值。
同时,PickupPal依赖摒除网络媒体和“现实生活”的隔阂而存在。PickupPal以一种极端琐碎
的方式提供网络服务——它通过把用户配对而创造价值。但这种价值只能通过真实存在的司机
和真实存在的乘客,在真实存在的高速公路上驾驶着真实存在的汽车体现出来。
PickupPal是社会化媒体作为现实社会一部分而真实存在,同时又在
改进而不是脱离现实的一个例子。对为千万普通市民提供协调性资源的
公共媒体的利用,标志着现代媒体已经和我们熟悉的媒体大相径庭。诚
然,我们所熟悉的媒体大都是拥有专业的制作人和业余用户的20世纪媒
体模式,但其根深蒂固的经济和制度逻辑却并非始于20世纪,而是15世
纪。
古登堡经济原理或许不适用了
美因茨
[3]
的一位印刷商,约翰尼斯·古登堡(Johannes
Gutenberg),在15世纪中叶率先在欧洲使用了活字印刷。当时印刷厂
已经投入使用,但由于每页都要刻满文字,因此印刷速度非常慢且操作
费力。古登堡意识到如果将每一个字母都单独刻字,就可以根据所需将这些字母重新排列。这些雕刻好的字母活字可以用于编排新的页面,这
样就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将活字排列组成一整篇文章。
活字印刷术为善于思考的欧洲人带来了另外一些东西:书籍的极大
丰富。在古登堡之前,根本没有那么多的书。一名誊写员仅用一支羽毛
笔、一瓶墨水和一叠牛皮纸就能抄写一本书,但是整个过程非常枯燥,速度也极慢,因此一小本书的价格就非常昂贵。
到15世纪末,一个抄写员抄写一本500页的书大概要30个弗洛林,而里波利(Ripoli),一
个威尼斯印刷商,大概能以同样的价格印制300本同样的书。因此大多数誊写员都放弃了抄写现
有书籍。
13世纪,圣文德(Saint Bonaventure),一位圣芳济会的修道士,描述了人们写书的4种方式:完全抄录一部作品,一次从几部作品中进
行抄录,抄录一部现有的作品并融入自己的改编,或部分创作自己的作
品并从别处加以借鉴。以上每一种分类都有自己的名称,比如誊写员或
作家,但是圣文德似乎没有考虑到(当然更没有予以描述),一个人可
以创作一部完全原创的作品的可能性。在那个时代,很少有书存在,仅
有的书多半是《圣经》的副本,因此所谓的写书主要都是关于重新制作
或重新组合现有的文字,远远不是指创作新作品。
活字印刷术打破了这个瓶颈,当然日益壮大的欧洲印刷商做的第一
件事就是印刷更多《圣经》。印刷商开始将《圣经》翻译成通俗的语言
并印刷出版,用当时的语言而不是拉丁文。这样做不仅是为了方便,更
因为牧师们希望《圣经》可以成为布道的素材。随后印刷商开始出版亚
里士多德、伽林(Galen)、维吉尔(Virgil)和一些从中世纪流传下来
的作家作品的新版本。这还不够,印刷机可以印出更多的东西。印刷商
的下一步举措既简单又惊人:印刷新书。在活字印刷术出现之前,欧洲
大部分可读的作品都是以拉丁文的形式出现的,且至少有近千年的历
史。然而转瞬间,书籍便开始使用起了地方性语言,书的内容也变成了
讲述近几个月而不是几百年前的事情。此时的书籍数量繁多、品类不同、内容契合现实、语言通俗易懂。其实,“小说”(novel)这个词就出
现在这段时期,指的是具有全新内容的书。
然而这种从根本上解决生产力闲置的办法——创作人们之前从未读
过的新书,出现了新的问题,其问题主要是经济风险。如果一个印刷商
生产了一本新书但却没有人愿意读,那么他就失去了继续创造生产的资
源。而印刷《圣经》或是亚里士多德作品的印刷商就从来不用担心他们
印的书没有人读。每个出版新小说的印刷商都面临着风险,那么印刷商
该如何应对这种风险呢?
他们的答案是,让承担风险的人——印刷商,同时为书的质量负
责。没有明确的原因说明为什么擅长经营出版社的人就要同样擅长决策
哪本书值得出版。但出版社的开销很大,因此需要有专门的工作人员来
经营。因为材料得先于需求生产出来,所以一家出版社的经济风险在于
生产。事实上,承担一本书不畅销的可能性的责任标志着从印刷商(仅
仅制造神圣作品的副本)向出版商(为新生事物而冒险)的转变。
自古登堡以后很多新形式的媒体相继出现:图像和声音都被编码,形成照片或是音乐光盘,电磁波被用来制作收音机和电视。这些接踵而
来的变革,虽不尽相同,但同样具有古登堡经济(Gutenberg
economics)理论的核心概念:大量地投资。无论是印刷厂还是电视
塔,拥有一种生产方式的开销是很大的,这令追求新事物从根本上来说
成为了一项高风险的运作。如果拥有或经营一条很昂贵的生产线,抑或
需要聘请员工的话,那么你就适用古登堡经济原理。无论在哪里运用古
登堡经济原理,不管你是威尼斯出版商还是好莱坞制作人,你都要冒着
跟15世纪的经营管理一样的风险,那时的制作商要在读者阅读前判断哪
些书籍更优秀。在这个领域几乎所有的媒体都是由“媒体”创作的,直到
几年前我们还一直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只需要按一下“发表”的按钮
每年岁末,国家图书基金会(National Book Foundation)都会在其
颁奖晚宴上颁发美国文学卓越贡献奖(Distinguished Contribution to
American Letters)的奖章。2008年,该奖项授予了1976年出版的《女勇
士》(The Woman Warrior )的作者马克辛·洪·金斯顿(Maxine Hong
Kingston)
[4]。虽说金斯顿因为这部30年前的旧作而得到承认是桩喜
事,但她在演讲中讲述的一段发生在2008年的故事,却令在座的出版商
都不寒而栗。
金斯顿说,2008年初,巴拉克·奥巴马到她家乡夏威夷的时候,她写了一篇颂扬他的社论。
不幸的是,她投稿的所有报社都拒绝发表。而此时,她很高兴地意识到此次的拒绝并没有像过
去一样打击她。因为,现在她可以登陆Open.Salon.com,一个文学交流网站。正如她所说,“我
所要做的就是打字,然后点击一个标明‘发表’的按钮。是的,有这么个按钮。瞧!我的文章发
表了。”
是的,有这么一个按钮。发表文章曾经是我们需要获得许可后才能
做的事,我们要征得出版商的准许。而现在,我们不再需要如此了。出
版商仍旧在选材、编辑以及市场运作领域发挥着作用(例如,除我之外
还有很多人协助改进这本书),但是他们不再限定着个人和公共作品的
界限。从金斯顿关于遭拒的欣喜中,我们发现了一个长久存在但隐藏得
很深的真相。
以往,即便是“已经出版过作品的作者”,也无法单凭自己的能力出版作品。想想列出来的
这一组概念:公众的注意(publicity)、宣传(publicize)、出版(publish)、出版物
(publication)、宣传者(publicist)、出版商(publisher)。
[5]
所有这些都集中在使事物公众化的过程中,此前该过程极其困难、复杂并且开销极大,然而现在这些都已不成问题。
不得不说,金斯顿写的社论并不精彩。内容单调乏味,曲意逢迎,更谈不上有分析见地。政治话语并没有因为这一篇社论的出现得到任何
丰富。但发表自主权的增加,通常就会产生这样的结果。在古登堡之前,几乎每部书都是出类拔萃的杰作。在古登堡之后,人们所拥有的只
是看过就丢的****、乏味的游记和关于富绅的圣徒传记般的记述,这些对除了历史学家外的现代人来说毫无意义。媒体的最大张力一向莫
过于,自由和品质构成了两种相互矛盾的目标,也有人一直坚决主张,以牺牲出版物的质量为代价换取发表自由度的增长是得不偿失。
早在16世纪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
[6]
就发现:“书太多便成灾。根本没有限制狂热写作
的措施;每个人都必将成为作家;有些人为了名利而变得名声大噪,另一些人则是为了一己私
利。”爱伦·坡(Edgar Allan Poe)在1845年评论道:“这个时代最大的祸害就是每一门学问都有
太多的书。阻碍我们获得准确信息的最大障碍就是摆在读者面前乱七八糟的书,而我们必须从
中去其糟粕,取其精华。”
这些论断相当正确。出版自由度的增加确实降低了出版物的平均水
平——怎样才能避免这种情况呢?马丁·路德和爱伦·坡都依赖印刷机,他们很容易获得出版机会,但他们却希望出版机制不要增加出版的整体
数量:对我来说便宜得多,而对你来说还是遥不可及。然而,经济学却
不是这样解释的。普通人出版图书越容易,出版图书的质量也就越一
般,但参与公共讨论的自由度的增加多少会产生一些弥补价值。
第一个好处就是实验的形式得到了拓展。尽管活字印刷的广泛应用
大大降低了印刷品的平均质量,但同样刺激了小说、报纸和科学期刊的
出现。报刊令马丁·路德的《九十五条论纲》(Ninety-five Theses )和哥
白尼的《天体运行论》(On the Revolution of the Celestial Spheres )得
以广泛传播,变化的文本形式影响着今天我们所知的欧洲的崛起。某一
领域的成本降低意味着可以开展更多的实验,交流成本的降低意味着可
以开展更多关于思维和表达的实验。
这种实验的能力同时也扩大了创作者的数量并使其多样化。1991年
纳奥米·沃尔夫(Naomi Wolfe)
[7]
在她的《美丽神话》(The Beauty
Myth )一书中对女性杂志在女人一生中所起的作用表示既庆幸又难
过。她说,这些杂志为理所当然的女性观点提供了场所,但视角往往被广告人歪曲了:“广告商都是在蛮荒西部看似彬彬有礼的审查官。他们
模糊了编辑自由和市场需求的界限……一本妇女杂志的赢利并不是来自
其定价,因此其内容不能偏离广告内容太远。”在另一方面,在《美丽
神话》出版近20年后的今天,作家梅利莎·麦克尤恩(Melissa
McEwan)在她的博客上发表了一篇700字的有关日常女人厌恶症的有趣
随笔:
有很多关于女人的笑话……是对我感兴趣的男人为了撩惹我在我面前讲的,仿佛在滑稽地
提醒我二等公民的身份。当讲这些笑话的人将他们的快乐建立在他们知道他们会让我沮丧、厌
烦、受伤害的基础上时,我不打算理会这些欺侮我的伎俩。我要是笑了,他们会自我感觉良
好;我不笑,他们依然会自我感觉很好。总之怎么都是他们赢我输。
这篇题为“我们令人遗憾地达成可怕的交易”(The Terrible Bargain
We Have Regretfully Struck )的文章吸引了几百人参与评论,更引起了
上万读者的阅读,评论的大意都是“感谢你说出了我一直在想的东西”。
这篇文章之所以会被全社会所知道,就是因为麦克尤恩点击了标明“发
表”的按钮。其博客恰恰提供了沃尔夫想象的那种写作空间,在这里女
人们可以随心所欲地聊天,不必担心男人的监视抑或广告商的审查。这
里的作品不是写给任何个人的,也没有特意以政治意图激怒他人——但
要害也正是在这里。沃尔夫所说的杂志读者和博客读者可能会有同样的
反应,但杂志无法以激怒其他读者、特别是广告商为代价来取悦于这些
读者,杂志承担不起这样的后果。但麦克尤恩愿意(也有能力)为了说
出一些她想说的话而冒险得罪一些人。
沃尔夫所说的争论主要是针对女性杂志,但绝不可能只针对女性杂
志。麦克尤恩所用的自我发表的模式也不是独一无二的——现在人们一
天中会对各种各样的议题谈论上百万次,这些议题涵盖无数的兴趣社
区。社区成员可以像这样大声公开地彼此交流是一个巨大的转变,即使
在缺乏质量过滤的前提下,这种转变也十分有价值。诚然,这种价值的
产生正是因为无法提前进行质量过滤:对质量的定义越来越多,比主流
写作(以及音乐、电影等)尚能得到广泛的统一认识的时期多得多,每个团体的定义都不一样。
资源匮乏要比丰富更容易解决,因为当某样东西越来越稀少的时
候,我们会简单地想到它比从前更珍贵,这仅仅是一个概念上的小变
化。而丰富则不同:它的出现意味着我们可以开始像浪费一切廉价的
东西一样去处理此前珍贵的东西,仿佛它们便宜得能被拿去做实验似
的。 因为丰富改变了我们曾经习以为常的平衡状态,它能令在匮乏中
成长的我们迷失方向。当某项资源稀少时,控制该资源的人会觉得资源
本身很珍贵,而不会停下来考虑该资源的价值中有多少是由于资源稀缺
造成的。
美国长途电话费降低后的很多年里,我年长的亲属们仍旧会在打电话时声明这是“长途”电
话。这种电话先前的时候很特别,因为它们很贵。人们花了很长时间才明白便宜的长途电话与
此前觉得长途电话本身昂贵的认识是无关的。
同样地,当出版(使某事公开的过程)从困难变得轻松,习惯了旧
有体系的人通常会认为业余出版者出版的东西不好,仿佛出版是一件多
么严肃的事情,尽管它从来不是。当人们十分在意出版的成本和成果的
时候,出版显得是件很严肃的事情——如果出错太多就会面临失业。但
是如果这些因素不存在了,风险自然也就不存在了。一项曾经被视作很
有价值的活动被证明其价值只是一时的偶然,如同经济学的变化所显示
的那样。
美国小说家哈维·史威多斯(Harvey Swados)对简装书的看法
是,“美国公众读书习惯的革命,究竟是意味着我们将被淹没在一大堆
不断降低大众品味的垃圾中,还是意味着我们如今可以轻松获得越来越
多的便宜的经典书籍,这已经成为了一个对我们的社会和文化发展都非
常重要的问题。”
史威多斯对此的观察发生在1951年,当时简装本的图书已经流行20
年之久。奇怪的是,当时他自己也无法回答这个问题。其实这个问题的答案在1951年就已经显而易见了。公众无须在如洪流般的垃圾和广泛可
求的文学经典中做出选择,而是两者都可以拥有(我们也正是这样做
的)。
“两者都拥有”不仅是对史威多斯这个问题的答案,也是每当传播过
剩时的答案,这种过剩从印刷机发明就开始了。印刷最早是为了使《圣
经》和托勒密(Ptolemy)作品的传播价格更低廉,但所有这些旧有的
文化一点也满足不了科技的进步空间或者读者的期冀。即便是在今天,如果没有对新鲜事物的不断尝试,我们就不会有“不断增加的经典清
单”。如果世上存在某种简单的公式,可以让人写出连续数十年甚至几
个世纪都能得到赞誉的作品,那我们就不再需要不断尝试了。但事实是
没有这样的简单公式,因此我们的尝试仍须继续。
在不断尝试创造新事物的过程中,自由不断增加,随之增加的还有
劣质的材料,虽然尝试的目的是为了创造出广受赞誉的东西。这正是15
世纪印刷界的实际情况,也是当今社会化媒体的现实写照。和此前
的“匮乏”相比,“过剩”带来的是平均水平的下跌,但随着时间的流逝,不断的尝试终究会带来回报,多样化的发展扩大了新的可能,其中最好
的东西给我们带来了越来越好的作品。有了印刷机,出版业越来越重
要,因为文盲减少了,文化和科学写作造福社会,尽管随之也出现了一
大堆垃圾。
媒体,社会的连接组织
我们并非在见证印刷革命的重归,所有的革命都是不同的(就好像
是说所有的惊奇都是出人意料的)。如果社会的变化很容易被立即接
受,那么它就称不上革命了。而今天,革命集中在对业余爱好者融入
生产者的震惊里,我们发表公共言论时不再需要借助专业人士的帮助
或许可。 社会化媒体没有引发韩国的烛光抗议,也没有培养PickupPal
用户更多的环境意识。这些影响都是由意图改变公共交流方式的公民们
造成的,他们发现自己终于拥有了这样的机会。
这种公开发表言论以及将我们的才能凝结在一起的能力,与我们之
前习以为常的媒体的基础概念大不相同:我们不是在消费媒体,而是
在利用媒体。 因此,我们之前对媒体根深蒂固的概念现在正在慢慢剥
离。
以电视为例,电视将移动的图像和声音进行编码,先通过无线电媒
介,然后通过电缆传播,随后利用专门的解码设备再转化回图像和声
音。用这种方式传递的内容的名称是什么?答案是电视节目。那呈现图
像的设备又叫什么呢?答案是电视机。那制作播发内容、传递播放信号
的这些人叫什么呢——他们工作的领域又叫什么呢?答案当然也是电视
业。工作在电视领域的人们为您的电视机制作电视节目。
你可以从商店购买电视机在家里看,但是你买的电视机并不是你所
看的电视节目,你看的电视内容也不是你买的那台机器。单这样说或许
难以理解,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却一点儿都不难理解,因为我们从来都不
用刻意去考虑电视究竟是什么,而我们就用“电视”这个词统称一个集合
体的所有不同的部分:行业、内容和方式。这种表达方式让我们的认知
有些模糊,但如果我们总想弄明白现实生活中每个系统的每个细节,我
们会不堪重负。这样的集合体——既包括物体,也包括产业,还包括产品、服务和商业模式,并非独一无二地只在电视业存在。例如,收集并
保护罕见的初版书的人,和那些购买充斥于市场的言情小说,废寝忘食
地阅读,却在下一星期就把书扔到一边的人,都可以理所当然地被称为
爱书之人。
这种集合体之所以很容易实现,是因为公共媒体的大环境长久以来
一直很稳定。公共媒体最近的一次大变革还是电视的出现。在电视成为
中坚力量的60年里,我们看见的变化其实很小——比如盒式录像带或者
彩色电视机。有线电视是20世纪40年代末(电视开始普及)与90年代末
(数字网络开始成为公众生活的正常组成部分)之间媒体行业里出现的
最重要的变化。
“媒体”这个词本身就是个集合,同时指过程、产品和产出。媒体,正如我们说了几十年的那样,它主要表现为一系列产业的产出,由一个
特定的专业阶层经营,并且其中心在英语国家,即在伦敦、纽约和洛杉
矶。媒体这个词既指这些行业,也指它们所制作的作品,也包括那些
作品对社会的影响。 只要媒体环境相对稳定,那么以这种方式来阐
述“媒体”就是合理的。
尽管如此,有时我们还是不得不将一个体系中的每部分都分开来考
虑,因为这些部分无法一起运作。如果你花5分钟提醒自己(如果你还
没到30岁,那就用魔法召唤一下)20世纪的媒体对于成年人来说是什么
样的——由数个电视网络和一些主流的报刊杂志组成,而今天的媒体看
上去既奇怪又新潮。当环境稳定到连把经由电缆而不是天线获得电视信
号都能被当做剧变时,有一种媒体的出现会非常令人震惊,这种媒体能
让世界上的任何一个人都无限制地完美复制由他人无偿提供的作品。同
样令人震惊的还有这种媒体将广播和对话模式完全混合在一起,使二者
之间没有明显的区别。捆绑在“媒体”这个词身上的诸多概念正在解体。
我们需要一种新的针对这个词汇的概念,一种能摈弃诸如“某种由专业人士创造的供业余人士消费的东西”这样内涵的概念。
我个人认为:媒体是社会的连接组织(connective tissue)。
媒体就是你如何知道朋友的生日聚会在何时何地举行;媒体就是你如何了解德黑兰在发生
什么,特古西加尔巴(Tegucigalpa)
[8]
的领导者是谁,中国的茶叶价格是多少;媒体就是你如
何知道同事给他的孩子起了什么名字;媒体就是你如何知道你下个会议将在哪里开;媒体就是
你是如何知道10米之外在发生什么事情。
所有这些都可以被分为公共媒体(如一小组专业人士制作的视觉信
息或印制的传播信息)和个人媒体(如普通人的信件或电话),而现在
这两种模式已经融合在一起了。
互联网是后古登堡经济时代的第一个公共媒体。你根本无须理会互
联网的内在工作结构,只需体会它与此前500年间的媒体模式的不同之
处就足够了。因为所有的数据都是数字化的(用数字表达),所以不会
再存在类似于副本的情况。无论是一封电子情书还是一篇无聊的公司报
告,每条数据与同一数据的其他版本都是完全一样的。
你也可以看到这一点在日常生活中的体现。没有人会说,“给我一
个你电话号码的副本”。你的电话号码对每个人来说都是一样的。由于
数字这个奇异的特质,旧有的区分专业和业余人士的副本制作工具的方
式不复存在。过去印刷机为前者制作高质量的版本,复印机为我们复制
其他的东西,而现在每个人都能利用媒体制作完全一样的版本,以至于
旧有的鉴别方式根本无法分辨同样精准的原版和复制版。
另外,数码制作的方法是对称的。发射信号的电视台耗资巨大、配
置复杂,而接收信号的电视机却相对十分简单。当有人买了一台电视机
时,消费者的数量增加了一个,但创造者的数量并没有发生变化。而当
有人买了一台电脑或是一部移动电话时,消费者和制造者的数量都增加
了一个。天才的分布仍然是不平衡的,但是简单的制造和分享的能力现
在变得广为分布并连年扩大。数字网络不断增加着所有媒体的流动性(fluidity)。原本只能在单
向公共媒体(如书籍和电影)和双向个人媒体(如电话)间进行的选
择,如今扩展出了第三个选项:从个人到公众的可延展的双向媒体操
作。 各个群体可以在像广播一样的媒体环境下交流对话。这项新的选
择在原有的广播媒体和通信媒体间架起了一座桥梁。所有的媒体可以相
互转化。
一本书可以同时在一千个不同的场所引发公众的讨论;一封用于对话的电子邮件可以被参
与者公布出来;一篇供公共消费的文章可以引发私下的争论,而其中的部分内容也许日后也会
公之于众。曾几何时,像收音机和电话这样的公共媒体和个人媒体使用截然不同的设备和网
络,但现在我们正以从前从未企及的方式在个人媒体和公共媒体间不停地转换。
最后,新的媒体形式囊括了经济学的转变。互联网造成的情形是,每个人都在付费,然后每个人都得以使用。互联网并非单由一家公司所
有,并单独经营其整个体系,它只不过是一系列有关如何进行两点间数
据传递的协议。任何遵从此类协议的人,无论是个体的手机使用者还是
经营一家大公司的人,都可以成为网络的合格成员。网络基础设施并不
归网络内容制作人所有,它属于任何一个付费使用网络的人,无论出于
何种使用方式。这种向后古登堡经济学的转变很大程度上为我们所见
的慷慨、公开、有创造力的行为提供了便捷的方式,它有着可互换的
完美版本,彼此对话的能力,对称的产出和低廉的成本。
做“酒吧”里的业余人士
由于我们所了解的公共媒体直到最近为止都受到古登堡经济学的限
制,因此无须思考,我们就能估量到媒体亟待专业人士保证其存在的事
实。我们认定,我们作为受众,不仅仅被移交到被动消费的地位上,而
且喜欢这样的地位。在我们头脑中有关媒体业的潜在理论的指导下,前
述那种慷慨、公开而又极富创造力的行为看起来着实令人费解。与很多
令人讶异的行为类似的是,这种错误行为主要源于将某一偶然事件的发生当做是一个深刻的真理。
大家分享各自的作品、视频、病症甚至是车上空位的动机并不是对
金钱的渴求。有人经营像YouTube和facebook这样的服务是想要获利,而他们确实也做到了。业余爱好者无偿提供作品给那些通过收集和分享
这些作品来获取利润的人,这似乎很不公平,至少传统媒体的经销商会
付款给他们的撰稿人。在这种非专业人士能够分享作品的新服务形式
下,获益的不是心满意足的作者而是提供分享平台的所有者,这就导致
了一个明显的问题:为什么这些人要无偿劳动?尼古拉斯·卡尔
(Nicholas Carr)
[9]
称这种形式为“数字化佃农” (digital
sharecropping),在美国内战后的时期,佃农是那些在土地上耕作,但
既没有土地所有权也没有产品拥有权的农民。在数字化佃农形式下,平
台的拥有者赚钱,而写东西的人却赚不到,卡尔认为这种形式明显不公
平。
奇怪的是,真正遭受这种不公平待遇的当事人却并未对此表示义愤
填膺。那些分享照片、视频以及文章的人并没有期待回报,他们只是想
要分享而已。对于数字化佃农的不满在一定程度上只是专业人士的嫉妒
——明显是专业媒体制作人对业余玩家的竞争感到不安。但是也有另外
一个更深层次的解释:我们在使用一个专业媒体的概念来指代种种业
余人士的行为,而非专业媒体人的出发点和专业人士有着本质上的不
同。 如果我们把提供“大笑猫”的网站ICanHasCheezburger看做是15世纪
印刷模式的现代版模型,那么网站的工作人员无偿付出劳动的事实就不
仅仅令人讶异而更是有失公允。然而如果这些撰稿人不是工作人员又会
怎样呢?要是他们确实就是义务奉献,他们的撰稿行为纯粹是资源共享
而非商业出版又怎么样呢?要是他们的劳动是爱的奉献又该如何呢?
“大笑猫”可以被看做是一个传统媒体的路径,但这不意味着它遵循与《时代周刊》这样的
专业媒体路径相同的内在逻辑。打个比方,“大笑猫”就像是一个本土的小酒吧。酒吧是商业化
经营,那里卖的东西通常都是把便宜得多的东西加大利润出售。酒保提供的服务无非是开酒、洗盘子。如果酒吧里一杯啤酒的价格是商店里的两倍的话,那人们为什么不将酒吧关掉而直接
选择在家喝更便宜的啤酒呢?
如同YouTube的所有者一样,酒吧老板经营的奇妙之处在于他提供
比他兜售的商品和服务更有价值的东西,他的价值是消费者自己为彼此
创造的。人们愿意多花钱在酒吧喝酒而不在家独饮,是因为酒吧轻松的
氛围更适合喝酒。酒吧吸引那些想找人随便说说话或者仅仅是喜欢有人
在周围的人。和一个人在家相比,大家更喜欢呆在酒吧里面。这种诱惑
力足够大,两者间的差异也值得偿付。“数字化佃农”的逻辑意味着酒吧
老板在剥削他的消费群体,因为消费者在酒吧的交流是他们愿意多付酒
钱的原因之一。但事实上没有一个消费者的思维方式是这样的。相反,他们更愿意认为酒吧老板开辟了一个便于交际、饱受欢迎的环境,在这
样的环境里他们更有机会彼此交流,为此他们愿意多付些钱。
然而,“数字化佃农”的逻辑有时也的确适用,有时人们的感受也正
如卡尔假设的那样。“数字化佃农”影响最大的实例之一来自美国在线
(America Online,AOL)网络服务的志愿者们。
在20世纪80和90年代,美国在线迅速成长,因为人们发现其友好有益的形象很吸引人。它
的社区领导者们,一个完全自发组成的群体,经常出现在公共聊天室和其他场所,引导讨论、关注侮辱或诋毁的语言、在总体上维护大局平稳。1999年,这些领导人中的两个,布莱恩·威廉
姆斯(Brian Williams)和凯利·哈利塞(Kelly Hallisey)代表一万志愿者起诉美国在线,要求后
者至少应该为其劳动支付最低薪水。
假设威廉姆斯、哈利塞以及其他所有的领导人都自愿奉献他们的时
间,而且数十年如一日(威廉姆斯估计他所贡献出的时间有数千小时之
多),那就很难明白为什么后来他们会觉得自己遭受了虐待。答案在于
究竟是什么产生了变化,就如同某段关系变质了一样。在一次采访中,威廉姆斯痛斥在线服务的商业化。“现在的情况越来越像是公司试图从
原本免费的奴隶劳工身上榨取每一个美元。从前,在网站上没有现在这
些无处不见的广告,网站就是一个丰富的社区,人们为了在一起而在一
起,现在的情况完全变了。”这种从社团驱动到广告驱动的变化改变了领导者们的感受。当美国在线不再对他们的劳动提供看得见的欣赏后,他们开始套用“数字化佃农”的逻辑。(该诉讼到目前为止已经经历了第
二个十年,涉及数千名前任社区领导,至今尚未得到判决。)
人类对彼此联系有着内在的看重。基于这种现实,“数字化佃农”的
逻辑就丧失了其大部分的说服力。业余人士不是专业人士的缩小版。人
们有时乐于因金钱以外的原因而去做一些事。业余媒体与专业媒体不
同。帮助我们分享的服务之所以兴旺发达,就是因为这些服务使我们原
本就喜欢做的事现在操作起来更便捷和便宜。换句话说,市场的作用之
一就是为我们在市场之外所专注投入的事情提供平台,这个平台的形式
可以是酒吧,也可以是网站。15世纪的媒体制作模式尚不允许这样的分
享存在,因为其本身的成本和风险都导致需要有专业人士参与到运作的
每一个步骤中,而现在则不一样了。
工具,赋予我们行为发生的可能
我在纽约大学的互动电信项目(Interactive Telecommunications
Program)中任教,这是一个跨学科的研究生项目。在我任教的那些年
里,我的学生的平均年龄基本保持不变,而我的平均年龄却连年以惊人
的速度递增。现在我的学生都要比我小上15岁20岁。由于我一直以来都
在试图传递一种观念——媒体在不断地演变发展,因此我现在不得不把
我年轻的时光当做历史一样教授给我的学生们。看起来在我的学生们还
没到15岁之前,我成长中所经历的稳定的时代就已经结束了,这些孩子
们还在上小学的时候,我就在以成人的眼光看待媒体的变革了。
尽管近半个世纪以来,媒体一直在收缩,但我的学生对媒体范围的
了解还仅仅局限于信息量的不断丰富。他们从来都不知道曾经存在过这
样的媒体世界:电视里只有三个频道,傍晚观众唯一的选择是观看白人
用英语读报纸。他们可以理解这种从稀缺到过剩的转变,因为今天我们
还在经历这样的过程。但还有一件更难对他们解释清楚的事就是:如果你身为一名生活在那样的世界里的公民,当你觉得自己有必要公开发表
点意见的时候,自己却没有这样的权利。就是这样,媒体内容不是由用
户创造的。如果你有足够的资本可以在公开场合发表言论的话,那么从
严格意义上讲,你就已经不再是一名用户了。影评出自影评人,公众舆
论来自专栏作家,报道来源于记者。适于凡人谈话的空间仅仅局限于餐
桌和饮水机旁,偶尔会以书信的方式(这个方式太麻烦也很少见,以致
很多书信都是以“很抱歉这么长时间没有写信给你了”这样的话开
头……)。
在那个时候,任何人都能拍照片、写文章、创作歌曲,但是他们无
法令其创作出来的东西广泛流传。向公众传递信息是一件公众无法做到
的事情,由于缺少彼此轻易就能发生联系的能力,我们创作的动机都被
压制住了。对广播和印刷媒体的接触是如此受限,那些尝试制作点什么
的业余人士要么被猜忌,要么受到怜悯。自费出版作品的作者不是被当
做有钱人,就是被认做爱慕虚荣。发行小册子或是举着标语游行示威的
人都被当做精神错乱。《纽约时报》已故专栏作家威廉·赛菲尔
(William Safire)归纳出这种划分的界线:
数年来我屡次开车穿越马萨诸塞大道,途经副总统的家时,都注意到一个形单影只、意志
坚决的男人穿越这条街,他举着条幅说他被牧师鸡奸了。我断定那人一定是个疯子,但也正因
此我忽略掉了本世纪最大一桩宗教丑闻的线索。
当我告诉我的学生们普通群众的沉默都是装出来的时候,他们纷纷
表示赞同。但即便他们能够从智力上明白那个世界,我仍旧可以感觉出
来,他们对那个世界缺乏切身感受。他们从来都没有生活在一个不能公
开发表言论的世界里,他们很难想象那样的世界与如今他们视为理所当
然的参与行为环境究竟有何不同。
英国广播公司记者尼克·高英(Nik Gowing),在关于媒体危机的
《“漫天谎言”和黑天鹅》(“Skyful of Lies” and Black Swan )一书中,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2005年7月,伦敦地铁和公交车发生爆炸后的几个小时里,政府坚持认为是某种功率骤增造
成了此次巨大的损毁和伤亡。即便就在几年前,这种解释仍是公众得以知道的唯一信息,这也
给足了政府时间,令其在编造好反映事实真相的故事之前做好充分的事件调查。但正如高英所
说,“在公有领域(public domain)内,在前80分钟时间里,有1 300篇博文示意事件的起因是爆
炸物。”
当谎言对所有人都显得越来越明显的时候,政府实在无法坚持说事
件是由功率骤增造成的。可拍照手机和照片分享网站的全球化,使得公
众可以看见地铁的内部以及双层公共汽车的顶盖被炸得粉碎的影像——
证据与官方的解释完全不符。爆炸发生后不到两个小时的时间里,伊恩
·布莱尔爵士(Sir Ian Blair),伦敦市区警察局长官,公开承认此次爆
炸是恐怖分子所为。尽管他尚未完全掌控局面,他的助手也不赞成他这
样做,但他还是公开承认了,因为人们没等他开始说就已经试图去了解
事件真相了。此前,警察的选择是“我们要不要告诉公众点什么”,到
2005年,则变成了“我们要不要成为公众谈话中的一部分”。布莱尔决定
一开始就告诉公众真相,因为旧有的假定公众内部不会产生讨论的策略
已经失效了。
对我们的新举动感到惊讶的人们,认为行为是一个稳定型的东西,但事实并非如此。多年来人类少有动机上的变化,但是机会总是随着
社会环境或多或少发生着变化。在机会变化小的世界里,行为的变化
也就很小,但当机会有了大的变动,行为也会随之变化,只要这个机
会诉诸了人类的真实动机。
对认知盈余的利用使人们得以用更慷慨、更公开、更加社会化的方
式来表现自己,而不再保留自己原有的身份,比如用户和电视迷。这种
变化的原材料是我们的空闲时间,这样的时间我们可以用来投入到各个
事业中去,从娱乐到文化变革。然而,如果我们需要的只是空闲时间,那么现在的变革半个世纪前就该出现了。现在,我们还拥有任由我们支
配的工具,以及这些工具所提供给我们的新机遇。并不是我们的工具塑造了我们的行为,但是工具赋予了我们行为
发生的可能。 当今灵活变通、便宜便捷、万象包罗的媒体提供给我们
各种前所未有的机会。在“媒体”的世界里,我们就像孩子一样,安静地
在边上围坐成一圈,吸收着圆圈中央大人们为我们创造的一切。但现
在,这个旧世界已经让位于一个全新的世界,在这里大多数形式的交
流,不管是公开的还是私下的,都以某种形式可为任何人所用。尽管我
们接受这些新的正在发生的行为,而且新型媒体也为其存在提供了新的
方式,但我们仍旧需要解释原因。只有能帮助人们做其想做的事情时,新的工具才得以被利用。那么,到底是什么激发了这些从前作为受众的
人们开始参与到媒体活动中呢?
[1] 2005年10月,韩国政府发布和修改了《促进信息化基本法》《信息通信基本保护法》等法规。2006年底,韩国
国会通过了《促进使用信息通信网络及信息保护关联法》,规定韩国各主要网站在网民留言之前,必须对其身份证号等
信息进行记录。——译者注
[2] 口袋妖怪,日本任天堂公司于1996年推出的一款游戏。——译者注
[3] 德国莱茵兰·普法尔茨州首府和最大城市,位于莱茵河左岸,正对美因河注入莱茵河的入口处。——译者注
[4] 马克辛·洪·金斯顿,又名汤亭亭,华裔美国女作家,《女勇士》是其代表作。——译者注
[5] 这一系列词都含有“publi-”这个前缀,与“public”同源。——译者注
[6] 马丁·路德,16世纪欧洲宗教改革倡导者,新教路德宗创始人。——译者注
[7] 美国著名女权主义作家兼学者。——译者注
[8] 洪都拉斯首都。——译者注
[9] 美国作家,其著作主要涉及科技、商业以及文化方面,代表作有《IT不再重要》《浅薄》等。——译者注第3章 无酬的动机
为什么“葛洛班之友慈善组织”的参与者不仅没有报酬,还会搭上自
己的钱,却乐此不疲?为什么一群业余爱好者做的连专业设计师作品的
边儿都够不着的网站,会风靡美国?网络意味着我们最终发现,人们真
正感兴趣的领域是如此之广阔,广阔到疯狂的地步。数字网络让分享变
得廉价,让全世界的人都成为潜在的参与者。想要分享的动机才是驱动
力,而技术仅仅是一种方法。
内在动机是一张包罗万象的标签,把人们可能从一项活动中获得的
或基于活动本身的回报所造成的各种激励因素聚集在一起。
过去组织的门槛非常高,而如今这些障碍已经被大大削弱,我们中
的任何人都可以轻易地找到志同道合者。
驾驭我们认知盈余的手段是我们获得的一种新工具,它可以使参与
成为可能并给参与者带来回报。
乔希·葛洛班(Josh Groban)是受过古典训练的专业男中音歌唱
家,演唱那些被称做古典混合乐或是流行歌剧(popera,pop 与 opera的合
称)的歌曲,这是一种颇受欢迎的曲风——把一些歌剧的标准曲目的风
格,如《圣母颂》(Ave Maria ),融入到充满灵性的意大利和英国流
行音乐,如《在阳光下》(Alla Luce Del Sole )、《为了你》(Per Te )
和《举起我》(You Raise Me Up )中去。葛洛班非常成功,到目前为止,他的4张专辑在美国都创造了200多万张的销量。他有才华、充满激情,而又魅力四射,他的粉丝团上至奶奶级别,下至青春少女。换句话说,他所拥有的听众,用传统媒体是很难聚集在一起的,因为没有一个广播
节目会覆盖如此广泛的年龄段。这使得葛洛班写下了一个成功利用网络的故事。像东方神起一样,他的歌迷通常会网罗新的歌迷。歌迷们用一种口口相传的营销模式迅速
为他做宣传。你可以在JoshGroban.com 上见到他们,在那里骨干粉丝团
称自己为 “葛洛班之友”(Grobanites), 所有有关葛洛班的事情则被叫
做“班务”(Grobania)。
如今,一个艺术家利用网络寻找粉丝的故事屡见不鲜,有意思的
是,粉丝们聚在一起的时候会发生些什么。
2002年,一些“葛洛班之友”计划在葛洛班21岁生日的时候送他礼物。礼物的选择让粉丝们
很为难:毕竟,他们喜欢的人是一个年轻的成年男人,并且这个男人已经得到了名望、财富和
无数的仰慕。他还想要什么呢?经过“葛洛班之友”们的一番讨论,很多想法被驳回,比如一个
男人需要多少泰迪熊呢?茱莉·克拉克(Julie Clarke),“葛洛班之友”之一,提出了募捐的建
议,以葛洛班的名义进行一次慈善捐款。他们决定把所筹善款捐给大卫·福斯特基金会(David
Foster Foundation),该基金会是一个慈善团体,由葛洛班的制作人经营,帮助弱势群体中的青
年人。克拉克同意承办这次捐赠,并最终筹集到了1000多美元的善款。葛洛班很惊喜,大卫·福
斯特基金会也很高兴,捐款的人也洋溢着成就感。
看到这次的成功,克拉克和另一位在筹集资金活动中认识的“葛洛
班之友”瓦莱丽·索奇(Valerie Sooky)一起把筹集善款当做“班务”的一
部分。每当葛洛班巡回演出的时候,他的粉丝都会在演唱会前聚在一起
欢迎他。“葛洛班之友”们在每次这样的聚会时都会进行募捐,每次往往
都会募集到上百美元。这类募捐使得粉丝们每年可以聚一次,但
JoshGroban.com每天都在进行着募捐。因此,克拉克建议举办一场在线
慈善拍卖为葛洛班明年的生日做准备。她和索奇拉来了梅甘·马库斯
(Megan Markus),这个19岁的“葛洛班之友”热切希望能够帮忙设计拍
卖网页。所有这一切显然都是业余爱好者的“杰作”:这是马库斯第一次
做网页设计的工作,很多拍卖物都是“葛洛班之友”自己做的或是捐出来
的。拍卖系统很笨拙,所有的叫价都不得不手动输入。最后,在花了几
个星期学会运行不熟悉的软件之后,这些“葛洛班之友”们举行了第一次
拍卖。几天下来,他们筹集到了16000美元,比以往任何一次募捐筹到的
钱都多。接着,他们进行了一场又一场拍卖。一年中,他们募集到了
75000美元。为葛洛班下一个生日进行的捐款使筹款额达到了顶点,仅
此一次就筹到了将近24000美元。
克拉克、索奇和马库斯意识到她们做的事情非常有意义。钱还是源
源不断地进来,但当每个人都高兴地支持大卫·福斯特基金会的时候,资金却并不是由福斯特的人筹来的。因此,他们问葛洛班,他们怎么样
才能更加紧密地一起工作。这对葛洛班的律师来说是一个挑战,因为这
确实是一桩新鲜事——艺人建立慈善组织通常是由艺人自身提供资金
的,因此,并没有有组织地从粉丝那里接受捐赠的先例。
最终,葛洛班的律师根据501(c)3条款
[1]
,创建了一个非营利性的
公司,并起了一个虽缺乏想象力但很实用的名字:乔希·葛洛班基金会
(The Josh Groban Foundation)。其主要职能是建立了一个合法的募捐
渠道,使得有慈善心的“葛洛班之友”们以葛洛班的名义募捐,使基金会
得到捐款,然后分配钱款。一时间,这个公司运行得很好——“葛洛班
之友”们继续募捐并且确定有价值的新的受益人(目前同基金会合
作)。
到2004年,慷慨的“葛洛班之友”们发展得比基金会本身还要快,作
为一种支付钱款的引擎,没人能联系到基金会中的人,甚至连一个邮箱
地址都没有,而随着“葛洛班之友”人数不断增加,内部管理问题也变得
更加复杂。当组织在规模、年限、抱负上增长的时候,类似的事情总会
发生。对“葛洛班之友”来说,三个问题同时出现了。建立者探讨着该怎
样处理新出现的复杂情况:他们是应该变成乔希·葛洛班基金会的志愿
者分支还是成立他们自己的组织?经过一年多的讨论(临时性的小组经
常会在一起讨论),他们是粉丝、想要联系更多的粉丝这一事实左右了
他们的决定。“我们是他们中的一员,他们认识我们,他们相信我们。”后来索奇跟我解释的时候这样说。最终,他们建立了一个自己的
非营利性组织——“葛洛班之友慈善组织”(Grobanites for Charity)。
最初的生日募捐和开始时的社会责任最终促使了两个组织的建立,目前两个组织组成了一个整体行使职能:“葛洛班之友慈善组织”筹集资
金,“乔希·葛洛班基金会”分配资金。
与传统的慈善机构相比,“葛洛班之友”的一切都背道而驰。通常的非营利组织,像“救助儿
童”(Save the Children)和“塞拉俱乐部”(Sierra Club),都是先建立组织,再招募成员;先成
立机构,再筹集钱款。“葛洛班之
友慈善组织”却是先有成员,再有目标,在成立机构之前,其成员就已经在筹集善款了。并
且,建立者甚至是在他人解决了所有的法律问题后才成立机构的。
葛洛班之友的成功接踵而来。其他的“葛洛班之友”团队也开始做慈
善工作。“葛洛班之友为非洲”是“葛洛班之友慈善组织”下的一个尚未被
承认的分支机构,为对抗非洲的贫穷和艾滋病而努力。这个团队是在葛
洛班全球巡回演出第一次到南非之后建立的。在那里,葛洛班见到了纳
尔逊·曼德拉(Nelson Mandela),并宣布为了非洲儿童支持慈善事
业。“葛洛班之友”中准备欢迎他到亚特兰大巡回演出的一队人决定,为
了葛洛班的这个目标单独组成一个机构,同其他“葛洛班之友”以及乔希
·葛洛班基金会紧密合作。至今,“葛洛班之友为非洲”已经筹集到了15
万美元的善款。
对于“葛洛班之友慈善组织”来说,最重要的问题不是“他们哪儿来
的时间开展慈善事业”,我们知道“葛洛班之友”有自由的时间,也能够
在他们想要联系媒体的时候与媒体联系上。“他们怎么协调各个团
队?”这个问题也不重要。该问题的答案我们也很熟悉:JoshGroban.com
为人们提供了一个聚会、分享想法和目标、彼此鼓励的场所,也给予他
们一个招募志同道合的“葛洛班之友”的机会。
令人迷惑的问题是“为什么”。为什么这些女性把筹集钱款放在第一位?为什么在乔希·葛洛班基金会已经存在的基础上,“葛洛班之友慈善
组织”还会成立一个单独的机构?这可不是“大笑猫”,经营“葛洛班之友
慈善组织”是一项艰巨的工作。参与者不仅没有报酬,还会搭上自己的
钱。所有的事情都是在网上进行的,是什么促使人们为了没有明显回报
的东西放弃自己的时间和金钱呢?
热爱胜于金钱
1970年,罗切斯特大学(University of Roshester)心理研究专家爱
德华·德西(Edward Deci)做了一个非常简单但却至今仍有争议的实
验。
这个实验是在一种名为“索玛”(Soma)的解谜游戏的基础上进行的。索玛立方体是一个木
质立方体,能分为7小块。每块的形状都是唯一的,有T型,L型等。这7小块只有一种方法才能
组成一个大立方体。此外,它们也能组成数以百万计的其他形状。索玛立方体的玩法是对照着
要组成形状的图纸,然后把这7小块组装成图纸中的形状。实际做起来比听上去要难。德西正是
基于这种玩法来开展他的观察的。
实验伊始,德西把索玛木块和能用它们拼成的三四种形状的图纸给
实验参与者们。当被试(都是男性)熟悉了那些小木块时,德西便让他
们把这些木块拼成图表中那三四种形状,但没有告诉他们如何组装。德
西对数十组被试都重复了这个过程,所有被试都以为组装这些形状就是
实验本身。事实上并非如此。在做出说明并对被试们观察了大半个小时
后,德西会离开教室,告诉参与者们休息一下并等他回来。在他离开教
室的时候,德西通过一面单面镜对被试观察了整整8分钟。被试们在这
休息的8分钟内的行为才是实验的真正内容。
当德西不在的时候,被试们可以自由活动。德西在实验室里放置了
杂志和其他设施(因为那是20世纪70年代,因此杂志包括《纽约客》
《时代》和《花花公子》,外加一个烟灰缸)。尽管这些东西很容易拿
到,但仍有很多被试继续自觉地玩着这个解谜游戏,在这8分钟里他们平均花4分钟在索玛上。德西返回后便解散了被试,记录下他们在休息
时的活动,并以此做为实验的参照。
而后德西邀请同一批被试进行了第二批索玛解谜,但其中有一点不
同。这次他让一半人和上次一样解谜;而对于另外一半,他告诉他们每
拼出一个图案就能得到一美元(在那个年代一美元对参与实验的学生来
说很值钱)。同样他们会被要求休息,留在实验室里被秘密地观察8分
钟。那些知道立方体可以成为他们潜在收入来源的被试平均比他们先前
在休息时间钻研索玛立方体的时间多了1分钟。
然后德西又做了第三个实验,这次他只是简单地重复了他最初做的
那个实验:所有被试都被要求组装图案,并且没有人会得到收入。在这
个阶段,尽管他们每人都收到同样的指令,但那些在前一个实验中获得
收入的人们,在休息时对组装图案的兴趣比他们能获得收入时的情况明
显下降。他们在索玛上花的时间平均下降了2分钟,也就是说在收入被
剥夺后,他们的关注时间下降了两倍,正如当收入被计入实验时,他们
的关注时间上升了两倍一样。尽管在第一个实验中他们会自觉地玩这个
解谜游戏,但当他们又一次有机会自觉玩游戏时,先前获得收入的记忆
很轻易地就降低了他们的兴趣。
在心理学文献中,为了阐释自愿参与而设计的实验被称为“自由选
择”(free choice)测试——当某人能控制自己的行为时,他有多大的可
能会表现出一种特定的行为?德西的索玛实验发现,解谜游戏的报酬会
降低同一行为的自由选择度。
德西的结论是,人类的动机并不纯粹是附加性的,为了兴趣而做
事和为了报酬而做事是截然不同的。 这个实验证实了一个心理学理
论,动机分为两大类——内在动机和外在动机。内在动机能让行为本身
就成为一种回报。 在索玛立方体的案例中,那些在休息时继续解谜的
参与者们很明显是被拼装成功的满足感激起了兴趣。而对外在动机来说,回报来自于行为之外,而不在于行为本身。 报酬就是外在动机的
一个经典例子,这也正是为什么让参与者通过拼装图案来得到报酬的原
因所在。
得到丰厚的报酬可以让原本不受欢迎的行为变得受欢迎和划得来
(因此社区里才能雇用到垃圾工)。但德西的实验提出,外在动机并不
总是最有效的动机,增大外在动机实际上可能降低内在动机。他断定,像得到报酬这样的外在动机能驱逐像喜欢该事物本身这样的内在动机
(一种动机驱逐另一种动机的概念也存在于关于电视观看的文献中——
看电视驱逐了社交活动)。
自那以后,其他研究者也开始了对驱逐效应(crowding-out effect)
的研究并得到了类似的结论。
1993年,布鲁诺·弗雷发现,当瑞士居民被问起,如果政府要在他们的生活区域里建造一座
核废料贮藏库,他们是否会赞成该计划时,对这个问题的赞成和反对之声基本持平。当弗雷改
述了这个问题,告诉他们如果建造废料贮藏库,那么政府可能给他们发放补贴时,民众态度反
而变成了以三比一的比例反对这个计划。当建立废料贮藏库变成一种能获得政府补贴的行为,而不是一种公民义务时,这种行为不受欢迎的程度上升了两倍。
弗雷和他的同事洛伦茨·戈特(Lorenz Goette)最近的研究表明,在
真实世界中,当钱被用来作为志愿行为的回报时,它会降低志愿者贡献
的平均劳动时间。马克斯·普朗克考古人类研究所(Max Planck Institute
for Evolutionary Anthropology)主任迈克尔·托马塞罗(Michael
Tomasello)最近出示了一些实验性证据证明,把外在的报偿和14个月
大的婴孩喜欢的活动联系在一起,而后又将其取走时,这种驱逐效应在
他们身上也会发生。
出发点是兴趣还是金钱,会让人们在做事时表现得不一样,这一观
点似乎并不会让那些既有工作又有业余兴趣的人感到惊讶,然而心理学
界却有很多人认为德西的结论并非真理。1970年,人类动机理论以及在教室和工作场所对报酬的实际应用,常常基于简单的刺激观念——对现
有活动增加新的酬劳能让人干得更多。这一构架几乎没有对不同的动机
进行区分,并且现钞始终是一种具有最多功能的刺激因素。德西关于酬
劳能驱逐其他动机的结论对已有理论和实践是个公然的违抗,他对驱逐
效应的实验和其后的研究提出了一种学术性异议,这一异议一直持续至
今。
1994年,阿尔伯塔大学(University of Alberta)的朱蒂·卡梅隆
(Judy Cameron)和大卫·皮尔斯(David Pierce)分析了一系列实验参
与者完成各种任务并获得报酬的研究结果。他们的元分析(将多个研究
结果进行分析的称谓)彻底否定了这种驱逐效应的存在。德西和他的研
究伙伴理查德·瑞恩(Richard Ryan)于1999年做出回应,他们指出卡梅
隆和皮尔斯的分析中包含了许多诸如“若你支付报酬,人们就会被激励
着去完成他们不感兴趣的任务”这样的研究,这些结果本就毫无争议。
而德西所调查的是内在动机对一件参与者感兴趣的事情的影响。德西和
瑞恩自己的元分析在去除了一些令人厌烦的任务后,又一次发现了驱逐
效应。卡梅隆和皮尔斯在2001年的第二次元分析中承认对自由选择的驱
逐效应可以在外在动机介入的时候产生。尽管如此,卡梅隆和皮尔斯仍
对驱逐效应在真实世界中是否重要保持怀疑。他们关注的主要是院舍式
环境中出现的报酬,譬如学校和工厂。对他们而言,驱逐效应似乎集中
在人们有很大自由来选择自己行为的环境中。因此卡梅隆和皮尔斯认定
虽然驱逐效应是真实的,却也是小众的。毕竟,有多少地方能让人们对
行为的自由选择仅仅和自己有关?
然而,在一个自由时间和才能已经是相互联系的资源的时代,这个
问题的答案是“到处都是”。
自治和胜任感
德西对于内在和外在动机以及金钱驱逐兴趣的理论框架,很清晰地
解释了葛洛班之友慈善组织。当涉及到对善款去向的决定时,慈善机构
间的差异非常大:有多少钱能流入实际受益人手中,有多少用于日常运
营花费,其中包括机构管理人的薪水。美国慈善协会(The American
Institute of Philanthropies)把那些将募集到的善款的40%作为运营费
用,另外60%用于慈善事业的慈善机构定义为合格——不糟糕,但也不
算好,而运营费用控制在15%,捐献出85%善款的慈善机构则可以被评
为优秀。那么葛洛班之友慈善组织呢?他们会提取从伙伴中募集而来的
善款的百分之多少用于运营呢?答案是百分之零。他们卖很多力气,但
并不从中获得薪水,甚至愿意投入尽可能多的时间和金钱。葛洛班之友
慈善组织并非一种偶然形成的热爱,而是经过设计和“共同努
力”(incorporated)的热爱行为。实际上“共同努力”这个词就是“付诸实
践”(embodied)的意思——共同努力就是一个群体将努力和目标付诸
实践的具体表现。
内在动机是一张包罗万象的标签,把人们可能从一项活动中获得
的或基于活动本身的回报所造成的各种激励因素聚集在一起。 德西把
两种内在动机标注为“个人的”:自治的愿望(指决定我们做什么,怎
么做)和有胜任感的愿望(指能够胜任我们所做的事)。 在索玛实验
中,在休息时间仍然继续组装那些方块的学生就是受到自治的愿望(工
作在他们掌握之中)和有胜任感的愿望(索玛立方体是一种通过持续努
力就能在技术上有所提高的游戏)的推动。这一发现在游戏中十分典
型。一个关于电子游戏的研究表明,最吸引玩家的并非游戏中高仿真的
画面和暴力场景,而是玩家在精通这个游戏后能够控制并胜任它的感
觉。
另一方面,通过组装方块来获取报酬的那一组人的内在动机消失了。他们对于自治的感觉由于可以预见的外在动机的出现而被驱走了。
同样,基于胜任的愉悦感一旦被报酬所影响,就不再成为一种愉悦。当
他们提高解谜能力是出于增加报酬的目的时,那么基于游戏本身来完成
同样的任务就失去了足够的价值,这也就破坏了人们的自由选择。
同样地,葛洛班之友慈善组织和乔希·葛洛班基金会也并非仅仅在
合同和薪水方面有区别。这两个组织在保留葛洛班之友内在动机的方式
上,每一个方面都不一样。
例如,葛洛班基金会甚至没有自己的网站,它只在JoshGroban.com网站上有一个登载简讯
和新闻稿的小小板块,干净、专业、充满极简主义。而葛洛班之友慈善组织的网站看上去则完
全不一样,它就像1996年那个年代匆匆建立起来的东西,一圈套一圈,这种调调在早年的网站
设计中很普遍——手绘的心形列表,提示浏览部分的彩色标签,等等。换句话说,它看上去很
业余,而实际上它就是由业余爱好者创立的。它不但“不专业”,而且是出于“业余爱好”这个词
的本意而被创立的:某人出于热爱而做一些事情。
马库斯从十几岁时开始就一直为葛洛班之友们设计网站,最早的拍
卖网站就是她的第一项成就,为葛洛班之友慈善组织设计网店是一笔很
可观的学习经验。在工作中学习,看上去可能和感觉到胜任感的愿望背
道而驰,但是胜任感是一种移动目标。
接手一项过于庞大繁复的工作可能会让人泄气,但接受一项过于简
单、毫无挑战的工作同样令人感到无趣和无精打采。胜任感最容易产生
于当工作处于能力范围边缘时。“我自己完成了一件不错的事情”的感觉
总是比“请专业人士替我完美地完成了这件事”的感觉要好得多。
这种效果很普遍。追溯到最初的网络年代,一个叫做Geocities的网
站为它的用户提供个人主页,人们可以在主页上发表文章、图画和照片
等任何东西给别人看。这个网站启动的时候,我正在纽约为一家网络设
计公司管理制作部门,当时我很确信Geocities会倒闭。我看到过为了设
计一个有用的网站而进行的大量工作,从导航、设计到排版,我知道一
群业余爱好者做的东西甚至连专业设计师作品的边儿都够不着。当时网络上遍布专业网站,没有人会想要他们那些看起来平淡无奇的页面。
我对于Geocities网页设计水平的判断是正确的,但对于它的流行程
度,我的判断大错特错。它很快就成为了当时最受欢迎的网站之一。我
当时没有理解到的是,设计水平并不是衡量一个网站的唯一标尺。网页
并不仅仅需要单一的品质,它们需要各方面的品质。设计简洁固然很
好,但其他方面的品质或许更重要,例如亲自完成一件事的满足感,或
在完成事情的过程中学到了东西。人们不会主动寻求糟糕的设计,这只
是因为大多数人并非好的设计师,但这不会让他们停止自己创造事物。
自己创造的事物就算很普通,和消费别人创造的质量上乘的事物相
比,它仍然有一种与众不同的吸引力。 我对于Geocities所犯的错误,源自于我以为业余爱好者们除了消费以外不会做任何事情——那也是我
最后一次犯那样的错误。
成员资格和慷慨
2006年,哈佛大学法学教授尤海·本克勒(Yochai Benkler)和纽约
大学教授海伦·尼森鲍姆(Helen Nissenbaum)写了一篇标题长得让人一
口气读不下来的论文:《基于公地的对等生产和美德》(Commons-
Based Peer Production and Virtue )。“基于公地的对等生产”是本克勒称
呼那些依靠志愿贡献来运营的系统的术语——那些依靠认知盈余的系
统。他们在文中对这种参与所依赖和鼓励的积极特性进行了阐述。和德
西一样,本克勒和尼森鲍姆关注个人品性,如自治和胜任感。不同之处
在于,德西的索玛立方体实验主要关注个人动机,而他们则花了大量时
间在一种只有我们成为团体中一员才能感觉到的动机——社会动机上。
他们把社会动机划分为宽泛的两大类:一类围绕着联系和成员,另一类
则围绕着分享和慷慨。
在观察了一些参与性的例子,尤其是同伴们通过分享进行的软件开
发(此一模式叫做开源软件)的例子之后,本克勒和尼森鲍姆认定社会动机能加强个人动机;我们新的传播网络鼓励成员加入和分享,两者无
论从自身还是对外部来讲都是有益的,并且它们也能为自治和能力提供
支持。德西早先的索玛立方体实验的确抓住了这一效应的一条线索:
像“你很棒”或者“你玩这个游戏比平均水平好多了”。这些完成索玛立方
体解谜后的口头回报能让他们更好地完成解谜,这种改进甚至在口头反
馈结束后仍能持续下去。口头反馈似乎就像另一种外在报酬,如同金钱
一样。然而当它被很真诚地表达出来,并且出自于某个接受表扬者所尊
敬的人之口时,它就成为了一种内在回报,因为它的形成依赖于一种联
系的感觉。
组织的社会形式甚至可以影响到那些看上去最私人化的议题。凯瑟
琳·斯通(Katherine Stone),一位为遭受焦虑症的妇女谋求福利的倡议
者,注意到了近来越来越多的产后志愿团体通过Meetup.com网站组织起
来,该网站提供的是一种用互联网来协调真实世界中具有相似兴趣者在
线下会面的服务。斯通将这种快速增长的现象解释为:“经历产后抑郁
症的妇女想要并且需要和其他与自己一样的妇女谈心、分享,来证明她
们不孤单,来证明她们会康复。”想要分享的动机才是驱动力,而技术
仅仅是一种方法。
对于个人和社会动机的反馈环可以应用于大多数认知盈余的使用情
形,从维基百科,到拼车网站PickupPal,再到葛洛班之友慈善组织。葛
洛班之友们的捐赠者和支持者们得到了两种信息:我这么做了和我们这
么做了。
在成员和分享方面产生变化的潜力表现在葛洛班之友网站的设计
上。现如今,设计一个网站似乎和形成成员归属感关系不大,但由业余
爱好者设计的东西,实际上可能比专业设计师的设计更好地创造了成员
环境,恰如“大笑猫”网站所传达的信息:你也能玩这个游戏。
作为一种类比,想象一下你在《美丽住宅》和《美好家园》杂志中所看到的各种厨房,它们的设计十分完美,所有的东西都各就各位,所
有的东西都井井有条。我的厨房不是那样的。(没准你的也不是那
样。)但如果你是一次宴会的客人,你可能都不敢踏入一个像《美丽住
宅》里那样的厨房,因为它的设计实际上并不是在向你大声喊着“进来
帮忙吧!”另一方面,我的厨房大声喊出的是“如果你愿意的话,你不必
因为自己拿着刀切胡萝卜块而感到不安。”
马库斯的葛洛班之友慈善组织网站也沿着类似的方向发展。它的设
计和JoshGroban.com相比显得不怎么高雅,但它无论是形象还是气质看
起来都非常有魅力,这个网站的方方面面都体现着这种魅力。首页上各
种各样的链接和你想象的差不多——捐献、拍卖、关于我们,等等。此
外还有一个叫做“感谢您”的部分,看上去像这样:
特别感谢……
·莎丽,她慷慨地贡献出自己的时间来编织款式新颖的运动衫、T恤衫和无檐小便帽来为慈
善筹钱。
·艾伦,她捐献出乔希(和大卫·福斯特)的肖像,为慈善筹得数千美元。
·琳达,她制作了我们葛洛班之友慈善组织的卡片,并把这些感谢卡片寄给大卫·福斯特基金
会的捐 ......
作者授权湛庐文化(Cheers Publishing)作中国大陆(地区)电子
版发行(限简体中文)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书名:认知盈余
著者:(美)克莱·舍基
字数:159 000
电子书定价:29.99美元
Cognitive surplus: creativity and generosity in a connected age by Clay
Shirky.
Copyright ? Clay Shirky,2010互联网新时代的晨光
马化腾
腾讯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
最近有幸读了两本克莱·舍基的书。第一本是《未来是湿的》,相
信大家都知道。
《认知盈余》是第二本。作者不愧为“互联网革命最伟大的思考
者”,他对互联网给人类所带来的行为举止以及文化的变迁洞若观火。
这两本著作一脉相承,它们所探讨的是这样几个问题:
随着全球用户接触互联网的门槛变得越来越低,互联网用户数量变得更加庞大,它们将形
成什么样的社会形态?我们该如何顺应这种变化?而作为互联网的从业者们,又该如何从中寻
找自己的机会?
克莱·舍基应该是一个坚定的“分享主义”倡导者。如果说,《未来
是湿的》告诉我们世界正在进入一个分享的世界,人人都在享受分享所
带来的“红利”,那么《认知盈余》便是在进一步阐述,我们得以分享的
资源禀赋。
任何时候,人们都不缺乏分享的欲望,为什么克莱·舍基会把它作
为一个重点问题来研究?这得益于互联网所带来的技术革命,用通俗的
话来说,就是“天时、地利、人和”。
首先是天时。 互联网的高速运算、处理能力,让每个从业者得以
高效、快速地完成自己的工作。这意味着,每个人可以享受更多工作之
外的时间;
其次是地利。 通讯成本的下降、带宽的增加,让用户接触互联网的成本变得更加低廉。网络不再是少数精英群体的专利,它像水和电一
样,成了生活的必需品;
最后是人和。 接触成本的降低,不可避免地使得互联网用户呈现
爆发式增长,网民和现实生活中的人群,二者的边界变得越来越模糊。
正如克莱·舍基所言,“对网络的传统看法认为它是一个独立的空间,一
个有别于现实世界的虚拟空间……而现在,越来越多的人使用电脑和智
能手机,虚拟信息空间的整个概念都在退化。”
网络世界越来越接近现实世界,意味着基于这个概念建立起来的互
联网商业模式将要被重新架构。
我曾经说过,不管已经出现了多少大公司,人类依然处于互联网时
代的黎明时分,微微的晨光还照不亮太远的路。在这个行当里,不管一
家公司的赢利状况有多么喜人,也随时面临被甩出发展潮流的风险。
发展潮流的漩涡正在席卷我们,网络正在发生演变。过去,我们可
以把网络解读为一种精英享用的新兴工具,它向用户提供的是一个接触
传统精英文化的更加便捷的通道,也就是说互联网是内容的传递者而不
是生产者;现在则不同,每个人都可以成为内容的生产者,互联网作为
一个社会形态的元素,正在为社会源源不断地输出新的内容、制造新的
话题。
“认知盈余”是新时代网民赋予互联网从业者最大的红利之一。 什
么是“认知盈余”,克莱·舍基给出的定义很简单,就是受过教育,并拥
有自由支配时间的人,他们有丰富的知识背景,同时有强烈的分享欲
望,这些人的时间汇聚在一起,产生巨大的社会效应。可以说,facebook、twitter以及维基百科的成功,都是“认知盈余”的功劳。在中
国,微博的兴起,同样有赖于它。参与分享的网民数量越来越多,力量越来越强大,互联网产业也随
之迎来“核聚变”,原来我们所熟知的商业模式,随时可能成为泡影。每
一个从业者必须认识到,如果你不能学会主动迎接,不对这种网民自由
参与分享的精神保持敬畏之心,你就会被炸得粉碎。
一个新的互联网时代即将到来。这将是一个鼓励分享、平台崛起的
时代。靠单一产品赢得用户的时代已经过去、渠道为王的传统思维不再
吃香。在新的时代,如果还背着这些包袱,那就等于给波音787装了一
个拖拉机的马达,想飞也飞不起来。如何铸造一个供更多合作伙伴共
同创造、供用户自由选择的平台,才是互联网新时代从业者需要思考
的问题。 这个新时代,不再信奉传统的弱肉强食般的“丛林法则”,它
更崇尚的是“天空法则”。所谓“天高任鸟飞”,所有的人在同一天空下,但生存的维度并不完全重合,麻雀有麻雀的天空,老鹰也有老鹰的天
空。决定能否成功、有多大成功的,是自己发现需求、主动创造分享平
台的能力。
在这个平台上,用户将是内容的主导者、分享的提供者。每个用
户的知识贡献、内容分享,是这个平台赖以成功、赖以繁荣的重要保
障, “少数人使用廉价的工具,投入很少的时间和金钱,就能在社会中
开拓出足够的集体善意,创造出五年前没人能够想象的资源”。任何有
意打破这种保障的行为,都将受到市场的惩罚。
从去年年底开始,我就一直在思考,如何能将腾讯打造成一个供更
多合作伙伴自由创业、供更多用户自由分享的开放平台。这是一个“摸
着石头过河”的过程,它需要腾讯内外都改变心态,用更加开放的大脑
去迎接变革。这段时间以来,我们已经拥有了一些经验,也总结了很多
教训。无论如何,我相信,这是一条正确的道路。我也相信,坚持走下
去,互联网新时代的晨光就在不远的前方。
最后想说的一点感慨是:互联网真是个神奇的东西。我最近在一部科幻小说中,看到了一段对于“四维世界”的描写,仅仅在熟知的三维世
界上叠加了一个维度,整个宇宙立即变得无比寥廓、无比美妙。克莱·
舍基的每一次发现,其实都是在提示我们,未来人类世界的一个全新
的发展维度。 在互联网的推动下,整个人类社会都变成了一个妙趣无
穷的实验室。我们这一代人,每个人都是这个伟大试验的设计师和参与
者。这个试验,值得我们屏气凝神、心怀敬畏、全情投入。
感谢湛庐文化与胡泳老师,将如此前沿的互联网思想引入中国。认知盈余作为一种可能
胡泳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新媒介批评者
克莱·舍基很勤奋,2008年出版了《未来是湿的:无组织的组织力
量》,仅隔两年,又推出一部力作《认知盈余:自由时间的力量》。
自由时间的利用
《认知盈余》可以说是《未来是湿的》一书的续篇。《未来是湿
的》关注的是社会化媒体的影响;而《认知盈余》的核心主题是,随着
在线工具促进了更多的协作,人们该怎样学会更加建设性地利用自由时
间也即闲暇,来从事创造性活动而不仅仅是消费。用舍基自己的话来
说:“本书从上一本书遗留的地方开始,观察人类的联网如何让我们将
自由时间看待成一种共享的全球性资源,并通过设计新的参与及分享方
式来利用它们。”该书进而分析了这些崭新的文化生产形式背后的路径
和动机,它们无一例外地与人类的表达相关。
舍基对传统媒体在相当程度上采取了鄙夷的态度,他认为,哪怕
是网上最愚蠢和疯狂的创造和分享的举措(例如汇集数千张“大笑
猫”的图片),也比坐在电视机前被动消费数以千亿计小时的节目强。
(根据舍基的统计,美国人一年花在看电视上的时间大约2000亿个小
时。)
认为新媒体与传统媒体判若鸿沟的人通常也强调代际的变化。旧媒
体对新媒体感到不安,很大程度上缘于上一代人对年轻人所拥有的新科技感到不安,尤其是上一代人对于已进入年轻人文化核心的新媒体感到
不安。从过去媒体恐慌症的历史(如漫画、摇滚乐、电子游戏机、电视
等等)来看,大人对网络内容的一切恐惧,不过是来自于对孩子自主与
自行界定媒体品味需求的不安感。比如,年轻人接受游戏,而年长的人
则大多拒绝它。一旦年轻人长大,年长的人逝去,游戏也会像昔日的摇
滚乐成为无足争论之事。所以,反对游戏的人不仅需要面对事实,还需
要面对历史。
舍基这样的新媒体鼓吹者一般坚信,历史站在自己的一边。他观察
到,在电视历史上首次出现了一部分年轻人看电视的时间少于他们父辈
的现象。拥有更快捷的互动媒介的年轻一代正在把他们的行为从单纯对
媒介的消费中转变过来。甚至当他们观看在线视频的时候,看似和电视
没什么两样,但他们却有机会针对这些素材发表评论、分享、贴上标
签、评分或者排名,当然还可以和世界上其他的观众一起讨论。这个区
别实际上是参与同围观的区别:参与者会给反馈,而围观者不会。对参
与社区的人们来说,电影、书籍和电视剧创造的不仅是一种消费的机
会,它们创造的还是一种回应、讨论、争辩甚至创造的机会。舍基把媒
介消费的这种转变称为“净认知盈余”。
导致媒介消费量减少的选择可以是微小的,同时又是庞大的。 微
小的选择是一种个人行为;某人只是简单地决定下一个小时要用来创造
一些事物,而不是单纯地看电视。然而数以百万计的微小选择的集合最
终可能导致庞大的集体行为。全世界的认知盈余太多了,多到即使微
小的变化都能累积为巨大的结果。
而一旦改变了认知盈余的使用方法,我们将不得不重新界定“媒
介”(media)这个词能代表什么。媒介在过去意味着一种商业的集合,今天,由于我们不仅消费,也创造和分享,并且我们还有能力彼此联
系,所以,媒介正从一种特殊的经济部门转变为一种有组织的廉价而又全球适用的分享工具。
舍基最爱讲的故事是一个四岁小姑娘的轶事。他在公开演讲中提过
这个故事,在本书中它也出现了,甚至成为本书最后一章的标题:“寻
找鼠标,世界是‘闲’的”。
这个故事是这样的:舍基的一位朋友和他四岁的女儿一起看DVD。电影放到一半时,小姑
娘毫无征兆地从沙发上跳起来跑到电视机屏幕背后去。他的这位朋友以为她想看看电影里的演
员是不是真的躲在屏幕背后,但是这并不是小姑娘要找的。小姑娘围着屏幕后面的电线绕来绕
去。她爸爸问:“你在做什么?”小姑娘从屏幕后方探出头来说,“找鼠标。”
这个故事可以再一次看出舍基对年轻人使用新媒体的方式寄予的厚
望:年轻人足以开始吸收身处的文化,但是对其文化的前身却知之甚
少,所以完全不必受过去的媒介文化的污染。
消费、创造与分享
关掉电视的人干什么呢?年轻人越来越多地用电脑、手机和其他联
网设备取代电视。这并非简单的硬件转移,而是用户习惯的重大迁移:
人们现在可以一起做很多更有用、更好玩的事情了。
舍基在书中列举了大量协同行动的例子,比如维基百科的编纂就是他最爱引证的证据之
一,还有些例子听上去颇有些匪夷所思:在韩国民众持续抗议进口美国牛肉的事件当中,一群
某个韩国男孩乐队组合的少女粉丝通过在网上的松散联系,竟然几乎迫使政府下台。
对旧媒体、旧机构做事方式的憎厌、对新技术的拥抱以及对下一代
年轻人的期许,所有这些混合起来,导致舍基倾向于讲述从电视中解放
的社会革命故事的一半:在《认知盈余》,以及在更早的著作《未来是
湿的》里面,舍基笔下的几乎所有网络集体行动都是积极的,每个人似
乎都在使用互联网令我们这个世界变得更加美好。对于这样的论证方
式,那些反技术决定论者当然也会乐于举出成打的例子,证明数字科技
在生活品质的创造上,其摧毁能力大于贡献能力。舍基的另外一个问题是,他低估了文化消费的价值。在网络上创造
愚蠢的东西的价值,果真高于阅读一本复杂的侦探小说的价值吗?是不
是只要是创造就拥有了某种神圣性,而只要是消费就显示了低级智慧?
美国文化批评家史蒂文·约翰逊在他2005年出版的著作《坏事变好事》
(Everything Bad Is Good for You )中,曾以游戏和电视剧为例,直接向
下述说法发起挑战:大众文化是一种致人愚蠢的东西。
例如,约翰逊争辩说,情节简单、黑白分明的电视剧早已失去市
场,今天再看《豪门恩怨》,我们会十分惊异于它的天真做作。现在的
电视剧叙述线索纷繁错乱,人物暧昧难明,常常含有需要观众主动填补
的隐喻空间,要靠观众自行猜测人物与事件、人物与人物之间的关系。
甚至连真人秀节目都在调动观众的预测性想象。在这种情况下,电视也
和游戏一样,向人们提出了更高的认知能力上的要求。由此,大众文化
使现代人变得聪明了,而不是相反。
约翰逊的结论很难说是证据充足的,但同样应该指出,那些关于大
众文化消费对大众的头脑充满损害性的责难,也并不完全站得住脚。舍
基低估了创造性生产的质量问题——平庸是创造性生产的供应增加所必
然带来的副作用。由此,我们是不是可以确定,消费一些伟大的文化产
品,要胜于创造另一只“大笑猫”?
在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舍基犯了其他媒介消费的批判者(比如说波
兹曼)所易犯的同样毛病:我们不需要引用德里达的观点也可以知道,文本阅读本身就是一个创造性行为,我们必须不断地向字句的模糊性之
中注入意义。头脑在这里并不是简单地被浪费;我们要怀疑舍基对于创
造的定义:并不是只有我们的想法结晶为物理的或者可见的剩余物才算
是创造。况且,在我们真正创造出任何有意义的产物之前,我们必得经
历一个消费和吸收的过程,并对我们所消费和吸收的进行思考。这也就
是尼采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所言,我们必须先变成啜饮一切水的骆驼,才会成为狮子。
当然,只要舍基不把他对媒介和认知盈余的观察弄得那么两极化,这些批评其实也是无的放矢的。舍基正确地指出,人们使用媒介具有三
种目的:消费、创造与分享。20世纪的媒介作为一种单一事件发展着:
消费。但眼下我们正在越来越多地创造和分享媒介,这是件值得大书特
书的事情。不过,消费的行为并不会全然消失,而是会继续扮演重要作
用。第1章 当自由时间累积成认知盈余
美国人一年花在看电视上的时间约为2000亿个小时,这几乎是2000
个维基百科项目每年所需要的时间。想象一下,如果我们将全世界受教
育公民的自由时间看成一个集合体,一种认知盈余,那么,这种盈余会
有多大?我们已经忘记了我们的自由时间始终是属于我们自己的,我们
可以凭借自己的意愿来消费它们,我们可以通过累积将平庸变成优秀,而真正的鸿沟在于什么都不做和做点儿什么。
庞大的选择是一种集体行为,是数以百万计的微小选择的集合。全
世界的认知盈余太多了,多到即使微小的变化都能累积成巨大的后果。
20世纪,社会生活的原子化使我们远离了参与文化,以至于当它回
归时,我们需要用“参与文化”这样一个词汇来描述它。
将我们的关注点拓展到包括创造和分享,并不需要通过个人行为的
大幅度转变来使结果发生巨大变化。
18世纪20年代,整个伦敦正忙着把自己灌得酩酊大醉。整个城市都
陷入了对杜松子酒的狂热之中,这种现象的出现很大程度上是由那些从
农村来城市找工作的人所推动的。杜松子酒具有不少吸引人的特质:酿
造它的谷物在当地就能买到;它的包装比啤酒更有型;它比进口葡萄酒
便宜得多。因此杜松子酒成为了这些深深地承受着新城市生活压力的新
兴人群的一种麻醉剂,生活压力催生了一系列新的行为举止,包括对杜
松子酒的狂热。
卖杜松子酒的手推车在伦敦街头随处可见;如果你买不起一整杯的
话,你可以买一块被酒浸泡过的抹布;如果你醉了,需要睡一觉来解
酒,会有价格低廉的小旅馆按钟点出租草席供你休息,而这门生意也相当兴旺。对于那些突然陷入一种陌生而又缺乏人情味的生活的人来说,杜松子酒就像一种社会润滑剂,使他们不至于彻底崩溃。杜松子酒能让
它的消费者一点一点地崩溃。这是一种城市规模的集体性酗酒。
对杜松子酒的狂热确有其事:在18世纪初,杜松子酒的消费突飞猛
进,甚至当啤酒和葡萄酒销量不佳时依然如此。这也是一种认知的转
变。英格兰的权贵们对他们在伦敦街头看到的景象越来越警觉了。人口
数量以一种史无前例的速率增长,可以预见随之而来的一系列生活环
境、公共卫生以及各种犯罪问题的不断滋长。尤其让他们感到不安的
是,伦敦的妇女也开始沉溺于酒精,她们经常聚在那些有男有女的杜松
子酒廊里,用自己的行为来肯定杜松子酒对社会规范的腐蚀作用。
人们为什么会喝杜松子酒并不难理解,它兼具口感好与容易让人喝
醉两种特点,是一种迷人的混合物,尤其是在一个清醒节制被高估的混
乱世界里。在早年的工业社会中,饮用杜松子酒为涌入城市、尤其是集
中在伦敦的人群提供了一种应对机制。工业化使伦敦成为了人口流入最
多的城市。从17世纪中叶到18世纪中叶,伦敦人口的增幅达到英国全境
人口增幅的2.5倍;到1750年,每10个英国人中就有1个住在伦敦,这个
比例在一个世纪以前是25∶1。
工业化不仅创造了新的工作方式,还创造了新的生活方式,因为人
口重置破坏了乡村生活所共有的古老习惯,而大量人口涌入也使新的人
口密度破坏了旧有的城市生活模式。为了恢复工业化前的社会规范,从
18世纪20年代末起,议会开始查封杜松子酒。此后历经30余年,议会通
过了一条又一条法律来禁止生产、消费和销售杜松子酒。委婉地说,这
种策略没有见效,结果却演变成了一场长达30年之久的猫捉老鼠游戏。
现实往往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议会禁止“调味烈酒”,于是酿酒商便不再在酒浆中加入杜松子。销售杜松子酒被宣布为非
法,妇女们便将卖酒用的酒瓶藏在裙子底下。还有一些深具企业家精神的小贩创造了一种名叫“喵咪咪”的橱柜,它被放置在街边,顾客可以随意接近。只要顾客知道密码,把钱交给里面
的卖主,就能买到一小杯杜松子酒。
平息这种狂热的并不是任何一套法律。杜松子酒的消费被视为一个
亟待解决的问题,然而事实上它作为表象反映出了一个真正的问题——
戏剧性的社会变革,以及旧有城市模式在适应这种变化时表现出的乏
力。帮助平息对杜松子酒的狂热的,正是围绕着伦敦令人难以置信的社
会密度产生的新城市现状进行的社会重建。这种重建最终将伦敦变成了
大家公认的最早一批现代化城市之一。当谈论起“工业化社会”时,我们
所说的很多制度事实上都是应工业化的环境而生,而非由工业化本身造
成的。互助型社会使除开家族和宗教关系外的人们也能共同处理风险。
集中的人口促使咖啡馆以及后来的餐馆遍地开花。政党也开始招募城市
中的穷人,并将响应他们的人提名为候选人。只有在城市密度不再被视
为危机,而仅仅被当做一个事实甚至机会时,才会出现上述这些变化。
造成杜松子酒大量消费的原因,有一半是人们想通过麻痹自己来抵
御对城市生活的恐惧,而这种消费开始回落,是因为新的社会结构减轻
了这种恐惧。人口数量和社会总财富的增长使创造新的社会制度成为
可能。和丧失理智的群众不同,新社会的建筑师们察觉到,工业化的
副产品——某种公民盈余(civic surplus)出现了。
那我们呢?我们在历史上的代际变迁又是怎样的呢?那一部分仍时
常被我们称做“工业化社会”的全球人口,事实上早已转变成后工业化形
态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了农村人口流失、城市化发展以及郊区人
口密度增长的趋势,辅以在几乎所有人群中都不断提高的教育水平,标
志着愿意思考和谈话、而不是生产或运输物料的人数的空前增加。在这
样的转变过程中,我们的“杜松子酒”,一种虽饱受批评却能让我们在由
一个社会转变为另一个社会的过程中放轻松的润滑剂,会是什么呢?
答案是情景喜剧(sitcom)。看喜剧,或者肥皂剧(soap opera)、古装剧(costume drama)以及电视上播出的各种娱乐节目,侵吞了发达
国家公民的大量自由时间。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持续增长的国内生产总值、教育水平以及人
均寿命迫使工业化社会去努力解决一个全国性的、之前从未遇到过的问
题,那就是自由时间 。受教育人群可支配的自由时间不断累积并激
增,究其原因,一是受教育人群自身数量飞涨,二是人们寿命越来越长
但工作时间却越来越短。(有部分人口在20世纪40年代前便经历了教育
和自由时间的急剧上升,但当时这种趋势仅发生在城市地区,并且大萧
条推翻了很多当时的潮流,无论涉及到教育还是下班后的时间。)这一
改变还削弱了传统消磨时间的方式,而这种削弱是郊区化的产物——远
离城市,远离邻里,不断更换工作,不断搬家。战后美国每年积累的自
由时间总计有数十亿小时之多,但是人们野炊的频率和保龄球社团的数
量却开始出现倒退。我们究竟用这些时间做什么去了?大多数情况下,我们在看电视。
我们看《我爱露西》(I Love Lucy )
[1]
,看《盖里甘的岛》(Gilligan's Island )
[2]
,看
《马尔柯姆的一家》(Malcolm in the Middle )
[3]
,看《绝望的主妇》(Desperate Housewives)
[4]。我们有太多有待消磨的自由时间,但能消磨这些时间的趣事却太少,以至于每个发达国
家的公民都开始看电视,好像这是一种义务似的。很快看电视就消耗掉了我们最大部分的自由
时间:全世界的人们平均每周花在看电视上的时间超过20小时。
在媒介史上,只有广播和电视一样做到过无处不在,并且很多时
候,收听广播都伴随着其他活动,比如工作或者旅行。而通常情况下,对大多数人来讲,看电视就是他们在从事的活动。因为电视同时调动视
觉和听觉,甚至只是稍微关注一下的人都会挪不开步子。作为消费的先
决条件,电视把人们粘在了椅子和沙发上。
情景喜剧就是我们的杜松子酒,是在面对社会变迁危机时的一种能
够无限扩张的反应。通过饮用杜松子酒的行为,不难解释为什么人们会
看电视节目——有一部分确实不错。令人难以解释的是,收看电视节目是怎么一步一步成为每一个发达国家市民的第二职业的。药理学家会
说:“过量成毒药。”适量摄入酒精和咖啡因都没问题,可过量就会致
命。同样,电视的问题也不在于节目的内容,而在于节目的量:对于个
人以及整个文化的影响都取决于量。我们不仅收看好节目和烂节目,其
实我们什么都看——情景喜剧、肥皂剧、电视导购节目(infomercial)
以及家庭购物节目。人们往往在关心当时正在播放什么节目之前就已经
决定要看电视。关键并不在于我们看什么,而在于我们一生会看多长时
间,是一个又一个小时,日复一日,还是年复一年。某个出生于1960年
的人到目前为止已经看了约5万小时的电视节目,而且很有可能在他离
世之前还会再看3万小时。
这种状况并非美国独有。20世纪50年代以来,任何一个GDP持续增
长的国家都无一例外地面临人类事务的重新排序。整个发达国家社会做
得最多的三件事,分别是工作、睡觉和看电视。尽管已经有相当多的证
据表明看电视过多是造成人们不快乐的原因之一,但现实依然如故。
2007年,在由《经济心理学》杂志(Journal of Economic Psychology )发起的一项《看电视
让我们变快乐了吗?》(Does Watching TV Make Us Happy? )的让人如梦方醒的研究中,行为
经济学家布鲁诺·弗雷(Bruno Frey)、克里斯蒂娜·贝尼希(Christine Benesch)和阿洛伊斯·斯
塔策(Alois Stutzer)断定,不仅不快乐的人群比快乐的人群看更多电视,而且人们常常会为了
看电视而把其他活动推到一边,而那些活动虽然并非即刻愉悦人心,但却能提供长久的满足
感。从另一方面来说,花过多时间来看电视和不断增长的物质欲以及焦虑感存在着联系。
对于看过多电视可能对身体有害的思考一直被人提及。近半个世纪
以来,媒介批评家们面对电视给社会带来的影响不断地绞着他们的双
手,连手掌心都快搓破了。从牛顿·米诺(Newton Minow)
[5]
称电视
为“茫茫荒原”(vast wasteland)的著名论述,到“傻瓜盒子”(idiot
box)或“蠢材显像管”(boob tube)等绰号,再到罗纳德·达尔(Ronald
Dahl)在《查理和巧克力工厂》(Charlie and the Chocolate Factory )
中对痴迷于电视的迈克·蒂维(Mike Teavee)的缺德描述。
[6]
尽管说了
那么多刻薄话,他们的抱怨却从来都没起作用——在过去50年中,人们用于看电视的平均时间每年都在增长。我们已经了解了电视对人们快乐
程度的影响,这些了解起初只是道听途说,后来有数十年心理学方面的
研究做支持,但仍然没有阻碍人们看电视时间的增长,这一活动仍然主
宰着我们的休闲时间。为什么会这样呢?
议会的反对并没有减少人们对杜松子酒的消费,出于同样的原因,急剧增长的电视观看本身也并不是问题,它只是问题的一种反映形式。
人类是社会性动物,但自由时间的激增和某种社会资产的稳步减少趋
于一致,这种社会资产便是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与依靠。 线索之一便
是,观察电视收看时间的急速增长是如何导致其他活动,尤其是社交活
动被取代的。正如吉伯·福尔斯(Jib Fowles)在《为何观看》(Why
Viewers Watch )一书中所解释的,“看电视主要替代了三项活动:其他
娱乐、社交,以及睡眠。”一种叫做“社交替代假说”(social surrogacy
hypothesis)的理论认为,电视的消极作用之一是,它减少了人与人之
间接触的时间。
社交替代分为两部分。福尔斯陈述了第一部分——我们已经看了太
多电视,以至于取代了我们消磨时间的其他方式,包括和家人及朋友在
一起的时间;另一部分则是荧幕上的人物组成了一群想象中的朋友。来
自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的心理学家杰伊·德里克(Jaye Derrick)、希拉·加布里埃尔(Shira Gabriel),以及来自迈阿密大学的库尔特·胡根
伯格(Kurt Hugenberg)共同研究得出,当人们感觉孤独时,会转台到
自己喜欢的电视节目,收看这些节目会让他们感到不那么孤独。这种转
移解释了电视是如何成为最受拥戴的可选活动的,甚至当收看时间多到
和不愉快密切相关并诱发不快时依然如此:不管看电视有什么坏处,反
正总比感觉自己很孤独要好,即使事实上你确实是孤独的。因为看电视
是一件可以独立完成的事情,而且电视在缓解人们孤独感的同时,恰好
具备能够流行起来的特性,尤其是当社会由人口稠密的城市和联系紧密
的乡村走向通勤工作和频繁迁移造成的相对断裂时。只要家里有一台电视机,那人们即使想要多看一个小时也不需要付出额外的代价。
于是看电视创造了某种单调的重复工作(treadmill)。路易吉诺·布
鲁尼(Luiginao Bruni)和卢卡·斯坦卡(Luca Stanca)在《经济行为与
组织》杂志(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and Organization )中一篇
《独自观看》(Watching Alone )的论文中指出,看电视在通过单独活
动推掉社交活动的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马可·桂(Marco Gui)
和卢卡·斯坦卡在他们2009年的论文《看电视,满足感和幸福感》
(Television Viewing, Satisfaction and Happiness )中也提到了相同的现
象:电视在提高人们的实利主义和物欲方面起着重要作用,因而能导致
个体低估人际关系给生活带来满足感的相对重要性,也因此导致了人们
过多地从事产生收益的活动而对关系活动投入不足。将“对关系活动投
入不足”这句干巴巴的经济学术语译成通俗语言,就是指花很少时间来
陪家人和朋友。 正是由于看太多的电视使我们将更多的精力转而投入
到物质满足上,因此花在社交方面的时间就减少了。
我真正弄明白人们为何决定把最大部分的自由时间花在对单一媒介
的消费上,是在2008年我写的一本关于社会化媒体的书《未来是湿的》
(Here Comes Everybody )
[7]
出版以后。当时一位电视制片人在试图决
定是否让我在她的节目上讨论这本书时问我:“你认为目前社会化媒体
有哪些有趣的用处?”
我向她提起了维基百科,一部经协作完成的百科全书,我还向她提
及了维基百科上关于冥王星的文章。
早在2006年,冥王星就被从太阳系行星俱乐部中剔除了——天文学家认定它和其他行星很
不一样,因此他们计划对行星进行重新定义,以将冥王星排除在外。此事件引发了对维基百科
上冥王星这一词条的编辑高峰。考虑到冥王星地位的改变,人们频繁地对该词条进行编辑修
改。最热衷于此事的一小组编辑人员,在如何最贴切描述冥王星地位的改变这一问题上,并未
达成一致。他们更新了关于冥王星的词条——从章节到句子,甚至到词语的选择都互相较劲,最终把文章的本质内容从“冥王星是太阳系第九大行星”改成了“冥王星是一颗位于太阳系边缘,形状不规则,围绕不规则轨道旋转的石头”。我原以为那位制片人和我会开始一个关于知识的社会结构、权力的
本质或者任何一个谈到维基百科都经常会引出的话题。但是,她没有提
到任何此类问题。相反,她叹息道:“人们哪儿来的时间?”听到这些,我立刻插话说:“别人可以问,但是做电视这一行的人绝对不能问这样
的问题。你应该清楚那些时间是从哪儿来的。”她知道,因为她供职于
一个在过去50年中消磨掉公民大量自由时间的行业。
想象一下,如果我们将全世界受教育公民的自由时间看成一个集
合体,一种认知盈余(cognitive surplus),那么,这种盈余会有多
大? 为了算清这笔账,需要一个计量单位,那么就让我们从维基百科
开始吧。
设想将所有人花在维基百科上的时间总数作为一种计量单位——将对每一篇文章的每一处
编辑,对每一次编辑的讨论,包括用维基百科上现有的任何一种语言完成的,时间统统加起
来,截至我跟电视制片人说话的那一刻,大概代表了一亿个小时的人类思考。
马丁·瓦滕伯格(Martin Wattenberg),一位致力于研究维基百科的
IBM研究员,帮助我得到了这一数据。虽然他用的是“在信封背面涂涂
画画”的粗略算法,但在数量级方面是正确无误的。显然,累计达一亿
小时的思考时间已经很多了,然而和我们花在电视上的时间相比,这些
时间仍是小巫见大巫。
美国人一年花在看电视上的时间大约是2000亿个小时。这几乎是
2000个维基百科项目每年所需要的时间,甚至这个时间的一个零头都无
比庞大:每周末我们都会花大约1亿小时仅仅用来看电视。这是很大一
部分盈余。那些提出“人们哪儿来的时间”花在维基百科上的人没有意识
到,相比我们全部所拥有的自由时间的总和而言,维基百科项目所占用
的时间是多么微不足道。这是一个不平凡的时代,因为我们现在可以
把自由时间当做一种普遍的社会资产,用于大型的共同创造的项目,而不是一组仅供个人消磨的一连串时间。一开始社会完全不知道应该如何处理任何盈余——这也正是为什么
这些时间会成为盈余的原因所在。大多数情况下,当余下一块很大规模
的自由时间时(每年数以十亿计甚至数以万亿计小时),我们便会将它
消磨在看电视上,因为我们认为以这种方式来消磨这部分时间比现有其
他可供选择的方式要好。当然,我们也可以在室外玩耍,读书看报,或
者和朋友一起搞音乐创作。但大多数情况下我们不会那么做,因为和简
单地坐下看电视相比,那些活动的门槛太高。发达国家的生活中包含了
太多消极参与:我们在工作中是办公室寄生虫,在家又成了沙发土
豆。 如果认定比起其他事情来,我们更想做消极参与者,那么这种状
态就很容易解释。这种现实在过去数十年中似乎合情合理。很多证据支
持这一观点,而反对之声并不多。
然而现在,在电视历史上首次出现了一部分年轻人看电视的时间少
于他们父辈的现象。一些针对中学生、宽带用户和YouTube用户的研究
已经注意到了这种变化,并且基本的观察结果总是一致的:拥有更快捷
的互动媒介的年轻一代正在把他们的行为从单纯对媒介的消费中转变过
来。甚至当他们观看在线视频的时候,这种行为看似和看电视没什么两
样,但他们却有机会针对这些素材发表评论、分享、贴上标签、评分或
者排名,当然还可以和世界上其他的观众一起讨论。
丹·希尔(Dan Hill)在一篇被广泛转载的网络文章《为什么〈迷失〉
[8]
会成为一种新媒
介》中指出,这部电视剧的观众不仅仅是观众——他们协同创造了一部围绕此剧的内容汇编,叫做“迷失百科”(Lostpedia) ——真的,除此之外还能叫什么呢。换句话说,甚至当他们看电
视的时候,很多互联网用户都会参与进来,而这种和参与相关的行为同消极的消费行为之间存
在着某种区别。
导致电视消费量减少的选择可以是微小的,同时也可以是庞大的。
微小的选择是一种个人行为,一个人只是简单地决定下一个小时是用来
和朋友聊天、玩游戏还是创造一些事物,而不再是单纯地看电视。庞大
的选择则是一种集体行为,是数以百万计的微小选择的集合。整个人
群中不断累积的对参与态度的转变,使得维基百科的产生成为可能。这种对自由时间的使用选择使得电视行业为之震惊,因为“看电视是消
磨时光的最好办法,这一曾经为观众所认可的观念”,已经作为社会的
一种不变特征存在了很久。一位研究协同工作的英国学者查理·利德比
特(Charlie Leadbeater)在报告中指出,一位电视主管人员最近告诉
他,年轻人的分享行为会随着他们长大而逐渐消失,因为工作会耗费他
们太多的精力,以至于在他们回家后的空闲时间里除了“瘫在电视机
前”什么都不想做。轻信“这种行为过去稳定,因此将来也会稳定”是错
误的——这不仅仅错误,而且构成了一种特殊的错误。
奶昔错误
麦当劳想提高奶昔销量,因此雇用了一些研究员来弄清楚顾客最关
注奶昔的哪种特质。是要做得更稠?更甜?还是更凉?几乎所有研究员
关注的都是产品。然而其中一个叫杰拉德·博斯特尔(Gerald Berstell)
的研究员却选择了忽略奶昔本身,对顾客进行研究。
他每天坐在麦当劳里长达18个小时,观察都有哪些人在什么时候买奶昔。最终,他得出了
一个令人惊讶的发现:很多奶昔都是在早上被销售出去的——奇怪,显然在早上8点时喝奶昔并
不适合火腿、鸡蛋这样的早餐样式。博斯特尔还从早上购买奶昔的人群的行为中得出了三条其
他线索,买家通常独自一人,除了奶昔外他们几乎不买任何其他食物,他们从不在店里喝奶
昔。
显然这些早餐喝奶昔的人都是上班族,他们打算在开车上班途中
喝。这些行为实际上显而易见,但其他研究人员却忽略了,因为它们不
符合有关奶昔和早餐的正常思维。博斯特尔和他的同事们在发表于《哈
佛商业评论》的一篇《为你的产品找到正确的角色》(Finding the Right
Job for Your Product )的文章中指出,理解到底发生了什么事的关键是
停止孤立地观察产品,并放弃对早餐的传统理解。取而代之的是,博斯
特尔关注着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顾客早上8点钟购买奶昔的目的是什
么?”如果你想在开车的时候进食,就必须选一些可以用一只手吃的东
西。它不能太烫,不能溅得到处都是,也不能太油腻。同时它必须可
口,并且需要花一些时间来吃完。没有一种传统早餐符合这些诉求,因
此那些顾客会购买奶昔来取而代之,不再顾及刻板的早餐传统。
除了博斯特尔外,所有研究人员都忽略了这一事实。他们犯了两种
错误,我们可以称之为“奶昔错误”(milkshake mistakes)。
第一种错误是主要关注产品本身,认为对于产品来讲每个要点都存
在于产品的属性中,没有顾及到顾客想让它扮演怎样的角色,即他们购
买奶昔的目的是什么。
第二种错误是对人们早餐常吃食物种类的观念过于狭隘,仿佛所有
习惯都是根深蒂固的传统,而不是累积起来的偶然事件一样。当顾客需
要食物来起一些非传统的作用时——在他们早晨上班的路途中作为填饱
肚子的东西和娱乐,那么不管是奶昔本身还是早餐的历史就都不重要
了,顾客并不是为了这些原因而购买奶昔的。
联想到媒体,我们也面临同样的问题。当我们谈起网络和短信的作
用时,我们很容易犯奶昔错误,我们只会关注工具本身。我这么说是根
据我的自身经验,20世纪90年代我开展了大量关于电脑和互联网性能的
研究,却很少考虑到其实是人类的欲望塑造了它们。
新媒体工具的社会化应用令人惊叹,究其原因,一部分在于这些应
用方式的可能性并不固有存在于工具本身之中。从便携式收音机到个人
电脑,整整一代人在个人技术的伴随下成长起来,因此他们会把新的媒
体工具纳为己用也并不奇怪。然而,人们对社会科技的使用却很少由工
具本身来决定。当我们使用网络时,最重要的是我们获得了同他人联
系的接口。我们想和别人联系在一起,这是一种电视无法替代的诉
求,但实际上我们可以通过使用社会化媒体来满足它。我们很容易设想,当今的世界反映了某种对社会的理想表达,所有
背离这种神圣传统的事情都是骇人听闻和不正当的。尽管互联网已经出
现了40年,万维网技术也已出现了20年,社会中以往喜欢将大量自由时
间用于消费的个体成员开始主动创造并分享事物,但仍有很多人对此感
到惊讶。和以往相比,这种创造并分享的行为的确令人惊讶。然而媒介
的单纯消费从来都不是一个神圣的传统,它们仅仅是一连串偶然事件的
累积,当人们使用新的传播工具能达到旧有媒体无法完成的目标时,它
们就失效了。
举例来说,一种叫做Ushahidi
[9]
的服务平台被开发出来,用于帮助
肯尼亚居民对发生种族暴力进行预警。
2007年12月,一次极具争议的选举使得支持和反对姆瓦伊·齐贝吉(Mwai Kibaki)总统的
双方陷入针锋相对的境地。一位名叫奥赖·奥科罗(Ory Okolloh)的肯尼亚政治活跃人士,在自
己的博客上记录了一次由于肯尼亚政府禁止主流媒体报道而引发的暴力冲突。而后她请读者将
他们所见证的暴力,通过电子邮件或者在她的博客上发表评论的形式传递出来。
事实证明这种方式非常受欢迎,她的博客“肯尼亚博学者”(Kenyan
Pundit)成为第一人称报道的一个重要来源。人们对此事的关注度不断
上升,以至于短短数日后奥科罗的博客便再也无法承受如此庞大的信息
量。于是她设想了一种服务平台,并把它命名为“Ushahidi”,这个平台
可以自动收集群众的报道(她曾经是手动收集的),并且能在地图上实
时显示报道中冲突发生的地点。她在博客中流露出了这个想法,引起了
程序员埃里克·赫斯曼(Erik Hersman)和大卫·考比亚(David Kobia)
的兴趣。他们三人进行了一次电话会议,仔细讨论了如何使这种服务平
台有效运作。三天后,第一版Ushahidi平台问世了。
肯尼亚选举后,人们通常只能发现发生在他们身边的暴力冲突。因
为没有社会资源,人们无法确认出事地点,无法了解到底发生了什么,也无法知道如何提供援助。我们通常依靠政府或者专业媒体来获得集体
暴乱方面的信息,但在2008年初的肯尼亚,鉴于党派狂热和审查机制,专业媒体不会报道这些内容,而政府对此也不愿意报道任何消息。
Ushahidi的开发被用于收集那些可用但分散的信息,将所有个人观
察所得的碎片编织成一幅全国性的画面。即使公众想了解的信息存在于
政府的某些机构,但由于Ushahidi的信息是由市民们提供的点点滴滴经
过重现所绘制出来的,因此它们比权威部门的信息更容易获得。这个项
目虽从网页开始起步,但Ushahidi的开发人员很快便增加了可以通过手
机短信来上传信息的功能,此时报道的信息流才真正开始不停地涌入。
在Ushahidi启动了数月后,哈佛大学肯尼迪政治学院做了一次分析。通
过对比Ushahidi和主流媒体提供的数据,他们认为Ushahidi在报道暴力
冲突的发生、冲突后的抗议以及非死亡暴力事件方面做得更好,并且报
道范围也更大——涵盖了广阔的地理区域,包括农村地区。
所有这些信息都是有用的——全世界的政府在被关注时都显得对公
民不那么极端,同时,肯尼亚的非政府组织通过对这些数据的使用来锁
定人道主义救援对象。但这仅仅是一个开始。在意识到这个网站的潜力
后,创立者们决定将Ushahidi变成一个平台,任何人都能设立自己的服
务并通过短信来收集、定位信息。这个想法使充分利用大量集体信息变
得容易,并且从最初的肯尼亚开始向别国传播开去。自从它在2008年首
次亮相以来,Ushahidi已经被用于追踪刚果国内类似的暴力事件,用于
监督印度和墨西哥的投票点及预防投票者作弊,用于报道数个东非国家
的重要药品供应量,还曾用于海地和智利地震后的伤员搜救工作。
少数人使用廉价的工具,投入很少时间和金钱,就能在社会中开拓
出足够多的集体善意,创造出5年前没人能够想象的资源。和许多有意
义的故事一样,Ushahidi的故事教会了我们几个不同的道理:
人们想做一些事情来让世界变得更美好;当他们受到邀请时愿意伸
出援手;在尝试新事物时,使用简单灵活的工具可以排除很多困难;如
果你想充分利用认知盈余,不必拥有一台高级的电脑,一部手机就足够了。然而这个故事教给我们最重要的道理之一是:一旦你弄明白如何通
过一种让他人在意的方式来充分利用认知盈余,那么他人也会复制你
的技术,一而再再而三地传遍世界。
为帮助困境中痛苦的人们而设计出来的Ushahidi网站是伟大的,然
而并非所有的传播工具都被如此大量地使用。事实上,大多数情况都并
非如此。每个人都看得到像Ushahidi或维基百科这样杰出的项目,然
而,与它们相对应的,存在着无数的做完即废的一次性工作,这些工作
投入极少,除了成为低俗笑话,也起不到更积极的作用。
眼下最标准的例子就是“大笑猫”(lolcat),一张可爱的猫咪图片会因为被加上一个可爱的
标题而显得更可爱。“猫配标题”这种做法的理想效果是能让观众大声笑出来,因此在“猫”前面
加上“大笑”二字。
收集这类图片最多的是一家名叫ICanHasCheezburg的网站,它是以它最初的图像来命名
的:一只灰色的猫张着嘴,狂躁地瞪着眼睛,配以“我能吃奶酪三明治吗?”的标题(“大笑
猫”的糟糕拼写让它声名狼藉)。ICanHasCheezburg网站拥有超过3000幅“大笑猫”的图片,比
如“我今天过得不爽”、“我偷了你一些吃的,谢谢,再见”以及“强盗猫刚吃了你的玉米煎饼”。
每个标题下都跟着数以百计也以“大笑猫”口吻写的评论。我们现在已经远离了Ushahidi。
“大笑猫”的诞生过程可以被提名为最愚蠢的创造行为。当然也会有
其他候选者,但“大笑猫”无疑是其中最全面的案例之一。成型很快,也
不需要什么技术含量,一张“大笑猫”图片所拥有的社会价值仅仅和一个
坐上去就发出放屁声的垫子相当,它的文化寿命如同蜉蝣一般短暂。任
何看到“大笑猫”的人都会在第一时间得到一条与之相关联的信息:你也
能玩这个游戏。由于“大笑猫”被创造得如此轻而易举,因此谁都可以在
一只可爱的猫咪图片旁加上一个笨拙的标题(狗、大颊鼠或海象——在
ICanhasCheezburg网站上,大家在浪费时间方面是平等的),然后和全
世界分享这一创造。
“大笑猫”图片虽然不能说话,但它们内部却存在着种种统一的准
则,从“标题要按照发音来拼写”到“字母要用无衬线字体”。就连愚蠢的深度也得加以规定,换句话说,某些方式创造出的“大笑猫”是错误的,而另一些方式创造出的“大笑猫”是正确的,也就是说,这其中存在着一
定的质量标准,甚至制约。无论这个世界对下一只“大笑猫”的需求有多
小,“你也能玩这个游戏”的信息相对我们所习惯的媒介来说体现出了一
种变化。再愚蠢的创造也是一种创造。
很多针对“大笑猫”的反对之声都着眼于它有多么愚蠢:就算你的猫
让人笑死,也没有多大的意义。就创造的范围来说,平庸和优秀之间确
实有着天壤之别。然而,不管怎样,平庸仍然处在创造的范围内,你可
以通过累积将平庸变成优秀。真正的鸿沟在于什么都不做和做点儿什么
之间,而创造“大笑猫”的人已经跨过了这道坎。
只要媒介的假定目的是允许普通人消费那些经专业创造而成的素
材,那么经业余创造的素材的增值便显得难以理解。业余创造的素材显
得很不专业——例如“大笑猫”就是卡通网络的一种低质量替代品。但是
在这一整段时间里,如果我们使用媒介的目的不仅仅是让它提供专业内
容呢?如果我们一直以来总是既想生产又想消费,但是没有人给我们这
样的机会呢?“你也可以玩这个游戏”中蕴含的愉悦并不仅仅存在于创
造,它同样存在于分享中。 “用户生成的内容”(user-generated
content)这个当前用于描述业余者的创造行动的词组所阐述的其实不仅
仅是个人行为,更是一种社会行为。“大笑猫”不仅仅是由用户生成的,它更是被用户分享的东西。事实上,分享才是愉悦的来源——没有人创
造一只“大笑猫”的目的是为了给自己留着。
20世纪,社会生活的原子化使我们远离了参与文化,以至于当它回
归时,我们需要用“参与文化”(participatory culture)这样一个词汇来描
述它。在20世纪之前,我们并没有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词组来形容参与文
化。这实际上是一种同义反复,文化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便是参与——聚
会、活动和表演,除了这些地方,文化还能从哪儿来呢?和别人一起创造并分享某样事物,这一简单的举动至少代表了对某种旧有文化模型
的回应,而这种文化模型现在正披着科技的外衣。
只要你接受了人们实际上很喜欢创造并分享事物这个观点,不管分
享的内容有多笨拙,完成得有多糟糕,并且能够理解“让彼此都能欢
笑”和“付钱让别人做一些让我们发笑的事情”是两种不同行为的话,那
么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卡通网络就成了“大笑猫”的一种低质量替代品
了。
多即是不同
当人们在调查一种像维基百科、Ushahidi或者“大笑猫”这样的新兴
文化产物时,要回答“人们哪儿来的时间”这样的问题出人意料地简单。
我们总能抽出时间来做我们感兴趣的事情,因为那些事情吸引着我
们,而这些时间是从争取每周40小时工作制的斗争中得来的。在19世纪
末为谋求更好的工作环境而进行的抗议活动中,有一句很受欢迎的工人
口号是这样说的:“8小时工作,8小时睡觉,8小时做我们想做的
事!”一个多世纪后的今天,对无组织时间显见而具体的利用已经成为
了工业化廉价商品的一部分。 然而在过去50年中,我们却把这来之不
易的时间的大部分都花在了一项简单的活动上,这种行为普遍到连我们
自己都已经忘记了我们的空闲时间始终属于我们自己,我们可以凭自己
的意愿来消费它们。
“人们哪儿来的时间”,问这样问题的人通常并不是在寻求答案。这
个问题很浮夸,说明问问题的人认为某些特定的行为很愚蠢。
在我和前面那位电视制片人的谈话中,我也提到了《魔兽世界》(World of Warcraft ),一款基于包括骑士、精灵和恶魔在内的魔幻设定的网络游戏。《魔兽世界》中的很多挑战都非
常困难,因为它们很难被单个玩家征服。相反,玩家们需要组织在一起形成公会,即一种由很
多成员构成的复杂的虚拟社会结构。在我描述这些公会和需要其成员们完成的任务时,我知道
那位制片人是怎样看待魔兽世界玩家的:成年男女蹲在地下室里扮演精灵?都是些失败者。答案显而易见:他们至少在做一些事情。你看过《盖里甘的岛》中
的这样一个情节吗?人们就快离开那个岛的时候盖里甘陷入了混乱,于
是他们没走成。这个情节我在成长的过程中看过很多遍。每次看到这个
时长为半小时的情节时,我都没有在分享照片、上传视频或者在一个邮
件列表上对话。
对此我曾经有一个不变的借口——那些事情中没有一件是我小时候
就能做的,那时候我能做的就是每年花数千小时在《盖里甘的岛》、《帕特里奇一家》(The Patridge Family )
[10]
和《霹雳娇娃》
(Charlie's Angels )
[11]
上。不管你认为蹲在地下室里扮精灵有多可
怜,我都可以以自身经验来告诉你:蹲在地下室里纠结金杰(Ginger)
和玛丽·安(Mary Ann)
[12]
谁更可爱更糟糕。
戴夫·希基(David Hickey),一位反传统的艺术历史学家和文化批
评家,在1997年写了一篇《和打酱油者搞浪漫》(Romancing the Looky-
Loos )的文章,他在文中讨论了各种各样的音乐听众。这篇文章的标题
来自于他父亲,身为音乐家的父亲把一群仅仅去消费的特殊听众叫
做“打酱油的人”(looky-loos)
[13]。要做一个打酱油的人首先得去参加
一场活动,尤其是现场活动,但他们和你在电视上盲目地收看这个活动
的效果一样:
他们在门口买票入场,但对活动没有做出任何贡献——没有给予活动任何肯定或否定,让
你可以与之结伴或者反对他们。
而参与者却不一样。参与是一种行为,它让你觉得自己的出席很
重要,让你在看到或听到某些东西时觉得自己的回应也是活动的一部
分。 希基引用了音乐家韦纶·詹宁斯(Waylon Jennings)在讨论为懂得
参与的听众演奏是怎样一种感觉时说的一段话:
他们从小酒吧里发现了你,因为他们知道你在做什么,于是你便觉得自己是在为他们演
奏。而且如果你做错了,你马上就会知道。参与者会给反馈,而围观者不会。即使在活动结束后,参与行为还
能进行得如火如荼——对整个社团的人来说,电影、书籍和电视剧创造
的不仅是一种消费的机会。它们创造的还是一种回应、讨论、争辩甚至
创造的机会。
20世纪的媒介作为一种单一事件发展着,这种单一事件就是消费。
在那个时代,鼓舞媒介的问题是:“如果我们生产得更多,你会消费得
更多吗?”人们对于这个问题的普遍回答曾经是“是”,因为人们平均每
年都会消费更多的电视资源。但实际上媒介就像铁人三项运动,由三种
不同的活动组成:人们喜欢消费,但他们也喜欢创造和分享。 我们总
是喜欢所有这三种活动,但直到最近为止,电视媒介依然只回报其中的
一种。
电视是不平衡的,如果我拥有一个电视台,而你拥有一台电视机,那么我可以跟你说话,但你却无法跟我说话。相反,电话却是平衡的。
如果你购买了消费手段,那么你也自动获得了创造手段。当你购买电话
时,没有人会问你只用来收听还是也会用来打电话这样的问题,参与行
为固有地存在于电话中。对于电脑来说也一样,当你买了一台可以消费
数字内容的机器时,你同时也购买了一台可以创造内容的机器。此外,你还能和你的朋友分享这些素材,你可以告诉他们你消费、创造和分享
的事物。这些并不是它的附加特性,而是基本要素中的一部分。
日积月累的迹象表明,如果你为人们提供了创造和分享的机会,那
么他们有时会和你辩论,即使他们此前从没有过那样的举动,即使他们
对此并不像专业人士那样精通。这并不能说明我们将停止盲目地看电
视,它仅仅说明了消费已经不是我们利用媒介的唯一方式。对于我们每
年消耗的一万亿小时的空闲时间来说,任何转变——不管多么微小,都可能是很大一部分时间。
将我们的关注点拓展到包括创造和分享在内,并不需要通过个人行为的大幅度转变来使结果发生巨大变化。全世界的认知盈余太多了,多
到即使微小的变化都能累积成巨大的后果。
试想一下,99%的事物都和原先一样,人们仍像以前那样消费着99%的电视资源,但那些
时间中的1%发生了变化,开始被用于创造和分享。相关人群每年仍然会花多达一万亿小时的时
间来看电视,而这些时间中的1%就比每年用于维基百科的时间的一百倍还多。
规模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因为盈余需要能够被累积起来。对于像
Ushahidi这样的工作,人们必须同心协力贡献自己的空余时间来创造认
知盈余,而不仅仅是完成一系列微不足道而又彼此分离的个人行为。
累积规模一部分和受教育人群如何利用空闲时间有关,另一部分则取决
于累积行为本身,和人们越来越多地在单一的分享型媒介空间内彼此互
联有关。2010年,全球通过互联网联系到一起的人口即将超过20亿,手
机用户更是早已突破了30亿。因为全世界大概有45亿成年人(全球人口
约30%的年龄在15岁以下),所以我们生活在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中
——对大多数居民来说,作为全球范围内互动组织的一部分已经变得再
正常不过。
规模能区分大小盈余作用之间的不同。我第一次发现这个原理是在
30年前。那时父母为了给我过16岁生日,送我去纽约城找我的堂兄。我
的反应和你们眼中被扔进那种环境的中西部孩子很像,我心中充满了对
高楼、人群和喧闹的敬畏。但是除了那些大事以外,我还注意到了一件
小事——切片比萨,它改变了我对于可能性的观念。
我曾经在我家乡一家叫做肯氏的比萨店里打工。在那儿我认识到了这样一个道理:顾客要
比萨,你做比萨,20分钟后你把比萨交到顾客手上。这个过程很简单,也可预测。但是切片比
萨却完全不同。你不可能知道谁会要一角,因此你要提前把馅饼做好,因为顾客的全部要求就
是在20分钟之内进来拿了切片比萨后走人,而且他们拿的只是一小角比萨,而不是一整块。
在我16岁时,那个启发了我的切片比萨,它所蕴涵的意义是:当群
体足够大时,不可预知的可以变得可预知。 如今任何一天你都不必知
道谁会来买比萨,只需要确定一定会有人来买就行。一旦对于需求的确定开始远离个人顾客,而向集体顾客回流,那么崭新的行为种类便成为
可能。如果我16岁那年有更多的流动资金,那我也会在观察雇出租车和
等公交车两种行为的过程中发现同样的原理。更普遍的是,一个事件
发生的可能性就是它可能发生的次数和频率的或然率。 在我长大的地
方,顾客在下午3点购买一小片切片比萨的可能性太低,因此我们不会
冒险提前做好一整张比萨。而在34号大街和第六大道的拐角处,你就可
以做上一整张比萨来等待生意上门。任何人类活动,无论看上去多么
不可能,在人群中发生的可能性都会增加。规模较大的盈余和小盈余
就是不同。
物理学家菲利普·安德森(Philip Anderson)说过:“多即不
同。”(More is different.) 当你把某样东西累积了很多时,它就会以新
的形式来表现,而我们新的媒介工具正在以一种空前的规模累积我们创
造和分享的个人能力。想想下面这个问题,其答案在近年来发生了戏剧
性的变化:一个拿着相机的人遭遇一件全球性大事件的可能性有多大?
如果你从一个自我中心的角度阐述这个问题,那就是,我能遇到这
件事的概率有多大?这种概率很小,小到让人难以察觉,并且从个人角
度来推断的话,总体概率似乎也很小。
我们认识新的媒介工具所带来的文化变革非常艰难的原因之一就在
于,我们惯于以自我为中心(egocentric)看待事物,而这是错误的路
径。一个拿着相机的人遭遇一件全球性大事的可能性,仅仅和事件目击
者人数以及他们中带着相机的比例有关。第一个数字会根据事件不同展
开上下浮动,而第二个数字——带着相机的人,从2000年的数百万人上
升到如今的超过十亿人。照相机现在已经被植入了手机中,因而提升了
随时会携带相机的人数。我们已经多次看到这种新情况产生的作用:
2005年伦敦地铁恐怖袭击事件、2006年泰国政变、2008年奥克兰警察杀死黑人奥斯卡·格兰
特(Oscar Grant)案,以及2009年伊朗大选后出现的动荡局面——所有这些和数不清的更多事件都被相机拍了下来,并上传到网上让更多人看到。一个拿着相机的人遭遇一件全球性大事的
可能性,很快就变成了一个事件会有目击者看到的可能性。
规模上的变化意味着曾经不可能的事情变成了可能,曾经不太可能
的事情变成了肯定。我们曾经依靠专业的摄影记者来记录那些事件,而
现在我们越来越多地成为了彼此的基础设施。用这种方式来看待分享或
许比较冷血——我们越来越多地通过陌生人随机决定分享的内容来了解
世界,但即使这样也是对人类有好处的。正如库尔特·冯内古特(Kurt
Vonnegut)在《泰坦的海妖》(The Sirens of Titans )中借主角之口说
出的:“人身上发生的最糟糕的事就是,他们对任何人和任何事都没有
用处。”我们融合认知盈余的方式会让这种命运不太可能马上到来。
我们正在越来越多地创造和分享媒介,因此我们不得不重新学
习“媒介”这个词代表着什么。
“媒介”(media),简单而言就是任何传播中的中间层,无论它如字母表般久远还是像手机
般现代。最直接并相对中庸的定义则是,过去数十年中另外一种来自于媒介消费模式的概念:
媒介涉及到商业的集合,从报纸杂志到广播电视,媒介用特殊的方式来创造素材、用特殊的方
式来赚钱。
如果我们仅仅使用媒介来指代这些商业形式和素材,这个词汇就会
变成一个时代错误,而妨碍当今发生的事情。我们平衡消费与创造和
分享的能力以及彼此联系的能力,正在把人们对媒介的认识从一种特
殊的经济部门,转变为一种有组织的廉价而又全球适用的分享工具。
认知盈余,一种全新的资源
在这本书中,我讲述了随着全世界累积的自由时间不断聚集而产生
的新资源。使我们有权使用这种资源的最重要的两个转变已经产生——
全球受教育人口累积起来的每年超过一万亿小时的自由时间,以及公
共媒介的发明和扩散, 它使得以前被排除在外的普通市民能够利用自
由时间从事自己喜欢或关心的活动。这两个事实适用于本书中所有的故事,从Ushahidi这样的富有启发性的分享到像“大笑猫”那样仅供自娱自
乐的活动。认识到这两种变化,认识到它们和20世纪媒介的不同,仅仅
是理解今天会发生什么和明天可能发生什么的开始。
我在之前写的《未来是湿的》一书中,讲述了社会化媒体历史性的
崛起,以及随之产生的群体行为环境的改变。本书从上一本书遗留的
地方开始,观察人类的联网如何让我们将自由时间看成一种共享的全
球性资源,并通过设计新的参与及分享方式来利用它们。 我们的认知
盈余只是一种可能,它自身并不代表任何事物,也做不了任何事情。为
了了解我们能利用这一新资源来做什么,我们不仅要了解那些可以利用
它的活动种类,而且要知道如何以及在哪里利用它们。
当警察想要了解某人是否会采取特殊行动时,他们会寻找一些手
段、动机或机会。手段和动机是指怎样和为什么要采取这种特殊行动,而机会指的是在哪里行动以及和谁一起行动。人们有能力、动机和机会
来利用不断累积的自由时间做一些事情吗?对这些问题的积极回答能帮
助建立人和行动之间的联系。把这个问题放大来阐述的话,手段、动机
和机会能帮助解释社会上出现的新行为。了解一件因为我们的认知盈余
而变得可能的事情,意味着理解我们累积自由时间的方式,利用这种新
型资源的动机以及我们事实上正在彼此创造的机会的本质。在接下来的
三章中,我将具体阐述怎样和为什么要利用认知盈余,以及在认知盈余
背后存在着什么。
尽管花了这些篇幅,我仍然没有描述我们可以利用认知盈余来做
什么,因为我们只有通过集体才能去做事情,这是一个社会性问题,而不仅仅是个人的事。 要想从共享的自由时间和才能中得到任何东
西,我们必须彼此协作,因此利用认知盈余并不仅仅是个人喜好的堆
积。不同用户群体的文化对成员间的互相期待以及成员如何一起工作的
影响巨大。文化会决定我们从认知盈余中获得的价值中有多少仅仅是公用的(communal),被参与者所欣赏,但对整体社会没太多用处,而有多少是公民的(civic)。 (你可以把“公用”和“公民”的对比看做
是“大笑猫”和“Ushahidi”的对比。)在第2章第4章阐述完手段、动机和
机会后,我将会讲述用户文化的问题以及公用价值和公民价值的对比。
最后一章作为全书推理性最强的一章,具体阐述了我们从对认知盈
余的成功利用中获得的经验,这些经验能够指引我们,因为更多的认知
盈余正在以更重要的方式被利用着。尽管由于社会系统的复杂性,尤其
是在包含了不同的主动参与者的情况下,这些经验不能被简单地当成药
方使用,但它们可以作为一种导轨(guide rail)来帮助你的新项目避免
面临某些特定的困境。
从过去孤立的时间和才能中脱颖而出的认知盈余,仅仅是一种原材
料。要从中获得价值,我们必须让它变得有用或者能利用它做一些事
情。我们大家并不仅仅是认知盈余的来源,也是设计它的使用方式的
人,这种设计是通过参与,以及当我们以新的方式联系在一起时对彼此
的期待而展开的。
[1] 《我爱露西》是一部美国黑白电视情景喜剧,由CBS从1951年10月15日到1957年5月6日播放。它是美国20世纪
50年代最著名的情景喜剧系列,至今还被认为是最精彩的电视节目之一,被频繁重播。——译者注
[2] 《盖里甘的岛》是美国20世纪60年代的著名情景喜剧,由CBS从1964年9月26日到1967年9月4日播放。——译者
注
[3] 《马尔柯姆的一家》是福克斯电视网播出的电视喜剧,从2000年1月9日到2006年5月14日播放,该剧曾获得多个
奖项。——译者注
[4] 《绝望的主妇》描写了一个虚构的美国小镇上一群妇女的生活,在表面光鲜的郊区社区中,充满了秘密和罪
行。自从该电视剧于2004年10月3日在ABC首播以来,收获了无数奖项,首播季吸引了2100万观众,在2007年,它成为
全世界最流行的电视剧之一,观众达1.2亿。2010年,它成为全球观看人数最多的系列剧集,在68个国家和地区中平均
拥有5100万观众。它也是2010年美国收益第三大的电视剧,每半小时创收274万美元。——译者注
[5] 牛顿·米诺(1926—) ,美国律师,曾任联邦通信委员会主席。——译者注
[6] 《查理和巧克力工厂》是英国作家罗纳德·达尔于1964年出版的童书,描写了查理·贝克特和其他4个孩子在一家
巧克力工厂中的冒险。其中一个叫做迈克·蒂维的孩子因为爱看电视,做了很多蠢事。——译者注
[7] 本书中文版已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译者注
[8] 《迷失》(Lost ),ABC于2004—2010年播放的电视连续剧,共有六季,曾获得多个奖项。——译者注[9] Ushahidi,斯瓦西里语,意为“目击”或者“证明”。
[10] 《帕特里奇一家》是ABC播出的美国电视剧,描写一个丧偶的母亲和她的5个孩子如何走上音乐道路的故事。
播放时间是1970年9月25日到1974年8月31日。——译者注
[11] 《霹雳娇娃》是一部关于三位女私家侦探的电视连续剧,是比较早地让妇女扮演传统上男人占据的角色的作品
之一。它从1976—1981年一直在ABC播放,是美国20世纪70年代最成功的电视剧之一。——译者注
[12] 《盖里甘的岛》中的两个女性角色,就好比中文语境中的红玫瑰与白玫瑰。——译者注
[13] “looky-loos”是一个人造词,用来指只围观、不参与的人,故用中文新词“打酱油者”译之。——译者注第2章 工具赋予的可能性
当韩国民众在首尔市中心展开轰轰烈烈的示威游行时,谁也不会想
到,在游行中,一半以上的参与者,竟然都是十几岁的小女孩儿。是什
么让这些年幼到连选举权都没有的小姑娘接连数周,夜以继日地在公园
里抗议?……对认知盈余的利用使人们得以用更慷慨、更公开、更加社
会化的方式来表现自己。现在,除了时间,我们还拥有任由我们支配的
工具,并不是我们的工具塑造了我们的行为,但是工具赋予了行为发生
的可能。
新的媒体形式囊括了经济学的转变,这种转变很大程度上为我们所
见的慷慨、公开、有创造力的行为提供了便捷的方式。
原本只能在单向公共媒体(如书籍和电影)和双向个人媒体(如电
话)间进行的选择,如今扩展出了第三个选项:从个人到公众的可延展
的双向媒体操作。
旧世界已经让位于一个全新的世界,在这里,大多数形式的交流,不管是公开的还是私下的,都以某种形式可为任何人所用。
早在2003年,美国多个牛肉源被发现带有疯牛病菌(学名“牛海绵
状脑病”),其后韩国便禁止从美国进口牛肉。除少数的特殊情况外,这项禁令一直持续了5年。一直以来韩国就是美国的第三大牛肉出口市
场,因此这项禁令成为了两国政府间的敏感问题。最终,在2008年4
月,韩国总统李明博和美国总统乔治·布什就重新开放韩国对美国的牛
肉市场问题进行了磋商,并以此作为两国更为广泛的自由贸易协议的试
行。表面上看来,这项自由贸易协议结束了此前的禁令,但那是在韩国
民众参与进来之前。当年5月,美国牛肉重返韩国市场的消息一经披露,韩国民众就在
贯穿首尔市中心的绿化带——清溪川公园举行了公开抗议。抗议以烛光
守夜的形式开始,大量民众聚集在公园过夜。此次抗议具有一些与众不
同的特点,其一是持续时间长:抗议并没有逐渐趋于平息,反而持续了
数个星期;其二是抗议的涉及面广:尽管示威开始的时候规模很小,但
随后人数增加到了数千人,最终达到上万人。截至6月初,此次抗议已
成为韩国自1987年争取恢复民主选举以来最大规模的抗议示威。大量民
众对清溪川公园的长时间占据破坏了大片绿地。
然而,最不同寻常的却是参与抗议的民众本身,这里所指的不是民
众的数量,而是他们的构成。此前韩国的抗议游行大多是由政党或工会
组织的。但在针对疯牛病的抗议中,一半以上的参与者(包括初期的组
织者)都是青少年,特别是十几岁的小女孩儿。
这些“烛光女孩”年纪太小而没有选举权,她们不是任何政党的成员,而且她们中的大多数
人在此之前也没有参与过任何公众性的政治活动。这些人的参与使守夜行动成为韩国首例家庭
式抗议:在长达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很多人举家出现在公园里,他们甚至经常带着婴幼儿。无
论哪个国家的政府在调查威胁国家安全的可能因素时,都不会担心十几岁的小女孩儿。那她们
究竟来自哪里呢?
这些女孩一直都存在——毕竟,她们是韩国的公民,只是此前她们
没有被大批地动员起来。民主国家既培养也依赖公民的知足常乐。当一
个国家的公民足够满意而不出现在街上游行的时候,这样的民主国家是
正常运行的;而一旦公民上街示威,那么就意味着这个国家有什么地方
做的不对了。由此看来,小女孩儿们的参与着实是个问题:是什么令这
些年幼到连选举权都没有的小姑娘接连数周,夜以继日地出现在公园里
抗议呢?
韩国政府曾试图指责一些政治外围团体和试图挑衅的组织蓄意破坏
韩美之间的关系,然而此次抗议游行的规模如此之大,持续时间如此之
久,很快便令政府之前的解释显得空洞无力。这些孩子是怎么变得如此激进的?南加州大学的文化人类学家伊藤瑞子(Mimi Ito),一位致力
于研究青少年行为和通信技术之间的交叉关系的学者,引用一名13岁烛
光女孩的话解释了小姑娘参加抗议的动机,她说:“是因为东方神起
(Dong Bang Shin Ki,DBSK)我才来这儿的。”
东方神起既不是一个政党组织也不是一个热衷于政治活动的团体。东方神起只是一个男子
乐团(意为“上帝从东方升起”),各地的男子乐团都有这样一个习惯,乐队中的每一名成员都
象征着一种不同的类型:金俊秀浪漫可爱;沈昌珉高大英俊、健硕黝黑,等等。他们俊朗潇
洒,大多对政治漠不关心,也鲜有对外交政策的言论发表,就连抗议性的音乐作品都没有发表
过。然而他们却是韩国女孩儿们的重要注意力焦点。
当韩国市场重新向美国牛肉打开大门时,拥有近百万用户的乐队粉
丝网站“仙后座”(Cassiopeia)的公告版面上发布了禁令被取消的消
息,很多抗议者便是率先由此得知此事的。
“是因为东方神起我才来这儿的”和“是东方神起让我来这儿的”并不
是一回事。东方神起从未真正建议任何公共甚至政治活动。但他们的网
站或多或少向这些小女孩们提供了一个可以随心所欲讨论包括政治在内
的所有问题的平台。她们开始焦虑,事实上是接二连三的为围绕着重新
开放韩国市场可能造成的健康和政治问题而感到焦虑。女孩儿们对李明
博政府辱没国家尊严、危害民众健康的妥协行为惊恐万分,心怀愤懑,于是她们聚集在一起,决定要对此采取些行动。
东方神起的网站为成百上千的韩国年轻人聚集在一起提供了一个平
台,也提供了一个理由。在这个平台上,发生在校园或咖啡店里的原本
稍纵即逝的对话获得了两种此前只有专业的媒体制作人才能拥有的特
质:可及性和永久性。可及性的意思是一个人写的东西可以被一群人读
懂,而永久性是指给出的作品一直存在。当人们接触了网络之后,可及
性和永久性都会增加,而韩国是世界上人与人联系最为紧密的国家。首
尔居民利用电脑和移动电话上网的质量、速度和范围的平均水平均好于
伦敦、巴黎和纽约居民。诸如Pop Seoul 和K-Popped 这样的八卦娱乐媒体报道东方神起的时
候,从未曾询问过读者对政府食品进口政策的看法。同前面提到的两个
八卦网站一样,东方神起的公告板也不是一种特定的政治环境,但与八
卦网站不同的是,这些公告板也不是完全无关政治的。它们由其参与者
塑造,具有参与者所赋予的特征。主流韩国媒体报道牛肉禁令的解除,一小部分专业媒体制作者将此消息传达给一大批彼此不太搭界的业余媒
体用户(这是20世纪广播媒介和印刷媒介的常态)。与之不同的是,无
论什么时候东方神起的粉丝在“仙后座”上发布消息,不管是金俊秀剪了
新发型还是韩国政府的进口政策有变,都会像韩国报纸上的文章一样被
广泛公开地传播开来,远比电视上的消息更加唾手可得——因为网络上
的东西总比电视上的东西更容易被分享。此外,这些零星而业余的媒体
用户不是沉默的消费者,而是喧闹的制造者,他们本身就可以按照自己
的意愿对各种消息做出反应和转载。在针对疯牛病的抗议事件中,联合
起来的韩国民众们一个比一个激进,既使是13岁的孩子也不例外。
韩国对美国牛肉的政策究竟应当如何,很多人对此其实不甚了了。
但是李明博总统对协议做出的改变令韩国民众感到不安,他们本期望政
府在更改决议时可以顾及自己的利益,然而政府却没有这么做。当因年
幼而没有选举权的孩子们出现在街道上反对政府政策时,这一举动着实
撼动了政府——此前政府习惯于享受缺乏公众监督的高度的行事自由。
在这次围绕食品安全(当然,随着抗议的进行,教育政策和居民身份问
题也被一并提了出来)这样的街头巷尾热点问题的大规模抗议事件中,李明博政府的声望大打折扣。2008年2月李明博是以接近75%的支持率
进入内阁的,然而,仅在5月一个月,其支持率便骤然跌至不到20%。
到了6月,抗议仍然没有结束,李明博政府终于决定让抗议者适可而止了,于是下令警察镇
压抗议游行——警察饶有兴致地开始了行动。一时间,网络上到处充斥着警察用水炮和警棍袭
击并无暴力行为的抗议人群的景象;成千上万的观众在线观看警察踢打十几岁小姑娘头的视
频。镇压与李氏政府的初衷大相径庭。一时间,公众对韩国警察的谴责之声四起,甚至蔓延到
国际社会,亚洲人权委员会(Asian Human Rights Commission)等组织都开始着手调查此事。
由于暴力镇压,抗议得到了更多的关注,规模也更加壮大。6月10日是20世纪80年代韩国军国主义政府结束,重新恢复民主制
的纪念日。在临近2008年6月10日时,针对疯牛病的示威活动呈现出一
种全面的反政府抗议的趋势。无奈之下,李明博总统在电视上为没有充
分征询民众意见就取消美国牛肉进口的禁令而向全体国民道歉。至此,抗议活动结束了。他不得不迫使所有内阁成员辞职,重新议定从美国进
口牛肉的限制协议,从整体上向国民解释攸关自由贸易协议的究竟是什
么。他对民众说道:“此前我以为,在我任期满一年之前我若不对政策
做出些挑战就不能称之为胜任,因此,当选总统后,我有些操之过
急。”
李明博总统的一系列举措起作用了。虽然仍有人对李明博和李氏政
府及其某些政策不满意,但听到总统承认自己未直接向公众征求意见是
错误的,看见总统向采用极端手段镇压抗议的内阁直接开火,民众的不
满情绪大大缓解。尽管耗费了大量的政治资本,李明博仍旧取得了部分
胜利,而公园里的抗议者同样也赢得了一些东西。民众渴望在重要问题
上有话语权,如果正常渠道无法实现,那么像东方神起的公告板这样的
地方总能提供给大家他们想要的协调行动。
首尔的普通居民使用了一种对“从前作为受众的人们”(The People
Formerly Known as the Audience)既不鼓励沉默也不禁止发声的交流媒
体,这个说法是我纽约大学的同事杰·罗森(Jay Rosen)最喜欢用的。
我们习惯了依赖媒体将信息传达给我们:电视里的人告诉我们,由于恐
惧疯牛病,韩国政府禁止美国牛肉进口,同样也是电视里的人告诉我
们,牛肉禁令解除了。
然而,在韩国此次抗议期间,媒体不再仅仅是信息的来源,而同时
开始成为协调的核心力量。参加广场上抗议的孩子们使用东方神起公告
板,也使用Daum、Naver、Cyworld和其他一些门户网站的在线聊天室
进行对话。他们还通过手机发送图像和文字信息,不仅为了传播信息和发表言论,也为了依靠这些信息和言论采取行动——无论是在网上还是
在现实中。就因为这样做,这些孩子们改变了韩国政府的运行环境。
对网络的传统看法大多认为,它是一个独立的空间,一个有别于现
实世界的虚拟信息空间,是历史的一种偶然。追溯到当初网民数量还很
少的时候,我们日常生活中认识的大部分人还都不在这少数的网民中。
而现在,越来越多的人使用电脑和智能手机,虚拟信息空间的整个概念
都在退化。我们的社会化媒体工具不是现实生活的一个选项,而是它的
一部分,尤其是社会化媒体已经日益成为现实世界中应对突发事件的协
调工具时,就像在清溪川公园里所显示的那样。
这种与日俱增的公众参与所带来的的长期影响将会怎样,现在还不
十分清楚。韩国总统的任期是五年一届,所以李明博再也不用面对选
民。另外,韩国政府强势推行上网实名制
[1]。(值得注意的是,这项规
定只适用于月访问者超过10万人次的网站,这无疑给该规定增添了政治
意味。)政府试图将百姓带回到我们称之为知足常乐的状态。就这样,政府和人民之间的竞争开始成为一场军备竞赛,但这场竞赛的参与者是
崭新的阶层。当十几岁的小姑娘们无须专业的组织和组织者发起,就能
帮忙组织一场令政府焦躁异常的抗议时,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领
域。正如伊藤瑞子所形容的:
他们参与抗议大多并非立足于他们日常生活的具体条件,而是源于他们共享同一媒体而凝
结成的团结力量。尽管孩子们在网上所做的很多事都被看做是琐碎而无关紧要的,但正是这些
事练就了他们相互团结、相互交流的能力,最终,他们动员起来。从口袋妖怪(Pokemon)
[2]
到大量的政治抗议,不是独特的媒体表达形式,而是如何将这种媒体表述和社会行为绑定在一
起,造就了这独一无二的历史性时刻,也造就了当今崛起的一代。
关注数字媒体的人通常会担心面对面的交流方式会没落,但是在首
尔,世界上有线网络和无线网络最为发达的地方,数字媒体的影响却恰
恰相反。数字工具对于协调人类交往和现实世界活动至关重要。认为媒
体是相对隔离于“现实世界”之外的领域的传统观念,将不再适用于类似于针对疯牛病抗议的情况,事实上,也不适用于人们利用社会化媒体安
排现实活动的多种方式。不仅社会化媒体在崭新的族群——也就是我
们的手中有了新的一面,当沟通工具掌握在新的族群手中时,也会呈
现出新的特点。
新方法,解决老问题
交通问题,尤其是上下班高峰时段的交通问题,是现在亟待以社会
方式解决的现实问题。上下班都要历尽一番周折,更有千百万的人一周
有5天都要忍受这样的折磨。乍看之下这个问题似乎和媒体毫无关联,但有效解决交通拥堵的重要方法之一就是合伙搭车(carpooling),合
伙搭车的关键并不在于汽车本身,而在于协调。合伙用车并不需要新
车,需要的仅仅是现有汽车的最新消息。
PickupPal.com是众多新消息渠道之一,它是一个为协调路线相同的司机和乘客而设计的合
伙搭车网站。司机提供报价,如果乘客同意的话,系统就会让司机和乘客彼此联系。就像任何
一份一句话商业计划书一样,有太多的细节藏在后面,大到如何找出相近路线、相同时间以达
成一宗可接受的组合,小到如何在最少泄露个人信息的前提下让司机和乘客相互联系。
PickupPal同样面临着规模的问题——当司机和乘客的数量处于某一
临界数字以下时,系统很难运行,当然超过临界数字越多则越好。同样
是使用该系统的两个人,一个三次中配对成功了一次,另一个十次中配
对成功了九次,这两者对该系统的认可程度一定截然不同。三中一是备
选方案,而十中九则变成了常规。解决PickupPal规模问题的最基本方法
是从社交可能性较高的地方着手,再向其周边扩展。由于该系统对大城
市周边通勤最有效,与PickupPal合作的是可以向员工或成员发布拼车信
息(该策略亦能协助增强使用者之间的信任感)的公司和组织。
PickupPal同样整合了像facebook这样的现有社交工具,以便尽可能容易
地找到合适的拼车伙伴。上述这些策略非常有效:到2009年底,PickupPal.com已经拥有了107个国家的超过140000的用户。
PickupPal提供的服务和我们所知的认知盈余大致相似。当每个人都
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解决上下班高峰的拥堵问题时,办法只能是每个人
买辆车自己开。然而这样的“解决方式”无疑只能使问题雪上加霜。一旦
我们把上下班高峰问题当做协调问题来看,我们便能想到不仅是一两个而且是一大堆解决办法。在合伙用车的情景中,马路上的汽车数量会演
变成一种机会,因为每一辆有空位的汽车都有可能找到同路人。
PickupPal将过剩的汽车和驾驶员重新整合,把他们当做潜在的共享资
源。只要能使用允许群组交流的媒体,人们就可以依赖司机和乘客间的
信息变化寻求解决交通问题的新方法,此一方法使人人都能受益。
对大多数人都有益,却未见得对公交公司也有益。2008年5月,位
于安大略湖区的汽车公司Trentway-Wagar聘请了一位私家侦探来使用
PickupPal。侦探确认了PickupPal的运营方式如广告所述,并以书面文字
陈述了他支付司机60美元搭车到蒙特利尔的事实。凭借这一证据,Trentway-Wagar向安大略公路交通管理局(Ontario Highway Transport
Board, OHTB)请愿,要求关闭PickupPal网站,理由是PickupPal以帮助
协调司机和乘客的名义启动,但它运作得太好了,已经不像一个合伙搭
车网站了。Trentway-Wagar引用了《安大略公用机动车条例》(Ontario
Public Vehicles Act )第11章,其中规定合伙搭车只能发生在家庭和工作
两种情况下(学校和医院除外),并须在政府规定的线路内;同时,每
天的司机必须是同一个人;此外,汽油和途中的开支应按周支付。
Trentway-Wagar主张鉴于合伙用车曾经很不方便,因此应当一如既
往地“不便”,一旦这种“不便”消失,就应当有法令重新介入。奇怪的
是,一个机构在担负起协助解决某一社会问题责任的同时,亦扮演着保
护该问题的角色,因为这种机构的存在是以社会对其管理行为的持续需
求为前提的。公交公司提供着至关重要的服务——公共交通运输,然而
它们亦放纵自己去限制竞争,阻止把旅客从一个地方送到另一个地方的
替代性方式,就像Trentway-Wagar所做的那样。
安大略公路交通管理局支持Trentway-Wagar公交车公司的诉讼,下
令禁止PickupPal在安大略的营运。PickupPal就此事进行了抗辩,但在听
证会上失败了。然而公众开始关注此事,在油价飙升、重视环境、财政缩减的年代,几乎没有人站在Trentway-Wagar一边。从在线请愿书到T
恤销售,公众从各种渠道的回应都传递着同一个信息:保护PickupPal。
人们对于无法享受PickupPal网络服务所带来的不便进行的讨论激烈
到令政府无法回避。在Trentway-Wagar赢得了短暂几周的胜利之后,安
大略立法机关修改了公用机动车条例的相关规定,使PickupPal重新合法
化。
PickupPal主要从以下几方面利用社会化媒体:
首先,PickupPal能够迅速为其用户提供充足的信息以解决现实生活中的问题。PickupPal无
法在缺少令潜在司机和乘客共享其各自路线的信息交流媒介的条件下独立存在。
其次,它创造了集合价值(aggregate value)——用户越多,匹配的可能性就越大。原有的
逻辑,如电视逻辑,仅仅把观众当做个体的集合,每个个体都无法为彼此创造真正的价值。而
数字媒体的逻辑则不同,它承认这些从前作为受众的人们每天都可以为彼此创造价值。
同时,PickupPal依赖摒除网络媒体和“现实生活”的隔阂而存在。PickupPal以一种极端琐碎
的方式提供网络服务——它通过把用户配对而创造价值。但这种价值只能通过真实存在的司机
和真实存在的乘客,在真实存在的高速公路上驾驶着真实存在的汽车体现出来。
PickupPal是社会化媒体作为现实社会一部分而真实存在,同时又在
改进而不是脱离现实的一个例子。对为千万普通市民提供协调性资源的
公共媒体的利用,标志着现代媒体已经和我们熟悉的媒体大相径庭。诚
然,我们所熟悉的媒体大都是拥有专业的制作人和业余用户的20世纪媒
体模式,但其根深蒂固的经济和制度逻辑却并非始于20世纪,而是15世
纪。
古登堡经济原理或许不适用了
美因茨
[3]
的一位印刷商,约翰尼斯·古登堡(Johannes
Gutenberg),在15世纪中叶率先在欧洲使用了活字印刷。当时印刷厂
已经投入使用,但由于每页都要刻满文字,因此印刷速度非常慢且操作
费力。古登堡意识到如果将每一个字母都单独刻字,就可以根据所需将这些字母重新排列。这些雕刻好的字母活字可以用于编排新的页面,这
样就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将活字排列组成一整篇文章。
活字印刷术为善于思考的欧洲人带来了另外一些东西:书籍的极大
丰富。在古登堡之前,根本没有那么多的书。一名誊写员仅用一支羽毛
笔、一瓶墨水和一叠牛皮纸就能抄写一本书,但是整个过程非常枯燥,速度也极慢,因此一小本书的价格就非常昂贵。
到15世纪末,一个抄写员抄写一本500页的书大概要30个弗洛林,而里波利(Ripoli),一
个威尼斯印刷商,大概能以同样的价格印制300本同样的书。因此大多数誊写员都放弃了抄写现
有书籍。
13世纪,圣文德(Saint Bonaventure),一位圣芳济会的修道士,描述了人们写书的4种方式:完全抄录一部作品,一次从几部作品中进
行抄录,抄录一部现有的作品并融入自己的改编,或部分创作自己的作
品并从别处加以借鉴。以上每一种分类都有自己的名称,比如誊写员或
作家,但是圣文德似乎没有考虑到(当然更没有予以描述),一个人可
以创作一部完全原创的作品的可能性。在那个时代,很少有书存在,仅
有的书多半是《圣经》的副本,因此所谓的写书主要都是关于重新制作
或重新组合现有的文字,远远不是指创作新作品。
活字印刷术打破了这个瓶颈,当然日益壮大的欧洲印刷商做的第一
件事就是印刷更多《圣经》。印刷商开始将《圣经》翻译成通俗的语言
并印刷出版,用当时的语言而不是拉丁文。这样做不仅是为了方便,更
因为牧师们希望《圣经》可以成为布道的素材。随后印刷商开始出版亚
里士多德、伽林(Galen)、维吉尔(Virgil)和一些从中世纪流传下来
的作家作品的新版本。这还不够,印刷机可以印出更多的东西。印刷商
的下一步举措既简单又惊人:印刷新书。在活字印刷术出现之前,欧洲
大部分可读的作品都是以拉丁文的形式出现的,且至少有近千年的历
史。然而转瞬间,书籍便开始使用起了地方性语言,书的内容也变成了
讲述近几个月而不是几百年前的事情。此时的书籍数量繁多、品类不同、内容契合现实、语言通俗易懂。其实,“小说”(novel)这个词就出
现在这段时期,指的是具有全新内容的书。
然而这种从根本上解决生产力闲置的办法——创作人们之前从未读
过的新书,出现了新的问题,其问题主要是经济风险。如果一个印刷商
生产了一本新书但却没有人愿意读,那么他就失去了继续创造生产的资
源。而印刷《圣经》或是亚里士多德作品的印刷商就从来不用担心他们
印的书没有人读。每个出版新小说的印刷商都面临着风险,那么印刷商
该如何应对这种风险呢?
他们的答案是,让承担风险的人——印刷商,同时为书的质量负
责。没有明确的原因说明为什么擅长经营出版社的人就要同样擅长决策
哪本书值得出版。但出版社的开销很大,因此需要有专门的工作人员来
经营。因为材料得先于需求生产出来,所以一家出版社的经济风险在于
生产。事实上,承担一本书不畅销的可能性的责任标志着从印刷商(仅
仅制造神圣作品的副本)向出版商(为新生事物而冒险)的转变。
自古登堡以后很多新形式的媒体相继出现:图像和声音都被编码,形成照片或是音乐光盘,电磁波被用来制作收音机和电视。这些接踵而
来的变革,虽不尽相同,但同样具有古登堡经济(Gutenberg
economics)理论的核心概念:大量地投资。无论是印刷厂还是电视
塔,拥有一种生产方式的开销是很大的,这令追求新事物从根本上来说
成为了一项高风险的运作。如果拥有或经营一条很昂贵的生产线,抑或
需要聘请员工的话,那么你就适用古登堡经济原理。无论在哪里运用古
登堡经济原理,不管你是威尼斯出版商还是好莱坞制作人,你都要冒着
跟15世纪的经营管理一样的风险,那时的制作商要在读者阅读前判断哪
些书籍更优秀。在这个领域几乎所有的媒体都是由“媒体”创作的,直到
几年前我们还一直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只需要按一下“发表”的按钮
每年岁末,国家图书基金会(National Book Foundation)都会在其
颁奖晚宴上颁发美国文学卓越贡献奖(Distinguished Contribution to
American Letters)的奖章。2008年,该奖项授予了1976年出版的《女勇
士》(The Woman Warrior )的作者马克辛·洪·金斯顿(Maxine Hong
Kingston)
[4]。虽说金斯顿因为这部30年前的旧作而得到承认是桩喜
事,但她在演讲中讲述的一段发生在2008年的故事,却令在座的出版商
都不寒而栗。
金斯顿说,2008年初,巴拉克·奥巴马到她家乡夏威夷的时候,她写了一篇颂扬他的社论。
不幸的是,她投稿的所有报社都拒绝发表。而此时,她很高兴地意识到此次的拒绝并没有像过
去一样打击她。因为,现在她可以登陆Open.Salon.com,一个文学交流网站。正如她所说,“我
所要做的就是打字,然后点击一个标明‘发表’的按钮。是的,有这么个按钮。瞧!我的文章发
表了。”
是的,有这么一个按钮。发表文章曾经是我们需要获得许可后才能
做的事,我们要征得出版商的准许。而现在,我们不再需要如此了。出
版商仍旧在选材、编辑以及市场运作领域发挥着作用(例如,除我之外
还有很多人协助改进这本书),但是他们不再限定着个人和公共作品的
界限。从金斯顿关于遭拒的欣喜中,我们发现了一个长久存在但隐藏得
很深的真相。
以往,即便是“已经出版过作品的作者”,也无法单凭自己的能力出版作品。想想列出来的
这一组概念:公众的注意(publicity)、宣传(publicize)、出版(publish)、出版物
(publication)、宣传者(publicist)、出版商(publisher)。
[5]
所有这些都集中在使事物公众化的过程中,此前该过程极其困难、复杂并且开销极大,然而现在这些都已不成问题。
不得不说,金斯顿写的社论并不精彩。内容单调乏味,曲意逢迎,更谈不上有分析见地。政治话语并没有因为这一篇社论的出现得到任何
丰富。但发表自主权的增加,通常就会产生这样的结果。在古登堡之前,几乎每部书都是出类拔萃的杰作。在古登堡之后,人们所拥有的只
是看过就丢的****、乏味的游记和关于富绅的圣徒传记般的记述,这些对除了历史学家外的现代人来说毫无意义。媒体的最大张力一向莫
过于,自由和品质构成了两种相互矛盾的目标,也有人一直坚决主张,以牺牲出版物的质量为代价换取发表自由度的增长是得不偿失。
早在16世纪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
[6]
就发现:“书太多便成灾。根本没有限制狂热写作
的措施;每个人都必将成为作家;有些人为了名利而变得名声大噪,另一些人则是为了一己私
利。”爱伦·坡(Edgar Allan Poe)在1845年评论道:“这个时代最大的祸害就是每一门学问都有
太多的书。阻碍我们获得准确信息的最大障碍就是摆在读者面前乱七八糟的书,而我们必须从
中去其糟粕,取其精华。”
这些论断相当正确。出版自由度的增加确实降低了出版物的平均水
平——怎样才能避免这种情况呢?马丁·路德和爱伦·坡都依赖印刷机,他们很容易获得出版机会,但他们却希望出版机制不要增加出版的整体
数量:对我来说便宜得多,而对你来说还是遥不可及。然而,经济学却
不是这样解释的。普通人出版图书越容易,出版图书的质量也就越一
般,但参与公共讨论的自由度的增加多少会产生一些弥补价值。
第一个好处就是实验的形式得到了拓展。尽管活字印刷的广泛应用
大大降低了印刷品的平均质量,但同样刺激了小说、报纸和科学期刊的
出现。报刊令马丁·路德的《九十五条论纲》(Ninety-five Theses )和哥
白尼的《天体运行论》(On the Revolution of the Celestial Spheres )得
以广泛传播,变化的文本形式影响着今天我们所知的欧洲的崛起。某一
领域的成本降低意味着可以开展更多的实验,交流成本的降低意味着可
以开展更多关于思维和表达的实验。
这种实验的能力同时也扩大了创作者的数量并使其多样化。1991年
纳奥米·沃尔夫(Naomi Wolfe)
[7]
在她的《美丽神话》(The Beauty
Myth )一书中对女性杂志在女人一生中所起的作用表示既庆幸又难
过。她说,这些杂志为理所当然的女性观点提供了场所,但视角往往被广告人歪曲了:“广告商都是在蛮荒西部看似彬彬有礼的审查官。他们
模糊了编辑自由和市场需求的界限……一本妇女杂志的赢利并不是来自
其定价,因此其内容不能偏离广告内容太远。”在另一方面,在《美丽
神话》出版近20年后的今天,作家梅利莎·麦克尤恩(Melissa
McEwan)在她的博客上发表了一篇700字的有关日常女人厌恶症的有趣
随笔:
有很多关于女人的笑话……是对我感兴趣的男人为了撩惹我在我面前讲的,仿佛在滑稽地
提醒我二等公民的身份。当讲这些笑话的人将他们的快乐建立在他们知道他们会让我沮丧、厌
烦、受伤害的基础上时,我不打算理会这些欺侮我的伎俩。我要是笑了,他们会自我感觉良
好;我不笑,他们依然会自我感觉很好。总之怎么都是他们赢我输。
这篇题为“我们令人遗憾地达成可怕的交易”(The Terrible Bargain
We Have Regretfully Struck )的文章吸引了几百人参与评论,更引起了
上万读者的阅读,评论的大意都是“感谢你说出了我一直在想的东西”。
这篇文章之所以会被全社会所知道,就是因为麦克尤恩点击了标明“发
表”的按钮。其博客恰恰提供了沃尔夫想象的那种写作空间,在这里女
人们可以随心所欲地聊天,不必担心男人的监视抑或广告商的审查。这
里的作品不是写给任何个人的,也没有特意以政治意图激怒他人——但
要害也正是在这里。沃尔夫所说的杂志读者和博客读者可能会有同样的
反应,但杂志无法以激怒其他读者、特别是广告商为代价来取悦于这些
读者,杂志承担不起这样的后果。但麦克尤恩愿意(也有能力)为了说
出一些她想说的话而冒险得罪一些人。
沃尔夫所说的争论主要是针对女性杂志,但绝不可能只针对女性杂
志。麦克尤恩所用的自我发表的模式也不是独一无二的——现在人们一
天中会对各种各样的议题谈论上百万次,这些议题涵盖无数的兴趣社
区。社区成员可以像这样大声公开地彼此交流是一个巨大的转变,即使
在缺乏质量过滤的前提下,这种转变也十分有价值。诚然,这种价值的
产生正是因为无法提前进行质量过滤:对质量的定义越来越多,比主流
写作(以及音乐、电影等)尚能得到广泛的统一认识的时期多得多,每个团体的定义都不一样。
资源匮乏要比丰富更容易解决,因为当某样东西越来越稀少的时
候,我们会简单地想到它比从前更珍贵,这仅仅是一个概念上的小变
化。而丰富则不同:它的出现意味着我们可以开始像浪费一切廉价的
东西一样去处理此前珍贵的东西,仿佛它们便宜得能被拿去做实验似
的。 因为丰富改变了我们曾经习以为常的平衡状态,它能令在匮乏中
成长的我们迷失方向。当某项资源稀少时,控制该资源的人会觉得资源
本身很珍贵,而不会停下来考虑该资源的价值中有多少是由于资源稀缺
造成的。
美国长途电话费降低后的很多年里,我年长的亲属们仍旧会在打电话时声明这是“长途”电
话。这种电话先前的时候很特别,因为它们很贵。人们花了很长时间才明白便宜的长途电话与
此前觉得长途电话本身昂贵的认识是无关的。
同样地,当出版(使某事公开的过程)从困难变得轻松,习惯了旧
有体系的人通常会认为业余出版者出版的东西不好,仿佛出版是一件多
么严肃的事情,尽管它从来不是。当人们十分在意出版的成本和成果的
时候,出版显得是件很严肃的事情——如果出错太多就会面临失业。但
是如果这些因素不存在了,风险自然也就不存在了。一项曾经被视作很
有价值的活动被证明其价值只是一时的偶然,如同经济学的变化所显示
的那样。
美国小说家哈维·史威多斯(Harvey Swados)对简装书的看法
是,“美国公众读书习惯的革命,究竟是意味着我们将被淹没在一大堆
不断降低大众品味的垃圾中,还是意味着我们如今可以轻松获得越来越
多的便宜的经典书籍,这已经成为了一个对我们的社会和文化发展都非
常重要的问题。”
史威多斯对此的观察发生在1951年,当时简装本的图书已经流行20
年之久。奇怪的是,当时他自己也无法回答这个问题。其实这个问题的答案在1951年就已经显而易见了。公众无须在如洪流般的垃圾和广泛可
求的文学经典中做出选择,而是两者都可以拥有(我们也正是这样做
的)。
“两者都拥有”不仅是对史威多斯这个问题的答案,也是每当传播过
剩时的答案,这种过剩从印刷机发明就开始了。印刷最早是为了使《圣
经》和托勒密(Ptolemy)作品的传播价格更低廉,但所有这些旧有的
文化一点也满足不了科技的进步空间或者读者的期冀。即便是在今天,如果没有对新鲜事物的不断尝试,我们就不会有“不断增加的经典清
单”。如果世上存在某种简单的公式,可以让人写出连续数十年甚至几
个世纪都能得到赞誉的作品,那我们就不再需要不断尝试了。但事实是
没有这样的简单公式,因此我们的尝试仍须继续。
在不断尝试创造新事物的过程中,自由不断增加,随之增加的还有
劣质的材料,虽然尝试的目的是为了创造出广受赞誉的东西。这正是15
世纪印刷界的实际情况,也是当今社会化媒体的现实写照。和此前
的“匮乏”相比,“过剩”带来的是平均水平的下跌,但随着时间的流逝,不断的尝试终究会带来回报,多样化的发展扩大了新的可能,其中最好
的东西给我们带来了越来越好的作品。有了印刷机,出版业越来越重
要,因为文盲减少了,文化和科学写作造福社会,尽管随之也出现了一
大堆垃圾。
媒体,社会的连接组织
我们并非在见证印刷革命的重归,所有的革命都是不同的(就好像
是说所有的惊奇都是出人意料的)。如果社会的变化很容易被立即接
受,那么它就称不上革命了。而今天,革命集中在对业余爱好者融入
生产者的震惊里,我们发表公共言论时不再需要借助专业人士的帮助
或许可。 社会化媒体没有引发韩国的烛光抗议,也没有培养PickupPal
用户更多的环境意识。这些影响都是由意图改变公共交流方式的公民们
造成的,他们发现自己终于拥有了这样的机会。
这种公开发表言论以及将我们的才能凝结在一起的能力,与我们之
前习以为常的媒体的基础概念大不相同:我们不是在消费媒体,而是
在利用媒体。 因此,我们之前对媒体根深蒂固的概念现在正在慢慢剥
离。
以电视为例,电视将移动的图像和声音进行编码,先通过无线电媒
介,然后通过电缆传播,随后利用专门的解码设备再转化回图像和声
音。用这种方式传递的内容的名称是什么?答案是电视节目。那呈现图
像的设备又叫什么呢?答案是电视机。那制作播发内容、传递播放信号
的这些人叫什么呢——他们工作的领域又叫什么呢?答案当然也是电视
业。工作在电视领域的人们为您的电视机制作电视节目。
你可以从商店购买电视机在家里看,但是你买的电视机并不是你所
看的电视节目,你看的电视内容也不是你买的那台机器。单这样说或许
难以理解,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却一点儿都不难理解,因为我们从来都不
用刻意去考虑电视究竟是什么,而我们就用“电视”这个词统称一个集合
体的所有不同的部分:行业、内容和方式。这种表达方式让我们的认知
有些模糊,但如果我们总想弄明白现实生活中每个系统的每个细节,我
们会不堪重负。这样的集合体——既包括物体,也包括产业,还包括产品、服务和商业模式,并非独一无二地只在电视业存在。例如,收集并
保护罕见的初版书的人,和那些购买充斥于市场的言情小说,废寝忘食
地阅读,却在下一星期就把书扔到一边的人,都可以理所当然地被称为
爱书之人。
这种集合体之所以很容易实现,是因为公共媒体的大环境长久以来
一直很稳定。公共媒体最近的一次大变革还是电视的出现。在电视成为
中坚力量的60年里,我们看见的变化其实很小——比如盒式录像带或者
彩色电视机。有线电视是20世纪40年代末(电视开始普及)与90年代末
(数字网络开始成为公众生活的正常组成部分)之间媒体行业里出现的
最重要的变化。
“媒体”这个词本身就是个集合,同时指过程、产品和产出。媒体,正如我们说了几十年的那样,它主要表现为一系列产业的产出,由一个
特定的专业阶层经营,并且其中心在英语国家,即在伦敦、纽约和洛杉
矶。媒体这个词既指这些行业,也指它们所制作的作品,也包括那些
作品对社会的影响。 只要媒体环境相对稳定,那么以这种方式来阐
述“媒体”就是合理的。
尽管如此,有时我们还是不得不将一个体系中的每部分都分开来考
虑,因为这些部分无法一起运作。如果你花5分钟提醒自己(如果你还
没到30岁,那就用魔法召唤一下)20世纪的媒体对于成年人来说是什么
样的——由数个电视网络和一些主流的报刊杂志组成,而今天的媒体看
上去既奇怪又新潮。当环境稳定到连把经由电缆而不是天线获得电视信
号都能被当做剧变时,有一种媒体的出现会非常令人震惊,这种媒体能
让世界上的任何一个人都无限制地完美复制由他人无偿提供的作品。同
样令人震惊的还有这种媒体将广播和对话模式完全混合在一起,使二者
之间没有明显的区别。捆绑在“媒体”这个词身上的诸多概念正在解体。
我们需要一种新的针对这个词汇的概念,一种能摈弃诸如“某种由专业人士创造的供业余人士消费的东西”这样内涵的概念。
我个人认为:媒体是社会的连接组织(connective tissue)。
媒体就是你如何知道朋友的生日聚会在何时何地举行;媒体就是你如何了解德黑兰在发生
什么,特古西加尔巴(Tegucigalpa)
[8]
的领导者是谁,中国的茶叶价格是多少;媒体就是你如
何知道同事给他的孩子起了什么名字;媒体就是你如何知道你下个会议将在哪里开;媒体就是
你是如何知道10米之外在发生什么事情。
所有这些都可以被分为公共媒体(如一小组专业人士制作的视觉信
息或印制的传播信息)和个人媒体(如普通人的信件或电话),而现在
这两种模式已经融合在一起了。
互联网是后古登堡经济时代的第一个公共媒体。你根本无须理会互
联网的内在工作结构,只需体会它与此前500年间的媒体模式的不同之
处就足够了。因为所有的数据都是数字化的(用数字表达),所以不会
再存在类似于副本的情况。无论是一封电子情书还是一篇无聊的公司报
告,每条数据与同一数据的其他版本都是完全一样的。
你也可以看到这一点在日常生活中的体现。没有人会说,“给我一
个你电话号码的副本”。你的电话号码对每个人来说都是一样的。由于
数字这个奇异的特质,旧有的区分专业和业余人士的副本制作工具的方
式不复存在。过去印刷机为前者制作高质量的版本,复印机为我们复制
其他的东西,而现在每个人都能利用媒体制作完全一样的版本,以至于
旧有的鉴别方式根本无法分辨同样精准的原版和复制版。
另外,数码制作的方法是对称的。发射信号的电视台耗资巨大、配
置复杂,而接收信号的电视机却相对十分简单。当有人买了一台电视机
时,消费者的数量增加了一个,但创造者的数量并没有发生变化。而当
有人买了一台电脑或是一部移动电话时,消费者和制造者的数量都增加
了一个。天才的分布仍然是不平衡的,但是简单的制造和分享的能力现
在变得广为分布并连年扩大。数字网络不断增加着所有媒体的流动性(fluidity)。原本只能在单
向公共媒体(如书籍和电影)和双向个人媒体(如电话)间进行的选
择,如今扩展出了第三个选项:从个人到公众的可延展的双向媒体操
作。 各个群体可以在像广播一样的媒体环境下交流对话。这项新的选
择在原有的广播媒体和通信媒体间架起了一座桥梁。所有的媒体可以相
互转化。
一本书可以同时在一千个不同的场所引发公众的讨论;一封用于对话的电子邮件可以被参
与者公布出来;一篇供公共消费的文章可以引发私下的争论,而其中的部分内容也许日后也会
公之于众。曾几何时,像收音机和电话这样的公共媒体和个人媒体使用截然不同的设备和网
络,但现在我们正以从前从未企及的方式在个人媒体和公共媒体间不停地转换。
最后,新的媒体形式囊括了经济学的转变。互联网造成的情形是,每个人都在付费,然后每个人都得以使用。互联网并非单由一家公司所
有,并单独经营其整个体系,它只不过是一系列有关如何进行两点间数
据传递的协议。任何遵从此类协议的人,无论是个体的手机使用者还是
经营一家大公司的人,都可以成为网络的合格成员。网络基础设施并不
归网络内容制作人所有,它属于任何一个付费使用网络的人,无论出于
何种使用方式。这种向后古登堡经济学的转变很大程度上为我们所见
的慷慨、公开、有创造力的行为提供了便捷的方式,它有着可互换的
完美版本,彼此对话的能力,对称的产出和低廉的成本。
做“酒吧”里的业余人士
由于我们所了解的公共媒体直到最近为止都受到古登堡经济学的限
制,因此无须思考,我们就能估量到媒体亟待专业人士保证其存在的事
实。我们认定,我们作为受众,不仅仅被移交到被动消费的地位上,而
且喜欢这样的地位。在我们头脑中有关媒体业的潜在理论的指导下,前
述那种慷慨、公开而又极富创造力的行为看起来着实令人费解。与很多
令人讶异的行为类似的是,这种错误行为主要源于将某一偶然事件的发生当做是一个深刻的真理。
大家分享各自的作品、视频、病症甚至是车上空位的动机并不是对
金钱的渴求。有人经营像YouTube和facebook这样的服务是想要获利,而他们确实也做到了。业余爱好者无偿提供作品给那些通过收集和分享
这些作品来获取利润的人,这似乎很不公平,至少传统媒体的经销商会
付款给他们的撰稿人。在这种非专业人士能够分享作品的新服务形式
下,获益的不是心满意足的作者而是提供分享平台的所有者,这就导致
了一个明显的问题:为什么这些人要无偿劳动?尼古拉斯·卡尔
(Nicholas Carr)
[9]
称这种形式为“数字化佃农” (digital
sharecropping),在美国内战后的时期,佃农是那些在土地上耕作,但
既没有土地所有权也没有产品拥有权的农民。在数字化佃农形式下,平
台的拥有者赚钱,而写东西的人却赚不到,卡尔认为这种形式明显不公
平。
奇怪的是,真正遭受这种不公平待遇的当事人却并未对此表示义愤
填膺。那些分享照片、视频以及文章的人并没有期待回报,他们只是想
要分享而已。对于数字化佃农的不满在一定程度上只是专业人士的嫉妒
——明显是专业媒体制作人对业余玩家的竞争感到不安。但是也有另外
一个更深层次的解释:我们在使用一个专业媒体的概念来指代种种业
余人士的行为,而非专业媒体人的出发点和专业人士有着本质上的不
同。 如果我们把提供“大笑猫”的网站ICanHasCheezburger看做是15世纪
印刷模式的现代版模型,那么网站的工作人员无偿付出劳动的事实就不
仅仅令人讶异而更是有失公允。然而如果这些撰稿人不是工作人员又会
怎样呢?要是他们确实就是义务奉献,他们的撰稿行为纯粹是资源共享
而非商业出版又怎么样呢?要是他们的劳动是爱的奉献又该如何呢?
“大笑猫”可以被看做是一个传统媒体的路径,但这不意味着它遵循与《时代周刊》这样的
专业媒体路径相同的内在逻辑。打个比方,“大笑猫”就像是一个本土的小酒吧。酒吧是商业化
经营,那里卖的东西通常都是把便宜得多的东西加大利润出售。酒保提供的服务无非是开酒、洗盘子。如果酒吧里一杯啤酒的价格是商店里的两倍的话,那人们为什么不将酒吧关掉而直接
选择在家喝更便宜的啤酒呢?
如同YouTube的所有者一样,酒吧老板经营的奇妙之处在于他提供
比他兜售的商品和服务更有价值的东西,他的价值是消费者自己为彼此
创造的。人们愿意多花钱在酒吧喝酒而不在家独饮,是因为酒吧轻松的
氛围更适合喝酒。酒吧吸引那些想找人随便说说话或者仅仅是喜欢有人
在周围的人。和一个人在家相比,大家更喜欢呆在酒吧里面。这种诱惑
力足够大,两者间的差异也值得偿付。“数字化佃农”的逻辑意味着酒吧
老板在剥削他的消费群体,因为消费者在酒吧的交流是他们愿意多付酒
钱的原因之一。但事实上没有一个消费者的思维方式是这样的。相反,他们更愿意认为酒吧老板开辟了一个便于交际、饱受欢迎的环境,在这
样的环境里他们更有机会彼此交流,为此他们愿意多付些钱。
然而,“数字化佃农”的逻辑有时也的确适用,有时人们的感受也正
如卡尔假设的那样。“数字化佃农”影响最大的实例之一来自美国在线
(America Online,AOL)网络服务的志愿者们。
在20世纪80和90年代,美国在线迅速成长,因为人们发现其友好有益的形象很吸引人。它
的社区领导者们,一个完全自发组成的群体,经常出现在公共聊天室和其他场所,引导讨论、关注侮辱或诋毁的语言、在总体上维护大局平稳。1999年,这些领导人中的两个,布莱恩·威廉
姆斯(Brian Williams)和凯利·哈利塞(Kelly Hallisey)代表一万志愿者起诉美国在线,要求后
者至少应该为其劳动支付最低薪水。
假设威廉姆斯、哈利塞以及其他所有的领导人都自愿奉献他们的时
间,而且数十年如一日(威廉姆斯估计他所贡献出的时间有数千小时之
多),那就很难明白为什么后来他们会觉得自己遭受了虐待。答案在于
究竟是什么产生了变化,就如同某段关系变质了一样。在一次采访中,威廉姆斯痛斥在线服务的商业化。“现在的情况越来越像是公司试图从
原本免费的奴隶劳工身上榨取每一个美元。从前,在网站上没有现在这
些无处不见的广告,网站就是一个丰富的社区,人们为了在一起而在一
起,现在的情况完全变了。”这种从社团驱动到广告驱动的变化改变了领导者们的感受。当美国在线不再对他们的劳动提供看得见的欣赏后,他们开始套用“数字化佃农”的逻辑。(该诉讼到目前为止已经经历了第
二个十年,涉及数千名前任社区领导,至今尚未得到判决。)
人类对彼此联系有着内在的看重。基于这种现实,“数字化佃农”的
逻辑就丧失了其大部分的说服力。业余人士不是专业人士的缩小版。人
们有时乐于因金钱以外的原因而去做一些事。业余媒体与专业媒体不
同。帮助我们分享的服务之所以兴旺发达,就是因为这些服务使我们原
本就喜欢做的事现在操作起来更便捷和便宜。换句话说,市场的作用之
一就是为我们在市场之外所专注投入的事情提供平台,这个平台的形式
可以是酒吧,也可以是网站。15世纪的媒体制作模式尚不允许这样的分
享存在,因为其本身的成本和风险都导致需要有专业人士参与到运作的
每一个步骤中,而现在则不一样了。
工具,赋予我们行为发生的可能
我在纽约大学的互动电信项目(Interactive Telecommunications
Program)中任教,这是一个跨学科的研究生项目。在我任教的那些年
里,我的学生的平均年龄基本保持不变,而我的平均年龄却连年以惊人
的速度递增。现在我的学生都要比我小上15岁20岁。由于我一直以来都
在试图传递一种观念——媒体在不断地演变发展,因此我现在不得不把
我年轻的时光当做历史一样教授给我的学生们。看起来在我的学生们还
没到15岁之前,我成长中所经历的稳定的时代就已经结束了,这些孩子
们还在上小学的时候,我就在以成人的眼光看待媒体的变革了。
尽管近半个世纪以来,媒体一直在收缩,但我的学生对媒体范围的
了解还仅仅局限于信息量的不断丰富。他们从来都不知道曾经存在过这
样的媒体世界:电视里只有三个频道,傍晚观众唯一的选择是观看白人
用英语读报纸。他们可以理解这种从稀缺到过剩的转变,因为今天我们
还在经历这样的过程。但还有一件更难对他们解释清楚的事就是:如果你身为一名生活在那样的世界里的公民,当你觉得自己有必要公开发表
点意见的时候,自己却没有这样的权利。就是这样,媒体内容不是由用
户创造的。如果你有足够的资本可以在公开场合发表言论的话,那么从
严格意义上讲,你就已经不再是一名用户了。影评出自影评人,公众舆
论来自专栏作家,报道来源于记者。适于凡人谈话的空间仅仅局限于餐
桌和饮水机旁,偶尔会以书信的方式(这个方式太麻烦也很少见,以致
很多书信都是以“很抱歉这么长时间没有写信给你了”这样的话开
头……)。
在那个时候,任何人都能拍照片、写文章、创作歌曲,但是他们无
法令其创作出来的东西广泛流传。向公众传递信息是一件公众无法做到
的事情,由于缺少彼此轻易就能发生联系的能力,我们创作的动机都被
压制住了。对广播和印刷媒体的接触是如此受限,那些尝试制作点什么
的业余人士要么被猜忌,要么受到怜悯。自费出版作品的作者不是被当
做有钱人,就是被认做爱慕虚荣。发行小册子或是举着标语游行示威的
人都被当做精神错乱。《纽约时报》已故专栏作家威廉·赛菲尔
(William Safire)归纳出这种划分的界线:
数年来我屡次开车穿越马萨诸塞大道,途经副总统的家时,都注意到一个形单影只、意志
坚决的男人穿越这条街,他举着条幅说他被牧师鸡奸了。我断定那人一定是个疯子,但也正因
此我忽略掉了本世纪最大一桩宗教丑闻的线索。
当我告诉我的学生们普通群众的沉默都是装出来的时候,他们纷纷
表示赞同。但即便他们能够从智力上明白那个世界,我仍旧可以感觉出
来,他们对那个世界缺乏切身感受。他们从来都没有生活在一个不能公
开发表言论的世界里,他们很难想象那样的世界与如今他们视为理所当
然的参与行为环境究竟有何不同。
英国广播公司记者尼克·高英(Nik Gowing),在关于媒体危机的
《“漫天谎言”和黑天鹅》(“Skyful of Lies” and Black Swan )一书中,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2005年7月,伦敦地铁和公交车发生爆炸后的几个小时里,政府坚持认为是某种功率骤增造
成了此次巨大的损毁和伤亡。即便就在几年前,这种解释仍是公众得以知道的唯一信息,这也
给足了政府时间,令其在编造好反映事实真相的故事之前做好充分的事件调查。但正如高英所
说,“在公有领域(public domain)内,在前80分钟时间里,有1 300篇博文示意事件的起因是爆
炸物。”
当谎言对所有人都显得越来越明显的时候,政府实在无法坚持说事
件是由功率骤增造成的。可拍照手机和照片分享网站的全球化,使得公
众可以看见地铁的内部以及双层公共汽车的顶盖被炸得粉碎的影像——
证据与官方的解释完全不符。爆炸发生后不到两个小时的时间里,伊恩
·布莱尔爵士(Sir Ian Blair),伦敦市区警察局长官,公开承认此次爆
炸是恐怖分子所为。尽管他尚未完全掌控局面,他的助手也不赞成他这
样做,但他还是公开承认了,因为人们没等他开始说就已经试图去了解
事件真相了。此前,警察的选择是“我们要不要告诉公众点什么”,到
2005年,则变成了“我们要不要成为公众谈话中的一部分”。布莱尔决定
一开始就告诉公众真相,因为旧有的假定公众内部不会产生讨论的策略
已经失效了。
对我们的新举动感到惊讶的人们,认为行为是一个稳定型的东西,但事实并非如此。多年来人类少有动机上的变化,但是机会总是随着
社会环境或多或少发生着变化。在机会变化小的世界里,行为的变化
也就很小,但当机会有了大的变动,行为也会随之变化,只要这个机
会诉诸了人类的真实动机。
对认知盈余的利用使人们得以用更慷慨、更公开、更加社会化的方
式来表现自己,而不再保留自己原有的身份,比如用户和电视迷。这种
变化的原材料是我们的空闲时间,这样的时间我们可以用来投入到各个
事业中去,从娱乐到文化变革。然而,如果我们需要的只是空闲时间,那么现在的变革半个世纪前就该出现了。现在,我们还拥有任由我们支
配的工具,以及这些工具所提供给我们的新机遇。并不是我们的工具塑造了我们的行为,但是工具赋予了我们行为
发生的可能。 当今灵活变通、便宜便捷、万象包罗的媒体提供给我们
各种前所未有的机会。在“媒体”的世界里,我们就像孩子一样,安静地
在边上围坐成一圈,吸收着圆圈中央大人们为我们创造的一切。但现
在,这个旧世界已经让位于一个全新的世界,在这里大多数形式的交
流,不管是公开的还是私下的,都以某种形式可为任何人所用。尽管我
们接受这些新的正在发生的行为,而且新型媒体也为其存在提供了新的
方式,但我们仍旧需要解释原因。只有能帮助人们做其想做的事情时,新的工具才得以被利用。那么,到底是什么激发了这些从前作为受众的
人们开始参与到媒体活动中呢?
[1] 2005年10月,韩国政府发布和修改了《促进信息化基本法》《信息通信基本保护法》等法规。2006年底,韩国
国会通过了《促进使用信息通信网络及信息保护关联法》,规定韩国各主要网站在网民留言之前,必须对其身份证号等
信息进行记录。——译者注
[2] 口袋妖怪,日本任天堂公司于1996年推出的一款游戏。——译者注
[3] 德国莱茵兰·普法尔茨州首府和最大城市,位于莱茵河左岸,正对美因河注入莱茵河的入口处。——译者注
[4] 马克辛·洪·金斯顿,又名汤亭亭,华裔美国女作家,《女勇士》是其代表作。——译者注
[5] 这一系列词都含有“publi-”这个前缀,与“public”同源。——译者注
[6] 马丁·路德,16世纪欧洲宗教改革倡导者,新教路德宗创始人。——译者注
[7] 美国著名女权主义作家兼学者。——译者注
[8] 洪都拉斯首都。——译者注
[9] 美国作家,其著作主要涉及科技、商业以及文化方面,代表作有《IT不再重要》《浅薄》等。——译者注第3章 无酬的动机
为什么“葛洛班之友慈善组织”的参与者不仅没有报酬,还会搭上自
己的钱,却乐此不疲?为什么一群业余爱好者做的连专业设计师作品的
边儿都够不着的网站,会风靡美国?网络意味着我们最终发现,人们真
正感兴趣的领域是如此之广阔,广阔到疯狂的地步。数字网络让分享变
得廉价,让全世界的人都成为潜在的参与者。想要分享的动机才是驱动
力,而技术仅仅是一种方法。
内在动机是一张包罗万象的标签,把人们可能从一项活动中获得的
或基于活动本身的回报所造成的各种激励因素聚集在一起。
过去组织的门槛非常高,而如今这些障碍已经被大大削弱,我们中
的任何人都可以轻易地找到志同道合者。
驾驭我们认知盈余的手段是我们获得的一种新工具,它可以使参与
成为可能并给参与者带来回报。
乔希·葛洛班(Josh Groban)是受过古典训练的专业男中音歌唱
家,演唱那些被称做古典混合乐或是流行歌剧(popera,pop 与 opera的合
称)的歌曲,这是一种颇受欢迎的曲风——把一些歌剧的标准曲目的风
格,如《圣母颂》(Ave Maria ),融入到充满灵性的意大利和英国流
行音乐,如《在阳光下》(Alla Luce Del Sole )、《为了你》(Per Te )
和《举起我》(You Raise Me Up )中去。葛洛班非常成功,到目前为止,他的4张专辑在美国都创造了200多万张的销量。他有才华、充满激情,而又魅力四射,他的粉丝团上至奶奶级别,下至青春少女。换句话说,他所拥有的听众,用传统媒体是很难聚集在一起的,因为没有一个广播
节目会覆盖如此广泛的年龄段。这使得葛洛班写下了一个成功利用网络的故事。像东方神起一样,他的歌迷通常会网罗新的歌迷。歌迷们用一种口口相传的营销模式迅速
为他做宣传。你可以在JoshGroban.com 上见到他们,在那里骨干粉丝团
称自己为 “葛洛班之友”(Grobanites), 所有有关葛洛班的事情则被叫
做“班务”(Grobania)。
如今,一个艺术家利用网络寻找粉丝的故事屡见不鲜,有意思的
是,粉丝们聚在一起的时候会发生些什么。
2002年,一些“葛洛班之友”计划在葛洛班21岁生日的时候送他礼物。礼物的选择让粉丝们
很为难:毕竟,他们喜欢的人是一个年轻的成年男人,并且这个男人已经得到了名望、财富和
无数的仰慕。他还想要什么呢?经过“葛洛班之友”们的一番讨论,很多想法被驳回,比如一个
男人需要多少泰迪熊呢?茱莉·克拉克(Julie Clarke),“葛洛班之友”之一,提出了募捐的建
议,以葛洛班的名义进行一次慈善捐款。他们决定把所筹善款捐给大卫·福斯特基金会(David
Foster Foundation),该基金会是一个慈善团体,由葛洛班的制作人经营,帮助弱势群体中的青
年人。克拉克同意承办这次捐赠,并最终筹集到了1000多美元的善款。葛洛班很惊喜,大卫·福
斯特基金会也很高兴,捐款的人也洋溢着成就感。
看到这次的成功,克拉克和另一位在筹集资金活动中认识的“葛洛
班之友”瓦莱丽·索奇(Valerie Sooky)一起把筹集善款当做“班务”的一
部分。每当葛洛班巡回演出的时候,他的粉丝都会在演唱会前聚在一起
欢迎他。“葛洛班之友”们在每次这样的聚会时都会进行募捐,每次往往
都会募集到上百美元。这类募捐使得粉丝们每年可以聚一次,但
JoshGroban.com每天都在进行着募捐。因此,克拉克建议举办一场在线
慈善拍卖为葛洛班明年的生日做准备。她和索奇拉来了梅甘·马库斯
(Megan Markus),这个19岁的“葛洛班之友”热切希望能够帮忙设计拍
卖网页。所有这一切显然都是业余爱好者的“杰作”:这是马库斯第一次
做网页设计的工作,很多拍卖物都是“葛洛班之友”自己做的或是捐出来
的。拍卖系统很笨拙,所有的叫价都不得不手动输入。最后,在花了几
个星期学会运行不熟悉的软件之后,这些“葛洛班之友”们举行了第一次
拍卖。几天下来,他们筹集到了16000美元,比以往任何一次募捐筹到的
钱都多。接着,他们进行了一场又一场拍卖。一年中,他们募集到了
75000美元。为葛洛班下一个生日进行的捐款使筹款额达到了顶点,仅
此一次就筹到了将近24000美元。
克拉克、索奇和马库斯意识到她们做的事情非常有意义。钱还是源
源不断地进来,但当每个人都高兴地支持大卫·福斯特基金会的时候,资金却并不是由福斯特的人筹来的。因此,他们问葛洛班,他们怎么样
才能更加紧密地一起工作。这对葛洛班的律师来说是一个挑战,因为这
确实是一桩新鲜事——艺人建立慈善组织通常是由艺人自身提供资金
的,因此,并没有有组织地从粉丝那里接受捐赠的先例。
最终,葛洛班的律师根据501(c)3条款
[1]
,创建了一个非营利性的
公司,并起了一个虽缺乏想象力但很实用的名字:乔希·葛洛班基金会
(The Josh Groban Foundation)。其主要职能是建立了一个合法的募捐
渠道,使得有慈善心的“葛洛班之友”们以葛洛班的名义募捐,使基金会
得到捐款,然后分配钱款。一时间,这个公司运行得很好——“葛洛班
之友”们继续募捐并且确定有价值的新的受益人(目前同基金会合
作)。
到2004年,慷慨的“葛洛班之友”们发展得比基金会本身还要快,作
为一种支付钱款的引擎,没人能联系到基金会中的人,甚至连一个邮箱
地址都没有,而随着“葛洛班之友”人数不断增加,内部管理问题也变得
更加复杂。当组织在规模、年限、抱负上增长的时候,类似的事情总会
发生。对“葛洛班之友”来说,三个问题同时出现了。建立者探讨着该怎
样处理新出现的复杂情况:他们是应该变成乔希·葛洛班基金会的志愿
者分支还是成立他们自己的组织?经过一年多的讨论(临时性的小组经
常会在一起讨论),他们是粉丝、想要联系更多的粉丝这一事实左右了
他们的决定。“我们是他们中的一员,他们认识我们,他们相信我们。”后来索奇跟我解释的时候这样说。最终,他们建立了一个自己的
非营利性组织——“葛洛班之友慈善组织”(Grobanites for Charity)。
最初的生日募捐和开始时的社会责任最终促使了两个组织的建立,目前两个组织组成了一个整体行使职能:“葛洛班之友慈善组织”筹集资
金,“乔希·葛洛班基金会”分配资金。
与传统的慈善机构相比,“葛洛班之友”的一切都背道而驰。通常的非营利组织,像“救助儿
童”(Save the Children)和“塞拉俱乐部”(Sierra Club),都是先建立组织,再招募成员;先成
立机构,再筹集钱款。“葛洛班之
友慈善组织”却是先有成员,再有目标,在成立机构之前,其成员就已经在筹集善款了。并
且,建立者甚至是在他人解决了所有的法律问题后才成立机构的。
葛洛班之友的成功接踵而来。其他的“葛洛班之友”团队也开始做慈
善工作。“葛洛班之友为非洲”是“葛洛班之友慈善组织”下的一个尚未被
承认的分支机构,为对抗非洲的贫穷和艾滋病而努力。这个团队是在葛
洛班全球巡回演出第一次到南非之后建立的。在那里,葛洛班见到了纳
尔逊·曼德拉(Nelson Mandela),并宣布为了非洲儿童支持慈善事
业。“葛洛班之友”中准备欢迎他到亚特兰大巡回演出的一队人决定,为
了葛洛班的这个目标单独组成一个机构,同其他“葛洛班之友”以及乔希
·葛洛班基金会紧密合作。至今,“葛洛班之友为非洲”已经筹集到了15
万美元的善款。
对于“葛洛班之友慈善组织”来说,最重要的问题不是“他们哪儿来
的时间开展慈善事业”,我们知道“葛洛班之友”有自由的时间,也能够
在他们想要联系媒体的时候与媒体联系上。“他们怎么协调各个团
队?”这个问题也不重要。该问题的答案我们也很熟悉:JoshGroban.com
为人们提供了一个聚会、分享想法和目标、彼此鼓励的场所,也给予他
们一个招募志同道合的“葛洛班之友”的机会。
令人迷惑的问题是“为什么”。为什么这些女性把筹集钱款放在第一位?为什么在乔希·葛洛班基金会已经存在的基础上,“葛洛班之友慈善
组织”还会成立一个单独的机构?这可不是“大笑猫”,经营“葛洛班之友
慈善组织”是一项艰巨的工作。参与者不仅没有报酬,还会搭上自己的
钱。所有的事情都是在网上进行的,是什么促使人们为了没有明显回报
的东西放弃自己的时间和金钱呢?
热爱胜于金钱
1970年,罗切斯特大学(University of Roshester)心理研究专家爱
德华·德西(Edward Deci)做了一个非常简单但却至今仍有争议的实
验。
这个实验是在一种名为“索玛”(Soma)的解谜游戏的基础上进行的。索玛立方体是一个木
质立方体,能分为7小块。每块的形状都是唯一的,有T型,L型等。这7小块只有一种方法才能
组成一个大立方体。此外,它们也能组成数以百万计的其他形状。索玛立方体的玩法是对照着
要组成形状的图纸,然后把这7小块组装成图纸中的形状。实际做起来比听上去要难。德西正是
基于这种玩法来开展他的观察的。
实验伊始,德西把索玛木块和能用它们拼成的三四种形状的图纸给
实验参与者们。当被试(都是男性)熟悉了那些小木块时,德西便让他
们把这些木块拼成图表中那三四种形状,但没有告诉他们如何组装。德
西对数十组被试都重复了这个过程,所有被试都以为组装这些形状就是
实验本身。事实上并非如此。在做出说明并对被试们观察了大半个小时
后,德西会离开教室,告诉参与者们休息一下并等他回来。在他离开教
室的时候,德西通过一面单面镜对被试观察了整整8分钟。被试们在这
休息的8分钟内的行为才是实验的真正内容。
当德西不在的时候,被试们可以自由活动。德西在实验室里放置了
杂志和其他设施(因为那是20世纪70年代,因此杂志包括《纽约客》
《时代》和《花花公子》,外加一个烟灰缸)。尽管这些东西很容易拿
到,但仍有很多被试继续自觉地玩着这个解谜游戏,在这8分钟里他们平均花4分钟在索玛上。德西返回后便解散了被试,记录下他们在休息
时的活动,并以此做为实验的参照。
而后德西邀请同一批被试进行了第二批索玛解谜,但其中有一点不
同。这次他让一半人和上次一样解谜;而对于另外一半,他告诉他们每
拼出一个图案就能得到一美元(在那个年代一美元对参与实验的学生来
说很值钱)。同样他们会被要求休息,留在实验室里被秘密地观察8分
钟。那些知道立方体可以成为他们潜在收入来源的被试平均比他们先前
在休息时间钻研索玛立方体的时间多了1分钟。
然后德西又做了第三个实验,这次他只是简单地重复了他最初做的
那个实验:所有被试都被要求组装图案,并且没有人会得到收入。在这
个阶段,尽管他们每人都收到同样的指令,但那些在前一个实验中获得
收入的人们,在休息时对组装图案的兴趣比他们能获得收入时的情况明
显下降。他们在索玛上花的时间平均下降了2分钟,也就是说在收入被
剥夺后,他们的关注时间下降了两倍,正如当收入被计入实验时,他们
的关注时间上升了两倍一样。尽管在第一个实验中他们会自觉地玩这个
解谜游戏,但当他们又一次有机会自觉玩游戏时,先前获得收入的记忆
很轻易地就降低了他们的兴趣。
在心理学文献中,为了阐释自愿参与而设计的实验被称为“自由选
择”(free choice)测试——当某人能控制自己的行为时,他有多大的可
能会表现出一种特定的行为?德西的索玛实验发现,解谜游戏的报酬会
降低同一行为的自由选择度。
德西的结论是,人类的动机并不纯粹是附加性的,为了兴趣而做
事和为了报酬而做事是截然不同的。 这个实验证实了一个心理学理
论,动机分为两大类——内在动机和外在动机。内在动机能让行为本身
就成为一种回报。 在索玛立方体的案例中,那些在休息时继续解谜的
参与者们很明显是被拼装成功的满足感激起了兴趣。而对外在动机来说,回报来自于行为之外,而不在于行为本身。 报酬就是外在动机的
一个经典例子,这也正是为什么让参与者通过拼装图案来得到报酬的原
因所在。
得到丰厚的报酬可以让原本不受欢迎的行为变得受欢迎和划得来
(因此社区里才能雇用到垃圾工)。但德西的实验提出,外在动机并不
总是最有效的动机,增大外在动机实际上可能降低内在动机。他断定,像得到报酬这样的外在动机能驱逐像喜欢该事物本身这样的内在动机
(一种动机驱逐另一种动机的概念也存在于关于电视观看的文献中——
看电视驱逐了社交活动)。
自那以后,其他研究者也开始了对驱逐效应(crowding-out effect)
的研究并得到了类似的结论。
1993年,布鲁诺·弗雷发现,当瑞士居民被问起,如果政府要在他们的生活区域里建造一座
核废料贮藏库,他们是否会赞成该计划时,对这个问题的赞成和反对之声基本持平。当弗雷改
述了这个问题,告诉他们如果建造废料贮藏库,那么政府可能给他们发放补贴时,民众态度反
而变成了以三比一的比例反对这个计划。当建立废料贮藏库变成一种能获得政府补贴的行为,而不是一种公民义务时,这种行为不受欢迎的程度上升了两倍。
弗雷和他的同事洛伦茨·戈特(Lorenz Goette)最近的研究表明,在
真实世界中,当钱被用来作为志愿行为的回报时,它会降低志愿者贡献
的平均劳动时间。马克斯·普朗克考古人类研究所(Max Planck Institute
for Evolutionary Anthropology)主任迈克尔·托马塞罗(Michael
Tomasello)最近出示了一些实验性证据证明,把外在的报偿和14个月
大的婴孩喜欢的活动联系在一起,而后又将其取走时,这种驱逐效应在
他们身上也会发生。
出发点是兴趣还是金钱,会让人们在做事时表现得不一样,这一观
点似乎并不会让那些既有工作又有业余兴趣的人感到惊讶,然而心理学
界却有很多人认为德西的结论并非真理。1970年,人类动机理论以及在教室和工作场所对报酬的实际应用,常常基于简单的刺激观念——对现
有活动增加新的酬劳能让人干得更多。这一构架几乎没有对不同的动机
进行区分,并且现钞始终是一种具有最多功能的刺激因素。德西关于酬
劳能驱逐其他动机的结论对已有理论和实践是个公然的违抗,他对驱逐
效应的实验和其后的研究提出了一种学术性异议,这一异议一直持续至
今。
1994年,阿尔伯塔大学(University of Alberta)的朱蒂·卡梅隆
(Judy Cameron)和大卫·皮尔斯(David Pierce)分析了一系列实验参
与者完成各种任务并获得报酬的研究结果。他们的元分析(将多个研究
结果进行分析的称谓)彻底否定了这种驱逐效应的存在。德西和他的研
究伙伴理查德·瑞恩(Richard Ryan)于1999年做出回应,他们指出卡梅
隆和皮尔斯的分析中包含了许多诸如“若你支付报酬,人们就会被激励
着去完成他们不感兴趣的任务”这样的研究,这些结果本就毫无争议。
而德西所调查的是内在动机对一件参与者感兴趣的事情的影响。德西和
瑞恩自己的元分析在去除了一些令人厌烦的任务后,又一次发现了驱逐
效应。卡梅隆和皮尔斯在2001年的第二次元分析中承认对自由选择的驱
逐效应可以在外在动机介入的时候产生。尽管如此,卡梅隆和皮尔斯仍
对驱逐效应在真实世界中是否重要保持怀疑。他们关注的主要是院舍式
环境中出现的报酬,譬如学校和工厂。对他们而言,驱逐效应似乎集中
在人们有很大自由来选择自己行为的环境中。因此卡梅隆和皮尔斯认定
虽然驱逐效应是真实的,却也是小众的。毕竟,有多少地方能让人们对
行为的自由选择仅仅和自己有关?
然而,在一个自由时间和才能已经是相互联系的资源的时代,这个
问题的答案是“到处都是”。
自治和胜任感
德西对于内在和外在动机以及金钱驱逐兴趣的理论框架,很清晰地
解释了葛洛班之友慈善组织。当涉及到对善款去向的决定时,慈善机构
间的差异非常大:有多少钱能流入实际受益人手中,有多少用于日常运
营花费,其中包括机构管理人的薪水。美国慈善协会(The American
Institute of Philanthropies)把那些将募集到的善款的40%作为运营费
用,另外60%用于慈善事业的慈善机构定义为合格——不糟糕,但也不
算好,而运营费用控制在15%,捐献出85%善款的慈善机构则可以被评
为优秀。那么葛洛班之友慈善组织呢?他们会提取从伙伴中募集而来的
善款的百分之多少用于运营呢?答案是百分之零。他们卖很多力气,但
并不从中获得薪水,甚至愿意投入尽可能多的时间和金钱。葛洛班之友
慈善组织并非一种偶然形成的热爱,而是经过设计和“共同努
力”(incorporated)的热爱行为。实际上“共同努力”这个词就是“付诸实
践”(embodied)的意思——共同努力就是一个群体将努力和目标付诸
实践的具体表现。
内在动机是一张包罗万象的标签,把人们可能从一项活动中获得
的或基于活动本身的回报所造成的各种激励因素聚集在一起。 德西把
两种内在动机标注为“个人的”:自治的愿望(指决定我们做什么,怎
么做)和有胜任感的愿望(指能够胜任我们所做的事)。 在索玛实验
中,在休息时间仍然继续组装那些方块的学生就是受到自治的愿望(工
作在他们掌握之中)和有胜任感的愿望(索玛立方体是一种通过持续努
力就能在技术上有所提高的游戏)的推动。这一发现在游戏中十分典
型。一个关于电子游戏的研究表明,最吸引玩家的并非游戏中高仿真的
画面和暴力场景,而是玩家在精通这个游戏后能够控制并胜任它的感
觉。
另一方面,通过组装方块来获取报酬的那一组人的内在动机消失了。他们对于自治的感觉由于可以预见的外在动机的出现而被驱走了。
同样,基于胜任的愉悦感一旦被报酬所影响,就不再成为一种愉悦。当
他们提高解谜能力是出于增加报酬的目的时,那么基于游戏本身来完成
同样的任务就失去了足够的价值,这也就破坏了人们的自由选择。
同样地,葛洛班之友慈善组织和乔希·葛洛班基金会也并非仅仅在
合同和薪水方面有区别。这两个组织在保留葛洛班之友内在动机的方式
上,每一个方面都不一样。
例如,葛洛班基金会甚至没有自己的网站,它只在JoshGroban.com网站上有一个登载简讯
和新闻稿的小小板块,干净、专业、充满极简主义。而葛洛班之友慈善组织的网站看上去则完
全不一样,它就像1996年那个年代匆匆建立起来的东西,一圈套一圈,这种调调在早年的网站
设计中很普遍——手绘的心形列表,提示浏览部分的彩色标签,等等。换句话说,它看上去很
业余,而实际上它就是由业余爱好者创立的。它不但“不专业”,而且是出于“业余爱好”这个词
的本意而被创立的:某人出于热爱而做一些事情。
马库斯从十几岁时开始就一直为葛洛班之友们设计网站,最早的拍
卖网站就是她的第一项成就,为葛洛班之友慈善组织设计网店是一笔很
可观的学习经验。在工作中学习,看上去可能和感觉到胜任感的愿望背
道而驰,但是胜任感是一种移动目标。
接手一项过于庞大繁复的工作可能会让人泄气,但接受一项过于简
单、毫无挑战的工作同样令人感到无趣和无精打采。胜任感最容易产生
于当工作处于能力范围边缘时。“我自己完成了一件不错的事情”的感觉
总是比“请专业人士替我完美地完成了这件事”的感觉要好得多。
这种效果很普遍。追溯到最初的网络年代,一个叫做Geocities的网
站为它的用户提供个人主页,人们可以在主页上发表文章、图画和照片
等任何东西给别人看。这个网站启动的时候,我正在纽约为一家网络设
计公司管理制作部门,当时我很确信Geocities会倒闭。我看到过为了设
计一个有用的网站而进行的大量工作,从导航、设计到排版,我知道一
群业余爱好者做的东西甚至连专业设计师作品的边儿都够不着。当时网络上遍布专业网站,没有人会想要他们那些看起来平淡无奇的页面。
我对于Geocities网页设计水平的判断是正确的,但对于它的流行程
度,我的判断大错特错。它很快就成为了当时最受欢迎的网站之一。我
当时没有理解到的是,设计水平并不是衡量一个网站的唯一标尺。网页
并不仅仅需要单一的品质,它们需要各方面的品质。设计简洁固然很
好,但其他方面的品质或许更重要,例如亲自完成一件事的满足感,或
在完成事情的过程中学到了东西。人们不会主动寻求糟糕的设计,这只
是因为大多数人并非好的设计师,但这不会让他们停止自己创造事物。
自己创造的事物就算很普通,和消费别人创造的质量上乘的事物相
比,它仍然有一种与众不同的吸引力。 我对于Geocities所犯的错误,源自于我以为业余爱好者们除了消费以外不会做任何事情——那也是我
最后一次犯那样的错误。
成员资格和慷慨
2006年,哈佛大学法学教授尤海·本克勒(Yochai Benkler)和纽约
大学教授海伦·尼森鲍姆(Helen Nissenbaum)写了一篇标题长得让人一
口气读不下来的论文:《基于公地的对等生产和美德》(Commons-
Based Peer Production and Virtue )。“基于公地的对等生产”是本克勒称
呼那些依靠志愿贡献来运营的系统的术语——那些依靠认知盈余的系
统。他们在文中对这种参与所依赖和鼓励的积极特性进行了阐述。和德
西一样,本克勒和尼森鲍姆关注个人品性,如自治和胜任感。不同之处
在于,德西的索玛立方体实验主要关注个人动机,而他们则花了大量时
间在一种只有我们成为团体中一员才能感觉到的动机——社会动机上。
他们把社会动机划分为宽泛的两大类:一类围绕着联系和成员,另一类
则围绕着分享和慷慨。
在观察了一些参与性的例子,尤其是同伴们通过分享进行的软件开
发(此一模式叫做开源软件)的例子之后,本克勒和尼森鲍姆认定社会动机能加强个人动机;我们新的传播网络鼓励成员加入和分享,两者无
论从自身还是对外部来讲都是有益的,并且它们也能为自治和能力提供
支持。德西早先的索玛立方体实验的确抓住了这一效应的一条线索:
像“你很棒”或者“你玩这个游戏比平均水平好多了”。这些完成索玛立方
体解谜后的口头回报能让他们更好地完成解谜,这种改进甚至在口头反
馈结束后仍能持续下去。口头反馈似乎就像另一种外在报酬,如同金钱
一样。然而当它被很真诚地表达出来,并且出自于某个接受表扬者所尊
敬的人之口时,它就成为了一种内在回报,因为它的形成依赖于一种联
系的感觉。
组织的社会形式甚至可以影响到那些看上去最私人化的议题。凯瑟
琳·斯通(Katherine Stone),一位为遭受焦虑症的妇女谋求福利的倡议
者,注意到了近来越来越多的产后志愿团体通过Meetup.com网站组织起
来,该网站提供的是一种用互联网来协调真实世界中具有相似兴趣者在
线下会面的服务。斯通将这种快速增长的现象解释为:“经历产后抑郁
症的妇女想要并且需要和其他与自己一样的妇女谈心、分享,来证明她
们不孤单,来证明她们会康复。”想要分享的动机才是驱动力,而技术
仅仅是一种方法。
对于个人和社会动机的反馈环可以应用于大多数认知盈余的使用情
形,从维基百科,到拼车网站PickupPal,再到葛洛班之友慈善组织。葛
洛班之友们的捐赠者和支持者们得到了两种信息:我这么做了和我们这
么做了。
在成员和分享方面产生变化的潜力表现在葛洛班之友网站的设计
上。现如今,设计一个网站似乎和形成成员归属感关系不大,但由业余
爱好者设计的东西,实际上可能比专业设计师的设计更好地创造了成员
环境,恰如“大笑猫”网站所传达的信息:你也能玩这个游戏。
作为一种类比,想象一下你在《美丽住宅》和《美好家园》杂志中所看到的各种厨房,它们的设计十分完美,所有的东西都各就各位,所
有的东西都井井有条。我的厨房不是那样的。(没准你的也不是那
样。)但如果你是一次宴会的客人,你可能都不敢踏入一个像《美丽住
宅》里那样的厨房,因为它的设计实际上并不是在向你大声喊着“进来
帮忙吧!”另一方面,我的厨房大声喊出的是“如果你愿意的话,你不必
因为自己拿着刀切胡萝卜块而感到不安。”
马库斯的葛洛班之友慈善组织网站也沿着类似的方向发展。它的设
计和JoshGroban.com相比显得不怎么高雅,但它无论是形象还是气质看
起来都非常有魅力,这个网站的方方面面都体现着这种魅力。首页上各
种各样的链接和你想象的差不多——捐献、拍卖、关于我们,等等。此
外还有一个叫做“感谢您”的部分,看上去像这样:
特别感谢……
·莎丽,她慷慨地贡献出自己的时间来编织款式新颖的运动衫、T恤衫和无檐小便帽来为慈
善筹钱。
·艾伦,她捐献出乔希(和大卫·福斯特)的肖像,为慈善筹得数千美元。
·琳达,她制作了我们葛洛班之友慈善组织的卡片,并把这些感谢卡片寄给大卫·福斯特基金
会的捐 ......
您现在查看是摘要介绍页, 详见PDF附件(3215KB,18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