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的快乐.pdf
http://www.100md.com
2020年2月20日
 |
| 第1页 |
 |
| 第10页 |
 |
| 第11页 |
 |
| 第22页 |
 |
| 第36页 |
 |
| 第343页 |
参见附件(2235KB,393页)。
哲学的快乐,哲学在我们生活当中看似没有太多的关联,可是哲学又能为生活带来快乐和激情,这本书以哲学的方式来介绍生活,让你的生活更加的精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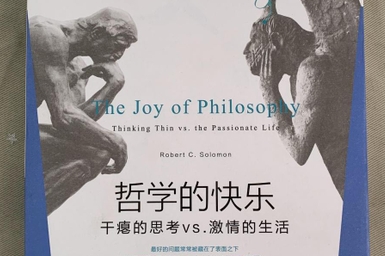
哲学的快乐介绍
在本书中,所罗门教授以哲学的干瘪和职业化为主线,用他所受的分析哲学训练与对大陆哲学的热爱,以一种存在主义的情怀,重新追问什么是激情、正义、悲剧、死亡、自我等等,论辩这些奠基哲学的永恒追问所受的冷遇,探讨理性的人类该如何运用自己的各种情感,突破理性的界限,拥抱爱和智慧,过上善与好的公共生活和个人生活,并让每个热爱思考和生活的人,都能勇敢、真诚地去发现并珍惜哲学中蕴含的无穷快乐。
哲学的快乐作者
罗伯特·所罗门(1942—2007),世界著名哲学家和哲学教师,生前是美国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的“QuincyLee百年纪念”讲席教授和杰出授课教授,特别擅长用日常生活中的例子来解释大哲学家复杂的思想,同时又不失其严格性。他在密歇根大学获得博士学位,曾在普林斯顿大学、匹兹堡大学和加州大学执教,尤精于尼采、存在主义哲学和情感理论的研究。
哲学的快乐主目录
导言丰盈和干瘪的哲学
第一章激情的生活
第二章情感的政治
第三章合理性及其兴衰
第四章正义、同情、复仇
第五章生活的悲剧感
第六章直面死亡的思考
第七章人格同一性的复兴
第八章哲学中的欺骗、自我与自欺
后记“分析哲学”毁了哲学吗?
哲学的快乐书摘
什么是哲学的快乐?我过去也常说,它就是那种因看清楚所有观念如何关联而来的兴奋。可如今我会说,它是看见其他人以各自的方式看清楚所有观念如何关联而眼睛发亮时,我感到的那种兴奋。
“哲学的快乐”。任何一个曾花时间进行哲学探究的人都不会对这个表述感到奇怪。我的哲学家朋友是我所知的最投入——且不说着迷或上瘾——的人。一些人在与“大问题”的搏斗中感到快乐(或许还伴随着一些苦恼)。另一些人在厘清难以忍受的晦涩文本中感到快乐。如今,更多的人则是在用逻辑和独特的哲学语言处理愈益精细、令人困惑的“难题”中感到快乐。我认识许多画家、音乐家、政治家、学者、商人和捞钱能手——他们都是些很投入的人,但都没有我的哲学家朋友们那么投入。而且这种情形并不只是出现在这一行里的佼佼者身上。事实上,他们更小心谨慎,也更少热情,远不如我在小型学院甚至高中遇见的数百位优秀又充满热情的老师。对于后者而言,哲学的快乐就是哲学的快乐,而不只是学有所成的专家的快乐。
我们周围最活泼和充满生机的人(当然不是那些以此谋生的人)懂得哲学的快乐。甚至那些生活空虚、悲惨的人,有时也在哲学中找到一种涌动着活力的生活(而且不只是“慰藉”)。雄心勃勃的哲学大部头——绝大多数未出版也无人阅读——有在监狱和低廉的租屋中写就的,也有在失意职员和落魄律师形单影只的房间里和杂乱的办公桌上写成的。那样的地方也不乏思辨和热情。诸如“心灵生活”和“观念世界”这些平淡的表达是无法抓住哲学的活力、兴奋和快乐的。它不是烹饪的快乐,当然也不是性爱的快乐,但它无疑仍是快乐。
哲学的快乐截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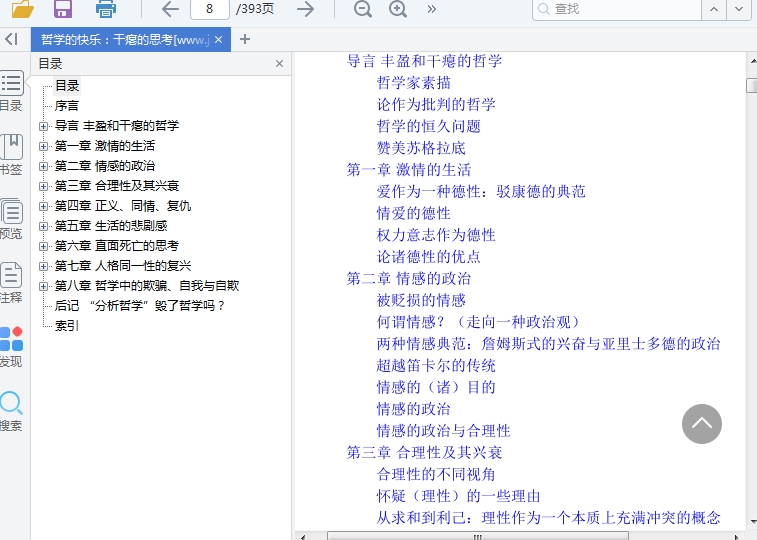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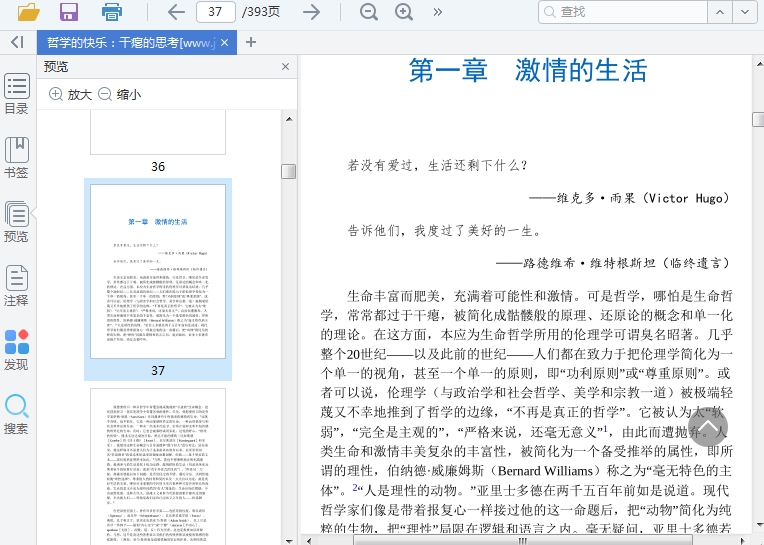
(美) 所罗门 著
陈高华 译
哲学的快乐:干瘪的思考vs.激情的
生活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桂林?THE JOY OF PHILOSOPHY:THINKING THIN VERSUS THE PASSIONATE LIFE
by Robert C. Solomon
Copyright ? 1999 by Robert C. Solomon
THE JOY OF PHILOSOPHY: THINKING THIN VERSUS THE PASSIONATE LIFE, FIRST
EDITION was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English in 1999.
This transla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throug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哲学的快乐:干瘪的思考vs.激情的生活 (美) 所罗门著 ; 陈高华译.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 4
ISBN 978-7-5495-5262-7
Ⅰ. ①哲… Ⅱ. ①所… ②陈… Ⅲ. ①哲学思想-世界-通俗读物
Ⅳ. ①B1-4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83636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桂林市中华路22号 邮政编码:541001
网址:www.bbtpress.com
出版人:何林夏目录
CONTENTS
序言
导言 丰盈和干瘪的哲学
哲学家素描
论作为批判的哲学
哲学的恒久问题
赞美苏格拉底
第一章 激情的生活
爱作为一种德性:驳康德的典范
情爱的德性
权力意志作为德性
论诸德性的优点
第二章 情感的政治
被贬损的情感
何谓情感?(走向一种政治观)
两种情感典范:詹姆斯式的兴奋与亚里士多德的政治
超越笛卡尔的传统
情感的(诸)目的
情感的政治
情感的政治与合理性
第三章 合理性及其兴衰
合理性的不同视角
怀疑(理性)的一些理由
从求和到利己:理性作为一个本质上充满冲突的概念情感的理性与理性的情感基础
第四章 正义、同情、复仇
正义与复仇:缺失的典范
正义vs.复仇:毫无根据的对立
正义的善柔一面:同情与道德情操
正义的肮脏一面:为怨恨一辩
作为正义的复仇:报复的合理性
正义如何令人满意
第五章 生活的悲剧感
悲剧的替代:责备与权利资格
恶的问题
谴责受害者:“自由意志”的解决方案
返回的俄狄浦斯:悲剧之死
命运、简便命运与看不见的手
好运气、坏运气以及毫无运气:为感激一辩
悲剧的意义
第六章 直面死亡的思考
死亡恋癖、病态的唯我论
直面死亡的思考
拒斥死亡:简史
从拒斥死亡到死亡恋癖
大胆的设想:“死亡什么也不是”
干瘪的死神:作为悖谬的死亡
恐惧死亡:害怕什么呢?
超越病态的唯我论:死亡的社会维度
第七章 人格同一性的复兴
困惑的进展
人格同一性与存在的社会自我
人格同一性与德性伦理学人格同一性与文化多元主义
爱中的人格同一性
人格同一性的复兴
第八章 哲学中的欺骗、自我与自欺
为什么是真理?
哲学意义上的真理与谎言
欺骗、自欺与自我
纠缠之网:作为一种整体现象的表里不一
表里不一的自我与自欺的自我
后记 “分析哲学”毁了哲学吗?
索引序言
我想我特别容易对运动的魔力倾心。
——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
(Vladimir Nabokov),《洛丽塔》(Lolita)
我们相遇那年,他四十五岁。念大学时,他是位(田径)运动员,课程对他来说只是兄弟聚会和周六球赛之间的插曲,不过还算不错,他
坚持了下来(但也就如此而已)。大学毕业后,他成了一位成功的生意
人、不错的网球选手、有头有脸的社会成功人士,可谓美国梦的化身。
可如今,他的反手拍开始失误,他会在又一次收购中不由自主地问一些
连自己都说不清楚的问题。他开始觉得,生活虽然充实,可又怎样
呢?“空洞乏味。”他自语道。于是,他发现了哲学的快乐。这并不是什
么智识上的装模作样,也不是规定的必修课程。像一个小孩一样,他对
这个新玩艺儿表现出了无尽的热情。他手里有一些书(绝大多数学人会
把它们当作“通俗”或“二流”读物不屑一顾),一些可在保时捷上播放的
演讲录音带,他还晓得一些随处可见的人名和不少观念。但他真正获得
的是一生所爱,一种生生不息的惊异感和着迷感。
三十年后,就像许多人的情形那样,哲学于我仍是颇多快乐和喜悦
的源泉。不过,“快乐”和“喜悦”在专业哲学中可不是上得了台面的词。
那位曾把哲学颂赞为“快乐的智慧”的尼采(Nietzsche),尽管在诸多圈子里大受欢迎,仍被人们认为“不是一位哲学家”而遭轻视。他的文辞太
过华丽,充满了讽刺和挖苦,且太过私人化了。总之,他的乐子太多
了。(用了太多的感叹号!)他是一个舞者,一个哲学顽童,是一个身
处伟大的苏格拉底传统中的反讽者,是一个好开玩笑的滑稽演员,他把
一切都纳入了他的哲学中——健康要诀、秘方、闲谈、保险杆贴纸、童
谣、失恋慰语、大众心理学、通俗物理学、一点玄妙深奥的东西、社会
评论、神话学史、纷争不已的语言学、家庭内斗、政治诽谤、中伤性的
辱骂、战争宣言、琐碎的抱怨、自大狂、亵渎神明的言语、拙劣的笑
话、小聪明过头的双关语、戏仿和剽窃。职业哲学家抱怨他不够严格,甚至缺乏一个一致的论题。可是,为什么要用纯粹论证的纤纤骨架来糟
蹋这样一场盛宴呢?尼采深知如何从哲学——他的“快乐的科学”(gaya
scienza)中——获得快乐。
我当然没有与尼采竞赛的自负,或效仿尼采深不可测的激情和识
见,或模仿他奇妙绝伦的“风格”,但对于他的那种哲学之乐,我确实深
有同感。与当下的多数哲学不同,它既不热衷于论证,也不热衷于优雅
地驳倒对手。它也不是后现代主义者所谓的“游戏”,不在于以撩起他人
的惊慌和混乱为乐。它实际所意指的,是超越论证的干瘪,进入哲学的
丰盈,是设法增益我们的经验,而不是“证明一个观点(point)”。学过
平面几何的我们都知道,点(point)是没有维度的,因此它没有纹理,没有颜色,当然也就没有深度。相应的,我这本书不是一个论证,更没
有展现一种“理论”。一些读者会越来越恼怒地发现,我常常毫无章法,不给出“观点”、不提供“证明”,而是不断转换视角甚至主题,为的是发
现有待探究的新东西。我主要关注的是,摧毁一些陈旧的壁垒,也就是
学院哲学与其丧失的听众之间、干瘪的逻辑与丰盈的修辞之间、哲学理
性与哲学激情之间、“分析”哲学与“欧陆”哲学之间、哲学与其他一切之
间的那些壁垒。
哲学已经变得太“严肃”,成了一门有其内行和“专家”的“职业”。它
不再属于每个人了(如果它曾经属于过的话),因为它有其技术要求,有专门却仍难以索解的问题和谜团,还有学术等级和学术派系。恰如我
在本书中所揭示的那样,问题在于哲学变得太“干瘪”、纤弱、贫瘠,(用一个完全恰当的病理学术语来说)还厌食。哲学的许多领域都已经
被简化为逻辑和论点批判,被简化为“解构”、贩卖行话以及令人窒息的
元哲学。具体的经验和科学的研究、宗教和灵性,诸如此类,要么被当
作毫不相关加以拒斥,要么被当作纯粹的研究“对象”而假意抬举。至于
那些需要人们实际观察世界并生活于其中的问题,他们傲慢地一笑了
之,不痛不痒地丢下一句“那不是些经验问题吗?”。过去所谓的那
种“思辨”不再盛行,更别说什么“愿景之类”了。哲学往日追求的那种无
所不包、丰盈、充实和通吃的理想,已经让位于贫乏简陋的新哲学,无
论其形式是线性论证还是后现代犬儒主义。
我的一位同事曾在我们(南)加州一所声誉不错的大学做讲座,谈
论哲学的这种狭隘性。他有所思虑地说,近来的哲学已经变得很像俗话
里的盲人摸象。在场的几位著名哲学家中,最著名的那位却骄傲地承
认,他“只对解剖象鼻感兴趣,至于大象会不会死掉,他并不在意”。
在这本书中,我倒想一瞥活生生的大象,或者,我至少不愿仅仅摸
一摸了无生气的象鼻和象牙。如今,许多哲学家主张所谓的“纯”哲学,即剥去了一切只剩骨架的哲学:逻辑和论证以及空荡荡的哲学史(这种
哲学史有时始于19世纪末弗雷格[Frege]的形式主义)。相反,我这
本书所提供的,全然是“不纯粹的哲学”,恰如伟大的智利诗人巴勃罗·
聂鲁达(Pablo Neruda)曾(谈到他的诗)时说的那样:“像旧衣服、像
沾着污渍和羞耻的身体一样不纯粹,里头夹带着褶皱、观察、幻梦、失
眠、预言、直言的爱恨、愚蠢、震惊、牧歌、政治信念、否定、怀疑、肯定和税收。”1
在这本书接下来的篇幅中,我最多只能说自己探究了一些永恒哲学
问题的另一类观点。这本书并不严肃,尤其不是常常会激起人们道德义
愤那种意义上的严肃。我更愿意人们说它“不过是在与(严肃的)观念嬉戏”。那就是哲学的样子(我敢这样说吗)。它不严肃,只是与那些
确有所指的观念戏耍。这并不是说我将在书中埋伏各种笑料,更别说让
人捧腹大笑了。我担心,我对快乐的表达会局限于一些绰号、副词、讽
刺的评论和糟糕的双关语。时下人们认为,只有在那些身材苗条、沐浴
在阳光中、轻盈的二十几岁青年没心没肺的露齿笑容里才能找到快乐,但这种说法并不全然真实。我们也可以在哲学家们一生充盈的沉思冥想
中找到它。
感谢新西兰奥克兰大学哲学系;感谢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哲学系和人
文研究院;感谢我的好朋友,《东西方哲学》杂志的编辑罗杰·阿姆斯
(Roger Ames);感谢本书编辑,牛津大学出版社的辛西娅·里德
(Cynthia Read);感谢我的诤友伯恩德·马格努斯(Bernd Magnus)、亚瑟·丹托(Arthur Danto)、杰伊·胡雷特(Jay Hullett)、保罗·伍德鲁
夫(Paul Woodruff)、亚历山大·内哈马斯(Alexander Nehamas)、理
查德·罗蒂(Richard Rorty)、彼得·克劳斯(Peter Kraus),尤其要感谢
弗里斯乔夫·伯格曼(Frithjof Bergmann),关于哲学的快乐和丰富,他
教给我最多。
当然,最终要感谢的是凯西·希金斯(Kathy Higgins),因为她不断
地为我和哲学带来快乐。
注释
1.Pablo Neruda,“On Impure Poetry,”inSelected Poems(New
York:Grove Press,1961).导言 丰盈和干瘪的哲学
(全然就是存在,一点儿也不少)
摩尔(G.E.Moore)带头反抗,我怀着一种解放感追随其后……我
们相信草是绿的,太阳与星星依然存在,哪怕没人知晓它们。那个一度
干瘪的逻辑世界如今变得丰富多彩。
——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
哲学史中有诸多反讽之事。无疑,伯特兰·罗素在评述“分析”哲学
起源时的那种自鸣得意,是其中一桩。罗素追随弗雷格和摩尔“反抗”实
际上把人类经验的方方面面都融入了自己哲学的黑格尔(Hegel)。可
是,由于对德国唯心主义的误解,罗素(错误地)秉持这样一种信念,即德国唯心主义认为世界是由观念而不是由坚实可靠的物质组成的,正
因为此,他才认为在他的哲学中,“那个一度干瘪的逻辑世界……变得
丰富多彩”。1然而,由此肇始的一百年来的“分析”运动,却最终使哲学
变得干瘪和逻辑化了。2
我们可以同意罗素的说法,即哲学的快乐在于其丰富多彩。然而可
悲的是,作为一门“学科”的哲学竟窄化成一套概念技巧,认同“干瘪”而
反对丰富多彩,完全偏重论证和逻辑分析,进而摒弃了黑格尔的“思
辨”想象以及他那无所不包的经验概念(用后现代主义者同样干瘪的行
话来说,就是“总体化”3)。如今,哲学要求“专业化”、技术、有限的关注和严格性,而不是视野、好奇心和开放性。黑格尔的理想是无所不包
的“理解”。但今天,哲学领域一些最卓著的文章却都是一连串符号和难
以理解的行话,只有不多的几个同行会感兴趣。恰如政治哲学家约翰·
罗尔斯(John Rawls)在他的那本划时代巨著《正义论》(A Theory of
Justice)开头宣称的那样,哲学的主要目标就是不断把对话提升到“更高
的抽象层次”。4但是,哲学(如黑格尔所主张的那样)并不一定要抽
象,也还有穿行于细节中的具体哲学,显现在有血有肉的观念辩证法之
中,远比纯粹的筋骨丰富。用威尔弗里德·塞拉斯(Wilfrid Sellars)的
话说,它的成功在于“看清事物是如何联系在一起的”。而它的兴盛则在
于将无论是否显著的平常之物变得神秘玄妙:时间、生命、心灵、自
我,以及我们与世界是如何“联系在一起的”。
哲学是或者应该是一种魔法。它并不是对我们生活的一种逃避,相
反,它是通向我们生活的一扇新窗户——或者诸多新窗户。因此,与其
说它是抽象,不如说是洞见和视野。从最早的吠陀派到存在主义者,伟
大的哲学家们都提供了令人眼花且扰人心智的洞见和视野,以及种种令
我们头晕和让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暂时不知所措的观念。然而,这种魔法
般的快乐感已然丧失或已遭抛弃,我虽不情愿这样说,可情形确实如
此。今天的哲学家太扫兴,急于反驳,固执地不愿去理解(或倾听)陈
述不完善的替代方案,一心想着贬低洞见和热情。我念研究生时,一位
与我同龄且很有天分和创造力的女生提交了一篇极具创造性的哲学论
文。可她的老师却蛮横地视之为垃圾,并以《旧约》中才有的愤怒对她
吼道:“哲学不是搞笑!”(她如今是位一流学者,不过是在另一领
域。)今天,最有才情的研究生仍会因同样的斥责而被逐出哲学领域。
哲学不是搞笑!
在国内旅行时,我常常遇见各种各样的人——成功的商人、艺术家
以及其他一些人,当然也有学者——他们往往直截了当地用些熟悉的话
与我说笑。开头是“我曾经上过一门哲学课,但是……”我知道接下来会
说些什么。开头的几个音节就令我厌烦。有时会是某种无辜的恼人话语,如“可我什么也记不起来了”。更常出现的则是“但我讨厌它”,接着
则是对老师毫无奉承的典型描述:一个既冷淡又自负、显然有点小聪明
且有意炫耀的人。通常我会问,这个烂人是谁?结果这位仁兄常常是同
行里颇为知名的人物。他(几乎总是他)有着不俗的出版记录,他毕生
的工作就是(在成百上千个学生中)激发一两个学生从事哲学,以此继
续祸害下一代。那种认为哲学的命运单悬于我们激发哲学之乐的集体能
力这条线上的想法,常常会遭来轻视。单单这种说法就会被人们激烈地
指责为把哲学当成“娱乐”,进而重申专业能力和“学科的完整性”。
什么是哲学的快乐?我过去也常说,它就是那种因看清楚所有观念
如何关联而来的兴奋。可如今我会说,它是看见其他人以各自的方式看
清楚所有观念如何关联而眼睛发亮时,我感到的那种兴奋。
“哲学的快乐”。任何一个曾花时间进行哲学探究的人都不会对这个
表述感到奇怪。我的哲学家朋友是我所知的最投入——且不说着迷或上
瘾——的人。一些人在与“大问题”的搏斗中感到快乐(或许还伴随着一
些苦恼)。另一些人在厘清难以忍受的晦涩文本中感到快乐。如今,更
多的人则是在用逻辑和独特的哲学语言处理愈益精细、令人困惑的“难
题”中感到快乐。我认识许多画家、音乐家、政治家、学者、商人和捞
钱能手——他们都是些很投入的人,但都没有我的哲学家朋友们那么投
入。而且这种情形并不只是出现在这一行里的佼佼者身上。事实上,他
们更小心谨慎,也更少热情,远不如我在小型学院甚至高中遇见的数百
位优秀又充满热情的老师。对于后者而言,哲学的快乐就是哲学的快
乐,而不只是学有所成的专家的快乐。
我们周围最活泼和充满生机的人(当然不是那些以此谋生的人)懂
得哲学的快乐。甚至那些生活空虚、悲惨的人,有时也在哲学中找到一
种涌动着活力的生活(而且不只是“慰藉”)。雄心勃勃的哲学大部头
——绝大多数未出版也无人阅读——有在监狱和低廉的租屋中写就的,也有在失意职员和落魄律师形单影只的房间里和杂乱的办公桌上写成的。那样的地方也不乏思辨和热情。诸如“心灵生活”和“观念世界”这些
平淡的表达是无法抓住哲学的活力、兴奋和快乐的。它不是烹饪的快
乐,当然也不是性爱的快乐,但它无疑仍是快乐。哲学家素描
[哲学中]凡是能够说的事情,都能够说清楚,而凡是不能说的事
情,就该保持沉默。
——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逻辑哲学论》(Tractatus Logico-Philosophicus)
这是20世纪晚期的一位哲学家的素描。他(例子依旧几乎总是他)
站在一小群听众前。他正苦恼着。他的双眼尽管有神,却无所关注;或
许它们是在反视自身。他的眉上有一道深纹,表明他皱着眉——不,是
沉着脸——一只手不停地在前额揉动,仿佛不如此他的头或脑袋就会爆
炸。对于那些喜欢用典的人来说,他像极了罗丹(Rodin)著名的《思
想者》(The Thinker),或者《拉奥孔》(Laocoon)中那位面容扭
曲、极度不幸的父亲和祭司——古代世界中对苦楚最为揪心和悲惨的刻
画。他说起话来断断续续,几近于口吃,表明了观念间的堵塞以及他试
图寻找恰当字眼的紧张程度。他在那条踩烂了的道上,焦躁不安、不由
自主、毫无规则地踱着步,从一个角落走到另一个角落,眼睛从未落在
那些全神贯注但困惑不已的听众身上。他的一只手时而掩嘴、时而揉
眼、时而抓鼻、时而敲敲后颈,又或者在腋下挠挠,焦躁地说几句又停
顿下来,而另一只手不断地拿起一根粉笔又放下,偶尔像是要写点什
么,但除了一个“x”或长方形之外,什么也没有写出来。折磨人的(意
味深长的)停顿也不少。这种情形估计得让伟大的神经精神病学家奥利
弗·萨克斯(Oliver Sachs)医生来诊断一番。这简直就是神经衰弱、自
恋、思想背叛自身和语言急需放假的一个活生生的剧场。这就是哲学,这就是哲学家。苦楚,因哲学而遭受的苦楚。哲学是一种疾病,唯一的解药是……更多的哲学。
我刚才所勾勒的这幅肖像属于一位极易辨认的历史人物,即路德维
希·维特根斯坦,虽然他的哲学日渐黯淡,但他的人生却成了20世纪哲
学生活的不朽标志之一。尽管维特根斯坦的学生中很少有他那样的天
才,或认同他那种维也纳式的病态生活观,但其中有很多人模仿他的手
势、风格、一脸不安,仿佛他的骚动不安他们也能感同身受。结果就
是,随后两个世代的哲学师生搞起哲学来,就像是在公开表演自我驱
魔。他们在大学导论课上表演,而那些本就想要加入这种表演(而不是
嘲笑这种表演)的学生也受到鼓励参与进来。这种课程的绝大部分仍是
令人生厌地一成不变,但是这种风格、表演、严肃性已经使哲学——像
维特根斯坦自己抱怨的那样——变成了一种精神病理学。
在电影《雨人》(Rain Man)中,演技出众的达斯汀·霍夫曼
(Dustin Hoffman)所扮演的自闭症患者雷蒙德(Raymond)回应压力
的方式,就是试着一遍又一遍地解答阿伯特(Abbott)和科斯特洛
(Costello)的经典喜剧包袱:“谁在一垒?”他的哥哥(汤姆·克鲁斯
[Tom Cruise]饰演)被惹恼了,向他吼道:“这是一个谜,是一个玩
笑。如果你明白这一点,或许会好些。”从精神病学上来说,这句话或
许很幼稚,但它也同样深刻。任何一个见识过今日许多极具才华、声名
卓著的哲学家苦思冥想情形的人,都不会对这句话所呈现的那种病理感
到陌生。众所周知,哲学难题极其费解,甚至不可索解,这一事实被认
为是其深刻性的明证。5但是,不可索解或许也是理智自虐的一个标
志,或者说得更天真无害一些,是理智自慰的一个标志。哲学难题既不
可索解,也无足轻重,这种意识让人们有很好的理由认为,对这些难题
的探究最终“只是为了探究本身”。也就是说,是为了好玩,为了随之而
来的纯粹快乐,尽管我们在探究途中也会有挣扎和牢骚。维特根斯坦自
己曾这样写道,一本哲学书完全可能满篇玩笑。当然,他自己从没写过
这样一本哲学书。哲学里头——我们别再装模作样,就直说吧——没什么真正事关生
死的东西。医生、工程师、联邦储备局成员或爆破小组的专家要是出了
错,确实会有后果。一个哲学家出了错,没人会死,没有什么会相撞、爆炸或崩塌,贫困或失业不会增加,股市也不会暴跌。当然,一些优秀
哲学家遭到曲解,从而引发灾难,这种情形在历史上古今皆有。但这些
是例外,而非通则,即便如此,也很难说是困守书斋的哲学家们自己把
世界置于危险之中。实际上,无须负责的哲学会带给人一种解放感。甚
至像马克思和卢梭这种乖戾之人,不管他们的个性有多阴郁,曾在这个
世界上表达或激起了多少狂暴情绪,他们自己显然也有许多快乐。
我猜,绝大多数哲学家是作为叛逆者,为了寻求一种深刻的自由而
进入哲学领域的。但讽刺的是,我们现在却打着“专业化”和“学科完
整”的旗号,成了自我强加的权威主义的囚徒。自由的思想和野性的观
念已变得不合时宜;成为一个哲学家必须遵守“纪律”(discipline)。在
大学招生手册之外,没有什么地方还把哲学描述为“人生的思考”或“自
我省察”,更别提什么观念的快乐了。恰如某位一流的哲学从业者曾权
威十足地说过那样,“哲学有逻辑学和科学哲学就够了”。随着对“什么
是哲学”盖棺定论,自由、想象、通俗易懂,尤其是敏感,也就被抛掷
一边了。论作为批判的哲学
严肃是浅薄者的唯一避难所。
——奥斯卡·王尔德(Oscar Wilde)
哲学像绝大多数学术和知识学科一样,在很大程度上成了批判之
学。这种情形的益处很明显:敏锐的批判显然对民主制度而言至为根
本,也是健全科学的本质所在。它创造了一种辩证法,真理(或至少是
更好的理解)可借此从不成熟或片面的观念中浮现出来。它让理论化变
得有趣,甚至更具责任感。理论上讲,它至少有助于消除欺诈和愚蠢。
还应该补充说,它还增加竞争力,对于许多受心灵生活吸引的好斗分子
而言,批判本身就成了诸多乐趣之源。不过,批判也会过度。特别是,如今在许多哲学行家看来,哲学不过是对论证的审查,以及制造对立的
论证。观念和识见呢?它们现在不过是攻击的目标。
初涉哲学的大一新生,仿佛置身于娱乐性的射击场,学的是如何击
落伟大哲学家们的论证。(“柏拉图认为什么什么:这个说法的问题在
哪儿?”“康德主张什么什么:请给出一个反例。”“约翰·斯图亚特·穆勒
[John Stuart Mill]得出结论说什么什么:那难道不是一个‘愚蠢的错
误’吗?”)较为资深的哲学家们则在论文中娴熟地展现自己的技能,开
头总是“某人主张什么什么,但我将表明他她失败了”。在一个“不发表
就灭亡”的时代,哲学成了吹毛求疵的技能。论证越来越“严谨”,视
野、知识和趣味越来越狭小。为了免于在论证中夹带难免有诸多弱点的
原创性,哲学家们常常列举的是一些最没创意的例子(比如,常常是弗
雷格在1900年举过的例子,或者再早一个世纪的康德所采用的例子,甚
至是两千多年前亚里士多德用过的例子)。关注的范围越来越狭隘,越来越形式化——可供咀嚼的鲜肉越来越少,更无扰人心智的个人情感。
哲学的快乐在很大程度上只剩下摧毁,即“撕裂”和毁灭的乐趣,不消
说,这里头包括“解构”论证的乐趣。黑格尔那种建构性(“思辨性”)视
野的乐趣,用连前人自己都没用过的方式去解读前人观念的乐趣,通过
哲学产生新观念甚至是不同寻常的经历的乐趣,已经看不到了。6论证
和反驳:除此之外哲学家还需要知道别的吗?
我现在教书,竭力遵循过去所谓的宽容原则。粗略来讲,就是一个
观点即便听来像胡说八道,我们也应该试着去搞清楚表述者心中可能的
想法,或者其令人厌烦的表面下可能藏着的好想法。(当然,这是随堂
回答学生提问时的一项基本教学技能。)我常常听到同事们因某个笔
误、事实错误、解释不当或(最为糟糕的)逻辑谬误,就把一篇文章、整本书甚至一个人的学术生涯一棒子打死。至于其中还有什么价值,他
们错过了。当然,我在现实中也只是偶尔能贯彻自己的原则。只要来一
点荒唐的政治主张、一点新时代运动(New Age)或后现代主义的自以
为是、一个挑衅我所维护过的珍贵观念的反面论点,我就几乎会不可避
免地恢复到我的职业枪手模式,那些费城、安娜堡、普林斯顿和道奇市
的神枪手老师把我调教得可好了。不过,至少我知道自己这种做法有
错。在哲学中击败对手或许有点意思,但哲学的快乐却藏身别处:它存
在于思想的相互碰撞中,植根于对新观点的上下求索中,生发于让每日
都变得饶有趣味甚至引人入胜的愿景构建中。当然,批判有其位置,但
是,批判只是(或者应该只是)我们形塑观念、扩展视野的一种工具。
它不是(或者不应该是)目的本身。7
在这本书中(其实此书本身就过于吹毛求疵),我想要回到一种较
为古老、更为“浪漫的”哲思模式。它不会没有论证——实际上,人们可
以把整本书看作对哲学之“干瘪”的反驳——不过这本书的结构更多是与
观念本身的复杂性有关,而非标准化的分析方式。坦白说,我常常并不
知道我的这些探究会把我带向何处。这就是激情与证明之间的差异。确
实,我厌恶逻辑的“干瘪”,盛赞哲学的激情以及由之而来的丰盈。然而,至少自柏拉图以来,哲学家们就对激情心存警惕,更不用说自逻辑
实证主义者(他们有自己的理由)以来,哲学还对浪漫主义提防有加。
确实,与单把糟糕的论证批得体无完肤相比,思辨和激情以及深究人类
经验的努力之中,则蕴含了危险重重。
鉴于在上世纪时对于经验主义“唯此独尊”(nothing but)的强烈偏
爱,这同一批人竟然坚决抵制谈论经验,尤其是生活的感受和具体细
节,就显得不可思议了。8取而代之的是,焦点集中到了“逻辑形式”之
上。或许,这种对逻辑形式的强调可以归因于人们误读了柏拉图——一
位最具想象力的哲学家——及他对形式(Forms)的迷恋。这种强调肯
定可追溯到康德颂赞的先天(a priori)概念(但这么做并不意味着对经
验的贬低)。至于黑格尔,他尽管坚持无所不包,但仍极其危险地摆弄
着“概念”,即19世纪版的“更高的抽象层次”,因此,人们有时阅读(和
抨击)他,并不是因他的丰盈,而是因其无所不包的干瘪。9
在今日的英美哲学中,对干瘪的极力主张可以说是弗雷格——罗素
——(早期)维特根斯坦固执于逻辑分析和形式分析的一个延续——甚
至复兴。这一主张也持续存在于后现代主义关于元哲学毫无分量的夸大
其词之中,它尽管(常常在形式上)坚持多元主义和碎片化,却仍对寻
常的人类经验视而不见,甚或加以轻蔑。10然而,强调批判和解构的最
终结果有两个,一方面是对于“有趣观念”近似犬儒的彻底怀疑主义,另
一方面是一种补偿心理,即着迷于纯粹形式、推论和论证,以及寻找他
人立场的错误,但自己避免采取任何立场。11这种犬儒主义对热情——
实际上是一切激情或情绪——自然深表怀疑。因此,无论其起源多么厚
重,哲学如今已变得轻若鸿毛,毫无实质和内容可言。
当然,即使最丰盈的哲学也仍是十分干瘪的,完全是一种粉饰,不
过是事物的表层(而非“深度”)。马克·吐温(Mark Twain)——美国最
伟大的哲学家之一——坚持认为,“真理就在表面”。哲学中的“深刻”更
可能是一种概览,是一种观看之道而非“挖掘”之术。哲学不是论证,而是分辨、沉思和视野。如果哲学是丰盈和充实的,那是因为生活本身是
丰盈和充实的。哲学关涉的是生活。甚至可以说,哲学于生活(至少是
省察的生活)至为紧要,但哲学毕竟不是生活,只是借生活为己用而
已。当然,哲学也不是生活展现其血肉的骨架,就好像哲学是基础,其
余一切皆血肉。哲学不可以完全是一种单向度的推理,但是,即使在其
最为充实处,哲学仍无可争辩地是干瘪的,哪怕它不是逻辑的。因为无
论有没有哲学,草地依旧焕发着浓浓绿意。
或许是因为哲学的干瘪让人预感不祥,如今出现了大量谈论哲学终
结(end of philosophy)的文章和书籍,“终结”既可以解释为线性的目标
或目的,又可以解释为终点,它们在其二义性上大做文章,让人不胜其
烦。一些作者直言不讳,宣称哲学已经“死亡”或“耗尽”。另一些作者则
含糊其辞。柯乃尔·韦斯特(Cornel West)和约翰·拉赫曼(John
Rajchman)宣称“后分析哲学”的来临,试图以此来震动学术界,但迄今
还没察觉到有任何改变。12走向“后分析”哲学(或如今被谬称为“实用主
义”)的运动,不过是一些战略性微调,操作者们仍是同一批熟悉的玩
家。技术统治论依然纹丝不动,骄傲地展示着爱丽丝·默多克(Iris
Murdoch)在数十年前就警告过的“干枯”,只不过那时这一领域还很丰
润。但是,问题越是“干瘪”,定义越是清晰,似乎也就越是难以索解。
比如,“真理”已经被简化为一个毫无意义的术语,许多哲学家确信他们
不久就会彻底根除它了,至少在哲学中可以做到这一点。13同样的,“自
我”这一观念已经干瘪得不可辨认,当然也就无足轻重了。14生活的核心
概念被简化为逻辑悖论和难题,哲学家们因此而遭到谴责(其实是自我
谴责):哲学被搞坏了。他们宣称,这些年来我们一直在对付的都
是“伪问题”,但是他们的声望、薪水以及对这一行当的把持却有增无
减。哲学的恒久问题
生活迟早会把我们全都变成哲学家。
——莫里斯·赖瑟琳(Maurice Riseling)
犬儒(“反讽”)的观点认为,哲学无非就是拿着薪水的哲学家们当
下在做的一切。对此我不敢苟同,我认为哲学的动力和动机源自非常真
实、具体可见且带有普遍性的人类问题。这不是要否认,如尼采所指出
的那样,某种奇特的“求真意志”的存在,也不是要否认对难题和悖论的
着迷,这种着迷一旦被激发就可能久久不散,且不为外物所动。但哲学
不是这个样子的。它是与生活的恒久问题的搏斗。我们都是哲学家,我
们必须使哲学民主化,尽管哲学有其久远的精英起源。哲学不是一门专
业,不是一个职业,也不是有其规则和口令的排外俱乐部。哲学不过是
对诸如激情、正义、悲剧、死亡、自我同一性以及哲学本身等问题的思
考,因此,哲学绝不是一小群受过大学训练的专业人士的领地或特权。
在最重要也最为政治不正确的意义上,哲学是我们人的存在方式之
中固有的。我们思考。我们感受。有一些问题——或许可以认为它们
是“哲学的先行条件”(又称之为“人的境况”)——我们毫无选择,只能
去思考和感受。无论这些问题的概念和细节在不同文化之间有何差异,它们都不出所料地包括了美好生活的本性、我们最强有力的激情的位置
和根据、我们在他人中间的位置、正义问题、悲剧的种种解释、死亡显
而易见的终结性、人自己的同一性以及思考、反思、意识和哲学的指向
和目的。
这就是(一些)恒久的哲学问题。有哲学家(理查德·罗蒂就是最为著名的例子15)认为,没有什么恒久的哲学问题。在我看来,这种说
法显然是错误的(而罗蒂本人在其他地方也很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
当然,对于这些问题,你可以给出一个“丰盈的”描述,由此表明它们无
非是一时一地一些人的问题,甚至是1973年美国哲学协会成员的特定问
题。但是,生命本身的问题,与任何特定的哲学传统都无关,比如,我
们对自身的脆弱和终将一死的意识。无论是否存在某种思考死亡的正
确“逻辑”,死亡都是让我们心存敬畏的一个普遍“事实”(海德格尔断
言,是“我们最为必然的可能性”)。当然,将生命及其(各种)意义
——相应地还有死亡的意义和本性——概念化的方式很多很多。不过我
认为,对死亡的意识,可以说是一个“哲学的先行条件”,它当然不是哲
学家的发明,但仍为哲学所塑造(也塑造着哲学)。16
要说哲学中存在着恒久问题,在某种程度上恰恰是在指出,或许还
在抱怨:哪怕对这些问题“最为干瘪的”描述,也是狭隘和有失偏颇的,因此也就没那么“恒久”了。(恰如尼采所言,并不存在事实和原始文
本,存在的仅仅是种种解释。)比如,有一个不错的观点认为,我们现
在所谓的心——身问题,事实上与特定时期的学问和追求有关:神经心
理学和计算机科学这些令人兴奋的学科融通交汇,和基督教的身体与灵
魂分离说、笛卡尔(笛卡尔主义)的“二元实体”哲学、语言哲学与心灵
哲学专业交叉形成的新见,以及英语本身某些特质的影响。相反,在日
本、古希腊,在尼日利亚的约鲁巴人那里,就没有这样的区分,因此也
就没有这样的问题。
不过,这意味着什么呢?这并不是要否认还存在其他引起同样不安
的问题和“分离”。(也不是说其他文化不接受神经科学的发现,那就太
荒谬了。)比如,在日本,一个人展现给外部世界看的“脸色”与他不愿
示人的私人感受之间的矛盾冲突,就受到了持续关注。约鲁巴人与绝大
多数人一样,关心灵魂的本性,他们在许多意义上把它与身体区分开
来。但是,严格意义上的心——身问题并不存在,因为(在日语和约鲁
巴语中)并不存在一个与“mind”(心灵)对等的词。(kokoro是日语中最接近mind的词,但它显然包含了笛卡尔式二分法中的“身体”才拥有的
各种特征。亚里士多德从来没有一个与机体区分的anima观念,而约鲁
巴人的ori所指的东西更像是“头”,而不是“内心”,与之相对照的则是身
体的其余部分。)可以认为,我们所谓的“心灵”是对一个人主观经验的
某些方面“最干瘪的”描述;而与之相对照的“身体”,同样也是用纯生理
术语所给出的极为干瘪的描述。
认为心——身问题不过是某个地方哲学传统在某一特定时期的一种
文化特性,纯属无稽之谈。如何为这一问题提供一个足够“干瘪的”描述
以囊括所有文化及其对立面,亦不是我这里的关注所在;况且,如此干
瘪地呈现这一问题可能会显得纤弱不堪,对我们而言也就无足轻重了。
我这里要探究的——与罗蒂时不时认可的后现代路子完全相对立——是
种种关注的核心是什么,它们不该仅仅被我们当作反讽或与无关紧要的
问题,而是值得作为典型的人的问题被重视,不管它们是否会被哲学家
认同,或是否能摆脱任何特定文化和哲学的观点。确实,某些观点只适
用于某些文化,而不适用于其他文化。但是,坚持认为某些关注本质上
是人特有的,并没有犯后现代主义者所谓的“本质化”和“总体化”之罪。
也不是要否认,如果人类变成完全不同种类的生物(比如,变得坚不可
摧或长生不老),那些恒久的问题也会大有不同。谈论“恒久的问题”,只是说某种形式下的某些问题,对我们而言是无法逃避的(这里的我们
是指,我们有限且必然褊狭的想象力能想到的所有人)。
加布里埃尔·马塞尔(Gabriel Marcel)把难题与奥秘区别开来后,抱怨(20世纪中叶的)哲学家们把心思都分给了难题,却对奥秘视而不
见。要是我来表述,方式会稍有不同,不过,在我看来,他的这种区分
却是难以避免的。他的写作很超前。就他力图阐明的意义——攸关每个
有思考能力之人的那些问题所处的混乱状态——上来看,哲学在美国最
好的大学中也已经差不多销声匿迹了。哲学不是提出更多艰深晦涩的新
问题,而是该将注意力集中在那些每个人——尤其是眼睛明澈、荷尔蒙
旺盛的大学生和四十五岁的职场男女——都遇到过的事情上。可是,“最好的”哲学系都成了学术技艺高超却对学生们无业可授的部门,也难怪那么多优秀的学生会离开哲学专业而转投宗教研究或文学系。但
在校园之外,这些学生却用本该在哲学课上才应有的热情追捧着新时代
运动的哲学。对此,我们与其感到愤怒或轻蔑,不如试着去探究下这些
追捧的动力从何而来,怎样才能使其满足,那样的话,我们的境况可能
会好很多。
哲学是一种真实的需求,它所针对的是真问题,不是伪问题。在人
的一生中,哲学会多次露面,最明显的是童年时期,这时它还未被置若
罔闻的父母和老师们扼杀掉;其次是青春期晚期,这时个人身份的认同
及个人在世界上的位置是什么之类的问题不停袭来;还有是在生活中遭
遇各种危机时——比如离婚、重病、至爱去世、个人失败、政治动荡。
在绝大多数人看来,回应这些切身的问题,正是(公众认可的)哲学家
存在的唯一理由,如果专业哲学家不愿这样做,那么,哲学慰藉的替代
品就一定会冒出来。书店架子上无所不在的自助图书就是一例明证。对
于不少智力尚可的人说,现在的怀疑主义专业户们到处挑刺,给论证找
瑕疵,给见解找漏洞,给好心情泼冷水,还觉得每个修辞手法背后都有
无法根除的自相矛盾,与其忍受这种单调乏味,还不如去看雪莉·麦克
雷恩(Shirley MacLaine)的性欲幻想。至少,麦克雷恩小姐似乎在她的
所作所为中乐此不疲。赞美苏格拉底
笑声是灵魂的语言。
——巴勃罗·聂鲁达
人们常常打趣说,苏格拉底从未发表过什么,所以他就灭亡了。然
而,他却成了我们的英雄,哲学家们的灵感和典范。没错,他之前也有
哲学家(人们稍带不屑地称之为前苏格拉底哲学家),可是若没有他,我们就难以想象哲学的生长或发展。柏拉图会写些什么呢?亚里士多德
从哪个智识平台出发呢?我们会如何来理解奥古斯丁(Augustine)或阿
奎那(Aquinas)呢?尼采的狂言(以及他的嫉妒[envy])也会短路
的(不过小城镇的新教仍给他留有机会)。苏格拉底的人格——以及他
的机智和才华——让我们所有人着迷。正是他的以身作则(以及柏拉图
对他的描绘)使哲学与诗歌、修辞和公共政治截然区分开来(且与它们
相对抗),独树一帜,自成一家,成了自我省察的学问。17
然而事实是,苏格拉底是一个自我包装过的江湖骗子。他有意坚称
自己无知愚昧,然后又据此宣扬自己是当时最有智慧的人。只要能够胜
出,什么糟糕的论证他都会用。他花言巧语,取笑嘲弄,混淆视听,连
蒙带骗。他的嘲笑都是人身攻击(ad hominem),这是他通常会犯的非
形式谬误之一。他是一个享乐者,却显然对爱和快乐甚至生命本身漠不
关心,或者说可以做到漠不关心。他为哲学而死,或者说,他想让我们
这么以为。但他是为自己而死的,是为“他灵魂的善”而死的,甚至他为
之献身的政治原则,现在看来也是可疑的、前后矛盾的,或许也是难以
忍受的。18从我们了解的关于苏格拉底的各种叙述来看,他并没有孑然一身,也极少苦思冥想,更没有一本正经过。哲学家孤独、忧郁、若有所思的
思想者形象,在他那儿基本对不上号。苏格拉底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社交
人物、一个宴饮狂、一个喋喋不休的话痨,还是一只围绕着问题(当
然,还有男孩)嗡嗡的牛虻。对于他,无论我们怎么说——他是智慧
的,他是勇敢的,他长得丑,他终究是一个会死的凡人(就像必然的三
段论里所说的那样)——他过得的确痛快。他的对话充满了俏皮话、颇
有意趣的轻侮和哲学式的闹剧。即便是在今天,人们仍能通过阅读感受
到他眼神的闪烁和言辞的动人,他追问他那些话题和心甘情愿的受害者
时的快乐,以及他表明观点、搞定论证、结束一段讨论以开启另一段讨
论时那种并非全是自夸的欢喜。或许,恰如两千年后的尼采——带着夹
杂着嫉妒的敬畏——说的那样,他根本就是一个小丑。可他是个多了不
起的小丑啊!他不但迷倒了雅典的年轻人,在死后几年内,还把古代世
界迷倒了。两千年后,他又迷倒了文艺复兴时期的新哲学家们和新生的
现代异教世界。他把哲学当作对话和有益的趣谈,可以嘲弄,也可以劝
诱。他认为哲学是快乐的智慧,是乐趣。
后来的哲学家或许会坐在中产阶级的火炉边持笔独饮,但苏格拉底
却是在庆祝宴会上举杯豪饮,后来他饮毒酒而死,也算得上死得其所
了。我们都知道,他被控“败坏雅典的青年”和不信城邦的神,前一项指
控过于模糊,难以证明,后一项指控他虽然加以否认,却是不争的事
实。他在指控他的陪审团面前夸耀自己的所为,并且认为自己不应受
罚,反该得赏。他被不公正地判处了死刑,但这是他自己激怒陪审团所
致,而且陪审团还为此再三犹豫。(毫无疑问,一些陪审员已然料到历
史将会如何评价这一判决。)他的朋友克力同(Crito)自告奋勇要帮他
逃狱出城,却被拒绝了。为什么呢?因为一些臭名昭著的糟糕论证。不
过,他或许也意识到了历史将给予自己的位置。那是每一个殉道者的幻
想,只是很少人(还有个例外)会如此成功。对照一下亚里士多德,他
曾用福斯塔夫式(Falstaff)19的口气宣称:“雅典不能再得到第二次对
哲学犯罪的机会。”20在智勇双全里,智慧还是更重要一些。无论过去还是如今,苏格拉底都是一个悖论,后来哲学中所有的困
惑和冲力都源自这个非凡人物,如同话语源自他那从不停歇的嘴。他坚
持理性,但使他胜出的是雄辩术。靠着纯粹的个人魅力,他给自己确立
起一个充满激情而不耽于沉思的形象。他总是即问即答,但没有什么仔
细推敲过的理论。实际上,人们不清楚他是否有一套理论,更不清楚他
是否对自己的问题有一个答案。甚至他那伟大的《理想国》——这部作
品让西方在随后的两千年里一直为“什么是正义”争论不休——也没有明
确的结论,至少暗示了可能根本没有结论。
苏格拉底认为定义是充分必要条件,能够涵盖但不排除每一个适当
的实例,不过他自己更善于提出巧妙的反例和机敏的反驳。他在驳斥完
所有提出来的定义后,不会提出另一个注定白费的定义,而是讲述一个
神话或寓言,虚构一个城邦或把灵魂描述成一群野马和马夫的合体,回
忆一次假想出来的与缪斯的会面或沉浸于灵魂不朽的冥思中。事实上,他是一个神话制造者,是神话和反神话的雕刻家——形式世界、真实存
在的世界、逃离洞穴、完全正直的理想、灵魂不朽。他认为应该把诗人
赶出理想国,因为他们是坑蒙拐骗之徒,然而他自己就是其中最伟大的
诗人,最大的坑蒙拐骗之徒。
因此苏格拉底有两个,一个是两千五百年前有血有肉的激情人士,另一个则与毫无生气的逻辑建构联系在一起,专注于一些可疑的论证和
狂妄的来世理论。我们牢牢记住了苏格拉底对难题和悖论的迷恋,却忽
略了激励过他的那些深切的个人忧虑和不可抑制的幽默感。更糟糕的
是,哲学如今又呈现出一种排斥他人的自命不凡感,完全不屑于绝大多
数学生和哲学爱好者的深切关注。苏格拉底是对的:哲学可以是且应该
是一种快乐,而不是一种负担。这倒不是说哲学挺容易,也不是说怎样
都行。但是,苏格拉底面对死亡,要比绝大多数哲学家彼此会面以及在
研讨室里面对学生时从容得多。今日那些深刻的思想家极其痛苦的形
象,可不是苏格拉底的样子。轻松快乐的笑声或咯咯一笑,那才是智慧
最恰切的表达。注释
1.见My Mental Development一文,载于P.Schilpp所编的The
Philosophy of Bertrand Russell(La Salle,IL:Open Court,1975)。事
实上,罗素所回应的是英国的一些“黑格尔主义者”,这些人与他们的德
国前辈们有很大不同。
2.许多哲学家坚持认为,他们研究哲学的方式——还原论的、干瘪
的和逻辑的——是唯一真正的哲学。实际上,我们有一些人已经讨论过
组建“真正的哲学”这样一个子系科的合理性(我一位优秀的逻辑学家同
事曾自嘲地称逻辑学乃“猛男哲学”),而留给我们其他人的,则是谈论
驳杂生活的滥情角色。
3.我针对“干瘪”的运动决不限于“分析”哲学。比如吉尔·德勒兹
(Gilles Deleuze)后结构主义的形式主义,虽然充满着虚无主义的叫
嚣,却仍像分析哲学的任何产物一样乏力又无趣。
4.见罗尔斯的A Theory of Justice(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1),第8页。这绝不是要搁置或贬低难题(比如,芝诺[Zeno]的飞矢不动,回到过去后自杀,想想成为一只蝙蝠会是什么
样或中文屋里头的那个家伙是否懂中文,争论功能不良的电传机上剩余
部分的人的身份,指挥失控的电车,或者戳戳缸中之脑)。搞懂这些荒
唐的脑筋急转弯是训练脑力的极佳方式,而巧妙解答的过程又是一种美
学享受,可以与精彩的数学证明相媲美。不过,不能把这个和哲学混淆
(更不能以为这是哲学的专一领域)。
5.实际上,甚至寻常的经验长期以来也是哲学嘲弄和怀疑的对
象:“可这难道不是一个经验问题吗?”紧接着(或至少隐含着)的一句
话往往是:“那可不是哲学!”于是,哲学的主题变得日益狭小,以至于
丧失了太多内容,实际上已经毫无分量可言。6.罗伯特·诺齐克(诺齐克)在他最近的三本书——Philosophical
Explanations(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1),The Examined Life(New York:Simon andSchuster,1989)和The
Nature of Rationality(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3)——中实际上表述的全是这种类似的感受。但是,他在优雅地表
明自己从好斗的“击败”型哲学模式转变为更适宜的新路径之后,仍情不
自禁地展示他那炉火纯青的战斗技能。对此我也深有体会。
7.逻辑实证主义者自称经验主义者,但这仅仅是因为他们重视科
学。对他们而言,“经验”本身是一个抽象概念,是他们关于证据和证实
概念的干瘪的、纯粹逻辑的讨论的一个部分。“唯此独尊”(nothing
but)一词出自詹姆斯(William James),他把经验主义的“唯此独尊”态
度与理性主义的“还有更多”态度相对照。然而,詹姆斯本人尽管可能曾
是一位“彻底的经验主义者”,但他绝不是一个推崇“唯此独尊”的哲学
家。
8.当然,我首先想到的是罗素对唯心主义的抨击,但是,同样的抨
击也出自后现代主义阵营,尤其是吉尔·德勒兹。事实上,他那本被过
度追捧的谈论尼采的书,其中有大部分是对黑格尔和黑格尔主义极其不
当的抨击。见H.Tomlinson翻译的Nietzsche and Philosophy(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3)。
9.当然,存在着“普通的”后现代主义者和“绝对的”后现代主义者之
分,不过我所想的是德勒兹、利奥塔(Lyotard)和乔治·巴塔耶
(George Bataille)这些极其干瘪的、自诩的“虚无主义”。
10.在后现代主义哲学中,避免采取立场已经被提升为一个哲学原
则。最近的一些法国学术明星都在嘲讽他们的前辈(尤其是萨特)太主
观,过于强调主体。(别忘了,萨特认为意识主体什么也不是,但照
让-吕克·南希[Jean-Luc Nancy]的说法,萨特的这种主张显然仍太主观
了。)11.见John Rajchman与Cornel West合著的Post-Analytic
Philosophy(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5)。
12.这里我们谈论的不只是后现代的碎片。这也是唐纳德·戴维森
(Donald Davidson)的一个立场,见其The Folly of Trying to Define
Truth一文,载于总第93期、1996年6月第6期Journal of Philosophy,第
263——278页。
13.在分析哲学中,人们可以从西德尼·休梅克(Sidney Shoemaker)
和约翰·佩里(John Perry)的早期著作到德里克·帕菲特(Derek Parfit)
和认知科学的近期著作中追溯这一失重的来龙去脉。(欧文·弗拉纳根
[Owen Flanagan]仍勇敢地为这一观念的持续有效性进行辩护,见他的
Self Expressions[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在大陆
哲学中,人们同样可以发现自我概念的瓦解,这一点既体现在萨特较具
实质性的“意识即虚无”这一主张,也体现在福柯(Foucault)、德勒兹
和让-吕克·南希对主体性的彻底摒弃中。
14.示例见他的Essays on Heidegger and Others,载于Philosophical
Papers(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1),第22页。罗蒂
自己绝大多数时候只谈其他哲学家提出的问题,但他坚持认为人类生活
的现实问题——比如贫穷、政治压迫、经济剥削、暴行和种族主义——
不是哲学问题。但这要归咎于他关于何为哲学以及哲学何为过度干瘪的
概念。在发动革命与心智自慰之间,还存在着一个丰富的对话空间,而
罗蒂自己已然成功地参与其中。
15.众所周知,苏格拉底认为未经省察的生活不值得过,但是,他
在哪些意义上省察或有没有省察自己的生活,这一点完全不清楚。显
然,他所想的并不是在现代的自我省察观念中无所不在的“内省”观念。
他似乎也不认为真正省察过的生活与寻常生活及其俗事有何相似。因
此,佩吉·努南(Peggy Noonan)在谈及她的前任上司罗纳德·里根
(RonaldReagan)时说,他就证明了未经省察的生活也是值得过的。在这个玩笑背后,隐藏着大量的哲学问题。
16.见Paul Woodruff的文章Plato on Education,收录于Amelie Rorty
编著的Philosophers on Education(New York:Routledge,1998)。
17.见伟大的独立记者I.F.斯通(I.F.Stone)撰写的未得到应有评价
但很杰出的耙粪之作The Trial of Socrates(Boston:Little Brown,1988)。
18.译者注:福斯塔夫是莎士比亚名剧《亨利四世》中的一个放荡
不羁的人物。
19.译者注:亚里士多德也曾被指不敬神差点被判刑,后来他想法
子逃出了雅典。
20.“深刻的思想家”这个词总带有一种轻蔑的意味,它源自科布
(Lee J.Cobb)1954年的电影《码头风云》(On the Waterfront)。不
过,我这个借来的反讽应该用维特根斯坦临终之言来平衡一下,很有苏
格拉底的风格:“告诉他们,我度过了美好的一生。”引自Rush Rhees所
编的Recollections of Wittgenstein(Lanham,Mo.:Rowman Little field,1981),也见M.O’C.Dury的文章Notes on Conversations(同上,76-
171),以及Terry Eagleton与Derek Jarman的剧本
Wittgenstein(London:British Film Institute,1993)。第一章 激情的生活
若没有爱过,生活还剩下什么?
——维克多·雨果(Victor Hugo)
告诉他们,我度过了美好的一生。
——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临终遗言)
生命丰富而肥美,充满着可能性和激情。可是哲学,哪怕是生命哲
学,常常都过于干瘪,被简化成骷髅般的原理、还原论的概念和单一化
的理论。在这方面,本应为生命哲学所用的伦理学可谓臭名昭著。几乎
整个20世纪——以及此前的世纪——人们都在致力于把伦理学简化为一
个单一的视角,甚至一个单一的原则,即“功利原则”或“尊重原则”。或
者可以说,伦理学(与政治学和社会哲学、美学和宗教一道)被极端轻
蔑又不幸地推到了哲学的边缘,“不再是真正的哲学”。它被认为太“软
弱”,“完全是主观的”,“严格来说,还毫无意义”1,由此而遭抛弃。人
类生命和激情丰美复杂的丰富性,被简化为一个备受推举的属性,即所
谓的理性,伯纳德·威廉姆斯(Bernard Williams)称之为“毫无特色的主
体”。2“人是理性的动物。”亚里士多德在两千五百年前如是说道。现代
哲学家们像是带着报复心一样接过他的这一命题后,把“动物”简化为纯
粹的生物,把“理性”局限在逻辑和语言之内。毫无疑问,亚里士多德若
是地下有知,肯定会被吓坏。我想要捍卫一种在哲学中常遭忽视或蔑视的“丰盈的”生命概念,进
而借此捍卫一套在伦理学中常遭忽视的德性。首先,我想要捍卫的是哲
学家萨姆·基恩(Sam Keen)在同题著作中所提倡的激情的生命。3这既
不奇怪,也不陌生。它是一种由情感所界定的生命,一种由热情参与和
信念所界定的生命,一种由一次或多次追寻、宏伟计划和无所不包的感
情所界定的生命。有时,它也会被描绘成用狂乱、过度的野心、“致死
的疾病”、根本无法达成的目标、绝无可能的感情(比如歌德
[Goethe]的《浮士德》[Faust]、克尔凯郭尔[Kierkegaard]和尼
采)。我想用这种生命概念与日常道德和“做个好人”进行对比,显而易
见,我这样做并不是要人们为了追求前者而放弃后者。尼采常常因
其“非道德者”的姿态和好战者的隐喻而遭误解,但我——基于坚实的文
本——深信他的意图绝非如此。4当然,我也不想独断地宣称充满激
情、强调参与的生活要优于较为安静、循规蹈矩的生活(用波西米亚反
叛者如今的标准行话说,就是“布尔乔亚式的生活”)。5但是另一方
面,我确实想提出如下问题:是否仅仅过得不错、遵纪守法、功利性地
权衡“理性选择”、尊重他人的权利和契约以及一点点自以为是,就是美
好生活的全部,哪怕在非道德的空间里头充斥着种种可容许的快乐和成
就。生活的意义不是为那些纯然的“好人”准备的,生命应灿烂燃烧,不
该寂然荒废,这种古代人、浪漫主义者和当代的摇滚歌手都有过的憧
憬,不该被人们——即使是我们这些已过而立之年的人——轻易摒
弃。6
在更深的层面上,曾有许多哲学家——包括苏格拉底、斯宾诺莎
(Spinoza)、叔本华(Schopenhauer),以及斯多葛学派(Stoics)、佛陀、孔子和庄子,甚至还包括亚当·斯密(Adam Smith),以上只是
其中一些例子——提倡“内心安宁”或“宁静”(ataraxia[不动心]、apatheia[无欲]、涅槃、道、安)作为至善。这也是我要加以质疑
的。当然,这不是说这些思想家以及他们的传统曾推崇或提倡情感的彻
底缺席。(例如,亚当·斯密就是道德情操的坚定辩护者;各种同情甚至极乐,在亚洲传统中也至为根本。)但他们或多或少全都固执地认
为,强烈、狂暴的情感——那种“席卷我们”的情感——非常麻烦,而且
常常是灾难性甚至是致命性的。
相反,在这一章中,我要提倡酒神式生命情调的正当性,它体现
在“能量”、“热情”、“魅力”甚至“迷狂”这些动态而非静态的隐喻、观念
中。7这也是荷马(Homer)、拜伦(Byron)和艾伦·金斯堡(Allen
Ginsberg)所倡议的充满爱欲的生活概念,这种生活或许有时因绝望和
忧世而难以承受,但也会因快乐和勃勃生机而振奋。绝大多数哲学家更
加熟悉的维特根斯坦就是一个不寻常的例子,众所周知,他的生活很神
经质,却也令人羡慕(不只是因为他的天才)。确实,拒绝在幸福与苦
楚(还有“善”与“恶”)之间做最终的区分,可能是我想要辩护的观点之
一,但这个不同寻常的论点不在这里要说的范围之内。(不过在第五章
对此有一次拙劣的尝试。)我较为温和的观点是:一种有德性的生活可
能不只是许多哲学家和当代道德权威敦促我们的那样,成为好相处的邻
居、受人尊敬的公民、有责任心的同事,以及有爱却毫无生气的人。
对此,可用更清晰的哲学方式来表述如下:在本书中,我首先要提
升伦理学中常受忽视的一维——激情或更一般的情感——的重要性。8
所谓的德性伦理学,即强调对行动者及其品格的伦理评价,如今被认可
为以行动和原则为中心的理论以及效果论之外的一个可行方案。不可否
认,德性概念已经被一些哲学家削得纤薄不堪,让人难以忍受,但是如
我所见,德性伦理学的优点在于,它丰富了道德描述和道德生活。9众
所周知,义务原则和效用原则也同样是干瘪的。集中于德性和品格问
题,能有助于整体地考量人格、历史、环境、文化和各方面的重要性。
当然,至于什么可算作德性、德性如何确切地与品格、原则和行动发生
关联这些问题,还存在着巨大的分歧。不过在这些问题之外,我还想增
加一个问题:伦理学中,德性和品格与情感是如何关联的。
很显然,人们谈及的许多(哪怕不是绝大多数)德性都与情感有所关联,不过常常是以负面的方式关联在一起。比如,勇气与克服恐惧有
很大关系,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Nicomachean Ethics)
中对此有详细阐述。菲利帕·福特(Philippa Foot)曾有一个著名的说
法:德性是情感的“矫正”,是把较为粗俗、自利的情感约束起来。10绝
大多数传统的恶习(贪婪、纵欲、自傲、愤怒,或许还有嫉妒,不过值
得注意的是,懒惰不在其中)都可以轻而易举地被定义为情感过度。可
是,上述任何情感的缺乏则常常被当作德性(禁欲、贞洁、谦虚等
等)。因此,尼采(在多处)警告我们说,莫把“缺乏情感的人”11等同
于好人。
更为正面地来看,主张道德情感的理论家弗朗西斯·哈奇森
(Francis Hutcheson)、休谟(Hume)、沙夫茨伯里(Shaftsbury)、斯密以及叔本华认为,一切伦理学都建基于同情、怜悯或同感
(Mitleid)这样的情感,不过这些情感(或情操)常常被认为是懦弱、情绪化的,甚至更糟。(当然,尼采认为这些情感极为糟糕,显得装模
作样、飞扬跋扈和伪善。12)就勇敢而言,德性是情感的调节器(“好脾
气”和“讲理”也是如此)。就同情而言,情感就是一种动机。因此,富
有同情心或显得同情本身就可以被认为是一种德性,而不只像亚里士多
德和绝大多数德性论理学家所主张的那样,是一种持久的“人格状态”。
(设想一个铁石心肠的人,在真正需要的时候表现了一次同情心。)
不过,亚里士多德也承认一些情感是德性,比如他把骄傲算作一种
德性(尽管他所说的骄傲与我们的骄傲观念极不相同),也稍带歉意和
牵强地把羞耻心当作一种“准德性”。(一个没有羞耻心的人大概也不会
有骄傲感,或者如埃塞俄比亚人的谚语所说的那样,“没有羞耻心的人
不会有荣誉感”。)换句话说,情感本身可以是一种德性,当然,这要
取决于各种具体情况的限制,还得考虑其强度和适当性。
这就是我在此要探寻的主张:激情本身就可以是德性。(当然,它
们也可以是恶习。)在《伦理学》(Ethics)第二卷中,亚里士多德问到,德性应被当作激情,还是更确切地说,被当作“人格状态”;他坚决
反对前者而主张后者。我并不否认,一般而言,德性是人格状态(或者
就此来说,激情可以是人格状态),但在我看来,激情(比如爱)也可
以是德性。
亚里士多德认为,激情稍纵即逝。这是一个常见的想当然。不过我
要说,激情(与短暂的情绪爆发、脾气发作、疯狂迷恋等不同)向来是
持久的——实际上是“难以消除的”。13尤其是,激情似乎仅仅指称强烈
持久的情感。说一个人“爱得很激情,不过每次只一会儿工夫”,除非是
在刻薄地开玩笑,否则就不知道这种说法有什么意义。因此,我要挑战
当前关于德性的标准描述(用伯纳德·威廉姆斯的说法):“一种选择或
拒斥行动的人格倾向。”14激情和情感不是纯粹的“人格倾向”,当然,从
其最为浅显的意义上来说,它们确实有助于促进选择某种行动、采取某
种方式。
但一种情感不是一种倾向;它首先是一种体验和“在世存
有”(beingin-the-world)的方式。如此说来(用吉尔伯特·赖尔[Gilbert
Ryle]15发明的行话讲就是),它是偶发事件性的,而不是倾向性的。
这不是要去否认激情可以持续很长一段时间——甚至一生——也不是要
去否认激情可以包括种种倾向,甚至是拥有其他情感的倾向。(我常常
听到这样的说法,在此基础上,爱不是一种情感,而是一种拥有情感的
倾向。16就像这一领域的诸多主张一样,这在我看来是对何谓拥有一种
情感的过度简化——也搞错了恋爱是怎么回事。)此外,激情作为德
性,不仅无须是一种人格倾向;甚至可以“与人格不相称”,与人们通常
对这个人的期待完全相悖。17“坠入爱河”以及由压力所激发的英勇行为
常常是这种“失常”的例证。确实,这些例子有足够的说服力,促使我们
去认真考虑把激情算作一种德性,而非人格倾向。
我首先想要挑战的,是一些反对康德所谓的伦理学中“倾向”优先的
标准观点,它们源自康德派的传统——尽管有人会争论,这并不是康德本人的说法。18随后,我想关注一种特别的情感:爱。这个字义杂乱的
词所涉甚广,从亲子之爱到圣人般的虔诚之爱都包括在内,但其中只有
一些可算作是有激情的。我们所谓的“浪漫的”爱、“炽热燃烧的”爱(如
简·奥斯汀[Jane Austen]在《理智与情感》[Sense and Sensibility]中
描述的那样,或如琼[June]和约翰尼·卡什[Johnny Cash]的“火
环”[Ring of Fire]所吟唱的那样),无疑属于其中。数千年前,柏拉
图为情爱(eros)这种激情辩护,认为它是一种德性。亚里士多德或许
较为谨慎,他为友爱(philia)的德性辩护(实际上,它是《伦理学》
中篇幅最长的论述),但它在多大程度上是激情而不是我们所谓的“亲
爱”(affection),就不得而知了。这里我不会思虑所谓的对人类的爱
(agape,caritas[博爱]),同时我会把怜悯、同情之类的情感放到后
面的章节(第四章),当然,它们在伦理学中由来已久,不仅存在于基
督教、儒家学说和佛教中,也存在于18世纪以理性为导向的欧洲启蒙运
动时期盛行的“道德情操论”中。19这里,我将采取一条更为艰难的道
路,为我们现在所谓的浪漫爱、情爱辩护,主张它们是一种德性——而
且是一种堪称典范的德性。在此,我的目标就是要把整个德性(以及恶
习)的形象颠倒过来,或者确切地说,与头脑保持一定距离来展望它
们。(有人说从“心”来看,但从生理学上来看,那是个含糊不清的概
念。)我要为人们所谓的热情辩护,主张它是一种德性,因爱的依恋而
生的热情就是最显然的例子。
冒着过于理智的嫌疑,让我先来对我的主张做一个重要的限定性描
述。当我说要为激情的生命辩护,且主张激情也是德性时,得先说清
楚,并非任何激情或情感都是德性,纵然有些情感是德性,那也不可能
一直是德性。20比如,我非常警惕某些集体情感:战争狂热、种族主义
以及一切导致种族屠杀的激情。(对于在体育竞技中不可避免会出现的
那些类似的“升华”或“错位”的激情,我并不乐观。体育迷们平时没什么
可高兴的事,除了买票去现场或坐在家里看电视之外,无事可做,因
此,对于我而言,他们那种毫无拘束的快乐,永远是一个令人不安的
谜。)有些情感不在德性的范围内(比如嫉妒),同时,情感超过一定的程度或强度(当然,对于这种量化的说法,我有所质疑),就绝不是
德性了。
比如,以爱为例,激情与迷恋之间就有着微妙的区分(香料商与牛
仔裤制造者常常忽视这一区分),我绝不会为迷恋辩护(当然,它们之
间的区分在于双方是否有互动,而不在于激情本身)。不当的爱、愚蠢
的爱、占有欲太强的爱(这或许更应称之为猜忌[jealousy]):这些
都不是德性,也不是有德性的,不过,即使愚蠢的爱也比完全没有爱展
现了更多的德性。但是,若想搞清楚德性本质的关键,就要格外留意激
情的爱与迷恋的爱(包括性的迷恋)之间的区分和关联。人们常说,德
性关涉的是可控之物,而“失控”正是有德性的对立面。(想想“精湛技
艺”[virtuostiy]21一词)但是,爱的本性就在于其不能被掌控,或者说
不能完全被掌控,而是与他人的突发奇想和福祉以及命运紧密相连。我
们发现,激情和欲望起伏不定,完全无视我们的希望和承诺。所谓迷
恋,或许正是翻涌变动的人生之海里所必需的牢固依靠,而所谓激情则
部分地要归因于伴随这种迷恋的不确定性。我要主张的是,正是这种激
情,这种面对不确定性时的激奋,和失控时的坦然接受,构成了爱的德
性。
最后,我想通过弗里德里希·尼采这位最具胆识和令人兴奋的现代
德性伦理学家的著作,对上述哲学颠覆加以概括。尼采有时称自己是一
位“非道德者”;然而,这种有点过分雕饰的自我描述,并不是要拒斥伦
理学,而是拒斥由康德以及(历史地来看)犹太——基督教传统所奠定
的那种广为人知的道德观。与此相对,尼采也捍卫过某种形式的“德性
伦理学”(他当然不会喜欢这个丑陋的标签),其中处于首要位置的,不只是德性,还有激情。直白点说,伦理学不是一种外在的强加,无论
这种强加是出自上帝、法律还是“畜群”,同时,它也不包括通常所认为
的有助于直接改善社会福利或公益的算计和人格状态。它不遵从内在理
性的道德律或“良心”的要求,而且就这点而言,它也不包括常常被基督
教徒颂赞为博爱的那种普遍的爱。“什么是善?一切提升权力感的事物。”尼采在其显然具有论战性的著作《敌基督者》(Antichrist)开头
如是写道。我认为,“权力感”与情感和激情很有关系。
在尼采更早的著作《快乐的科学》(The Gay Science)中,题目本
身就显示了对激情生活的辩护:la gaya scienzia(快乐的科学),游吟
诗人的生活,充满柔情和爱的生活。因此,尼采的“非道德主义”常常被
认为与唯美主义关系密切,即认为伦理学和伦理判断可还原或转化为审
美和审美判断。22这不是我在本书中要持的立场,虽然我认为这话说得
挺有道理。相反,我想追究尼采对激情的强调,尤其是他那激人奋进又
令人毛骨悚然的“权力意志”观念,它所强调的不是美学而是某种别的东
西:“能量”、“热情”、“力量”以及“自制”,不过这种自制不是说要克服
激情,恰恰相反,是要培育激情。很显然,这不只是在反对康德的实践
理性、功利主义的计算以及享乐主义,还要反对伦理学中由道德情操理
论家和(较为贴近尼采所想的)叔本华所主张的较为温和的情感概念。
不过在继续论述之前,还得强调一下,我认为权力意志在尼采学说中的
地位经常会被误解和夸大,被提升到了一个在其哲学中不应有的地
位。23我仅仅主张,有一种近乎可信的关于德性和恶习的伦理学,与盛
行的“德性伦理学”迥然不同,或者更宽泛一点,与各种出于“实践理
性”的伦理学极为不同。我必须抱歉地对戈雅(Goya)说,制造出恶魔
的,不只是理性的沉睡,还有理性的霸权。24爱作为一种德性:驳康德的典范
爱作为爱好是不能告诫的,然而出于责任自身的爱,尽管不是爱好
的对象,甚至自然地、不可抑止地被嫌弃,却是实践的而不是情感上的
爱,这种爱坐落在意志之中,不依感受为转移。
——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基础》
(Grounding of the Metaphysics of Morals)
它[爱]毫不犹豫地带着它的渣滓冲了进来……它甚至懂得如何在
政府文件和哲学手稿中偷偷塞进示爱的字条和小卷的发丝。它每一天都
酝酿和孵化出最糟糕、最扰人的吵闹和争执,毁坏最珍贵的关系、破坏
最牢固的盟约。……为什么会有这些嘈杂和纷扰?……这只是一个人人
皆有其偶的问题。(有品位的读者应该把这种习语转换为阿里斯托芬式
的语言。)为何这样的琐屑小事会如此重要?
——亚瑟·叔本华,《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
(World as Will and Idea)
叔本华是众多对导师反戈相向的康德主义者中的一位。这位伟大的
悲观主义者或许沉湎于康德的世界观,但却反对其伦理学。在他看来,伦理学的核心和基础是同感(Mitleid),而不是实践理性。但是涉及性
爱时,叔本华并不比康德更有识见(但无疑比康德更有经验)。他语带
讥讽地说道,“渣滓、嘈杂和纷扰”。当然,在叔本华那里,人类生活中
一切——艺术、佛教和他自己的哲学除外——在实质上都是微不足道
的。在他看来,爱显然不会拯救生活。实际上,一般所谓的激情不过是意志的挣扎,正是意志以它非凡且形而上学的无目的性规定并支配着我
们所有人。除了同情(康德也称之为“美”25),叔本华也贬低“倾向”,尤其不屑于理会激情,认为它不过是非理性。像康德一样,他显然也认
为浪漫感情与道德价值完全无关。
自启蒙运动以来,康德的道德判断和合理性典范就一直在伦理学中
保持着霸权。尽管康德的理性主义锋芒有所钝化,他的道德判断概念也
已然扩宽,但其首要的焦点仍确凿无疑,他的追随者们甚至毫无顾忌地
认为这一点显而易见:道德哲学若不客观、冷静、基于原则、排除具体
的自我指涉和摆脱个人“偏见”,就什么也不是。比如,伯纳德·格特
(Bernard Gert)在《道德规则》(The Moral Rules)一书中就认为感情
毫无道德价值,并且坚持认为:“感情在道德上的重要性,仅限于它们
能引导道德上的善行这个含义范围内。”26这个典范的骇人之处在于它所
忽略的东西,最明显的是绝大多数情感,特别是爱,除非它们有助于激
发责任感,或者能促进“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善”。伯纳德·威廉姆斯指
出,那种根据康德的观点认为善行应出于原则而非个人感受的说法,是
荒唐的。无论这种说法是否真是康德的主张,人们都可以设想一下把这
个观点移植到激情之爱领域的情形。光是这个提议就够骇人听闻了。
(人们一下想到的就是“夫妻的义务”。)还是想想爱的诸多快乐、感受
和责任吧;与其坚持认为爱(再怎么样也)与道德无涉,我们更愿意把
爱当作一种德性来对待,并抛弃完全没有人情味的“康德式”道德观。
格特认为,爱以及其他“感情”之所以可贵,在于它们有助于带
来“道德上的善行”,这种说法有其诱人之处。然而,不管爱是否能“带
来”值得赞许的行动,我们感情的价值都不会取决于因之而来的行动及
其后果。27爱是最具说服力的例子:在爱中,我们行动的价值取决于其
所表达的感情。爱或许会激发慷慨甚至英雄般的行动,但爱的德性仍卓
然独立。(苏格拉底在《会饮》[Symposium]中正是借此批评斐德罗
[Paedrus]。因为斐德罗赞美爱[善行]的结果而不是爱本身的德
性。)我们可能会认为(《理智与情感》中)的玛丽安(Marianne)愚蠢,但仍能钦佩她的激情,与此相反,爱德华七世时代的文学
(Edwardian literature)中随处可见的依原则行事的康德式绅士,倒是令
人反感十足。爱不仅会令人感到满足,而且那些已然不爱的人(不管他
们是否也失去过所爱),或那些害怕自己不能爱的人,所担心的肯定不
光是他们的品格,还有他们作为人的完整性——这与任何关于行动或表
现的问题毫无关系。我们(他们的朋友)也会为他们担心。爱本身就是
令人称羡的,与其作用和结果无关。28
反对把爱及其他感情看作道德的基本要素,这与《新约》中对爱
(即使这里所说的爱是博爱[agape],而不是情爱[eros])作为至高
德性的强调不一致,而《新约》的意图显然不会出于功利主义或康德主
义。这一部分开头援引的关于“病态的爱”的段落,正是康德对这一反常
情形试图作出的解释。他似乎认为,唯有能够被“命令”的,在道德上才
是必须的,而爱作为一种激情是无法被命令的。这个具体的主张常常惹
人争议,比如,爱德华·桑科夫斯基(Edward Sankowski)在关于爱和道
德责任的论文中,就论证说,我们人类至少有责任去促进或回避滋养爱
的条件。29对于唯有能够被命令的才是道德的(甚至是必须的)这一主
张,人们也可以质疑;因为许多构成“好人格”的要素,可以经由教养而
来,但不可通过命令而获得。人们还可以认为——我就常常这样认为
——情感比我们通常认为的更出于自愿、更受我们的控制,而且不仅仅
就我们能够促进或避开造成它们常常涌现的那些条件而言。当然,这也
不是说,爱这种情感就如同冒出一个想法或移动一下手指那样,可以仅
凭意志或意愿而产生。用丹托式的语言来说,就爱而言,或许并不存在
所谓的“基本行动”。30认为爱(或任何德性行动)可以凭空产生,无疑
是一个误解。
康德似乎认同《新约》中的伦理,因为他坚持认为道德的核心总是
普遍共相,而德性总是具体殊相。31而且根据绝大多数关于基督教之爱
的解释,爱显然侧重于对具体之人的爱。典型的基督徒会爱每一个具体
的人。他或她的情感和尊重不只是留给普遍共相(上帝、人性)。实际上,甚至康德都主张我们要在一个人那里爱人性。此外,爱,尤其是情
爱或浪漫之爱,不仅是具体的,还是有选择的,甚至是排他的,把本来
寻常之人提升到不同寻常的高度,并赋予其不同寻常的特权。在这种情
形中,“绝对命令”的观念——普遍的“应该”——是可笑的。根据康德的
模型,爱的特殊性似乎是非理性的一个典范——我们倾向于把自己(在
此则是把我们最亲近的人)当作例外的一个版本。一个会爱的人若坚持
要客观冷静地对待每一个人,包括他或她的爱人,肯定会让人觉得面目
可憎。
人们有时会说,一般所谓的情感,尤其是爱,都是非理性的,因此
不可能是德性,因为它们反复无常。32它们完全来去无影,不可把捉。
它们只是偶然,没有理性的必然性和理性的持续性。不过同样的,想一
想“不可索解”这样的指责吧。33众所周知,要让一个恋爱中的人清除这
种情感有多么困难,哪怕如今它已成了难以承受的痛苦之源。更确切地
说,爱会自我加强,随时间而扩张,并通过爱找到越来越多的理由去
爱。34我要表明,这并不是反对情感的一个论证,而是针对其德性的一
个方面。我们批评的,是那种转瞬即逝的幻象,而非不可动摇的热爱。
我们称之为非理性的,是突发的愤怒,而非根深蒂固和毋庸置辩的仇恨
(这倒不是说突发的愤怒总是不正当或不合适的,也不是说长期的愤怒
不会偶尔有些非理性甚至疯狂)。确实,情感是固执且难以驾驭的,但
也正因为此——与根本上不那么可靠、依原则产生的行动不同——它们
才在伦理学中不可或缺。一个出于激情而斗争的人,或许比为了一个抽
象原则而斗争的人更为可靠。难以驾驭是情感的德性,恰如合理化是理
性的弊病一样。实际上,我们甚至可以说,情感的真理(部分)正在于
它们的难以驾驭性,它们对变化的抵触。
人们也说,爱和其他情感会混淆或扭曲我们的经验,因此不是德性
的。但让我们想一想:一个其貌不扬的恋人殷切地看着他那个同样平常
的所爱说,“你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我们会如何理解这句话?自我
欺骗?疯狂?但绝不是盲目,因为问题不在于他瞎了眼。实际上,他甚至有理由说比我们看到的更多,或更深刻。面对这种无礼的质问,我们
这位陶醉其中的恋人或许会愤恨地做出让步,或许会做出一种现象学的
退让说:“好吧,在我看来她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但我们知道,哲
学会如何对待这种限定——认识论上理所当然的轻蔑。难道我们把这种
特有的看法当作爱的德性而非恶习,不是更好吗?(很显然,这一论点
不能被毫无批判地普遍施于其他情感。)
客观地说,爱可能与哲学伦理学要强调的一切都背道而驰——客观
性、非个人性、公正性、普遍性以及对证据与论证的尊重,等等。然
而,在我看来,这种“非理性”构成了我们最重要的一些道德特征。我们
彼此关心,无论是否有什么证据或论证表明我们应该如此。我们发觉彼
此的美、魅力和吸引力时,似乎也没有共同的参照标准。如果一个恋
人“总是见异思迁”,或者受朋友的意见左右,那我们就会看轻他或她,而不是看重他或她。许多人甚至认为,继续去爱一个显然完全不值得去
爱的人虽然是愚蠢的,但仍是值得称赞的。(大众舆论似乎证实了这种
毫无道理的爱,比如,有些女人爱上并嫁给了入狱的罪犯或等待行刑的
杀人犯,如近来的一部电影《死囚漫步》[Dead Man Walking]中的情
形那样。)爱(或爱着)本身就是德性,而且是一种重要的德性,与之
相比,合理性反倒显得苍白无力。情爱的德性
总之,我的论点就是:爱是最古老的神,是诸神中最光荣的神,是
人类一切善行和幸福的赐予者,无论对活人还是对亡灵都一样。
——斐德罗,见柏拉图的《会饮》
感性的升华叫作爱;它是对于基督教的伟大胜利。
——尼采,《偶像的黄昏》(Twilight of the Idols)
我的上述论点,绝大多数实际上适用于一切类型的爱(以及其他感
情),但是,要为激情的生活辩护,所需的范例仍是性爱或情爱。人们
可能会认为,父母亲子之爱中可以找到诸多德性,尽管如此,人们仍可
以质疑伴随情爱而生的焦虑和不安中是否也存在着同样的德性。在这方
面,就要注意情爱与博爱、“性”爱与无私无性的爱之间的区别。这个区
别,经过柏拉图到保罗基督教稳固的制度化之间的数世纪,日益变得粗
暴且不利于情爱。情爱被认为是纯然情欲的,并被简化为性欲,但它当
然不是这样。博爱被形容为无私的给予,与此相对,情爱就成了自私的
占有和渴求。博爱甚至被理想化到了一种唯有对上帝才可能有的态度,因此,它实际上无法应用于我们人类同胞的感情。与此相对,情爱被贬
低为渎神的世俗之物,没有一丝一毫的灵性。
把爱当作一种德性,首先就要(再次)扩展情爱的范围。但为了主
张情爱至少共享博爱的某些德性,人们不必否定博爱的可欲性(或可能
性)。情爱不同于博爱之处,在于情爱充满着利己欲望,但它并不因此
就是自私的,而且这种欲望也不必然就是性欲。它包括较笼统的在一起
的身体欲望,比如“被欣赏”和“一起幸福”的个人欲望、“为你做最好的那个人”的激发性欲望,以及“我能为你做任何事”的“利他”欲望。但要
注意的是,道德语言之所以在这些想法中失去了效力,并不是因为退回
到了前道德或非道德的领域,而是因为“你的”与“我的”之间的区分开始
消失了。
情爱贬损的一个关键因素,在于对性的反对。人们通常错误地认
为,在性行为中,他人被当作纯粹的欲望“对象”,由此也使人们认为情
爱是堕落的,所寻求的不过是一己之满足。让我们来看看康德对此问题
的看法:
由于性欲不是人对他人之为人的拥有倾向,而是对他人之性别的占
有倾向,因此性欲就是人性的堕落原理,它使人偏爱一种性别甚于另一
种,而且通过欲望的满足玷污了这一性别。35
然而,问题(恰如柏拉图在两千三百年前提出的那样)无疑在于,当一个人对他人有性欲时,这个人所欲求的是什么。在《会饮》中,阿
里斯托芬(Aristophanes)认为,人所欲求的不只是性的交合,还有与
他人永恒的(再次)合一;而苏格拉底则认为,人真正想要的是形式。
即使我们认为这些目标就情爱而言过于荒诞,但很显然的是,希腊人
——与康德和许多现代人相反——认为性欲不只是对性的欲望,而且根
本不与德性欲望相对立。至少这一点是显然的:性欲是一种以性为中介
的对他人的强烈欲望。问题依然是:欲求的是什么?我们决不应一开始
就假设这一问题的答案与性对象有关。实际上,若根据从黑格尔和萨特
(Sartre)那里得来的线索,我们反而会认为这与性主体紧密相关,因
为作为性主体的人,即是性活动的行动者,又是性经验的接受者(或共
同创造者)。36
换而言之,一个人对他人充满激情的依恋是一种德性,因为它体现
了一种尊重,尽管这种尊重确实与康德和康德派的那种抽象、干瘪的尊
重迥然不同。以为性欲与尊重不可共存,可以说是青少年的典型噩梦。
(人们还可以补充说,人一旦发现自己身处这样的约会活动中,就很容易有这种青少年心态。)这种噩梦完全不是出于经验和智慧的呼声。性
欲是最亲密的依赖形式,需要全身心的投入。确实,人们会发出疑问,道德领域(当然,诸多规则和禁令除外)之所以产生如此强烈的排斥
性,究竟有多少是因为以下情况:性不可避免是身体性的,而且涉及的
是身体最肮脏、最易受伤害、最柔弱的部位。这与康德的“理智”世界中
那个纯化了的“主体”有多远的距离啊!针对康德的反驳,我们或许可以
说,在爱的性行为中(很显然这不是艾伦·戈德曼[Alan Goldman]所
谓的“纯然性行为”),人激情地爱着的是他人本身。37在我看来,这是
我们最为推崇的终极形式的尊重,它不只是对法律的尊重,也不只是对
让他人自行其是的尊重,而是完全的、无所不包的接纳,以及由这种对
他人的接纳而来的快乐。
这一尊重常常受到忽视或被否认的一个方面,就是爱人之间的平等
这一前提条件。鉴于现代人指责爱是贬损和压迫妇女的工具,上述说法
可能显得古怪,但是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很显然——不管我们离真正的
(社会、经济、政治)平等有多远——浪漫爱的出现,只有在妇女从传
统从属的社会和经济角色中得到一定的解放后才有可能。也就是说,唯
有当妇女开始对她们的生活——尤其是她们的爱人和丈夫——有更多选
择时,所谓的浪漫爱才会出现。人们可以想想约翰·弥尔顿(John
Milton)笔下的亚当,这个在浪漫爱时代早期创造出来的角色,特意向
上帝要求的不是一个纯粹的玩伴或伴侣或自己的镜像,而是一个平等
者,因为“不平等者之间,哪有社会之有序,哪有和谐或真正的欢
欣”?38或者借用司汤达的话,我们可以说,在找不到平等者的地方,爱
就会去创造平等者,因为平等之于浪漫爱,恰如权威之于父母身份,乃
基本之物——无论人们是否充分认识到这一点或借此行动。
然而,就我们的目的而言,或许最重要的在于如下事实:与所倡议
的绝大多数德性(友善、可信赖、公正、谦逊、节制甚至勇敢)不同,爱是令人刺激的。当然,其中一些刺激与性有关,而我在前几页的论述
中尽力避免主张性欲本身就是一种德性。不过,性欲既不是一种恶习,也不应被贬低,尽管它很显然可以被用作表达各种邪恶和淫秽讯息的媒
介。但是,性行为中令人激动的感觉不应被简化或局限为通常(且含糊
地)所谓的“兴奋”。身体的兴奋就像性“本身”一样,在道德和享乐上是
中立的;它在我们生活中的角色取决于语境,尤其取决于与之相伴随的
情感和以之作为“表达”的关系。不过,对于性的诸多刺激,也许从我们
的脆弱性、我们对他人的开放性来理解更好,后者显然比诸多公认的德
性所指认的方式更“基本”。性爱的某些刺激源自不确定性,最初交往时
尤其如此,但是,我无疑要表明,新奇的刺激不应与爱混为一谈。39克
尔凯郭尔将一般所谓的爱的开放性描述为“信仰的跳跃”、“主观真
理”、“面对客观不确定性时的坚定”(尽管他对性爱冷嘲热讽)。这里
特别要注意的是,性爱涉及选择问题(这多么像是个命运问题啊),而
选择——连续的选择——很容易导致存在主义式的焦虑,即使结果早已
注定。
然而,性爱刺激的最终理由,用自我同一性这一哲学术语来表达最
好。人们常常根据情感的“强度”40来区分激情和普通情感、情感和不带
感情色彩的信念或判断,但我认为,更好的解释可以用经济学术语来
说,即所谓的情感“投入”。激情决定了自我,它们是自我的重大“投
入”,绝大多数情感做不到这一点。要注意的是,爱或许可以(部分
地)被定义为在他人身上并且通过他人来定义自己。不用说,这完全不
同于叔本华把爱视作性欲加哲学混乱的观点。它更像是柏拉图原创
的“阿里斯托芬式”爱的说法的最新翻版:两个被分成两半的灵魂的“成
全”和“融合”。41对此,我无法在这里深入分析,但它表明爱的“强
度”(以及其他激情和情感)要比纯粹的神经和荷尔蒙躁动深刻得多。
爱的那种激动人心的忠诚与依恋,与所有倡导不动情
(apatheia)、颂赞心灵平静的哲学截然对立,因为无论爱带来的快乐
和安全是什么,毫无激情的冷淡都不在其列。因此,从克律西波斯
(Chrysippus)到斯宾诺莎的斯多葛派,即便是在为某种更宽广的宇宙
心态辩护时,也对爱这种狂热、易受挫的激情心怀警惕。在这一点上,弗洛伊德与佛陀一致同意,“欲望就是受苦”,唯有终止欲望(“死亡本
能”、涅槃)才能带来解脱。在这里,“成熟”的智慧永远对年轻人纠缠
不休:要当心爱带来的狂喜,因为它最终只会令人失望。对这些观点的
辩护无论是出于审慎之故还是以德性之名,人们都不可能从中期待一种
对于激情生活的辩护,或爱是德性的观点。到这儿,我们绕了一圈,又
回到了一开始对情感的综合考察以及对爱的具体探究所希望达到的视角
转换。假设我们不通过平静的永恒之眼来看待生活,而是用我们的实际
经历来看待生活:短暂、急迫,不是理性要去解开的迷惑或奥秘。42假
设我们把激情本身当作至善——当然不是随便哪种激情,而是那些被爱
之类的激情所定义的生命,不是那些由宁静和心灵平静所定义的生
命。43一如往常,在这里我们必须提防诡辩和“说服性的”定义。如果说
放弃心灵平静就意味着要带着失败感、挫折感、良心不安或屈辱感去生
活,那么,激情的生活概念一点儿也不值得推崇。但是,如果爱的德性
之一是持续的刺激,而且这种刺激并不只是原本平静、“令人满意”的生
活的标点停顿(尽管“满意”这个观念可以被曲解以符合哲学的成见),那么,我们就应该认真对待这样一种生活识见:“骚动”而非其缺乏,才
是我们的最终渴望。而对这种生活识见最出色的描绘和展现,无疑是尼
采那些生气勃勃的散文。权力意志作为德性
什么是善?凡是增强我们人类权力感,增强我们人类的权力意志以
及权力本身的东西,都是善。
什么是恶?凡是源于虚弱的东西都是恶。
什么是幸福?幸福不过是那种意识到权力在增长,意识到反抗被克
服的感觉。
幸福不是心满意足,而是更多的权力,不是和平本身,而是战斗;
不是德性而是能干(文艺复兴时期的德性,也即virtü,恰恰是和道德
无关的德性)。
——尼采,《敌基督者》
当然,尼采自己言过其实了。夸张(以及不自量力)是热情的常见
症状。于是,基于一两句较为夸张的格言,好几代杰出的理性主义哲学
家就完全对尼采不屑一顾(“不是一个哲学家!”)。(据说,著名的耶
鲁大学哲学家布兰德·布兰夏德[Bland Blandshard]曾把尼采的一本著
作甩到了屋子另一角。这种对于尼采的常见态度直到最近才有所转
变。44)尼采夸大了他对道德的反感,变化地称之为“奴隶道德”和“畜群
道德”,并叛逆地称自己是一位“非道德者”。事实上,尼采认为自己
有“一种更加严峻的道德”45,而我也已经提示过,尼采真正的意思是
说,我们应从一个不同的“视角”来理解道德和道德性本身,这个不同的
视角就是我们现在所谓的德性伦理学。他同样夸大了自己对宗教的反感
(“上帝已死”是其开始),但可以争辩说,这种反感是在捍卫他童年时
代的路德教义中的精华,以及他认为早被德国人(尤其是他过去的朋友
理查德·瓦格纳[Richard Wagner])抛弃的精神性。他最为著名的夸
张,是“没有真理”(却又坚持完全的诚实)这一(前后不一致的)观点。不过,最引人注目又令人误解的夸张言辞,是关于“权力意志”的谈
论,这一观点最初在《朝霞》(Daybreak,1881年)中初显威力,又在
其后期的哲学著作《敌基督者》(1889年,出版于1895年)的开头明显
过分夸张的说法(见前面引文)中达到顶峰。
这不是全面探究尼采哲学的地方,甚至也不是探究他的“权力意
志”观念诸种细微之处的地方。但我应该清楚表明,为何我要把尼采而
不是亚里士多德当作我在德性伦理学领域的终极导师,以及激情生活的
捍卫者。因此,我将(简洁地)勾勒一下我所谓的尼采式德性理论。我
无法罗列一份“尼采的德性”清单,而这在亚里士多德那里轻而易举就可
以做到(不过人们或许注意到,尽管亚里士多德设定了“两端间的中
道”这一标准,但他的清单仍无法摆脱即兴而为[ad hoc]的嫌疑)。首
先,最明显的一点是,尼采可不是有体系的思想家。其次,尼采坚持认
为,我们每一个人有他或她“自己的德性”,甚至为某人的德性命名就等
于使之变得“常见”而否定了其独特性。现在流行的一种后现代主张认
为,尼采没有一种伦理学,也没有做任何断言,甚至没有提出“道德建
议”,因此反对这种关于尼采哲学的分析。然而,哪怕只是随便翻翻尼
采众多文字中的任意一部分,都会发现这样的主张站不住脚。46尽管如
此,这种解读方式仍吸引了一些非常优秀的尼采学者,其中有伯恩德·
马格努斯和亚历山大·内哈马斯。不过,我不打算在这里处理这些问
题。47不如让我出于启发的目的,在假设尼采确实给出了一些建议(事
实上无所不包,从营养指南到如何拯救世界)的前提下,试着谈一谈关
于这些建议的系统性观点——或确切地说,尼采那以“权力意志”为名的
德性伦理学——可能会是什么样子。
尼采所说的“权力”(Macht)一词到底是什么意思,历来广受争
议。这要部分归因于海德格尔复杂却又极不合理的分析,他说尼采
是“权力意志的形而上学家”;还要部分归因于瓦尔特·考夫曼(Walter
Kaufmann)在其经典著作《尼采:哲学家、心理学家、敌基督者》
(Nietzsche:Philosopher,Psychologist,Antichrist)中对这一概念的过分关注;但尤其要归因于这个词不祥的“军靴”味,因为它易于吸引亲法
西斯主义者,且无疑会让自由主义者感到惊惧。但是,尼采十分明确地
拒斥了针对他人的权力观念(包括政治权力,或德意志帝国);而且尽
管他确实赞成竞争,但也坚持认为,权力的首要意义在于自我控制。因
此人们也可以合理地认为,尼采心里所想的是创造力,是艺术家、诗人
和偶尔搞哲学的人的权力。尼采把权力等同于“精神化”,但同时警告
说,宗教和哲学中多数误作“精神”的东西,其实配不上这个名称。具体
而言,德国“精神”之所以变得如此毫无价值,就在于它已经彻底且自觉
地衰弱了,背负着错误的德性负担(尤其是谦卑之类的基督教德性,他
的精神同侪休谟称之为“僧侣德性”),并进一步被尼采所谓的“畜群”摧
毁。我要说,权力意志的关键是一种强烈的自我感,一种充满激情却有
纪律的自我,它追随自己强有力的“本能”,又能完全地“克服自
己”,“赋予自己的品格以个性”,“成为真正的自己”。48
上面这种描述中明显欠缺的,是诸如理性和反思这样的哲学德性。
与绝大多数道德哲学家(包括亚里士多德,不过他明确主张,经由教养
而来的正确行为要先于伦理推理)相比,尼采无疑更热衷于德性行为不
带反思的“自然而然”。但是,他也坚持理性的位置,而且他(像亚里士
多德那样)认为,体现在行动中的理性要比反思合理性中的理性更为重
要。比如,对于力的胜利。由于一种古老的奴隶习俗,我们一见到力就双腿发
软,不由自主要在它面前屈膝。然而,一种力是否可敬和可敬到什么程
度,取决于它所包含的理性的程度:因此,我们必须确定,力到底在什
么程度上被某些更高的东西克服了,这些更高的东西现在把力用作一种
手段和工具。
尼采对“力量”(Kraft)众所周知的强调,尤其是在《道德的谱系》
(On the Genealogy of Morals)的第一卷中,必须以许多这样的限制为
背景来考量。简单地把权力等同于力量(如尼采自己常常暗示的那样,上引《敌基督者》的原文就很明显),就会把尼采认作一个野蛮人或道德上的达尔文主义者,而他显然不是这样的人。如果我们认真对待超人
(übermensch)这个在尼采那里卡通化了的形象,那最好把它解释为尼
采的德性伦理学的投射,他理想的化身。49把超人刻画为野蛮人科南
(Conan the Barbarian),无疑对尼采不公;当他(更为常见地)谈
论“更高类型”时,他心里明确想到的常常是大诗人歌德。50
尼采式的德性有哪些?或许可以这样说,首先且最为明显的一点:
其中许多是“异教的”德性,它们(与在休谟那里一样)意在与基督教的
或“僧侣的”德性形成对照,后者在德国被重述为“资产阶级的”德性,这
一点尼采很清楚。因此,一份尼采式德性的主要清单,与亚里士多德式
德性清单很像:勇敢、慷慨、诚实、可信赖、节制(sophrosyne)、公
正、骄傲、友善和机智。但是,这份希腊的或“异教的”德性清单肯定不
是亚里士多德的清单,而且尼采心中所想的也不是亚里士多德笔下的绅
士贵族。他认为,古希腊三大哲人——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
德——的哲学全都是完全“败坏的”。尤其是,他认为亚里士多德的伦理
学不过是一种一厢情愿的思想,竟以为雅典可恢复它一度拥有而肯定不
会再现的荣光。俘获了尼采想象力的希腊,是前苏格拉底的希腊,索福
克勒斯(Sophocles)笔下准神话的希腊,以及荷马笔下战士的希腊。因
此,尼采对这些“异教的”德性的理解,必须回到过去,回到一个迥然不
同的年代,回到一种迥然不同的精神。此外,尼采对这些德性的看法也
与亚里士多德的截然不同,或许,这源于他一开始就拒斥“中道标准”以
及雅典人对“节制”的坚持。这反过来就要求对拥有一种德性有一个新理
解,而衣着讲究的绅士行为在此至多只有一丁点儿作用而已。
或许,这一丁点儿作用体现如下:尼采自己坚持“谦恭有礼”乃一基
本德性。当然,尼采并不反对亲切和友爱这些德性,且就其对社会德性
的关注而言(这当然不是他的主要兴趣所在),他也绝非如其有时自我
描述的那样,是那种“迎面痛击”的强硬派。(这种自我描述最明显的例
子就是他发表的对怜悯[Mitleid——也译作“同情”和“同感”]的诸多反
驳,但我认为,这种反驳有着完全不同的用意。)不过,尼采与亚里士多德更具戏剧性的差异,可以在对上述前两个德性——勇敢和慷慨——
的分析中找到,并由此引导我们进入激情生活的主题。
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勇敢就是对恐惧的克服。或者换一种说法,勇
敢就是具有恰当分量的恐惧:不能过多(否则就是怯懦),也不能太少
(否则就是鲁莽)。在亚里士多德那里,这种心理上的动态变化并不清
楚(比如说,克制情感到底是什么意思),不过清楚的是,勇敢需要一
定程度的恐惧。现在,让我们来看看如下这幅画面,它类似于亚里士多
德对《伊利亚特》(The Iliad)中赫克托耳(Hector)的勇敢的运用。51
阿基里斯(Achilles)因好友普特罗克勒斯(Patroclus)之死而暴怒,满
脑子都是报仇雪恨(“正义”)地冲向特洛伊城外的战场。他毫不畏惧。
在这种目标明确的狂怒中,恐惧完全没有一席之地。那么,说处于这种
状态下的阿基里斯“勇敢”,在我们看来即使不算荒谬,也显得过于轻描
淡写了。
我们自己在这里对勇敢的理解与亚里士多德一致。所谓勇敢,就是
对阻力(即恐惧)的克服程度。但是,若我们从尼采(和荷马)的角度
来看这个问题,恐惧与勇敢似乎并非互补,而是对立,因此,堪称勇敢
的是阿基里斯,而非那些双腿打颤却“强迫自己”站稳的可怜士兵。
(“勇敢”一词曾带有这种尼采式意蕴,但现在多少沾染些亚里士多德所
谓的“勇气”的含义。)换而言之,勇敢并不是对情感(即恐惧)的克
服,它恰恰是由不可抗拒、巧妙“协作”且指向明确的情感构成,不仅没
有排斥,反而整合了人的荣誉感,还可能因为其专注感而被解读为冷
静。激情的德性,就在于它的这种力量、效率和有效性,而不是这种仅
是表面化的冷静。
类似的分析,对于慷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称之为“赠予
的德性”)也是可能的。它不是单纯的付出,也不是付出的习惯。让我
们在当前盛行的慈善背景下来考量慷慨吧,这种慈善要求:“捐到心疼
为止!”人们可以设想这样一个捐赠者,他苦苦地与自己的吝啬作斗争,反反复复掂量着良心的负担与街上酒店里打折的贝夫堡红酒孰轻孰
重。最后,慷慨克服了阻力,德性得到了极好展现。但是要注意,首
先,一个人越是挣扎,德性就越少。亚里士多德认为,实际上,一切德
性的实现都是快乐的,而不是痛苦的;这本身就是对某人是否有德性的
一个检测。然而,可以设想一个人的慷慨在于我们称之为“流溢”的本
性。我听说,米克·贾格尔(Mick Jagger)在巡回演唱就是这样。他钱
多得自己(或任何人)都不知道怎么花,于是乐得自由撒钱,不管领受
者是谁,理由得当与否,他都不分青红皂白地给予。人们可以认为,这
种快乐的抛弃行为是真慷慨,无须为个人的损失而挣扎,只有一种随充
满感而来的流溢。
因此,其他德性也呈现为伟大灵魂的精神的“流溢”,是一个丰盈者
的“流溢”。若认为德性并非如此,而是与自利和个人需要相对的义务
感,那就倒退到了尼采所谓的病态德性的模型,即康德和基督教那里呈
现的模型,其中精神贫乏者(而非富有者)成为了关注之所在。为贵族
写作的亚里士多德,可谓介于两者之间。但是,尼采式德性的首要构成
因素是一种激情的充盈,一种独立世界顶端的俯视感。有这样一种伦理
观,就不必对金钱、声誉和权力念念不忘。穷困潦倒、不被学术同行所
注意且身体状况极其糟糕的尼采,就是一个恰当的例子。实际上,甚至
是节制(上述解释最易想到的反例)都代表着一种充盈,一种轻快的自
律感。对此,想想尼采关于饮食、健康和创造性幸福的诸多带有加州风
格的评论就知道了。
这种新伦理学的关键,就是“流溢”和丰盈处于核心位置。尼采在他
的著作中到处都运用了这样的术语和形象。不过,接下来让我们对这些
术语所指向的画面稍稍加以充实吧。在尼采看来,美好生活并不在于谦
逊(最低意义上的“满足”,拥有所需要的一切),而在于活力勃发、激
情、情爱,或是尼采常以那个世纪的哲学风格所说的“生命”。唯有拥有
充足的资源(很可能这些资源全是精神性的),一个人才能发展出“风
格”(遵守纪律,而非追随时尚)和“深度”,用美国习语来说,就是“有灵魂”,它意味着复杂、纷争、好胜的“酒神精神”。如果尼采有一种形
而上学(而且称之为“权力意志”不会完全令人误解的话),那它也是一
种非常现代的形而上学,是一种能量而非物质(或者可以说是“非物
质”)的形而上学。它会是一种动态的形而上学(与通常所谓的“过程哲
学”迥然有别),一种可以称得上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之名的形而
上学。尼采在其最后的著作《瞧!这个人》(Ecce Homo)中说“我是炸
药”,此时,它展现的既不是即将来临的精神失常的征兆,也不是“反
讽”,甚至也不是在放肆宣称自己哲学的潜在效应。他是在以一种独一
无二的恰当隐喻概括其哲学,并使之个性化。论诸德性的优点
既然灵魂的状态有三种:感情、能力与人格状态,德性必是其中之
一。[但是]德性与恶习不是感情。因为首先,我们并不是因为我们的感
情,而是因为我们的德性或恶习而被称为好人或坏人的。而且……我们
被称赞或谴责也不是因为我们的感情。其次,我们愤怒或恐惧并不是出
于选择,而德性则是选择的或包含着选择的。同样由于这些原因,德性
也不是能力。因为首先,我们不是仅仅由于感受到这些感情的能力而被
称为好人或坏人,而被称赞或谴责的……因此,既然德性既不是感情也
不是能力,那么它们就必定是人格状态。
——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
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及其对德性的关注,优点在于他的叙述较为具
体和丰富,并以自己的方式把生活的激情融进了美好生活的本质之中,而没有把生活的复杂性简化为一个“干瘪的”原则问题或理性论证或“最
大多数人的最大善”。但什么是德性呢?如果德性不过是抽象原则的个
人实现——履行义务的倾向或出于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善行动——那么伦
理学就会再次变得干瘪和逻辑化,缺乏个人和情感色彩。52我要试图表
明的是,德性伦理学可以有完全不同的设想,而上述这种简化的做法极
不恰当。
但是,甚至在亚里士多德那里都有一种强烈的倾向认为,激情是极
度自发、甚至是“刺激——反应”的方式,好像情感不同于德性,只是对
具体情形的反应而已。确实,它们看起来可能是这样。根据亚里士多德
的说法,德性是极其语境化的。实际上,如何确定德性是德性,取决于
其语境。在战士、政治家和艾滋病患者身上,勇敢的意义各有不同。一种语境下的德性在另一种语境下,可能就是恶习了,比如对贫困者的慷
慨(亚里士多德的“大方”)就与对宠坏的孩子的慷慨截然对立。在对德
性的定义中53,亚里士多德强调德性是一种“人格状态”,但是,在同一
本著作的其他地方,他又强调“知觉”和具体情形的重要性。而且,恰如
亚里士多德自己清楚的那样,绝大多数激情(和情感)并不是热情或愤
怒的随意爆发。情感多少具有一定的系统性,因为它们一起形成了一个
人的“性格”。当一种不寻常的情感“爆发”出来时(同样,可能是陷入热
恋或者对新生儿全神贯注的疼爱),这种情感不该被理解成一种纯粹
的“爆发”,而是一个激烈的重新构成,如果确实可以相信这种情感的
话,那可以说它重构并重新定义了个体的生命。
有人极力主张德性是一种品格状态而不是一种激情,但这种看法甚
至不适用于亚里士多德德性清单上的首要德性——勇敢。无疑,在阿基
里斯的情境中,勇敢是日常必需。而在今天,要求或推崇身体勇敢——
尤其是亚里士多德视作典范的战场上的勇敢——的情形极少。因此,勇
敢看起来就会是一种“爆发”,或突如其来的英雄行为或正直行为,而不
像是一种持续、显著的人格状态。但是,我们会因此否定勇敢作为一种
德性的地位吗?不会,即使这种勇敢显得愚蠢,也不会减损其作为一种
德性的地位。勇敢地挺身阻挡持枪的街头抢匪或青年帮派,通常(至
多)会被当作愚勇而非勇敢,但尽管如此,这也不会减弱这种行为的德
性,而且也不能仅仅将其当作一种“爆发”,而应把它看成某种“内心深
处”、长久潜藏的东西的呈现,甚至可以说是一个不一样的自我的呈
现。
爱确实可以是愚蠢的,但它也常常(实际上典型地)被认为“与个
性不符”。在爱中受挫折,最好的情形会让人变得高贵,糟糕的情形则
让人感到羞辱或陷入悲剧境地,但是,不愿去爱或没有能力去爱,则意
味着一个人不足以为人。尽管许多哲学家坚持道德是一个理性问题,德
性不同于激情,但情感在我们的道德世界中,仍保有一个基本位置。注释
1.这里所指涉的经典文本是A.J.Ayer所著的Language,Truth and
Logic(New York:Dover,1952)。
2.见伯纳德·威廉姆斯的著作Shame and Necessity(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7)。
3.见萨姆·基恩的著作The Passionate Life(New York:
HarperRow,197x)。
4.例见我的论文A More Severe Morality:Nietzsche's Affirmative
Ethics,收录于拙著From Hegel to Existentialism(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8)。另可见Lester Hunt的作品Nietzsche and the
Origin of Virtue(New York:Routledge,1991)。
5.我对这一点的澄清,要归功于乔治·谢尔(George Sher)提出的好
问题。
6.“燃烧”和“荒废”的隐喻取自尼尔·扬(Neil Young)。这种隐喻的
类似版本可见《旧约》、亚历山大大帝、英国和德国的浪漫主义诗人和
瓦尔特·佩特(Walter Pater)。
7.无疑,这些行为存在着神经生理学的解释,比如,可能是因为蓝
斑之类的脑干区异常,又或是去甲肾上腺素血清促性腺激素之类的化
学物质不足或过剩。我不怀疑,大部分“激情的生活”是慢性疾病而不是
教养的结果,但是,问题——如果我们不回避德性是否必须是“人所控
制”之物这样的问题——在于激情的生活是否能被当作有德性的生活,如果可以,那这种生活的德性可能是什么。
8.其中的一些论题,见伯纳德·威廉姆斯的文章Morality and the
Emotions,载于其作品Problems of the Self(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 Press,1973),不过,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及后来的尼
采,早就谈到过这些论题。
9.我要把这种对于德性的洞见与当今对于这个术语充满争议的使用
明确区分开来。在Bill Bennett的Book of Virtues发表一个世纪之前,尼
采曾这样谈及德性:“而且有这样一些人,他们认为说‘德性是必需的’这
样的话是一种德性;然而根本上他们只相信警察是必需的。”见由
W.Kaufmann翻译的Thus Spoke Zarathustra(New York:Viking,1954)
中的第二部分On the Virtuous,第207页。
10.见菲利帕·福特的文章Virtues and Vices,载于其著作Virtues and
Vices and Other Essays(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1978)。这
种对亚里士多德的看法有些牵强,例见倪德卫(David Steward
Nivison)比较亚里士多德和孟子的优秀论文Mencius and Motivation,载
于Journal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Religion(September 1979)关于传
统中国哲学的特刊,第419页。
11.译者注:原文为eviscerated man(被掏空内脏的人),暗指善于
约束或控制自己的情感的人。
12.特别见R.J.Hollingdale翻译的Daybreak(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2)。
13.具体见Amelie Rorty的著作Explaining Emotions(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0)。
14.见伯纳德·威廉姆斯的著作Ethics and the Limits of
Philosophy(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5),第9
页。参见David Ross翻译的亚里士多德作品Nicomachean
Ethics(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54)第三卷。威廉·弗兰克
纳(William Frankena)并非德性伦理学的拥护者,但他主张德性无非是服从理性原则的倾向,由此清除了这一值得研究的主题。
15.见赖尔的著作Concept of Mind(New York:Barnes and Noble,1949)。
16.例见O.H.Green的文章Emotions and Belief,载于American
Philosophical Quarterly Monograph,1972年第6期。
17.当然,一种新的不同“品格”可能因失常而显露出来,比如坠入爱
河或因新生儿的到来而情绪失控。尽管如此,德性仍在于拥有这种情
感,而非随后显现的品格倾向。(“此前我不知道他有这样一种情
感。”)
18.见Barbara Herman的著作The Practice of Moral
Judgment(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3)。
19.这里我要提到的不仅有伟大的苏格兰道德学家,著名的有大卫·
休谟和亚当·斯密(他比其同事弗朗西斯·哈奇森和沙夫茨伯里勋爵更注
重情感),还有卢梭,他在其教育论著(比如《爱弥儿》[Emile])中强
调了自然情感的重要性,这里的自然情感是相对于那些常常被称为理性
的“不自然的”、“败坏的”算计而言。在此,或许可以对我们所熟知的西
方观点与中国古典思想做一个有趣的对比。因此,儒家学者杜维明区分
了教化的人类情感与纯粹的“自然”情感,由此倒转了苏格兰学者对道德
情感自然性的强调。见杜维明的著作Centrality and
Commonality(Albany:SUNY Press,1989)。
20.比如,即使爱是德性,也可能在有些情形中会显得愚蠢荒唐,当然,人们会反驳“爱有时会是邪恶的”这样的说法。当然,邪恶的激情
的确存在着,但也许不应被称之为“爱”(而应被称作“迷恋”)——比
如,《呼啸山庄》(Wuthering Heights)中的希斯克利夫(Heathcliff)
对凯西(Cathy)的毁灭性激情,似乎就像这种情形。然而,我们可能坚持认为,即使爱有时显得愚蠢或具有毁灭性,它仍可以是一种德性,就像即使正义会带来灾难,我们仍坚称正义是一种德性,或者诚实导致
的结果可能比一个完全“善意”的谎言带来的结果要糟糕得多时,我们仍
坚称诚实是一种德性。但另一方面我想,我们要在德性行为中间做一些
细致的区分,补充其他一些独立于德性说法的标准。我这里的澄清要感
谢罗伯特·奥迪(Robert Audi)提出的好问题。
21.孔子在强调我们所谓的“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时,反复提到仁者
的“精湛技艺”(编注:在英文翻译时,“仁”常被译为virtuosity,这个词
实际上指“精湛技艺”)。精湛技艺一词是音乐中的常见用语,这绝非偶
然,而且,既然孔子明了音乐在生命中的核心位置,“精湛技艺”就不是
一个误译。
22.见内哈马斯的著作Nietzsche:Life as Literature(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5)。
23.我要说,对“权力意志”毫无根据的过度强调,主要来自海德格
尔,他几乎一点也不尊重文本,使用起来过于随意。在英美学界,瓦尔
特·考夫曼在其《尼采》(Nietzsche,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53)一书中对这一概念有详尽阐述,使得尼采至少
在一个仍然反纳粹、重实证的哲学世界里得到了尊重。不过,这种解释
所依据的主要文本,是尼采未出版的笔记,不过这个比较可疑。因为这
个概念本身就带有太多叔本华式的意志味,而这恰恰又是尼采一直努力
摆脱的东西。确实,尼采在其伦理学著作中大量运用了力量、健康和权
力这些隐喻,他也的确认同用权力去纠正享乐主义中存在的明显缺陷,回应极端的宗教行为(尤其是禁欲主义)所引起的心理学之谜。但我相
信,将权力意志——或任何类似之物——设想为尼采整个哲学的生长
点,是一个严重的解释错误。(关于“重构”这样一个“体系”的天才尝
试,见John Richardson的著作Nietzsche's System[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关于对由他人编辑的尼采那本名为《权力意志》[The Will to Power]一书的过度使用和滥用的质疑,见Bernd Magnus
的作品Author,Writer,Text:The Will to Power,载于总第22期、1990
年第2期International Studies in Philosophy,第49——57期。)
24.见戈雅的著作Caprichos(1797,New York:Dover,1970)。
25.见由John T.Goldthwait翻译的Observations on the Feeling of the
Beautiful and the Sublime(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60)。这个早期观点与这部分开头援引的略带讽刺的说法
schmelzender Theilnehmung(温存的同情)形成了鲜明对照。
26.见Bernard Gert的著作The Moral Rules(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8)。
27.从对行动和品格的关注到对感情的关注,这种转变可以说在18
世纪的欧洲就已发生,最明显的是卢梭的著作,当然也体现在道德情操
理论家的著作中。茱莉亚·安纳斯(Julia Annas)提到一个反对激情的古
老论点,认为激情会导致过度。但是,“过度”指的是什么呢?这里的问
题难道不就在于“过度”的可欲性吗?如果“过度”指的就是坏的行为,那
么功利主义和德性伦理学就有充足的理据来谴责这种行为。但是,如
果“过度”指的是激情本身,那么古代的论点就回避了问题实质。我主
张,在一定的意义上,激情本身就是善。倘若如此,激情的“过度”就是
不可能的,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言,德性的过度是不可能的一样。
28.不过,这并不是要否认爱可能会有不恰当的对象。柏拉图预示
了这一点,他坚持认为,爱(eros)不能仅仅是欲望,而必须是对善的
欲望。通俗来说,我认为他的意思是,一个人不能因某人的邪恶特性而
爱这个人。这种观点与当下盛行的见识截然不同,比如在许许多多的电
影中,都会有一个道德堕落的人被认为“爱上”了另一个人,而且正是因
为前者的道德堕落才爱上的(比如裘德洛·德·拉克洛[Choderlos de
Laclos]的书信体小说《危险关系》[Dangerous Liaisons]的几部电影改编,例见1988年史蒂芬·弗雷斯[Stephen Frears]执导、格伦·克洛斯[Glenn
Close]和约翰·马尔科维奇[John Malkovich]主演的版本)。这一说明要归
功于罗伯特·奥迪提出的难题。
29.见Edward Sankowski的文章Responsibility of Persons for Their
Emotions,载于Canadian Journal of Philosophy,1977年第7期,第829
——840页。
30.见丹托的文章Basic Action,收录于其著作Analytical Philosophy
of Action(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3)。
31.尼采把这一观点发挥到了极致,认为德性不仅是特殊的——即
有特殊的对象——而且在种类上也是特殊的,德性是有德性的人独有
的。
32.例见威廉姆斯的Morality and the Emotions一文。
33.见罗蒂的著作Explaining Emotions。
34.这不是一个先天论证,而且在经验中有许多显而易见的反例,比如猛增的离婚率。但是,爱常常会结束这一事实,并不有损于如下论
点:爱是一种情感过程,会随着持久的亲密、熟悉、了解、理解和共同
经历而愈益(或能够)加强和“加深”。对这一过程最为诗意的描述,是
司汤达(Stendhal)所描写的“结晶化”,借此,被爱之人会积累越来越
多的魅力和德性。见C.K.Scott-Moncrieff翻译的司汤达作品On
Love(New York:Liveright,1947),第28——34页。
35.见L.W.Beck翻译的康德作品Lectures on Ethics(Indianapolis:
Bobbs-Merrill,1963),第164页。
36.萨特有些搞混了这一简洁的主张,因为他坚持认为在性行为
中,我们试图把他人变成纯然的性主体——甚至变成纯然的性对象——但我们必定不会成功。见由Hazel Barnes翻译的Being and
Nothingness(New York:Simon and Schuster,1956)第三部分中的
Concrete Relations with Others。
37.见Alan Goldman的Plain Sex一文,载于Philosophy and Public
Affairs第3期第6页。艾伦·索布尔(Alan Soble)在他的《爱的结构》
(The Structure of Love,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90)中
对爱的存在论有详尽论述。
38.见John Milton的文章On Marriage and Divorce,收录于Robert
C.Solomon与Kathleen M.Higgins合编的The Philosophy of(Erotic)
Love(Lawrence: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1991),第79——84页。
39.见拙著About Love(Lanham,Md.:RowmanLittlefield,1994),第二章。
40.“强度”一词过于单维和量化,而且常常与生理上的兴奋相混淆
(且以后者来衡量)。但是,最强烈的激情可以是“平静的”(休谟
语),而最琐屑的怒气也可以是“暴烈的”(休谟语)。
41.对此,我在About Love的194页有详细辩护。
42.在《道德经》中,有这样的区分:热爱生活且完满地生活的
人、热爱生活却未能完满地生活的人,以及过于热爱生活以致过于强调
死亡的人。在这一方面,老子或许可以与伊壁鸠鲁做一个有趣的比较。
见由Stephen Addis和Stanley Lombardo翻译的老子著作Tao Te
Ching(Indianapolis:Hackett,1993)。
43.在《狗的秘密生活》(The Hidden Life of Dogs,Boston:
Houghton Mifflin,1993)中,伊丽莎白·马歇尔·托马斯(Elizabeth
Marshall Thomas)对比较神经学一个广为人知的发现进行了反思,狗的大脑有自我平衡的“牵引”,因此能够平静地休息,两眼凝视如禅定,以
至于我们与它们生活在一起都会认得和喜爱这种表情,但是,灵长类动
物的大脑受到的“牵引”,是以这个词在反主流文化中呈现出来的意义上
说的,即过度刺激的“牵引”、永不停息的躁动的“牵引”,以及人本身
的“牵引”。弗洛伊德错误地把自我平衡模式用于人类灵魂(要是他论及
的是狗的话,就对了)。
44.见Kathleen M.Higgins的著作Nietzsche's
Zarathustra(Philadelphia:Temple University Press,1987),第ix——x
页。
45.这个说法出自尼采写给保罗·李(Paul Rée)的一封信。见A
More Severe Morality:Nietzsche's Affirmative Philosophy一文,收入在拙
著From Hegel to Existentialism一书中。
46.例如,“对哲学的唯一批判就是……证明某事,主要是试着看看
一个人是否能够按照哲学来生活,这在大学里是永远学不来的:大学里
教的永远是用一种话语来批判另一种话语”。见由R.J.Hollingdale翻译的
尼采作品Untimely Meditation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2),第八章,第187页的Schopenhauer as Educator。
47.见Bernd Magnus,Stanley Stewart和Jean-Pierre Mileur的著作
Nietzsche's Case:Philosophy asand Literature(New York:Routledge,1994),以及内哈马斯的著作Nietzsche:Life as Literature。我自己论点
的阐释,见我的Nietzsche Ad Hominem,Perspectivism,Personality and
Ressentiment一文,收录于Bernd Magnus和Katheleen M.Higgins合编的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Nietzsch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6)一书中。
48.语出品达(Pindar)。引自W.Kaufmann翻译的Gay Science(New
York:Ramdon House,1968)。49.事实上,“超人”只出现在《查拉图斯特如是说》的开头,它在尼
采哲学中并没有实质性的地位。
50.明显的例子见Skirmishes of an Untimely Man一文,收录于
W.Kaufman翻译的Twilight of the Idols(New York:Random House,1968)一书中,特别是§§49-50。
51.见荷马的著作The Iliad,xv,348-351,以及亚里士多德的著作
Nicomachean Ethics第三卷第八章(1116)。罗斯(在对亚里士多德的
翻译的一个脚注中)指出,这一引文更像是在描述阿伽门农
(Agamemnon)而不是赫克托耳(Ethics 17.68);另见亚里士多德
(1117):“激情有时也被认作勇敢……因为激情首先就是冲向危险的
渴望……”因此,荷马才说“他的激情充满力量”。亚里士多德更进一
步,认为出于激情而行动的人并非真勇敢,倒是更像野兽。他们行动不
是“为了荣誉,也不是在规则的指引下”(同上)。尽管如此,他仍补充
说:“他们拥有某种和勇敢类似的东西。”
52.例见T.M.Scanlon的著作What We Owe to Each
Other(Cambridge,Mass.:Harvard,1999)和Simon Blackburn的杰出
评论,发表于1999年2月21日的The Washington Post书评部分,第24版。
53.见亚里士多德的Nicomachean Ethics,第二卷,第五章。第二章 情感的政治
灭绝激情和欲望,仅仅为了预防它们的愚蠢以及这种愚蠢的不快后
果,这在我们今天看来,本身就只是一种极端的愚蠢。
——尼采,《偶像的黄昏》
哲学家常常把“理性”与“激情”对举,典型的做法是捍卫前者而反对
后者,并主张哲学本身即理性之爱。这至少意味着,哲学倾向于对激情
置之不理。几乎在任何一本入门性的逻辑学教科书和伦理学著作里,都
会把“诉诸情感”当作一种“非形式”谬误列举出来,或许用不着不惜代价
去避免它,但至少要在学期论文中躲开它。哲学被重新定义为对论证的
阐述和批判,这是理性的专属领域。“激烈的”论争寻常可见,但仍被认
为不妥当。不带感情的分析受到鼓励,而激情的辩护被压制。哲学或许
仍被忠实地描述为智慧之“爱”,但这种爱几乎不再有苏格拉底(如果不
是柏拉图)处理这一主题时所具有的那种饱满热情了。于是,今日的理
想,即便不是后现代犬儒主义的那种深思熟虑的无欲(apatheia),也
是一种冷静,一种沉思的超然。激情的生活几无显露的机会。
即使我们发现一位伟大的哲学家为激情辩护,反对过分提倡理性,结果也难有教益,反倒是弥漫着一股怀疑主义味道。最著名的当属大卫
·休谟,他认为“理性是而且应当是激情的奴隶”,直截了当地摒弃了视
伦理学为理性事务这一漫长的传统。但他这样做,至少暗示了——当然也为他人设置好了舞台去讨论——这样的观点:道德在理性的把握之
外,并且在某种基本的意义上是不可争辩的。通过把理性和激情并举,休谟实际上与历史上一长串的哲学家一样,把情感与理性对立起来,并
使二者分离。休谟仅仅是倒转了这个对立而已。笛卡尔及其同胞马勒伯
朗士(Malebranche)曾根据生理学的“精气”(animal spirits)来分析情
感,并明确把它归为心灵的低劣部分——如果它确实属于灵魂的一部分
的话。(休谟同样也使用了这个术语。)莱布尼茨(Leibniz)认为情感
是“含混的知觉”,而康德则把它当作“病态的爱”(作为一种情感的爱)
不予理会,并把它与《圣经》和实践理性所控制的较为适当的爱区分开
来。康德或许也说过,“若无热情,就不会有伟大的成就”(通常认为这
个说法出自黑格尔),但很显然,在他对更高人类能力的宏伟“批
判”中,热情本身微不足道。
我们要谈论的“情感的政治”,正是基于这种最粗浅的理解。哲学史
上,情感多数时候被当作灵魂里头的游民无产阶级(lumpen
proletariat),在生产经济中没有什么作用,却依然是需要为之恐惧的负
担和危险,应尽可能有效地被控制。情感的政治否认它们的正当性和重
要性,由此表明对它们的压制和忽视的合情合理。现在,就让我们开始
考量一下这个以哲学的“干瘪”之名发动的“政治”运动吧。被贬损的情感
道德家的疯狂在于其要求的不是控制激情,而是根除激情。他们的
结论永远是:唯有柔弱者是好人。
——尼采,《敌基督者》
“道德家的疯狂”在当今的哲学文献中依然存在。让我举两个例子来
说明一下,一个是我们最卓越且思想开放的一位道德哲学家最近的演
讲,一个是一位知名心灵哲学家的论文。
在就任美国哲学协会(太平洋分部)会长的演说中,乔尔·范伯格
(Joel Feinberg)问道:“在处理实践伦理学的问题上,诉诸情感若有用
的话,那它的用处何在?”1他以通常的回答开头:“对这一问题最唐突
的回答是‘没有任何重要性;情感是一回事,论证是另一回事,而且没
有什么比情感更能蒙蔽心灵了’。”(19页)范伯格拒斥了这种“唐突
的”回答,但他的结论绝不是热心地认同情感;他承认,感情在伦理学
中是“相关的”,或者说至少不是毫无关联的,他得出结论说:“在有效
的人道主义与在灵活控制下对人类基本情感的维持之间,没有处理不了
的冲突。”好像这样说还不够谨慎似的,他补充说:“我希望这个结论不
是太过乐观。”(42页)
范伯格对情感在伦理学中的位置的仔细分析,值得进一步展开来仔
细回应,但这里我只想提醒大家注意,他在被迫提出他那个“乐观的”论
点——情感在伦理思考中并非完全不相关——时,是极其谨慎且带着防
备心的。请注意,为了给情感腾出一丁点儿空间,他要费多大的劲儿
啊,比如就好像说,在争论堕胎问题时,一名孕妇对自己身体、胎儿、“道德”和声誉以及她对胎儿父亲和自己人生规划的感受不过是些私
人轶事,只会转移主题,而哲学家们关于胎儿的地位和权利以及妇女控
制自己身体的(抽象)权利的论证,是唯一正当的关注所在。无论这种
伦理学的利弊何在,其重点都完全集中于原则以及支撑它们的论证,而
情感对于我们的道德思考没有任何值得一提的贡献。2
第二个值得提及的例子是杰罗姆·谢弗(Jerome Shaffer)发表于
1983年的《一个关于情感的评估》(An Assessment of Emotion)一
文。3谢弗以一个关于“情感遭际”的例子开始:“我沿着弯道行驶,看见
路上横着一根木头。我认为它可能对身体造成伤害,而我不想如此。我
脸色发白,心跳加速,胃在收紧。我猛地踩了刹车。”4毫不意外的是,谢弗用这个以及类似的情感例子得出结论说,情感不是特别令人愉悦或
有价值的经验,因此“对于生活的主要关切而言,既无必要,大体上也
不可欲”。5稍作反思就可以认定,这种无人乐于见到的惊慌情形,完全
不可以当作情感的典范。实际上,人们可以反驳说,惊慌不是一种情
感,尽管它的心理活动与某些情感类似。无论如何,并非所有的情感能
用“脸色发白、心跳加速、胃在收紧”等等来描述,更不用说定义了。想
想,若用我们的主要例子,比如正义得以伸张时感受到的强大满足感,或者可能长达数十年充满激情的恋爱经历,就会出现截然不同的分析。
(谢弗在同一篇论文中对作为情感的爱分析时,把爱简化为“小鹿乱
撞”和“波动、过电、汹涌或充血”,由此得出结论说,爱不过是一种没
有什么价值的情感。这绝不是打动特里斯坦[Tristan]和伊索尔德
[Isolde]的激情。)此外,我们乐意赞成,道路中间横着一根木头并
不是一种可欲的经历,但也不必由此得出结论说,恐惧本身是一种不可
欲的经历。6实际上我们知道,在较为安全的环境下,数百万的人愿意
排队付上十美元让精心设计得千奇百怪的自然和非自然现象吓破胆,这
些现象包括龙卷风、食人鲨、大猩猩、侏罗纪克隆动物、各种火星人和
其他外星人、飞木、流动的岩浆和杀人狂。
事实上,谢弗的情感“评估”是一次政治诽谤,不过他进行论证时的油滑方式,也表明了情感的政治地位之低。我们可以想象这样一种情
形,一位哲学家在同样专业的期刊上发表一篇评估逻辑的论文,其中以
一个荒诞的诡辩作为典型案例,并由此得出结论说逻辑在我们的生活中
并不特别重要或并非可欲的。可是,哲学中针对情感的偏见过于强大,以至于这样一种不公或轻率的抨击都无法引来抗辩,相反,若是为情感
辩护,无论这种辩护是多么冷静和负责任,都会招来这样的指责:软心
肠的多愁善感。
大体而言,现代美国哲学对情感在哲学中的作用既缺乏兴趣,又极
不信任,我认为这种说法并非夸大之词。(哪怕我们最著名的两位哲学
家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和约翰·杜威[John Dewey]对此有浓
厚的兴趣,也还是如此。)根据盛行的方案来看,哲学家们应当设法保
持理性,而不应充满激情或——甚至更糟——情绪化。哲学家们应该评
价论证,而不应“陷入”某个立场。(我有位同事对正在写内容极易情绪
化的文章的学生们说,他“丝毫也不关心他们相信什么,而只关注他们
的论证是否有效”。)事实上,人们开始怀疑,当今哲学话语获得尊重
的标准,是否就在于没有任何情绪反应。哲学论题必须冷静且尽可能形
式化地加以论证,由此抵消华丽辞藻的魅惑效应,避免诉诸情感。那
么,像克尔凯郭尔或尼采这样的哲学家因为颂赞激情胜过理性,而被不
屑一顾地说成“不是真正的哲学家”,也就不那么意外了。这种为人熟知
的排外政治使情感边缘化,也就进而使推崇情感的哲学家边缘化了。
即使情感确实出现在哲学中,它们的地位也会被认为很次要;对它
们的分析,也只是个附带问题。比如,笛卡尔和休谟堪称典范的情感理
论,就通常被忽视。别的不说,笛卡尔的论著《论灵魂的激情》(On
the Passions of the Soul)包含了他对心灵与身体之间的微妙关系持久不
断的沉思,通常却被撇在一边,人们偏爱的是更诱人的《沉思录》
(Meditations)以及更具方法论性质的《指导心灵的规则》(Rules for
the Direction of the Mind)。学生们会被要求阅读休谟的巨著《人性
论》(A Treatise of Human Nature),但通常只限于第一卷和第三卷,而论激情的第二卷则被排除在外。同样的,阅读斯宾诺莎的学生通常只
到《伦理学》第二卷就戛然而止,而对斯宾诺莎自己无疑认作是整个研
究之核心的三卷论激情的雄文置之不顾。7偶尔也有名为“情感哲学”的
课程,但通常会被认为很古怪很边缘,就像是“新时代哲学302号”或“爱
与性的哲学”这类课程,是那些头脑不清和易于激动的人才热衷的哲
学。
但是,即便在情感确实成了关注焦点之时,处理它的方式常常也太
像如今哲学处理一切问题的那种做法——形式化、客观化、论辩性、无
激情——换句话说,完全与主题本身无涉,甚至与之对立。在这一领域
的大多数著作中,丰富的情感话题被简化为对“意向性”的本性、“认
知”的各种形式、心理范畴的正确理解之类干瘪的逻辑分析。我并不反
对这样的研究,而且觉得其中一些颇为有趣,但是,情感却杳无踪迹。
我这样说并无意冒犯。不过,若认识论的目标之一是增进我们的知识,那么我们情感的“知识价值”似乎应该是一个基本的探究方向。8实际
上,许多关于情感的研究似乎把情感说成不过是“感受”,由此来打发或
舒缓我们的情感。人们确实可以论证说,现代哲学过分强调认识论而忽
视情感,泄露了对于哲学和人性之本性的一个不加批判且很可能错误的
假设:我们首先是认知的存在者,其次或许在病态的意义上才是感受的
造物。从政治上来看,这显然有助于那些善于认知和长于理性的人,而
那些将敏感和激情奉为首要德性的人,则因此而被降低和贬损。(妇
女“较敏感而缺乏理性”的这一传统形象,在政治上看来,并非与这一指
责毫不相干。)何谓情感?(走向一种政治观)
伦理哲学家通过诉诸自己的下丘脑边缘系统的情感中枢,就直觉地
知道义务论的道德准则。
——威尔逊(E.O.Wilson),《社会生物学》(Sociobiology)
“何谓情感?”威廉·詹姆斯一百年前为《心灵》(Mind)杂志撰写
的论文就以此为标题,一字不差地问过。9自西方哲学开端以来,哲学
家们就一直关心且担忧情感的本性。苏格拉底和前苏格拉底的哲学家
们,对于情感在理想人生中的位置,就提出过深刻的问题,只是他们提
出的问题并不一致。尽管这个学科是在追求理性中发展起来的(很大程
度上是因为苏格拉底及其学生柏拉图),但情感一直潜藏在背后,是理
性的一个威胁,对哲学和哲学家而言也是一个危险。或许,这就是为何
关于理性和情感最经久不衰的隐喻是主人和奴隶:其中,理性的智慧牢
牢掌控一切,危险的情感冲动则被安全地抑制住、疏导开,或者更理想
化一点,变得与理性和谐一致。
主奴隐喻显示的两个特征,至今仍决定着许多关于情感的哲学观
点。首先是情感的次要角色,人们认为情感较原始而少理智、较粗野而
不可靠、较危险因而要受到理性控制(亚里士多德和其他开明的雅典人
正是用这一论证来证明奴隶制这一政治制度的合理性)。其次且更为深
刻的,是理性——情感的区分本身,好像我们所涉及的是两种截然不同
的自然天性、灵魂的两个相互冲突和敌对的方面。甚至那些力图整合两
者、想把其中一个简化为另一个的哲学家(典型的做法是把情感简化为理性的劣等类型,即“含混的知觉”或“扭曲的判断”),也坚持这一区分
并继续主张理性的优越性。因此,休谟宣称理性是激情的奴隶,就成了
他激烈反抗传统习见的一个标志,但就算是对情感结构有着天才分析的
休谟,也没有脱开古老模型和隐喻的窠臼。
“何谓情感?”这个问题——说白了——不只是一个理论问题,也不
只是对情感取得一种充分理解或解释的尝试。它首先是一个实践问题,因为我们摆脱不了情感,且要通过情感来生活。简而言之,我们的情感
就是我们的生活。在同样的意义上,我说一个人必须活在婚姻中并且通
过婚姻而生活,而仅仅理解“婚姻:制度、历史以及相关的法律、相关
的奇异趣事和不寻常的案例……”是不够的。从这样一个切入点来
看,“何谓婚姻”是一个存在论的追问,而不是一个社会学的探讨。实际
上,这里不是在说某个婚姻的特殊性,也不是在探讨某人自己的婚姻。
这就是为何这一问题对于我们如此重要,为何仅有笼统的概念(比如离
婚与复合的数据)对我们没有什么实际助益的缘由所在。但是,在一般
知识与我们生活的具体环境之间的,是理论与实践的相互依赖。如果人
们把婚姻理解为一种个人的、充满激情的承诺,那么婚姻本身就主要由
这样的一种理解构成,如果同样的婚姻被理解为不幸的命运安排,或一
种社会或家庭责任,那它当然会是一个完全不同样子。
情感也是如此,如果人们把情感理解为基本上无意识的生理反应
——比如以研究较多的“惊吓反应”(startle response)为模型——那么人
们就会把自己的情感经验理解为干扰、不幸、疾病的短暂发作或身体的
奇怪颤抖和收缩。10另一方面,如果情感被理解为政治行为或战略性的
社会行为,那么这种理解不仅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人们的情感“观”,还
会影响人们的情感行为和感受。因此,我要主张,一种情感首先是一种
不间断的实践,人们主动与他人一道参与其中。它不单单是一种现象,不只是“某种就这样发生的事”。它不仅是个人的,也是人际的、社会建
构的和习得的。拥有一种情感,无论是承受因它而来的痛苦,还是尽其
可能地发挥它的价值,首先就是一种社会和政治实践,要与他人一起过一种正派、充满激情的生活,就不能缺少这种终极的实践。
这并不是说理论没有位置。相反,我会像反对理性与激情之间的可
恶对立一样,坚定地反对理论与实践之间的有害对立,并且把它看成同
一运动的构成部分。我们时常被告知理论生活就是不带激情、纯粹探究
的生活,然而这不过是个假象,一旦我们了解任何一位严肃的科学家或
学者,就绝不会怀疑他们探索的基本激情,不管怎样描述都一样。11无
论实践受理论驱动,还是理论以实践为导向,把这两者分隔开来都是错
的。我们如何反思我们的情感,必定与我们如何经历它们有关,其中包
括我们如何将它们理性化,如何用它们来对待自身和他人,以及我们如
何用它们给自己的不良行为找理由或借口。12
有鉴于此,我要论证三个否定性的论点,它们对于我在这本书中运
用的情感概念至为重要。第一个也是最为重要的论点是,情感不是感
受;第二个论点是,不管我们可以从人类神经生物学以及相关学科获得
多少知识,情感不是或至少不能被简化为生理现象;第三个论点是,情
感不能仅仅根据个人行为来理解,这里的“仅仅”一词并不是要否认情感
在行为中的表达,也不是要否认情感在某种意义上是个人经历,而是要
否定这样一种可能:在理论或实践上对自己或他人情感的充分理解,可
以不考虑相关的社会背景、文化、社会和人际关系,以及这些条件下行
为的“意义”。也正因为认识到这一点,我才使用“情感的政治”这样的表
述。
人们在完全无害的意义上,常常把情感说成是感受,包括各种各样
的意识,其中最显著的有长期的爱和感情。但是我要否定的那种意义绝
非无害,尽管如尼采曾写到的那样,它是可以“被驳斥的”。这种说法最
著名的捍卫者是威廉·詹姆斯,他主张情感是一系列的感觉(由可指明
的生理骚乱引发,而后者又由令人不安的知觉引发)。20世纪初,詹姆
斯的观点受到坎农(W.B.Cannon,《身体的智慧》[The Wisdom of the
Body]一书的作者)和他的实用主义同行约翰·杜威的质疑,他们指出,我们的全部情感要比我们相对贫乏的感觉复杂和精致得多。13举个
熟悉的例子,羞耻与尴尬之间的差异就无法简单地根据感觉或它们的生
理原因来理解。要理解这一差异,就必须参照社会性灾难发生时感受到
的责任、所处的社会处境和文化。应当注意“感受到的责任”这一表述,因为它不是詹姆斯意义上的“感受”,而是一种观看或理解或解释具体处
境中(一个人自己的)社会行为的十分复杂的方式,这种方式是习得
的。在其他地方,我称这种“观看方式”为判断,并且认为情感正是由这
样的判断构成的。14
或许人们会说,情感是一种感受这种观点非常合理,因为如果一个
人有一种感情,他或她必定在某种意义上感受到它,也就是说,对它有
意识。无须说,在这一点上,有一大堆现象学问题向我们涌来。我们所
用的“意识到”一词是什么意思?它能排除无意识情感的可能性吗?有时
我们被证明自己所谓的感觉错了,也就是说我们所拥有的感情是错的,那么,它能排除这种可能性,或这个明显的事实吗?这种思考削弱了传
统的笛卡尔式主张,即我们能够立即意识到自己的心理过程,包括情
感,因为无意识这个观念——这点弗洛伊德做过辩护,且否认行为这种
我们所熟知的情感伎俩也能证明其存在——表明,我们无法与自己的情
感反应和解,甚至无法“与之接触”。尽管如此,我们仍难以否认笛卡尔
式主张的意义,如果某个东西能算作情感(与纯粹的身体抽搐或机械行
为相对),那么主体对它的意识就是一个基本条件;这可以说是不可避
免的要求。然而,这和威廉·詹姆斯所主张的情感即感受是完全不同
的。
情感可以简化为生理现象的观点,只是偶尔被当作常识论点(而且
通常是作为隐喻)提起。确实,我们长期运用生理学、机械学以及“水
力学”的形象来捕捉情感的机制和感受。15如今,在谈论情感状态时,盛
行的是计算机隐喻(“输入输出”、“过载”、“界面”等等)。但是,人类
情感的生理学模型,或者更确切一点,神经学模型的最重要动力,来自
医疗实践和科学理论领域。整整一个世纪之前,两位医生对他们的同行说,心理学必须考虑新近发展起来的神经科学。威廉·詹姆斯写道:“心
理学家被迫变成了一定程度上的神经生理学家。”大约与此同时,弗洛
伊德把他所谓的“心灵器官”确定为大脑。16今天,我们完全可以理解这
些努力。通过把各种心理疾病“简化”为神经生物学上的功能障碍,神经
病学在过 ......
陈高华 译
哲学的快乐:干瘪的思考vs.激情的
生活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桂林?THE JOY OF PHILOSOPHY:THINKING THIN VERSUS THE PASSIONATE LIFE
by Robert C. Solomon
Copyright ? 1999 by Robert C. Solomon
THE JOY OF PHILOSOPHY: THINKING THIN VERSUS THE PASSIONATE LIFE, FIRST
EDITION was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English in 1999.
This transla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throug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哲学的快乐:干瘪的思考vs.激情的生活 (美) 所罗门著 ; 陈高华译.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 4
ISBN 978-7-5495-5262-7
Ⅰ. ①哲… Ⅱ. ①所… ②陈… Ⅲ. ①哲学思想-世界-通俗读物
Ⅳ. ①B1-4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83636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桂林市中华路22号 邮政编码:541001
网址:www.bbtpress.com
出版人:何林夏目录
CONTENTS
序言
导言 丰盈和干瘪的哲学
哲学家素描
论作为批判的哲学
哲学的恒久问题
赞美苏格拉底
第一章 激情的生活
爱作为一种德性:驳康德的典范
情爱的德性
权力意志作为德性
论诸德性的优点
第二章 情感的政治
被贬损的情感
何谓情感?(走向一种政治观)
两种情感典范:詹姆斯式的兴奋与亚里士多德的政治
超越笛卡尔的传统
情感的(诸)目的
情感的政治
情感的政治与合理性
第三章 合理性及其兴衰
合理性的不同视角
怀疑(理性)的一些理由
从求和到利己:理性作为一个本质上充满冲突的概念情感的理性与理性的情感基础
第四章 正义、同情、复仇
正义与复仇:缺失的典范
正义vs.复仇:毫无根据的对立
正义的善柔一面:同情与道德情操
正义的肮脏一面:为怨恨一辩
作为正义的复仇:报复的合理性
正义如何令人满意
第五章 生活的悲剧感
悲剧的替代:责备与权利资格
恶的问题
谴责受害者:“自由意志”的解决方案
返回的俄狄浦斯:悲剧之死
命运、简便命运与看不见的手
好运气、坏运气以及毫无运气:为感激一辩
悲剧的意义
第六章 直面死亡的思考
死亡恋癖、病态的唯我论
直面死亡的思考
拒斥死亡:简史
从拒斥死亡到死亡恋癖
大胆的设想:“死亡什么也不是”
干瘪的死神:作为悖谬的死亡
恐惧死亡:害怕什么呢?
超越病态的唯我论:死亡的社会维度
第七章 人格同一性的复兴
困惑的进展
人格同一性与存在的社会自我
人格同一性与德性伦理学人格同一性与文化多元主义
爱中的人格同一性
人格同一性的复兴
第八章 哲学中的欺骗、自我与自欺
为什么是真理?
哲学意义上的真理与谎言
欺骗、自欺与自我
纠缠之网:作为一种整体现象的表里不一
表里不一的自我与自欺的自我
后记 “分析哲学”毁了哲学吗?
索引序言
我想我特别容易对运动的魔力倾心。
——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
(Vladimir Nabokov),《洛丽塔》(Lolita)
我们相遇那年,他四十五岁。念大学时,他是位(田径)运动员,课程对他来说只是兄弟聚会和周六球赛之间的插曲,不过还算不错,他
坚持了下来(但也就如此而已)。大学毕业后,他成了一位成功的生意
人、不错的网球选手、有头有脸的社会成功人士,可谓美国梦的化身。
可如今,他的反手拍开始失误,他会在又一次收购中不由自主地问一些
连自己都说不清楚的问题。他开始觉得,生活虽然充实,可又怎样
呢?“空洞乏味。”他自语道。于是,他发现了哲学的快乐。这并不是什
么智识上的装模作样,也不是规定的必修课程。像一个小孩一样,他对
这个新玩艺儿表现出了无尽的热情。他手里有一些书(绝大多数学人会
把它们当作“通俗”或“二流”读物不屑一顾),一些可在保时捷上播放的
演讲录音带,他还晓得一些随处可见的人名和不少观念。但他真正获得
的是一生所爱,一种生生不息的惊异感和着迷感。
三十年后,就像许多人的情形那样,哲学于我仍是颇多快乐和喜悦
的源泉。不过,“快乐”和“喜悦”在专业哲学中可不是上得了台面的词。
那位曾把哲学颂赞为“快乐的智慧”的尼采(Nietzsche),尽管在诸多圈子里大受欢迎,仍被人们认为“不是一位哲学家”而遭轻视。他的文辞太
过华丽,充满了讽刺和挖苦,且太过私人化了。总之,他的乐子太多
了。(用了太多的感叹号!)他是一个舞者,一个哲学顽童,是一个身
处伟大的苏格拉底传统中的反讽者,是一个好开玩笑的滑稽演员,他把
一切都纳入了他的哲学中——健康要诀、秘方、闲谈、保险杆贴纸、童
谣、失恋慰语、大众心理学、通俗物理学、一点玄妙深奥的东西、社会
评论、神话学史、纷争不已的语言学、家庭内斗、政治诽谤、中伤性的
辱骂、战争宣言、琐碎的抱怨、自大狂、亵渎神明的言语、拙劣的笑
话、小聪明过头的双关语、戏仿和剽窃。职业哲学家抱怨他不够严格,甚至缺乏一个一致的论题。可是,为什么要用纯粹论证的纤纤骨架来糟
蹋这样一场盛宴呢?尼采深知如何从哲学——他的“快乐的科学”(gaya
scienza)中——获得快乐。
我当然没有与尼采竞赛的自负,或效仿尼采深不可测的激情和识
见,或模仿他奇妙绝伦的“风格”,但对于他的那种哲学之乐,我确实深
有同感。与当下的多数哲学不同,它既不热衷于论证,也不热衷于优雅
地驳倒对手。它也不是后现代主义者所谓的“游戏”,不在于以撩起他人
的惊慌和混乱为乐。它实际所意指的,是超越论证的干瘪,进入哲学的
丰盈,是设法增益我们的经验,而不是“证明一个观点(point)”。学过
平面几何的我们都知道,点(point)是没有维度的,因此它没有纹理,没有颜色,当然也就没有深度。相应的,我这本书不是一个论证,更没
有展现一种“理论”。一些读者会越来越恼怒地发现,我常常毫无章法,不给出“观点”、不提供“证明”,而是不断转换视角甚至主题,为的是发
现有待探究的新东西。我主要关注的是,摧毁一些陈旧的壁垒,也就是
学院哲学与其丧失的听众之间、干瘪的逻辑与丰盈的修辞之间、哲学理
性与哲学激情之间、“分析”哲学与“欧陆”哲学之间、哲学与其他一切之
间的那些壁垒。
哲学已经变得太“严肃”,成了一门有其内行和“专家”的“职业”。它
不再属于每个人了(如果它曾经属于过的话),因为它有其技术要求,有专门却仍难以索解的问题和谜团,还有学术等级和学术派系。恰如我
在本书中所揭示的那样,问题在于哲学变得太“干瘪”、纤弱、贫瘠,(用一个完全恰当的病理学术语来说)还厌食。哲学的许多领域都已经
被简化为逻辑和论点批判,被简化为“解构”、贩卖行话以及令人窒息的
元哲学。具体的经验和科学的研究、宗教和灵性,诸如此类,要么被当
作毫不相关加以拒斥,要么被当作纯粹的研究“对象”而假意抬举。至于
那些需要人们实际观察世界并生活于其中的问题,他们傲慢地一笑了
之,不痛不痒地丢下一句“那不是些经验问题吗?”。过去所谓的那
种“思辨”不再盛行,更别说什么“愿景之类”了。哲学往日追求的那种无
所不包、丰盈、充实和通吃的理想,已经让位于贫乏简陋的新哲学,无
论其形式是线性论证还是后现代犬儒主义。
我的一位同事曾在我们(南)加州一所声誉不错的大学做讲座,谈
论哲学的这种狭隘性。他有所思虑地说,近来的哲学已经变得很像俗话
里的盲人摸象。在场的几位著名哲学家中,最著名的那位却骄傲地承
认,他“只对解剖象鼻感兴趣,至于大象会不会死掉,他并不在意”。
在这本书中,我倒想一瞥活生生的大象,或者,我至少不愿仅仅摸
一摸了无生气的象鼻和象牙。如今,许多哲学家主张所谓的“纯”哲学,即剥去了一切只剩骨架的哲学:逻辑和论证以及空荡荡的哲学史(这种
哲学史有时始于19世纪末弗雷格[Frege]的形式主义)。相反,我这
本书所提供的,全然是“不纯粹的哲学”,恰如伟大的智利诗人巴勃罗·
聂鲁达(Pablo Neruda)曾(谈到他的诗)时说的那样:“像旧衣服、像
沾着污渍和羞耻的身体一样不纯粹,里头夹带着褶皱、观察、幻梦、失
眠、预言、直言的爱恨、愚蠢、震惊、牧歌、政治信念、否定、怀疑、肯定和税收。”1
在这本书接下来的篇幅中,我最多只能说自己探究了一些永恒哲学
问题的另一类观点。这本书并不严肃,尤其不是常常会激起人们道德义
愤那种意义上的严肃。我更愿意人们说它“不过是在与(严肃的)观念嬉戏”。那就是哲学的样子(我敢这样说吗)。它不严肃,只是与那些
确有所指的观念戏耍。这并不是说我将在书中埋伏各种笑料,更别说让
人捧腹大笑了。我担心,我对快乐的表达会局限于一些绰号、副词、讽
刺的评论和糟糕的双关语。时下人们认为,只有在那些身材苗条、沐浴
在阳光中、轻盈的二十几岁青年没心没肺的露齿笑容里才能找到快乐,但这种说法并不全然真实。我们也可以在哲学家们一生充盈的沉思冥想
中找到它。
感谢新西兰奥克兰大学哲学系;感谢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哲学系和人
文研究院;感谢我的好朋友,《东西方哲学》杂志的编辑罗杰·阿姆斯
(Roger Ames);感谢本书编辑,牛津大学出版社的辛西娅·里德
(Cynthia Read);感谢我的诤友伯恩德·马格努斯(Bernd Magnus)、亚瑟·丹托(Arthur Danto)、杰伊·胡雷特(Jay Hullett)、保罗·伍德鲁
夫(Paul Woodruff)、亚历山大·内哈马斯(Alexander Nehamas)、理
查德·罗蒂(Richard Rorty)、彼得·克劳斯(Peter Kraus),尤其要感谢
弗里斯乔夫·伯格曼(Frithjof Bergmann),关于哲学的快乐和丰富,他
教给我最多。
当然,最终要感谢的是凯西·希金斯(Kathy Higgins),因为她不断
地为我和哲学带来快乐。
注释
1.Pablo Neruda,“On Impure Poetry,”inSelected Poems(New
York:Grove Press,1961).导言 丰盈和干瘪的哲学
(全然就是存在,一点儿也不少)
摩尔(G.E.Moore)带头反抗,我怀着一种解放感追随其后……我
们相信草是绿的,太阳与星星依然存在,哪怕没人知晓它们。那个一度
干瘪的逻辑世界如今变得丰富多彩。
——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
哲学史中有诸多反讽之事。无疑,伯特兰·罗素在评述“分析”哲学
起源时的那种自鸣得意,是其中一桩。罗素追随弗雷格和摩尔“反抗”实
际上把人类经验的方方面面都融入了自己哲学的黑格尔(Hegel)。可
是,由于对德国唯心主义的误解,罗素(错误地)秉持这样一种信念,即德国唯心主义认为世界是由观念而不是由坚实可靠的物质组成的,正
因为此,他才认为在他的哲学中,“那个一度干瘪的逻辑世界……变得
丰富多彩”。1然而,由此肇始的一百年来的“分析”运动,却最终使哲学
变得干瘪和逻辑化了。2
我们可以同意罗素的说法,即哲学的快乐在于其丰富多彩。然而可
悲的是,作为一门“学科”的哲学竟窄化成一套概念技巧,认同“干瘪”而
反对丰富多彩,完全偏重论证和逻辑分析,进而摒弃了黑格尔的“思
辨”想象以及他那无所不包的经验概念(用后现代主义者同样干瘪的行
话来说,就是“总体化”3)。如今,哲学要求“专业化”、技术、有限的关注和严格性,而不是视野、好奇心和开放性。黑格尔的理想是无所不包
的“理解”。但今天,哲学领域一些最卓著的文章却都是一连串符号和难
以理解的行话,只有不多的几个同行会感兴趣。恰如政治哲学家约翰·
罗尔斯(John Rawls)在他的那本划时代巨著《正义论》(A Theory of
Justice)开头宣称的那样,哲学的主要目标就是不断把对话提升到“更高
的抽象层次”。4但是,哲学(如黑格尔所主张的那样)并不一定要抽
象,也还有穿行于细节中的具体哲学,显现在有血有肉的观念辩证法之
中,远比纯粹的筋骨丰富。用威尔弗里德·塞拉斯(Wilfrid Sellars)的
话说,它的成功在于“看清事物是如何联系在一起的”。而它的兴盛则在
于将无论是否显著的平常之物变得神秘玄妙:时间、生命、心灵、自
我,以及我们与世界是如何“联系在一起的”。
哲学是或者应该是一种魔法。它并不是对我们生活的一种逃避,相
反,它是通向我们生活的一扇新窗户——或者诸多新窗户。因此,与其
说它是抽象,不如说是洞见和视野。从最早的吠陀派到存在主义者,伟
大的哲学家们都提供了令人眼花且扰人心智的洞见和视野,以及种种令
我们头晕和让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暂时不知所措的观念。然而,这种魔法
般的快乐感已然丧失或已遭抛弃,我虽不情愿这样说,可情形确实如
此。今天的哲学家太扫兴,急于反驳,固执地不愿去理解(或倾听)陈
述不完善的替代方案,一心想着贬低洞见和热情。我念研究生时,一位
与我同龄且很有天分和创造力的女生提交了一篇极具创造性的哲学论
文。可她的老师却蛮横地视之为垃圾,并以《旧约》中才有的愤怒对她
吼道:“哲学不是搞笑!”(她如今是位一流学者,不过是在另一领
域。)今天,最有才情的研究生仍会因同样的斥责而被逐出哲学领域。
哲学不是搞笑!
在国内旅行时,我常常遇见各种各样的人——成功的商人、艺术家
以及其他一些人,当然也有学者——他们往往直截了当地用些熟悉的话
与我说笑。开头是“我曾经上过一门哲学课,但是……”我知道接下来会
说些什么。开头的几个音节就令我厌烦。有时会是某种无辜的恼人话语,如“可我什么也记不起来了”。更常出现的则是“但我讨厌它”,接着
则是对老师毫无奉承的典型描述:一个既冷淡又自负、显然有点小聪明
且有意炫耀的人。通常我会问,这个烂人是谁?结果这位仁兄常常是同
行里颇为知名的人物。他(几乎总是他)有着不俗的出版记录,他毕生
的工作就是(在成百上千个学生中)激发一两个学生从事哲学,以此继
续祸害下一代。那种认为哲学的命运单悬于我们激发哲学之乐的集体能
力这条线上的想法,常常会遭来轻视。单单这种说法就会被人们激烈地
指责为把哲学当成“娱乐”,进而重申专业能力和“学科的完整性”。
什么是哲学的快乐?我过去也常说,它就是那种因看清楚所有观念
如何关联而来的兴奋。可如今我会说,它是看见其他人以各自的方式看
清楚所有观念如何关联而眼睛发亮时,我感到的那种兴奋。
“哲学的快乐”。任何一个曾花时间进行哲学探究的人都不会对这个
表述感到奇怪。我的哲学家朋友是我所知的最投入——且不说着迷或上
瘾——的人。一些人在与“大问题”的搏斗中感到快乐(或许还伴随着一
些苦恼)。另一些人在厘清难以忍受的晦涩文本中感到快乐。如今,更
多的人则是在用逻辑和独特的哲学语言处理愈益精细、令人困惑的“难
题”中感到快乐。我认识许多画家、音乐家、政治家、学者、商人和捞
钱能手——他们都是些很投入的人,但都没有我的哲学家朋友们那么投
入。而且这种情形并不只是出现在这一行里的佼佼者身上。事实上,他
们更小心谨慎,也更少热情,远不如我在小型学院甚至高中遇见的数百
位优秀又充满热情的老师。对于后者而言,哲学的快乐就是哲学的快
乐,而不只是学有所成的专家的快乐。
我们周围最活泼和充满生机的人(当然不是那些以此谋生的人)懂
得哲学的快乐。甚至那些生活空虚、悲惨的人,有时也在哲学中找到一
种涌动着活力的生活(而且不只是“慰藉”)。雄心勃勃的哲学大部头
——绝大多数未出版也无人阅读——有在监狱和低廉的租屋中写就的,也有在失意职员和落魄律师形单影只的房间里和杂乱的办公桌上写成的。那样的地方也不乏思辨和热情。诸如“心灵生活”和“观念世界”这些
平淡的表达是无法抓住哲学的活力、兴奋和快乐的。它不是烹饪的快
乐,当然也不是性爱的快乐,但它无疑仍是快乐。哲学家素描
[哲学中]凡是能够说的事情,都能够说清楚,而凡是不能说的事
情,就该保持沉默。
——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逻辑哲学论》(Tractatus Logico-Philosophicus)
这是20世纪晚期的一位哲学家的素描。他(例子依旧几乎总是他)
站在一小群听众前。他正苦恼着。他的双眼尽管有神,却无所关注;或
许它们是在反视自身。他的眉上有一道深纹,表明他皱着眉——不,是
沉着脸——一只手不停地在前额揉动,仿佛不如此他的头或脑袋就会爆
炸。对于那些喜欢用典的人来说,他像极了罗丹(Rodin)著名的《思
想者》(The Thinker),或者《拉奥孔》(Laocoon)中那位面容扭
曲、极度不幸的父亲和祭司——古代世界中对苦楚最为揪心和悲惨的刻
画。他说起话来断断续续,几近于口吃,表明了观念间的堵塞以及他试
图寻找恰当字眼的紧张程度。他在那条踩烂了的道上,焦躁不安、不由
自主、毫无规则地踱着步,从一个角落走到另一个角落,眼睛从未落在
那些全神贯注但困惑不已的听众身上。他的一只手时而掩嘴、时而揉
眼、时而抓鼻、时而敲敲后颈,又或者在腋下挠挠,焦躁地说几句又停
顿下来,而另一只手不断地拿起一根粉笔又放下,偶尔像是要写点什
么,但除了一个“x”或长方形之外,什么也没有写出来。折磨人的(意
味深长的)停顿也不少。这种情形估计得让伟大的神经精神病学家奥利
弗·萨克斯(Oliver Sachs)医生来诊断一番。这简直就是神经衰弱、自
恋、思想背叛自身和语言急需放假的一个活生生的剧场。这就是哲学,这就是哲学家。苦楚,因哲学而遭受的苦楚。哲学是一种疾病,唯一的解药是……更多的哲学。
我刚才所勾勒的这幅肖像属于一位极易辨认的历史人物,即路德维
希·维特根斯坦,虽然他的哲学日渐黯淡,但他的人生却成了20世纪哲
学生活的不朽标志之一。尽管维特根斯坦的学生中很少有他那样的天
才,或认同他那种维也纳式的病态生活观,但其中有很多人模仿他的手
势、风格、一脸不安,仿佛他的骚动不安他们也能感同身受。结果就
是,随后两个世代的哲学师生搞起哲学来,就像是在公开表演自我驱
魔。他们在大学导论课上表演,而那些本就想要加入这种表演(而不是
嘲笑这种表演)的学生也受到鼓励参与进来。这种课程的绝大部分仍是
令人生厌地一成不变,但是这种风格、表演、严肃性已经使哲学——像
维特根斯坦自己抱怨的那样——变成了一种精神病理学。
在电影《雨人》(Rain Man)中,演技出众的达斯汀·霍夫曼
(Dustin Hoffman)所扮演的自闭症患者雷蒙德(Raymond)回应压力
的方式,就是试着一遍又一遍地解答阿伯特(Abbott)和科斯特洛
(Costello)的经典喜剧包袱:“谁在一垒?”他的哥哥(汤姆·克鲁斯
[Tom Cruise]饰演)被惹恼了,向他吼道:“这是一个谜,是一个玩
笑。如果你明白这一点,或许会好些。”从精神病学上来说,这句话或
许很幼稚,但它也同样深刻。任何一个见识过今日许多极具才华、声名
卓著的哲学家苦思冥想情形的人,都不会对这句话所呈现的那种病理感
到陌生。众所周知,哲学难题极其费解,甚至不可索解,这一事实被认
为是其深刻性的明证。5但是,不可索解或许也是理智自虐的一个标
志,或者说得更天真无害一些,是理智自慰的一个标志。哲学难题既不
可索解,也无足轻重,这种意识让人们有很好的理由认为,对这些难题
的探究最终“只是为了探究本身”。也就是说,是为了好玩,为了随之而
来的纯粹快乐,尽管我们在探究途中也会有挣扎和牢骚。维特根斯坦自
己曾这样写道,一本哲学书完全可能满篇玩笑。当然,他自己从没写过
这样一本哲学书。哲学里头——我们别再装模作样,就直说吧——没什么真正事关生
死的东西。医生、工程师、联邦储备局成员或爆破小组的专家要是出了
错,确实会有后果。一个哲学家出了错,没人会死,没有什么会相撞、爆炸或崩塌,贫困或失业不会增加,股市也不会暴跌。当然,一些优秀
哲学家遭到曲解,从而引发灾难,这种情形在历史上古今皆有。但这些
是例外,而非通则,即便如此,也很难说是困守书斋的哲学家们自己把
世界置于危险之中。实际上,无须负责的哲学会带给人一种解放感。甚
至像马克思和卢梭这种乖戾之人,不管他们的个性有多阴郁,曾在这个
世界上表达或激起了多少狂暴情绪,他们自己显然也有许多快乐。
我猜,绝大多数哲学家是作为叛逆者,为了寻求一种深刻的自由而
进入哲学领域的。但讽刺的是,我们现在却打着“专业化”和“学科完
整”的旗号,成了自我强加的权威主义的囚徒。自由的思想和野性的观
念已变得不合时宜;成为一个哲学家必须遵守“纪律”(discipline)。在
大学招生手册之外,没有什么地方还把哲学描述为“人生的思考”或“自
我省察”,更别提什么观念的快乐了。恰如某位一流的哲学从业者曾权
威十足地说过那样,“哲学有逻辑学和科学哲学就够了”。随着对“什么
是哲学”盖棺定论,自由、想象、通俗易懂,尤其是敏感,也就被抛掷
一边了。论作为批判的哲学
严肃是浅薄者的唯一避难所。
——奥斯卡·王尔德(Oscar Wilde)
哲学像绝大多数学术和知识学科一样,在很大程度上成了批判之
学。这种情形的益处很明显:敏锐的批判显然对民主制度而言至为根
本,也是健全科学的本质所在。它创造了一种辩证法,真理(或至少是
更好的理解)可借此从不成熟或片面的观念中浮现出来。它让理论化变
得有趣,甚至更具责任感。理论上讲,它至少有助于消除欺诈和愚蠢。
还应该补充说,它还增加竞争力,对于许多受心灵生活吸引的好斗分子
而言,批判本身就成了诸多乐趣之源。不过,批判也会过度。特别是,如今在许多哲学行家看来,哲学不过是对论证的审查,以及制造对立的
论证。观念和识见呢?它们现在不过是攻击的目标。
初涉哲学的大一新生,仿佛置身于娱乐性的射击场,学的是如何击
落伟大哲学家们的论证。(“柏拉图认为什么什么:这个说法的问题在
哪儿?”“康德主张什么什么:请给出一个反例。”“约翰·斯图亚特·穆勒
[John Stuart Mill]得出结论说什么什么:那难道不是一个‘愚蠢的错
误’吗?”)较为资深的哲学家们则在论文中娴熟地展现自己的技能,开
头总是“某人主张什么什么,但我将表明他她失败了”。在一个“不发表
就灭亡”的时代,哲学成了吹毛求疵的技能。论证越来越“严谨”,视
野、知识和趣味越来越狭小。为了免于在论证中夹带难免有诸多弱点的
原创性,哲学家们常常列举的是一些最没创意的例子(比如,常常是弗
雷格在1900年举过的例子,或者再早一个世纪的康德所采用的例子,甚
至是两千多年前亚里士多德用过的例子)。关注的范围越来越狭隘,越来越形式化——可供咀嚼的鲜肉越来越少,更无扰人心智的个人情感。
哲学的快乐在很大程度上只剩下摧毁,即“撕裂”和毁灭的乐趣,不消
说,这里头包括“解构”论证的乐趣。黑格尔那种建构性(“思辨性”)视
野的乐趣,用连前人自己都没用过的方式去解读前人观念的乐趣,通过
哲学产生新观念甚至是不同寻常的经历的乐趣,已经看不到了。6论证
和反驳:除此之外哲学家还需要知道别的吗?
我现在教书,竭力遵循过去所谓的宽容原则。粗略来讲,就是一个
观点即便听来像胡说八道,我们也应该试着去搞清楚表述者心中可能的
想法,或者其令人厌烦的表面下可能藏着的好想法。(当然,这是随堂
回答学生提问时的一项基本教学技能。)我常常听到同事们因某个笔
误、事实错误、解释不当或(最为糟糕的)逻辑谬误,就把一篇文章、整本书甚至一个人的学术生涯一棒子打死。至于其中还有什么价值,他
们错过了。当然,我在现实中也只是偶尔能贯彻自己的原则。只要来一
点荒唐的政治主张、一点新时代运动(New Age)或后现代主义的自以
为是、一个挑衅我所维护过的珍贵观念的反面论点,我就几乎会不可避
免地恢复到我的职业枪手模式,那些费城、安娜堡、普林斯顿和道奇市
的神枪手老师把我调教得可好了。不过,至少我知道自己这种做法有
错。在哲学中击败对手或许有点意思,但哲学的快乐却藏身别处:它存
在于思想的相互碰撞中,植根于对新观点的上下求索中,生发于让每日
都变得饶有趣味甚至引人入胜的愿景构建中。当然,批判有其位置,但
是,批判只是(或者应该只是)我们形塑观念、扩展视野的一种工具。
它不是(或者不应该是)目的本身。7
在这本书中(其实此书本身就过于吹毛求疵),我想要回到一种较
为古老、更为“浪漫的”哲思模式。它不会没有论证——实际上,人们可
以把整本书看作对哲学之“干瘪”的反驳——不过这本书的结构更多是与
观念本身的复杂性有关,而非标准化的分析方式。坦白说,我常常并不
知道我的这些探究会把我带向何处。这就是激情与证明之间的差异。确
实,我厌恶逻辑的“干瘪”,盛赞哲学的激情以及由之而来的丰盈。然而,至少自柏拉图以来,哲学家们就对激情心存警惕,更不用说自逻辑
实证主义者(他们有自己的理由)以来,哲学还对浪漫主义提防有加。
确实,与单把糟糕的论证批得体无完肤相比,思辨和激情以及深究人类
经验的努力之中,则蕴含了危险重重。
鉴于在上世纪时对于经验主义“唯此独尊”(nothing but)的强烈偏
爱,这同一批人竟然坚决抵制谈论经验,尤其是生活的感受和具体细
节,就显得不可思议了。8取而代之的是,焦点集中到了“逻辑形式”之
上。或许,这种对逻辑形式的强调可以归因于人们误读了柏拉图——一
位最具想象力的哲学家——及他对形式(Forms)的迷恋。这种强调肯
定可追溯到康德颂赞的先天(a priori)概念(但这么做并不意味着对经
验的贬低)。至于黑格尔,他尽管坚持无所不包,但仍极其危险地摆弄
着“概念”,即19世纪版的“更高的抽象层次”,因此,人们有时阅读(和
抨击)他,并不是因他的丰盈,而是因其无所不包的干瘪。9
在今日的英美哲学中,对干瘪的极力主张可以说是弗雷格——罗素
——(早期)维特根斯坦固执于逻辑分析和形式分析的一个延续——甚
至复兴。这一主张也持续存在于后现代主义关于元哲学毫无分量的夸大
其词之中,它尽管(常常在形式上)坚持多元主义和碎片化,却仍对寻
常的人类经验视而不见,甚或加以轻蔑。10然而,强调批判和解构的最
终结果有两个,一方面是对于“有趣观念”近似犬儒的彻底怀疑主义,另
一方面是一种补偿心理,即着迷于纯粹形式、推论和论证,以及寻找他
人立场的错误,但自己避免采取任何立场。11这种犬儒主义对热情——
实际上是一切激情或情绪——自然深表怀疑。因此,无论其起源多么厚
重,哲学如今已变得轻若鸿毛,毫无实质和内容可言。
当然,即使最丰盈的哲学也仍是十分干瘪的,完全是一种粉饰,不
过是事物的表层(而非“深度”)。马克·吐温(Mark Twain)——美国最
伟大的哲学家之一——坚持认为,“真理就在表面”。哲学中的“深刻”更
可能是一种概览,是一种观看之道而非“挖掘”之术。哲学不是论证,而是分辨、沉思和视野。如果哲学是丰盈和充实的,那是因为生活本身是
丰盈和充实的。哲学关涉的是生活。甚至可以说,哲学于生活(至少是
省察的生活)至为紧要,但哲学毕竟不是生活,只是借生活为己用而
已。当然,哲学也不是生活展现其血肉的骨架,就好像哲学是基础,其
余一切皆血肉。哲学不可以完全是一种单向度的推理,但是,即使在其
最为充实处,哲学仍无可争辩地是干瘪的,哪怕它不是逻辑的。因为无
论有没有哲学,草地依旧焕发着浓浓绿意。
或许是因为哲学的干瘪让人预感不祥,如今出现了大量谈论哲学终
结(end of philosophy)的文章和书籍,“终结”既可以解释为线性的目标
或目的,又可以解释为终点,它们在其二义性上大做文章,让人不胜其
烦。一些作者直言不讳,宣称哲学已经“死亡”或“耗尽”。另一些作者则
含糊其辞。柯乃尔·韦斯特(Cornel West)和约翰·拉赫曼(John
Rajchman)宣称“后分析哲学”的来临,试图以此来震动学术界,但迄今
还没察觉到有任何改变。12走向“后分析”哲学(或如今被谬称为“实用主
义”)的运动,不过是一些战略性微调,操作者们仍是同一批熟悉的玩
家。技术统治论依然纹丝不动,骄傲地展示着爱丽丝·默多克(Iris
Murdoch)在数十年前就警告过的“干枯”,只不过那时这一领域还很丰
润。但是,问题越是“干瘪”,定义越是清晰,似乎也就越是难以索解。
比如,“真理”已经被简化为一个毫无意义的术语,许多哲学家确信他们
不久就会彻底根除它了,至少在哲学中可以做到这一点。13同样的,“自
我”这一观念已经干瘪得不可辨认,当然也就无足轻重了。14生活的核心
概念被简化为逻辑悖论和难题,哲学家们因此而遭到谴责(其实是自我
谴责):哲学被搞坏了。他们宣称,这些年来我们一直在对付的都
是“伪问题”,但是他们的声望、薪水以及对这一行当的把持却有增无
减。哲学的恒久问题
生活迟早会把我们全都变成哲学家。
——莫里斯·赖瑟琳(Maurice Riseling)
犬儒(“反讽”)的观点认为,哲学无非就是拿着薪水的哲学家们当
下在做的一切。对此我不敢苟同,我认为哲学的动力和动机源自非常真
实、具体可见且带有普遍性的人类问题。这不是要否认,如尼采所指出
的那样,某种奇特的“求真意志”的存在,也不是要否认对难题和悖论的
着迷,这种着迷一旦被激发就可能久久不散,且不为外物所动。但哲学
不是这个样子的。它是与生活的恒久问题的搏斗。我们都是哲学家,我
们必须使哲学民主化,尽管哲学有其久远的精英起源。哲学不是一门专
业,不是一个职业,也不是有其规则和口令的排外俱乐部。哲学不过是
对诸如激情、正义、悲剧、死亡、自我同一性以及哲学本身等问题的思
考,因此,哲学绝不是一小群受过大学训练的专业人士的领地或特权。
在最重要也最为政治不正确的意义上,哲学是我们人的存在方式之
中固有的。我们思考。我们感受。有一些问题——或许可以认为它们
是“哲学的先行条件”(又称之为“人的境况”)——我们毫无选择,只能
去思考和感受。无论这些问题的概念和细节在不同文化之间有何差异,它们都不出所料地包括了美好生活的本性、我们最强有力的激情的位置
和根据、我们在他人中间的位置、正义问题、悲剧的种种解释、死亡显
而易见的终结性、人自己的同一性以及思考、反思、意识和哲学的指向
和目的。
这就是(一些)恒久的哲学问题。有哲学家(理查德·罗蒂就是最为著名的例子15)认为,没有什么恒久的哲学问题。在我看来,这种说
法显然是错误的(而罗蒂本人在其他地方也很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
当然,对于这些问题,你可以给出一个“丰盈的”描述,由此表明它们无
非是一时一地一些人的问题,甚至是1973年美国哲学协会成员的特定问
题。但是,生命本身的问题,与任何特定的哲学传统都无关,比如,我
们对自身的脆弱和终将一死的意识。无论是否存在某种思考死亡的正
确“逻辑”,死亡都是让我们心存敬畏的一个普遍“事实”(海德格尔断
言,是“我们最为必然的可能性”)。当然,将生命及其(各种)意义
——相应地还有死亡的意义和本性——概念化的方式很多很多。不过我
认为,对死亡的意识,可以说是一个“哲学的先行条件”,它当然不是哲
学家的发明,但仍为哲学所塑造(也塑造着哲学)。16
要说哲学中存在着恒久问题,在某种程度上恰恰是在指出,或许还
在抱怨:哪怕对这些问题“最为干瘪的”描述,也是狭隘和有失偏颇的,因此也就没那么“恒久”了。(恰如尼采所言,并不存在事实和原始文
本,存在的仅仅是种种解释。)比如,有一个不错的观点认为,我们现
在所谓的心——身问题,事实上与特定时期的学问和追求有关:神经心
理学和计算机科学这些令人兴奋的学科融通交汇,和基督教的身体与灵
魂分离说、笛卡尔(笛卡尔主义)的“二元实体”哲学、语言哲学与心灵
哲学专业交叉形成的新见,以及英语本身某些特质的影响。相反,在日
本、古希腊,在尼日利亚的约鲁巴人那里,就没有这样的区分,因此也
就没有这样的问题。
不过,这意味着什么呢?这并不是要否认还存在其他引起同样不安
的问题和“分离”。(也不是说其他文化不接受神经科学的发现,那就太
荒谬了。)比如,在日本,一个人展现给外部世界看的“脸色”与他不愿
示人的私人感受之间的矛盾冲突,就受到了持续关注。约鲁巴人与绝大
多数人一样,关心灵魂的本性,他们在许多意义上把它与身体区分开
来。但是,严格意义上的心——身问题并不存在,因为(在日语和约鲁
巴语中)并不存在一个与“mind”(心灵)对等的词。(kokoro是日语中最接近mind的词,但它显然包含了笛卡尔式二分法中的“身体”才拥有的
各种特征。亚里士多德从来没有一个与机体区分的anima观念,而约鲁
巴人的ori所指的东西更像是“头”,而不是“内心”,与之相对照的则是身
体的其余部分。)可以认为,我们所谓的“心灵”是对一个人主观经验的
某些方面“最干瘪的”描述;而与之相对照的“身体”,同样也是用纯生理
术语所给出的极为干瘪的描述。
认为心——身问题不过是某个地方哲学传统在某一特定时期的一种
文化特性,纯属无稽之谈。如何为这一问题提供一个足够“干瘪的”描述
以囊括所有文化及其对立面,亦不是我这里的关注所在;况且,如此干
瘪地呈现这一问题可能会显得纤弱不堪,对我们而言也就无足轻重了。
我这里要探究的——与罗蒂时不时认可的后现代路子完全相对立——是
种种关注的核心是什么,它们不该仅仅被我们当作反讽或与无关紧要的
问题,而是值得作为典型的人的问题被重视,不管它们是否会被哲学家
认同,或是否能摆脱任何特定文化和哲学的观点。确实,某些观点只适
用于某些文化,而不适用于其他文化。但是,坚持认为某些关注本质上
是人特有的,并没有犯后现代主义者所谓的“本质化”和“总体化”之罪。
也不是要否认,如果人类变成完全不同种类的生物(比如,变得坚不可
摧或长生不老),那些恒久的问题也会大有不同。谈论“恒久的问题”,只是说某种形式下的某些问题,对我们而言是无法逃避的(这里的我们
是指,我们有限且必然褊狭的想象力能想到的所有人)。
加布里埃尔·马塞尔(Gabriel Marcel)把难题与奥秘区别开来后,抱怨(20世纪中叶的)哲学家们把心思都分给了难题,却对奥秘视而不
见。要是我来表述,方式会稍有不同,不过,在我看来,他的这种区分
却是难以避免的。他的写作很超前。就他力图阐明的意义——攸关每个
有思考能力之人的那些问题所处的混乱状态——上来看,哲学在美国最
好的大学中也已经差不多销声匿迹了。哲学不是提出更多艰深晦涩的新
问题,而是该将注意力集中在那些每个人——尤其是眼睛明澈、荷尔蒙
旺盛的大学生和四十五岁的职场男女——都遇到过的事情上。可是,“最好的”哲学系都成了学术技艺高超却对学生们无业可授的部门,也难怪那么多优秀的学生会离开哲学专业而转投宗教研究或文学系。但
在校园之外,这些学生却用本该在哲学课上才应有的热情追捧着新时代
运动的哲学。对此,我们与其感到愤怒或轻蔑,不如试着去探究下这些
追捧的动力从何而来,怎样才能使其满足,那样的话,我们的境况可能
会好很多。
哲学是一种真实的需求,它所针对的是真问题,不是伪问题。在人
的一生中,哲学会多次露面,最明显的是童年时期,这时它还未被置若
罔闻的父母和老师们扼杀掉;其次是青春期晚期,这时个人身份的认同
及个人在世界上的位置是什么之类的问题不停袭来;还有是在生活中遭
遇各种危机时——比如离婚、重病、至爱去世、个人失败、政治动荡。
在绝大多数人看来,回应这些切身的问题,正是(公众认可的)哲学家
存在的唯一理由,如果专业哲学家不愿这样做,那么,哲学慰藉的替代
品就一定会冒出来。书店架子上无所不在的自助图书就是一例明证。对
于不少智力尚可的人说,现在的怀疑主义专业户们到处挑刺,给论证找
瑕疵,给见解找漏洞,给好心情泼冷水,还觉得每个修辞手法背后都有
无法根除的自相矛盾,与其忍受这种单调乏味,还不如去看雪莉·麦克
雷恩(Shirley MacLaine)的性欲幻想。至少,麦克雷恩小姐似乎在她的
所作所为中乐此不疲。赞美苏格拉底
笑声是灵魂的语言。
——巴勃罗·聂鲁达
人们常常打趣说,苏格拉底从未发表过什么,所以他就灭亡了。然
而,他却成了我们的英雄,哲学家们的灵感和典范。没错,他之前也有
哲学家(人们稍带不屑地称之为前苏格拉底哲学家),可是若没有他,我们就难以想象哲学的生长或发展。柏拉图会写些什么呢?亚里士多德
从哪个智识平台出发呢?我们会如何来理解奥古斯丁(Augustine)或阿
奎那(Aquinas)呢?尼采的狂言(以及他的嫉妒[envy])也会短路
的(不过小城镇的新教仍给他留有机会)。苏格拉底的人格——以及他
的机智和才华——让我们所有人着迷。正是他的以身作则(以及柏拉图
对他的描绘)使哲学与诗歌、修辞和公共政治截然区分开来(且与它们
相对抗),独树一帜,自成一家,成了自我省察的学问。17
然而事实是,苏格拉底是一个自我包装过的江湖骗子。他有意坚称
自己无知愚昧,然后又据此宣扬自己是当时最有智慧的人。只要能够胜
出,什么糟糕的论证他都会用。他花言巧语,取笑嘲弄,混淆视听,连
蒙带骗。他的嘲笑都是人身攻击(ad hominem),这是他通常会犯的非
形式谬误之一。他是一个享乐者,却显然对爱和快乐甚至生命本身漠不
关心,或者说可以做到漠不关心。他为哲学而死,或者说,他想让我们
这么以为。但他是为自己而死的,是为“他灵魂的善”而死的,甚至他为
之献身的政治原则,现在看来也是可疑的、前后矛盾的,或许也是难以
忍受的。18从我们了解的关于苏格拉底的各种叙述来看,他并没有孑然一身,也极少苦思冥想,更没有一本正经过。哲学家孤独、忧郁、若有所思的
思想者形象,在他那儿基本对不上号。苏格拉底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社交
人物、一个宴饮狂、一个喋喋不休的话痨,还是一只围绕着问题(当
然,还有男孩)嗡嗡的牛虻。对于他,无论我们怎么说——他是智慧
的,他是勇敢的,他长得丑,他终究是一个会死的凡人(就像必然的三
段论里所说的那样)——他过得的确痛快。他的对话充满了俏皮话、颇
有意趣的轻侮和哲学式的闹剧。即便是在今天,人们仍能通过阅读感受
到他眼神的闪烁和言辞的动人,他追问他那些话题和心甘情愿的受害者
时的快乐,以及他表明观点、搞定论证、结束一段讨论以开启另一段讨
论时那种并非全是自夸的欢喜。或许,恰如两千年后的尼采——带着夹
杂着嫉妒的敬畏——说的那样,他根本就是一个小丑。可他是个多了不
起的小丑啊!他不但迷倒了雅典的年轻人,在死后几年内,还把古代世
界迷倒了。两千年后,他又迷倒了文艺复兴时期的新哲学家们和新生的
现代异教世界。他把哲学当作对话和有益的趣谈,可以嘲弄,也可以劝
诱。他认为哲学是快乐的智慧,是乐趣。
后来的哲学家或许会坐在中产阶级的火炉边持笔独饮,但苏格拉底
却是在庆祝宴会上举杯豪饮,后来他饮毒酒而死,也算得上死得其所
了。我们都知道,他被控“败坏雅典的青年”和不信城邦的神,前一项指
控过于模糊,难以证明,后一项指控他虽然加以否认,却是不争的事
实。他在指控他的陪审团面前夸耀自己的所为,并且认为自己不应受
罚,反该得赏。他被不公正地判处了死刑,但这是他自己激怒陪审团所
致,而且陪审团还为此再三犹豫。(毫无疑问,一些陪审员已然料到历
史将会如何评价这一判决。)他的朋友克力同(Crito)自告奋勇要帮他
逃狱出城,却被拒绝了。为什么呢?因为一些臭名昭著的糟糕论证。不
过,他或许也意识到了历史将给予自己的位置。那是每一个殉道者的幻
想,只是很少人(还有个例外)会如此成功。对照一下亚里士多德,他
曾用福斯塔夫式(Falstaff)19的口气宣称:“雅典不能再得到第二次对
哲学犯罪的机会。”20在智勇双全里,智慧还是更重要一些。无论过去还是如今,苏格拉底都是一个悖论,后来哲学中所有的困
惑和冲力都源自这个非凡人物,如同话语源自他那从不停歇的嘴。他坚
持理性,但使他胜出的是雄辩术。靠着纯粹的个人魅力,他给自己确立
起一个充满激情而不耽于沉思的形象。他总是即问即答,但没有什么仔
细推敲过的理论。实际上,人们不清楚他是否有一套理论,更不清楚他
是否对自己的问题有一个答案。甚至他那伟大的《理想国》——这部作
品让西方在随后的两千年里一直为“什么是正义”争论不休——也没有明
确的结论,至少暗示了可能根本没有结论。
苏格拉底认为定义是充分必要条件,能够涵盖但不排除每一个适当
的实例,不过他自己更善于提出巧妙的反例和机敏的反驳。他在驳斥完
所有提出来的定义后,不会提出另一个注定白费的定义,而是讲述一个
神话或寓言,虚构一个城邦或把灵魂描述成一群野马和马夫的合体,回
忆一次假想出来的与缪斯的会面或沉浸于灵魂不朽的冥思中。事实上,他是一个神话制造者,是神话和反神话的雕刻家——形式世界、真实存
在的世界、逃离洞穴、完全正直的理想、灵魂不朽。他认为应该把诗人
赶出理想国,因为他们是坑蒙拐骗之徒,然而他自己就是其中最伟大的
诗人,最大的坑蒙拐骗之徒。
因此苏格拉底有两个,一个是两千五百年前有血有肉的激情人士,另一个则与毫无生气的逻辑建构联系在一起,专注于一些可疑的论证和
狂妄的来世理论。我们牢牢记住了苏格拉底对难题和悖论的迷恋,却忽
略了激励过他的那些深切的个人忧虑和不可抑制的幽默感。更糟糕的
是,哲学如今又呈现出一种排斥他人的自命不凡感,完全不屑于绝大多
数学生和哲学爱好者的深切关注。苏格拉底是对的:哲学可以是且应该
是一种快乐,而不是一种负担。这倒不是说哲学挺容易,也不是说怎样
都行。但是,苏格拉底面对死亡,要比绝大多数哲学家彼此会面以及在
研讨室里面对学生时从容得多。今日那些深刻的思想家极其痛苦的形
象,可不是苏格拉底的样子。轻松快乐的笑声或咯咯一笑,那才是智慧
最恰切的表达。注释
1.见My Mental Development一文,载于P.Schilpp所编的The
Philosophy of Bertrand Russell(La Salle,IL:Open Court,1975)。事
实上,罗素所回应的是英国的一些“黑格尔主义者”,这些人与他们的德
国前辈们有很大不同。
2.许多哲学家坚持认为,他们研究哲学的方式——还原论的、干瘪
的和逻辑的——是唯一真正的哲学。实际上,我们有一些人已经讨论过
组建“真正的哲学”这样一个子系科的合理性(我一位优秀的逻辑学家同
事曾自嘲地称逻辑学乃“猛男哲学”),而留给我们其他人的,则是谈论
驳杂生活的滥情角色。
3.我针对“干瘪”的运动决不限于“分析”哲学。比如吉尔·德勒兹
(Gilles Deleuze)后结构主义的形式主义,虽然充满着虚无主义的叫
嚣,却仍像分析哲学的任何产物一样乏力又无趣。
4.见罗尔斯的A Theory of Justice(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1),第8页。这绝不是要搁置或贬低难题(比如,芝诺[Zeno]的飞矢不动,回到过去后自杀,想想成为一只蝙蝠会是什么
样或中文屋里头的那个家伙是否懂中文,争论功能不良的电传机上剩余
部分的人的身份,指挥失控的电车,或者戳戳缸中之脑)。搞懂这些荒
唐的脑筋急转弯是训练脑力的极佳方式,而巧妙解答的过程又是一种美
学享受,可以与精彩的数学证明相媲美。不过,不能把这个和哲学混淆
(更不能以为这是哲学的专一领域)。
5.实际上,甚至寻常的经验长期以来也是哲学嘲弄和怀疑的对
象:“可这难道不是一个经验问题吗?”紧接着(或至少隐含着)的一句
话往往是:“那可不是哲学!”于是,哲学的主题变得日益狭小,以至于
丧失了太多内容,实际上已经毫无分量可言。6.罗伯特·诺齐克(诺齐克)在他最近的三本书——Philosophical
Explanations(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1),The Examined Life(New York:Simon andSchuster,1989)和The
Nature of Rationality(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3)——中实际上表述的全是这种类似的感受。但是,他在优雅地表
明自己从好斗的“击败”型哲学模式转变为更适宜的新路径之后,仍情不
自禁地展示他那炉火纯青的战斗技能。对此我也深有体会。
7.逻辑实证主义者自称经验主义者,但这仅仅是因为他们重视科
学。对他们而言,“经验”本身是一个抽象概念,是他们关于证据和证实
概念的干瘪的、纯粹逻辑的讨论的一个部分。“唯此独尊”(nothing
but)一词出自詹姆斯(William James),他把经验主义的“唯此独尊”态
度与理性主义的“还有更多”态度相对照。然而,詹姆斯本人尽管可能曾
是一位“彻底的经验主义者”,但他绝不是一个推崇“唯此独尊”的哲学
家。
8.当然,我首先想到的是罗素对唯心主义的抨击,但是,同样的抨
击也出自后现代主义阵营,尤其是吉尔·德勒兹。事实上,他那本被过
度追捧的谈论尼采的书,其中有大部分是对黑格尔和黑格尔主义极其不
当的抨击。见H.Tomlinson翻译的Nietzsche and Philosophy(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3)。
9.当然,存在着“普通的”后现代主义者和“绝对的”后现代主义者之
分,不过我所想的是德勒兹、利奥塔(Lyotard)和乔治·巴塔耶
(George Bataille)这些极其干瘪的、自诩的“虚无主义”。
10.在后现代主义哲学中,避免采取立场已经被提升为一个哲学原
则。最近的一些法国学术明星都在嘲讽他们的前辈(尤其是萨特)太主
观,过于强调主体。(别忘了,萨特认为意识主体什么也不是,但照
让-吕克·南希[Jean-Luc Nancy]的说法,萨特的这种主张显然仍太主观
了。)11.见John Rajchman与Cornel West合著的Post-Analytic
Philosophy(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5)。
12.这里我们谈论的不只是后现代的碎片。这也是唐纳德·戴维森
(Donald Davidson)的一个立场,见其The Folly of Trying to Define
Truth一文,载于总第93期、1996年6月第6期Journal of Philosophy,第
263——278页。
13.在分析哲学中,人们可以从西德尼·休梅克(Sidney Shoemaker)
和约翰·佩里(John Perry)的早期著作到德里克·帕菲特(Derek Parfit)
和认知科学的近期著作中追溯这一失重的来龙去脉。(欧文·弗拉纳根
[Owen Flanagan]仍勇敢地为这一观念的持续有效性进行辩护,见他的
Self Expressions[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在大陆
哲学中,人们同样可以发现自我概念的瓦解,这一点既体现在萨特较具
实质性的“意识即虚无”这一主张,也体现在福柯(Foucault)、德勒兹
和让-吕克·南希对主体性的彻底摒弃中。
14.示例见他的Essays on Heidegger and Others,载于Philosophical
Papers(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1),第22页。罗蒂
自己绝大多数时候只谈其他哲学家提出的问题,但他坚持认为人类生活
的现实问题——比如贫穷、政治压迫、经济剥削、暴行和种族主义——
不是哲学问题。但这要归咎于他关于何为哲学以及哲学何为过度干瘪的
概念。在发动革命与心智自慰之间,还存在着一个丰富的对话空间,而
罗蒂自己已然成功地参与其中。
15.众所周知,苏格拉底认为未经省察的生活不值得过,但是,他
在哪些意义上省察或有没有省察自己的生活,这一点完全不清楚。显
然,他所想的并不是在现代的自我省察观念中无所不在的“内省”观念。
他似乎也不认为真正省察过的生活与寻常生活及其俗事有何相似。因
此,佩吉·努南(Peggy Noonan)在谈及她的前任上司罗纳德·里根
(RonaldReagan)时说,他就证明了未经省察的生活也是值得过的。在这个玩笑背后,隐藏着大量的哲学问题。
16.见Paul Woodruff的文章Plato on Education,收录于Amelie Rorty
编著的Philosophers on Education(New York:Routledge,1998)。
17.见伟大的独立记者I.F.斯通(I.F.Stone)撰写的未得到应有评价
但很杰出的耙粪之作The Trial of Socrates(Boston:Little Brown,1988)。
18.译者注:福斯塔夫是莎士比亚名剧《亨利四世》中的一个放荡
不羁的人物。
19.译者注:亚里士多德也曾被指不敬神差点被判刑,后来他想法
子逃出了雅典。
20.“深刻的思想家”这个词总带有一种轻蔑的意味,它源自科布
(Lee J.Cobb)1954年的电影《码头风云》(On the Waterfront)。不
过,我这个借来的反讽应该用维特根斯坦临终之言来平衡一下,很有苏
格拉底的风格:“告诉他们,我度过了美好的一生。”引自Rush Rhees所
编的Recollections of Wittgenstein(Lanham,Mo.:Rowman Little field,1981),也见M.O’C.Dury的文章Notes on Conversations(同上,76-
171),以及Terry Eagleton与Derek Jarman的剧本
Wittgenstein(London:British Film Institute,1993)。第一章 激情的生活
若没有爱过,生活还剩下什么?
——维克多·雨果(Victor Hugo)
告诉他们,我度过了美好的一生。
——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临终遗言)
生命丰富而肥美,充满着可能性和激情。可是哲学,哪怕是生命哲
学,常常都过于干瘪,被简化成骷髅般的原理、还原论的概念和单一化
的理论。在这方面,本应为生命哲学所用的伦理学可谓臭名昭著。几乎
整个20世纪——以及此前的世纪——人们都在致力于把伦理学简化为一
个单一的视角,甚至一个单一的原则,即“功利原则”或“尊重原则”。或
者可以说,伦理学(与政治学和社会哲学、美学和宗教一道)被极端轻
蔑又不幸地推到了哲学的边缘,“不再是真正的哲学”。它被认为太“软
弱”,“完全是主观的”,“严格来说,还毫无意义”1,由此而遭抛弃。人
类生命和激情丰美复杂的丰富性,被简化为一个备受推举的属性,即所
谓的理性,伯纳德·威廉姆斯(Bernard Williams)称之为“毫无特色的主
体”。2“人是理性的动物。”亚里士多德在两千五百年前如是说道。现代
哲学家们像是带着报复心一样接过他的这一命题后,把“动物”简化为纯
粹的生物,把“理性”局限在逻辑和语言之内。毫无疑问,亚里士多德若
是地下有知,肯定会被吓坏。我想要捍卫一种在哲学中常遭忽视或蔑视的“丰盈的”生命概念,进
而借此捍卫一套在伦理学中常遭忽视的德性。首先,我想要捍卫的是哲
学家萨姆·基恩(Sam Keen)在同题著作中所提倡的激情的生命。3这既
不奇怪,也不陌生。它是一种由情感所界定的生命,一种由热情参与和
信念所界定的生命,一种由一次或多次追寻、宏伟计划和无所不包的感
情所界定的生命。有时,它也会被描绘成用狂乱、过度的野心、“致死
的疾病”、根本无法达成的目标、绝无可能的感情(比如歌德
[Goethe]的《浮士德》[Faust]、克尔凯郭尔[Kierkegaard]和尼
采)。我想用这种生命概念与日常道德和“做个好人”进行对比,显而易
见,我这样做并不是要人们为了追求前者而放弃后者。尼采常常因
其“非道德者”的姿态和好战者的隐喻而遭误解,但我——基于坚实的文
本——深信他的意图绝非如此。4当然,我也不想独断地宣称充满激
情、强调参与的生活要优于较为安静、循规蹈矩的生活(用波西米亚反
叛者如今的标准行话说,就是“布尔乔亚式的生活”)。5但是另一方
面,我确实想提出如下问题:是否仅仅过得不错、遵纪守法、功利性地
权衡“理性选择”、尊重他人的权利和契约以及一点点自以为是,就是美
好生活的全部,哪怕在非道德的空间里头充斥着种种可容许的快乐和成
就。生活的意义不是为那些纯然的“好人”准备的,生命应灿烂燃烧,不
该寂然荒废,这种古代人、浪漫主义者和当代的摇滚歌手都有过的憧
憬,不该被人们——即使是我们这些已过而立之年的人——轻易摒
弃。6
在更深的层面上,曾有许多哲学家——包括苏格拉底、斯宾诺莎
(Spinoza)、叔本华(Schopenhauer),以及斯多葛学派(Stoics)、佛陀、孔子和庄子,甚至还包括亚当·斯密(Adam Smith),以上只是
其中一些例子——提倡“内心安宁”或“宁静”(ataraxia[不动心]、apatheia[无欲]、涅槃、道、安)作为至善。这也是我要加以质疑
的。当然,这不是说这些思想家以及他们的传统曾推崇或提倡情感的彻
底缺席。(例如,亚当·斯密就是道德情操的坚定辩护者;各种同情甚至极乐,在亚洲传统中也至为根本。)但他们或多或少全都固执地认
为,强烈、狂暴的情感——那种“席卷我们”的情感——非常麻烦,而且
常常是灾难性甚至是致命性的。
相反,在这一章中,我要提倡酒神式生命情调的正当性,它体现
在“能量”、“热情”、“魅力”甚至“迷狂”这些动态而非静态的隐喻、观念
中。7这也是荷马(Homer)、拜伦(Byron)和艾伦·金斯堡(Allen
Ginsberg)所倡议的充满爱欲的生活概念,这种生活或许有时因绝望和
忧世而难以承受,但也会因快乐和勃勃生机而振奋。绝大多数哲学家更
加熟悉的维特根斯坦就是一个不寻常的例子,众所周知,他的生活很神
经质,却也令人羡慕(不只是因为他的天才)。确实,拒绝在幸福与苦
楚(还有“善”与“恶”)之间做最终的区分,可能是我想要辩护的观点之
一,但这个不同寻常的论点不在这里要说的范围之内。(不过在第五章
对此有一次拙劣的尝试。)我较为温和的观点是:一种有德性的生活可
能不只是许多哲学家和当代道德权威敦促我们的那样,成为好相处的邻
居、受人尊敬的公民、有责任心的同事,以及有爱却毫无生气的人。
对此,可用更清晰的哲学方式来表述如下:在本书中,我首先要提
升伦理学中常受忽视的一维——激情或更一般的情感——的重要性。8
所谓的德性伦理学,即强调对行动者及其品格的伦理评价,如今被认可
为以行动和原则为中心的理论以及效果论之外的一个可行方案。不可否
认,德性概念已经被一些哲学家削得纤薄不堪,让人难以忍受,但是如
我所见,德性伦理学的优点在于,它丰富了道德描述和道德生活。9众
所周知,义务原则和效用原则也同样是干瘪的。集中于德性和品格问
题,能有助于整体地考量人格、历史、环境、文化和各方面的重要性。
当然,至于什么可算作德性、德性如何确切地与品格、原则和行动发生
关联这些问题,还存在着巨大的分歧。不过在这些问题之外,我还想增
加一个问题:伦理学中,德性和品格与情感是如何关联的。
很显然,人们谈及的许多(哪怕不是绝大多数)德性都与情感有所关联,不过常常是以负面的方式关联在一起。比如,勇气与克服恐惧有
很大关系,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Nicomachean Ethics)
中对此有详细阐述。菲利帕·福特(Philippa Foot)曾有一个著名的说
法:德性是情感的“矫正”,是把较为粗俗、自利的情感约束起来。10绝
大多数传统的恶习(贪婪、纵欲、自傲、愤怒,或许还有嫉妒,不过值
得注意的是,懒惰不在其中)都可以轻而易举地被定义为情感过度。可
是,上述任何情感的缺乏则常常被当作德性(禁欲、贞洁、谦虚等
等)。因此,尼采(在多处)警告我们说,莫把“缺乏情感的人”11等同
于好人。
更为正面地来看,主张道德情感的理论家弗朗西斯·哈奇森
(Francis Hutcheson)、休谟(Hume)、沙夫茨伯里(Shaftsbury)、斯密以及叔本华认为,一切伦理学都建基于同情、怜悯或同感
(Mitleid)这样的情感,不过这些情感(或情操)常常被认为是懦弱、情绪化的,甚至更糟。(当然,尼采认为这些情感极为糟糕,显得装模
作样、飞扬跋扈和伪善。12)就勇敢而言,德性是情感的调节器(“好脾
气”和“讲理”也是如此)。就同情而言,情感就是一种动机。因此,富
有同情心或显得同情本身就可以被认为是一种德性,而不只像亚里士多
德和绝大多数德性论理学家所主张的那样,是一种持久的“人格状态”。
(设想一个铁石心肠的人,在真正需要的时候表现了一次同情心。)
不过,亚里士多德也承认一些情感是德性,比如他把骄傲算作一种
德性(尽管他所说的骄傲与我们的骄傲观念极不相同),也稍带歉意和
牵强地把羞耻心当作一种“准德性”。(一个没有羞耻心的人大概也不会
有骄傲感,或者如埃塞俄比亚人的谚语所说的那样,“没有羞耻心的人
不会有荣誉感”。)换句话说,情感本身可以是一种德性,当然,这要
取决于各种具体情况的限制,还得考虑其强度和适当性。
这就是我在此要探寻的主张:激情本身就可以是德性。(当然,它
们也可以是恶习。)在《伦理学》(Ethics)第二卷中,亚里士多德问到,德性应被当作激情,还是更确切地说,被当作“人格状态”;他坚决
反对前者而主张后者。我并不否认,一般而言,德性是人格状态(或者
就此来说,激情可以是人格状态),但在我看来,激情(比如爱)也可
以是德性。
亚里士多德认为,激情稍纵即逝。这是一个常见的想当然。不过我
要说,激情(与短暂的情绪爆发、脾气发作、疯狂迷恋等不同)向来是
持久的——实际上是“难以消除的”。13尤其是,激情似乎仅仅指称强烈
持久的情感。说一个人“爱得很激情,不过每次只一会儿工夫”,除非是
在刻薄地开玩笑,否则就不知道这种说法有什么意义。因此,我要挑战
当前关于德性的标准描述(用伯纳德·威廉姆斯的说法):“一种选择或
拒斥行动的人格倾向。”14激情和情感不是纯粹的“人格倾向”,当然,从
其最为浅显的意义上来说,它们确实有助于促进选择某种行动、采取某
种方式。
但一种情感不是一种倾向;它首先是一种体验和“在世存
有”(beingin-the-world)的方式。如此说来(用吉尔伯特·赖尔[Gilbert
Ryle]15发明的行话讲就是),它是偶发事件性的,而不是倾向性的。
这不是要去否认激情可以持续很长一段时间——甚至一生——也不是要
去否认激情可以包括种种倾向,甚至是拥有其他情感的倾向。(我常常
听到这样的说法,在此基础上,爱不是一种情感,而是一种拥有情感的
倾向。16就像这一领域的诸多主张一样,这在我看来是对何谓拥有一种
情感的过度简化——也搞错了恋爱是怎么回事。)此外,激情作为德
性,不仅无须是一种人格倾向;甚至可以“与人格不相称”,与人们通常
对这个人的期待完全相悖。17“坠入爱河”以及由压力所激发的英勇行为
常常是这种“失常”的例证。确实,这些例子有足够的说服力,促使我们
去认真考虑把激情算作一种德性,而非人格倾向。
我首先想要挑战的,是一些反对康德所谓的伦理学中“倾向”优先的
标准观点,它们源自康德派的传统——尽管有人会争论,这并不是康德本人的说法。18随后,我想关注一种特别的情感:爱。这个字义杂乱的
词所涉甚广,从亲子之爱到圣人般的虔诚之爱都包括在内,但其中只有
一些可算作是有激情的。我们所谓的“浪漫的”爱、“炽热燃烧的”爱(如
简·奥斯汀[Jane Austen]在《理智与情感》[Sense and Sensibility]中
描述的那样,或如琼[June]和约翰尼·卡什[Johnny Cash]的“火
环”[Ring of Fire]所吟唱的那样),无疑属于其中。数千年前,柏拉
图为情爱(eros)这种激情辩护,认为它是一种德性。亚里士多德或许
较为谨慎,他为友爱(philia)的德性辩护(实际上,它是《伦理学》
中篇幅最长的论述),但它在多大程度上是激情而不是我们所谓的“亲
爱”(affection),就不得而知了。这里我不会思虑所谓的对人类的爱
(agape,caritas[博爱]),同时我会把怜悯、同情之类的情感放到后
面的章节(第四章),当然,它们在伦理学中由来已久,不仅存在于基
督教、儒家学说和佛教中,也存在于18世纪以理性为导向的欧洲启蒙运
动时期盛行的“道德情操论”中。19这里,我将采取一条更为艰难的道
路,为我们现在所谓的浪漫爱、情爱辩护,主张它们是一种德性——而
且是一种堪称典范的德性。在此,我的目标就是要把整个德性(以及恶
习)的形象颠倒过来,或者确切地说,与头脑保持一定距离来展望它
们。(有人说从“心”来看,但从生理学上来看,那是个含糊不清的概
念。)我要为人们所谓的热情辩护,主张它是一种德性,因爱的依恋而
生的热情就是最显然的例子。
冒着过于理智的嫌疑,让我先来对我的主张做一个重要的限定性描
述。当我说要为激情的生命辩护,且主张激情也是德性时,得先说清
楚,并非任何激情或情感都是德性,纵然有些情感是德性,那也不可能
一直是德性。20比如,我非常警惕某些集体情感:战争狂热、种族主义
以及一切导致种族屠杀的激情。(对于在体育竞技中不可避免会出现的
那些类似的“升华”或“错位”的激情,我并不乐观。体育迷们平时没什么
可高兴的事,除了买票去现场或坐在家里看电视之外,无事可做,因
此,对于我而言,他们那种毫无拘束的快乐,永远是一个令人不安的
谜。)有些情感不在德性的范围内(比如嫉妒),同时,情感超过一定的程度或强度(当然,对于这种量化的说法,我有所质疑),就绝不是
德性了。
比如,以爱为例,激情与迷恋之间就有着微妙的区分(香料商与牛
仔裤制造者常常忽视这一区分),我绝不会为迷恋辩护(当然,它们之
间的区分在于双方是否有互动,而不在于激情本身)。不当的爱、愚蠢
的爱、占有欲太强的爱(这或许更应称之为猜忌[jealousy]):这些
都不是德性,也不是有德性的,不过,即使愚蠢的爱也比完全没有爱展
现了更多的德性。但是,若想搞清楚德性本质的关键,就要格外留意激
情的爱与迷恋的爱(包括性的迷恋)之间的区分和关联。人们常说,德
性关涉的是可控之物,而“失控”正是有德性的对立面。(想想“精湛技
艺”[virtuostiy]21一词)但是,爱的本性就在于其不能被掌控,或者说
不能完全被掌控,而是与他人的突发奇想和福祉以及命运紧密相连。我
们发现,激情和欲望起伏不定,完全无视我们的希望和承诺。所谓迷
恋,或许正是翻涌变动的人生之海里所必需的牢固依靠,而所谓激情则
部分地要归因于伴随这种迷恋的不确定性。我要主张的是,正是这种激
情,这种面对不确定性时的激奋,和失控时的坦然接受,构成了爱的德
性。
最后,我想通过弗里德里希·尼采这位最具胆识和令人兴奋的现代
德性伦理学家的著作,对上述哲学颠覆加以概括。尼采有时称自己是一
位“非道德者”;然而,这种有点过分雕饰的自我描述,并不是要拒斥伦
理学,而是拒斥由康德以及(历史地来看)犹太——基督教传统所奠定
的那种广为人知的道德观。与此相对,尼采也捍卫过某种形式的“德性
伦理学”(他当然不会喜欢这个丑陋的标签),其中处于首要位置的,不只是德性,还有激情。直白点说,伦理学不是一种外在的强加,无论
这种强加是出自上帝、法律还是“畜群”,同时,它也不包括通常所认为
的有助于直接改善社会福利或公益的算计和人格状态。它不遵从内在理
性的道德律或“良心”的要求,而且就这点而言,它也不包括常常被基督
教徒颂赞为博爱的那种普遍的爱。“什么是善?一切提升权力感的事物。”尼采在其显然具有论战性的著作《敌基督者》(Antichrist)开头
如是写道。我认为,“权力感”与情感和激情很有关系。
在尼采更早的著作《快乐的科学》(The Gay Science)中,题目本
身就显示了对激情生活的辩护:la gaya scienzia(快乐的科学),游吟
诗人的生活,充满柔情和爱的生活。因此,尼采的“非道德主义”常常被
认为与唯美主义关系密切,即认为伦理学和伦理判断可还原或转化为审
美和审美判断。22这不是我在本书中要持的立场,虽然我认为这话说得
挺有道理。相反,我想追究尼采对激情的强调,尤其是他那激人奋进又
令人毛骨悚然的“权力意志”观念,它所强调的不是美学而是某种别的东
西:“能量”、“热情”、“力量”以及“自制”,不过这种自制不是说要克服
激情,恰恰相反,是要培育激情。很显然,这不只是在反对康德的实践
理性、功利主义的计算以及享乐主义,还要反对伦理学中由道德情操理
论家和(较为贴近尼采所想的)叔本华所主张的较为温和的情感概念。
不过在继续论述之前,还得强调一下,我认为权力意志在尼采学说中的
地位经常会被误解和夸大,被提升到了一个在其哲学中不应有的地
位。23我仅仅主张,有一种近乎可信的关于德性和恶习的伦理学,与盛
行的“德性伦理学”迥然不同,或者更宽泛一点,与各种出于“实践理
性”的伦理学极为不同。我必须抱歉地对戈雅(Goya)说,制造出恶魔
的,不只是理性的沉睡,还有理性的霸权。24爱作为一种德性:驳康德的典范
爱作为爱好是不能告诫的,然而出于责任自身的爱,尽管不是爱好
的对象,甚至自然地、不可抑止地被嫌弃,却是实践的而不是情感上的
爱,这种爱坐落在意志之中,不依感受为转移。
——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基础》
(Grounding of the Metaphysics of Morals)
它[爱]毫不犹豫地带着它的渣滓冲了进来……它甚至懂得如何在
政府文件和哲学手稿中偷偷塞进示爱的字条和小卷的发丝。它每一天都
酝酿和孵化出最糟糕、最扰人的吵闹和争执,毁坏最珍贵的关系、破坏
最牢固的盟约。……为什么会有这些嘈杂和纷扰?……这只是一个人人
皆有其偶的问题。(有品位的读者应该把这种习语转换为阿里斯托芬式
的语言。)为何这样的琐屑小事会如此重要?
——亚瑟·叔本华,《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
(World as Will and Idea)
叔本华是众多对导师反戈相向的康德主义者中的一位。这位伟大的
悲观主义者或许沉湎于康德的世界观,但却反对其伦理学。在他看来,伦理学的核心和基础是同感(Mitleid),而不是实践理性。但是涉及性
爱时,叔本华并不比康德更有识见(但无疑比康德更有经验)。他语带
讥讽地说道,“渣滓、嘈杂和纷扰”。当然,在叔本华那里,人类生活中
一切——艺术、佛教和他自己的哲学除外——在实质上都是微不足道
的。在他看来,爱显然不会拯救生活。实际上,一般所谓的激情不过是意志的挣扎,正是意志以它非凡且形而上学的无目的性规定并支配着我
们所有人。除了同情(康德也称之为“美”25),叔本华也贬低“倾向”,尤其不屑于理会激情,认为它不过是非理性。像康德一样,他显然也认
为浪漫感情与道德价值完全无关。
自启蒙运动以来,康德的道德判断和合理性典范就一直在伦理学中
保持着霸权。尽管康德的理性主义锋芒有所钝化,他的道德判断概念也
已然扩宽,但其首要的焦点仍确凿无疑,他的追随者们甚至毫无顾忌地
认为这一点显而易见:道德哲学若不客观、冷静、基于原则、排除具体
的自我指涉和摆脱个人“偏见”,就什么也不是。比如,伯纳德·格特
(Bernard Gert)在《道德规则》(The Moral Rules)一书中就认为感情
毫无道德价值,并且坚持认为:“感情在道德上的重要性,仅限于它们
能引导道德上的善行这个含义范围内。”26这个典范的骇人之处在于它所
忽略的东西,最明显的是绝大多数情感,特别是爱,除非它们有助于激
发责任感,或者能促进“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善”。伯纳德·威廉姆斯指
出,那种根据康德的观点认为善行应出于原则而非个人感受的说法,是
荒唐的。无论这种说法是否真是康德的主张,人们都可以设想一下把这
个观点移植到激情之爱领域的情形。光是这个提议就够骇人听闻了。
(人们一下想到的就是“夫妻的义务”。)还是想想爱的诸多快乐、感受
和责任吧;与其坚持认为爱(再怎么样也)与道德无涉,我们更愿意把
爱当作一种德性来对待,并抛弃完全没有人情味的“康德式”道德观。
格特认为,爱以及其他“感情”之所以可贵,在于它们有助于带
来“道德上的善行”,这种说法有其诱人之处。然而,不管爱是否能“带
来”值得赞许的行动,我们感情的价值都不会取决于因之而来的行动及
其后果。27爱是最具说服力的例子:在爱中,我们行动的价值取决于其
所表达的感情。爱或许会激发慷慨甚至英雄般的行动,但爱的德性仍卓
然独立。(苏格拉底在《会饮》[Symposium]中正是借此批评斐德罗
[Paedrus]。因为斐德罗赞美爱[善行]的结果而不是爱本身的德
性。)我们可能会认为(《理智与情感》中)的玛丽安(Marianne)愚蠢,但仍能钦佩她的激情,与此相反,爱德华七世时代的文学
(Edwardian literature)中随处可见的依原则行事的康德式绅士,倒是令
人反感十足。爱不仅会令人感到满足,而且那些已然不爱的人(不管他
们是否也失去过所爱),或那些害怕自己不能爱的人,所担心的肯定不
光是他们的品格,还有他们作为人的完整性——这与任何关于行动或表
现的问题毫无关系。我们(他们的朋友)也会为他们担心。爱本身就是
令人称羡的,与其作用和结果无关。28
反对把爱及其他感情看作道德的基本要素,这与《新约》中对爱
(即使这里所说的爱是博爱[agape],而不是情爱[eros])作为至高
德性的强调不一致,而《新约》的意图显然不会出于功利主义或康德主
义。这一部分开头援引的关于“病态的爱”的段落,正是康德对这一反常
情形试图作出的解释。他似乎认为,唯有能够被“命令”的,在道德上才
是必须的,而爱作为一种激情是无法被命令的。这个具体的主张常常惹
人争议,比如,爱德华·桑科夫斯基(Edward Sankowski)在关于爱和道
德责任的论文中,就论证说,我们人类至少有责任去促进或回避滋养爱
的条件。29对于唯有能够被命令的才是道德的(甚至是必须的)这一主
张,人们也可以质疑;因为许多构成“好人格”的要素,可以经由教养而
来,但不可通过命令而获得。人们还可以认为——我就常常这样认为
——情感比我们通常认为的更出于自愿、更受我们的控制,而且不仅仅
就我们能够促进或避开造成它们常常涌现的那些条件而言。当然,这也
不是说,爱这种情感就如同冒出一个想法或移动一下手指那样,可以仅
凭意志或意愿而产生。用丹托式的语言来说,就爱而言,或许并不存在
所谓的“基本行动”。30认为爱(或任何德性行动)可以凭空产生,无疑
是一个误解。
康德似乎认同《新约》中的伦理,因为他坚持认为道德的核心总是
普遍共相,而德性总是具体殊相。31而且根据绝大多数关于基督教之爱
的解释,爱显然侧重于对具体之人的爱。典型的基督徒会爱每一个具体
的人。他或她的情感和尊重不只是留给普遍共相(上帝、人性)。实际上,甚至康德都主张我们要在一个人那里爱人性。此外,爱,尤其是情
爱或浪漫之爱,不仅是具体的,还是有选择的,甚至是排他的,把本来
寻常之人提升到不同寻常的高度,并赋予其不同寻常的特权。在这种情
形中,“绝对命令”的观念——普遍的“应该”——是可笑的。根据康德的
模型,爱的特殊性似乎是非理性的一个典范——我们倾向于把自己(在
此则是把我们最亲近的人)当作例外的一个版本。一个会爱的人若坚持
要客观冷静地对待每一个人,包括他或她的爱人,肯定会让人觉得面目
可憎。
人们有时会说,一般所谓的情感,尤其是爱,都是非理性的,因此
不可能是德性,因为它们反复无常。32它们完全来去无影,不可把捉。
它们只是偶然,没有理性的必然性和理性的持续性。不过同样的,想一
想“不可索解”这样的指责吧。33众所周知,要让一个恋爱中的人清除这
种情感有多么困难,哪怕如今它已成了难以承受的痛苦之源。更确切地
说,爱会自我加强,随时间而扩张,并通过爱找到越来越多的理由去
爱。34我要表明,这并不是反对情感的一个论证,而是针对其德性的一
个方面。我们批评的,是那种转瞬即逝的幻象,而非不可动摇的热爱。
我们称之为非理性的,是突发的愤怒,而非根深蒂固和毋庸置辩的仇恨
(这倒不是说突发的愤怒总是不正当或不合适的,也不是说长期的愤怒
不会偶尔有些非理性甚至疯狂)。确实,情感是固执且难以驾驭的,但
也正因为此——与根本上不那么可靠、依原则产生的行动不同——它们
才在伦理学中不可或缺。一个出于激情而斗争的人,或许比为了一个抽
象原则而斗争的人更为可靠。难以驾驭是情感的德性,恰如合理化是理
性的弊病一样。实际上,我们甚至可以说,情感的真理(部分)正在于
它们的难以驾驭性,它们对变化的抵触。
人们也说,爱和其他情感会混淆或扭曲我们的经验,因此不是德性
的。但让我们想一想:一个其貌不扬的恋人殷切地看着他那个同样平常
的所爱说,“你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我们会如何理解这句话?自我
欺骗?疯狂?但绝不是盲目,因为问题不在于他瞎了眼。实际上,他甚至有理由说比我们看到的更多,或更深刻。面对这种无礼的质问,我们
这位陶醉其中的恋人或许会愤恨地做出让步,或许会做出一种现象学的
退让说:“好吧,在我看来她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但我们知道,哲
学会如何对待这种限定——认识论上理所当然的轻蔑。难道我们把这种
特有的看法当作爱的德性而非恶习,不是更好吗?(很显然,这一论点
不能被毫无批判地普遍施于其他情感。)
客观地说,爱可能与哲学伦理学要强调的一切都背道而驰——客观
性、非个人性、公正性、普遍性以及对证据与论证的尊重,等等。然
而,在我看来,这种“非理性”构成了我们最重要的一些道德特征。我们
彼此关心,无论是否有什么证据或论证表明我们应该如此。我们发觉彼
此的美、魅力和吸引力时,似乎也没有共同的参照标准。如果一个恋
人“总是见异思迁”,或者受朋友的意见左右,那我们就会看轻他或她,而不是看重他或她。许多人甚至认为,继续去爱一个显然完全不值得去
爱的人虽然是愚蠢的,但仍是值得称赞的。(大众舆论似乎证实了这种
毫无道理的爱,比如,有些女人爱上并嫁给了入狱的罪犯或等待行刑的
杀人犯,如近来的一部电影《死囚漫步》[Dead Man Walking]中的情
形那样。)爱(或爱着)本身就是德性,而且是一种重要的德性,与之
相比,合理性反倒显得苍白无力。情爱的德性
总之,我的论点就是:爱是最古老的神,是诸神中最光荣的神,是
人类一切善行和幸福的赐予者,无论对活人还是对亡灵都一样。
——斐德罗,见柏拉图的《会饮》
感性的升华叫作爱;它是对于基督教的伟大胜利。
——尼采,《偶像的黄昏》(Twilight of the Idols)
我的上述论点,绝大多数实际上适用于一切类型的爱(以及其他感
情),但是,要为激情的生活辩护,所需的范例仍是性爱或情爱。人们
可能会认为,父母亲子之爱中可以找到诸多德性,尽管如此,人们仍可
以质疑伴随情爱而生的焦虑和不安中是否也存在着同样的德性。在这方
面,就要注意情爱与博爱、“性”爱与无私无性的爱之间的区别。这个区
别,经过柏拉图到保罗基督教稳固的制度化之间的数世纪,日益变得粗
暴且不利于情爱。情爱被认为是纯然情欲的,并被简化为性欲,但它当
然不是这样。博爱被形容为无私的给予,与此相对,情爱就成了自私的
占有和渴求。博爱甚至被理想化到了一种唯有对上帝才可能有的态度,因此,它实际上无法应用于我们人类同胞的感情。与此相对,情爱被贬
低为渎神的世俗之物,没有一丝一毫的灵性。
把爱当作一种德性,首先就要(再次)扩展情爱的范围。但为了主
张情爱至少共享博爱的某些德性,人们不必否定博爱的可欲性(或可能
性)。情爱不同于博爱之处,在于情爱充满着利己欲望,但它并不因此
就是自私的,而且这种欲望也不必然就是性欲。它包括较笼统的在一起
的身体欲望,比如“被欣赏”和“一起幸福”的个人欲望、“为你做最好的那个人”的激发性欲望,以及“我能为你做任何事”的“利他”欲望。但要
注意的是,道德语言之所以在这些想法中失去了效力,并不是因为退回
到了前道德或非道德的领域,而是因为“你的”与“我的”之间的区分开始
消失了。
情爱贬损的一个关键因素,在于对性的反对。人们通常错误地认
为,在性行为中,他人被当作纯粹的欲望“对象”,由此也使人们认为情
爱是堕落的,所寻求的不过是一己之满足。让我们来看看康德对此问题
的看法:
由于性欲不是人对他人之为人的拥有倾向,而是对他人之性别的占
有倾向,因此性欲就是人性的堕落原理,它使人偏爱一种性别甚于另一
种,而且通过欲望的满足玷污了这一性别。35
然而,问题(恰如柏拉图在两千三百年前提出的那样)无疑在于,当一个人对他人有性欲时,这个人所欲求的是什么。在《会饮》中,阿
里斯托芬(Aristophanes)认为,人所欲求的不只是性的交合,还有与
他人永恒的(再次)合一;而苏格拉底则认为,人真正想要的是形式。
即使我们认为这些目标就情爱而言过于荒诞,但很显然的是,希腊人
——与康德和许多现代人相反——认为性欲不只是对性的欲望,而且根
本不与德性欲望相对立。至少这一点是显然的:性欲是一种以性为中介
的对他人的强烈欲望。问题依然是:欲求的是什么?我们决不应一开始
就假设这一问题的答案与性对象有关。实际上,若根据从黑格尔和萨特
(Sartre)那里得来的线索,我们反而会认为这与性主体紧密相关,因
为作为性主体的人,即是性活动的行动者,又是性经验的接受者(或共
同创造者)。36
换而言之,一个人对他人充满激情的依恋是一种德性,因为它体现
了一种尊重,尽管这种尊重确实与康德和康德派的那种抽象、干瘪的尊
重迥然不同。以为性欲与尊重不可共存,可以说是青少年的典型噩梦。
(人们还可以补充说,人一旦发现自己身处这样的约会活动中,就很容易有这种青少年心态。)这种噩梦完全不是出于经验和智慧的呼声。性
欲是最亲密的依赖形式,需要全身心的投入。确实,人们会发出疑问,道德领域(当然,诸多规则和禁令除外)之所以产生如此强烈的排斥
性,究竟有多少是因为以下情况:性不可避免是身体性的,而且涉及的
是身体最肮脏、最易受伤害、最柔弱的部位。这与康德的“理智”世界中
那个纯化了的“主体”有多远的距离啊!针对康德的反驳,我们或许可以
说,在爱的性行为中(很显然这不是艾伦·戈德曼[Alan Goldman]所
谓的“纯然性行为”),人激情地爱着的是他人本身。37在我看来,这是
我们最为推崇的终极形式的尊重,它不只是对法律的尊重,也不只是对
让他人自行其是的尊重,而是完全的、无所不包的接纳,以及由这种对
他人的接纳而来的快乐。
这一尊重常常受到忽视或被否认的一个方面,就是爱人之间的平等
这一前提条件。鉴于现代人指责爱是贬损和压迫妇女的工具,上述说法
可能显得古怪,但是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很显然——不管我们离真正的
(社会、经济、政治)平等有多远——浪漫爱的出现,只有在妇女从传
统从属的社会和经济角色中得到一定的解放后才有可能。也就是说,唯
有当妇女开始对她们的生活——尤其是她们的爱人和丈夫——有更多选
择时,所谓的浪漫爱才会出现。人们可以想想约翰·弥尔顿(John
Milton)笔下的亚当,这个在浪漫爱时代早期创造出来的角色,特意向
上帝要求的不是一个纯粹的玩伴或伴侣或自己的镜像,而是一个平等
者,因为“不平等者之间,哪有社会之有序,哪有和谐或真正的欢
欣”?38或者借用司汤达的话,我们可以说,在找不到平等者的地方,爱
就会去创造平等者,因为平等之于浪漫爱,恰如权威之于父母身份,乃
基本之物——无论人们是否充分认识到这一点或借此行动。
然而,就我们的目的而言,或许最重要的在于如下事实:与所倡议
的绝大多数德性(友善、可信赖、公正、谦逊、节制甚至勇敢)不同,爱是令人刺激的。当然,其中一些刺激与性有关,而我在前几页的论述
中尽力避免主张性欲本身就是一种德性。不过,性欲既不是一种恶习,也不应被贬低,尽管它很显然可以被用作表达各种邪恶和淫秽讯息的媒
介。但是,性行为中令人激动的感觉不应被简化或局限为通常(且含糊
地)所谓的“兴奋”。身体的兴奋就像性“本身”一样,在道德和享乐上是
中立的;它在我们生活中的角色取决于语境,尤其取决于与之相伴随的
情感和以之作为“表达”的关系。不过,对于性的诸多刺激,也许从我们
的脆弱性、我们对他人的开放性来理解更好,后者显然比诸多公认的德
性所指认的方式更“基本”。性爱的某些刺激源自不确定性,最初交往时
尤其如此,但是,我无疑要表明,新奇的刺激不应与爱混为一谈。39克
尔凯郭尔将一般所谓的爱的开放性描述为“信仰的跳跃”、“主观真
理”、“面对客观不确定性时的坚定”(尽管他对性爱冷嘲热讽)。这里
特别要注意的是,性爱涉及选择问题(这多么像是个命运问题啊),而
选择——连续的选择——很容易导致存在主义式的焦虑,即使结果早已
注定。
然而,性爱刺激的最终理由,用自我同一性这一哲学术语来表达最
好。人们常常根据情感的“强度”40来区分激情和普通情感、情感和不带
感情色彩的信念或判断,但我认为,更好的解释可以用经济学术语来
说,即所谓的情感“投入”。激情决定了自我,它们是自我的重大“投
入”,绝大多数情感做不到这一点。要注意的是,爱或许可以(部分
地)被定义为在他人身上并且通过他人来定义自己。不用说,这完全不
同于叔本华把爱视作性欲加哲学混乱的观点。它更像是柏拉图原创
的“阿里斯托芬式”爱的说法的最新翻版:两个被分成两半的灵魂的“成
全”和“融合”。41对此,我无法在这里深入分析,但它表明爱的“强
度”(以及其他激情和情感)要比纯粹的神经和荷尔蒙躁动深刻得多。
爱的那种激动人心的忠诚与依恋,与所有倡导不动情
(apatheia)、颂赞心灵平静的哲学截然对立,因为无论爱带来的快乐
和安全是什么,毫无激情的冷淡都不在其列。因此,从克律西波斯
(Chrysippus)到斯宾诺莎的斯多葛派,即便是在为某种更宽广的宇宙
心态辩护时,也对爱这种狂热、易受挫的激情心怀警惕。在这一点上,弗洛伊德与佛陀一致同意,“欲望就是受苦”,唯有终止欲望(“死亡本
能”、涅槃)才能带来解脱。在这里,“成熟”的智慧永远对年轻人纠缠
不休:要当心爱带来的狂喜,因为它最终只会令人失望。对这些观点的
辩护无论是出于审慎之故还是以德性之名,人们都不可能从中期待一种
对于激情生活的辩护,或爱是德性的观点。到这儿,我们绕了一圈,又
回到了一开始对情感的综合考察以及对爱的具体探究所希望达到的视角
转换。假设我们不通过平静的永恒之眼来看待生活,而是用我们的实际
经历来看待生活:短暂、急迫,不是理性要去解开的迷惑或奥秘。42假
设我们把激情本身当作至善——当然不是随便哪种激情,而是那些被爱
之类的激情所定义的生命,不是那些由宁静和心灵平静所定义的生
命。43一如往常,在这里我们必须提防诡辩和“说服性的”定义。如果说
放弃心灵平静就意味着要带着失败感、挫折感、良心不安或屈辱感去生
活,那么,激情的生活概念一点儿也不值得推崇。但是,如果爱的德性
之一是持续的刺激,而且这种刺激并不只是原本平静、“令人满意”的生
活的标点停顿(尽管“满意”这个观念可以被曲解以符合哲学的成见),那么,我们就应该认真对待这样一种生活识见:“骚动”而非其缺乏,才
是我们的最终渴望。而对这种生活识见最出色的描绘和展现,无疑是尼
采那些生气勃勃的散文。权力意志作为德性
什么是善?凡是增强我们人类权力感,增强我们人类的权力意志以
及权力本身的东西,都是善。
什么是恶?凡是源于虚弱的东西都是恶。
什么是幸福?幸福不过是那种意识到权力在增长,意识到反抗被克
服的感觉。
幸福不是心满意足,而是更多的权力,不是和平本身,而是战斗;
不是德性而是能干(文艺复兴时期的德性,也即virtü,恰恰是和道德
无关的德性)。
——尼采,《敌基督者》
当然,尼采自己言过其实了。夸张(以及不自量力)是热情的常见
症状。于是,基于一两句较为夸张的格言,好几代杰出的理性主义哲学
家就完全对尼采不屑一顾(“不是一个哲学家!”)。(据说,著名的耶
鲁大学哲学家布兰德·布兰夏德[Bland Blandshard]曾把尼采的一本著
作甩到了屋子另一角。这种对于尼采的常见态度直到最近才有所转
变。44)尼采夸大了他对道德的反感,变化地称之为“奴隶道德”和“畜群
道德”,并叛逆地称自己是一位“非道德者”。事实上,尼采认为自己
有“一种更加严峻的道德”45,而我也已经提示过,尼采真正的意思是
说,我们应从一个不同的“视角”来理解道德和道德性本身,这个不同的
视角就是我们现在所谓的德性伦理学。他同样夸大了自己对宗教的反感
(“上帝已死”是其开始),但可以争辩说,这种反感是在捍卫他童年时
代的路德教义中的精华,以及他认为早被德国人(尤其是他过去的朋友
理查德·瓦格纳[Richard Wagner])抛弃的精神性。他最为著名的夸
张,是“没有真理”(却又坚持完全的诚实)这一(前后不一致的)观点。不过,最引人注目又令人误解的夸张言辞,是关于“权力意志”的谈
论,这一观点最初在《朝霞》(Daybreak,1881年)中初显威力,又在
其后期的哲学著作《敌基督者》(1889年,出版于1895年)的开头明显
过分夸张的说法(见前面引文)中达到顶峰。
这不是全面探究尼采哲学的地方,甚至也不是探究他的“权力意
志”观念诸种细微之处的地方。但我应该清楚表明,为何我要把尼采而
不是亚里士多德当作我在德性伦理学领域的终极导师,以及激情生活的
捍卫者。因此,我将(简洁地)勾勒一下我所谓的尼采式德性理论。我
无法罗列一份“尼采的德性”清单,而这在亚里士多德那里轻而易举就可
以做到(不过人们或许注意到,尽管亚里士多德设定了“两端间的中
道”这一标准,但他的清单仍无法摆脱即兴而为[ad hoc]的嫌疑)。首
先,最明显的一点是,尼采可不是有体系的思想家。其次,尼采坚持认
为,我们每一个人有他或她“自己的德性”,甚至为某人的德性命名就等
于使之变得“常见”而否定了其独特性。现在流行的一种后现代主张认
为,尼采没有一种伦理学,也没有做任何断言,甚至没有提出“道德建
议”,因此反对这种关于尼采哲学的分析。然而,哪怕只是随便翻翻尼
采众多文字中的任意一部分,都会发现这样的主张站不住脚。46尽管如
此,这种解读方式仍吸引了一些非常优秀的尼采学者,其中有伯恩德·
马格努斯和亚历山大·内哈马斯。不过,我不打算在这里处理这些问
题。47不如让我出于启发的目的,在假设尼采确实给出了一些建议(事
实上无所不包,从营养指南到如何拯救世界)的前提下,试着谈一谈关
于这些建议的系统性观点——或确切地说,尼采那以“权力意志”为名的
德性伦理学——可能会是什么样子。
尼采所说的“权力”(Macht)一词到底是什么意思,历来广受争
议。这要部分归因于海德格尔复杂却又极不合理的分析,他说尼采
是“权力意志的形而上学家”;还要部分归因于瓦尔特·考夫曼(Walter
Kaufmann)在其经典著作《尼采:哲学家、心理学家、敌基督者》
(Nietzsche:Philosopher,Psychologist,Antichrist)中对这一概念的过分关注;但尤其要归因于这个词不祥的“军靴”味,因为它易于吸引亲法
西斯主义者,且无疑会让自由主义者感到惊惧。但是,尼采十分明确地
拒斥了针对他人的权力观念(包括政治权力,或德意志帝国);而且尽
管他确实赞成竞争,但也坚持认为,权力的首要意义在于自我控制。因
此人们也可以合理地认为,尼采心里所想的是创造力,是艺术家、诗人
和偶尔搞哲学的人的权力。尼采把权力等同于“精神化”,但同时警告
说,宗教和哲学中多数误作“精神”的东西,其实配不上这个名称。具体
而言,德国“精神”之所以变得如此毫无价值,就在于它已经彻底且自觉
地衰弱了,背负着错误的德性负担(尤其是谦卑之类的基督教德性,他
的精神同侪休谟称之为“僧侣德性”),并进一步被尼采所谓的“畜群”摧
毁。我要说,权力意志的关键是一种强烈的自我感,一种充满激情却有
纪律的自我,它追随自己强有力的“本能”,又能完全地“克服自
己”,“赋予自己的品格以个性”,“成为真正的自己”。48
上面这种描述中明显欠缺的,是诸如理性和反思这样的哲学德性。
与绝大多数道德哲学家(包括亚里士多德,不过他明确主张,经由教养
而来的正确行为要先于伦理推理)相比,尼采无疑更热衷于德性行为不
带反思的“自然而然”。但是,他也坚持理性的位置,而且他(像亚里士
多德那样)认为,体现在行动中的理性要比反思合理性中的理性更为重
要。比如,对于力的胜利。由于一种古老的奴隶习俗,我们一见到力就双腿发
软,不由自主要在它面前屈膝。然而,一种力是否可敬和可敬到什么程
度,取决于它所包含的理性的程度:因此,我们必须确定,力到底在什
么程度上被某些更高的东西克服了,这些更高的东西现在把力用作一种
手段和工具。
尼采对“力量”(Kraft)众所周知的强调,尤其是在《道德的谱系》
(On the Genealogy of Morals)的第一卷中,必须以许多这样的限制为
背景来考量。简单地把权力等同于力量(如尼采自己常常暗示的那样,上引《敌基督者》的原文就很明显),就会把尼采认作一个野蛮人或道德上的达尔文主义者,而他显然不是这样的人。如果我们认真对待超人
(übermensch)这个在尼采那里卡通化了的形象,那最好把它解释为尼
采的德性伦理学的投射,他理想的化身。49把超人刻画为野蛮人科南
(Conan the Barbarian),无疑对尼采不公;当他(更为常见地)谈
论“更高类型”时,他心里明确想到的常常是大诗人歌德。50
尼采式的德性有哪些?或许可以这样说,首先且最为明显的一点:
其中许多是“异教的”德性,它们(与在休谟那里一样)意在与基督教的
或“僧侣的”德性形成对照,后者在德国被重述为“资产阶级的”德性,这
一点尼采很清楚。因此,一份尼采式德性的主要清单,与亚里士多德式
德性清单很像:勇敢、慷慨、诚实、可信赖、节制(sophrosyne)、公
正、骄傲、友善和机智。但是,这份希腊的或“异教的”德性清单肯定不
是亚里士多德的清单,而且尼采心中所想的也不是亚里士多德笔下的绅
士贵族。他认为,古希腊三大哲人——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
德——的哲学全都是完全“败坏的”。尤其是,他认为亚里士多德的伦理
学不过是一种一厢情愿的思想,竟以为雅典可恢复它一度拥有而肯定不
会再现的荣光。俘获了尼采想象力的希腊,是前苏格拉底的希腊,索福
克勒斯(Sophocles)笔下准神话的希腊,以及荷马笔下战士的希腊。因
此,尼采对这些“异教的”德性的理解,必须回到过去,回到一个迥然不
同的年代,回到一种迥然不同的精神。此外,尼采对这些德性的看法也
与亚里士多德的截然不同,或许,这源于他一开始就拒斥“中道标准”以
及雅典人对“节制”的坚持。这反过来就要求对拥有一种德性有一个新理
解,而衣着讲究的绅士行为在此至多只有一丁点儿作用而已。
或许,这一丁点儿作用体现如下:尼采自己坚持“谦恭有礼”乃一基
本德性。当然,尼采并不反对亲切和友爱这些德性,且就其对社会德性
的关注而言(这当然不是他的主要兴趣所在),他也绝非如其有时自我
描述的那样,是那种“迎面痛击”的强硬派。(这种自我描述最明显的例
子就是他发表的对怜悯[Mitleid——也译作“同情”和“同感”]的诸多反
驳,但我认为,这种反驳有着完全不同的用意。)不过,尼采与亚里士多德更具戏剧性的差异,可以在对上述前两个德性——勇敢和慷慨——
的分析中找到,并由此引导我们进入激情生活的主题。
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勇敢就是对恐惧的克服。或者换一种说法,勇
敢就是具有恰当分量的恐惧:不能过多(否则就是怯懦),也不能太少
(否则就是鲁莽)。在亚里士多德那里,这种心理上的动态变化并不清
楚(比如说,克制情感到底是什么意思),不过清楚的是,勇敢需要一
定程度的恐惧。现在,让我们来看看如下这幅画面,它类似于亚里士多
德对《伊利亚特》(The Iliad)中赫克托耳(Hector)的勇敢的运用。51
阿基里斯(Achilles)因好友普特罗克勒斯(Patroclus)之死而暴怒,满
脑子都是报仇雪恨(“正义”)地冲向特洛伊城外的战场。他毫不畏惧。
在这种目标明确的狂怒中,恐惧完全没有一席之地。那么,说处于这种
状态下的阿基里斯“勇敢”,在我们看来即使不算荒谬,也显得过于轻描
淡写了。
我们自己在这里对勇敢的理解与亚里士多德一致。所谓勇敢,就是
对阻力(即恐惧)的克服程度。但是,若我们从尼采(和荷马)的角度
来看这个问题,恐惧与勇敢似乎并非互补,而是对立,因此,堪称勇敢
的是阿基里斯,而非那些双腿打颤却“强迫自己”站稳的可怜士兵。
(“勇敢”一词曾带有这种尼采式意蕴,但现在多少沾染些亚里士多德所
谓的“勇气”的含义。)换而言之,勇敢并不是对情感(即恐惧)的克
服,它恰恰是由不可抗拒、巧妙“协作”且指向明确的情感构成,不仅没
有排斥,反而整合了人的荣誉感,还可能因为其专注感而被解读为冷
静。激情的德性,就在于它的这种力量、效率和有效性,而不是这种仅
是表面化的冷静。
类似的分析,对于慷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称之为“赠予
的德性”)也是可能的。它不是单纯的付出,也不是付出的习惯。让我
们在当前盛行的慈善背景下来考量慷慨吧,这种慈善要求:“捐到心疼
为止!”人们可以设想这样一个捐赠者,他苦苦地与自己的吝啬作斗争,反反复复掂量着良心的负担与街上酒店里打折的贝夫堡红酒孰轻孰
重。最后,慷慨克服了阻力,德性得到了极好展现。但是要注意,首
先,一个人越是挣扎,德性就越少。亚里士多德认为,实际上,一切德
性的实现都是快乐的,而不是痛苦的;这本身就是对某人是否有德性的
一个检测。然而,可以设想一个人的慷慨在于我们称之为“流溢”的本
性。我听说,米克·贾格尔(Mick Jagger)在巡回演唱就是这样。他钱
多得自己(或任何人)都不知道怎么花,于是乐得自由撒钱,不管领受
者是谁,理由得当与否,他都不分青红皂白地给予。人们可以认为,这
种快乐的抛弃行为是真慷慨,无须为个人的损失而挣扎,只有一种随充
满感而来的流溢。
因此,其他德性也呈现为伟大灵魂的精神的“流溢”,是一个丰盈者
的“流溢”。若认为德性并非如此,而是与自利和个人需要相对的义务
感,那就倒退到了尼采所谓的病态德性的模型,即康德和基督教那里呈
现的模型,其中精神贫乏者(而非富有者)成为了关注之所在。为贵族
写作的亚里士多德,可谓介于两者之间。但是,尼采式德性的首要构成
因素是一种激情的充盈,一种独立世界顶端的俯视感。有这样一种伦理
观,就不必对金钱、声誉和权力念念不忘。穷困潦倒、不被学术同行所
注意且身体状况极其糟糕的尼采,就是一个恰当的例子。实际上,甚至
是节制(上述解释最易想到的反例)都代表着一种充盈,一种轻快的自
律感。对此,想想尼采关于饮食、健康和创造性幸福的诸多带有加州风
格的评论就知道了。
这种新伦理学的关键,就是“流溢”和丰盈处于核心位置。尼采在他
的著作中到处都运用了这样的术语和形象。不过,接下来让我们对这些
术语所指向的画面稍稍加以充实吧。在尼采看来,美好生活并不在于谦
逊(最低意义上的“满足”,拥有所需要的一切),而在于活力勃发、激
情、情爱,或是尼采常以那个世纪的哲学风格所说的“生命”。唯有拥有
充足的资源(很可能这些资源全是精神性的),一个人才能发展出“风
格”(遵守纪律,而非追随时尚)和“深度”,用美国习语来说,就是“有灵魂”,它意味着复杂、纷争、好胜的“酒神精神”。如果尼采有一种形
而上学(而且称之为“权力意志”不会完全令人误解的话),那它也是一
种非常现代的形而上学,是一种能量而非物质(或者可以说是“非物
质”)的形而上学。它会是一种动态的形而上学(与通常所谓的“过程哲
学”迥然有别),一种可以称得上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之名的形而
上学。尼采在其最后的著作《瞧!这个人》(Ecce Homo)中说“我是炸
药”,此时,它展现的既不是即将来临的精神失常的征兆,也不是“反
讽”,甚至也不是在放肆宣称自己哲学的潜在效应。他是在以一种独一
无二的恰当隐喻概括其哲学,并使之个性化。论诸德性的优点
既然灵魂的状态有三种:感情、能力与人格状态,德性必是其中之
一。[但是]德性与恶习不是感情。因为首先,我们并不是因为我们的感
情,而是因为我们的德性或恶习而被称为好人或坏人的。而且……我们
被称赞或谴责也不是因为我们的感情。其次,我们愤怒或恐惧并不是出
于选择,而德性则是选择的或包含着选择的。同样由于这些原因,德性
也不是能力。因为首先,我们不是仅仅由于感受到这些感情的能力而被
称为好人或坏人,而被称赞或谴责的……因此,既然德性既不是感情也
不是能力,那么它们就必定是人格状态。
——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
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及其对德性的关注,优点在于他的叙述较为具
体和丰富,并以自己的方式把生活的激情融进了美好生活的本质之中,而没有把生活的复杂性简化为一个“干瘪的”原则问题或理性论证或“最
大多数人的最大善”。但什么是德性呢?如果德性不过是抽象原则的个
人实现——履行义务的倾向或出于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善行动——那么伦
理学就会再次变得干瘪和逻辑化,缺乏个人和情感色彩。52我要试图表
明的是,德性伦理学可以有完全不同的设想,而上述这种简化的做法极
不恰当。
但是,甚至在亚里士多德那里都有一种强烈的倾向认为,激情是极
度自发、甚至是“刺激——反应”的方式,好像情感不同于德性,只是对
具体情形的反应而已。确实,它们看起来可能是这样。根据亚里士多德
的说法,德性是极其语境化的。实际上,如何确定德性是德性,取决于
其语境。在战士、政治家和艾滋病患者身上,勇敢的意义各有不同。一种语境下的德性在另一种语境下,可能就是恶习了,比如对贫困者的慷
慨(亚里士多德的“大方”)就与对宠坏的孩子的慷慨截然对立。在对德
性的定义中53,亚里士多德强调德性是一种“人格状态”,但是,在同一
本著作的其他地方,他又强调“知觉”和具体情形的重要性。而且,恰如
亚里士多德自己清楚的那样,绝大多数激情(和情感)并不是热情或愤
怒的随意爆发。情感多少具有一定的系统性,因为它们一起形成了一个
人的“性格”。当一种不寻常的情感“爆发”出来时(同样,可能是陷入热
恋或者对新生儿全神贯注的疼爱),这种情感不该被理解成一种纯粹
的“爆发”,而是一个激烈的重新构成,如果确实可以相信这种情感的
话,那可以说它重构并重新定义了个体的生命。
有人极力主张德性是一种品格状态而不是一种激情,但这种看法甚
至不适用于亚里士多德德性清单上的首要德性——勇敢。无疑,在阿基
里斯的情境中,勇敢是日常必需。而在今天,要求或推崇身体勇敢——
尤其是亚里士多德视作典范的战场上的勇敢——的情形极少。因此,勇
敢看起来就会是一种“爆发”,或突如其来的英雄行为或正直行为,而不
像是一种持续、显著的人格状态。但是,我们会因此否定勇敢作为一种
德性的地位吗?不会,即使这种勇敢显得愚蠢,也不会减损其作为一种
德性的地位。勇敢地挺身阻挡持枪的街头抢匪或青年帮派,通常(至
多)会被当作愚勇而非勇敢,但尽管如此,这也不会减弱这种行为的德
性,而且也不能仅仅将其当作一种“爆发”,而应把它看成某种“内心深
处”、长久潜藏的东西的呈现,甚至可以说是一个不一样的自我的呈
现。
爱确实可以是愚蠢的,但它也常常(实际上典型地)被认为“与个
性不符”。在爱中受挫折,最好的情形会让人变得高贵,糟糕的情形则
让人感到羞辱或陷入悲剧境地,但是,不愿去爱或没有能力去爱,则意
味着一个人不足以为人。尽管许多哲学家坚持道德是一个理性问题,德
性不同于激情,但情感在我们的道德世界中,仍保有一个基本位置。注释
1.这里所指涉的经典文本是A.J.Ayer所著的Language,Truth and
Logic(New York:Dover,1952)。
2.见伯纳德·威廉姆斯的著作Shame and Necessity(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7)。
3.见萨姆·基恩的著作The Passionate Life(New York:
HarperRow,197x)。
4.例见我的论文A More Severe Morality:Nietzsche's Affirmative
Ethics,收录于拙著From Hegel to Existentialism(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8)。另可见Lester Hunt的作品Nietzsche and the
Origin of Virtue(New York:Routledge,1991)。
5.我对这一点的澄清,要归功于乔治·谢尔(George Sher)提出的好
问题。
6.“燃烧”和“荒废”的隐喻取自尼尔·扬(Neil Young)。这种隐喻的
类似版本可见《旧约》、亚历山大大帝、英国和德国的浪漫主义诗人和
瓦尔特·佩特(Walter Pater)。
7.无疑,这些行为存在着神经生理学的解释,比如,可能是因为蓝
斑之类的脑干区异常,又或是去甲肾上腺素血清促性腺激素之类的化
学物质不足或过剩。我不怀疑,大部分“激情的生活”是慢性疾病而不是
教养的结果,但是,问题——如果我们不回避德性是否必须是“人所控
制”之物这样的问题——在于激情的生活是否能被当作有德性的生活,如果可以,那这种生活的德性可能是什么。
8.其中的一些论题,见伯纳德·威廉姆斯的文章Morality and the
Emotions,载于其作品Problems of the Self(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 Press,1973),不过,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及后来的尼
采,早就谈到过这些论题。
9.我要把这种对于德性的洞见与当今对于这个术语充满争议的使用
明确区分开来。在Bill Bennett的Book of Virtues发表一个世纪之前,尼
采曾这样谈及德性:“而且有这样一些人,他们认为说‘德性是必需的’这
样的话是一种德性;然而根本上他们只相信警察是必需的。”见由
W.Kaufmann翻译的Thus Spoke Zarathustra(New York:Viking,1954)
中的第二部分On the Virtuous,第207页。
10.见菲利帕·福特的文章Virtues and Vices,载于其著作Virtues and
Vices and Other Essays(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1978)。这
种对亚里士多德的看法有些牵强,例见倪德卫(David Steward
Nivison)比较亚里士多德和孟子的优秀论文Mencius and Motivation,载
于Journal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Religion(September 1979)关于传
统中国哲学的特刊,第419页。
11.译者注:原文为eviscerated man(被掏空内脏的人),暗指善于
约束或控制自己的情感的人。
12.特别见R.J.Hollingdale翻译的Daybreak(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2)。
13.具体见Amelie Rorty的著作Explaining Emotions(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0)。
14.见伯纳德·威廉姆斯的著作Ethics and the Limits of
Philosophy(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5),第9
页。参见David Ross翻译的亚里士多德作品Nicomachean
Ethics(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54)第三卷。威廉·弗兰克
纳(William Frankena)并非德性伦理学的拥护者,但他主张德性无非是服从理性原则的倾向,由此清除了这一值得研究的主题。
15.见赖尔的著作Concept of Mind(New York:Barnes and Noble,1949)。
16.例见O.H.Green的文章Emotions and Belief,载于American
Philosophical Quarterly Monograph,1972年第6期。
17.当然,一种新的不同“品格”可能因失常而显露出来,比如坠入爱
河或因新生儿的到来而情绪失控。尽管如此,德性仍在于拥有这种情
感,而非随后显现的品格倾向。(“此前我不知道他有这样一种情
感。”)
18.见Barbara Herman的著作The Practice of Moral
Judgment(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3)。
19.这里我要提到的不仅有伟大的苏格兰道德学家,著名的有大卫·
休谟和亚当·斯密(他比其同事弗朗西斯·哈奇森和沙夫茨伯里勋爵更注
重情感),还有卢梭,他在其教育论著(比如《爱弥儿》[Emile])中强
调了自然情感的重要性,这里的自然情感是相对于那些常常被称为理性
的“不自然的”、“败坏的”算计而言。在此,或许可以对我们所熟知的西
方观点与中国古典思想做一个有趣的对比。因此,儒家学者杜维明区分
了教化的人类情感与纯粹的“自然”情感,由此倒转了苏格兰学者对道德
情感自然性的强调。见杜维明的著作Centrality and
Commonality(Albany:SUNY Press,1989)。
20.比如,即使爱是德性,也可能在有些情形中会显得愚蠢荒唐,当然,人们会反驳“爱有时会是邪恶的”这样的说法。当然,邪恶的激情
的确存在着,但也许不应被称之为“爱”(而应被称作“迷恋”)——比
如,《呼啸山庄》(Wuthering Heights)中的希斯克利夫(Heathcliff)
对凯西(Cathy)的毁灭性激情,似乎就像这种情形。然而,我们可能坚持认为,即使爱有时显得愚蠢或具有毁灭性,它仍可以是一种德性,就像即使正义会带来灾难,我们仍坚称正义是一种德性,或者诚实导致
的结果可能比一个完全“善意”的谎言带来的结果要糟糕得多时,我们仍
坚称诚实是一种德性。但另一方面我想,我们要在德性行为中间做一些
细致的区分,补充其他一些独立于德性说法的标准。我这里的澄清要感
谢罗伯特·奥迪(Robert Audi)提出的好问题。
21.孔子在强调我们所谓的“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时,反复提到仁者
的“精湛技艺”(编注:在英文翻译时,“仁”常被译为virtuosity,这个词
实际上指“精湛技艺”)。精湛技艺一词是音乐中的常见用语,这绝非偶
然,而且,既然孔子明了音乐在生命中的核心位置,“精湛技艺”就不是
一个误译。
22.见内哈马斯的著作Nietzsche:Life as Literature(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5)。
23.我要说,对“权力意志”毫无根据的过度强调,主要来自海德格
尔,他几乎一点也不尊重文本,使用起来过于随意。在英美学界,瓦尔
特·考夫曼在其《尼采》(Nietzsche,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53)一书中对这一概念有详尽阐述,使得尼采至少
在一个仍然反纳粹、重实证的哲学世界里得到了尊重。不过,这种解释
所依据的主要文本,是尼采未出版的笔记,不过这个比较可疑。因为这
个概念本身就带有太多叔本华式的意志味,而这恰恰又是尼采一直努力
摆脱的东西。确实,尼采在其伦理学著作中大量运用了力量、健康和权
力这些隐喻,他也的确认同用权力去纠正享乐主义中存在的明显缺陷,回应极端的宗教行为(尤其是禁欲主义)所引起的心理学之谜。但我相
信,将权力意志——或任何类似之物——设想为尼采整个哲学的生长
点,是一个严重的解释错误。(关于“重构”这样一个“体系”的天才尝
试,见John Richardson的著作Nietzsche's System[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关于对由他人编辑的尼采那本名为《权力意志》[The Will to Power]一书的过度使用和滥用的质疑,见Bernd Magnus
的作品Author,Writer,Text:The Will to Power,载于总第22期、1990
年第2期International Studies in Philosophy,第49——57期。)
24.见戈雅的著作Caprichos(1797,New York:Dover,1970)。
25.见由John T.Goldthwait翻译的Observations on the Feeling of the
Beautiful and the Sublime(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60)。这个早期观点与这部分开头援引的略带讽刺的说法
schmelzender Theilnehmung(温存的同情)形成了鲜明对照。
26.见Bernard Gert的著作The Moral Rules(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8)。
27.从对行动和品格的关注到对感情的关注,这种转变可以说在18
世纪的欧洲就已发生,最明显的是卢梭的著作,当然也体现在道德情操
理论家的著作中。茱莉亚·安纳斯(Julia Annas)提到一个反对激情的古
老论点,认为激情会导致过度。但是,“过度”指的是什么呢?这里的问
题难道不就在于“过度”的可欲性吗?如果“过度”指的就是坏的行为,那
么功利主义和德性伦理学就有充足的理据来谴责这种行为。但是,如
果“过度”指的是激情本身,那么古代的论点就回避了问题实质。我主
张,在一定的意义上,激情本身就是善。倘若如此,激情的“过度”就是
不可能的,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言,德性的过度是不可能的一样。
28.不过,这并不是要否认爱可能会有不恰当的对象。柏拉图预示
了这一点,他坚持认为,爱(eros)不能仅仅是欲望,而必须是对善的
欲望。通俗来说,我认为他的意思是,一个人不能因某人的邪恶特性而
爱这个人。这种观点与当下盛行的见识截然不同,比如在许许多多的电
影中,都会有一个道德堕落的人被认为“爱上”了另一个人,而且正是因
为前者的道德堕落才爱上的(比如裘德洛·德·拉克洛[Choderlos de
Laclos]的书信体小说《危险关系》[Dangerous Liaisons]的几部电影改编,例见1988年史蒂芬·弗雷斯[Stephen Frears]执导、格伦·克洛斯[Glenn
Close]和约翰·马尔科维奇[John Malkovich]主演的版本)。这一说明要归
功于罗伯特·奥迪提出的难题。
29.见Edward Sankowski的文章Responsibility of Persons for Their
Emotions,载于Canadian Journal of Philosophy,1977年第7期,第829
——840页。
30.见丹托的文章Basic Action,收录于其著作Analytical Philosophy
of Action(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3)。
31.尼采把这一观点发挥到了极致,认为德性不仅是特殊的——即
有特殊的对象——而且在种类上也是特殊的,德性是有德性的人独有
的。
32.例见威廉姆斯的Morality and the Emotions一文。
33.见罗蒂的著作Explaining Emotions。
34.这不是一个先天论证,而且在经验中有许多显而易见的反例,比如猛增的离婚率。但是,爱常常会结束这一事实,并不有损于如下论
点:爱是一种情感过程,会随着持久的亲密、熟悉、了解、理解和共同
经历而愈益(或能够)加强和“加深”。对这一过程最为诗意的描述,是
司汤达(Stendhal)所描写的“结晶化”,借此,被爱之人会积累越来越
多的魅力和德性。见C.K.Scott-Moncrieff翻译的司汤达作品On
Love(New York:Liveright,1947),第28——34页。
35.见L.W.Beck翻译的康德作品Lectures on Ethics(Indianapolis:
Bobbs-Merrill,1963),第164页。
36.萨特有些搞混了这一简洁的主张,因为他坚持认为在性行为
中,我们试图把他人变成纯然的性主体——甚至变成纯然的性对象——但我们必定不会成功。见由Hazel Barnes翻译的Being and
Nothingness(New York:Simon and Schuster,1956)第三部分中的
Concrete Relations with Others。
37.见Alan Goldman的Plain Sex一文,载于Philosophy and Public
Affairs第3期第6页。艾伦·索布尔(Alan Soble)在他的《爱的结构》
(The Structure of Love,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90)中
对爱的存在论有详尽论述。
38.见John Milton的文章On Marriage and Divorce,收录于Robert
C.Solomon与Kathleen M.Higgins合编的The Philosophy of(Erotic)
Love(Lawrence: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1991),第79——84页。
39.见拙著About Love(Lanham,Md.:RowmanLittlefield,1994),第二章。
40.“强度”一词过于单维和量化,而且常常与生理上的兴奋相混淆
(且以后者来衡量)。但是,最强烈的激情可以是“平静的”(休谟
语),而最琐屑的怒气也可以是“暴烈的”(休谟语)。
41.对此,我在About Love的194页有详细辩护。
42.在《道德经》中,有这样的区分:热爱生活且完满地生活的
人、热爱生活却未能完满地生活的人,以及过于热爱生活以致过于强调
死亡的人。在这一方面,老子或许可以与伊壁鸠鲁做一个有趣的比较。
见由Stephen Addis和Stanley Lombardo翻译的老子著作Tao Te
Ching(Indianapolis:Hackett,1993)。
43.在《狗的秘密生活》(The Hidden Life of Dogs,Boston:
Houghton Mifflin,1993)中,伊丽莎白·马歇尔·托马斯(Elizabeth
Marshall Thomas)对比较神经学一个广为人知的发现进行了反思,狗的大脑有自我平衡的“牵引”,因此能够平静地休息,两眼凝视如禅定,以
至于我们与它们生活在一起都会认得和喜爱这种表情,但是,灵长类动
物的大脑受到的“牵引”,是以这个词在反主流文化中呈现出来的意义上
说的,即过度刺激的“牵引”、永不停息的躁动的“牵引”,以及人本身
的“牵引”。弗洛伊德错误地把自我平衡模式用于人类灵魂(要是他论及
的是狗的话,就对了)。
44.见Kathleen M.Higgins的著作Nietzsche's
Zarathustra(Philadelphia:Temple University Press,1987),第ix——x
页。
45.这个说法出自尼采写给保罗·李(Paul Rée)的一封信。见A
More Severe Morality:Nietzsche's Affirmative Philosophy一文,收入在拙
著From Hegel to Existentialism一书中。
46.例如,“对哲学的唯一批判就是……证明某事,主要是试着看看
一个人是否能够按照哲学来生活,这在大学里是永远学不来的:大学里
教的永远是用一种话语来批判另一种话语”。见由R.J.Hollingdale翻译的
尼采作品Untimely Meditation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2),第八章,第187页的Schopenhauer as Educator。
47.见Bernd Magnus,Stanley Stewart和Jean-Pierre Mileur的著作
Nietzsche's Case:Philosophy asand Literature(New York:Routledge,1994),以及内哈马斯的著作Nietzsche:Life as Literature。我自己论点
的阐释,见我的Nietzsche Ad Hominem,Perspectivism,Personality and
Ressentiment一文,收录于Bernd Magnus和Katheleen M.Higgins合编的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Nietzsch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6)一书中。
48.语出品达(Pindar)。引自W.Kaufmann翻译的Gay Science(New
York:Ramdon House,1968)。49.事实上,“超人”只出现在《查拉图斯特如是说》的开头,它在尼
采哲学中并没有实质性的地位。
50.明显的例子见Skirmishes of an Untimely Man一文,收录于
W.Kaufman翻译的Twilight of the Idols(New York:Random House,1968)一书中,特别是§§49-50。
51.见荷马的著作The Iliad,xv,348-351,以及亚里士多德的著作
Nicomachean Ethics第三卷第八章(1116)。罗斯(在对亚里士多德的
翻译的一个脚注中)指出,这一引文更像是在描述阿伽门农
(Agamemnon)而不是赫克托耳(Ethics 17.68);另见亚里士多德
(1117):“激情有时也被认作勇敢……因为激情首先就是冲向危险的
渴望……”因此,荷马才说“他的激情充满力量”。亚里士多德更进一
步,认为出于激情而行动的人并非真勇敢,倒是更像野兽。他们行动不
是“为了荣誉,也不是在规则的指引下”(同上)。尽管如此,他仍补充
说:“他们拥有某种和勇敢类似的东西。”
52.例见T.M.Scanlon的著作What We Owe to Each
Other(Cambridge,Mass.:Harvard,1999)和Simon Blackburn的杰出
评论,发表于1999年2月21日的The Washington Post书评部分,第24版。
53.见亚里士多德的Nicomachean Ethics,第二卷,第五章。第二章 情感的政治
灭绝激情和欲望,仅仅为了预防它们的愚蠢以及这种愚蠢的不快后
果,这在我们今天看来,本身就只是一种极端的愚蠢。
——尼采,《偶像的黄昏》
哲学家常常把“理性”与“激情”对举,典型的做法是捍卫前者而反对
后者,并主张哲学本身即理性之爱。这至少意味着,哲学倾向于对激情
置之不理。几乎在任何一本入门性的逻辑学教科书和伦理学著作里,都
会把“诉诸情感”当作一种“非形式”谬误列举出来,或许用不着不惜代价
去避免它,但至少要在学期论文中躲开它。哲学被重新定义为对论证的
阐述和批判,这是理性的专属领域。“激烈的”论争寻常可见,但仍被认
为不妥当。不带感情的分析受到鼓励,而激情的辩护被压制。哲学或许
仍被忠实地描述为智慧之“爱”,但这种爱几乎不再有苏格拉底(如果不
是柏拉图)处理这一主题时所具有的那种饱满热情了。于是,今日的理
想,即便不是后现代犬儒主义的那种深思熟虑的无欲(apatheia),也
是一种冷静,一种沉思的超然。激情的生活几无显露的机会。
即使我们发现一位伟大的哲学家为激情辩护,反对过分提倡理性,结果也难有教益,反倒是弥漫着一股怀疑主义味道。最著名的当属大卫
·休谟,他认为“理性是而且应当是激情的奴隶”,直截了当地摒弃了视
伦理学为理性事务这一漫长的传统。但他这样做,至少暗示了——当然也为他人设置好了舞台去讨论——这样的观点:道德在理性的把握之
外,并且在某种基本的意义上是不可争辩的。通过把理性和激情并举,休谟实际上与历史上一长串的哲学家一样,把情感与理性对立起来,并
使二者分离。休谟仅仅是倒转了这个对立而已。笛卡尔及其同胞马勒伯
朗士(Malebranche)曾根据生理学的“精气”(animal spirits)来分析情
感,并明确把它归为心灵的低劣部分——如果它确实属于灵魂的一部分
的话。(休谟同样也使用了这个术语。)莱布尼茨(Leibniz)认为情感
是“含混的知觉”,而康德则把它当作“病态的爱”(作为一种情感的爱)
不予理会,并把它与《圣经》和实践理性所控制的较为适当的爱区分开
来。康德或许也说过,“若无热情,就不会有伟大的成就”(通常认为这
个说法出自黑格尔),但很显然,在他对更高人类能力的宏伟“批
判”中,热情本身微不足道。
我们要谈论的“情感的政治”,正是基于这种最粗浅的理解。哲学史
上,情感多数时候被当作灵魂里头的游民无产阶级(lumpen
proletariat),在生产经济中没有什么作用,却依然是需要为之恐惧的负
担和危险,应尽可能有效地被控制。情感的政治否认它们的正当性和重
要性,由此表明对它们的压制和忽视的合情合理。现在,就让我们开始
考量一下这个以哲学的“干瘪”之名发动的“政治”运动吧。被贬损的情感
道德家的疯狂在于其要求的不是控制激情,而是根除激情。他们的
结论永远是:唯有柔弱者是好人。
——尼采,《敌基督者》
“道德家的疯狂”在当今的哲学文献中依然存在。让我举两个例子来
说明一下,一个是我们最卓越且思想开放的一位道德哲学家最近的演
讲,一个是一位知名心灵哲学家的论文。
在就任美国哲学协会(太平洋分部)会长的演说中,乔尔·范伯格
(Joel Feinberg)问道:“在处理实践伦理学的问题上,诉诸情感若有用
的话,那它的用处何在?”1他以通常的回答开头:“对这一问题最唐突
的回答是‘没有任何重要性;情感是一回事,论证是另一回事,而且没
有什么比情感更能蒙蔽心灵了’。”(19页)范伯格拒斥了这种“唐突
的”回答,但他的结论绝不是热心地认同情感;他承认,感情在伦理学
中是“相关的”,或者说至少不是毫无关联的,他得出结论说:“在有效
的人道主义与在灵活控制下对人类基本情感的维持之间,没有处理不了
的冲突。”好像这样说还不够谨慎似的,他补充说:“我希望这个结论不
是太过乐观。”(42页)
范伯格对情感在伦理学中的位置的仔细分析,值得进一步展开来仔
细回应,但这里我只想提醒大家注意,他在被迫提出他那个“乐观的”论
点——情感在伦理思考中并非完全不相关——时,是极其谨慎且带着防
备心的。请注意,为了给情感腾出一丁点儿空间,他要费多大的劲儿
啊,比如就好像说,在争论堕胎问题时,一名孕妇对自己身体、胎儿、“道德”和声誉以及她对胎儿父亲和自己人生规划的感受不过是些私
人轶事,只会转移主题,而哲学家们关于胎儿的地位和权利以及妇女控
制自己身体的(抽象)权利的论证,是唯一正当的关注所在。无论这种
伦理学的利弊何在,其重点都完全集中于原则以及支撑它们的论证,而
情感对于我们的道德思考没有任何值得一提的贡献。2
第二个值得提及的例子是杰罗姆·谢弗(Jerome Shaffer)发表于
1983年的《一个关于情感的评估》(An Assessment of Emotion)一
文。3谢弗以一个关于“情感遭际”的例子开始:“我沿着弯道行驶,看见
路上横着一根木头。我认为它可能对身体造成伤害,而我不想如此。我
脸色发白,心跳加速,胃在收紧。我猛地踩了刹车。”4毫不意外的是,谢弗用这个以及类似的情感例子得出结论说,情感不是特别令人愉悦或
有价值的经验,因此“对于生活的主要关切而言,既无必要,大体上也
不可欲”。5稍作反思就可以认定,这种无人乐于见到的惊慌情形,完全
不可以当作情感的典范。实际上,人们可以反驳说,惊慌不是一种情
感,尽管它的心理活动与某些情感类似。无论如何,并非所有的情感能
用“脸色发白、心跳加速、胃在收紧”等等来描述,更不用说定义了。想
想,若用我们的主要例子,比如正义得以伸张时感受到的强大满足感,或者可能长达数十年充满激情的恋爱经历,就会出现截然不同的分析。
(谢弗在同一篇论文中对作为情感的爱分析时,把爱简化为“小鹿乱
撞”和“波动、过电、汹涌或充血”,由此得出结论说,爱不过是一种没
有什么价值的情感。这绝不是打动特里斯坦[Tristan]和伊索尔德
[Isolde]的激情。)此外,我们乐意赞成,道路中间横着一根木头并
不是一种可欲的经历,但也不必由此得出结论说,恐惧本身是一种不可
欲的经历。6实际上我们知道,在较为安全的环境下,数百万的人愿意
排队付上十美元让精心设计得千奇百怪的自然和非自然现象吓破胆,这
些现象包括龙卷风、食人鲨、大猩猩、侏罗纪克隆动物、各种火星人和
其他外星人、飞木、流动的岩浆和杀人狂。
事实上,谢弗的情感“评估”是一次政治诽谤,不过他进行论证时的油滑方式,也表明了情感的政治地位之低。我们可以想象这样一种情
形,一位哲学家在同样专业的期刊上发表一篇评估逻辑的论文,其中以
一个荒诞的诡辩作为典型案例,并由此得出结论说逻辑在我们的生活中
并不特别重要或并非可欲的。可是,哲学中针对情感的偏见过于强大,以至于这样一种不公或轻率的抨击都无法引来抗辩,相反,若是为情感
辩护,无论这种辩护是多么冷静和负责任,都会招来这样的指责:软心
肠的多愁善感。
大体而言,现代美国哲学对情感在哲学中的作用既缺乏兴趣,又极
不信任,我认为这种说法并非夸大之词。(哪怕我们最著名的两位哲学
家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和约翰·杜威[John Dewey]对此有浓
厚的兴趣,也还是如此。)根据盛行的方案来看,哲学家们应当设法保
持理性,而不应充满激情或——甚至更糟——情绪化。哲学家们应该评
价论证,而不应“陷入”某个立场。(我有位同事对正在写内容极易情绪
化的文章的学生们说,他“丝毫也不关心他们相信什么,而只关注他们
的论证是否有效”。)事实上,人们开始怀疑,当今哲学话语获得尊重
的标准,是否就在于没有任何情绪反应。哲学论题必须冷静且尽可能形
式化地加以论证,由此抵消华丽辞藻的魅惑效应,避免诉诸情感。那
么,像克尔凯郭尔或尼采这样的哲学家因为颂赞激情胜过理性,而被不
屑一顾地说成“不是真正的哲学家”,也就不那么意外了。这种为人熟知
的排外政治使情感边缘化,也就进而使推崇情感的哲学家边缘化了。
即使情感确实出现在哲学中,它们的地位也会被认为很次要;对它
们的分析,也只是个附带问题。比如,笛卡尔和休谟堪称典范的情感理
论,就通常被忽视。别的不说,笛卡尔的论著《论灵魂的激情》(On
the Passions of the Soul)包含了他对心灵与身体之间的微妙关系持久不
断的沉思,通常却被撇在一边,人们偏爱的是更诱人的《沉思录》
(Meditations)以及更具方法论性质的《指导心灵的规则》(Rules for
the Direction of the Mind)。学生们会被要求阅读休谟的巨著《人性
论》(A Treatise of Human Nature),但通常只限于第一卷和第三卷,而论激情的第二卷则被排除在外。同样的,阅读斯宾诺莎的学生通常只
到《伦理学》第二卷就戛然而止,而对斯宾诺莎自己无疑认作是整个研
究之核心的三卷论激情的雄文置之不顾。7偶尔也有名为“情感哲学”的
课程,但通常会被认为很古怪很边缘,就像是“新时代哲学302号”或“爱
与性的哲学”这类课程,是那些头脑不清和易于激动的人才热衷的哲
学。
但是,即便在情感确实成了关注焦点之时,处理它的方式常常也太
像如今哲学处理一切问题的那种做法——形式化、客观化、论辩性、无
激情——换句话说,完全与主题本身无涉,甚至与之对立。在这一领域
的大多数著作中,丰富的情感话题被简化为对“意向性”的本性、“认
知”的各种形式、心理范畴的正确理解之类干瘪的逻辑分析。我并不反
对这样的研究,而且觉得其中一些颇为有趣,但是,情感却杳无踪迹。
我这样说并无意冒犯。不过,若认识论的目标之一是增进我们的知识,那么我们情感的“知识价值”似乎应该是一个基本的探究方向。8实际
上,许多关于情感的研究似乎把情感说成不过是“感受”,由此来打发或
舒缓我们的情感。人们确实可以论证说,现代哲学过分强调认识论而忽
视情感,泄露了对于哲学和人性之本性的一个不加批判且很可能错误的
假设:我们首先是认知的存在者,其次或许在病态的意义上才是感受的
造物。从政治上来看,这显然有助于那些善于认知和长于理性的人,而
那些将敏感和激情奉为首要德性的人,则因此而被降低和贬损。(妇
女“较敏感而缺乏理性”的这一传统形象,在政治上看来,并非与这一指
责毫不相干。)何谓情感?(走向一种政治观)
伦理哲学家通过诉诸自己的下丘脑边缘系统的情感中枢,就直觉地
知道义务论的道德准则。
——威尔逊(E.O.Wilson),《社会生物学》(Sociobiology)
“何谓情感?”威廉·詹姆斯一百年前为《心灵》(Mind)杂志撰写
的论文就以此为标题,一字不差地问过。9自西方哲学开端以来,哲学
家们就一直关心且担忧情感的本性。苏格拉底和前苏格拉底的哲学家
们,对于情感在理想人生中的位置,就提出过深刻的问题,只是他们提
出的问题并不一致。尽管这个学科是在追求理性中发展起来的(很大程
度上是因为苏格拉底及其学生柏拉图),但情感一直潜藏在背后,是理
性的一个威胁,对哲学和哲学家而言也是一个危险。或许,这就是为何
关于理性和情感最经久不衰的隐喻是主人和奴隶:其中,理性的智慧牢
牢掌控一切,危险的情感冲动则被安全地抑制住、疏导开,或者更理想
化一点,变得与理性和谐一致。
主奴隐喻显示的两个特征,至今仍决定着许多关于情感的哲学观
点。首先是情感的次要角色,人们认为情感较原始而少理智、较粗野而
不可靠、较危险因而要受到理性控制(亚里士多德和其他开明的雅典人
正是用这一论证来证明奴隶制这一政治制度的合理性)。其次且更为深
刻的,是理性——情感的区分本身,好像我们所涉及的是两种截然不同
的自然天性、灵魂的两个相互冲突和敌对的方面。甚至那些力图整合两
者、想把其中一个简化为另一个的哲学家(典型的做法是把情感简化为理性的劣等类型,即“含混的知觉”或“扭曲的判断”),也坚持这一区分
并继续主张理性的优越性。因此,休谟宣称理性是激情的奴隶,就成了
他激烈反抗传统习见的一个标志,但就算是对情感结构有着天才分析的
休谟,也没有脱开古老模型和隐喻的窠臼。
“何谓情感?”这个问题——说白了——不只是一个理论问题,也不
只是对情感取得一种充分理解或解释的尝试。它首先是一个实践问题,因为我们摆脱不了情感,且要通过情感来生活。简而言之,我们的情感
就是我们的生活。在同样的意义上,我说一个人必须活在婚姻中并且通
过婚姻而生活,而仅仅理解“婚姻:制度、历史以及相关的法律、相关
的奇异趣事和不寻常的案例……”是不够的。从这样一个切入点来
看,“何谓婚姻”是一个存在论的追问,而不是一个社会学的探讨。实际
上,这里不是在说某个婚姻的特殊性,也不是在探讨某人自己的婚姻。
这就是为何这一问题对于我们如此重要,为何仅有笼统的概念(比如离
婚与复合的数据)对我们没有什么实际助益的缘由所在。但是,在一般
知识与我们生活的具体环境之间的,是理论与实践的相互依赖。如果人
们把婚姻理解为一种个人的、充满激情的承诺,那么婚姻本身就主要由
这样的一种理解构成,如果同样的婚姻被理解为不幸的命运安排,或一
种社会或家庭责任,那它当然会是一个完全不同样子。
情感也是如此,如果人们把情感理解为基本上无意识的生理反应
——比如以研究较多的“惊吓反应”(startle response)为模型——那么人
们就会把自己的情感经验理解为干扰、不幸、疾病的短暂发作或身体的
奇怪颤抖和收缩。10另一方面,如果情感被理解为政治行为或战略性的
社会行为,那么这种理解不仅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人们的情感“观”,还
会影响人们的情感行为和感受。因此,我要主张,一种情感首先是一种
不间断的实践,人们主动与他人一道参与其中。它不单单是一种现象,不只是“某种就这样发生的事”。它不仅是个人的,也是人际的、社会建
构的和习得的。拥有一种情感,无论是承受因它而来的痛苦,还是尽其
可能地发挥它的价值,首先就是一种社会和政治实践,要与他人一起过一种正派、充满激情的生活,就不能缺少这种终极的实践。
这并不是说理论没有位置。相反,我会像反对理性与激情之间的可
恶对立一样,坚定地反对理论与实践之间的有害对立,并且把它看成同
一运动的构成部分。我们时常被告知理论生活就是不带激情、纯粹探究
的生活,然而这不过是个假象,一旦我们了解任何一位严肃的科学家或
学者,就绝不会怀疑他们探索的基本激情,不管怎样描述都一样。11无
论实践受理论驱动,还是理论以实践为导向,把这两者分隔开来都是错
的。我们如何反思我们的情感,必定与我们如何经历它们有关,其中包
括我们如何将它们理性化,如何用它们来对待自身和他人,以及我们如
何用它们给自己的不良行为找理由或借口。12
有鉴于此,我要论证三个否定性的论点,它们对于我在这本书中运
用的情感概念至为重要。第一个也是最为重要的论点是,情感不是感
受;第二个论点是,不管我们可以从人类神经生物学以及相关学科获得
多少知识,情感不是或至少不能被简化为生理现象;第三个论点是,情
感不能仅仅根据个人行为来理解,这里的“仅仅”一词并不是要否认情感
在行为中的表达,也不是要否认情感在某种意义上是个人经历,而是要
否定这样一种可能:在理论或实践上对自己或他人情感的充分理解,可
以不考虑相关的社会背景、文化、社会和人际关系,以及这些条件下行
为的“意义”。也正因为认识到这一点,我才使用“情感的政治”这样的表
述。
人们在完全无害的意义上,常常把情感说成是感受,包括各种各样
的意识,其中最显著的有长期的爱和感情。但是我要否定的那种意义绝
非无害,尽管如尼采曾写到的那样,它是可以“被驳斥的”。这种说法最
著名的捍卫者是威廉·詹姆斯,他主张情感是一系列的感觉(由可指明
的生理骚乱引发,而后者又由令人不安的知觉引发)。20世纪初,詹姆
斯的观点受到坎农(W.B.Cannon,《身体的智慧》[The Wisdom of the
Body]一书的作者)和他的实用主义同行约翰·杜威的质疑,他们指出,我们的全部情感要比我们相对贫乏的感觉复杂和精致得多。13举个
熟悉的例子,羞耻与尴尬之间的差异就无法简单地根据感觉或它们的生
理原因来理解。要理解这一差异,就必须参照社会性灾难发生时感受到
的责任、所处的社会处境和文化。应当注意“感受到的责任”这一表述,因为它不是詹姆斯意义上的“感受”,而是一种观看或理解或解释具体处
境中(一个人自己的)社会行为的十分复杂的方式,这种方式是习得
的。在其他地方,我称这种“观看方式”为判断,并且认为情感正是由这
样的判断构成的。14
或许人们会说,情感是一种感受这种观点非常合理,因为如果一个
人有一种感情,他或她必定在某种意义上感受到它,也就是说,对它有
意识。无须说,在这一点上,有一大堆现象学问题向我们涌来。我们所
用的“意识到”一词是什么意思?它能排除无意识情感的可能性吗?有时
我们被证明自己所谓的感觉错了,也就是说我们所拥有的感情是错的,那么,它能排除这种可能性,或这个明显的事实吗?这种思考削弱了传
统的笛卡尔式主张,即我们能够立即意识到自己的心理过程,包括情
感,因为无意识这个观念——这点弗洛伊德做过辩护,且否认行为这种
我们所熟知的情感伎俩也能证明其存在——表明,我们无法与自己的情
感反应和解,甚至无法“与之接触”。尽管如此,我们仍难以否认笛卡尔
式主张的意义,如果某个东西能算作情感(与纯粹的身体抽搐或机械行
为相对),那么主体对它的意识就是一个基本条件;这可以说是不可避
免的要求。然而,这和威廉·詹姆斯所主张的情感即感受是完全不同
的。
情感可以简化为生理现象的观点,只是偶尔被当作常识论点(而且
通常是作为隐喻)提起。确实,我们长期运用生理学、机械学以及“水
力学”的形象来捕捉情感的机制和感受。15如今,在谈论情感状态时,盛
行的是计算机隐喻(“输入输出”、“过载”、“界面”等等)。但是,人类
情感的生理学模型,或者更确切一点,神经学模型的最重要动力,来自
医疗实践和科学理论领域。整整一个世纪之前,两位医生对他们的同行说,心理学必须考虑新近发展起来的神经科学。威廉·詹姆斯写道:“心
理学家被迫变成了一定程度上的神经生理学家。”大约与此同时,弗洛
伊德把他所谓的“心灵器官”确定为大脑。16今天,我们完全可以理解这
些努力。通过把各种心理疾病“简化”为神经生物学上的功能障碍,神经
病学在过 ......
您现在查看是摘要介绍页, 详见PDF附件(2235KB,39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