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事的本质.pdf
http://www.100md.com
2020年4月10日
 |
| 第1页 |
 |
| 第10页 |
 |
| 第11页 |
 |
| 第30页 |
 |
| 第38页 |
 |
| 第115页 |
参见附件(3524KB,501页)。
叙事的本质,叙事这一词在书中为读者们深刻的进行了解析,无论是关于社会还是生活上,在此书中都会读者奉上了精彩的内容,感兴趣的可以读读!

本书详细介绍
在过去的40年来,一直属于文学专业学生的核心书目,同时也是众多教师、作家及学者们的重要参考文献。本书的作者斯科尔斯和凯洛格将古典时期以来直至20世纪的叙事作品纳入研究视野,为读者梳理出一条令人信服的叙事发展史。他们的主要目的在于描述并分析叙事本质中所包含的重要元素:意义、人物、情节及视角。
如今,这部具有开创意义的著作通过修订与增补而成为其40周年版,当中包括詹姆斯·费伦新增的一篇前言,及其围绕1966年以来的叙事理论发展所书写的一个长篇章节。这部分新加入的内容,描述了叙事研究的各种原理与实践:结构主义叙事学、认知叙事学、女性主义叙事学以及修辞叙事学,尤其关注它们在人物、情节及叙事话语方面的研究。
书籍作者及译者
作者
罗伯特·斯科尔斯(1929一),布朗大学现代文化与传媒研究教授,英语、比较文学及现代文化与传媒名誉教授,安德鲁·W.梅隆名誉人文教授;曾于2004年担任美国现代语言协会(MLA)主席。
译者
于雷,南京大学文学博士,现为南京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系副教授,入选江苏省“青蓝工程”中青年学术带头人;目前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多篇学术代表作刊载于《外国文学评论》等专业领域刊物。作者介绍:罗伯特·斯科尔斯(1929一),布朗大学现代文化与传媒研究教授,英语、比较文学及现代文化与传媒名誉教授,安德鲁·W.梅隆名誉人文教授;曾于2004年担任美国现代语言协会(MLA)主席。
图书章节目录预览
1、叙事传统
2、书面叙事的口头传统
3、现代叙事的古典传统
4、叙事中的意义
5、叙事中的人物
6、叙事中的情节
7、叙事中的视角
8、叙事理论,1966-2006:一则叙事
名人推荐之点评
1、我不知道哪个更精彩:斯科尔斯与凯洛格奠基之作的新版,抑或是费伦继《叙事的本质》之后围绕该领域发生的一切所书写的新篇章。如果有读者问:“叙事理论究竟事关何物?”那么,这部著作便是答案之所在。
2、《叙事的本质》阐明了西方叙事传统。它以令人惊叹的技能将诸多叙事可能性——从萨迦和史诗一直到乔伊斯、普鲁斯特和福克纳的小说——编织在一起。同时,詹姆斯·费伦的新增章节本身亦凭借审慎的姿态与广博的知识,使得这一新版的经典之作获得了其存在的价值与重要意义。
叙事的本质截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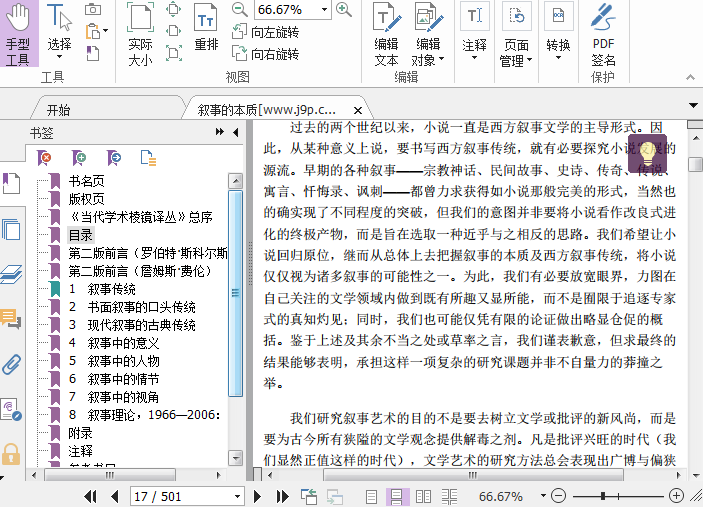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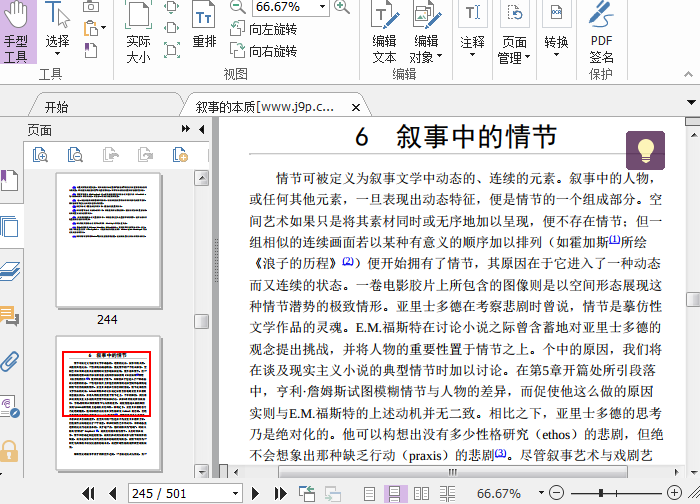
叙事的本质
[美]罗伯特·斯科尔斯 [美]詹姆斯·费伦
[美]罗伯特·凯洛格 著
南京大学出版社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叙事的本质(美)斯科尔斯,(美)费伦,(美)凯洛格著;于雷
译.--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1(2019.1重印)
(当代学术棱镜译丛张一兵主编)
书名原文:The nature of narrative
ISBN 978-7-305-13725-9
Ⅰ.①叙… Ⅱ.①斯… ②费… ③凯… ④于… Ⅲ.①叙事文学-研
究 Ⅳ.①I0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180092号
Copyright ? 2006 b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Inc.
“The Nature of Narrative,Fortieth Anniversary Edition” was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English in 2006.
This transla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4 by NJUP
Throug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江苏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10-2009-105号
出版发行 南京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南京市汉口路22号 邮 编 210093出 版 人 金鑫荣
丛 书 名 当代学术棱镜译丛
书 名 叙事的本质
作者 [美]罗伯特·斯科尔斯 [美]詹姆斯·费伦
[美]罗伯特·凯洛格
责任编辑 谭 天
照 排 南京南琳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印 刷 南京爱德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35×965 116 印张 29.75 字数439千
版 次 2015年1月第1版 2019年1月第3次印刷
ISBN 978-7-305-13725-9
网 址 http:www.njupco.com
官方微博 http:weibo.comnjupco
官方微信 njupress
销售热线 (025)83594756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南大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所购图书销售部门联系
调换《当代学术棱镜译丛》总序
自晚清曾文正创制造局,开译介西学著作风气以来,西学翻译蔚为
大观。百多年前,梁启超奋力呼吁:“国家欲自强,以多译西书为本;
学子欲自立,以多读西书为功。”时至今日,此种激进吁求已不再迫
切,但他所言西学著述“今之所译,直九牛之一毛耳”,却仍是事实。
世纪之交,面对现代化的宏业,有选择地译介国外学术著作,更是学界
和出版界不可推诿的任务。基于这一认识,我们隆重推出《当代学术棱
镜译丛》,在林林总总的国外学术书中遴选有价值篇什翻译出版。
王国维直言:“中西二学,盛则俱盛,衰则俱衰,风气既开,互相
推助。”所言极是!今日之中国已迥异于一个世纪以前,文化间交往日
趋频繁,“风气既开”无须赘言,中外学术“互相推助”更是不争的事
实。当今世界,知识更新愈加迅猛,文化交往愈加深广。全球化和本土
化两极互动,构成了这个时代的文化动脉。一方面,经济的全球化加速
了文化上的交往互动;另一方面,文化的民族自觉日益高涨。于是,学
术的本土化迫在眉睫。虽说“学问之事,本无中西”(王国维语),但“我们”与“他者”的身份及其知识政治却不容回避。但学术的本土
化绝非闭关自守,不但知己,亦要知彼。这套丛书的立意正在这里。
“棱镜”本是物理学上的术语,意指复合光透过“棱镜”便分解成
光谱。丛书之所以取名《当代学术棱镜译丛》,意在透过所选篇什,折
射出国外知识界的历史面貌和当代进展,并反映出选编者的理解和匠
心,进而实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目标。
本丛书所选书目大抵有两个中心:其一,选目集中在国外学术界新
近的发展,尽力揭橥域外学术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最新趋向和热点问题;其二,不忘拾遗补缺,将一些重要的尚未译成中文的国外学术著述
囊括其内。
众人拾柴火焰高。译介学术是一项崇高而又艰苦的事业,我们真诚
地希望更多有识之士参与这项事业,使之为中国的现代化和学术本土化
做出贡献。
丛书编委会
2000年秋于南京大学谨以此书纪念
罗伯特·L.凯洛格
(1928—2004)目 录
第二版前言(罗伯特·斯科尔斯)
第二版前言(詹姆斯·费伦)
1 叙事传统
2 书面叙事的口头传统
3 现代叙事的古典传统
4 叙事中的意义
5 叙事中的人物
6 叙事中的情节
7 叙事中的视角
8 叙事理论,1966—2006:一则叙事
附录
注释
参考书目
索引
致中国读者的话
《叙事的本质》译后谈第二版前言
一部学术著作若能历经四十载而依然再版,乃是件了不起的事情
——特别是那种由几位年轻气盛的小字辈学者所书之作。眼前的这本书
恰恰就属于这种情形。当年,罗伯特·凯洛格和我本人在弗吉尼亚大学
为二年级本科生开设了一门课,计划用一学年的时间讲授从荷马到乔伊
斯以来的叙事文学;而我俩就此课程所进行的数次讨论竟成了此书创作
的最初动因。这门课,我们教过几轮,几乎每天在回家路上均以此为话
题。这本书正是得益于那些授课经历与私下里的交流——当然,也得益
于这一课程本身所要求我们进行的大量研究工作。
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是开设此课程的理想人选。凯洛格当年正是
带着对乔伊斯的极大热情前往哈佛进行研究生阶段的深造。他是个非常
细致的人,当然也顺理成章地选择了中世纪文学作为其最初的研究内容
——一直孜孜不倦。我俩相识之际,他正在专攻古代冰岛文学,但他对
中世纪欧洲文学与文学现代主义有着非凡的功力。而我本人则选择了康
奈尔,其部分原因是,他们的研究生课程将小说作为一种文学类别纳入
研究体系,这在20世纪50年代是相当稀罕的。尽管我的硕士论文和博士
论文主要是探讨20世纪英美小说,但我在深造期间的学习涵盖了小说这
一整体类别,而且我在弗吉尼亚从教时,对于从18世纪英国小说到20世
纪美国小说的授课内容也做到了包罗万象。就我们那个时代的叙事文学
研究来说,罗伯特跟我通过合作而实现的历史视野乃是任何一个人所未
能企及的。(1)
我俩曾一直就合作出书的问题探讨了些时候,后来恰逢我获得威斯
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人文研究中心提供的为期一年的资助,研究叙事文学的历史与理论。这个机会意味着我可以为我们意向之中的携手之作先
行写出一份草稿,而那些因我知识局限所遗留的空缺部分则由罗伯特加
以添补。很久之前,我曾在纽约加登城(Garden City)的几所公立学校
学习过五年半的拉丁文,而在麦迪逊分校,我至少也学了些古希腊语的
基础知识。罗伯特懂得不少中世纪的欧洲语言,而且,我俩也懂好几种
现代语言。尽管我跟罗伯特对俄语都是门外汉,但我在本科阶段曾在韦
勒克(2)
门下修过一年俄国小说的课程。可以说,我们拥有了一定的合作
基础。
在麦迪逊分校,我还得到许多高级学者的智力支持,如研究中世纪
科学的专家马歇尔·克拉格特(Marshall Claggett),还有热尔曼·布瑞
(Germain Breé)——一位研究法国现代文学的学者,他们给予了我极
大的帮助。时任人文研究中心主任的马歇尔·克拉格特问我是否需要中
心提供相关书籍以帮助我的研究。于是,我交给他一份清单,列出一
些“洛布古典文库”(Loeb Classics)(3)
的书目——配有对照英文翻译的
古代希腊及拉丁文学丛书。他思忖了一会儿,终于开口说他认为中心应
该拥有全套丛书。几周后,这套丛书便抵达中心,我亲手帮他将这些书
开包上架。这些书对我的研究起了很大的作用,我可以在英语文本中迅
捷地找到关键段落,然后更加细致地分析希腊和拉丁原文;这样一来,我那业已生疏的拉丁文和差强人意的希腊文总算派上了用场。
于是,我写出自己章节的草稿,由罗伯特进行编辑,而后他也写出
自己两个章节的草稿(关于现代叙事的口头传统及叙事中的意义),由
我来编辑。就是这样,这本书出炉了,最终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差
不多三十五年后,罗伯特跟我碰巧在一次晚宴上相对而席,于是我们就
决定试探一下出版社是否有兴趣出第二版,结果一拍即合。我们随后便
开始策划这件事,但工作进展缓慢,而且后来罗伯特也不幸辞世。他是一名优秀的学者,一个伟大的人,也是一位知心朋友。就我而言,他的
离去也意味着第二版计划的夭折,因为我实在没有心情独自继续下去。
不过,时间的流逝总能多少抚平这样的伤痛,而出版社也保持着极大的
耐心,所以,过了一阵子,我就开始琢磨该如何对这本书进行修订。
许多年后,当我捧起这本书重温的时候,脑海中依然深深印记着当
年那两个毛头小伙勤奋苦读、博闻强记、沉冥思索的模样。他们知道的
东西,如今我已无法知晓;他们思考问题的方式也不再为我所用。这本
书似乎牢牢定格在它自己的时间里,几乎让修订工作成为不可完成的使
命。毕竟,《叙事的本质》曾经为开创叙事学研究做出过自己的贡献,而我本人也在其他著作中拓展了对叙事理论的思考,如《寓幻家》
(The Fabulators)(4)
、《文学结构主义》(Structuralism in
Literature)、《结构性寓幻》(Structural Fabulation)、《寓幻与元小
说》(Fabulation and Metafiction)、《文本的力量》(Textual Power)
以及《现代主义悖论》(Paradoxy of Modernism)等。当然,也有诸多
其他学者曾进入这一领域,在理论和历史研究两方面都创造出丰硕的学
术力作——如巴赫金、托多洛夫、热奈特、巴特以及麦基恩
(McKeon)——这里也只是列举了其中最负盛名的几位。不过《叙事
的本质》依旧在印,而且似乎还能够为叙事学历史与理论提供有效的视
角。当然,这一视角在某种程度上说也是代表了20世纪中期那一特殊的
历史时刻。
结合上述问题的考虑,我委实找不出理由要去重写此书并炮制一个
全新版本。不过,我逐渐意识到这样一个可行的方案:在重新出版原文
本的时候,可以做一些小的文体调整,并且邀请一位年轻学者就初版后
叙事研究的发展写个专题,作为对原书的补充。这就是事情进展的过
程。不过,那位参加该项目的新作者并非毛头小伙,但比我年轻。就我认识的人当中,他对过去几十年来叙事研究领域的发展最具发言权。这
个人正是詹姆斯·费伦(5)。多年来他一直担任《叙事》杂志的编辑;这
是“叙事研究协会”的机关刊物,也是叙事研究领域的顶级期刊。可以
说,没有费伦的合作,《叙事的本质》第二版将不会存在。他追溯了
《叙事的本质》初版后四十年的叙事研究新动向,在我看来,他的工作
做得非常出色。
罗伯特·斯科尔斯
(1) 本书若无特殊说明,页下注释均为译者注。
(2) 雷纳·韦勒克(René Wellek,1903—1995):捷克裔美国学者,20世纪享誉国际的文学
理论家、批评史家和比较文学家。
(3) 西方闻名遐迩的一套大型文献丛书,收录了古希腊罗马时期的典籍,由美国人詹姆士·
洛布(James Loeb)1910年策划。该丛书的特点之一,就是将原文(希腊文、拉丁文)和英文
翻译加以对照编排。
(4) “寓幻(小说)”这一提法因斯科尔斯的相关论著而得名,主要用以代指20世纪以来所出
现的、具有魔幻及后现代特征的反传统小说创作。诸如约翰·巴思和托马斯·品钦这样的作家,均系此文类创作的集大成者。
(5) 詹姆斯·费伦(James Phelan,1951— ):俄亥俄州立大学“杰出人文教授”、国际叙事
文学研究协会前主席、美国《叙事》杂志主编,当今北美最具影响的叙事理论家之一。第二版前言
早在1969年,我还只是波士顿学院一名英语专业大二的学生,正值
年轻气盛;记得在罗伯特·E.莱特(Robert E.Reiter)讲授的一门必修
课上,我首次接触到了《叙事的本质》。而后在1976年,我更为细致地
研读了这本书。当时,谢尔顿·萨克斯(1)
是芝加哥大学“叙事理论”方向的
导师,而我则将这本书纳入自己的阅读书单,作为应对该博士课程专业
考试的准备。在此后的岁月中,我时而会求助于这本书,也会向别人推
荐这本书,但我怎么也没料到斯科尔斯会盛情邀我为该书新版写“一个
关于叙事研究动向的部分”。这简直如梦幻一般——我居然要在伴随我
成长的作品中添加自己的文字。这感觉就如同说,倘若我是小说家,亨
利·詹姆斯或是弗吉尼亚·伍尔芙邀请我为《奉使记》(The
Ambassadors)或《达洛维夫人》的新版创作最后一章。面对这份奖
掖,你准会欣然应允;当然,也难免有几分惶恐和心虚。不过,你还是
想方设法去接手这份工作。而后,当发现先前的某些想法明显不妥时,你又会进行新的尝试,一直坚持到自己最终勉强有东西拿得出手。
在我所做的诸多设想中,有三点我需要在此强调一下。其一,我试
图保留斯科尔斯和凯洛格对文学叙事的聚焦,因为在我看来,要突出
《叙事的本质》与过去四十年来叙事学发展的连贯性,那是最好的办
法。同时我要指出,叙事理论的疆域已有所拓展,它将各种非文学叙事
也纳入其中,并且这种拓展会对文学叙事研究产生影响。其二,斯科尔
斯提出的讨论“叙事研究动向”的要求与我的想法不谋而合。也就是说,从实践意义上看,我并非去追溯1966年以来的叙事历史(后现代实验、数字叙事的出现、传记潮等),而是要提供一则关于叙事理论的叙事,并且在这一叙事中,我会穿插1966年以前及之后的文学叙事案例。我希望,这种运作模式能够让读者看到斯科尔斯和凯洛格作品中的理论部件
与最新的理论进展及观念之间的联系,同时我也能借此获得更大空间去
展现那些发展趋势。
其三,我既非对叙事研究动向进行完全独立的展现,也非妄图化约
出所谓“宏大的统一叙事场论”(Grand Unified Field Theory of
Narrative,GUFTON),相反,我寻求两者之间的中间路线。其原因在
于,若唯前者则势必摆出一副伪装的——而且,在我看来,也是难以维
系的——客观化姿态;若唯后者则会导致该领域的研究视野,以及该场
合下的修辞意旨表现出的一种不该有的狭隘性。当代叙事理论可谓纷繁
多样,因此,一个1966年以来“关于该领域发展动向的章节”不可能创立
出所谓“宏大的统一叙事场论”。当然,正是由于该领域的多样性,要梳
理出过去四十年叙事研究的演化就必须进行相当程度的筛选,而这种筛
选又必然反映出故事讲述者自身就该领域所持的观念,包括其中不同层
面相互联系的方式。结果,当我对自己的设想和筛选心存侥幸之际,我
也格外清楚地意识到,我的叙事并不能终结其他的可能性;而且,我以
为,我的读者们最好也抱有同样健康的意识。
最后,我要感谢戴维·赫尔曼(2)
、布赖恩·麦克黑尔(3)
、彼得·J.拉比
诺维茨(4)
以及罗伯特·斯科尔斯,他们为我的叙事提出了富有裨益的评
价。我也要感谢伊丽莎白·马尔什,她的编审如鹰眼一般敏锐,同时她
也为“引用文献”付出了辛勤劳动。当然,我最想对罗伯特·斯科尔斯深
表谢意,他以包容的信任邀请我在他与罗伯特·凯洛格的地标之作中进
献言论。
在我为此书所作的文字部分中,有些内容曾出现于先前我在《劳特
利奇叙事理论百科全书》(Routledge Encyclopedia of Narrative Theory)
中撰写的词条“叙事的修辞手法”(pp.500—504),由戴维·赫尔曼、曼弗雷德·雅恩(5)
及玛丽-劳雷·瑞安(6)
编(伦敦:劳特利奇,2005)。还
有些内容已经出现于我为《小说百科全书》所撰词条“情节”(pp.1008
—1011),由保罗·斯柯林尔编(芝加哥:费茨罗伊·迪尔波恩,1998)。我谨致谢上述两家出版社应允我将相关内容再次付印。
詹姆斯·费伦
(1) 谢尔顿·萨克斯(Sheldon Sacks,1930—1979):芝加哥大学英语与语言学教授,著名
期刊《批评探索》(Critical Inquiry)的首任主编。
(2) 戴维·赫尔曼(David Herman,1962— ):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英语教授,认知叙事
学研究的重要代表人物。
(3) 布赖恩·麦克黑尔(Brian McHale,1952— ):美国叙事理论家,俄亥俄州立大学杰出
人文教授。
(4) 彼得·J.拉比诺维茨(Peter J.Rabinowits,1944— ):美国汉密尔顿学院比较文学教
授、叙事理论家。
(5) 曼弗雷德·雅恩(Manfred Jahn,1943— ):德国科隆大学英语教授、叙事理论家。
(6) 玛丽-劳雷·瑞安(Marie-Laure Ryan,1946— ):美国叙事理论家、文学批评家及网络
文化学者。1 叙事传统
过去的两个世纪以来,小说一直是西方叙事文学的主导形式。因
此,从某种意义上说,要书写西方叙事传统,就有必要探究小说发展的
源流。早期的各种叙事——宗教神话、民间故事、史诗、传奇、传说、寓言、忏悔录、讽刺——都曾力求获得如小说那般完美的形式,当然也
的确实现了不同程度的突破,但我们的意图并非要将小说看作改良式进
化的终极产物,而是旨在选取一种近乎与之相反的思路。我们希望让小
说回归原位,继而从总体上去把握叙事的本质及西方叙事传统,将小说
仅仅视为诸多叙事的可能性之一。为此,我们有必要放宽眼界,力图在
自己关注的文学领域内做到既有所趣又显所能,而不是囿限于追逐专家
式的真知灼见;同时,我们也可能仅凭有限的论证做出略显仓促的概
括。鉴于上述及其余不当之处或草率之言,我们谨表歉意,但求最终的
结果能够表明,承担这样一项复杂的研究课题并非不自量力的莽撞之
举。
我们研究叙事艺术的目的不是要去树立文学或批评的新风尚,而是
要为古今所有狭隘的文学观念提供解毒之剂。凡是批评兴旺的时代(我
们显然正值这样的时代),文学艺术的研究方法总会表现出广博与偏狭
这两种对峙的趋向。批评的时代是具有自省意识的时代。其倾向表现为
制定规则、试图将艺术化约为科学,分级、归类,并最终评判孰是孰
非。这种理论批评通常基于某些作家的创作实践,其作品之所以成为经
典就在于它们迎合了“经典”之最为鄙俗的意义:循规蹈矩的正统文学实
践范式。此法试图对过去的文学加以化约,筛选出几个“经典”范例;这
无异于构建了一种人造的文学传统。而我们在此书中的目的则是要为我
们称之为叙事的重要文学形式提供一种新思路,纠正以往的狭隘理解。所有那些被我们意指为叙事的文学作品具有两大特点:一是有故
事,二是有讲故事的人。一部戏剧是一个没有讲故事者的故事;剧中人
物对我们在生活中的行动,直接进行亚里士多德称之为“摹仿”的实践。
与戏剧相仿,抒情诗也是一种直接展示,但只有单个演员(诗人或其替
身)在其中吟唱、沉思,或有意或无意地讲话给我们听。若像罗伯特·
弗罗斯特写《雇员之死》那样,再增加一个说话者,我们便接近了戏
剧。若像罗伯特·弗罗斯特写《正在消逝的红》那样,让这个说话者着
手讲述某一事件,我们便走向了叙事。因此,要使作品成为叙事,其必
要及充分条件,即一个说者(teller)和一则故事(tale)。
在西方世界,真正的叙事文学传统的确存在。可以说,所有艺术都
是传统化的,因为艺术家们在很大程度上正是从他们的前辈身上习得技
艺。在创作之初,他们总会以自己熟悉的前人成就为参照,设想各种摆
在自己面前的可能性。虽然他们可能会对传统添砖加瓦,为后人开创新
思路,但不可避免的是,其端倪总发自传统内部。作为读者、评论家或
艺术家,我们越是了解叙事传统的厚度与广度,就越能够在批评或艺术
层面做出更自由、更稳妥的甄别。对于20世纪中叶的读者而言,要想就
叙事传统获取恰如其分的判断,就不得不首先解决一个具体问题,即我
们必须设法避免将小说这一文学形式当作顶礼膜拜的对象。
所有现存的文学传统都具有一个特点,即当代叙事文学会逐渐挣脱
新近历史中的叙事文学。同样,伴随乔伊斯、普鲁斯特、托马斯·曼、劳伦斯及福克纳的出现,20世纪的叙事文学也已经开始了这一分道扬镳
的历程。具体说来,20世纪的叙事已经表现出对现实主义宗旨、取向及
其技法的剥离。而就此剥离所产生的影响,许多有趣的欧美叙事作家依
旧在探索、开发与拓展。不过,从总体上看,我们的评论者们对这种新
文学尚带有敌意,我们的批评家们也未将其提上议事日程,毕竟文学批评也同样受到传统观念的影响。
关于当代批评对当代叙事艺术中许多优秀的成果所采取的敌对姿
态,我们并不打算挑出一个或多个评论者作为例证,但我们倒是可以举
证一位伟大的学者兼批评家,其观点被公认为属于时下文学研究生院
(这里是培养教师、批评家乃至未来评论家的摇篮)中最具影响之列,而其针对现代文学的态度尽管不乏学识和敏锐,却与那种最为世俗的每
周评论有着惊人的相似。这位学者—评论家就是埃里希·奥尔巴赫(1)
,其英文版平装本《摹仿论》(Mimesis)乃是叙事研究领域中两三部最
具人气、最负影响的著作之一。而且,他的研究领域可谓广博:西方叙
事文学。尽管这是一部伟大的作品,但奥尔巴赫对现实主义原理的热心
专注使得他不愿或无法接受20世纪的小说,尤其是像弗吉尼亚·伍尔
芙、普鲁斯特和乔伊斯这样的作家。在他看来,《尤利西斯》就是一
个“大杂烩”,充斥着“露骨而又伤怀的愤世之情,以及令人费解的象征
主义”,并且他还断言,与该小说一样,“大部分其他采用多重意识反映
手法的小说也给读者留下令人绝望的印象。它们常常令人困惑,雾霭重
重,对其所描绘的现实透露出几分敌意”。
奥尔巴赫对后现实主义小说的不满,在二流学者当中引起了共鸣,我们几乎可以在当下文学评论和期刊的每一页上找到这样的不满;在那
里,许多优秀的当代作品不是受到敌视,就是遭遇冷落。目前学界对当
代文学的态度同样也制约着对过去文学的看法。因此,这种用19世纪现
实主义标尺衡量所有小说的倾向自然会妨碍我们理解其他各种叙事。
此“小说性”(novelistic)方法不仅让普鲁斯特、乔伊斯、杜雷尔(2)
和贝
克特深受其害,也使得斯宾塞、乔叟及沃弗兰·冯·埃森巴赫(3)
备受煎
熬。要想找到一种途径,使得叙事研究摆脱小说性方法的局限性,我们
就必须打破那些常用于叙事讨论过程中,诸如时间、语言及狭隘文类划分的条条框框。我们必须考察所有西方世界的叙事形式,在其发展过程
中所共有的要素——口头和书面、韵文与散文、事实与虚构。当然,这
样的尝试绝非空前之举,只是难得一见罢了。
事实上,正是带着这种意图,克拉拉·里夫(Clara Reeve)于1785
年出版了《穿越时代、国家与风尚的传奇之旅》(The Progress of
Romance through Times,Countries,and Manners)。这是第一部真正致
力于研究叙事传统的英文著作。面对传奇在18世纪所遭受的广泛偏见,克拉拉·里夫试图为这种形式构建一个谱系,既突出表明它曾为“古
人”所用,同时又以一视同仁的姿态将其与作为后继形态的小说区分开
来。她的这一区分如今已存留于我们的辞书当中,那些试图对叙事形式
进行甄别的批评家们依然会采用这一划分:
我将尝试这种区分,如果此法得当,不妨从之,——如若
不当,您尽可不为所动。传奇作为英雄体寓言,当以传奇人物
和事件为对象。——小说则是现实生活与风尚的写照,是小说
创作时代的图景。传奇以其崇高雅致的语言描述既从未发生,也不可能发生的故事。——小说则以亲切的口吻讲述那些每天
从我们眼前经过的事情,这些事情既可能发生在朋友身上,也
可能发生在我们自己身上;完美的小说以其闲适自然的方式再
现每一场景,使其可能性达到以假乱真的效果,最终让我们受
到故事人物或悲或喜的情绪感染,仿佛这些就是我们自己的感
受。
除了做出这一清晰明了而又富于价值的表述,克拉拉·里夫还探讨了
——尽管有些流于漫不经心——某些其他叙事类别:形形色色的“新奇
或另类”故事,包括像《格利佛游记》《鲁滨逊漂流记》《项狄传》和
《奥特朗托堡》这样的“现代派”作品;此外,还有另一类包括从童话到《拉索勒斯》(Rasselas)(4)
可谓包罗万象的“传说和寓言”。克拉拉同
时也对史诗与传奇进行了区分,并试图探究像“俄相之疑”(Osianic
Question)(5)
这样的棘手问题。(她在指出《费恩盖尔》[Fingal]
(6)
是“史
诗,而非诗歌”时,有所犹豫,但最终还是将俄相作品划归到传奇当
中)克拉拉明确指出,传奇既可是韵文也可为散文,但史诗以她看来,则必须是诗歌体的。她同时倾向于将史诗看作颂扬之辞;这样一来,一
则真正优秀的诗歌体传奇,如乔叟的《骑士的传说》(此例由克拉拉本
人所举)则该配得上史诗的头衔。
就克拉拉·里夫生活的时代及其所受教育的局限性而言,她的学术
广博与阐释的公允着实令人惊叹。她对“古人”的敬重,以及她对文学成
果的道德评判也为当时的学术前辈们所首肯。实际上,像她那样对叙事
文学进行全面研究的人是很少见的,这种情形也只是到最近方有所改
观;她的博学、平实及睿智,如果能为众多现代书评家们所习得,将会
对他们大有裨益。即使是今天,克拉拉·里夫在1785年遇到的种种困惑
依然对我们具有启发作用。她在探讨过小说和传奇之后,便在梳理其他
叙事形式的问题上陷入了困境——这同样也是现代批评家所无法回避
的。不过,最棘手的还在于她试图对类似“史诗”这种描述性的概念赋以
价值评判。现代批评中产生的一个最大问题,即来自将描述性与评价性
术语相混淆的倾向。比如,“悲剧性”(Tragic)和“现实性”(Realistic)
通常是作为褒义的缀语运用于文学作品。翻开任何一本期刊,我们几乎
都能在书评或剧评的字里行间发现这样的情况。一部正剧可能会因为缺
乏“悲剧性”而遭到叱责。一则叙事也可能由于“非现实性”而一败涂地。
但在我们这个时代,理解叙事文学的最大障碍在于“小说”这个词本身已
经被诸多价值观念所包裹。克拉拉·里夫之所以能够以这样一种相对客
观的眼光去审视传奇的发展,其原因之一,即她所生活的时代先于19世
纪——现实主义小说的伟大世纪。如今,正值20世纪中叶,而我们的叙事文学观却几乎沦为小说中心
化(novel-centered)的无望之境。读者们对叙事文学作品的期望源于他
们的小说阅读经验。他们对于叙事的判断来自对小说的理解。“小说”这
个字眼,一旦用在早期叙事作品身上,就成了褒义词。我们会在书的护
套或封面上看到,诸如乔叟的《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Troilus and
Criseyde)(7)
、杰弗里(8)
的《英国君王史》(History of the Kings of
Britain)和荷马的《奥德赛》这些形形色色的作品都被称为“第一部小
说”。不过,如果我们对这些称谓信以为真,则必然会感到失望。即便
是荷马,一旦被评判为“小说家”,也难免不露瑕疵。
小说中心论对叙事文学研究而言是不幸的,其原因有二。首先,它
将我们与历史上的叙事文学和文化割裂开来;再者,它将我们与未来的
文学甚至今天的先锋创作割裂开来。因此,要重塑历史,要接受未来,我们就必须真正还小说于原位。当然,我们不必为此放弃任何对现实主
义小说的景仰。当小说归其原位,像巴尔扎克、福楼拜、屠格涅夫、托
尔斯泰和乔治·艾略特这样的作家,并不会因此而失去其成就的光鲜夺
目,相反,还可能更加绚烂迷人。
我们不妨记住,西方世界的叙事传统绵延五千年,而小说只占了几
个世纪。当然,小说也拥有两百年的辉煌;无论现代欧洲在其他方面有
过怎样的失败,但就叙事文学的创作而言,她问心无愧;不过,那毕竟
只是五千年中的两百年而已。而我们的研究目的则在于探讨叙事文学的
一些种类,寻找叙事形式在历史发展中的模式,研究叙事艺术当中连贯
的或反复出现的要素,并借此探究这五千年传统中一些具有连续性的线
索脉络。与克拉拉·里夫的任务相比,我们要容易得多。虽然如今的叙
事艺术研究对于广博视野的要求,正如1785年时一样迫切,但这么多年
来的知识积累,业已让我们获得更多的必要研究手段。在过去的一百年中,我们通过各种资料,就文学的史前时期及前现
代文学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认知。那些18和19世纪的文学史家和批评家根
本无法获取的重要资料现在可为我们所用。自弗雷泽(Frazer)的《金
枝》开始,人类学家们便就原始社会中文学与文化的关系给我们提供了
宝贵信息,开创了如杰茜·韦斯顿(Jessie L.Weston)在《从仪式到传
奇》中所展现的文学研究方法。而关于文学如何与个体心理过程相联
系,心理学家们则给我们提供了同样重要的深邃之见(在此,荣格甚至
超越了弗洛伊德),继而造就了一个全新的成功学派——原型批评。此
外,口头文学研究的学子们,如帕里(9)
和洛德(10)
,使我们首次窥见书面
文学与口头文学的差异,以及书面叙事的口头传统。再者,文学研究者
们,如穆赖(11)
、康福德(12)
等古典学者及西奥多·盖斯特(13)
这位希伯来文
化专家也提出方法,使某些新的超文学(extra-literary)知识能够促进
我们对文学的理解。同时,艺术及文学史家,如厄文·帕诺夫斯基(14)
和
小罗伯森(15)
,也让我们对文化先辈的看法与世界观产生了空前的认
识。还有一位杰出的评论界的集大成者——诺斯洛普·弗莱(Northrop
Frye),他向我们展示了如何将文化研究与文学研究结合起来,使我们
空前地接近了一套完整的文学理论。
上述这些学者不仅赋予我们研究手段和学术发现,也为我们树立了
榜样;我们尝试着构建一种理论,尽量言简意赅地阐释叙事形式的种类
及它们如何产生并相互作用的机制。面对摆在我们面前的历史事实,面
对各种经过甄别分类的叙事(这种分类所采取的系统标尺常常相异,甚
至对峙),面对那些约定俗成的诸多“影响”、关联性及一致性,我们努
力做到既研究具体的棘手问题,同时也不忘满足对体系和规律的心理趋
向。而我们的结论正是凭借这样充分周全的探究与考证,得以在后面的
章节中展示。在本章的剩余部分,我们会提供一种“论证”或是注解,以
进行接下来更为细致的说明。作为对我们的叙事传统观进行的最简约展示,它所代表的并非作为一种因果论断以支撑我们的研究,而是我们在
研究过程中所发现的一种模式。
叙事传统当中的形式演化过程,在某种程度上可用生物进化加以类
比。人类由于将自己看成生物进化的终点,便自然会将进化看作是趋向
完美之境的努力。如果恐龙会说话,它也许会持不同见解。同样,一位
当代小说家也会将自己看作改良式进化的极品;但荷马如果能开口讲
话,他可能会反对这种看法。不过,史诗与恐龙均已绝迹。尽管我们可
以合成一部史诗,并做到与原始版本有几分形似,就像我们能够在博物
馆里拼装出恐龙一样,但问题是,原始版本得以产生的条件已不复存
在。大自然在创造那些漂亮的怪兽时所展示的纯真已经消逝,对此,她
绝不会去复原;而叙事艺术家们也无法凭借经验与想象对取自神话和历
史的素材加以真正原初性的组合。
当然,这种进化的类比法是站不住脚的。《伊利亚特》这一奇迹的
伟大之处,恰恰在于它乃是一只活着的恐龙。个体文学作品并不总会绝
迹,只是它们的形式可能会消亡。而它们的繁衍也并非自然选择的问
题。文学的进化在某些方面要比生物的进化更复杂。它是生物过程与辩
证过程的混合体;在这个过程中,不同的物种有时会组合为新的杂交
体,而该杂交体又会与其他旧的或新的形式进行组合;而且,一种原型
(type)会衍生出其预表性类型(antitype)(16)
,而该预表性类型又会与
其他形式进行组合,或与预表性类型的母体进行合成。
就如何对叙事形式进化的复杂运作过程加以规整与展示,很难找到
一种令人满意的途径。这里所提出的方案,乃是在混杂性与系统性之间
达成妥协。它并非模拟叙事艺术家实际的有意识或无意识的心理过程,而是作为一种便捷的方法使此过程能够为我们所把握。其宗旨在于通过
澄清此过程,以展示叙事文学重要形式之间现存的和历史上已存的主要关系。
在西方,书面叙事文学往往出现于相似的条件之下。它源自口头传
统,有一度曾保留了许多口头叙事的特点。我们将它所惯常采用的英雄
体诗歌叙事形式称为史诗。在其背后存在着形形色色的叙事形式,如宗
教神话、准历史传奇和虚构性民间传说,它们已经融合成一种传统叙
事,即神话、历史和虚构的混合体。对我们而言,早期书面叙事的最重
要层面即传统本身这一事实。史诗的故事讲述者说的是一个传统故事。
促使他讲故事的主要动因不是历史性的,也非创造性的,而是再创性的
(re-creative)。他在重述一个传统的故事,因此,他最需遵守的并非
事实,也非真理或娱乐,而是“神话”(mythos)自身——保留于传统之
中,由史诗的讲述者加以重新创作的故事。在古希腊,“神话”这个词的
精确含义正是如此:一个传统故事。
传统叙事在传达过程中必然要传达情节,即诸事件的轮廓。“情
节”这个词的所有意义都在于表明叙事框架。这样,一则神话便是一个
能够得以传达的情节。在亚里士多德看来,作为对行动加以摹仿的文学
作品,其灵魂正是情节(亚里士多德用“神话 ? ?”一词代之)。宗教神话,作为与宗教仪式相关的叙事形式,即一种神话叙事;而传奇和民间传说
在传统意义上也是神话性的,口头史诗亦是如此。在书面叙事史当中,一个明显的重要发展进程,便是逐渐摆脱那种以传统情节讲故事的神话
趋向所主导的叙事。我们可以在西方文学中发现两次这样的运动:一次
发生在古典语言当中,另一次发生在本土方言当中。(17)
在此进化过程
中,叙事文学倾向于朝两个相反的方向发展。这两大叙事分支的发展出
现于传统叙事力量的衰退之际,正确理解这一点对真正领会叙事形式的
进化至关重要。为此,我们必须既考虑这两大叙事分支之间产生分裂的
实质,同时也观照两者的互动与重聚。发端于史诗综合体的这两类背反叙事类别,不妨分别以经验性 ? ? ?
(empirical)与虚构性 ? ? ?
(fictional)加以称呼。两者均可看作是对故事叙
述过程中传统强势加以回避的方式。经验性叙事用对现实的忠实取代对
神话 ? ?
的忠实。我们可以将经验性叙事趋向细分为两个主要构件:历史性 ? ? ?
的(historical)和摹仿性 ? ? ?
的(mimetic)。历史性构件专门对事实之真和
具体历史保持忠实,而不是受制于历史在传统中的再现。它的演绎要求
具备时间与空间的准确丈量方式和以人与自然为媒介,而非通过超自然
手段达成的因果概念。在古代,经验性叙事首先通过其历史性构件得以
体现,正如希罗多德(Herodotus)和修昔底德(Thucydides)等作家那
样仔细地与《荷马史诗》划清界限。而摹仿性构件保持忠实的对象则不
是事实之真,而是感受与环境之真;它依赖于对当下的观察,而不是对
历史的调查。它赖以发展的条件是通过社会学及心理学意义上的观念去
审视行为与心理过程,就像亚历山大时期(18)
的哑剧(Alexandrian
Mime)所表现出来的特点。摹仿性形式是所有叙事形式中发展最慢的
一种。在古代,那些最突出的摹仿性因素不仅出现在狄奥佛拉斯特式的 ? ? ? ? ? ? ? ?
人物 ? ?
(19)
(与哑剧形式对应的叙事)中,也呈现于狄奥克里特(20)
那首现
实主义“田园诗”《阿多尼斯》(即第15首)当中,或是如裴特洛纽斯(21)
在“特里马尔奇奥的宴席”(Dinner at Trimalchio's)(22)
中所描绘的段落。
摹仿性叙事与神话性叙事正相反,因为前者趋向于无情节
(plotlessness),其最终的形式乃是“生活的切片”。传记和自传均为经
验性叙事形式。在传记这一先行发展的形式中,历史性趋向起着决定性
作用,而在自传当中,摹仿性趋向则占据主导地位。
虚构性 ? ? ?
叙事分支,则以对理想的忠实取代对神话 ? ?
的忠实。我们可以
将虚构性叙事趋向也细分为两大构成:传奇性 ? ? ?
(romantic)与教寓性 ? ? ?
(didactic)。小说的创作者既摆脱了传统的束缚,也摆脱了经验主义的
圈囿。他的眼睛所关注的并非外部世界而是读者,他希冀带给他们欢乐或教诲,赋予他们所想或所需之物。经验性叙事着眼于某种真实,而虚
构性叙事则着眼于美或善。传奇的世界是理想的世界,在其中占上风的
是诗性的正义,所有语言的艺术与修饰都被用以渲染叙事。摹仿性叙事
旨在对精神过程加以心理学意义的再现,而传奇叙事则以修辞形式表露
思想。正如这两大叙事分支的总称(经验性和虚构性)所暗示的那样,在叙事文学的天地里,它们所代表的对立性就类似于科学和艺术对于终
极真理的方式之别。在古代,希腊传奇以其修辞化与情欲化之间的协调
性成为传奇叙事的典型。我们可以看出,史诗在从《奥德赛》到《阿尔
戈》(Argonautica)(23)
的演进过程中变得越发文学化和虚构化,直到
出现像《埃塞俄比亚遗事》(Aethiopica)(24)
这样纯粹的传奇。在现代
语言中,从《罗兰之歌》(25)
到克雷蒂安(26)
的《帕西瓦尔》再到《居鲁
士大帝》(Grand Cyrus)(27)
的发展,也表明了同样的演化模式。
至于教寓性的虚构文学类别,我们可以称之为寓言 ? ?;如果说传奇由
美学趋向操控,那么寓言则由知识及伦理趋向所操控。按照人类思维的
既有方式,寓言往往追求短小叙事,而当艺术家头脑中迸发出合理想象
时,寓言则大力借助传奇进行叙事表达。伊索寓言可谓寓言之典范,但
将寓言与传奇加以常规组合的重要例证则要数色诺芬(28)
的《居鲁士的
教育》(Cyropaedia),以及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叙事寓言。而梅
尼普讽刺(Menippean satire)(29)
则是与反传奇(anti-romance)相结合
的寓言,就像卢希安(30)
的《真实故事》(True History)发端于戏仿奥
德修斯的历险那样。文学史诗在维吉尔(Vergil)的作品中经历了从传
奇性叙事到教寓性叙事的演进,难怪但丁在《神曲》中会让维吉尔担当
向导。当教寓性叙事与传奇性叙事面临像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就诗歌
所发出的那种责难时,它们便会在彼此身上寻找合理性及相互支持。锡
德尼就文学所进行的“辩护”,正是基于此处我们论及的这一重要类别中
所包含的虚构性层面。他坚持要求文学既展现一种理想的或“金色”的世界,同时也能寓教于乐。不过,费尔丁在《约瑟夫·安德鲁斯》的前言
及其他场合讲到自己的创作时,则注重这一脉络的经验性层面,强调以
作品对整体人性的忠实为基础;当然,他也试图为读者提供乐趣与教
寓。
我们先前一直在探讨史诗综合体在瓦解过程中所衍生的两种对立门
派。现在,我们则必须简要考察一种新的叙事综合体,这是后文艺复兴
叙事文学的主要发展。其渐进式历程的始初最晚得从薄伽丘算起,当
然,它的真正茁壮发展乃是在17及18世纪的欧洲。这一新的综合体可以
在像塞万提斯这样的作家身上得以清晰的体现,其伟大作品力图在经验
性与虚构性两种强大的趋向之间寻求平衡。小说作为一种文学形式的出
现正发端于塞万提斯所开创的这个综合体。小说不是通常所认为的传奇
之对立物,而是叙事文学中经验性和虚构性元素联手打造的产物。摹仿
(常青睐人物(31)
和“生活的切片”之类的短小样式)和历史(其过分地科
学化会导致其文学性的丧失)在小说中与传奇和寓言进行合成,共同构
建一个伟大的综合性文学形式,正如远古传说、民间故事和宗教神话也
在史诗中产生过创造性的融合。有迹象表明,在20世纪,这种伟大的汇
聚又将发生,而小说就像史诗所经历的那样,必然会为新形式让出其
位,因为它是个不稳定的聚合物,其瓦解势必分离出当中的组成元素。
小说衰变之复杂容不得我们在此进行详细探讨,但我们可以注意到各种
衰变的征兆:乔伊斯和普鲁斯特采用极端的手法与之抗衡;伊萨克·迪
内森(32)
和劳伦斯·杜雷尔寻求传奇的回归;塞缪尔·贝克特将自然主义化
约为荒诞性;塞利纳(33)
和霍克斯(34)
的科幻小说及梦魇小说得以兴旺;
甚至在畅销书单上(往往为社会学叙事和间谍—历险故事所瓜分),玛
丽·麦卡锡(35)
和伊恩·弗莱明(36)
也会不禁让我们想起狄奥佛拉斯特式的人
物及希腊传奇所体现的古代小说传统。小说在其不稳定性之中能够体现出几分总体的叙事本质。它在直接
的话语者(或抒情诗的作者)与戏剧对行动的直接展现之间,在对现实
和理想的忠实之间寻求平衡;它比其他文学艺术形式拥有更大的极限发
挥,当然也因此付出了代价——沦为不尽完美的形式。作为所有学科中
最不正式的成员,小说提供的天地之广阔绝非任何一部孤立的著作所能
囊括,它不断引发文学性的颠覆,革新文学创作手段。那些最伟大的叙
事总是不遗余力地进行尝试。如威廉·福克纳所云,叙事文学既可能使
一位作家在审慎中获得成功,也可能让一位作家虽败犹荣。从历史的角
度看,它一直是文学门类中最具多样性、最富于变化的一种,换言之,也就是最具生命力的形式。尽管叙事文学不乏瑕疵,但它始终——从史
诗到小说——是最受欢迎、最具影响的文学类别,它比任何其他文学形
式都更能赢得其文化语境中最广泛的读者,更能够对超文学性影响做出
积极回应。在下面几个章节中,我们将着重探讨叙事艺术的多样性、复
杂性及其惯常的矛盾性。
(1) 埃里希·奥尔巴赫(Erich Auerbach,1892—1957):德国文献学家、比较文学家及文学
批评家,曾执教于耶鲁大学,著有《摹仿论:西方文学所描绘的现实》。
(2) 劳伦斯·杜雷尔(Lawrence Durrell,1912—1990):英国当代诗人兼小说家,著有小说
四部曲《亚历山大港四重奏》(Alexandria Quartet)。
(3) 沃弗兰·冯·埃森巴赫(Wolfram von Eschenbach,约1170—1220):中世纪德国诗人,生
平不详,其标志性作品《帕西瓦尔》(Parzival)是最重要的德国中世纪史诗之一,讲述亚瑟王
朝骑士帕西瓦尔寻求圣杯的漫长历程。
(4) 塞缪尔·约翰逊于1759年出版的小说,讲述阿比西尼亚(Abyssinia,今埃塞俄比亚)王
子厌倦“欢乐谷”的闲适生活,逃往埃及,探索幸福生活的哲学奥秘。
(5) 俄相(Ossian,公元3世纪):传说中古代爱尔兰最伟大的诗人、武士,其遗作后为18
世纪英国诗人詹姆斯·麦克弗森(James Macpherson)发掘、整理、翻译,但“遗作”的真伪在学
术界一直争议不断。
(6) 詹姆斯·麦克弗森宣称从盖尔语翻译、由俄相创作的古代史诗。
(7) 乔叟基于传统故事进行重新演绎的爱情悲剧,全诗讲述了特洛伊战争期间特洛伊王子特洛伊罗斯与特洛伊女子克瑞西达之间的悲欢离合。
(8) 杰弗里(Geoffrey of Monmouth,约1100—1155):中世纪英国编年史家,著有《英国
君王史》,对亚瑟王传奇在欧洲的普及起到了重要作用。
(9) 弥尔曼·帕里(Milman Parry,1902—1935):美国史诗学者,口头文学研究的革命性人
物。
(10) 阿尔伯特·洛德(Albert Lord,1912—1991):美国史诗学者,曾作为帕里的助手前往
波斯尼亚进行口头文学研究。二人共同创立了著名的“帕里—洛德模式”(又称“口头程式理
论”)。
(11) 穆赖(Gilbert Murray,1866—1957):英国古典学家,古希腊语言与文化学者。
(12) 康福德(F.M.Cornford,1874—1943):英国古典学家、诗人,著有《修昔底德:
神话与历史之间》《微观学术界研究》等代表作。
(13) 西奥多·盖斯特(Theodore Gaster,1906—1992):英国裔美国希伯来文化专家,著名
圣经学者,曾为弗雷泽的《金枝》进行批注并出版单卷节本。
(14) 厄文·帕诺夫斯基(Erwin Panofsky,1892—1968):德国艺术史家,后移民美国,现
代图像学研究的重要代表人物,著有《圣像画法研究》。
(15) 小罗伯森(D.W.Robertson,Jr.,1914—1992):美国学者,欧洲中世纪文学史
家,最杰出的乔叟研究专家之一。
(16) 此处所谓的“预表性类型”类似于《圣经》阐释中的“预表论”(typology),即一种原型
(《旧约》)当中已经预示了另一后继形态(《新约》)的某些元素。如果前者称为“原型”,那么后者即“预表性类型”。
(17) 就西方文化来说,“古典语言”通常指欧洲大陆在“古典时代”(公元前8世纪—后5世
纪)所使用的希腊文与拉丁文;而“本土方言”则指“古典语言”之外的民族方言,如中世纪欧洲
传奇文学用以创作的罗曼语,就是由诸多民族方言(如法语)构成的语族。
(18) 亚历山大时期:在希腊化时期及罗马时期以埃及亚历山大港为文化中心的历史阶段,其影响包括文学、语言学、哲学、医学及科学等众多领域。
(19) 狄奥佛拉斯特式的人物(Theophrastian Character):狄奥佛拉斯特(Theophrastus,公
元前372?—前287)是亚里士多德的学生,古希腊哲学家,其研究涵盖哲学、生物学、物理
学、伦理学等众多领域。其《人物论》(The Characters)介绍了献媚者、自负者、无礼者等各
种典型人物,对西方文学具有深远影响。
(20) 狄奥克里特(Theocritus,约公元前308—前240):古希腊田园诗的创始人。
(21) 裴特洛纽斯(Petronius,?—公元66?):古罗马讽刺家,疑为古罗马讽刺情色小说《塞
坦瑞肯》(Satyricon)的作者。
(22) 《塞坦瑞肯》当中26—78章的部分,讲述自由民暴发户特里马尔奇奥以奢华的宴席款
待宾客的故事。(23) 公元前3世纪创作、仅存的希腊化时期史诗,讲述了神话传说中的伊阿宋(Jason)及
其阿尔戈号勇士(Argonauts)智取金羊毛的故事。
(24) 又称《提亚戈尼斯与卡里克列娅》(Theagenes and Chariclea),由公元3世纪希腊传
奇作家赫利奥多罗斯(Heliodorus)创作的传奇。该作品自16世纪起风行欧洲,曾对英国早期传
奇小说产生影响。故事讲述埃塞俄比亚公主卡里克列娅因母亲怀她时凝视白色大理石雕像而生
来肤白,母后为避通奸嫌疑,将其送交他人抚养。成年后,卡里克列娅经历了与提亚戈尼斯的
爱情,以及接踵而至的磨难,关键时刻其身世为父王所知,继而得以与提亚戈尼斯终成眷属。
(25) 法国史诗,讲述查理曼大帝的侄儿罗兰奋勇战死疆场的故事。
(26) 克雷蒂安·德·特罗亚(Chrétien de Troyes,约1140—1190):法国中世纪诗人及传奇作
家。
(27) 17世纪法国小说,由苏德莱兄妹(Madeleine and Georges de Scudéry)创作,长达十
卷,两百多万字,讲述古代波斯帝国居鲁士大帝的传奇人生。
(28) 色诺芬(Xenophon,约公元前434—前355):古希腊历史学家、散文家,富于传奇色
彩的希腊“万人”雇佣军首领之一,著有“半虚构性”政治传奇《居鲁士的教育》,讲述波斯帝国
君主居鲁士大帝作为一代英明统治者所接受的教育。
(29) 古罗马学者瓦罗(Varro)的作品,现已失传;题名中的“梅尼普”,指公元前3世纪的
希腊讽刺家梅尼普斯(Menippus);现在,“梅尼普讽刺”常用于指文学作品中带有狂想意味而
又不乏思想的夸张性讽刺。
(30) 卢希安(Lucian,117—180):古希腊修辞学家及讽刺家,所著小说《真实故事》讲
述了主人公等一行人被狂风卷入外太空之后的离奇见闻。这部作品是目前已知的最早涉及外太
空、外星人和星际大战的科幻小说。
(31) 此处所谓的“人物”是指,上文提到的《人物论》当中的速写式人物。
(32) 伊萨克·迪内森(Isak Dinesen,1885—1962):丹麦小说家,著有《哥特传说七则》和
《走出非洲》等作品。
(33) 塞利纳(Louis-Ferdinand Céline,1894—1961):法国现代主义作家,对贝克特、萨特
及巴特等作家均产生过影响。
(34) 霍克斯(John Hawkes,1925—1998):美国作家,以超现实主义风格著称。
(35) 玛丽·麦卡锡(Mary McCarthy,1912—1989):美国作家及评论家。
(36) 伊恩·弗莱明(Ian Fleming,1908—1964):英国作家,詹姆斯·邦德的缔造者。2 书面叙事的口头传统
无人知晓人类掌握语言的历史究竟有多长。如果系统进化链上处于
人与猿之间某个“未知环节”的生物创造了语言,那么,语言可能要比人
类自身的历史久远得多。也许在数百万年以前,人便最初开始向自己或
他人复述某一令他愉悦的话语,并由此造就了文学。从某种意义上说,那就是西方叙事文学的开端。不过,我们将避免就该主题穷根溯源。要
理解远古时代的文学,任何针对荷马以来的叙事所做出的研究论断都显
得力不从心。那些作品本身所描绘的内容常常只能大致算是类人化生物
(anthropomorphic creatures)的所作所为;即便当时的语言能够为我们
所理解,也只会让未经训练的读者陷入迷惘或引起他们的憎恶。批评家
们难免会生搬硬套,试图将神话、传说、民间故事这些熟知的类别强加
在与此分类法相抵触的文本体系之上。
文学(就其词源的严格意义来说)若没有书写便无从产生。从定义
上看,它就是文字的艺术。我们的先辈曾持有一种观念,认为“书面语
言艺术”和“口头语言艺术”这一偶然的差异——如文学 ? ?
这个词所暗示
——导致了书面叙事与口头叙事之间的有效区分:前者因体现文明而可
为理解,后者则因体现原始而令人费解。近年来,我们已经对此产生了
不同的认识。口头叙事和书面叙事尽管在形式上存在差别,且差别很
甚,但在文化意义上,两者则没有任何差别。弥尔曼·帕里(Milman
Parry),作为研究英雄体诗歌口头创作的最杰出权威之一,曾写
到,“文学之所以分成两大派别主要倒不是因为存在两种文化,而是因
为存在两种形式 ? ?
:一部分文学成为口头性的 ? ? ? ? ? ? ? ? ? ? ?
,另一部分成为书面性 ? ? ? ? ? ? ? ? ?
的 ?”。在本章中,我们将通过考察古代希腊及北欧口头叙事来关注书面
叙事的传统,尤其会着重探讨口头叙事诗对此后书面叙事形式的影响。我们会研究口头叙事与书面叙事的一些形式之异,并不失时机地强调指
出:这些差异乃文学形式之异,而非甄别原始文化与文明文化的标准。
因此,我们会抛开文学 ? ?
这个词的词源学意义而在广义上对其加以运用,使其意指所有的语言艺术,既包括口头的,也包括书面的。
在我们这个时代,阅读与书写已成为普遍技能,而文盲则陷入文化
和经济上的匮乏;经验似乎已经证实文盲现象与文化贫困之间的联系。
不过,仅从我们的现代经验去概括,以为每个时代中所有不识字的个体
都是文化的贫乏者,则不仅有悖逻辑,而且也缺乏真实。读写技能,作
为我们几乎普遍掌握的独特现代形式,乃是文艺复兴文化与技术革命的
成果;但它不仅在很大程度上使我们对语言属性的认识发生偏颇,同时
也让文盲 ? ?
这个词肩负耻辱之重。读写能力使人们放弃对牧师或教师的依
赖。书籍和阅读能力成为受压迫者发现自由的途径。在我们这样一个读
写的时代,书籍变成了自由与真理的象征。焚书或禁书意味着对人性的
亵渎。这种做法并非将代表人类精神的财物视为专门的——甚至算不上
是主要的——仇视对象,相反,它所染指的乃是人类精神的象征物。
当然,并非每个时代都会对抄写员的墨迹和排版工的技艺表现出此
般理想化的观念。在《斐德若篇》(Phaedrus)(1)
中,苏格拉底讲了一
个故事,说埃及一位叫图提(Thoth)的神发明了书写文字。为了与人
们分享自己的发明,他便来到统治整个埃及的神塔穆斯(Thamus)跟
前。他向国王展示自己的文字,声称它们不仅会提高埃及人的记忆力,同时也会增强其智慧。此时,塔穆斯回答道:
哦,聪明绝顶的图提,有人会发明新技术,则有人会评判
那一技术对其使用者而言是祸还是福。如今,你作为文字之
父,出于个人情感,恰恰将文字的真实功能说反了。你这个发
明会导致文字使用者因忽视记忆而丧失头脑中的学问;因为他们可以依赖那些疏离于头脑的外在文字,进而丧失回忆事情的
能力。你非但没有发明一剂良药去增强记忆,反倒是为记忆炮
制出一种低级的替代品。你教给学生的乃是如何在缺乏真智慧
的时候伪装智慧;因为他们似乎无需教导便已经成为饱学之
士;他们好像满腹经纶,而实际却孤陋寡闻;而且他们还将为
公众所憎恶,成为一帮缺乏智慧却看似拥有智慧的人。
在我们的文化中,印刷文字的神圣性有时会将苏格拉底的担心发挥
到极致。以印刷形式表现的文字对我们来说,其真实性已经超越了活人
嘴巴发出的声音,以及这些声音所代表的概念。书籍虽仅仅是物化的客
体,却时而凌驾于世人所敬仰的智慧之上。任何谎言或怒语,一旦凭借
印刷的尊容得以展现,便会拥有千倍的威胁。能读会写的人士因其自身
的健忘甚至不敢想象那些目不识丁的诗人与讲故事者如何创造出伟大的
文学。我们很难设想古希腊人居然会允许遭到诗人和教师鄙视的仆人与
簿记员阶层独自享用米诺斯B类线性文字(Minoan Linear B)(2)
书写体
系(发现于克诺索斯和皮洛斯两地的皇宫废墟)。但是,证据似乎显
示,B类线性文字要比《荷马史诗》的创作至少早五百年之久,它在迈
锡尼时期希腊人的文学或教育中没有扮演任何角色。这一事实部分解释
了该文字系统为何最终被迈锡尼时期的希腊人所摒弃。而腓尼基字母
(Phoenician alphabet)引入希腊大陆地区(再次由簿记员阶层发起)的
时间通常被确定在8世纪。在弥尔曼·帕里做出结论性的发现之前,这听
上去似乎匪夷所思;现在,我们知道,《荷马史诗》的创作要远远早于
希腊文字在现代意义上的广泛使用。
帕里就《伊利亚特》及《奥德赛》的口头创作所进行的阐释包括两
个部分;两者均证实了这样一种假说,即口头创作文学与书面文学得以
区分的基础在其形式而不在其内容。正如我们接触《荷马史诗》那样,帕里的研究亦以《荷马史诗》的书面文本为起点。他注意到,传统饰语
和措辞尽管一直是后来西方传统中“史诗风格”构成当中的一个次要元
素,但却总是被荷马用在相同的格律及语义情景当中。荷马语汇的这些
传统元素在数量及质量上要比后来诗人的作品丰富得多;帕里将它们称
为程式(formulas)。按其定义,程式即“在相同的格律条件下得以反复
运用的一组词,以表达某个恒定的核心理念”。用于阿伽门农
(Agamemnon)身上的固定饰语,如“阿特柔斯(Atreus)之子”和“众士
之王”;而“戴着耀眼头盔”则用在赫克托(Hector)身上;用以指大海的
则包括如“朱红似酒的”“澎湃激荡的”和“充满回响的”等饰语。这些固定
饰语一直被认为是荷马风格的特征,而其效果则为继阿波罗尼奥斯(3)
以
后的文学史诗作家所效仿。不过,直到帕里发现整个荷马语料库——约
27 000行六音步诗句——完全是程式化的,批评家们方意识到,过去一
直看似表面化的文体风格特征,事实上作为不可回避的证据证实了《伊
利亚特》和《奥德赛》系口头创作。比如,《伊利亚特》前15行中90%
显然是程式化的;也就是说,在荷马语料库的其他地方,研究者在同样
的格律环境中找到了与之相匹配的相同语汇群。就我们所知,任何一个
《荷马史诗》段落的程式化百分比几乎是一样的。在我们已知的书面文
学诗人的作品中,逐字重复的百分比与前者相比差距甚远。正相反,书
面文学诗人力图赋予每一行诗以独特性,而把重复的短语留作营造特殊
的修辞效果。
帕里研究的第二部分在某些方面甚至比第一部分更有成效。为了反
向证实其第一个推断,即高度程式化的诗歌语汇乃口头创作的证据,帕
里着手说明,口头诗人凡创作必用程式。他们在即兴创作时以其诗歌传
统中的惯用程式为基础,组织符合格律和语义的诗句。帕里在南斯拉夫
对南部斯拉夫语口头史诗进行研究时发现,基督教和穆斯林吟唱诗人都
能够在名为古兹拉琴(gusle)(4)
的单弦乐器伴奏下创作出在篇幅、复杂性及文学趣味方面接近《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的史诗。这些吟唱诗
人认为自己能够一字不差地重复一整部史诗;他们所引以为豪的是,自
己能记住在其看来是所谓固定“口头文本”的东西。然而,当帕里就同一
位吟唱诗人的同一首歌曲分别进行了两次记录后,他发现两次表演很少
有完全一致的情况。在这两个版本中,单独的诗句和诗节的创作均存在
差异,但是两者都使用了相同的程式。从诗句构成的层面来看,识别口
头创作的恒定条件是传统程式的存在,而不是两个文本之间逐行的相似
性。
尽管帕里的发现的确为基于真凭实据的猜想提供了更为坚实的基
础,但它们无法就有关荷马的所有问题为我们提供最终的答案。依据帕
里在南斯拉夫的调查,以及世界其他地区有关口头创作史诗的报告,我
们便能够——比如说——重新构想荷马的身份问题,当然我们还是无法
对此给予明确的答案。口头诗歌叙事传统当中的个体吟唱诗人与书面叙
事传统里的个体诗人是一样重要的,但是吟唱诗人的角色与诗人的角色
却有着天壤之别。吟唱诗人完全依赖其传统。他所学会的情节及对其进
行详尽阐发的各种片段,甚至他用以组织诗句的短语,都是传统性的,广义地说,就是“程式化”的。他既非创作,也非记忆某一固定文本。每
次表演均是一次独立的创造之举。在吟唱诗人实际演绎一则叙事之前,此诗歌并不存在,而只是以吟唱诗人传统这一抽象工具,潜在于无数其
他诗歌当中。反过来说,当诗歌终了,它也就不存在了。只有当吟唱诗
人本人或某个听众在一次表演过程中发现传统之外的某样新东西,该诗
歌方能影响传统,继而在那些听众的记忆中产生些许永恒性。
或许是因为这些诗歌只是对传统的演示,而非个人智慧的发明,大
多数口头创作的叙事诗尽管以书面文本的形式加以保留,却并未联系到
具体诗人的名字,甚至传统上就没有这种做法。将《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的创作归功于荷马或将古冰岛语《诗体埃达》(Poetic Edda)(5)
归功于“智者塞蒙恩德”(S?mundur the Wise),这些结论虽然已为我们
当今的口头传统知识所大力证实,但仅属例外。基涅武甫
(Cynewulf)(6)
的文本显然属于盎格鲁—撒克逊口头叙事,而作为贯穿
于这些文本之中的如尼文(runic)(7)
签名则成了让学者们大伤脑筋的问
题。这些签名或许应该被视为代指某位抄写者或口头诗人;他既熟悉书
写,同时也对自己的作者身份怀揣几分书卷气的怜惜。对于书面创作者
来说,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但对于口头诗人而言则相当不可思议。事
实是,无论这些签名的来源是什么,基涅武甫的叙事依旧如《贝奥武
甫》一样具有修辞上的高度程式化和传统性。不管基涅武甫是谁,与其
姓名相系的诗篇均创作于通常的盎格鲁—撒克逊口头传统,而并不能以
任何现代意义代表一位具体诗人的作品。我们使用某位具体诗人的姓名
去指示一则口头叙事的作者身份,无非是为了权宜之便,如荷马与基涅
武甫的例子,或出于对传统的尊重,如《塞蒙恩德的埃达》;因此,关
于诗歌背后的创作者,我们应该将其角色更多地视为歌者或表演者,而
非现代观念里的“作者身份”。
有一种看法认为诗体叙事可能会在口头传递的过程中“受损”,但这
不过是针对口头传统机制产生的普遍误解。假若一首口头创作的诗歌,如古冰岛语《沃卢斯帕》(V?luspá)(8)
,变得艰深晦涩,那么这种麻烦
产生的原因,无非有二:拙劣的表演,或更有可能的是手稿传递过程中
产生的讹误。一场口头表演或许平庸无奇,但不会艰深晦涩或是遭
到“文本性损伤”。另一方面,一位伟大的吟唱诗人历经多年艺术修养的
完善,往往能够超越他曾听过的任何表演。即便只是聆听一场拙劣的表
演,他也能了解到一个故事——基本情节和人物姓名,并且他能够运用
自己对传统的把握吟唱出一首比原曲长许多倍、编排更精致的作品。在
这种情况下,我们不妨认为:一首诗在口头传递的过程中恰恰得到了“完善”,当然,此说法也多少与“文本性损伤”的观点犯了同样的错
误。因为这就意味着一种作为实体存在的诗歌被传递了,然而这并非口
头传统中的情形。我们可以认为,诗歌里的诸多元素被传递了——情
节、片段、人物的观念、关于历史事件的知识、传统性母题、语汇等,但是我们不能以为被口头传递的乃是这首诗歌本身。
我们可以将荷马看作众多希腊史诗吟唱者中最杰出的一位艺术大
师,虽然他在本质上无法超越其所在的传统,但却能够在表演中将传统
推向最佳境界。依照这种观点,或许我们既能最大限度地接近通常观念
中的荷马,同时又尽量不损及口头创作的实际状态。荷马之伟大在于其
传统之伟大。他在知识及情感方面所营造的广博与共鸣,他在表现具体
的人与事时所展示的客观性与准确性,他的虔诚与讽刺所体现的爱憎分
明,——这些成就乃属于名为“荷马”的古希腊史诗传统,而并不属于局
限在个体观察与记忆当中的某位孤立的诗人。口头诗人与其所处的文学
文化之间存在着相当密切的联系。书面文学追求创新性与个性表达,但
这些机会对于口头诗人而言是极其稀少的。口头吟唱者在遵循传统的基
础上将个体天赋发挥到极致,或许也可以说,在因循个体天赋的基础上
将传统形式发挥到极致。两者不过是同一实体的不同层面而已。没有诗
歌,传统便会消亡;没有传统,诗歌也就无以存在。
然而,传统也能发生变化。它可以调整自己——当然进程是缓慢的
——不仅适应其诗歌所再现的外在文化及物质世界,甚至对诗歌赖以构
建的语言形式的变化也能做出反应。荷马文本基本是属于爱奥尼语
(Ionic)(9)
风格的,它们对古风特色与地区方言进行的糅合乃是一种妥
协:一方面是最古老的阿卡狄亚—塞浦路斯语(Arcadian-Cypriot)(10)
和爱奥尼语形式,对此,传统在向希腊大陆地区转移的过程中无法彻底
加以遗弃;另一方面是稍晚出现的阿提卡语(Attic)(11)
形式,对此,传统则加以运用,力图保持作品的当代性和可阅读性。作为一首口头创
作的古英语史诗,《贝奥武甫》也表现出相似的语言糅合特点,其传统
回溯至麦西亚(Mercia)(12)
的文化繁盛期,而其基本语言则属于稍后的
西撒克逊模式。
只要有可能,新的语言形式就会逐渐替代先前的旧形式,此外,口
头诗歌传统也可对旧的程式进行类推,从而生成新的程式。例如,“贵
族之梦”(eorla dream)作为一种盎格鲁—撒克逊的半行诗程式(13)
往往
用以描述“贵族扈从的快乐”。但随着基督教主题和故事的逐渐引入,该
传统便以旧程式为依托创造出所谓“天使之梦”(engla dream)的新程
式,用以描述“天使的快乐”。用口头诗歌语汇研究者们的术语说,“贵
族之梦”与“天使之梦”这两个程式构成了一种“程式模版”或“程式系统”。
按照帕里的定义,程式系统指的是“在思想及语汇层面足够相似的一组
短语,诗人在运用它们的时候毫无疑问不仅将其视为独立的程式,同时
也把它们当作某一类型的程式”。这些抽象系统或模版的存在,将传统
语汇的渐进式演变纳入研究视角。更重要的是,程式模版在具体吟唱诗
人的演艺中所发挥的作用也受到了关注。阿尔伯特·B.洛德的著作《故
事歌手》(The Singer of Tales)进一步推进并深化了帕里在南斯拉夫的
研究及其就《荷马史诗》的口头创作所形成的理论。洛德认为:
构建诗句的根本元素是基本的程式模版。可以有根据地
说,具体程式本身对吟唱诗人的重要性仅仅产生于程式的基本
模版植入其思维之际。当诗人到达这一境界,他对学习程式的
依赖性会越来越小,而更多的则在于对程式模版中的语汇进行
替换。……这便是其艺术的整体基础。
于是,在诗句构成的层面上,口头诗歌传统的基本实体并非一成不
变的程式(当然,依据这种固定程式,我们可以准确识别诗歌的口头创作身份),而是抽象化模版,凭借它们吟唱者能够创造新的语汇。在此
层面上,传统与其说是包含一套固定的元素,不如说是包含一种“语
法”。这种语法叠加在口语的常规语法之上,但与后者存在相似之处,即对这种语法的习得乃是处于意识层面之下的过程;同时,伴随这种语
法会对认识及构想外部世界产生强烈的约束力。围绕思想的演化必然存
在双重约束机制:一是通常认为的语言结构限制;二是传统智慧的“语
法”限制。艾里克·A.哈弗洛克(14)
曾发表颇具说服力的观点,认为柏拉图
在《理想国》中对诗人的责难是一种革命性的尝试,他力图将希腊思想
从口头传统的“语法”独裁中一劳永逸地解放出来。
写出既具格律又可被理解的诗句,并非口头诗人面临的唯一挑战。
在某种程度上,他还必须在表演的过程中“编造”故事。关于口头叙事诗
的“形态学”,人们对其抽象化程式模版有所了解,而对其更为重要元素
的认识则相对不足。帕里与洛德认为,在南部斯拉夫语及希腊语口头史
诗中存在着他们称之为传统“主题”的东西。另外,他们对盎格鲁—撒克
逊语、古冰岛语、古法语及古芬兰语口头叙事诗也做了相似的传统主题
元素分析。洛德曾将口头诗歌的“主题”定义为“以传统诗歌之程式化风
格讲述故事的常用观念群”。在《奥德赛》当中存在着数次程式化的描
绘,用以讲述热情好客的主人欢迎一位来访者;按照洛德对该术语的理
解,这就构成了一种口头“主题”。在日耳曼口头叙事当中,一群贵族随
从围着国王觥筹交错,自矜自夸,这种所谓“贵族之梦”的描写则构成了
那个传统当中的一种“主题”。对于口头叙事诗而言,用“主题”一词去定
义其风格手法当中的形式元素在实践上存在很大的困难,原因是这个词
同样用于一般的文学批评中,其意义不仅多样化,而且有时候会相当矛
盾。
在分析口头创作的诗歌时,我们专门使用了“主题”(theme)一词,而根据希腊修辞学,我们则提出“论题”(topos)这一替代性术语。
这个概念因恩斯特·罗伯特·库提乌斯(15)
在其《欧洲文学和拉丁中世纪》
一书中的研究而广为接受。我们并无意暗示希腊修辞学家们所使用的具
体“论题”与古希腊史诗中被帕里、洛德称为“主题”的概念之间存在必然
的历史关联,而是说,从结构性视角来看,那些多少趋于程式化的修辞
元素,如欢乐之土 ? ? ? ?
(16)
(描写理想的景致)和少年老成 ? ? ? ?
(17)
(出于对年轻
人的称赞而认为其拥有长者的智慧),与口头叙事诗中的程式化观念群
非常相似,从而使得该描述性术语同样具有存在的必要性。
一则“论题”,不管出现在口头叙事还是书面叙事中,乃是一种传统
的意象。对它进行识别甚或分析的基础,并非诗人用以构建“论题”的程
式或经过独特安排的语汇,而是这些语汇所指的意象。关于叙事意象的
主题分析,我们会在第四章进行详尽的后续讨论。在此处,我们不妨言
简意赅:如果一则“论题”指示的是外部世界,那么,其含义就是一个母 ?
题 ?
(motif);如果该“论题”指示的是无形的观念和概念世界,那么,其
含义就是一个主题 ? ?。于是,传统性“论题”便包含两种元素:传统母题,如主人公遁入冥界——这在历史上可谓经久不衰;传统主题,如寻觅智
慧或下降阴府(18)
——这更易于经受渐进式的嬗变或最终的替换。口头
叙事的“论题”得以识辨的基础是其在一个既定的母题与一个既定的主题
间建立的恒定联系。另一方面,就书面叙事而言,母题与主题的关系即
便是在传统性“论题”当中,也往往会受制于诗人的操控。当然,古代叙
事“论题”的主题内容分析起来颇为棘手。正如日耳曼口头诗歌传统中的
那些“论题”,荷马式“论题”有一度也同宗教仪式紧密联系着。因此,即
便其叙事显著摆脱了直接崇拜的束缚,而它们的主题内容却仍留存着些
许宗教色彩。
口头叙事诗的“论题”常以模式化序列得以展现,一个“论题”会挑选另一个“论题”,抑或作为一个整体的系列“论题”会挑选另一个整体化系
列“论题”。洛德从《奥德赛》当中列举一例对此模式化加以说明;在他
看来,奥德修斯回归故里之际对伊萨卡(19)
人的试探正是通过重复一
种“论题”模式来表现的,其母题是“凌辱”(abuse)、“责难”(rebuke)
和“认出”(recognition)。在此母题模式之下存在这样一个主题,即“经
过伪装的再生之神由于未被卑劣之徒认出而遭到后者的拒斥”。该模式
始于第17卷,此处奥德修斯受到墨兰提俄斯(Melanthius)(20)
的凌辱 ? ?
,随后又遭到欧迈俄斯(Eumaeus)(21)
的责难 ? ?
,接着被奥德修斯的狗阿尔
戈斯(Argus)认出 ? ?。而后安提诺俄斯(Antinous)、欧律马科斯
(Eurymachus)及克忒西波斯(Ctesippus)(22)
对奥德修斯实施了凌辱;
责难则由奥德修斯妻子的求婚者及忒勒玛科斯(Telemachus)(23)
实施;
认出奥德修斯则包括与伊洛斯(Irus)(24)
的决斗、欧律克勒亚
(Eurycleia)(25)
那一幕,以及射箭比赛。这种模式说明,篇幅处于单
个“论题”与整部诗歌之间的结构性元素可以掌控逐个“论题”的编排。我
们不妨用“神话”(myth)(26)
这一术语来指代“论题”的这种铰链序列。一
方面是“论题”,另一方面是整部诗歌,而神话正如这两者一样,包括叙
事含义的两个基本层面:对于外部世界的再现 ? ?
(母题)和针对我们思维
中的观念和概念进行的阐释 ? ?
(主题)。
神话的再现层面是情节 ? ?;而其阐释层面(与“论题”和整部诗歌的情
形一样)则是主题 ? ?。口头吟唱者在将神话融入自己的诗歌时,必须同时
表现这两个层面。随着现代意义上读写时代的到来,或是由于某种激进
的文化变异,口头诗体叙事便会寿终正寝;此时,神话的阐释层面演变
为寓言和推论式的哲学写作,而神话的再现层面则演变为历史和其他经
验化叙事形式。
情节与主题相结合的传统属性作为口头叙事诗的特征,只是史诗综合体的一个方面。史诗的另一个特征是,它在宗教神话与世俗叙事之间
择取了中间路线;前者的故事完全外在于世俗世界中的历史人物与事
件,而后者的故事则完全发生于由历史人物与事件所构成的世俗世界内
部,或即便是发生于一个虚幻世界,其运作法则也同样掌控着现实世
界。也许,要认识口头史诗所构建的复杂综合体,最简单的方法便是将
其视为原始文化的唯一文学产品。这种看法当然过于简单化,但公证体
现了口头史诗的作用:它不仅保存了传统的诗歌“语法”(借此可以理解
和思考新经验),而且保存了文化中最重要的宗教、政治及伦理价值
观。经典荷马文本的确立经历了一个渐进式过程,自其肇始400年后,柏拉图意识到荷马式教育(paideia)这一垄断格局乃是思想进步的大
敌。只要荷马依然作为唯一的导师主宰着所有学科,那么,通向哲学思
索的唯一渠道便只能是围绕其“隐含意义”而进行的寓言式解读。
《荷马史诗》以其书面形式为我们所接受,然而关于它获取书面形
式的具体过程,我们则几乎一无所知。大量证据显示,希腊史诗传统中
的大多数传统故事乃是以非史诗形式(主要是戏剧形式)历经后世而得
以留存。某些非《荷马史诗》表演,甚至在绝迹之前便产生了书面形
式。来自西嘉(Sicca)(27)
的优提齐乌斯·普罗克洛斯(28)
曾编撰《文学选
读》(Chrestomathy),如今已经失传,不过从弗提乌斯(29)
(约820—
891)等人对此书进行的概述中,我们可以得知亚历山大时期希腊人尚
可获取的书面文本史诗的名称、大致篇幅(以行数或卷数表示)及内
容。这些文本中没有一例达到《伊利亚特》或《奥德赛》的篇幅,这似
乎说明了荷马文本无论在表演方面还是文字记载方面都具有不同寻常之
处。
在公元8世纪、7世纪和6世纪的希腊,书写的用途一定与我们今天
的情况有着天壤之别。无论在7世纪的希腊还是1200年后的北欧,铭刻碑石的存在本身并不代表以书写为基础的教育体系或文学文化。在南斯
拉夫史诗中,书面文件甚至电报被提及的频率之高,足以说明口头文学
传统能够通过紧密贴近其他用途的书写形式而得以幸存。如果我们要想
象传统荷马文本的某一粗劣原型得以通过口述听写的方式进行书面载
录,那我们就必须相信,对于文字和书写的运用在历经数个世纪的发展
之后已经成为熟练技能。不过,仅仅将书写引入文化中的某一单个领域
还远不足以产生任何接近现代意义上的“读写技能”。因为那意味着我们
需要拥有一种稳固确立的、建立在文字基础之上的教育传统——而这一
观念,即便对7世纪的希腊人来说,也会让他们颇感震怒。
洛德在南斯拉夫的研究说明,有多种方式可以用来将口头叙事转化
为书面形式,但几乎所有这些尝试均是对现场口头表演的拙劣再现。如
果吟唱者让抄写员听写,或者在其会写字的情形下,由他亲自听写,他
的表演定要比正常状态下慢得多。在这种情况下,他很容易失去节奏和
思维的连贯性。书面文本要想优于实际的演出,必须符合几个条件:吟
唱者愿意缓慢而耐心地让抄写员进行听写;抄写员对该传统烂熟于心;
在碰到出错的诗行,抄写员可以停下来让吟唱者重复。既然最终的文本
对于吟唱者而言可能并无任何用处,那么吟唱者与抄写员付出如此艰辛
的劳动,则理应存在某种特殊情况以构成其创作动机。这或许应该是依
采风者的要求所为。在我们看来,书面《荷马史诗》文本的产生定是源
于某种与此相类似的创作方法。
当口头表演化约为两个“作者”的书写,表演者和抄写员,并继而进
入一种准文学传统,真正的口头传统并不会受影响。然而,最终可能对
其形成挑战的乃是从新建立的文本传统中所衍生出的伪“口头传统”。于
是,一种新型的职业演艺者便开始同真正的吟唱者产生竞争,他们只是
记忆书面文本,而后四处朗诵。当“口头传统”这个词被文学学者们误用之际,往往指的就是这种口头朗诵,它依赖于事先用笔和纸这种现代方
式创作的固定文学文本。能够将真正的口头传统与书面再现区分开来的
因素是创作的方法,而不是表现的模式。洛德根据自己在南斯拉夫的研
究可以轻松地对真正的口头创作和书面文本的口头朗诵进行甄别。一种
是程式化的,而另一种则不是。
关于“过渡文本”(transitional text)这种代表口头与书面创作组合的
形式,尽管一些荷马学者、中世纪研究专家及其他人(包括我们自己)
对此深信不疑,但似乎并不可能。一切通过直接观察现存传统所获得的
证据,均促使我们推导出这样的结论:即便诗人自己进行创作,很明
显,他只会择其一——要不采用传统的口头程式法(展示口头传统的所
有特色),要不采用文学方式(展示文学创作所特有的思想和语汇的创
新)。不过,关于荷马文本的传播,真正有可能且最令人信服的猜想则
是:那种原汁原味的口头表演会通过誊写的方式与其书面文本的口头朗
诵相结合,继而逐渐发展为一种准文学传统。如果此现象发生,那么书
面文本便可能凌驾于真正的口头传统之上,从而获得最优秀的抄写员与
表演者的共同关注。面对不断推广的读写技能和基于权威文本意义上的
正规学术性教育,真正的口头传统在文化中的地位便会慢慢降低。同
时,真正新式的书面文学形式开始从旧式口头传统与新式学术传统的融
合中产生。
或许,关于《荷马史诗》获得其传统书面形式的过程,我们的推测
不该完全依赖于对今天南斯拉夫或中世纪北欧相似情形的认识。尽管书
面基督教文化对欧洲其他地方的本土口头传统产生了强大压力与潜在影
响,但要让一种域外书面传统对希腊口头史诗产生任何类似的影响,却
是难以想象的。在希腊,这种过渡一定是在主导文学文化内部渐进发展
的,即一种形式在某种程度上自愿让位于另一种形式。而在欧洲其他地方,口头传统不是突然遭到外来强势书写传统的压制,就是遁入隐蔽之
所,成为愚昧无知的农夫在草舍锅台边的娱乐。一方面是7世纪希腊的
《荷马史诗》吟唱者,另一方面是19世纪波斯尼亚或卡累利阿
(Karelia)(30)
的吟唱者,但两者的身份是难以相提并论的。古希腊的吟
唱诗人被王子们尊为大师,而其他的吟唱诗人则是为了取悦那些尚未摆
脱文化愚昧者(illiterates)身份的观众,当然,这里的“愚昧者”完全是
基于其可怕的现代意义。
圣经《旧约》文本中有很多源于口头传统的证据,因此,古代希伯
来人可能也经历了从口头到书面叙事之数世纪的漫长演化过程。我们也
许可以想象,他们与古代希腊人的情形存在相似之处。但是,在这两条
文化巨脉汇合之际,它们的影响横扫了整个欧洲。它们带来了读写技能
和对权威文本的尊重。就希伯来这条血脉而言,其最重要之处便在于它
以一个权威性文本去争得绝对的虔诚。阿尔昆(Alcuin)——一位9世
纪的英国学者,查理曼宫廷中复兴古典文学的杰出人物——曾言简意赅
地表明了教会对异教诗歌的态度。当他得知诺森比亚
(Northumbria)(31)
的林迪斯坊(Lindisfarne)修道院中僧侣们正以吟唱
有关日耳曼英雄英叶德(Ingeld)的史诗作为娱乐时,他带着几分讥讽
质问他们,“英叶德与基督何干?”阿尔昆的怒吼响彻了基督教统治下的
整个中世纪。
稍早于此,关于盎格鲁—撒克逊时期诺森比亚内部这两种文化的对
立,还有个故事对于我们则更有意义。这就是圣比德(32)
在《英国人民
基督教史》(The Ecclesiastical History of the English People)当中讲述
的关于诗人凯德蒙(33)
的故事,小F.P.马古恩(34)
曾将其称为“一位盎格鲁
—撒克逊口头诗人的个案史”。据说在希尔达(35)
(658—680)担当惠特
比修道院院长期间,院中的僧侣曾向凯德蒙讲解宗教信条与叙事,而凯德蒙则以此为基础创作出许多英语叙事诗。在圣比德关于凯德蒙的叙述
中,最突出之处乃是关于这位中年的凡夫俗子如何奇迹般的获得创作叙
事诗的天赋。凯德蒙原先并不会当众作诗;每逢节日庆典,竖琴便会在
众人手中传递,大家轮流吟唱,而凯德蒙却抽身离去,直到某日,一位
天使现于其梦中,要求他吟唱创世的故事。这则神奇之梦,作为一种解
释,说明了凯德蒙如何在人到中年之际能够运用完全传统化的口头程式
进行卓越的诗歌创作,以专门服务于基督教的宣讲。圣比德指出,凯德
蒙从未创作过“任何无关痛痒或毫无用处的诗歌;相反,他的虔诚之言
只适用于那些关乎宗教的诗篇”。另一种解释是,传统的盎格鲁—撒克
逊程式模版之所以为凯德蒙用来创作其《赞美诗》(Hymn),以及现
存的那些围绕“创世纪”及“出埃及记”所进行的盎格鲁—撒克逊语改编
(如果它们果真代表其表演的话)——乃要归功于他在私下里对技艺的
学习和练习;他不急于进行首次公开表演,而是一直等到发现如何将其
诗歌用于效忠上帝。
传统上,与凯德蒙所经历的梦幻奇迹相联系的还有一个故事,它保
存在神秘的拉丁文《序言》(Praefatio)和《诗篇》(Versus)当中,现代研究理论将它们与古撒克逊语诗歌《救世主》(Heliand)和《创
世纪》(Genesis)相联系。这两个拉丁文本大致可追溯到10世纪,但只
留存在马提亚·弗拉齐乌斯(36)
的《真理见证者目录》(Catalogus Testium
Veritatis,1562)第二版中;它们在简短的篇幅中不乏矛盾地描述了
(1)查理曼之子,法兰克皇帝“虔诚者路易”(执政期814—840)所下
达的命令,“撒克逊国有个人被其同胞们视为杰出的诗人,他必须负责
将《旧约》和《新约》翻译成日耳曼语言,如此,神的教诲不仅能让文
化之士享有,也可让愚昧之众领会”。(2)“正是这位诗人,当他还完
全不了解诗艺之际,却在睡梦中受命依照他自己的(撒克逊)语格律将
圣典之法改编为诗歌。”这些故事的共同之处在于,它们均指涉了本土口头叙事传统——这
一传统经过调整不仅适应了普通读本文化,而且也应和了圣经读本文
化。对于像凯德蒙这样的诗人或是创作《序言》的无名氏撒克逊神谕诗
人(vates)而言,问题不只是对抄写员进行口授,而主要是运用传统程
式及“论题”去表达全新的情节与观念。我们很难想象还会有其他诗歌能
够表现出比《救世主》更高的程式化。在这部作品中,程式或程式模板
几乎包含于每一诗节,它们既可能反复出现于该诗作本身,抑或出现在
盎格鲁—撒克逊的诗歌语料库中。当然,其传统化特征并不局限于程式
化创作。它还运用了许多如《贝奥武甫》等世俗诗歌中出现的传统母
题。这些母题清晰地说明,古撒克逊口头传统乃是新近衍生于英雄体的
文化,而这种文化则迥异于那些为《救世主》提供情节基础的《新约》
叙事。不过,同样清楚的是,撒克逊诗人与中世纪基督教文化保持着紧
密联系。当他们充分顾及传统程式和母题的时候,其叙事就相当于对下
列这些文本进行了一番细致的改述:他提安(37)
四福音合参的伪著、拉
巴努斯(38)
对《马太福音》的批注、圣比德对《路加福音》《马可福
音》的批注,以及阿尔昆对《约翰福音》的批注等。
纵观13世纪的古冰岛语《诗体埃达》、古高地德语(39)
《希尔德布
兰特之歌》(Lay of Hildebrand)(40)
,诸如《瓦尔迪尔》
(Waldere)(41)
、《戴欧》(Deor)(42)
、《威德西斯》
(Widsith)(43)
,以及残诗《费恩堡之战》(Finnsburg Fragment)(44)
这
样的盎格鲁—撒克逊语诗歌,乃至于法罗群岛(45)
的英雄体歌谣(直到
上世纪方以书面形式记录下来),我们可以发现,这些诗歌具有口头创
作和英雄体文化相融合的明显痕迹。不过,由于日耳曼口头传统早在圣
经文本到来之前便已兴盛,因此,要对它进行研究,我们的最佳考察文
本莫过于盎格鲁—撒克逊史诗《贝奥武甫》。这首诗存于仅有的一部手
稿当中,大约在10世纪末由两位抄写员书写而成。如所有刚才提到的其他诗歌一样(除去法罗语歌谣),《贝奥武甫》可能并非直接抄录自口
头表演。大部分学者将其多样化的语言形式及拼写,看作是两个半世纪
之久的文本传统的证据,并因此将其创作时间确定为8世纪早期。关于
《贝奥武甫》系口头创作这一论断,学界已经找不出合理的质疑。其措
辞具有显著的程式化特征,其“论题”同样为相似的古英语及其他日耳曼
语诗歌所采用。
很显然,口头诗人能够通过书本,或至少可以借助文字中介,而获
取故事和主题,但在《贝奥武甫》中,书卷学习的证据则微乎其微。不
管是其风格还是其内容,似乎都在说明,古代日耳曼的确存在高度发达
的口头史诗。当然,我们无法知晓这种传统究竟发达至何种程度,或者
在自行其是的情况下又会如何发展。但罗马—基督教文化的进犯则完全
湮没了这种传统。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要想当然地以为史诗传
统只是为远古人类所独有的特征,事实远非如此。我们已经认识到,对
于相对未受侵扰的希腊人来说,史诗是真正现代文学及哲学文化到来之
前的最后一个阶段。其他各种证据,如精良的武器和舰船,以及先进的
政治和法律制度,均说明北欧的异教徒们正在接近8世纪希腊人所经历
的文化发展。当基督教于公元400至1000年之间的数世纪中进入北欧
时,它所遭遇的文学文化已经形成了融合神话与摹仿的史诗综合体,并
正值分化之际,由此带来法律、宗谱、神话、宗教仪式及世俗叙事小说
等独立门类。
《贝奥武甫》的吟唱者关注的是丹麦人与弗里斯兰人
(Frisians)(46)
及希索巴特(Heatho-Bards)人(47)
之间的关系所代表的
更广泛的社会与政治意义,或是一位明君的必备道德素养,这些都是其
史诗传统的特点;它们不仅出现在埃达文选里,同样也出现在《流浪
者》(The Wanderer)(48)
、《威德西斯》及《戴欧》当中。而在较此晚很多的传奇当中,像《高文爵士与绿衣骑士》及无数其他涉及亚瑟王朝
的故事,尽管存在政治和道德主题,但均不甚关乎具体时空下的实际问
题,也游离于积极的政治生活之外。在史诗中,维护社会秩序乃是至善
至上的目标,而主人公体格与智力的修行都以此为尊。史诗的社会往往
是特定的社会,其残垣断壁可由现代考古学家进行甄别。《贝奥武甫》
的哀歌之风在一定程度上只是源自主人公为保护其社会免于妖敌肆虐而
喋血疆场。然而在更大程度上,这悲情的产生却是由于我们认识到贝奥
武甫的力量和智慧遭受了徒劳的消耗。他身上的那些品质未能在丹麦人
和耶阿特人(Geats)(49)
当中流芳百世,而他所援救的社会也因无法躲
避纯粹社会性的诟病而注定走向衰亡。
就像荷马一样,《贝奥武甫》的创作者同样描绘了一位在现场进行
表演的口头吟唱诗人。贝奥武甫于牡鹿厅(Heorot)(50)
击败戈兰德尔
(Grendel)之后的那个早上,丹麦人前来察看那只带血的胳膊,并走
访戈兰德尔得以消隐的那个沾满血迹的湖泊。作为他们欢庆的一部分,一位诗曲满腹的吟唱诗人就贝奥武甫的事迹创作了一首新作品,“编织
得如行云流水一般”。这位诗人接着讲到屠龙者西格蒙德
(Sigemund),又提到赫里摩达(Heremod)——一位丹麦国王,其罪
恶行径与贝奥武甫和西格蒙德的英勇之举形成鲜明对照。这个小段落
(B版手稿867—915行)的意义在于,它不仅说明在口头传统中,神话
所保留的价值观如何用来指导对于当下事件的理解,同时也说明当下事
件如何被传统兼收并蓄。通过将贝奥武甫击败戈兰德尔,以及西格蒙德
屠龙这两个母题相联系,这位吟唱者就诗歌结尾处贝奥武甫本人与龙妖
对抗的意义做出了一个主题性的陈述。这场屠龙之战,至少在某种意义
上说,可以理解为对戈兰德尔片段的重述,在那一处,西格蒙德已经作
为一则类比被作者加以引证。《贝奥武甫》再次表现出与《荷马史诗》的相似,它凭借其传统语
汇和历史典故传达出这样一种印象,即这类诗作势必在其所描绘的贵族
社会中得以吟唱。换言之,我们觉得,一群农夫或虔诚的僧侣只会推崇
圣徒的生平或是一首有关其社会及精神楷模的歌谣,而不适合成为欣赏
《贝奥武甫》的听众。我们从古罗马作家那里听到大量描绘日耳曼文化
的抒情短歌(cantilenae)或田园诗(carmina rustica),但这部作品绝
非此类题材的范例。如果我们的直觉是正确的,那么《贝奥武甫》所代
表的恰恰是让真正的口头传统发挥其至上的文化功效,即针对天子的教
育。而当英国皈依基督教,以及作为贵族教育基础的读本文化得以确立
之后,此种功效在许多代人的历史长河中则再也不可能实现了。这就证
明,该作品确系早期创作。
假如阿尔弗雷德大帝(King Alfred)阅读或听别人朗诵《贝奥武
甫》,那么,他准会心存些许伴有优越感的怀古之情;正如我们在面对
某个久已逝去的文明时,也难免会有相同的感受。阿尔弗雷德对于读写
和书籍的态度完全是现代意义的。在他看来,懂得阅读的人寥寥无几,这无疑是他那个时代巨大的文化耻辱;他建立学校和图书馆的目的并非
去永久保存像《贝奥武甫》这样的作品。历史、法律、哲学,以及《圣
经》方是他心仪的课程。当他打发闲暇之际,吟唱诗人会伴随其左右,而他也乐于学习他们的基本技艺,但无论他如何快乐,其国家政策注定
了口头文学的消亡。阿尔弗雷德之所以被尊称为“大帝”,主要是由于他
与古代传统决裂的勇气,而并非其保存这些传统的努力。
与盎格鲁—撒克逊口头叙事相比,像《罗兰之歌》这一极具代表性
的古法语口头叙事艺术似乎对书本更具亲和力,也更为时下的基督教文
化所接受。《罗兰之歌》的创作比《贝奥武甫》至少要晚300年之久
——约公元1100年,但我们同样觉得该作品大致描绘了催生其创作的那种贵族式、英雄体文化。中世纪传统一直认为,《罗兰之歌》的某一版
本曾被行吟诗人泰耶弗(Taillefer)拿来吟唱,以鼓励即将奔赴黑斯廷
斯战役(Battle of Hastings)的诺曼将士。这种说法与许多关于英雄体
诗歌如何在战场上发挥宣传功能的叙述不谋而合。古法语史诗传统的兴
旺极为持久——足足延续到中世纪鼎盛期,而我们通常把这个时期同传
奇,以及由传奇和普罗旺斯语(Proven?al)(51)
抒情诗所激发的文学革
命相联系;这就证实,一种合理的传统必然具备持久性和灵活性。小
S.G.尼克尔斯(S.G.Nichols,Jr.)在调查数部古法语“武功
歌”(chansons de geste)(52)
的程式模板及“论题”时得出结论:《罗兰之
歌》文本乃形成于“口头程式化的传统语汇”。
在日耳曼北部,文化融合的可能性似乎并不缺乏,但对于古法语史
诗传统来说,只有将这种融合进行得更加激进,方足以解释加斯顿·帕
里斯(53)
所谓的“罗曼语(54)
形式的日耳曼精神”(esprit gemanique dans une
forme romane)。根据查理曼的传记作家艾因哈德(55)
的说法,查理曼
(执政期768—814)与其子“虔诚者路易”一样乐衷于将拉丁文学技艺的
成果赋予自己的日耳曼臣民。在《查理曼大帝传》(Vita Caroli
Magni)中,艾因哈德记载说,查理曼将撒克逊人、弗里斯兰人及图林
根人(56)
的未成文法编撰成书面文件。更有意味的是,他还让人“把过去
那些欢庆古代君王武功勋业的陋俗之歌写出来以传后辈”。当然,最重
要的则在于他保持了一个国家的基本稳定,使莱茵河两岸分别讲日耳曼
语的法兰克人及撒克逊人和讲法语的民族团结起来,这样便促使口头史
诗传统中的主题和形式元素跨越语言壁垒,实现其从日耳曼语向罗曼语
的传播。此时,日耳曼传统一方面正成为教会的服务工具,另一方面也
正以书面形式被记录下来,留给(有望识字的)子孙后代,而罗曼语史
诗传统则成功地得以在查理曼开创的新世界中幸存和兴盛。到了11世纪,那些征服英国的北欧人正说着法语。以往日耳曼的军
事及政治组织天赋正于第四、第五代日耳曼领袖的统治下,得以在欧洲
的罗曼语地区恢复生机;这场在异国土地上复兴英雄勋业的运动同样缔
造了异邦语言对英雄体传统的复兴。就古法语史诗传统能够反映当下时
代变化这一点来说,最好的例证莫过于它对罗兰之死的处理方式。778
年,加斯科尼人(Gascon)(57)
在比利牛斯山区对查理曼后卫部队发动
进攻,但艾因哈德在其叙述中只是将此事件作为一个小插曲,安置在针
对北方撒克逊人和南方意大利人的军事行动之间。此处只有一种可能
性,即讲巴斯克语的加斯科尼人发起攻击的动机只是出于他们对独立的
向往和对法兰克人侵略自己领土的憎恶。这次战斗中的阵亡人员中除却
许多其他人员外,还包括“御膳官埃吉哈德(Eggihard)、宫伯安塞尔姆
(Anselm)和布列塔尼(Brittany)边区总督罗兰”。在这次交战之后,艾因哈德明确表示,没有任何讨伐行动能够用来对付加斯科尼人。身着
轻装作战于熟悉地形,他们乘着夜色的掩护带着从法兰克军队辎重中获
取的丰厚战利品顺利撤离,而此时那些全副武装的法兰克人还没来得及
调遣。
从8世纪到11世纪,这一故事片段的呈现,即我们现在所熟悉的样
式。巴斯克人和法兰克人变成了穆斯林和基督徒。这两支军队进行了一
场世界大战,其结果是:一个实质上的11世纪法兰西民族与一个11世纪
的战斗教会(Church Militant)(58)
在岌岌可危之中得以幸存。于是,这
种沉闷的历史叙述将其政治及社会寓意进行了大力引申,以反映第一次
十字军东征时期的欧洲现实状态——从8世纪的部族社会群向现代欧洲
过渡。与此同时,该历史叙述也在篇幅上有所收缩。这种寓意引申之所
以能够发生,原因就在于史诗传统能够多少准确反映当下社会的重要事
实与价值观念。当然,史诗的英雄观则要求对历史叙述加以收缩。在出
现于这场战役的人物中,罗兰从最次要的角色被提升为最重要的形象,而两支庞大军阵之间的全部问题则直接聚焦于他一人身上。
不过,如果没有格外的谨慎,而只是将罗兰之死的历史叙述与诗歌
描绘进行对比,则会让人误入迷途。大多数研究中世纪史诗的学者都知
道自己在调查过程中所依赖的相关实物乃是各种文本——民间故事、生
殖神话、历史纪事,以及教父神学(patristic theology)(59)
等。诚然,这些文本有一个极大的优势,即它们能确凿地证实自身的存在。但是,书面文本不可能在口头传统研究中被赋予高度的实用价值,至少不能以
平常方式对它们加以信赖。我们有必要结合文本和我们对于具体历史事
件的知识(不局限于当时的叙述)以尽量重构口头传统的属性。正是古
法语口头传统缔造了《罗兰之歌》(或牛津手稿(60)
所参照的那个版
本,类似情形在先前讨论《贝奥武甫》和《荷马史诗》时亦曾得以概
述)。如果我们按常规着手研究,即关注一个事件的历史性叙述,那么
史诗对这一事件的处理则会表现为,以明显非历史性的神话和“论题”对
其进行富于想象的歪曲和参合。另一方面,假如我们首先尽力重构口头
传统这一准确概念,那我们则会认为,历史事件不仅侵扰了传统的神话
与“论题”素材,而且还进而要求传统做出某种适应性调整,而不是反
之。贝奥武甫的原型无疑存在于盎格鲁—撒克逊史诗传统中,直到后来
他才与6世纪发生于丹麦与哥特兰(Gotland)(61)
的历史事件相联系。古
法语史诗传统中罗兰的原型也在《罗兰之歌》衍生的过程中成为历史事
件推崇的对象。
因此,在分析任何口头诗体叙事与历史的关系时,便会遇到一个实
际问题,即传统神话和“论题”在多大程度上可能已被替换为适时再现的
独特事件(如果我们能够借助考古和文学推论去重构那些事件的话)。
如果此替换是彻底的,那么,该传统则不能被称为史诗性传统,相反,它已经接近了格律化纪事。倘若没有发生任何显著的替换,那么,此传统便会演化为宗教神话或是(当“论题”被明显清空了其仪式内容或寓言
内容时)传奇。口头史诗会通过再现历史事件去替换一些传统神话
及“论题”,此外也会通过再现更为笼统的假想现实去替换其他神话
与“论题”。我们发现,那些体现出显著心理及社会类型的人物在其行为
上所依照的自然法则(natural laws)也同样适用于现实中的人。
所以,我们在分析《贝奥武甫》这样的史诗时,不能以为它们源自
民间故事和生殖神话对心理学和历史学的入侵。同样,在探讨具体诗歌
之际,我们也不可将历史学和心理学当作进犯者。真正迷恋它们的乃是
口头传统,而并非个别诗作。任何单独的口头表演或文本既为其传统语
法所造,亦为之所限,且只反映该传统所固有的无限可能性当中的一种
方案。当我们不再将纯粹神话或纯粹摹仿当作规范,那么,中世纪传统
诗体叙事当中针对确凿历史事件的影射则显得再正常不过。当然,同样
正常的是,它们的历史也不会是塔西佗(62)
、圣比德或C.V.韦奇伍德(63)
书写的那种历史。贝奥武甫身上带有谷神的痕迹不足为奇,但他却算不
上是另一个奥利西斯(Osiris)(64)。虽然我们在上文将口头史诗传统称
作综合体,但它并不是意识化的产物。当然,它也并非发端于某一纯粹
状态,而后又将自己提炼成另一种纯粹状态。唯有此综合体——而非任
何一种纯粹的形态——方可被称作是史诗性的。
古法语史诗在与克雷蒂安及其追随者创作的传奇不期而遇时衍生出
一种诗歌类型,对此,我们尚无专门的称呼。然而,我们发现16世纪大
卫·林赛(65)
的一部杰出的小作品《乡绅梅尔德伦传》(Squire Meldrum)
正是这一类型的绝佳范例。从《罗兰之歌》到《乡绅梅尔德伦传》这条
发展脉络不仅包括像巴伯(66)
的《布鲁斯本纪》(Bruce)及布莱因·哈里
(67)
的《威廉·华莱士列传》(Wallace)这样的书面英语诗歌,还包括西
班牙的《熙德之歌》(Poema de mio Cid)——这部作品直到英雄熙德1099年辞世后约一代人有余的时间方得以创作。从历史的角度看,《熙
德之歌》在叙述上极为准确,其口头风格清晰、有力,完全没有渲染之
迹。其中产阶级主人公壮举背后的动因既是出于自身社会抱负和女儿们
的利益,同样也是出于罗兰式英雄的个人荣辱观或查理曼对于统一基督
教帝国的梦想。《熙德之歌》不同于《乡绅梅尔德伦传》,因为它的故
事所关注的仍然是民族舞台上的英雄。他击溃了庞大的穆斯林军队而成
为其民众的救世主。但《熙德之歌》乃是大众之歌,这一点有别于《罗
兰之歌》,甚至更有别于《贝奥武甫》和埃达歌谣。与早期史诗相比,其受众在社会性层面上(如果不是在历史性层面上)进一步疏离了对于
丰功伟业的歌颂。《熙德之歌》赖以产生的口头传统同样是歌谣创作的
源泉。其文化取向的弱化恰恰反映了史诗传统,尤其是口头史诗传统。
《布鲁斯本纪》和《威廉·华莱士列传》尽管系具体作者的书面创作,但延续了旧式史诗传统的内核,并有所创新。对于当下读者而言,它们
的新意在于试图将新经验叙事的内容与旧虚构叙事的风格加以综合。这
一文类的作品有时被称为“纪事性诗歌”(chronicle poems),不过“格律
化传记”(metrical biographies)也是一种可行的概念。
纪事性诗歌与我们所谓的寓言式解剖(allegorical anatomy)——另
一种在某种程度上遭到忽略的文类,其代表作品包括诸如《玫瑰传奇》
(The Romance of the Rose)(68)
和《农夫皮尔斯》(Piers Plowman)(69)
等引起学界关注的长篇诗作——在中世纪方言叙事诗歌中占据相当大的
比重。以现代批评视角对这两种形式加以分析并非易事。在某些方面,它们的定位似乎介于史诗传统因解体而产生的两极之间:散文体历史与
格律化传奇,两者不难在现代意义上加以识别。斯诺里·斯特卢森(70)
与
让·德·热安维尔(71)
创作的历史著作在诸多方面堪比古典时期的历史创
作。当然,传奇也从不缺乏仰慕者。但是这两种主要文类并没有穷尽叙
事的可能性。寓言式解剖斡旋于哲学推论与传奇之间——其复杂性我们将在后面的章节加以探讨,而格律化传记和纪事性诗歌则介乎传奇与历
史之间。正是这后一条介乎传奇与历史之间的路线引领着史诗走向小
说;在所有以口头传统循此路线发展的中世纪叙事形式当中,要数冰岛
的家族萨迦(72)
(family saga)走得最远,而后才为拉丁典籍和《圣经》
所超越。
对于13世纪的冰岛来说,文化孤立显而易见,而这恰恰使得其叙事
艺术的价值几乎达到了一种不可思议的高度。它可能借鉴了爱尔兰散文
体叙事,并得益于日耳曼民族对散文风格及世俗史所与生俱来的天赋;
不过,这一传统即便确实如此,却并无相关记录得以留存下来。就家族
萨迦而言,虽然它们没有对后来的欧洲散文体小说产生实质性影响,但
形成了其自身纯粹的形式、内容及风格,并因此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独
立的研究价值。它们不属于书面萨迦传统,因为后者突出作者身份及文
学借鉴(literary borrowing)这些颇具现代意义的操作原则。家族萨迦
的风格在具体文本之间表现出明显的一致性和程式化。尽管许多评论家
在它们当中找到相似的段落以证明家族萨迦作者之间的文学借鉴关系;
但这种相似性若被看作惯常的口头传统因素则更易理解。虽然这些家族
萨迦无疑属于书面创作,虽然每一个单独的萨迦文本理应由一位作者独
自创作,但现有证据似乎并不能说明这些作者乃是依赖于书本或个体发
挥来获取其故事的主要元素。如果这些家族萨迦的创作只是任何类似现
代意义上的个体行为,那么,它们将会失去其现有的光彩。
公元1000年左右的冰岛已掌握了书写,伴随其议会将基督教确立为
国教,它至少拥有三种经过完善演化的口头传统。第一种便是口头诗歌
传统,其残余在《诗体埃达》中尚有所保存;关于此传统,我们的证据
基本来自其在形式及主题方面与其他遗留下来的异教性日耳曼叙事诗之
间的相似之处,当然,这也暗示了两者均具有明显前读写文化(pre-literate culture)的渊源。此外,埃达诗歌本身的程式和“论题”也提供了
辅助性证据。第二种口头传统是法律,即由选举出来的法律演讲人(73)
(“lawspeaker”)于三年任期内的每一年在议会背诵《法典》三分之一
的内容。第三种口头传统是历史。如果设想在斯堪的纳维亚文化当中存
在一种包罗万象的口头史诗传统——融汇世俗史、法律、神话、仪式及
民族智慧结晶等各种元素,那我们认定它应该远早于870年的“冰岛定
居”。到了12世纪和13世纪,我们则不仅能找到书面证据以说明它已经
演化为一种高度分异的文学文化,同时还能借助于推论性证据以说明其
相对古风(antiquity)的一面。换言之,在冰岛人掌握书写之前,他们
已进一步朝向实质性的现代叙事形式发展——既包括散文体,也包括诗
歌体——在这个方面,他们要早于书面《荷马史诗》产生之际的希腊
人。正是凭借其文化上的孤立性,冰岛人通过激进的革新将《圣经》到
来之前业已兴盛的日耳曼叙事传统继续发扬光大。他们做出这样一种展
示,即目不识丁的艺术家们虽极少受到读本和书写的影响,却能够创作
出世俗史和现实主义的散文体小说。由于人们通常以为,伟大的艺术散
文和世俗史在缺乏书写与具体作家身份的情况下是不可能得以发展的,所以在过去,冰岛叙事的卓越品性恰恰一直被当作最佳证据以推翻家族
萨迦系口头创作的观点。然而,伴随《荷马史诗》范式的建立,以品性
求证的论断即便尚未完全遭到颠覆,至少也难以站得住脚了。
家族萨迦或“冰岛人萨迦”(íslendinga s?gur),只是数个重要冰岛
散文类别中的一种。除它们以外,一方面是关于各位君王和主教的诸多
传记,尤其是历史,如《斯特龙戈萨迦》(Sturlunga Saga)(74)
和《天
下:挪威列王纪》——内容分别涉及发生于当时冰岛的事件,以及挪威
诸君王的生平;另一方面是所谓的“古代萨迦”(“sagas of former
times”),以散文体形式复述早先口头诗体叙事传统的主题,即英雄和
神话故事——《诗体埃达》中还保留着一些实例。《沃尔松萨迦》(75)(其故事与德国史诗《尼伯龙根之歌》几乎同时出现),以及《霍尔夫
斯·克拉卡萨迦》(76)
(类似于《贝奥武甫》)正是这类萨迦叙事。最后
需要指出的是,“古代萨迦”似乎与许多经过翻译的法国传奇(“骑士萨
迦”[riddara s?gur])通过融合而衍生出所谓“奇幻萨迦”(“lying sagas”)
这样的杂交品。“奇幻萨迦”的创作到了现代时期仍得以继续,与之并存
的还有极其丰富的民间故事传统,以及被称为“韵文”(“rhymes”)的通
俗化歌谣体叙事诗。
我们在上文姑且就13世纪冰岛的叙事文类简要做了一个专业性概
述,既说明口头史诗传统在适当的条件下如何能够产生出裂变的巨大能
量,同时也说明不同的叙事趋向如何能够快速渗透到各个独立的叙事类
别中。在冰岛,我们不仅看到了希腊模式的重复,即史诗综合体让位于
历史和传奇;而且,我们还在家族萨迦中发现了一种融合神话与摹仿的
新综合体——现实主义的虚构叙事。自埃达叙事失去其文学精英的关注
到最后一部家族萨迦得以创作的那三百年(1000—1300)间,冰岛见证
了其叙事形式的衰退和演进,而同样的发展过程在欧洲本土则耗费了两
倍以上的时间。
在《天下》(如此称呼是因为其第一部分头两个字的意思是“天
下”[“the world's circle”])的序言中,斯诺里·斯特卢森告诉我们,其作品
所依据的是历史创作的口头传统。他的主要资料包括宫廷诗人用以颂扬
所侍君主的诗歌,以及“智者阿里”(77)
几乎全凭口头传统所创作的历史作
品,另外还包括那些饱学之士所提供的信息(可能通过对话)。作为头
脑清醒的历史学家,斯诺里唯实求真。在其序言中,他就如何运用其口
头资源及判断各种变量的可靠性阐发了一套比较周全的方法。他所提到
的宫廷诗歌必定在历史创作的口头传统中扮演过复杂的角色。它不是传
统的埃达诗歌,而是在押韵和措辞方面更为复杂的作品——吟游诗歌(skaldic poetry)(78)。
正如家族萨迦那样,《天下》当中存在着大量的吟游诗,而且所联
系到的有名有姓的诗人通常在历史上都确有其人。如果将口头创作仅仅
看成是运用一套固定的口头“语法”面对受众进行的快速创作,那么在此
意义上,这些吟游诗可能还算不上是口头创作;当然,它们在创作时,或至少在传播的过程中,并未使用书面材料。这些短小、固定的诗歌文
本在以书面萨迦文本的终极形式出现之前,虽历经许多代人的岁月却仍
得以幸存而完好无损。它们常被用来体现一则故事当中的重要时刻,不
仅具有主题功能,亦可发挥结构功能。或许,在历史性散文的口头传统
当中,它们算得上是一种重要元素。
与希罗多德相比,斯诺里的思维习惯在实证性方面明显逊色于其希
腊前辈,他对历史叙事形式的看法相对而言不够缜密。他虽然唯实求
真,但其标尺却是诗性的,而非实证性的。尽管他就奥丁(Odin)(79)
的兴起所做的讲述,以及他通常对神话人物所进行的处理均表现出相当
的合理性,但他不像希罗多德那样从总体上将诗人质疑为幻视幻听的群
体,当然也缺乏希罗多德就或然性所持有的理性标准。就叙事形式而
言,斯诺里热衷于谱系模式,这种形式使他能够运用所掌握的素材去详
细描绘那些自己颇感兴趣且十分了解的统治者,如圣·奥拉夫(80)。斯诺
里的叙事绝非希腊式的——后者将经过理性检验的叙事熔铸于一种统一
的局限形式中;而斯诺里的叙事则是经过诗性的检验,以谱系叙事的松
散形式加以展现。
从某种意义上说,《斯特龙戈萨迦》(“斯特龙戈家族史”)相对于
《天下》来说代表了一种进步。由于它将数个作者创作的历史叙事松散
地组合在一起,因而在形式上缺乏足够的统一性,算不上一部独立的作
品。但是,这个故事集将其主题限定于大致发生在1120至1280年之间冰岛的历史事件,而且,作为这部作品的内核,斯特拉·索尔达森(81)
的
《冰岛人萨迦》(íslendinga Saga)以完全令人信服的口吻讲述了政治
动荡及斗争时期那些伟大人物及虚构人物的生平。若与修昔底德相比,《斯特龙戈萨迦》可能只是将轶事和密集堆砌的细节拼凑在一起罢了;
但冰岛人在其世俗史当中对希腊历史学家的神话元素进行了剥离,使之
更为强烈地产生一种准确(但未必总是艺术化)叙述的印象。在《斯特
龙戈萨迦》,以及有关冰岛法律的书面记录中,我们发现原始日耳曼理
性主义被推向了极致。法律只是作为一种粗劣替代品以取代希腊历史学
家们所操守的、经过充分演化的理性思想传统。从异教性的日耳曼文化
中,根本没有衍生出任何类似于希腊哲学推论的东西。也许正是出于这
个原因,将神话从历史叙事中加以清除变得更为紧迫。如果说冰岛的历
史学方法总是趋向于传统而非趋向于推论性思想,那么这一传统则要归
功于那些讲求实际的律师们所进行的实用主义改良。法律演讲人和历史
学家绝大多数时候是由同一个人扮演的。
家族萨迦利用了历史学典型的谱系构架,但其聚焦范围则往往要狭
小得多。比如,在《尼雅尔萨迦》(Njáls Saga)(82)
中,故事仅限于三
代人,而重点则放在古恩纳尔和尼雅尔那一代人身上。正如《斯特龙戈
萨迦》中所出现的一些个人历史那样,《尼雅尔萨迦》的叙事表达也是
直接取材于源自冰岛生活的母题;事实上,这也是个完美的母题,它使
得家族世仇这一谱系化叙事模式表现出整体感与具体性。民法在冰岛的
兴盛虽然牺牲(或代替)了其他领域的公共生活,但它本身却不可避免
地将一种近乎人为的秩序施加于冰岛人的生活之上,从而为萨迦创作者
们提供了现成的叙事表现素材,并自然产生出一种贴近历史及当代现实
生活的独特叙事类别。萨迦在一位大师手中所能展现的那种力量与洞
察,乃是传奇作家们无以企及的。尼雅尔本人作为法律人士恰恰陷入了
一场无视法律的家族斗争之中。在他身上,我们看到了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冲突,它作为一个特点体现了虚构与经验这两种趋向的融合;而由此
所获得的问题化品性则使得这类叙事作品,一方面迥异于传奇——因为
传奇中的叙事及其诗性的正义更易于把握,另一方面又与历史的必然性
大相径庭。
在家族萨迦获得其书面创作的那段时期,《诗体埃达》当中所保留
的口头诗体叙事传统究竟有多重要?这个问题似乎不可能有答案。无
疑,萨迦的人物与事件在某种程度上(或许要超过人们通常所认为的比
例)来自埃达叙事的传统“论题”。哈尔盖德(Hallgerd)(83)
是《尼雅尔
萨迦》中少数几个非历史性人物之一,她与埃达诗《西格尔德短歌》中所出现的布伦希尔德(Brynhildr)(84)
相映成趣。另外,在《格雷蒂尔萨迦》(Grettis Saga)(85)
中有一场历
险,当时格雷蒂尔跳入潭中去挑战魔兽,这一幕与《贝奥武甫》里的一
个片段惊人的相似。甚至在《尼雅尔萨迦》中,古恩纳尔这一人物的意
义也多少来自早先史诗对该形象的构想。他所遭遇的世仇不仅吞噬了自
己,也吞噬了尼雅尔家族。这不只是例证了一个风雨飘摇的现实,以及
与之形成对照的法治理性观念,而是展示了主人公的神话理想与法治理
性观念之间的冲突;这种冲突在历史上的确使得斯特龙戈时代呈现出一
片天下大乱的局面,当然,也正是在这一时期,萨迦的创作出现了。从
某种意义上说,家族萨迦就是散文化的史诗,它一方面对神话及寓言性
元素进行大幅度缩减,另一方面又大力强化历史与摹仿的重要性。不
过,由于这种抑制神话、强化摹仿的倾向表现得近乎彻底,所以它们有
时似乎更像小说,而不是史诗。
冰岛叙事艺术的真正奇迹在于历史,没有它,家族萨迦可能无从产
生。它完全基于事实,充满谱系性的枝节,而且(如《斯特龙戈萨迦》
所示)在描绘具体人物时也是直言不讳。关于家族萨迦,一种最简化的理解就是:它将历史和法律这一层面与传统史诗这一层面加以融合,而
史诗的“论题”及神话又几乎总是让位于代表理性及世俗现实的主题、情
节及母题。史诗自身几乎无法抵御历史和基督教的双重侵袭,而只得以
诗歌的身份被更具“诗性的”吟游诗所取代。那种将埃达短歌看作叙事演
化之“前史诗阶段”的理论似乎毫无根据,因为这些经过高度凝缩的英雄
体叙事典范所反映出来的恰恰是背离史诗这一整体文化运动,而不是走
向史诗。在更为早先的时期,埃达传统无疑曾经是经验性叙事与虚构性
叙事之间的中间路线,而到了12世纪,史诗已经难以为继。其神话的力
量因基督教而元气大伤,同时,其情节的有效性也受到历史和法律的挑
战。
假如没有城市文明,没有哲学思辨的传统,也没有“生活切
片”(slice-of-life)式的讽刺传统,那么小说在理论上是不可能产生的。
然而,冰岛的家族萨迦倒是代表着一种由旧式史诗与新的经验性形式组
合而成的二次综合体(re-synthesis),它与三百年后欧洲其他地区所出
现的这种二次综合体至少在某些方面表现出相似性。继斯特龙戈时代之
后的数个世纪中,随着欧洲中世纪逐渐向冰岛逼近,旧式史诗叙事的纯
虚构趋向虽然依旧可以通过诸多思想虚空的“古代萨迦”“骑士萨
迦”及“奇幻萨迦”得以彰显,但它的经验性趋向却已消耗于那些伟大的
历史作品与家族萨迦之中,以至于在那些充满恐惧的黑暗世纪中,再也
无法创造出不朽的丰碑之作。
萨迦 ? ?
这个表述从“segja”(冰岛语意为“讲述”)这个字派生而来,在
冰岛语当中现用以指任何散文体叙事,无论篇幅长短,也无论是口头还
是书面。当冰岛人着手将许多代人作为口头叙事存在的传统故事书写下
来的时候,他们显然不仅用萨迦 ? ?
这个词代指故事,而且也用它来代指对
故事的书面记录。那些用以区分历史(萨迦 ? ?)、家族萨迦(冰岛人萨 ? ? ? ?迦 ?)、英雄体萨迦(古代萨迦 ? ? ? ?)、传奇(骑士萨迦 ? ? ? ?),以及美妙历险
(奇幻萨迦 ? ? ? ?)的术语都是现代意义上的。尽管这样的区分对于专家而言
既具有逻辑性也不乏必要性,但对于一般的文学研究者来说,“萨迦”这
个词最好能比它在现今冰岛语中的使用多一分意义上的限制。在大众化
的美国用法中,这是一个能够增色的字眼。那些对史诗感到腻味儿的读
者虽然不再因“史诗”而感到精神振奋,但如果《伊利亚特》这首诗被描
述为一部惊心动魄的特洛伊战争“萨迦”,他们却可能会趋之若鹜;而那
些用于电影剧本的“萨迦”和“史诗”,实际上更准确的提法应该叫作英雄
体传奇。如果没有其他具体修饰语的限制,“萨迦”这个词在文学批评中
的正确用法应该是代指冰岛的家族萨迦,以及其他类似的、达到小说篇
幅的现实主义传统散文体叙事。这里的关键词是“传统”,否则萨迦便无
法与小说区分开来。所谓“传统”,就是指带有口头创作之形式特征及修
辞特征的叙事。
口头创作的形式特征在上文已经有所描述。其中最重要的就包
括“程式化”语汇;也就是说,传统“语法”操控着口头创作的语言,它通
过对总体文化语言加以筛选以提取为数不多的模式,并借此形成符合格
律(指诗歌这种情形)、句法和语义的恰当表达。口头叙事艺术家一旦
掌握了这种“语法”,便能够面对观众进行口头创作。按照人类的普遍经
验,散文句式的口头创作要难于完全格律化诗歌的口头创作。一些批评
家认为,散文之所以无法发展成为口头创作,是因为人们很难驾驭散文
句式的逻辑和句法节奏。对于那些目不识丁的人来说,这就意味着诗歌
仅限于其美学功效,而诺斯洛普·弗莱所谓常规语言的“联想节
奏”(associative rhythm)(86)
也就只剩下其非美学用途。然而事实正相
反,只要详细分析家族萨迦当中著名的“萨迦风格”,我们便会发现冰岛
口头叙事散文当中实际上存在着一种“语法”描述。这种“语法”的存在正
是中世纪冰岛口头散文成就的主要基础。可以说,散文的口头创作必然是高度程式化的。
口头叙事的另一特点是母题与情节在主题意义上的一致性。此类意
义之所以成为可能,乃得益于传统“论题”和神话,而这些传统叙事元素
又同时掌控着故事对现实的再现及其对观念的阐释。为了探究一种叙事
语汇的程式化特征或其结构与主题的传统属性,批评家们所调查的叙事
体必须具有足够大的规模,以体现各种规范并至少能代表“传统”的一块
残片。幸运的是,我们拥有富足的荷马语料库。盎格鲁—撒克逊传统在
语料库方面则显得捉襟见肘,而对于埃达传统而言则可能是杯水车薪。
然而,口头创作的叙事除了其纯粹“形式化”的特点外,还在“修辞”——
姑且从狭义上这么称呼——层面上与个体叙事艺术家们的作品有所区
别。从这一方面来说,许多传统叙事即便没有同更多的文本进行比对,至少可被暂视为传统之作。
口头叙事总是采用一位权威性的可靠叙述者。他就像荷马及《旧
约》作者那样富于天赋,能够从所有角度对行动进行观察,道出人物心
中的秘密。我们习惯于将这位全知叙述者等同于作者,并以为该作者无
处不在地为我们阐释和评价其叙事中的人物与事件。不仅如此,我们还
习惯于认为这位可靠的、全知的,且无处不在的叙述者是“客观的”。我
们这样说的意思是,此类叙述者再次与荷马及《旧约》叙事的作者们表
现出相似性,他所谈论的并非是自己而是其故事当中的人物与行动。同
样,他也不会为了营造自己与其受众之间的亲密关系而牺牲他们对于故
事本身的认同。当亚里士多德赞扬荷马善于身栖他人性格之际,其所表
之意显然是指:荷马既非谈论自己,亦非将自己游离于故事的利害关系
之外。当然,如果从另一个意义上将“客观”理解为采用一种类似于中立
人物的视角去观察纯粹外部性的事件,那么,全知性叙述者还远算不上
是“客观”的。而他之所以被视为客观则既是因为他并非“主观”,也是因为在其本人与作者之间或在其自身的关注与故事所隐含的关注之间并不
存在反讽性的差异。在下文讨论叙述视角的一个章节中,我们将注意到
荷马对缪斯女神的召唤乃是朝向作者自省意识的发展。如果说,常规标
准将传统口头叙事看作是由一位“客观”的权威叙述者所进行的讲述,那
么,召唤缪斯这一高度模式化的手法则作为一种例外稍稍改变了这一标
准。
由于传统故事的作者与讲述者之间不存在反讽式差距,因此,我们
习惯上不对他们进行区分。受众分享叙述者的知识与价值观,在对故事
的人物及事件做出评判时总是依赖于后者。受众如叙述者一样具有料事
如神的洞察力,这就解释了传统叙事中仅有的虚构性反讽:叙述者和受
众均了解故事中的人物,而他们却不可能认识彼此,甚或是认识自己。
随着自省式讲述者在非传统书面叙事中的发展,这样的反讽情景不断增
加。在小说中,叙述者对人物的看法和人物对自身及其他人物的看法总
是存在着差异,而这种差异性又因为叙述者与读者对故事的不同看法而
得以增强。因此,在任何书面叙事中,作者与其叙述者之间通常会在认
识及价值观层面上表现出实际的——或至少是潜在的——反讽性差异。
传统口头叙事从修辞上看包括一位讲述者、其故事,以及一位隐含受众
(implied audience)。而非传统书面叙事在修辞层面上则包括摹仿 ? ?
或再 ?
现 ?
性的讲述者、故事及隐含读者。
从修辞意义上说,书写的运用使得创造性的个体叙事艺术家能够将
其故事的复杂性及潜在的反讽性推向一个更高的水平。这一新水平的实
现似乎源于自省式叙述者的引入,以及叙述者一方与作者及读者另一方
之间的反讽性差距。然而,借助于我们对口头叙事的讨论,可以发现,真正将空前的复杂性赋予书面叙事视角的因素并非叙述者的引入,而是
作者 ? ?
的引入。令人尴尬的是,在讨论口头叙事的整个过程中,我们不得不使用“现代意义上的作者”这种表述。我们已经指出,《荷马史诗》、《旧约》、《贝奥武甫》、《罗兰之歌》、家族萨迦、《卡勒瓦拉》
(Kalevala)(87)
、法罗语歌谣,以及其他口头叙事并非由“现代意义上
的作者”所创作。就通常用以吟唱的叙事诗而言,我们会提及“故事的吟
唱者”。就口头创作的散文体叙事而言,我们会谈到“故事的讲述者”。
不过在这两种情形下,他都算不上是一位作者:他乃是作为一种工具,借助表演这种具象化的形式来体现传统。他是叙述者。用斯蒂芬·迪达
勒斯(Stephen Dedalus)在《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中的话说,他将
其故事置于“同自己及他人的斡旋关系之中”。
无论斯蒂芬对抒情性、史诗性和戏剧性的著名定义代表了何种批评
意义或神秘意义,它们的确说明了一种现代趋向,即把作者从叙事中撤
回。像荷马或莎士比亚那样的作家往往拥有一种显著的本领——他们能
够表现得“像创世纪里的上帝……身处其创造物之中或背后或之外或之
上,踪影不见,形骸不存,似有修剪指甲时的那份淡然之态”(88)。为
此,浪漫主义批评家们曾有溢美之词,认为此乃“同情化想
象”(sympathetic imagination)作为重要诗歌技法所能企及的最高境
界。乔伊斯本人在解决如何让作者淡出的问题时,其方法在某种意义上
说可谓是戏剧化的。他试图将叙述者与叙事加以融合,这样一来,他对
于三种重要修辞元素——讲述者、故事及隐含读者——之间互动关系的
摹仿就如同一部戏剧对于剧作家的关系一样。但是,无论乔伊斯如何精
巧地设置其叙述者与故事及读者之间的关系,他的叙事依然是对叙述者
讲述故事这一过程的摹仿。如果我们让自己稍稍走进斯蒂芬那神秘的美
学世界中,我们也许可以将乔伊斯的技法描述为对“史诗化”形式的一
种“戏剧化”再现。
口头叙事与书面叙事之间的修辞性差异曾由诺斯洛普·弗莱做过部分研究。虽然大量以诗体及散文体出现的传统叙事均系口头创作,但对
于相关的研究成果,弗莱并不了解,或至少未曾加以运用。因此,在区
分史诗 ? ?
([epos]按我们的提法叫作口头叙事)和虚构(书面叙事)时,他所提到的两种“叙事呈现的根基”(radicals of presentation)并未获得
其真正的意义。按照弗莱的定义,史诗“这种文学类别进行叙事呈现的
根基是作为口诵人的作者或行吟诗人,而观众则是其所面对的聆听
者”。虚构 ? ?
对于弗莱而言乃是“以印刷或书面文字为呈现根基的文学,如
小说和随笔”。这一区分尽管在实践上难以奏效,但却不乏真知灼见。
某些口头叙事的确背离了在观众面前进行表演这一事实,然而,我们不
要忘记这第二个事实,即它们之所以诉诸印刷页面的形式乃是为了呈现
于我们 ? ?;所以,从此意义上说,这种背离本身倒未必会破坏弗莱那种鉴
别方法的有效性。不过,从另一方面看,许多极富创意的非传统性书面
叙事在以印刷页面的形式呈现给我们的时候,倒仿佛是在面对观众进行
口头表演。作为现代例证,我们可以想起康拉德(Conrad)笔下那些以
马洛(Marlow)为叙述者的小说。
叙事呈现的根基如今正日趋转向印刷,这乃是情理之中的事。在大
多数情形下,那些未曾由作者书写下来的叙事会有别于其他由作者加以
书面创作的叙事,因为前者无法创造出一个叙述者以区别于某个地位更
高的创造者。中世纪传奇作为一种叙事文类在修辞上称得上是弗莱所定
义的史诗,但却不符合我们所定义的“传统口头叙事”。最伟大的中世纪
传奇并非口头创作,当然,它们也曾非常依赖于传统元素,有的甚至直
接取材于口头传统或口头叙事的手稿本。那些与克雷蒂安·德·特罗亚、沃弗兰·冯·埃森巴赫及哥特弗里德·冯·斯特拉斯堡(89)
等姓名相联系的传
奇或许应该归功于那些作家个人的创造性天赋。像“骑士的故
事”(Knight's Tale)(90)
和《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这样的作品则完全
是在现代意义上进行的书面创作。不过,在中世纪的传奇中,我们经常会遇到像乔叟或沃弗兰笔下的那种叙述者,他们的作用被描绘成向读者
讲故事。沃弗兰的叙述者甚至向读者承认自己目不识丁,并因此增加了
自己与作者之间的距离。当中世纪的叙事艺术家们突然获得这种新的作
家身份时,他们发现自己尚缺乏准备,进而显得有些手足无措。就像所
有作家一样,他们试图“让自己淡出文本”。为此,最自然的途径便是在
相当程度上直接摹仿讲述者面对听众传诵其故事。不过,即便是这样的
应急措施还是打开了潘多拉的反讽之盒,让诸如乔叟、沃弗兰,以及
(文艺复兴时期的)拉伯雷和塞万提斯这样的大师去占领新的阵地。
如果抛开斯蒂芬的观念而仅借用其表述,那么我们可以说,口头故
事的讲述者“斡旋”于故事与受众之间。这里既不存在用以构成反讽关系
的作者,而且(这就等于同义反复)也不存在用以形成反讽关系的故事
本身。口头传统既是故事,也是作者。如果表演者以故事为代价去博得
受众的亲和,那就等于以作者自居,如此一来,他对传统的运用也不过
是为了推进其个人所构想的目标。讽刺,若要存在于口头传统,则必须
植入该传统本身当中去。它不会作为功能化的反讽性差距存在于“作
者”与其创造的叙述者之间,或存在于叙述者的关注与其故事的关注之
间。
当口头传统遭受书面文学这一主导力量的冲击而遁入“地下”时,它
会自然反映出那些维系其兴盛的参与者们在知识、审美及社会等诸方面
的经验。在现代时期,口头传统的处境如此艰难,歌谣和民间传说占据
了最佳口头文类的地位。令人遗憾的是,对于《贝奥武甫》和《诗体埃
达》的口头创作论,反对者们却常常从歌谣与民间传说当中寻找评判的
依据。曾有人断言,《贝奥武甫》并非纯粹意义上的歌谣,因而必定是
出自一位个体创作者之手。我们在讨论长篇叙事形式的时候,并未试图
将歌谣或民间传说视为书面文学的口头传统因素;因为它们是书面叙事的竞争对象而不是影响势力,这种情况至少持续到浪漫主义运动。
口头叙事的形式特点在歌谣及民间传说中多少都会发生一些变化。
对这些文类产生深刻影响的因素不仅包括书面文学理念,也包括固定文
本概念,即个体叙事实际上并非伴随每一次表演而重新进行创作。这些
文本无疑源自真正的口头传统,而且确切地说,它们也并非某一原始版
本的“变体”。不过,即便是最低程度地诉诸书写,它们所获得的固定性
(fixity)也会超越真正口头创作的程式化语汇。
然而,“同情化想象”不止在口头叙事中促使作者及修辞性反讽淡出
文本,同样也在掌控着歌谣的吟唱与民间传说的讲述。但是,我们所处
的文学世界却受制于另一种截然不同的反讽势力:一方面是保守派学者
力求为《贝奥武甫》留住作者,另一方面却是先锋派叙事艺术家们在摹
仿民间传说的讲述和歌谣的吟唱,对他们而言,让作者淡出文本是其孜
孜以求的完美境界。
(1) 柏拉图文艺对话录之一,通过苏格拉底的弟子斐德若的回忆转述了苏格拉底临刑前与朋
友、弟子及其追随者之间的对话。
(2) 米诺斯B类线性文字:古希腊克里特(Crete)文明时期,即米诺斯时期(Minoan
Period),公元前3000—公元前1100)的一种书写文字系统,出现于希腊字母的发明之前。
(3) 阿波罗尼奥斯(Apollonius Rhodius,生卒不详):又称“罗德人阿波罗尼奥
斯”(Apollonius of Rhodes),约公元前3世纪的亚历山大诗人,常在史诗中注入心理描述及传
奇特征,突出叙述者的权威性。
(4) 南斯拉夫常用于伴奏叙事歌曲的一弦小提琴。
(5) 《诗体埃达》:又称《老埃达》(The Elder Edda),关于北欧传说及神话的诗,由冰
岛历史学家塞蒙恩德(1056—1133)收集整理,故又称《塞蒙恩德的埃达》。
(6) 基涅武甫:兴起于公元9世纪的盎格鲁—撒克逊诗人。
(7) 如尼文:约公元200至1200年,北欧及不列颠等地区使用的书面文字系统。
(8) 《诗体埃达》中的第一首,也是最著名的一首,讲述了世界的创造及末日的降临;诗题原意为女祭司的预言。
(9) 爱奥尼语:古希腊的一种方言,早期希腊诗歌的创作语言。
(10) 阿卡狄亚—塞浦路斯语:伯罗奔尼撒半岛中部的阿卡狄亚及塞浦路斯岛使用的一种古
希腊方言。
(11) 阿提卡语:古代希腊阿提卡(Attica)地区的方言,约公元前5世纪至公元前4世纪成为
古典希腊文学的标准语言。
(12) 麦西亚:英国中世纪早期七国时代的国家之一,位于今英格兰中部。
(13) 半行诗程式:古代盎格鲁—撒克逊口头诗歌的特点之一,即一句分为两个半句。
(14) 哈弗洛克(Eric A.Havelock,1903—1988):英国古典学家,曾从教于哈佛和耶鲁等
北美高校,是著名的古希腊文化、历史研究专家。
(15) 恩斯特·罗伯特·库提乌斯(Ernst Robert Curtius,1886—1956):德国文学评论家及语
言学家。
(16) 此处的原文locus amoenus系拉丁文,意为快乐的地方。
(17) 此处的原文puer senex系拉丁文,意为年轻长者。
(18) 下降阴府:基督教神学中的概念,出现于《使徒信经》(Apostles'Creed)和《亚大纳
西信经》(Athanasian Creed)的信规当中,指耶稣殉难后降临阴间拯救正义之士的灵魂,使之
脱离罪恶与死亡的枷锁。从此意义上说,耶稣乃是战胜了地狱的黑暗。所以,耶稣“下降阴
府”不仅表述为“descended to the dead”,也在不少场合说成“the harrowing of hell”(字面义为“入
侵地狱”),原著在此处采用了后者。
(19) 伊萨卡(Ithaca):希腊西海岸的小岛,相传为奥德修斯的故乡。
(20) 墨兰提俄斯:《奥德赛》中的羊倌,羞辱以乞丐形象假扮的奥德修斯。
(21) 欧迈俄斯:《奥德赛》中的猪倌,奥德修斯的忠实追随者,当假扮乞丐的奥德修斯发
誓说奥德修斯必将归来时,欧迈俄斯指责其为骗取钱财而故意说谎。
(22) 安提诺俄斯、欧律马科斯及克忒西波斯:均为奥德修斯妻子的求婚者。
(23) 忒勒玛科斯:奥德修斯之子。
(24) 伊洛斯:《奥德赛》中的乞丐,与奥德修斯争夺乞讨地盘并为此进行决斗。
(25) 欧律克勒亚:奥德修斯的老仆人,她从前者腿上的伤疤认出其真实身份。
(26) “神话”这个词源自希腊文中的“mythos”,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常表示类似“情节”的概念。
(27) 西嘉:罗马帝国时期的非洲古城,在今天突尼斯境内。
(28) 优提齐乌斯·普罗克洛斯(Eutychius Proclus):公元2世纪语言学家,曾担任罗马帝国
皇帝马可·奥勒留(Marcus Aurelius)的老师。
(29) 弗提乌斯(Photius,生卒不详):公元9世纪君士坦丁堡大主教兼著名学者。(30) 卡累利阿:位于俄罗斯西北部、与芬兰接壤的地区,今有俄罗斯境内的卡累利阿自治
共和国,以及芬兰境内的北卡累利阿和南卡累利阿地区。
(31) 诺森比亚:中世纪不列颠的小王国。
(32) 圣比德(the Venerable Bede,约672—735):亦称比德,英国宗教史上著名的修士、学者及神学家,有“英国历史之父”的美誉。
(33) 凯德蒙(C?dmon,生卒不详):公元7世纪英国基督教诗人。相传其原为放牧者,后
于睡梦中偶然学会作诗,凡《圣经》中的段落,经他之手都能转化为美妙的宗教诗篇。
(34) 小F.P.马古恩(F.P.Magoun,Jr.,1895—1979):美国文学批评家,中世纪英语文
学研究专家。
(35) 希尔达(Hild of Whitby,约614—680):英国基督教女教士,曾创建著名的惠特比修
道院,死后被尊为圣徒。
(36) 马提亚·弗拉齐乌斯(Matthias Flacius,1520—1575):今南斯拉夫北部信义宗(即路
德教)神学家、新约圣经学家。
(37) 他提安(Tatian,约120—180):叙利亚基督徒,以叙利亚文写成《四部福音合参》
(Diatessaron,约160年),将四部福音的重要内容编为一整体性的故事,后被译为希腊文流
传,如今仅有一小部分存留下來。
(38) 拉巴努斯(Hrabanus Maurus,776—856):德国神学家、圣经诠释学家兼诗人。
(39) 古高地德语(Old High German):现代德语的原型,出现于5至11世纪中期。
(40) 《希尔德布兰特之歌》:现今仅存的一首用古德语写成的日耳曼英雄诗歌,讲述武士
希尔德布兰特与儿子疆场对决的故事。
(41) 《瓦尔迪尔》:古英语史诗,现只剩残卷,讲述英雄瓦尔迪尔与恋人逃离匈奴王的囚
禁、盗取宫廷财宝并对追缉者进行英勇反击的故事。
(42) 《戴欧》:古英语史诗,讲述诗人戴欧受贬之后,以自白的形式将自己的流亡生涯与
日耳曼神话及盎格鲁—撒克逊民间传说人物的相似经历进行类比。
(43) 《威德西斯》:古英语史诗,行吟诗人威德西斯(意为“远行”)自述其游历各地,并
介绍古代及当代著名君主和神话、传奇英雄。
(44) 《费恩堡之战》:古英语史诗,讲述丹麦王子赫纳甫(Hn?f)与其妹夫费恩(Finn)
之间的战斗。这个故事也作为一个片段穿插在《贝奥武甫》当中。
(45) 法罗群岛:今丹麦自治省,位于苏格兰与冰岛之间,其口传法罗语歌谣源自古代北欧
文明。
(46) 弗里斯兰人:古代位于现今荷兰及德国境内靠近北海南部的民族,属于日耳曼人的一
支。
(47) 希索巴特人:《贝奥武甫》当中与丹麦人进行战争的族裔,其名意为“战争须髯”(war-beards)。
(48) 《流浪者》:古英语诗歌,讲述一位年轻人在战争中失去战友与亲人,沦为流浪者的
辛酸历程。
(49) 耶阿特人:北欧日耳曼人的一支,活动于今瑞典南部,一说属于哥特族。
(50) 牡鹿厅:《贝奥武甫》中丹麦国王的宫殿。在这里,贝奥武甫保卫王室免遭食人怪戈
兰德尔的袭击,将之击败,并砍断其胳膊。
(51) 普罗旺斯语:中世纪法国南部奥克语(langue d'oc)的一种方言,通用于普罗旺斯;普
罗旺斯文学则起源于11、12世纪的行吟诗人,后带来整个中世纪欧洲方言文学的兴起。
(52) 11至14世纪流行于法国的一种长篇故事诗,以颂扬封建统治阶级的武功勋业为主要题
材,故称“武功歌”。
(53) 加斯顿·帕里斯(Gaston Paris,1839—1903):法国作家、学者,以研究中世纪法国文
学及传奇文学著称。
(54) 罗曼语:印欧语系的一支,起源于“通俗拉丁语”(Vulgar Latin),中世纪欧洲传奇文
学的创作语言,法语亦属于罗曼语族。
(55) 艾因哈德(Einhard,770-840),查理曼大帝的侍从秘书,法兰克王国史学家,“卡洛
林文艺复兴”的代表人物之一,曾为查理曼大帝立传。
(56) 图林根人:日耳曼人的一支,活动在位于德国中部的图林根,该地区于公元6世纪为法
兰克人所征服。
(57) 加斯科尼人:法国西南部比利牛斯地区(旧称加斯科尼省)的巴斯克语民族。
(58) 战斗教会:神学中指那些同邪恶及耶稣的敌人进行斗争的基督徒。
(59) 教父神学:基督教早期由所谓“教父”(Church Fathers)从事的神学研究。
(60) 《罗兰之歌》的版本众多,其中最古老的版本是12世纪的牛津手稿。
(61) 哥特兰:位于今瑞典南部,相传为贝奥武甫的故乡。
(62) 塔西佗(Tacitus,约55—120):古罗马杰出的历史学家。
(63) C.V.韦奇伍德(C.V.Wedgwood,1910—1997):英国历史学家及传记作家。
(64) 奥利西斯:埃及神话中的冥界之神及丰饶之神。
(65) 大卫·林赛(David Lindsay,约1486—1555):文艺复兴时期苏格兰诗人,其诗作《乡
绅梅尔德伦传》以历史人物梅尔德伦的功勋为基础,将中世纪晚期的传奇、纪事和讽刺融为一
体。
(66) 巴伯(John Barbour,约1320—1395):苏格兰诗人,著有诗篇《布鲁斯本纪》,讲述
苏格兰国王布鲁斯的丰功伟业。
(67) 布莱因·哈里(Blind Harry,约1440—1492):苏格兰诗人,所著诗体纪事《威廉·华莱士列传》,讲述苏格兰民族英雄威廉·华莱士抵抗英格兰入侵的功绩。
(68) 《玫瑰传奇》:13世纪法国寓言长诗,典雅情爱(courtly love)文学的典范之作,以
玫瑰作为贵族女性的象征,向世人宣讲情爱之道。前半部分由基洛姆·德·洛利思(Guillaume de
Lorris)所作,后半部分由让·德·梅恩(Jean de Meun)完成。
(69) 《农夫皮尔斯》:14世纪以中古英语创作的寓言体叙事诗歌,以数个梦境影射英国社
会现实与宗教。
(70) 斯诺里·斯特卢森(Snorri Sturluson,1179—1241):冰岛历史学家、诗人及法律演讲
人(lawspeaker),著有《散文埃达》(Prose Edda)及《天下或挪威列王纪》(Heimskringla
or the Lives of the Norse Kings)。
(71) 让·德·热安维尔(Jean de Joinville,1225—1317):中世纪法国著名编年史家。
(72) 萨迦:中世纪冰岛及挪威等北欧民族的口头叙事,原意为故事、传奇或历史;家族萨
迦是其中的一类。
(73) 法律演讲人:斯堪的纳维亚诸国(如瑞典、冰岛和挪威)的政府职位,起源于日耳曼
口头传统,但只在北欧演化为独特的政府职能。
(74) 《斯特龙戈萨迦》:古代冰岛萨迦,讲述颇具名望的斯特龙戈家族(the Sturlungs)的
历史。
(75) 《伏尔松萨迦》(V?lsunga Saga):古代冰岛萨迦,讲述伏尔松家族围绕宝藏、权力
与情爱等主题经历的兴与衰。
(76) 《霍尔夫斯·克拉卡萨迦》(Hrólfs Saga kraka):古代冰岛萨迦,讲述传说中的丹麦国
王霍尔夫斯·克拉卡及其族人的历险。
(77) “智者阿里”(Ari the Wise,1067—1148):冰岛杰出的编年史家,第一位用古斯堪的
纳维亚语创作历史的学者。
(78) 吟游诗歌:与埃达诗歌齐名的另一种古代斯堪的纳维亚诗歌形式,其主题多歌颂君王
的丰功伟业。
(79) 奥丁:古代北欧神话中的一位主神,掌管战争、死亡、智慧、诗歌等。
(80) 圣·奥拉夫(St.Olaf,995—1030):中世纪的一位挪威国王。
(81) 斯特拉·索尔达森(Sturla Thórdarson,1214—1284):冰岛政治家、萨迦作家及历史学
家。
(82) 《尼雅尔萨迦》:13世纪最著名的“冰岛人萨迦”之一,讲述了几个家族之间的世仇,以及争端的解决。当中包括武功盖世的古恩纳尔(Gunnar)和足智多谋的尼雅尔(Njal)。
(83) 哈尔盖德:《尼雅尔萨迦》中古恩纳尔的妻子,生性跋扈、喜好争斗。
(84) 布伦希尔德:古代北欧神话中的女勇士,英雄西格尔德的追随者,但因为一场爱情阴
谋而嫁给了古恩纳尔,后为此对西格尔德实施报复并将其杀死,但在后者的火葬现场,跳入柴堆自焚殉葬。
(85) 《格雷蒂尔萨迦》:“冰岛人萨迦”之一,讲述古代冰岛绿林好汉格雷蒂尔充满传奇色
彩的一生。
(86) “联想节奏”指的是那种深受韵律诗影响的常规语言节奏,它有助于实现自由诗及散文
语言当中的意义被唤起。
(87) 《卡勒瓦拉》:芬兰民族神话史诗,根据芬兰及卡累利阿民间故事编撰于19世纪,标
题意为“卡勒瓦(Kaleva)的领地”。
(88) 这段引文出自乔伊斯的小说《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主人公斯蒂芬 ......
[美]罗伯特·斯科尔斯 [美]詹姆斯·费伦
[美]罗伯特·凯洛格 著
南京大学出版社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叙事的本质(美)斯科尔斯,(美)费伦,(美)凯洛格著;于雷
译.--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5.1(2019.1重印)
(当代学术棱镜译丛张一兵主编)
书名原文:The nature of narrative
ISBN 978-7-305-13725-9
Ⅰ.①叙… Ⅱ.①斯… ②费… ③凯… ④于… Ⅲ.①叙事文学-研
究 Ⅳ.①I0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180092号
Copyright ? 2006 b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Inc.
“The Nature of Narrative,Fortieth Anniversary Edition” was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English in 2006.
This transla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4 by NJUP
Throug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江苏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10-2009-105号
出版发行 南京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南京市汉口路22号 邮 编 210093出 版 人 金鑫荣
丛 书 名 当代学术棱镜译丛
书 名 叙事的本质
作者 [美]罗伯特·斯科尔斯 [美]詹姆斯·费伦
[美]罗伯特·凯洛格
责任编辑 谭 天
照 排 南京南琳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印 刷 南京爱德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35×965 116 印张 29.75 字数439千
版 次 2015年1月第1版 2019年1月第3次印刷
ISBN 978-7-305-13725-9
网 址 http:www.njupco.com
官方微博 http:weibo.comnjupco
官方微信 njupress
销售热线 (025)83594756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南大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所购图书销售部门联系
调换《当代学术棱镜译丛》总序
自晚清曾文正创制造局,开译介西学著作风气以来,西学翻译蔚为
大观。百多年前,梁启超奋力呼吁:“国家欲自强,以多译西书为本;
学子欲自立,以多读西书为功。”时至今日,此种激进吁求已不再迫
切,但他所言西学著述“今之所译,直九牛之一毛耳”,却仍是事实。
世纪之交,面对现代化的宏业,有选择地译介国外学术著作,更是学界
和出版界不可推诿的任务。基于这一认识,我们隆重推出《当代学术棱
镜译丛》,在林林总总的国外学术书中遴选有价值篇什翻译出版。
王国维直言:“中西二学,盛则俱盛,衰则俱衰,风气既开,互相
推助。”所言极是!今日之中国已迥异于一个世纪以前,文化间交往日
趋频繁,“风气既开”无须赘言,中外学术“互相推助”更是不争的事
实。当今世界,知识更新愈加迅猛,文化交往愈加深广。全球化和本土
化两极互动,构成了这个时代的文化动脉。一方面,经济的全球化加速
了文化上的交往互动;另一方面,文化的民族自觉日益高涨。于是,学
术的本土化迫在眉睫。虽说“学问之事,本无中西”(王国维语),但“我们”与“他者”的身份及其知识政治却不容回避。但学术的本土
化绝非闭关自守,不但知己,亦要知彼。这套丛书的立意正在这里。
“棱镜”本是物理学上的术语,意指复合光透过“棱镜”便分解成
光谱。丛书之所以取名《当代学术棱镜译丛》,意在透过所选篇什,折
射出国外知识界的历史面貌和当代进展,并反映出选编者的理解和匠
心,进而实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目标。
本丛书所选书目大抵有两个中心:其一,选目集中在国外学术界新
近的发展,尽力揭橥域外学术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最新趋向和热点问题;其二,不忘拾遗补缺,将一些重要的尚未译成中文的国外学术著述
囊括其内。
众人拾柴火焰高。译介学术是一项崇高而又艰苦的事业,我们真诚
地希望更多有识之士参与这项事业,使之为中国的现代化和学术本土化
做出贡献。
丛书编委会
2000年秋于南京大学谨以此书纪念
罗伯特·L.凯洛格
(1928—2004)目 录
第二版前言(罗伯特·斯科尔斯)
第二版前言(詹姆斯·费伦)
1 叙事传统
2 书面叙事的口头传统
3 现代叙事的古典传统
4 叙事中的意义
5 叙事中的人物
6 叙事中的情节
7 叙事中的视角
8 叙事理论,1966—2006:一则叙事
附录
注释
参考书目
索引
致中国读者的话
《叙事的本质》译后谈第二版前言
一部学术著作若能历经四十载而依然再版,乃是件了不起的事情
——特别是那种由几位年轻气盛的小字辈学者所书之作。眼前的这本书
恰恰就属于这种情形。当年,罗伯特·凯洛格和我本人在弗吉尼亚大学
为二年级本科生开设了一门课,计划用一学年的时间讲授从荷马到乔伊
斯以来的叙事文学;而我俩就此课程所进行的数次讨论竟成了此书创作
的最初动因。这门课,我们教过几轮,几乎每天在回家路上均以此为话
题。这本书正是得益于那些授课经历与私下里的交流——当然,也得益
于这一课程本身所要求我们进行的大量研究工作。
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是开设此课程的理想人选。凯洛格当年正是
带着对乔伊斯的极大热情前往哈佛进行研究生阶段的深造。他是个非常
细致的人,当然也顺理成章地选择了中世纪文学作为其最初的研究内容
——一直孜孜不倦。我俩相识之际,他正在专攻古代冰岛文学,但他对
中世纪欧洲文学与文学现代主义有着非凡的功力。而我本人则选择了康
奈尔,其部分原因是,他们的研究生课程将小说作为一种文学类别纳入
研究体系,这在20世纪50年代是相当稀罕的。尽管我的硕士论文和博士
论文主要是探讨20世纪英美小说,但我在深造期间的学习涵盖了小说这
一整体类别,而且我在弗吉尼亚从教时,对于从18世纪英国小说到20世
纪美国小说的授课内容也做到了包罗万象。就我们那个时代的叙事文学
研究来说,罗伯特跟我通过合作而实现的历史视野乃是任何一个人所未
能企及的。(1)
我俩曾一直就合作出书的问题探讨了些时候,后来恰逢我获得威斯
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人文研究中心提供的为期一年的资助,研究叙事文学的历史与理论。这个机会意味着我可以为我们意向之中的携手之作先
行写出一份草稿,而那些因我知识局限所遗留的空缺部分则由罗伯特加
以添补。很久之前,我曾在纽约加登城(Garden City)的几所公立学校
学习过五年半的拉丁文,而在麦迪逊分校,我至少也学了些古希腊语的
基础知识。罗伯特懂得不少中世纪的欧洲语言,而且,我俩也懂好几种
现代语言。尽管我跟罗伯特对俄语都是门外汉,但我在本科阶段曾在韦
勒克(2)
门下修过一年俄国小说的课程。可以说,我们拥有了一定的合作
基础。
在麦迪逊分校,我还得到许多高级学者的智力支持,如研究中世纪
科学的专家马歇尔·克拉格特(Marshall Claggett),还有热尔曼·布瑞
(Germain Breé)——一位研究法国现代文学的学者,他们给予了我极
大的帮助。时任人文研究中心主任的马歇尔·克拉格特问我是否需要中
心提供相关书籍以帮助我的研究。于是,我交给他一份清单,列出一
些“洛布古典文库”(Loeb Classics)(3)
的书目——配有对照英文翻译的
古代希腊及拉丁文学丛书。他思忖了一会儿,终于开口说他认为中心应
该拥有全套丛书。几周后,这套丛书便抵达中心,我亲手帮他将这些书
开包上架。这些书对我的研究起了很大的作用,我可以在英语文本中迅
捷地找到关键段落,然后更加细致地分析希腊和拉丁原文;这样一来,我那业已生疏的拉丁文和差强人意的希腊文总算派上了用场。
于是,我写出自己章节的草稿,由罗伯特进行编辑,而后他也写出
自己两个章节的草稿(关于现代叙事的口头传统及叙事中的意义),由
我来编辑。就是这样,这本书出炉了,最终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差
不多三十五年后,罗伯特跟我碰巧在一次晚宴上相对而席,于是我们就
决定试探一下出版社是否有兴趣出第二版,结果一拍即合。我们随后便
开始策划这件事,但工作进展缓慢,而且后来罗伯特也不幸辞世。他是一名优秀的学者,一个伟大的人,也是一位知心朋友。就我而言,他的
离去也意味着第二版计划的夭折,因为我实在没有心情独自继续下去。
不过,时间的流逝总能多少抚平这样的伤痛,而出版社也保持着极大的
耐心,所以,过了一阵子,我就开始琢磨该如何对这本书进行修订。
许多年后,当我捧起这本书重温的时候,脑海中依然深深印记着当
年那两个毛头小伙勤奋苦读、博闻强记、沉冥思索的模样。他们知道的
东西,如今我已无法知晓;他们思考问题的方式也不再为我所用。这本
书似乎牢牢定格在它自己的时间里,几乎让修订工作成为不可完成的使
命。毕竟,《叙事的本质》曾经为开创叙事学研究做出过自己的贡献,而我本人也在其他著作中拓展了对叙事理论的思考,如《寓幻家》
(The Fabulators)(4)
、《文学结构主义》(Structuralism in
Literature)、《结构性寓幻》(Structural Fabulation)、《寓幻与元小
说》(Fabulation and Metafiction)、《文本的力量》(Textual Power)
以及《现代主义悖论》(Paradoxy of Modernism)等。当然,也有诸多
其他学者曾进入这一领域,在理论和历史研究两方面都创造出丰硕的学
术力作——如巴赫金、托多洛夫、热奈特、巴特以及麦基恩
(McKeon)——这里也只是列举了其中最负盛名的几位。不过《叙事
的本质》依旧在印,而且似乎还能够为叙事学历史与理论提供有效的视
角。当然,这一视角在某种程度上说也是代表了20世纪中期那一特殊的
历史时刻。
结合上述问题的考虑,我委实找不出理由要去重写此书并炮制一个
全新版本。不过,我逐渐意识到这样一个可行的方案:在重新出版原文
本的时候,可以做一些小的文体调整,并且邀请一位年轻学者就初版后
叙事研究的发展写个专题,作为对原书的补充。这就是事情进展的过
程。不过,那位参加该项目的新作者并非毛头小伙,但比我年轻。就我认识的人当中,他对过去几十年来叙事研究领域的发展最具发言权。这
个人正是詹姆斯·费伦(5)。多年来他一直担任《叙事》杂志的编辑;这
是“叙事研究协会”的机关刊物,也是叙事研究领域的顶级期刊。可以
说,没有费伦的合作,《叙事的本质》第二版将不会存在。他追溯了
《叙事的本质》初版后四十年的叙事研究新动向,在我看来,他的工作
做得非常出色。
罗伯特·斯科尔斯
(1) 本书若无特殊说明,页下注释均为译者注。
(2) 雷纳·韦勒克(René Wellek,1903—1995):捷克裔美国学者,20世纪享誉国际的文学
理论家、批评史家和比较文学家。
(3) 西方闻名遐迩的一套大型文献丛书,收录了古希腊罗马时期的典籍,由美国人詹姆士·
洛布(James Loeb)1910年策划。该丛书的特点之一,就是将原文(希腊文、拉丁文)和英文
翻译加以对照编排。
(4) “寓幻(小说)”这一提法因斯科尔斯的相关论著而得名,主要用以代指20世纪以来所出
现的、具有魔幻及后现代特征的反传统小说创作。诸如约翰·巴思和托马斯·品钦这样的作家,均系此文类创作的集大成者。
(5) 詹姆斯·费伦(James Phelan,1951— ):俄亥俄州立大学“杰出人文教授”、国际叙事
文学研究协会前主席、美国《叙事》杂志主编,当今北美最具影响的叙事理论家之一。第二版前言
早在1969年,我还只是波士顿学院一名英语专业大二的学生,正值
年轻气盛;记得在罗伯特·E.莱特(Robert E.Reiter)讲授的一门必修
课上,我首次接触到了《叙事的本质》。而后在1976年,我更为细致地
研读了这本书。当时,谢尔顿·萨克斯(1)
是芝加哥大学“叙事理论”方向的
导师,而我则将这本书纳入自己的阅读书单,作为应对该博士课程专业
考试的准备。在此后的岁月中,我时而会求助于这本书,也会向别人推
荐这本书,但我怎么也没料到斯科尔斯会盛情邀我为该书新版写“一个
关于叙事研究动向的部分”。这简直如梦幻一般——我居然要在伴随我
成长的作品中添加自己的文字。这感觉就如同说,倘若我是小说家,亨
利·詹姆斯或是弗吉尼亚·伍尔芙邀请我为《奉使记》(The
Ambassadors)或《达洛维夫人》的新版创作最后一章。面对这份奖
掖,你准会欣然应允;当然,也难免有几分惶恐和心虚。不过,你还是
想方设法去接手这份工作。而后,当发现先前的某些想法明显不妥时,你又会进行新的尝试,一直坚持到自己最终勉强有东西拿得出手。
在我所做的诸多设想中,有三点我需要在此强调一下。其一,我试
图保留斯科尔斯和凯洛格对文学叙事的聚焦,因为在我看来,要突出
《叙事的本质》与过去四十年来叙事学发展的连贯性,那是最好的办
法。同时我要指出,叙事理论的疆域已有所拓展,它将各种非文学叙事
也纳入其中,并且这种拓展会对文学叙事研究产生影响。其二,斯科尔
斯提出的讨论“叙事研究动向”的要求与我的想法不谋而合。也就是说,从实践意义上看,我并非去追溯1966年以来的叙事历史(后现代实验、数字叙事的出现、传记潮等),而是要提供一则关于叙事理论的叙事,并且在这一叙事中,我会穿插1966年以前及之后的文学叙事案例。我希望,这种运作模式能够让读者看到斯科尔斯和凯洛格作品中的理论部件
与最新的理论进展及观念之间的联系,同时我也能借此获得更大空间去
展现那些发展趋势。
其三,我既非对叙事研究动向进行完全独立的展现,也非妄图化约
出所谓“宏大的统一叙事场论”(Grand Unified Field Theory of
Narrative,GUFTON),相反,我寻求两者之间的中间路线。其原因在
于,若唯前者则势必摆出一副伪装的——而且,在我看来,也是难以维
系的——客观化姿态;若唯后者则会导致该领域的研究视野,以及该场
合下的修辞意旨表现出的一种不该有的狭隘性。当代叙事理论可谓纷繁
多样,因此,一个1966年以来“关于该领域发展动向的章节”不可能创立
出所谓“宏大的统一叙事场论”。当然,正是由于该领域的多样性,要梳
理出过去四十年叙事研究的演化就必须进行相当程度的筛选,而这种筛
选又必然反映出故事讲述者自身就该领域所持的观念,包括其中不同层
面相互联系的方式。结果,当我对自己的设想和筛选心存侥幸之际,我
也格外清楚地意识到,我的叙事并不能终结其他的可能性;而且,我以
为,我的读者们最好也抱有同样健康的意识。
最后,我要感谢戴维·赫尔曼(2)
、布赖恩·麦克黑尔(3)
、彼得·J.拉比
诺维茨(4)
以及罗伯特·斯科尔斯,他们为我的叙事提出了富有裨益的评
价。我也要感谢伊丽莎白·马尔什,她的编审如鹰眼一般敏锐,同时她
也为“引用文献”付出了辛勤劳动。当然,我最想对罗伯特·斯科尔斯深
表谢意,他以包容的信任邀请我在他与罗伯特·凯洛格的地标之作中进
献言论。
在我为此书所作的文字部分中,有些内容曾出现于先前我在《劳特
利奇叙事理论百科全书》(Routledge Encyclopedia of Narrative Theory)
中撰写的词条“叙事的修辞手法”(pp.500—504),由戴维·赫尔曼、曼弗雷德·雅恩(5)
及玛丽-劳雷·瑞安(6)
编(伦敦:劳特利奇,2005)。还
有些内容已经出现于我为《小说百科全书》所撰词条“情节”(pp.1008
—1011),由保罗·斯柯林尔编(芝加哥:费茨罗伊·迪尔波恩,1998)。我谨致谢上述两家出版社应允我将相关内容再次付印。
詹姆斯·费伦
(1) 谢尔顿·萨克斯(Sheldon Sacks,1930—1979):芝加哥大学英语与语言学教授,著名
期刊《批评探索》(Critical Inquiry)的首任主编。
(2) 戴维·赫尔曼(David Herman,1962— ):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英语教授,认知叙事
学研究的重要代表人物。
(3) 布赖恩·麦克黑尔(Brian McHale,1952— ):美国叙事理论家,俄亥俄州立大学杰出
人文教授。
(4) 彼得·J.拉比诺维茨(Peter J.Rabinowits,1944— ):美国汉密尔顿学院比较文学教
授、叙事理论家。
(5) 曼弗雷德·雅恩(Manfred Jahn,1943— ):德国科隆大学英语教授、叙事理论家。
(6) 玛丽-劳雷·瑞安(Marie-Laure Ryan,1946— ):美国叙事理论家、文学批评家及网络
文化学者。1 叙事传统
过去的两个世纪以来,小说一直是西方叙事文学的主导形式。因
此,从某种意义上说,要书写西方叙事传统,就有必要探究小说发展的
源流。早期的各种叙事——宗教神话、民间故事、史诗、传奇、传说、寓言、忏悔录、讽刺——都曾力求获得如小说那般完美的形式,当然也
的确实现了不同程度的突破,但我们的意图并非要将小说看作改良式进
化的终极产物,而是旨在选取一种近乎与之相反的思路。我们希望让小
说回归原位,继而从总体上去把握叙事的本质及西方叙事传统,将小说
仅仅视为诸多叙事的可能性之一。为此,我们有必要放宽眼界,力图在
自己关注的文学领域内做到既有所趣又显所能,而不是囿限于追逐专家
式的真知灼见;同时,我们也可能仅凭有限的论证做出略显仓促的概
括。鉴于上述及其余不当之处或草率之言,我们谨表歉意,但求最终的
结果能够表明,承担这样一项复杂的研究课题并非不自量力的莽撞之
举。
我们研究叙事艺术的目的不是要去树立文学或批评的新风尚,而是
要为古今所有狭隘的文学观念提供解毒之剂。凡是批评兴旺的时代(我
们显然正值这样的时代),文学艺术的研究方法总会表现出广博与偏狭
这两种对峙的趋向。批评的时代是具有自省意识的时代。其倾向表现为
制定规则、试图将艺术化约为科学,分级、归类,并最终评判孰是孰
非。这种理论批评通常基于某些作家的创作实践,其作品之所以成为经
典就在于它们迎合了“经典”之最为鄙俗的意义:循规蹈矩的正统文学实
践范式。此法试图对过去的文学加以化约,筛选出几个“经典”范例;这
无异于构建了一种人造的文学传统。而我们在此书中的目的则是要为我
们称之为叙事的重要文学形式提供一种新思路,纠正以往的狭隘理解。所有那些被我们意指为叙事的文学作品具有两大特点:一是有故
事,二是有讲故事的人。一部戏剧是一个没有讲故事者的故事;剧中人
物对我们在生活中的行动,直接进行亚里士多德称之为“摹仿”的实践。
与戏剧相仿,抒情诗也是一种直接展示,但只有单个演员(诗人或其替
身)在其中吟唱、沉思,或有意或无意地讲话给我们听。若像罗伯特·
弗罗斯特写《雇员之死》那样,再增加一个说话者,我们便接近了戏
剧。若像罗伯特·弗罗斯特写《正在消逝的红》那样,让这个说话者着
手讲述某一事件,我们便走向了叙事。因此,要使作品成为叙事,其必
要及充分条件,即一个说者(teller)和一则故事(tale)。
在西方世界,真正的叙事文学传统的确存在。可以说,所有艺术都
是传统化的,因为艺术家们在很大程度上正是从他们的前辈身上习得技
艺。在创作之初,他们总会以自己熟悉的前人成就为参照,设想各种摆
在自己面前的可能性。虽然他们可能会对传统添砖加瓦,为后人开创新
思路,但不可避免的是,其端倪总发自传统内部。作为读者、评论家或
艺术家,我们越是了解叙事传统的厚度与广度,就越能够在批评或艺术
层面做出更自由、更稳妥的甄别。对于20世纪中叶的读者而言,要想就
叙事传统获取恰如其分的判断,就不得不首先解决一个具体问题,即我
们必须设法避免将小说这一文学形式当作顶礼膜拜的对象。
所有现存的文学传统都具有一个特点,即当代叙事文学会逐渐挣脱
新近历史中的叙事文学。同样,伴随乔伊斯、普鲁斯特、托马斯·曼、劳伦斯及福克纳的出现,20世纪的叙事文学也已经开始了这一分道扬镳
的历程。具体说来,20世纪的叙事已经表现出对现实主义宗旨、取向及
其技法的剥离。而就此剥离所产生的影响,许多有趣的欧美叙事作家依
旧在探索、开发与拓展。不过,从总体上看,我们的评论者们对这种新
文学尚带有敌意,我们的批评家们也未将其提上议事日程,毕竟文学批评也同样受到传统观念的影响。
关于当代批评对当代叙事艺术中许多优秀的成果所采取的敌对姿
态,我们并不打算挑出一个或多个评论者作为例证,但我们倒是可以举
证一位伟大的学者兼批评家,其观点被公认为属于时下文学研究生院
(这里是培养教师、批评家乃至未来评论家的摇篮)中最具影响之列,而其针对现代文学的态度尽管不乏学识和敏锐,却与那种最为世俗的每
周评论有着惊人的相似。这位学者—评论家就是埃里希·奥尔巴赫(1)
,其英文版平装本《摹仿论》(Mimesis)乃是叙事研究领域中两三部最
具人气、最负影响的著作之一。而且,他的研究领域可谓广博:西方叙
事文学。尽管这是一部伟大的作品,但奥尔巴赫对现实主义原理的热心
专注使得他不愿或无法接受20世纪的小说,尤其是像弗吉尼亚·伍尔
芙、普鲁斯特和乔伊斯这样的作家。在他看来,《尤利西斯》就是一
个“大杂烩”,充斥着“露骨而又伤怀的愤世之情,以及令人费解的象征
主义”,并且他还断言,与该小说一样,“大部分其他采用多重意识反映
手法的小说也给读者留下令人绝望的印象。它们常常令人困惑,雾霭重
重,对其所描绘的现实透露出几分敌意”。
奥尔巴赫对后现实主义小说的不满,在二流学者当中引起了共鸣,我们几乎可以在当下文学评论和期刊的每一页上找到这样的不满;在那
里,许多优秀的当代作品不是受到敌视,就是遭遇冷落。目前学界对当
代文学的态度同样也制约着对过去文学的看法。因此,这种用19世纪现
实主义标尺衡量所有小说的倾向自然会妨碍我们理解其他各种叙事。
此“小说性”(novelistic)方法不仅让普鲁斯特、乔伊斯、杜雷尔(2)
和贝
克特深受其害,也使得斯宾塞、乔叟及沃弗兰·冯·埃森巴赫(3)
备受煎
熬。要想找到一种途径,使得叙事研究摆脱小说性方法的局限性,我们
就必须打破那些常用于叙事讨论过程中,诸如时间、语言及狭隘文类划分的条条框框。我们必须考察所有西方世界的叙事形式,在其发展过程
中所共有的要素——口头和书面、韵文与散文、事实与虚构。当然,这
样的尝试绝非空前之举,只是难得一见罢了。
事实上,正是带着这种意图,克拉拉·里夫(Clara Reeve)于1785
年出版了《穿越时代、国家与风尚的传奇之旅》(The Progress of
Romance through Times,Countries,and Manners)。这是第一部真正致
力于研究叙事传统的英文著作。面对传奇在18世纪所遭受的广泛偏见,克拉拉·里夫试图为这种形式构建一个谱系,既突出表明它曾为“古
人”所用,同时又以一视同仁的姿态将其与作为后继形态的小说区分开
来。她的这一区分如今已存留于我们的辞书当中,那些试图对叙事形式
进行甄别的批评家们依然会采用这一划分:
我将尝试这种区分,如果此法得当,不妨从之,——如若
不当,您尽可不为所动。传奇作为英雄体寓言,当以传奇人物
和事件为对象。——小说则是现实生活与风尚的写照,是小说
创作时代的图景。传奇以其崇高雅致的语言描述既从未发生,也不可能发生的故事。——小说则以亲切的口吻讲述那些每天
从我们眼前经过的事情,这些事情既可能发生在朋友身上,也
可能发生在我们自己身上;完美的小说以其闲适自然的方式再
现每一场景,使其可能性达到以假乱真的效果,最终让我们受
到故事人物或悲或喜的情绪感染,仿佛这些就是我们自己的感
受。
除了做出这一清晰明了而又富于价值的表述,克拉拉·里夫还探讨了
——尽管有些流于漫不经心——某些其他叙事类别:形形色色的“新奇
或另类”故事,包括像《格利佛游记》《鲁滨逊漂流记》《项狄传》和
《奥特朗托堡》这样的“现代派”作品;此外,还有另一类包括从童话到《拉索勒斯》(Rasselas)(4)
可谓包罗万象的“传说和寓言”。克拉拉同
时也对史诗与传奇进行了区分,并试图探究像“俄相之疑”(Osianic
Question)(5)
这样的棘手问题。(她在指出《费恩盖尔》[Fingal]
(6)
是“史
诗,而非诗歌”时,有所犹豫,但最终还是将俄相作品划归到传奇当
中)克拉拉明确指出,传奇既可是韵文也可为散文,但史诗以她看来,则必须是诗歌体的。她同时倾向于将史诗看作颂扬之辞;这样一来,一
则真正优秀的诗歌体传奇,如乔叟的《骑士的传说》(此例由克拉拉本
人所举)则该配得上史诗的头衔。
就克拉拉·里夫生活的时代及其所受教育的局限性而言,她的学术
广博与阐释的公允着实令人惊叹。她对“古人”的敬重,以及她对文学成
果的道德评判也为当时的学术前辈们所首肯。实际上,像她那样对叙事
文学进行全面研究的人是很少见的,这种情形也只是到最近方有所改
观;她的博学、平实及睿智,如果能为众多现代书评家们所习得,将会
对他们大有裨益。即使是今天,克拉拉·里夫在1785年遇到的种种困惑
依然对我们具有启发作用。她在探讨过小说和传奇之后,便在梳理其他
叙事形式的问题上陷入了困境——这同样也是现代批评家所无法回避
的。不过,最棘手的还在于她试图对类似“史诗”这种描述性的概念赋以
价值评判。现代批评中产生的一个最大问题,即来自将描述性与评价性
术语相混淆的倾向。比如,“悲剧性”(Tragic)和“现实性”(Realistic)
通常是作为褒义的缀语运用于文学作品。翻开任何一本期刊,我们几乎
都能在书评或剧评的字里行间发现这样的情况。一部正剧可能会因为缺
乏“悲剧性”而遭到叱责。一则叙事也可能由于“非现实性”而一败涂地。
但在我们这个时代,理解叙事文学的最大障碍在于“小说”这个词本身已
经被诸多价值观念所包裹。克拉拉·里夫之所以能够以这样一种相对客
观的眼光去审视传奇的发展,其原因之一,即她所生活的时代先于19世
纪——现实主义小说的伟大世纪。如今,正值20世纪中叶,而我们的叙事文学观却几乎沦为小说中心
化(novel-centered)的无望之境。读者们对叙事文学作品的期望源于他
们的小说阅读经验。他们对于叙事的判断来自对小说的理解。“小说”这
个字眼,一旦用在早期叙事作品身上,就成了褒义词。我们会在书的护
套或封面上看到,诸如乔叟的《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Troilus and
Criseyde)(7)
、杰弗里(8)
的《英国君王史》(History of the Kings of
Britain)和荷马的《奥德赛》这些形形色色的作品都被称为“第一部小
说”。不过,如果我们对这些称谓信以为真,则必然会感到失望。即便
是荷马,一旦被评判为“小说家”,也难免不露瑕疵。
小说中心论对叙事文学研究而言是不幸的,其原因有二。首先,它
将我们与历史上的叙事文学和文化割裂开来;再者,它将我们与未来的
文学甚至今天的先锋创作割裂开来。因此,要重塑历史,要接受未来,我们就必须真正还小说于原位。当然,我们不必为此放弃任何对现实主
义小说的景仰。当小说归其原位,像巴尔扎克、福楼拜、屠格涅夫、托
尔斯泰和乔治·艾略特这样的作家,并不会因此而失去其成就的光鲜夺
目,相反,还可能更加绚烂迷人。
我们不妨记住,西方世界的叙事传统绵延五千年,而小说只占了几
个世纪。当然,小说也拥有两百年的辉煌;无论现代欧洲在其他方面有
过怎样的失败,但就叙事文学的创作而言,她问心无愧;不过,那毕竟
只是五千年中的两百年而已。而我们的研究目的则在于探讨叙事文学的
一些种类,寻找叙事形式在历史发展中的模式,研究叙事艺术当中连贯
的或反复出现的要素,并借此探究这五千年传统中一些具有连续性的线
索脉络。与克拉拉·里夫的任务相比,我们要容易得多。虽然如今的叙
事艺术研究对于广博视野的要求,正如1785年时一样迫切,但这么多年
来的知识积累,业已让我们获得更多的必要研究手段。在过去的一百年中,我们通过各种资料,就文学的史前时期及前现
代文学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认知。那些18和19世纪的文学史家和批评家根
本无法获取的重要资料现在可为我们所用。自弗雷泽(Frazer)的《金
枝》开始,人类学家们便就原始社会中文学与文化的关系给我们提供了
宝贵信息,开创了如杰茜·韦斯顿(Jessie L.Weston)在《从仪式到传
奇》中所展现的文学研究方法。而关于文学如何与个体心理过程相联
系,心理学家们则给我们提供了同样重要的深邃之见(在此,荣格甚至
超越了弗洛伊德),继而造就了一个全新的成功学派——原型批评。此
外,口头文学研究的学子们,如帕里(9)
和洛德(10)
,使我们首次窥见书面
文学与口头文学的差异,以及书面叙事的口头传统。再者,文学研究者
们,如穆赖(11)
、康福德(12)
等古典学者及西奥多·盖斯特(13)
这位希伯来文
化专家也提出方法,使某些新的超文学(extra-literary)知识能够促进
我们对文学的理解。同时,艺术及文学史家,如厄文·帕诺夫斯基(14)
和
小罗伯森(15)
,也让我们对文化先辈的看法与世界观产生了空前的认
识。还有一位杰出的评论界的集大成者——诺斯洛普·弗莱(Northrop
Frye),他向我们展示了如何将文化研究与文学研究结合起来,使我们
空前地接近了一套完整的文学理论。
上述这些学者不仅赋予我们研究手段和学术发现,也为我们树立了
榜样;我们尝试着构建一种理论,尽量言简意赅地阐释叙事形式的种类
及它们如何产生并相互作用的机制。面对摆在我们面前的历史事实,面
对各种经过甄别分类的叙事(这种分类所采取的系统标尺常常相异,甚
至对峙),面对那些约定俗成的诸多“影响”、关联性及一致性,我们努
力做到既研究具体的棘手问题,同时也不忘满足对体系和规律的心理趋
向。而我们的结论正是凭借这样充分周全的探究与考证,得以在后面的
章节中展示。在本章的剩余部分,我们会提供一种“论证”或是注解,以
进行接下来更为细致的说明。作为对我们的叙事传统观进行的最简约展示,它所代表的并非作为一种因果论断以支撑我们的研究,而是我们在
研究过程中所发现的一种模式。
叙事传统当中的形式演化过程,在某种程度上可用生物进化加以类
比。人类由于将自己看成生物进化的终点,便自然会将进化看作是趋向
完美之境的努力。如果恐龙会说话,它也许会持不同见解。同样,一位
当代小说家也会将自己看作改良式进化的极品;但荷马如果能开口讲
话,他可能会反对这种看法。不过,史诗与恐龙均已绝迹。尽管我们可
以合成一部史诗,并做到与原始版本有几分形似,就像我们能够在博物
馆里拼装出恐龙一样,但问题是,原始版本得以产生的条件已不复存
在。大自然在创造那些漂亮的怪兽时所展示的纯真已经消逝,对此,她
绝不会去复原;而叙事艺术家们也无法凭借经验与想象对取自神话和历
史的素材加以真正原初性的组合。
当然,这种进化的类比法是站不住脚的。《伊利亚特》这一奇迹的
伟大之处,恰恰在于它乃是一只活着的恐龙。个体文学作品并不总会绝
迹,只是它们的形式可能会消亡。而它们的繁衍也并非自然选择的问
题。文学的进化在某些方面要比生物的进化更复杂。它是生物过程与辩
证过程的混合体;在这个过程中,不同的物种有时会组合为新的杂交
体,而该杂交体又会与其他旧的或新的形式进行组合;而且,一种原型
(type)会衍生出其预表性类型(antitype)(16)
,而该预表性类型又会与
其他形式进行组合,或与预表性类型的母体进行合成。
就如何对叙事形式进化的复杂运作过程加以规整与展示,很难找到
一种令人满意的途径。这里所提出的方案,乃是在混杂性与系统性之间
达成妥协。它并非模拟叙事艺术家实际的有意识或无意识的心理过程,而是作为一种便捷的方法使此过程能够为我们所把握。其宗旨在于通过
澄清此过程,以展示叙事文学重要形式之间现存的和历史上已存的主要关系。
在西方,书面叙事文学往往出现于相似的条件之下。它源自口头传
统,有一度曾保留了许多口头叙事的特点。我们将它所惯常采用的英雄
体诗歌叙事形式称为史诗。在其背后存在着形形色色的叙事形式,如宗
教神话、准历史传奇和虚构性民间传说,它们已经融合成一种传统叙
事,即神话、历史和虚构的混合体。对我们而言,早期书面叙事的最重
要层面即传统本身这一事实。史诗的故事讲述者说的是一个传统故事。
促使他讲故事的主要动因不是历史性的,也非创造性的,而是再创性的
(re-creative)。他在重述一个传统的故事,因此,他最需遵守的并非
事实,也非真理或娱乐,而是“神话”(mythos)自身——保留于传统之
中,由史诗的讲述者加以重新创作的故事。在古希腊,“神话”这个词的
精确含义正是如此:一个传统故事。
传统叙事在传达过程中必然要传达情节,即诸事件的轮廓。“情
节”这个词的所有意义都在于表明叙事框架。这样,一则神话便是一个
能够得以传达的情节。在亚里士多德看来,作为对行动加以摹仿的文学
作品,其灵魂正是情节(亚里士多德用“神话 ? ?”一词代之)。宗教神话,作为与宗教仪式相关的叙事形式,即一种神话叙事;而传奇和民间传说
在传统意义上也是神话性的,口头史诗亦是如此。在书面叙事史当中,一个明显的重要发展进程,便是逐渐摆脱那种以传统情节讲故事的神话
趋向所主导的叙事。我们可以在西方文学中发现两次这样的运动:一次
发生在古典语言当中,另一次发生在本土方言当中。(17)
在此进化过程
中,叙事文学倾向于朝两个相反的方向发展。这两大叙事分支的发展出
现于传统叙事力量的衰退之际,正确理解这一点对真正领会叙事形式的
进化至关重要。为此,我们必须既考虑这两大叙事分支之间产生分裂的
实质,同时也观照两者的互动与重聚。发端于史诗综合体的这两类背反叙事类别,不妨分别以经验性 ? ? ?
(empirical)与虚构性 ? ? ?
(fictional)加以称呼。两者均可看作是对故事叙
述过程中传统强势加以回避的方式。经验性叙事用对现实的忠实取代对
神话 ? ?
的忠实。我们可以将经验性叙事趋向细分为两个主要构件:历史性 ? ? ?
的(historical)和摹仿性 ? ? ?
的(mimetic)。历史性构件专门对事实之真和
具体历史保持忠实,而不是受制于历史在传统中的再现。它的演绎要求
具备时间与空间的准确丈量方式和以人与自然为媒介,而非通过超自然
手段达成的因果概念。在古代,经验性叙事首先通过其历史性构件得以
体现,正如希罗多德(Herodotus)和修昔底德(Thucydides)等作家那
样仔细地与《荷马史诗》划清界限。而摹仿性构件保持忠实的对象则不
是事实之真,而是感受与环境之真;它依赖于对当下的观察,而不是对
历史的调查。它赖以发展的条件是通过社会学及心理学意义上的观念去
审视行为与心理过程,就像亚历山大时期(18)
的哑剧(Alexandrian
Mime)所表现出来的特点。摹仿性形式是所有叙事形式中发展最慢的
一种。在古代,那些最突出的摹仿性因素不仅出现在狄奥佛拉斯特式的 ? ? ? ? ? ? ? ?
人物 ? ?
(19)
(与哑剧形式对应的叙事)中,也呈现于狄奥克里特(20)
那首现
实主义“田园诗”《阿多尼斯》(即第15首)当中,或是如裴特洛纽斯(21)
在“特里马尔奇奥的宴席”(Dinner at Trimalchio's)(22)
中所描绘的段落。
摹仿性叙事与神话性叙事正相反,因为前者趋向于无情节
(plotlessness),其最终的形式乃是“生活的切片”。传记和自传均为经
验性叙事形式。在传记这一先行发展的形式中,历史性趋向起着决定性
作用,而在自传当中,摹仿性趋向则占据主导地位。
虚构性 ? ? ?
叙事分支,则以对理想的忠实取代对神话 ? ?
的忠实。我们可以
将虚构性叙事趋向也细分为两大构成:传奇性 ? ? ?
(romantic)与教寓性 ? ? ?
(didactic)。小说的创作者既摆脱了传统的束缚,也摆脱了经验主义的
圈囿。他的眼睛所关注的并非外部世界而是读者,他希冀带给他们欢乐或教诲,赋予他们所想或所需之物。经验性叙事着眼于某种真实,而虚
构性叙事则着眼于美或善。传奇的世界是理想的世界,在其中占上风的
是诗性的正义,所有语言的艺术与修饰都被用以渲染叙事。摹仿性叙事
旨在对精神过程加以心理学意义的再现,而传奇叙事则以修辞形式表露
思想。正如这两大叙事分支的总称(经验性和虚构性)所暗示的那样,在叙事文学的天地里,它们所代表的对立性就类似于科学和艺术对于终
极真理的方式之别。在古代,希腊传奇以其修辞化与情欲化之间的协调
性成为传奇叙事的典型。我们可以看出,史诗在从《奥德赛》到《阿尔
戈》(Argonautica)(23)
的演进过程中变得越发文学化和虚构化,直到
出现像《埃塞俄比亚遗事》(Aethiopica)(24)
这样纯粹的传奇。在现代
语言中,从《罗兰之歌》(25)
到克雷蒂安(26)
的《帕西瓦尔》再到《居鲁
士大帝》(Grand Cyrus)(27)
的发展,也表明了同样的演化模式。
至于教寓性的虚构文学类别,我们可以称之为寓言 ? ?;如果说传奇由
美学趋向操控,那么寓言则由知识及伦理趋向所操控。按照人类思维的
既有方式,寓言往往追求短小叙事,而当艺术家头脑中迸发出合理想象
时,寓言则大力借助传奇进行叙事表达。伊索寓言可谓寓言之典范,但
将寓言与传奇加以常规组合的重要例证则要数色诺芬(28)
的《居鲁士的
教育》(Cyropaedia),以及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叙事寓言。而梅
尼普讽刺(Menippean satire)(29)
则是与反传奇(anti-romance)相结合
的寓言,就像卢希安(30)
的《真实故事》(True History)发端于戏仿奥
德修斯的历险那样。文学史诗在维吉尔(Vergil)的作品中经历了从传
奇性叙事到教寓性叙事的演进,难怪但丁在《神曲》中会让维吉尔担当
向导。当教寓性叙事与传奇性叙事面临像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就诗歌
所发出的那种责难时,它们便会在彼此身上寻找合理性及相互支持。锡
德尼就文学所进行的“辩护”,正是基于此处我们论及的这一重要类别中
所包含的虚构性层面。他坚持要求文学既展现一种理想的或“金色”的世界,同时也能寓教于乐。不过,费尔丁在《约瑟夫·安德鲁斯》的前言
及其他场合讲到自己的创作时,则注重这一脉络的经验性层面,强调以
作品对整体人性的忠实为基础;当然,他也试图为读者提供乐趣与教
寓。
我们先前一直在探讨史诗综合体在瓦解过程中所衍生的两种对立门
派。现在,我们则必须简要考察一种新的叙事综合体,这是后文艺复兴
叙事文学的主要发展。其渐进式历程的始初最晚得从薄伽丘算起,当
然,它的真正茁壮发展乃是在17及18世纪的欧洲。这一新的综合体可以
在像塞万提斯这样的作家身上得以清晰的体现,其伟大作品力图在经验
性与虚构性两种强大的趋向之间寻求平衡。小说作为一种文学形式的出
现正发端于塞万提斯所开创的这个综合体。小说不是通常所认为的传奇
之对立物,而是叙事文学中经验性和虚构性元素联手打造的产物。摹仿
(常青睐人物(31)
和“生活的切片”之类的短小样式)和历史(其过分地科
学化会导致其文学性的丧失)在小说中与传奇和寓言进行合成,共同构
建一个伟大的综合性文学形式,正如远古传说、民间故事和宗教神话也
在史诗中产生过创造性的融合。有迹象表明,在20世纪,这种伟大的汇
聚又将发生,而小说就像史诗所经历的那样,必然会为新形式让出其
位,因为它是个不稳定的聚合物,其瓦解势必分离出当中的组成元素。
小说衰变之复杂容不得我们在此进行详细探讨,但我们可以注意到各种
衰变的征兆:乔伊斯和普鲁斯特采用极端的手法与之抗衡;伊萨克·迪
内森(32)
和劳伦斯·杜雷尔寻求传奇的回归;塞缪尔·贝克特将自然主义化
约为荒诞性;塞利纳(33)
和霍克斯(34)
的科幻小说及梦魇小说得以兴旺;
甚至在畅销书单上(往往为社会学叙事和间谍—历险故事所瓜分),玛
丽·麦卡锡(35)
和伊恩·弗莱明(36)
也会不禁让我们想起狄奥佛拉斯特式的人
物及希腊传奇所体现的古代小说传统。小说在其不稳定性之中能够体现出几分总体的叙事本质。它在直接
的话语者(或抒情诗的作者)与戏剧对行动的直接展现之间,在对现实
和理想的忠实之间寻求平衡;它比其他文学艺术形式拥有更大的极限发
挥,当然也因此付出了代价——沦为不尽完美的形式。作为所有学科中
最不正式的成员,小说提供的天地之广阔绝非任何一部孤立的著作所能
囊括,它不断引发文学性的颠覆,革新文学创作手段。那些最伟大的叙
事总是不遗余力地进行尝试。如威廉·福克纳所云,叙事文学既可能使
一位作家在审慎中获得成功,也可能让一位作家虽败犹荣。从历史的角
度看,它一直是文学门类中最具多样性、最富于变化的一种,换言之,也就是最具生命力的形式。尽管叙事文学不乏瑕疵,但它始终——从史
诗到小说——是最受欢迎、最具影响的文学类别,它比任何其他文学形
式都更能赢得其文化语境中最广泛的读者,更能够对超文学性影响做出
积极回应。在下面几个章节中,我们将着重探讨叙事艺术的多样性、复
杂性及其惯常的矛盾性。
(1) 埃里希·奥尔巴赫(Erich Auerbach,1892—1957):德国文献学家、比较文学家及文学
批评家,曾执教于耶鲁大学,著有《摹仿论:西方文学所描绘的现实》。
(2) 劳伦斯·杜雷尔(Lawrence Durrell,1912—1990):英国当代诗人兼小说家,著有小说
四部曲《亚历山大港四重奏》(Alexandria Quartet)。
(3) 沃弗兰·冯·埃森巴赫(Wolfram von Eschenbach,约1170—1220):中世纪德国诗人,生
平不详,其标志性作品《帕西瓦尔》(Parzival)是最重要的德国中世纪史诗之一,讲述亚瑟王
朝骑士帕西瓦尔寻求圣杯的漫长历程。
(4) 塞缪尔·约翰逊于1759年出版的小说,讲述阿比西尼亚(Abyssinia,今埃塞俄比亚)王
子厌倦“欢乐谷”的闲适生活,逃往埃及,探索幸福生活的哲学奥秘。
(5) 俄相(Ossian,公元3世纪):传说中古代爱尔兰最伟大的诗人、武士,其遗作后为18
世纪英国诗人詹姆斯·麦克弗森(James Macpherson)发掘、整理、翻译,但“遗作”的真伪在学
术界一直争议不断。
(6) 詹姆斯·麦克弗森宣称从盖尔语翻译、由俄相创作的古代史诗。
(7) 乔叟基于传统故事进行重新演绎的爱情悲剧,全诗讲述了特洛伊战争期间特洛伊王子特洛伊罗斯与特洛伊女子克瑞西达之间的悲欢离合。
(8) 杰弗里(Geoffrey of Monmouth,约1100—1155):中世纪英国编年史家,著有《英国
君王史》,对亚瑟王传奇在欧洲的普及起到了重要作用。
(9) 弥尔曼·帕里(Milman Parry,1902—1935):美国史诗学者,口头文学研究的革命性人
物。
(10) 阿尔伯特·洛德(Albert Lord,1912—1991):美国史诗学者,曾作为帕里的助手前往
波斯尼亚进行口头文学研究。二人共同创立了著名的“帕里—洛德模式”(又称“口头程式理
论”)。
(11) 穆赖(Gilbert Murray,1866—1957):英国古典学家,古希腊语言与文化学者。
(12) 康福德(F.M.Cornford,1874—1943):英国古典学家、诗人,著有《修昔底德:
神话与历史之间》《微观学术界研究》等代表作。
(13) 西奥多·盖斯特(Theodore Gaster,1906—1992):英国裔美国希伯来文化专家,著名
圣经学者,曾为弗雷泽的《金枝》进行批注并出版单卷节本。
(14) 厄文·帕诺夫斯基(Erwin Panofsky,1892—1968):德国艺术史家,后移民美国,现
代图像学研究的重要代表人物,著有《圣像画法研究》。
(15) 小罗伯森(D.W.Robertson,Jr.,1914—1992):美国学者,欧洲中世纪文学史
家,最杰出的乔叟研究专家之一。
(16) 此处所谓的“预表性类型”类似于《圣经》阐释中的“预表论”(typology),即一种原型
(《旧约》)当中已经预示了另一后继形态(《新约》)的某些元素。如果前者称为“原型”,那么后者即“预表性类型”。
(17) 就西方文化来说,“古典语言”通常指欧洲大陆在“古典时代”(公元前8世纪—后5世
纪)所使用的希腊文与拉丁文;而“本土方言”则指“古典语言”之外的民族方言,如中世纪欧洲
传奇文学用以创作的罗曼语,就是由诸多民族方言(如法语)构成的语族。
(18) 亚历山大时期:在希腊化时期及罗马时期以埃及亚历山大港为文化中心的历史阶段,其影响包括文学、语言学、哲学、医学及科学等众多领域。
(19) 狄奥佛拉斯特式的人物(Theophrastian Character):狄奥佛拉斯特(Theophrastus,公
元前372?—前287)是亚里士多德的学生,古希腊哲学家,其研究涵盖哲学、生物学、物理
学、伦理学等众多领域。其《人物论》(The Characters)介绍了献媚者、自负者、无礼者等各
种典型人物,对西方文学具有深远影响。
(20) 狄奥克里特(Theocritus,约公元前308—前240):古希腊田园诗的创始人。
(21) 裴特洛纽斯(Petronius,?—公元66?):古罗马讽刺家,疑为古罗马讽刺情色小说《塞
坦瑞肯》(Satyricon)的作者。
(22) 《塞坦瑞肯》当中26—78章的部分,讲述自由民暴发户特里马尔奇奥以奢华的宴席款
待宾客的故事。(23) 公元前3世纪创作、仅存的希腊化时期史诗,讲述了神话传说中的伊阿宋(Jason)及
其阿尔戈号勇士(Argonauts)智取金羊毛的故事。
(24) 又称《提亚戈尼斯与卡里克列娅》(Theagenes and Chariclea),由公元3世纪希腊传
奇作家赫利奥多罗斯(Heliodorus)创作的传奇。该作品自16世纪起风行欧洲,曾对英国早期传
奇小说产生影响。故事讲述埃塞俄比亚公主卡里克列娅因母亲怀她时凝视白色大理石雕像而生
来肤白,母后为避通奸嫌疑,将其送交他人抚养。成年后,卡里克列娅经历了与提亚戈尼斯的
爱情,以及接踵而至的磨难,关键时刻其身世为父王所知,继而得以与提亚戈尼斯终成眷属。
(25) 法国史诗,讲述查理曼大帝的侄儿罗兰奋勇战死疆场的故事。
(26) 克雷蒂安·德·特罗亚(Chrétien de Troyes,约1140—1190):法国中世纪诗人及传奇作
家。
(27) 17世纪法国小说,由苏德莱兄妹(Madeleine and Georges de Scudéry)创作,长达十
卷,两百多万字,讲述古代波斯帝国居鲁士大帝的传奇人生。
(28) 色诺芬(Xenophon,约公元前434—前355):古希腊历史学家、散文家,富于传奇色
彩的希腊“万人”雇佣军首领之一,著有“半虚构性”政治传奇《居鲁士的教育》,讲述波斯帝国
君主居鲁士大帝作为一代英明统治者所接受的教育。
(29) 古罗马学者瓦罗(Varro)的作品,现已失传;题名中的“梅尼普”,指公元前3世纪的
希腊讽刺家梅尼普斯(Menippus);现在,“梅尼普讽刺”常用于指文学作品中带有狂想意味而
又不乏思想的夸张性讽刺。
(30) 卢希安(Lucian,117—180):古希腊修辞学家及讽刺家,所著小说《真实故事》讲
述了主人公等一行人被狂风卷入外太空之后的离奇见闻。这部作品是目前已知的最早涉及外太
空、外星人和星际大战的科幻小说。
(31) 此处所谓的“人物”是指,上文提到的《人物论》当中的速写式人物。
(32) 伊萨克·迪内森(Isak Dinesen,1885—1962):丹麦小说家,著有《哥特传说七则》和
《走出非洲》等作品。
(33) 塞利纳(Louis-Ferdinand Céline,1894—1961):法国现代主义作家,对贝克特、萨特
及巴特等作家均产生过影响。
(34) 霍克斯(John Hawkes,1925—1998):美国作家,以超现实主义风格著称。
(35) 玛丽·麦卡锡(Mary McCarthy,1912—1989):美国作家及评论家。
(36) 伊恩·弗莱明(Ian Fleming,1908—1964):英国作家,詹姆斯·邦德的缔造者。2 书面叙事的口头传统
无人知晓人类掌握语言的历史究竟有多长。如果系统进化链上处于
人与猿之间某个“未知环节”的生物创造了语言,那么,语言可能要比人
类自身的历史久远得多。也许在数百万年以前,人便最初开始向自己或
他人复述某一令他愉悦的话语,并由此造就了文学。从某种意义上说,那就是西方叙事文学的开端。不过,我们将避免就该主题穷根溯源。要
理解远古时代的文学,任何针对荷马以来的叙事所做出的研究论断都显
得力不从心。那些作品本身所描绘的内容常常只能大致算是类人化生物
(anthropomorphic creatures)的所作所为;即便当时的语言能够为我们
所理解,也只会让未经训练的读者陷入迷惘或引起他们的憎恶。批评家
们难免会生搬硬套,试图将神话、传说、民间故事这些熟知的类别强加
在与此分类法相抵触的文本体系之上。
文学(就其词源的严格意义来说)若没有书写便无从产生。从定义
上看,它就是文字的艺术。我们的先辈曾持有一种观念,认为“书面语
言艺术”和“口头语言艺术”这一偶然的差异——如文学 ? ?
这个词所暗示
——导致了书面叙事与口头叙事之间的有效区分:前者因体现文明而可
为理解,后者则因体现原始而令人费解。近年来,我们已经对此产生了
不同的认识。口头叙事和书面叙事尽管在形式上存在差别,且差别很
甚,但在文化意义上,两者则没有任何差别。弥尔曼·帕里(Milman
Parry),作为研究英雄体诗歌口头创作的最杰出权威之一,曾写
到,“文学之所以分成两大派别主要倒不是因为存在两种文化,而是因
为存在两种形式 ? ?
:一部分文学成为口头性的 ? ? ? ? ? ? ? ? ? ? ?
,另一部分成为书面性 ? ? ? ? ? ? ? ? ?
的 ?”。在本章中,我们将通过考察古代希腊及北欧口头叙事来关注书面
叙事的传统,尤其会着重探讨口头叙事诗对此后书面叙事形式的影响。我们会研究口头叙事与书面叙事的一些形式之异,并不失时机地强调指
出:这些差异乃文学形式之异,而非甄别原始文化与文明文化的标准。
因此,我们会抛开文学 ? ?
这个词的词源学意义而在广义上对其加以运用,使其意指所有的语言艺术,既包括口头的,也包括书面的。
在我们这个时代,阅读与书写已成为普遍技能,而文盲则陷入文化
和经济上的匮乏;经验似乎已经证实文盲现象与文化贫困之间的联系。
不过,仅从我们的现代经验去概括,以为每个时代中所有不识字的个体
都是文化的贫乏者,则不仅有悖逻辑,而且也缺乏真实。读写技能,作
为我们几乎普遍掌握的独特现代形式,乃是文艺复兴文化与技术革命的
成果;但它不仅在很大程度上使我们对语言属性的认识发生偏颇,同时
也让文盲 ? ?
这个词肩负耻辱之重。读写能力使人们放弃对牧师或教师的依
赖。书籍和阅读能力成为受压迫者发现自由的途径。在我们这样一个读
写的时代,书籍变成了自由与真理的象征。焚书或禁书意味着对人性的
亵渎。这种做法并非将代表人类精神的财物视为专门的——甚至算不上
是主要的——仇视对象,相反,它所染指的乃是人类精神的象征物。
当然,并非每个时代都会对抄写员的墨迹和排版工的技艺表现出此
般理想化的观念。在《斐德若篇》(Phaedrus)(1)
中,苏格拉底讲了一
个故事,说埃及一位叫图提(Thoth)的神发明了书写文字。为了与人
们分享自己的发明,他便来到统治整个埃及的神塔穆斯(Thamus)跟
前。他向国王展示自己的文字,声称它们不仅会提高埃及人的记忆力,同时也会增强其智慧。此时,塔穆斯回答道:
哦,聪明绝顶的图提,有人会发明新技术,则有人会评判
那一技术对其使用者而言是祸还是福。如今,你作为文字之
父,出于个人情感,恰恰将文字的真实功能说反了。你这个发
明会导致文字使用者因忽视记忆而丧失头脑中的学问;因为他们可以依赖那些疏离于头脑的外在文字,进而丧失回忆事情的
能力。你非但没有发明一剂良药去增强记忆,反倒是为记忆炮
制出一种低级的替代品。你教给学生的乃是如何在缺乏真智慧
的时候伪装智慧;因为他们似乎无需教导便已经成为饱学之
士;他们好像满腹经纶,而实际却孤陋寡闻;而且他们还将为
公众所憎恶,成为一帮缺乏智慧却看似拥有智慧的人。
在我们的文化中,印刷文字的神圣性有时会将苏格拉底的担心发挥
到极致。以印刷形式表现的文字对我们来说,其真实性已经超越了活人
嘴巴发出的声音,以及这些声音所代表的概念。书籍虽仅仅是物化的客
体,却时而凌驾于世人所敬仰的智慧之上。任何谎言或怒语,一旦凭借
印刷的尊容得以展现,便会拥有千倍的威胁。能读会写的人士因其自身
的健忘甚至不敢想象那些目不识丁的诗人与讲故事者如何创造出伟大的
文学。我们很难设想古希腊人居然会允许遭到诗人和教师鄙视的仆人与
簿记员阶层独自享用米诺斯B类线性文字(Minoan Linear B)(2)
书写体
系(发现于克诺索斯和皮洛斯两地的皇宫废墟)。但是,证据似乎显
示,B类线性文字要比《荷马史诗》的创作至少早五百年之久,它在迈
锡尼时期希腊人的文学或教育中没有扮演任何角色。这一事实部分解释
了该文字系统为何最终被迈锡尼时期的希腊人所摒弃。而腓尼基字母
(Phoenician alphabet)引入希腊大陆地区(再次由簿记员阶层发起)的
时间通常被确定在8世纪。在弥尔曼·帕里做出结论性的发现之前,这听
上去似乎匪夷所思;现在,我们知道,《荷马史诗》的创作要远远早于
希腊文字在现代意义上的广泛使用。
帕里就《伊利亚特》及《奥德赛》的口头创作所进行的阐释包括两
个部分;两者均证实了这样一种假说,即口头创作文学与书面文学得以
区分的基础在其形式而不在其内容。正如我们接触《荷马史诗》那样,帕里的研究亦以《荷马史诗》的书面文本为起点。他注意到,传统饰语
和措辞尽管一直是后来西方传统中“史诗风格”构成当中的一个次要元
素,但却总是被荷马用在相同的格律及语义情景当中。荷马语汇的这些
传统元素在数量及质量上要比后来诗人的作品丰富得多;帕里将它们称
为程式(formulas)。按其定义,程式即“在相同的格律条件下得以反复
运用的一组词,以表达某个恒定的核心理念”。用于阿伽门农
(Agamemnon)身上的固定饰语,如“阿特柔斯(Atreus)之子”和“众士
之王”;而“戴着耀眼头盔”则用在赫克托(Hector)身上;用以指大海的
则包括如“朱红似酒的”“澎湃激荡的”和“充满回响的”等饰语。这些固定
饰语一直被认为是荷马风格的特征,而其效果则为继阿波罗尼奥斯(3)
以
后的文学史诗作家所效仿。不过,直到帕里发现整个荷马语料库——约
27 000行六音步诗句——完全是程式化的,批评家们方意识到,过去一
直看似表面化的文体风格特征,事实上作为不可回避的证据证实了《伊
利亚特》和《奥德赛》系口头创作。比如,《伊利亚特》前15行中90%
显然是程式化的;也就是说,在荷马语料库的其他地方,研究者在同样
的格律环境中找到了与之相匹配的相同语汇群。就我们所知,任何一个
《荷马史诗》段落的程式化百分比几乎是一样的。在我们已知的书面文
学诗人的作品中,逐字重复的百分比与前者相比差距甚远。正相反,书
面文学诗人力图赋予每一行诗以独特性,而把重复的短语留作营造特殊
的修辞效果。
帕里研究的第二部分在某些方面甚至比第一部分更有成效。为了反
向证实其第一个推断,即高度程式化的诗歌语汇乃口头创作的证据,帕
里着手说明,口头诗人凡创作必用程式。他们在即兴创作时以其诗歌传
统中的惯用程式为基础,组织符合格律和语义的诗句。帕里在南斯拉夫
对南部斯拉夫语口头史诗进行研究时发现,基督教和穆斯林吟唱诗人都
能够在名为古兹拉琴(gusle)(4)
的单弦乐器伴奏下创作出在篇幅、复杂性及文学趣味方面接近《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的史诗。这些吟唱诗
人认为自己能够一字不差地重复一整部史诗;他们所引以为豪的是,自
己能记住在其看来是所谓固定“口头文本”的东西。然而,当帕里就同一
位吟唱诗人的同一首歌曲分别进行了两次记录后,他发现两次表演很少
有完全一致的情况。在这两个版本中,单独的诗句和诗节的创作均存在
差异,但是两者都使用了相同的程式。从诗句构成的层面来看,识别口
头创作的恒定条件是传统程式的存在,而不是两个文本之间逐行的相似
性。
尽管帕里的发现的确为基于真凭实据的猜想提供了更为坚实的基
础,但它们无法就有关荷马的所有问题为我们提供最终的答案。依据帕
里在南斯拉夫的调查,以及世界其他地区有关口头创作史诗的报告,我
们便能够——比如说——重新构想荷马的身份问题,当然我们还是无法
对此给予明确的答案。口头诗歌叙事传统当中的个体吟唱诗人与书面叙
事传统里的个体诗人是一样重要的,但是吟唱诗人的角色与诗人的角色
却有着天壤之别。吟唱诗人完全依赖其传统。他所学会的情节及对其进
行详尽阐发的各种片段,甚至他用以组织诗句的短语,都是传统性的,广义地说,就是“程式化”的。他既非创作,也非记忆某一固定文本。每
次表演均是一次独立的创造之举。在吟唱诗人实际演绎一则叙事之前,此诗歌并不存在,而只是以吟唱诗人传统这一抽象工具,潜在于无数其
他诗歌当中。反过来说,当诗歌终了,它也就不存在了。只有当吟唱诗
人本人或某个听众在一次表演过程中发现传统之外的某样新东西,该诗
歌方能影响传统,继而在那些听众的记忆中产生些许永恒性。
或许是因为这些诗歌只是对传统的演示,而非个人智慧的发明,大
多数口头创作的叙事诗尽管以书面文本的形式加以保留,却并未联系到
具体诗人的名字,甚至传统上就没有这种做法。将《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的创作归功于荷马或将古冰岛语《诗体埃达》(Poetic Edda)(5)
归功于“智者塞蒙恩德”(S?mundur the Wise),这些结论虽然已为我们
当今的口头传统知识所大力证实,但仅属例外。基涅武甫
(Cynewulf)(6)
的文本显然属于盎格鲁—撒克逊口头叙事,而作为贯穿
于这些文本之中的如尼文(runic)(7)
签名则成了让学者们大伤脑筋的问
题。这些签名或许应该被视为代指某位抄写者或口头诗人;他既熟悉书
写,同时也对自己的作者身份怀揣几分书卷气的怜惜。对于书面创作者
来说,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但对于口头诗人而言则相当不可思议。事
实是,无论这些签名的来源是什么,基涅武甫的叙事依旧如《贝奥武
甫》一样具有修辞上的高度程式化和传统性。不管基涅武甫是谁,与其
姓名相系的诗篇均创作于通常的盎格鲁—撒克逊口头传统,而并不能以
任何现代意义代表一位具体诗人的作品。我们使用某位具体诗人的姓名
去指示一则口头叙事的作者身份,无非是为了权宜之便,如荷马与基涅
武甫的例子,或出于对传统的尊重,如《塞蒙恩德的埃达》;因此,关
于诗歌背后的创作者,我们应该将其角色更多地视为歌者或表演者,而
非现代观念里的“作者身份”。
有一种看法认为诗体叙事可能会在口头传递的过程中“受损”,但这
不过是针对口头传统机制产生的普遍误解。假若一首口头创作的诗歌,如古冰岛语《沃卢斯帕》(V?luspá)(8)
,变得艰深晦涩,那么这种麻烦
产生的原因,无非有二:拙劣的表演,或更有可能的是手稿传递过程中
产生的讹误。一场口头表演或许平庸无奇,但不会艰深晦涩或是遭
到“文本性损伤”。另一方面,一位伟大的吟唱诗人历经多年艺术修养的
完善,往往能够超越他曾听过的任何表演。即便只是聆听一场拙劣的表
演,他也能了解到一个故事——基本情节和人物姓名,并且他能够运用
自己对传统的把握吟唱出一首比原曲长许多倍、编排更精致的作品。在
这种情况下,我们不妨认为:一首诗在口头传递的过程中恰恰得到了“完善”,当然,此说法也多少与“文本性损伤”的观点犯了同样的错
误。因为这就意味着一种作为实体存在的诗歌被传递了,然而这并非口
头传统中的情形。我们可以认为,诗歌里的诸多元素被传递了——情
节、片段、人物的观念、关于历史事件的知识、传统性母题、语汇等,但是我们不能以为被口头传递的乃是这首诗歌本身。
我们可以将荷马看作众多希腊史诗吟唱者中最杰出的一位艺术大
师,虽然他在本质上无法超越其所在的传统,但却能够在表演中将传统
推向最佳境界。依照这种观点,或许我们既能最大限度地接近通常观念
中的荷马,同时又尽量不损及口头创作的实际状态。荷马之伟大在于其
传统之伟大。他在知识及情感方面所营造的广博与共鸣,他在表现具体
的人与事时所展示的客观性与准确性,他的虔诚与讽刺所体现的爱憎分
明,——这些成就乃属于名为“荷马”的古希腊史诗传统,而并不属于局
限在个体观察与记忆当中的某位孤立的诗人。口头诗人与其所处的文学
文化之间存在着相当密切的联系。书面文学追求创新性与个性表达,但
这些机会对于口头诗人而言是极其稀少的。口头吟唱者在遵循传统的基
础上将个体天赋发挥到极致,或许也可以说,在因循个体天赋的基础上
将传统形式发挥到极致。两者不过是同一实体的不同层面而已。没有诗
歌,传统便会消亡;没有传统,诗歌也就无以存在。
然而,传统也能发生变化。它可以调整自己——当然进程是缓慢的
——不仅适应其诗歌所再现的外在文化及物质世界,甚至对诗歌赖以构
建的语言形式的变化也能做出反应。荷马文本基本是属于爱奥尼语
(Ionic)(9)
风格的,它们对古风特色与地区方言进行的糅合乃是一种妥
协:一方面是最古老的阿卡狄亚—塞浦路斯语(Arcadian-Cypriot)(10)
和爱奥尼语形式,对此,传统在向希腊大陆地区转移的过程中无法彻底
加以遗弃;另一方面是稍晚出现的阿提卡语(Attic)(11)
形式,对此,传统则加以运用,力图保持作品的当代性和可阅读性。作为一首口头创
作的古英语史诗,《贝奥武甫》也表现出相似的语言糅合特点,其传统
回溯至麦西亚(Mercia)(12)
的文化繁盛期,而其基本语言则属于稍后的
西撒克逊模式。
只要有可能,新的语言形式就会逐渐替代先前的旧形式,此外,口
头诗歌传统也可对旧的程式进行类推,从而生成新的程式。例如,“贵
族之梦”(eorla dream)作为一种盎格鲁—撒克逊的半行诗程式(13)
往往
用以描述“贵族扈从的快乐”。但随着基督教主题和故事的逐渐引入,该
传统便以旧程式为依托创造出所谓“天使之梦”(engla dream)的新程
式,用以描述“天使的快乐”。用口头诗歌语汇研究者们的术语说,“贵
族之梦”与“天使之梦”这两个程式构成了一种“程式模版”或“程式系统”。
按照帕里的定义,程式系统指的是“在思想及语汇层面足够相似的一组
短语,诗人在运用它们的时候毫无疑问不仅将其视为独立的程式,同时
也把它们当作某一类型的程式”。这些抽象系统或模版的存在,将传统
语汇的渐进式演变纳入研究视角。更重要的是,程式模版在具体吟唱诗
人的演艺中所发挥的作用也受到了关注。阿尔伯特·B.洛德的著作《故
事歌手》(The Singer of Tales)进一步推进并深化了帕里在南斯拉夫的
研究及其就《荷马史诗》的口头创作所形成的理论。洛德认为:
构建诗句的根本元素是基本的程式模版。可以有根据地
说,具体程式本身对吟唱诗人的重要性仅仅产生于程式的基本
模版植入其思维之际。当诗人到达这一境界,他对学习程式的
依赖性会越来越小,而更多的则在于对程式模版中的语汇进行
替换。……这便是其艺术的整体基础。
于是,在诗句构成的层面上,口头诗歌传统的基本实体并非一成不
变的程式(当然,依据这种固定程式,我们可以准确识别诗歌的口头创作身份),而是抽象化模版,凭借它们吟唱者能够创造新的语汇。在此
层面上,传统与其说是包含一套固定的元素,不如说是包含一种“语
法”。这种语法叠加在口语的常规语法之上,但与后者存在相似之处,即对这种语法的习得乃是处于意识层面之下的过程;同时,伴随这种语
法会对认识及构想外部世界产生强烈的约束力。围绕思想的演化必然存
在双重约束机制:一是通常认为的语言结构限制;二是传统智慧的“语
法”限制。艾里克·A.哈弗洛克(14)
曾发表颇具说服力的观点,认为柏拉图
在《理想国》中对诗人的责难是一种革命性的尝试,他力图将希腊思想
从口头传统的“语法”独裁中一劳永逸地解放出来。
写出既具格律又可被理解的诗句,并非口头诗人面临的唯一挑战。
在某种程度上,他还必须在表演的过程中“编造”故事。关于口头叙事诗
的“形态学”,人们对其抽象化程式模版有所了解,而对其更为重要元素
的认识则相对不足。帕里与洛德认为,在南部斯拉夫语及希腊语口头史
诗中存在着他们称之为传统“主题”的东西。另外,他们对盎格鲁—撒克
逊语、古冰岛语、古法语及古芬兰语口头叙事诗也做了相似的传统主题
元素分析。洛德曾将口头诗歌的“主题”定义为“以传统诗歌之程式化风
格讲述故事的常用观念群”。在《奥德赛》当中存在着数次程式化的描
绘,用以讲述热情好客的主人欢迎一位来访者;按照洛德对该术语的理
解,这就构成了一种口头“主题”。在日耳曼口头叙事当中,一群贵族随
从围着国王觥筹交错,自矜自夸,这种所谓“贵族之梦”的描写则构成了
那个传统当中的一种“主题”。对于口头叙事诗而言,用“主题”一词去定
义其风格手法当中的形式元素在实践上存在很大的困难,原因是这个词
同样用于一般的文学批评中,其意义不仅多样化,而且有时候会相当矛
盾。
在分析口头创作的诗歌时,我们专门使用了“主题”(theme)一词,而根据希腊修辞学,我们则提出“论题”(topos)这一替代性术语。
这个概念因恩斯特·罗伯特·库提乌斯(15)
在其《欧洲文学和拉丁中世纪》
一书中的研究而广为接受。我们并无意暗示希腊修辞学家们所使用的具
体“论题”与古希腊史诗中被帕里、洛德称为“主题”的概念之间存在必然
的历史关联,而是说,从结构性视角来看,那些多少趋于程式化的修辞
元素,如欢乐之土 ? ? ? ?
(16)
(描写理想的景致)和少年老成 ? ? ? ?
(17)
(出于对年轻
人的称赞而认为其拥有长者的智慧),与口头叙事诗中的程式化观念群
非常相似,从而使得该描述性术语同样具有存在的必要性。
一则“论题”,不管出现在口头叙事还是书面叙事中,乃是一种传统
的意象。对它进行识别甚或分析的基础,并非诗人用以构建“论题”的程
式或经过独特安排的语汇,而是这些语汇所指的意象。关于叙事意象的
主题分析,我们会在第四章进行详尽的后续讨论。在此处,我们不妨言
简意赅:如果一则“论题”指示的是外部世界,那么,其含义就是一个母 ?
题 ?
(motif);如果该“论题”指示的是无形的观念和概念世界,那么,其
含义就是一个主题 ? ?。于是,传统性“论题”便包含两种元素:传统母题,如主人公遁入冥界——这在历史上可谓经久不衰;传统主题,如寻觅智
慧或下降阴府(18)
——这更易于经受渐进式的嬗变或最终的替换。口头
叙事的“论题”得以识辨的基础是其在一个既定的母题与一个既定的主题
间建立的恒定联系。另一方面,就书面叙事而言,母题与主题的关系即
便是在传统性“论题”当中,也往往会受制于诗人的操控。当然,古代叙
事“论题”的主题内容分析起来颇为棘手。正如日耳曼口头诗歌传统中的
那些“论题”,荷马式“论题”有一度也同宗教仪式紧密联系着。因此,即
便其叙事显著摆脱了直接崇拜的束缚,而它们的主题内容却仍留存着些
许宗教色彩。
口头叙事诗的“论题”常以模式化序列得以展现,一个“论题”会挑选另一个“论题”,抑或作为一个整体的系列“论题”会挑选另一个整体化系
列“论题”。洛德从《奥德赛》当中列举一例对此模式化加以说明;在他
看来,奥德修斯回归故里之际对伊萨卡(19)
人的试探正是通过重复一
种“论题”模式来表现的,其母题是“凌辱”(abuse)、“责难”(rebuke)
和“认出”(recognition)。在此母题模式之下存在这样一个主题,即“经
过伪装的再生之神由于未被卑劣之徒认出而遭到后者的拒斥”。该模式
始于第17卷,此处奥德修斯受到墨兰提俄斯(Melanthius)(20)
的凌辱 ? ?
,随后又遭到欧迈俄斯(Eumaeus)(21)
的责难 ? ?
,接着被奥德修斯的狗阿尔
戈斯(Argus)认出 ? ?。而后安提诺俄斯(Antinous)、欧律马科斯
(Eurymachus)及克忒西波斯(Ctesippus)(22)
对奥德修斯实施了凌辱;
责难则由奥德修斯妻子的求婚者及忒勒玛科斯(Telemachus)(23)
实施;
认出奥德修斯则包括与伊洛斯(Irus)(24)
的决斗、欧律克勒亚
(Eurycleia)(25)
那一幕,以及射箭比赛。这种模式说明,篇幅处于单
个“论题”与整部诗歌之间的结构性元素可以掌控逐个“论题”的编排。我
们不妨用“神话”(myth)(26)
这一术语来指代“论题”的这种铰链序列。一
方面是“论题”,另一方面是整部诗歌,而神话正如这两者一样,包括叙
事含义的两个基本层面:对于外部世界的再现 ? ?
(母题)和针对我们思维
中的观念和概念进行的阐释 ? ?
(主题)。
神话的再现层面是情节 ? ?;而其阐释层面(与“论题”和整部诗歌的情
形一样)则是主题 ? ?。口头吟唱者在将神话融入自己的诗歌时,必须同时
表现这两个层面。随着现代意义上读写时代的到来,或是由于某种激进
的文化变异,口头诗体叙事便会寿终正寝;此时,神话的阐释层面演变
为寓言和推论式的哲学写作,而神话的再现层面则演变为历史和其他经
验化叙事形式。
情节与主题相结合的传统属性作为口头叙事诗的特征,只是史诗综合体的一个方面。史诗的另一个特征是,它在宗教神话与世俗叙事之间
择取了中间路线;前者的故事完全外在于世俗世界中的历史人物与事
件,而后者的故事则完全发生于由历史人物与事件所构成的世俗世界内
部,或即便是发生于一个虚幻世界,其运作法则也同样掌控着现实世
界。也许,要认识口头史诗所构建的复杂综合体,最简单的方法便是将
其视为原始文化的唯一文学产品。这种看法当然过于简单化,但公证体
现了口头史诗的作用:它不仅保存了传统的诗歌“语法”(借此可以理解
和思考新经验),而且保存了文化中最重要的宗教、政治及伦理价值
观。经典荷马文本的确立经历了一个渐进式过程,自其肇始400年后,柏拉图意识到荷马式教育(paideia)这一垄断格局乃是思想进步的大
敌。只要荷马依然作为唯一的导师主宰着所有学科,那么,通向哲学思
索的唯一渠道便只能是围绕其“隐含意义”而进行的寓言式解读。
《荷马史诗》以其书面形式为我们所接受,然而关于它获取书面形
式的具体过程,我们则几乎一无所知。大量证据显示,希腊史诗传统中
的大多数传统故事乃是以非史诗形式(主要是戏剧形式)历经后世而得
以留存。某些非《荷马史诗》表演,甚至在绝迹之前便产生了书面形
式。来自西嘉(Sicca)(27)
的优提齐乌斯·普罗克洛斯(28)
曾编撰《文学选
读》(Chrestomathy),如今已经失传,不过从弗提乌斯(29)
(约820—
891)等人对此书进行的概述中,我们可以得知亚历山大时期希腊人尚
可获取的书面文本史诗的名称、大致篇幅(以行数或卷数表示)及内
容。这些文本中没有一例达到《伊利亚特》或《奥德赛》的篇幅,这似
乎说明了荷马文本无论在表演方面还是文字记载方面都具有不同寻常之
处。
在公元8世纪、7世纪和6世纪的希腊,书写的用途一定与我们今天
的情况有着天壤之别。无论在7世纪的希腊还是1200年后的北欧,铭刻碑石的存在本身并不代表以书写为基础的教育体系或文学文化。在南斯
拉夫史诗中,书面文件甚至电报被提及的频率之高,足以说明口头文学
传统能够通过紧密贴近其他用途的书写形式而得以幸存。如果我们要想
象传统荷马文本的某一粗劣原型得以通过口述听写的方式进行书面载
录,那我们就必须相信,对于文字和书写的运用在历经数个世纪的发展
之后已经成为熟练技能。不过,仅仅将书写引入文化中的某一单个领域
还远不足以产生任何接近现代意义上的“读写技能”。因为那意味着我们
需要拥有一种稳固确立的、建立在文字基础之上的教育传统——而这一
观念,即便对7世纪的希腊人来说,也会让他们颇感震怒。
洛德在南斯拉夫的研究说明,有多种方式可以用来将口头叙事转化
为书面形式,但几乎所有这些尝试均是对现场口头表演的拙劣再现。如
果吟唱者让抄写员听写,或者在其会写字的情形下,由他亲自听写,他
的表演定要比正常状态下慢得多。在这种情况下,他很容易失去节奏和
思维的连贯性。书面文本要想优于实际的演出,必须符合几个条件:吟
唱者愿意缓慢而耐心地让抄写员进行听写;抄写员对该传统烂熟于心;
在碰到出错的诗行,抄写员可以停下来让吟唱者重复。既然最终的文本
对于吟唱者而言可能并无任何用处,那么吟唱者与抄写员付出如此艰辛
的劳动,则理应存在某种特殊情况以构成其创作动机。这或许应该是依
采风者的要求所为。在我们看来,书面《荷马史诗》文本的产生定是源
于某种与此相类似的创作方法。
当口头表演化约为两个“作者”的书写,表演者和抄写员,并继而进
入一种准文学传统,真正的口头传统并不会受影响。然而,最终可能对
其形成挑战的乃是从新建立的文本传统中所衍生出的伪“口头传统”。于
是,一种新型的职业演艺者便开始同真正的吟唱者产生竞争,他们只是
记忆书面文本,而后四处朗诵。当“口头传统”这个词被文学学者们误用之际,往往指的就是这种口头朗诵,它依赖于事先用笔和纸这种现代方
式创作的固定文学文本。能够将真正的口头传统与书面再现区分开来的
因素是创作的方法,而不是表现的模式。洛德根据自己在南斯拉夫的研
究可以轻松地对真正的口头创作和书面文本的口头朗诵进行甄别。一种
是程式化的,而另一种则不是。
关于“过渡文本”(transitional text)这种代表口头与书面创作组合的
形式,尽管一些荷马学者、中世纪研究专家及其他人(包括我们自己)
对此深信不疑,但似乎并不可能。一切通过直接观察现存传统所获得的
证据,均促使我们推导出这样的结论:即便诗人自己进行创作,很明
显,他只会择其一——要不采用传统的口头程式法(展示口头传统的所
有特色),要不采用文学方式(展示文学创作所特有的思想和语汇的创
新)。不过,关于荷马文本的传播,真正有可能且最令人信服的猜想则
是:那种原汁原味的口头表演会通过誊写的方式与其书面文本的口头朗
诵相结合,继而逐渐发展为一种准文学传统。如果此现象发生,那么书
面文本便可能凌驾于真正的口头传统之上,从而获得最优秀的抄写员与
表演者的共同关注。面对不断推广的读写技能和基于权威文本意义上的
正规学术性教育,真正的口头传统在文化中的地位便会慢慢降低。同
时,真正新式的书面文学形式开始从旧式口头传统与新式学术传统的融
合中产生。
或许,关于《荷马史诗》获得其传统书面形式的过程,我们的推测
不该完全依赖于对今天南斯拉夫或中世纪北欧相似情形的认识。尽管书
面基督教文化对欧洲其他地方的本土口头传统产生了强大压力与潜在影
响,但要让一种域外书面传统对希腊口头史诗产生任何类似的影响,却
是难以想象的。在希腊,这种过渡一定是在主导文学文化内部渐进发展
的,即一种形式在某种程度上自愿让位于另一种形式。而在欧洲其他地方,口头传统不是突然遭到外来强势书写传统的压制,就是遁入隐蔽之
所,成为愚昧无知的农夫在草舍锅台边的娱乐。一方面是7世纪希腊的
《荷马史诗》吟唱者,另一方面是19世纪波斯尼亚或卡累利阿
(Karelia)(30)
的吟唱者,但两者的身份是难以相提并论的。古希腊的吟
唱诗人被王子们尊为大师,而其他的吟唱诗人则是为了取悦那些尚未摆
脱文化愚昧者(illiterates)身份的观众,当然,这里的“愚昧者”完全是
基于其可怕的现代意义。
圣经《旧约》文本中有很多源于口头传统的证据,因此,古代希伯
来人可能也经历了从口头到书面叙事之数世纪的漫长演化过程。我们也
许可以想象,他们与古代希腊人的情形存在相似之处。但是,在这两条
文化巨脉汇合之际,它们的影响横扫了整个欧洲。它们带来了读写技能
和对权威文本的尊重。就希伯来这条血脉而言,其最重要之处便在于它
以一个权威性文本去争得绝对的虔诚。阿尔昆(Alcuin)——一位9世
纪的英国学者,查理曼宫廷中复兴古典文学的杰出人物——曾言简意赅
地表明了教会对异教诗歌的态度。当他得知诺森比亚
(Northumbria)(31)
的林迪斯坊(Lindisfarne)修道院中僧侣们正以吟唱
有关日耳曼英雄英叶德(Ingeld)的史诗作为娱乐时,他带着几分讥讽
质问他们,“英叶德与基督何干?”阿尔昆的怒吼响彻了基督教统治下的
整个中世纪。
稍早于此,关于盎格鲁—撒克逊时期诺森比亚内部这两种文化的对
立,还有个故事对于我们则更有意义。这就是圣比德(32)
在《英国人民
基督教史》(The Ecclesiastical History of the English People)当中讲述
的关于诗人凯德蒙(33)
的故事,小F.P.马古恩(34)
曾将其称为“一位盎格鲁
—撒克逊口头诗人的个案史”。据说在希尔达(35)
(658—680)担当惠特
比修道院院长期间,院中的僧侣曾向凯德蒙讲解宗教信条与叙事,而凯德蒙则以此为基础创作出许多英语叙事诗。在圣比德关于凯德蒙的叙述
中,最突出之处乃是关于这位中年的凡夫俗子如何奇迹般的获得创作叙
事诗的天赋。凯德蒙原先并不会当众作诗;每逢节日庆典,竖琴便会在
众人手中传递,大家轮流吟唱,而凯德蒙却抽身离去,直到某日,一位
天使现于其梦中,要求他吟唱创世的故事。这则神奇之梦,作为一种解
释,说明了凯德蒙如何在人到中年之际能够运用完全传统化的口头程式
进行卓越的诗歌创作,以专门服务于基督教的宣讲。圣比德指出,凯德
蒙从未创作过“任何无关痛痒或毫无用处的诗歌;相反,他的虔诚之言
只适用于那些关乎宗教的诗篇”。另一种解释是,传统的盎格鲁—撒克
逊程式模版之所以为凯德蒙用来创作其《赞美诗》(Hymn),以及现
存的那些围绕“创世纪”及“出埃及记”所进行的盎格鲁—撒克逊语改编
(如果它们果真代表其表演的话)——乃要归功于他在私下里对技艺的
学习和练习;他不急于进行首次公开表演,而是一直等到发现如何将其
诗歌用于效忠上帝。
传统上,与凯德蒙所经历的梦幻奇迹相联系的还有一个故事,它保
存在神秘的拉丁文《序言》(Praefatio)和《诗篇》(Versus)当中,现代研究理论将它们与古撒克逊语诗歌《救世主》(Heliand)和《创
世纪》(Genesis)相联系。这两个拉丁文本大致可追溯到10世纪,但只
留存在马提亚·弗拉齐乌斯(36)
的《真理见证者目录》(Catalogus Testium
Veritatis,1562)第二版中;它们在简短的篇幅中不乏矛盾地描述了
(1)查理曼之子,法兰克皇帝“虔诚者路易”(执政期814—840)所下
达的命令,“撒克逊国有个人被其同胞们视为杰出的诗人,他必须负责
将《旧约》和《新约》翻译成日耳曼语言,如此,神的教诲不仅能让文
化之士享有,也可让愚昧之众领会”。(2)“正是这位诗人,当他还完
全不了解诗艺之际,却在睡梦中受命依照他自己的(撒克逊)语格律将
圣典之法改编为诗歌。”这些故事的共同之处在于,它们均指涉了本土口头叙事传统——这
一传统经过调整不仅适应了普通读本文化,而且也应和了圣经读本文
化。对于像凯德蒙这样的诗人或是创作《序言》的无名氏撒克逊神谕诗
人(vates)而言,问题不只是对抄写员进行口授,而主要是运用传统程
式及“论题”去表达全新的情节与观念。我们很难想象还会有其他诗歌能
够表现出比《救世主》更高的程式化。在这部作品中,程式或程式模板
几乎包含于每一诗节,它们既可能反复出现于该诗作本身,抑或出现在
盎格鲁—撒克逊的诗歌语料库中。当然,其传统化特征并不局限于程式
化创作。它还运用了许多如《贝奥武甫》等世俗诗歌中出现的传统母
题。这些母题清晰地说明,古撒克逊口头传统乃是新近衍生于英雄体的
文化,而这种文化则迥异于那些为《救世主》提供情节基础的《新约》
叙事。不过,同样清楚的是,撒克逊诗人与中世纪基督教文化保持着紧
密联系。当他们充分顾及传统程式和母题的时候,其叙事就相当于对下
列这些文本进行了一番细致的改述:他提安(37)
四福音合参的伪著、拉
巴努斯(38)
对《马太福音》的批注、圣比德对《路加福音》《马可福
音》的批注,以及阿尔昆对《约翰福音》的批注等。
纵观13世纪的古冰岛语《诗体埃达》、古高地德语(39)
《希尔德布
兰特之歌》(Lay of Hildebrand)(40)
,诸如《瓦尔迪尔》
(Waldere)(41)
、《戴欧》(Deor)(42)
、《威德西斯》
(Widsith)(43)
,以及残诗《费恩堡之战》(Finnsburg Fragment)(44)
这
样的盎格鲁—撒克逊语诗歌,乃至于法罗群岛(45)
的英雄体歌谣(直到
上世纪方以书面形式记录下来),我们可以发现,这些诗歌具有口头创
作和英雄体文化相融合的明显痕迹。不过,由于日耳曼口头传统早在圣
经文本到来之前便已兴盛,因此,要对它进行研究,我们的最佳考察文
本莫过于盎格鲁—撒克逊史诗《贝奥武甫》。这首诗存于仅有的一部手
稿当中,大约在10世纪末由两位抄写员书写而成。如所有刚才提到的其他诗歌一样(除去法罗语歌谣),《贝奥武甫》可能并非直接抄录自口
头表演。大部分学者将其多样化的语言形式及拼写,看作是两个半世纪
之久的文本传统的证据,并因此将其创作时间确定为8世纪早期。关于
《贝奥武甫》系口头创作这一论断,学界已经找不出合理的质疑。其措
辞具有显著的程式化特征,其“论题”同样为相似的古英语及其他日耳曼
语诗歌所采用。
很显然,口头诗人能够通过书本,或至少可以借助文字中介,而获
取故事和主题,但在《贝奥武甫》中,书卷学习的证据则微乎其微。不
管是其风格还是其内容,似乎都在说明,古代日耳曼的确存在高度发达
的口头史诗。当然,我们无法知晓这种传统究竟发达至何种程度,或者
在自行其是的情况下又会如何发展。但罗马—基督教文化的进犯则完全
湮没了这种传统。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要想当然地以为史诗传
统只是为远古人类所独有的特征,事实远非如此。我们已经认识到,对
于相对未受侵扰的希腊人来说,史诗是真正现代文学及哲学文化到来之
前的最后一个阶段。其他各种证据,如精良的武器和舰船,以及先进的
政治和法律制度,均说明北欧的异教徒们正在接近8世纪希腊人所经历
的文化发展。当基督教于公元400至1000年之间的数世纪中进入北欧
时,它所遭遇的文学文化已经形成了融合神话与摹仿的史诗综合体,并
正值分化之际,由此带来法律、宗谱、神话、宗教仪式及世俗叙事小说
等独立门类。
《贝奥武甫》的吟唱者关注的是丹麦人与弗里斯兰人
(Frisians)(46)
及希索巴特(Heatho-Bards)人(47)
之间的关系所代表的
更广泛的社会与政治意义,或是一位明君的必备道德素养,这些都是其
史诗传统的特点;它们不仅出现在埃达文选里,同样也出现在《流浪
者》(The Wanderer)(48)
、《威德西斯》及《戴欧》当中。而在较此晚很多的传奇当中,像《高文爵士与绿衣骑士》及无数其他涉及亚瑟王朝
的故事,尽管存在政治和道德主题,但均不甚关乎具体时空下的实际问
题,也游离于积极的政治生活之外。在史诗中,维护社会秩序乃是至善
至上的目标,而主人公体格与智力的修行都以此为尊。史诗的社会往往
是特定的社会,其残垣断壁可由现代考古学家进行甄别。《贝奥武甫》
的哀歌之风在一定程度上只是源自主人公为保护其社会免于妖敌肆虐而
喋血疆场。然而在更大程度上,这悲情的产生却是由于我们认识到贝奥
武甫的力量和智慧遭受了徒劳的消耗。他身上的那些品质未能在丹麦人
和耶阿特人(Geats)(49)
当中流芳百世,而他所援救的社会也因无法躲
避纯粹社会性的诟病而注定走向衰亡。
就像荷马一样,《贝奥武甫》的创作者同样描绘了一位在现场进行
表演的口头吟唱诗人。贝奥武甫于牡鹿厅(Heorot)(50)
击败戈兰德尔
(Grendel)之后的那个早上,丹麦人前来察看那只带血的胳膊,并走
访戈兰德尔得以消隐的那个沾满血迹的湖泊。作为他们欢庆的一部分,一位诗曲满腹的吟唱诗人就贝奥武甫的事迹创作了一首新作品,“编织
得如行云流水一般”。这位诗人接着讲到屠龙者西格蒙德
(Sigemund),又提到赫里摩达(Heremod)——一位丹麦国王,其罪
恶行径与贝奥武甫和西格蒙德的英勇之举形成鲜明对照。这个小段落
(B版手稿867—915行)的意义在于,它不仅说明在口头传统中,神话
所保留的价值观如何用来指导对于当下事件的理解,同时也说明当下事
件如何被传统兼收并蓄。通过将贝奥武甫击败戈兰德尔,以及西格蒙德
屠龙这两个母题相联系,这位吟唱者就诗歌结尾处贝奥武甫本人与龙妖
对抗的意义做出了一个主题性的陈述。这场屠龙之战,至少在某种意义
上说,可以理解为对戈兰德尔片段的重述,在那一处,西格蒙德已经作
为一则类比被作者加以引证。《贝奥武甫》再次表现出与《荷马史诗》的相似,它凭借其传统语
汇和历史典故传达出这样一种印象,即这类诗作势必在其所描绘的贵族
社会中得以吟唱。换言之,我们觉得,一群农夫或虔诚的僧侣只会推崇
圣徒的生平或是一首有关其社会及精神楷模的歌谣,而不适合成为欣赏
《贝奥武甫》的听众。我们从古罗马作家那里听到大量描绘日耳曼文化
的抒情短歌(cantilenae)或田园诗(carmina rustica),但这部作品绝
非此类题材的范例。如果我们的直觉是正确的,那么《贝奥武甫》所代
表的恰恰是让真正的口头传统发挥其至上的文化功效,即针对天子的教
育。而当英国皈依基督教,以及作为贵族教育基础的读本文化得以确立
之后,此种功效在许多代人的历史长河中则再也不可能实现了。这就证
明,该作品确系早期创作。
假如阿尔弗雷德大帝(King Alfred)阅读或听别人朗诵《贝奥武
甫》,那么,他准会心存些许伴有优越感的怀古之情;正如我们在面对
某个久已逝去的文明时,也难免会有相同的感受。阿尔弗雷德对于读写
和书籍的态度完全是现代意义的。在他看来,懂得阅读的人寥寥无几,这无疑是他那个时代巨大的文化耻辱;他建立学校和图书馆的目的并非
去永久保存像《贝奥武甫》这样的作品。历史、法律、哲学,以及《圣
经》方是他心仪的课程。当他打发闲暇之际,吟唱诗人会伴随其左右,而他也乐于学习他们的基本技艺,但无论他如何快乐,其国家政策注定
了口头文学的消亡。阿尔弗雷德之所以被尊称为“大帝”,主要是由于他
与古代传统决裂的勇气,而并非其保存这些传统的努力。
与盎格鲁—撒克逊口头叙事相比,像《罗兰之歌》这一极具代表性
的古法语口头叙事艺术似乎对书本更具亲和力,也更为时下的基督教文
化所接受。《罗兰之歌》的创作比《贝奥武甫》至少要晚300年之久
——约公元1100年,但我们同样觉得该作品大致描绘了催生其创作的那种贵族式、英雄体文化。中世纪传统一直认为,《罗兰之歌》的某一版
本曾被行吟诗人泰耶弗(Taillefer)拿来吟唱,以鼓励即将奔赴黑斯廷
斯战役(Battle of Hastings)的诺曼将士。这种说法与许多关于英雄体
诗歌如何在战场上发挥宣传功能的叙述不谋而合。古法语史诗传统的兴
旺极为持久——足足延续到中世纪鼎盛期,而我们通常把这个时期同传
奇,以及由传奇和普罗旺斯语(Proven?al)(51)
抒情诗所激发的文学革
命相联系;这就证实,一种合理的传统必然具备持久性和灵活性。小
S.G.尼克尔斯(S.G.Nichols,Jr.)在调查数部古法语“武功
歌”(chansons de geste)(52)
的程式模板及“论题”时得出结论:《罗兰之
歌》文本乃形成于“口头程式化的传统语汇”。
在日耳曼北部,文化融合的可能性似乎并不缺乏,但对于古法语史
诗传统来说,只有将这种融合进行得更加激进,方足以解释加斯顿·帕
里斯(53)
所谓的“罗曼语(54)
形式的日耳曼精神”(esprit gemanique dans une
forme romane)。根据查理曼的传记作家艾因哈德(55)
的说法,查理曼
(执政期768—814)与其子“虔诚者路易”一样乐衷于将拉丁文学技艺的
成果赋予自己的日耳曼臣民。在《查理曼大帝传》(Vita Caroli
Magni)中,艾因哈德记载说,查理曼将撒克逊人、弗里斯兰人及图林
根人(56)
的未成文法编撰成书面文件。更有意味的是,他还让人“把过去
那些欢庆古代君王武功勋业的陋俗之歌写出来以传后辈”。当然,最重
要的则在于他保持了一个国家的基本稳定,使莱茵河两岸分别讲日耳曼
语的法兰克人及撒克逊人和讲法语的民族团结起来,这样便促使口头史
诗传统中的主题和形式元素跨越语言壁垒,实现其从日耳曼语向罗曼语
的传播。此时,日耳曼传统一方面正成为教会的服务工具,另一方面也
正以书面形式被记录下来,留给(有望识字的)子孙后代,而罗曼语史
诗传统则成功地得以在查理曼开创的新世界中幸存和兴盛。到了11世纪,那些征服英国的北欧人正说着法语。以往日耳曼的军
事及政治组织天赋正于第四、第五代日耳曼领袖的统治下,得以在欧洲
的罗曼语地区恢复生机;这场在异国土地上复兴英雄勋业的运动同样缔
造了异邦语言对英雄体传统的复兴。就古法语史诗传统能够反映当下时
代变化这一点来说,最好的例证莫过于它对罗兰之死的处理方式。778
年,加斯科尼人(Gascon)(57)
在比利牛斯山区对查理曼后卫部队发动
进攻,但艾因哈德在其叙述中只是将此事件作为一个小插曲,安置在针
对北方撒克逊人和南方意大利人的军事行动之间。此处只有一种可能
性,即讲巴斯克语的加斯科尼人发起攻击的动机只是出于他们对独立的
向往和对法兰克人侵略自己领土的憎恶。这次战斗中的阵亡人员中除却
许多其他人员外,还包括“御膳官埃吉哈德(Eggihard)、宫伯安塞尔姆
(Anselm)和布列塔尼(Brittany)边区总督罗兰”。在这次交战之后,艾因哈德明确表示,没有任何讨伐行动能够用来对付加斯科尼人。身着
轻装作战于熟悉地形,他们乘着夜色的掩护带着从法兰克军队辎重中获
取的丰厚战利品顺利撤离,而此时那些全副武装的法兰克人还没来得及
调遣。
从8世纪到11世纪,这一故事片段的呈现,即我们现在所熟悉的样
式。巴斯克人和法兰克人变成了穆斯林和基督徒。这两支军队进行了一
场世界大战,其结果是:一个实质上的11世纪法兰西民族与一个11世纪
的战斗教会(Church Militant)(58)
在岌岌可危之中得以幸存。于是,这
种沉闷的历史叙述将其政治及社会寓意进行了大力引申,以反映第一次
十字军东征时期的欧洲现实状态——从8世纪的部族社会群向现代欧洲
过渡。与此同时,该历史叙述也在篇幅上有所收缩。这种寓意引申之所
以能够发生,原因就在于史诗传统能够多少准确反映当下社会的重要事
实与价值观念。当然,史诗的英雄观则要求对历史叙述加以收缩。在出
现于这场战役的人物中,罗兰从最次要的角色被提升为最重要的形象,而两支庞大军阵之间的全部问题则直接聚焦于他一人身上。
不过,如果没有格外的谨慎,而只是将罗兰之死的历史叙述与诗歌
描绘进行对比,则会让人误入迷途。大多数研究中世纪史诗的学者都知
道自己在调查过程中所依赖的相关实物乃是各种文本——民间故事、生
殖神话、历史纪事,以及教父神学(patristic theology)(59)
等。诚然,这些文本有一个极大的优势,即它们能确凿地证实自身的存在。但是,书面文本不可能在口头传统研究中被赋予高度的实用价值,至少不能以
平常方式对它们加以信赖。我们有必要结合文本和我们对于具体历史事
件的知识(不局限于当时的叙述)以尽量重构口头传统的属性。正是古
法语口头传统缔造了《罗兰之歌》(或牛津手稿(60)
所参照的那个版
本,类似情形在先前讨论《贝奥武甫》和《荷马史诗》时亦曾得以概
述)。如果我们按常规着手研究,即关注一个事件的历史性叙述,那么
史诗对这一事件的处理则会表现为,以明显非历史性的神话和“论题”对
其进行富于想象的歪曲和参合。另一方面,假如我们首先尽力重构口头
传统这一准确概念,那我们则会认为,历史事件不仅侵扰了传统的神话
与“论题”素材,而且还进而要求传统做出某种适应性调整,而不是反
之。贝奥武甫的原型无疑存在于盎格鲁—撒克逊史诗传统中,直到后来
他才与6世纪发生于丹麦与哥特兰(Gotland)(61)
的历史事件相联系。古
法语史诗传统中罗兰的原型也在《罗兰之歌》衍生的过程中成为历史事
件推崇的对象。
因此,在分析任何口头诗体叙事与历史的关系时,便会遇到一个实
际问题,即传统神话和“论题”在多大程度上可能已被替换为适时再现的
独特事件(如果我们能够借助考古和文学推论去重构那些事件的话)。
如果此替换是彻底的,那么,该传统则不能被称为史诗性传统,相反,它已经接近了格律化纪事。倘若没有发生任何显著的替换,那么,此传统便会演化为宗教神话或是(当“论题”被明显清空了其仪式内容或寓言
内容时)传奇。口头史诗会通过再现历史事件去替换一些传统神话
及“论题”,此外也会通过再现更为笼统的假想现实去替换其他神话
与“论题”。我们发现,那些体现出显著心理及社会类型的人物在其行为
上所依照的自然法则(natural laws)也同样适用于现实中的人。
所以,我们在分析《贝奥武甫》这样的史诗时,不能以为它们源自
民间故事和生殖神话对心理学和历史学的入侵。同样,在探讨具体诗歌
之际,我们也不可将历史学和心理学当作进犯者。真正迷恋它们的乃是
口头传统,而并非个别诗作。任何单独的口头表演或文本既为其传统语
法所造,亦为之所限,且只反映该传统所固有的无限可能性当中的一种
方案。当我们不再将纯粹神话或纯粹摹仿当作规范,那么,中世纪传统
诗体叙事当中针对确凿历史事件的影射则显得再正常不过。当然,同样
正常的是,它们的历史也不会是塔西佗(62)
、圣比德或C.V.韦奇伍德(63)
书写的那种历史。贝奥武甫身上带有谷神的痕迹不足为奇,但他却算不
上是另一个奥利西斯(Osiris)(64)。虽然我们在上文将口头史诗传统称
作综合体,但它并不是意识化的产物。当然,它也并非发端于某一纯粹
状态,而后又将自己提炼成另一种纯粹状态。唯有此综合体——而非任
何一种纯粹的形态——方可被称作是史诗性的。
古法语史诗在与克雷蒂安及其追随者创作的传奇不期而遇时衍生出
一种诗歌类型,对此,我们尚无专门的称呼。然而,我们发现16世纪大
卫·林赛(65)
的一部杰出的小作品《乡绅梅尔德伦传》(Squire Meldrum)
正是这一类型的绝佳范例。从《罗兰之歌》到《乡绅梅尔德伦传》这条
发展脉络不仅包括像巴伯(66)
的《布鲁斯本纪》(Bruce)及布莱因·哈里
(67)
的《威廉·华莱士列传》(Wallace)这样的书面英语诗歌,还包括西
班牙的《熙德之歌》(Poema de mio Cid)——这部作品直到英雄熙德1099年辞世后约一代人有余的时间方得以创作。从历史的角度看,《熙
德之歌》在叙述上极为准确,其口头风格清晰、有力,完全没有渲染之
迹。其中产阶级主人公壮举背后的动因既是出于自身社会抱负和女儿们
的利益,同样也是出于罗兰式英雄的个人荣辱观或查理曼对于统一基督
教帝国的梦想。《熙德之歌》不同于《乡绅梅尔德伦传》,因为它的故
事所关注的仍然是民族舞台上的英雄。他击溃了庞大的穆斯林军队而成
为其民众的救世主。但《熙德之歌》乃是大众之歌,这一点有别于《罗
兰之歌》,甚至更有别于《贝奥武甫》和埃达歌谣。与早期史诗相比,其受众在社会性层面上(如果不是在历史性层面上)进一步疏离了对于
丰功伟业的歌颂。《熙德之歌》赖以产生的口头传统同样是歌谣创作的
源泉。其文化取向的弱化恰恰反映了史诗传统,尤其是口头史诗传统。
《布鲁斯本纪》和《威廉·华莱士列传》尽管系具体作者的书面创作,但延续了旧式史诗传统的内核,并有所创新。对于当下读者而言,它们
的新意在于试图将新经验叙事的内容与旧虚构叙事的风格加以综合。这
一文类的作品有时被称为“纪事性诗歌”(chronicle poems),不过“格律
化传记”(metrical biographies)也是一种可行的概念。
纪事性诗歌与我们所谓的寓言式解剖(allegorical anatomy)——另
一种在某种程度上遭到忽略的文类,其代表作品包括诸如《玫瑰传奇》
(The Romance of the Rose)(68)
和《农夫皮尔斯》(Piers Plowman)(69)
等引起学界关注的长篇诗作——在中世纪方言叙事诗歌中占据相当大的
比重。以现代批评视角对这两种形式加以分析并非易事。在某些方面,它们的定位似乎介于史诗传统因解体而产生的两极之间:散文体历史与
格律化传奇,两者不难在现代意义上加以识别。斯诺里·斯特卢森(70)
与
让·德·热安维尔(71)
创作的历史著作在诸多方面堪比古典时期的历史创
作。当然,传奇也从不缺乏仰慕者。但是这两种主要文类并没有穷尽叙
事的可能性。寓言式解剖斡旋于哲学推论与传奇之间——其复杂性我们将在后面的章节加以探讨,而格律化传记和纪事性诗歌则介乎传奇与历
史之间。正是这后一条介乎传奇与历史之间的路线引领着史诗走向小
说;在所有以口头传统循此路线发展的中世纪叙事形式当中,要数冰岛
的家族萨迦(72)
(family saga)走得最远,而后才为拉丁典籍和《圣经》
所超越。
对于13世纪的冰岛来说,文化孤立显而易见,而这恰恰使得其叙事
艺术的价值几乎达到了一种不可思议的高度。它可能借鉴了爱尔兰散文
体叙事,并得益于日耳曼民族对散文风格及世俗史所与生俱来的天赋;
不过,这一传统即便确实如此,却并无相关记录得以留存下来。就家族
萨迦而言,虽然它们没有对后来的欧洲散文体小说产生实质性影响,但
形成了其自身纯粹的形式、内容及风格,并因此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独
立的研究价值。它们不属于书面萨迦传统,因为后者突出作者身份及文
学借鉴(literary borrowing)这些颇具现代意义的操作原则。家族萨迦
的风格在具体文本之间表现出明显的一致性和程式化。尽管许多评论家
在它们当中找到相似的段落以证明家族萨迦作者之间的文学借鉴关系;
但这种相似性若被看作惯常的口头传统因素则更易理解。虽然这些家族
萨迦无疑属于书面创作,虽然每一个单独的萨迦文本理应由一位作者独
自创作,但现有证据似乎并不能说明这些作者乃是依赖于书本或个体发
挥来获取其故事的主要元素。如果这些家族萨迦的创作只是任何类似现
代意义上的个体行为,那么,它们将会失去其现有的光彩。
公元1000年左右的冰岛已掌握了书写,伴随其议会将基督教确立为
国教,它至少拥有三种经过完善演化的口头传统。第一种便是口头诗歌
传统,其残余在《诗体埃达》中尚有所保存;关于此传统,我们的证据
基本来自其在形式及主题方面与其他遗留下来的异教性日耳曼叙事诗之
间的相似之处,当然,这也暗示了两者均具有明显前读写文化(pre-literate culture)的渊源。此外,埃达诗歌本身的程式和“论题”也提供了
辅助性证据。第二种口头传统是法律,即由选举出来的法律演讲人(73)
(“lawspeaker”)于三年任期内的每一年在议会背诵《法典》三分之一
的内容。第三种口头传统是历史。如果设想在斯堪的纳维亚文化当中存
在一种包罗万象的口头史诗传统——融汇世俗史、法律、神话、仪式及
民族智慧结晶等各种元素,那我们认定它应该远早于870年的“冰岛定
居”。到了12世纪和13世纪,我们则不仅能找到书面证据以说明它已经
演化为一种高度分异的文学文化,同时还能借助于推论性证据以说明其
相对古风(antiquity)的一面。换言之,在冰岛人掌握书写之前,他们
已进一步朝向实质性的现代叙事形式发展——既包括散文体,也包括诗
歌体——在这个方面,他们要早于书面《荷马史诗》产生之际的希腊
人。正是凭借其文化上的孤立性,冰岛人通过激进的革新将《圣经》到
来之前业已兴盛的日耳曼叙事传统继续发扬光大。他们做出这样一种展
示,即目不识丁的艺术家们虽极少受到读本和书写的影响,却能够创作
出世俗史和现实主义的散文体小说。由于人们通常以为,伟大的艺术散
文和世俗史在缺乏书写与具体作家身份的情况下是不可能得以发展的,所以在过去,冰岛叙事的卓越品性恰恰一直被当作最佳证据以推翻家族
萨迦系口头创作的观点。然而,伴随《荷马史诗》范式的建立,以品性
求证的论断即便尚未完全遭到颠覆,至少也难以站得住脚了。
家族萨迦或“冰岛人萨迦”(íslendinga s?gur),只是数个重要冰岛
散文类别中的一种。除它们以外,一方面是关于各位君王和主教的诸多
传记,尤其是历史,如《斯特龙戈萨迦》(Sturlunga Saga)(74)
和《天
下:挪威列王纪》——内容分别涉及发生于当时冰岛的事件,以及挪威
诸君王的生平;另一方面是所谓的“古代萨迦”(“sagas of former
times”),以散文体形式复述早先口头诗体叙事传统的主题,即英雄和
神话故事——《诗体埃达》中还保留着一些实例。《沃尔松萨迦》(75)(其故事与德国史诗《尼伯龙根之歌》几乎同时出现),以及《霍尔夫
斯·克拉卡萨迦》(76)
(类似于《贝奥武甫》)正是这类萨迦叙事。最后
需要指出的是,“古代萨迦”似乎与许多经过翻译的法国传奇(“骑士萨
迦”[riddara s?gur])通过融合而衍生出所谓“奇幻萨迦”(“lying sagas”)
这样的杂交品。“奇幻萨迦”的创作到了现代时期仍得以继续,与之并存
的还有极其丰富的民间故事传统,以及被称为“韵文”(“rhymes”)的通
俗化歌谣体叙事诗。
我们在上文姑且就13世纪冰岛的叙事文类简要做了一个专业性概
述,既说明口头史诗传统在适当的条件下如何能够产生出裂变的巨大能
量,同时也说明不同的叙事趋向如何能够快速渗透到各个独立的叙事类
别中。在冰岛,我们不仅看到了希腊模式的重复,即史诗综合体让位于
历史和传奇;而且,我们还在家族萨迦中发现了一种融合神话与摹仿的
新综合体——现实主义的虚构叙事。自埃达叙事失去其文学精英的关注
到最后一部家族萨迦得以创作的那三百年(1000—1300)间,冰岛见证
了其叙事形式的衰退和演进,而同样的发展过程在欧洲本土则耗费了两
倍以上的时间。
在《天下》(如此称呼是因为其第一部分头两个字的意思是“天
下”[“the world's circle”])的序言中,斯诺里·斯特卢森告诉我们,其作品
所依据的是历史创作的口头传统。他的主要资料包括宫廷诗人用以颂扬
所侍君主的诗歌,以及“智者阿里”(77)
几乎全凭口头传统所创作的历史作
品,另外还包括那些饱学之士所提供的信息(可能通过对话)。作为头
脑清醒的历史学家,斯诺里唯实求真。在其序言中,他就如何运用其口
头资源及判断各种变量的可靠性阐发了一套比较周全的方法。他所提到
的宫廷诗歌必定在历史创作的口头传统中扮演过复杂的角色。它不是传
统的埃达诗歌,而是在押韵和措辞方面更为复杂的作品——吟游诗歌(skaldic poetry)(78)。
正如家族萨迦那样,《天下》当中存在着大量的吟游诗,而且所联
系到的有名有姓的诗人通常在历史上都确有其人。如果将口头创作仅仅
看成是运用一套固定的口头“语法”面对受众进行的快速创作,那么在此
意义上,这些吟游诗可能还算不上是口头创作;当然,它们在创作时,或至少在传播的过程中,并未使用书面材料。这些短小、固定的诗歌文
本在以书面萨迦文本的终极形式出现之前,虽历经许多代人的岁月却仍
得以幸存而完好无损。它们常被用来体现一则故事当中的重要时刻,不
仅具有主题功能,亦可发挥结构功能。或许,在历史性散文的口头传统
当中,它们算得上是一种重要元素。
与希罗多德相比,斯诺里的思维习惯在实证性方面明显逊色于其希
腊前辈,他对历史叙事形式的看法相对而言不够缜密。他虽然唯实求
真,但其标尺却是诗性的,而非实证性的。尽管他就奥丁(Odin)(79)
的兴起所做的讲述,以及他通常对神话人物所进行的处理均表现出相当
的合理性,但他不像希罗多德那样从总体上将诗人质疑为幻视幻听的群
体,当然也缺乏希罗多德就或然性所持有的理性标准。就叙事形式而
言,斯诺里热衷于谱系模式,这种形式使他能够运用所掌握的素材去详
细描绘那些自己颇感兴趣且十分了解的统治者,如圣·奥拉夫(80)。斯诺
里的叙事绝非希腊式的——后者将经过理性检验的叙事熔铸于一种统一
的局限形式中;而斯诺里的叙事则是经过诗性的检验,以谱系叙事的松
散形式加以展现。
从某种意义上说,《斯特龙戈萨迦》(“斯特龙戈家族史”)相对于
《天下》来说代表了一种进步。由于它将数个作者创作的历史叙事松散
地组合在一起,因而在形式上缺乏足够的统一性,算不上一部独立的作
品。但是,这个故事集将其主题限定于大致发生在1120至1280年之间冰岛的历史事件,而且,作为这部作品的内核,斯特拉·索尔达森(81)
的
《冰岛人萨迦》(íslendinga Saga)以完全令人信服的口吻讲述了政治
动荡及斗争时期那些伟大人物及虚构人物的生平。若与修昔底德相比,《斯特龙戈萨迦》可能只是将轶事和密集堆砌的细节拼凑在一起罢了;
但冰岛人在其世俗史当中对希腊历史学家的神话元素进行了剥离,使之
更为强烈地产生一种准确(但未必总是艺术化)叙述的印象。在《斯特
龙戈萨迦》,以及有关冰岛法律的书面记录中,我们发现原始日耳曼理
性主义被推向了极致。法律只是作为一种粗劣替代品以取代希腊历史学
家们所操守的、经过充分演化的理性思想传统。从异教性的日耳曼文化
中,根本没有衍生出任何类似于希腊哲学推论的东西。也许正是出于这
个原因,将神话从历史叙事中加以清除变得更为紧迫。如果说冰岛的历
史学方法总是趋向于传统而非趋向于推论性思想,那么这一传统则要归
功于那些讲求实际的律师们所进行的实用主义改良。法律演讲人和历史
学家绝大多数时候是由同一个人扮演的。
家族萨迦利用了历史学典型的谱系构架,但其聚焦范围则往往要狭
小得多。比如,在《尼雅尔萨迦》(Njáls Saga)(82)
中,故事仅限于三
代人,而重点则放在古恩纳尔和尼雅尔那一代人身上。正如《斯特龙戈
萨迦》中所出现的一些个人历史那样,《尼雅尔萨迦》的叙事表达也是
直接取材于源自冰岛生活的母题;事实上,这也是个完美的母题,它使
得家族世仇这一谱系化叙事模式表现出整体感与具体性。民法在冰岛的
兴盛虽然牺牲(或代替)了其他领域的公共生活,但它本身却不可避免
地将一种近乎人为的秩序施加于冰岛人的生活之上,从而为萨迦创作者
们提供了现成的叙事表现素材,并自然产生出一种贴近历史及当代现实
生活的独特叙事类别。萨迦在一位大师手中所能展现的那种力量与洞
察,乃是传奇作家们无以企及的。尼雅尔本人作为法律人士恰恰陷入了
一场无视法律的家族斗争之中。在他身上,我们看到了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冲突,它作为一个特点体现了虚构与经验这两种趋向的融合;而由此
所获得的问题化品性则使得这类叙事作品,一方面迥异于传奇——因为
传奇中的叙事及其诗性的正义更易于把握,另一方面又与历史的必然性
大相径庭。
在家族萨迦获得其书面创作的那段时期,《诗体埃达》当中所保留
的口头诗体叙事传统究竟有多重要?这个问题似乎不可能有答案。无
疑,萨迦的人物与事件在某种程度上(或许要超过人们通常所认为的比
例)来自埃达叙事的传统“论题”。哈尔盖德(Hallgerd)(83)
是《尼雅尔
萨迦》中少数几个非历史性人物之一,她与埃达诗《西格尔德短歌》中所出现的布伦希尔德(Brynhildr)(84)
相映成趣。另外,在《格雷蒂尔萨迦》(Grettis Saga)(85)
中有一场历
险,当时格雷蒂尔跳入潭中去挑战魔兽,这一幕与《贝奥武甫》里的一
个片段惊人的相似。甚至在《尼雅尔萨迦》中,古恩纳尔这一人物的意
义也多少来自早先史诗对该形象的构想。他所遭遇的世仇不仅吞噬了自
己,也吞噬了尼雅尔家族。这不只是例证了一个风雨飘摇的现实,以及
与之形成对照的法治理性观念,而是展示了主人公的神话理想与法治理
性观念之间的冲突;这种冲突在历史上的确使得斯特龙戈时代呈现出一
片天下大乱的局面,当然,也正是在这一时期,萨迦的创作出现了。从
某种意义上说,家族萨迦就是散文化的史诗,它一方面对神话及寓言性
元素进行大幅度缩减,另一方面又大力强化历史与摹仿的重要性。不
过,由于这种抑制神话、强化摹仿的倾向表现得近乎彻底,所以它们有
时似乎更像小说,而不是史诗。
冰岛叙事艺术的真正奇迹在于历史,没有它,家族萨迦可能无从产
生。它完全基于事实,充满谱系性的枝节,而且(如《斯特龙戈萨迦》
所示)在描绘具体人物时也是直言不讳。关于家族萨迦,一种最简化的理解就是:它将历史和法律这一层面与传统史诗这一层面加以融合,而
史诗的“论题”及神话又几乎总是让位于代表理性及世俗现实的主题、情
节及母题。史诗自身几乎无法抵御历史和基督教的双重侵袭,而只得以
诗歌的身份被更具“诗性的”吟游诗所取代。那种将埃达短歌看作叙事演
化之“前史诗阶段”的理论似乎毫无根据,因为这些经过高度凝缩的英雄
体叙事典范所反映出来的恰恰是背离史诗这一整体文化运动,而不是走
向史诗。在更为早先的时期,埃达传统无疑曾经是经验性叙事与虚构性
叙事之间的中间路线,而到了12世纪,史诗已经难以为继。其神话的力
量因基督教而元气大伤,同时,其情节的有效性也受到历史和法律的挑
战。
假如没有城市文明,没有哲学思辨的传统,也没有“生活切
片”(slice-of-life)式的讽刺传统,那么小说在理论上是不可能产生的。
然而,冰岛的家族萨迦倒是代表着一种由旧式史诗与新的经验性形式组
合而成的二次综合体(re-synthesis),它与三百年后欧洲其他地区所出
现的这种二次综合体至少在某些方面表现出相似性。继斯特龙戈时代之
后的数个世纪中,随着欧洲中世纪逐渐向冰岛逼近,旧式史诗叙事的纯
虚构趋向虽然依旧可以通过诸多思想虚空的“古代萨迦”“骑士萨
迦”及“奇幻萨迦”得以彰显,但它的经验性趋向却已消耗于那些伟大的
历史作品与家族萨迦之中,以至于在那些充满恐惧的黑暗世纪中,再也
无法创造出不朽的丰碑之作。
萨迦 ? ?
这个表述从“segja”(冰岛语意为“讲述”)这个字派生而来,在
冰岛语当中现用以指任何散文体叙事,无论篇幅长短,也无论是口头还
是书面。当冰岛人着手将许多代人作为口头叙事存在的传统故事书写下
来的时候,他们显然不仅用萨迦 ? ?
这个词代指故事,而且也用它来代指对
故事的书面记录。那些用以区分历史(萨迦 ? ?)、家族萨迦(冰岛人萨 ? ? ? ?迦 ?)、英雄体萨迦(古代萨迦 ? ? ? ?)、传奇(骑士萨迦 ? ? ? ?),以及美妙历险
(奇幻萨迦 ? ? ? ?)的术语都是现代意义上的。尽管这样的区分对于专家而言
既具有逻辑性也不乏必要性,但对于一般的文学研究者来说,“萨迦”这
个词最好能比它在现今冰岛语中的使用多一分意义上的限制。在大众化
的美国用法中,这是一个能够增色的字眼。那些对史诗感到腻味儿的读
者虽然不再因“史诗”而感到精神振奋,但如果《伊利亚特》这首诗被描
述为一部惊心动魄的特洛伊战争“萨迦”,他们却可能会趋之若鹜;而那
些用于电影剧本的“萨迦”和“史诗”,实际上更准确的提法应该叫作英雄
体传奇。如果没有其他具体修饰语的限制,“萨迦”这个词在文学批评中
的正确用法应该是代指冰岛的家族萨迦,以及其他类似的、达到小说篇
幅的现实主义传统散文体叙事。这里的关键词是“传统”,否则萨迦便无
法与小说区分开来。所谓“传统”,就是指带有口头创作之形式特征及修
辞特征的叙事。
口头创作的形式特征在上文已经有所描述。其中最重要的就包
括“程式化”语汇;也就是说,传统“语法”操控着口头创作的语言,它通
过对总体文化语言加以筛选以提取为数不多的模式,并借此形成符合格
律(指诗歌这种情形)、句法和语义的恰当表达。口头叙事艺术家一旦
掌握了这种“语法”,便能够面对观众进行口头创作。按照人类的普遍经
验,散文句式的口头创作要难于完全格律化诗歌的口头创作。一些批评
家认为,散文之所以无法发展成为口头创作,是因为人们很难驾驭散文
句式的逻辑和句法节奏。对于那些目不识丁的人来说,这就意味着诗歌
仅限于其美学功效,而诺斯洛普·弗莱所谓常规语言的“联想节
奏”(associative rhythm)(86)
也就只剩下其非美学用途。然而事实正相
反,只要详细分析家族萨迦当中著名的“萨迦风格”,我们便会发现冰岛
口头叙事散文当中实际上存在着一种“语法”描述。这种“语法”的存在正
是中世纪冰岛口头散文成就的主要基础。可以说,散文的口头创作必然是高度程式化的。
口头叙事的另一特点是母题与情节在主题意义上的一致性。此类意
义之所以成为可能,乃得益于传统“论题”和神话,而这些传统叙事元素
又同时掌控着故事对现实的再现及其对观念的阐释。为了探究一种叙事
语汇的程式化特征或其结构与主题的传统属性,批评家们所调查的叙事
体必须具有足够大的规模,以体现各种规范并至少能代表“传统”的一块
残片。幸运的是,我们拥有富足的荷马语料库。盎格鲁—撒克逊传统在
语料库方面则显得捉襟见肘,而对于埃达传统而言则可能是杯水车薪。
然而,口头创作的叙事除了其纯粹“形式化”的特点外,还在“修辞”——
姑且从狭义上这么称呼——层面上与个体叙事艺术家们的作品有所区
别。从这一方面来说,许多传统叙事即便没有同更多的文本进行比对,至少可被暂视为传统之作。
口头叙事总是采用一位权威性的可靠叙述者。他就像荷马及《旧
约》作者那样富于天赋,能够从所有角度对行动进行观察,道出人物心
中的秘密。我们习惯于将这位全知叙述者等同于作者,并以为该作者无
处不在地为我们阐释和评价其叙事中的人物与事件。不仅如此,我们还
习惯于认为这位可靠的、全知的,且无处不在的叙述者是“客观的”。我
们这样说的意思是,此类叙述者再次与荷马及《旧约》叙事的作者们表
现出相似性,他所谈论的并非是自己而是其故事当中的人物与行动。同
样,他也不会为了营造自己与其受众之间的亲密关系而牺牲他们对于故
事本身的认同。当亚里士多德赞扬荷马善于身栖他人性格之际,其所表
之意显然是指:荷马既非谈论自己,亦非将自己游离于故事的利害关系
之外。当然,如果从另一个意义上将“客观”理解为采用一种类似于中立
人物的视角去观察纯粹外部性的事件,那么,全知性叙述者还远算不上
是“客观”的。而他之所以被视为客观则既是因为他并非“主观”,也是因为在其本人与作者之间或在其自身的关注与故事所隐含的关注之间并不
存在反讽性的差异。在下文讨论叙述视角的一个章节中,我们将注意到
荷马对缪斯女神的召唤乃是朝向作者自省意识的发展。如果说,常规标
准将传统口头叙事看作是由一位“客观”的权威叙述者所进行的讲述,那
么,召唤缪斯这一高度模式化的手法则作为一种例外稍稍改变了这一标
准。
由于传统故事的作者与讲述者之间不存在反讽式差距,因此,我们
习惯上不对他们进行区分。受众分享叙述者的知识与价值观,在对故事
的人物及事件做出评判时总是依赖于后者。受众如叙述者一样具有料事
如神的洞察力,这就解释了传统叙事中仅有的虚构性反讽:叙述者和受
众均了解故事中的人物,而他们却不可能认识彼此,甚或是认识自己。
随着自省式讲述者在非传统书面叙事中的发展,这样的反讽情景不断增
加。在小说中,叙述者对人物的看法和人物对自身及其他人物的看法总
是存在着差异,而这种差异性又因为叙述者与读者对故事的不同看法而
得以增强。因此,在任何书面叙事中,作者与其叙述者之间通常会在认
识及价值观层面上表现出实际的——或至少是潜在的——反讽性差异。
传统口头叙事从修辞上看包括一位讲述者、其故事,以及一位隐含受众
(implied audience)。而非传统书面叙事在修辞层面上则包括摹仿 ? ?
或再 ?
现 ?
性的讲述者、故事及隐含读者。
从修辞意义上说,书写的运用使得创造性的个体叙事艺术家能够将
其故事的复杂性及潜在的反讽性推向一个更高的水平。这一新水平的实
现似乎源于自省式叙述者的引入,以及叙述者一方与作者及读者另一方
之间的反讽性差距。然而,借助于我们对口头叙事的讨论,可以发现,真正将空前的复杂性赋予书面叙事视角的因素并非叙述者的引入,而是
作者 ? ?
的引入。令人尴尬的是,在讨论口头叙事的整个过程中,我们不得不使用“现代意义上的作者”这种表述。我们已经指出,《荷马史诗》、《旧约》、《贝奥武甫》、《罗兰之歌》、家族萨迦、《卡勒瓦拉》
(Kalevala)(87)
、法罗语歌谣,以及其他口头叙事并非由“现代意义上
的作者”所创作。就通常用以吟唱的叙事诗而言,我们会提及“故事的吟
唱者”。就口头创作的散文体叙事而言,我们会谈到“故事的讲述者”。
不过在这两种情形下,他都算不上是一位作者:他乃是作为一种工具,借助表演这种具象化的形式来体现传统。他是叙述者。用斯蒂芬·迪达
勒斯(Stephen Dedalus)在《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中的话说,他将
其故事置于“同自己及他人的斡旋关系之中”。
无论斯蒂芬对抒情性、史诗性和戏剧性的著名定义代表了何种批评
意义或神秘意义,它们的确说明了一种现代趋向,即把作者从叙事中撤
回。像荷马或莎士比亚那样的作家往往拥有一种显著的本领——他们能
够表现得“像创世纪里的上帝……身处其创造物之中或背后或之外或之
上,踪影不见,形骸不存,似有修剪指甲时的那份淡然之态”(88)。为
此,浪漫主义批评家们曾有溢美之词,认为此乃“同情化想
象”(sympathetic imagination)作为重要诗歌技法所能企及的最高境
界。乔伊斯本人在解决如何让作者淡出的问题时,其方法在某种意义上
说可谓是戏剧化的。他试图将叙述者与叙事加以融合,这样一来,他对
于三种重要修辞元素——讲述者、故事及隐含读者——之间互动关系的
摹仿就如同一部戏剧对于剧作家的关系一样。但是,无论乔伊斯如何精
巧地设置其叙述者与故事及读者之间的关系,他的叙事依然是对叙述者
讲述故事这一过程的摹仿。如果我们让自己稍稍走进斯蒂芬那神秘的美
学世界中,我们也许可以将乔伊斯的技法描述为对“史诗化”形式的一
种“戏剧化”再现。
口头叙事与书面叙事之间的修辞性差异曾由诺斯洛普·弗莱做过部分研究。虽然大量以诗体及散文体出现的传统叙事均系口头创作,但对
于相关的研究成果,弗莱并不了解,或至少未曾加以运用。因此,在区
分史诗 ? ?
([epos]按我们的提法叫作口头叙事)和虚构(书面叙事)时,他所提到的两种“叙事呈现的根基”(radicals of presentation)并未获得
其真正的意义。按照弗莱的定义,史诗“这种文学类别进行叙事呈现的
根基是作为口诵人的作者或行吟诗人,而观众则是其所面对的聆听
者”。虚构 ? ?
对于弗莱而言乃是“以印刷或书面文字为呈现根基的文学,如
小说和随笔”。这一区分尽管在实践上难以奏效,但却不乏真知灼见。
某些口头叙事的确背离了在观众面前进行表演这一事实,然而,我们不
要忘记这第二个事实,即它们之所以诉诸印刷页面的形式乃是为了呈现
于我们 ? ?;所以,从此意义上说,这种背离本身倒未必会破坏弗莱那种鉴
别方法的有效性。不过,从另一方面看,许多极富创意的非传统性书面
叙事在以印刷页面的形式呈现给我们的时候,倒仿佛是在面对观众进行
口头表演。作为现代例证,我们可以想起康拉德(Conrad)笔下那些以
马洛(Marlow)为叙述者的小说。
叙事呈现的根基如今正日趋转向印刷,这乃是情理之中的事。在大
多数情形下,那些未曾由作者书写下来的叙事会有别于其他由作者加以
书面创作的叙事,因为前者无法创造出一个叙述者以区别于某个地位更
高的创造者。中世纪传奇作为一种叙事文类在修辞上称得上是弗莱所定
义的史诗,但却不符合我们所定义的“传统口头叙事”。最伟大的中世纪
传奇并非口头创作,当然,它们也曾非常依赖于传统元素,有的甚至直
接取材于口头传统或口头叙事的手稿本。那些与克雷蒂安·德·特罗亚、沃弗兰·冯·埃森巴赫及哥特弗里德·冯·斯特拉斯堡(89)
等姓名相联系的传
奇或许应该归功于那些作家个人的创造性天赋。像“骑士的故
事”(Knight's Tale)(90)
和《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这样的作品则完全
是在现代意义上进行的书面创作。不过,在中世纪的传奇中,我们经常会遇到像乔叟或沃弗兰笔下的那种叙述者,他们的作用被描绘成向读者
讲故事。沃弗兰的叙述者甚至向读者承认自己目不识丁,并因此增加了
自己与作者之间的距离。当中世纪的叙事艺术家们突然获得这种新的作
家身份时,他们发现自己尚缺乏准备,进而显得有些手足无措。就像所
有作家一样,他们试图“让自己淡出文本”。为此,最自然的途径便是在
相当程度上直接摹仿讲述者面对听众传诵其故事。不过,即便是这样的
应急措施还是打开了潘多拉的反讽之盒,让诸如乔叟、沃弗兰,以及
(文艺复兴时期的)拉伯雷和塞万提斯这样的大师去占领新的阵地。
如果抛开斯蒂芬的观念而仅借用其表述,那么我们可以说,口头故
事的讲述者“斡旋”于故事与受众之间。这里既不存在用以构成反讽关系
的作者,而且(这就等于同义反复)也不存在用以形成反讽关系的故事
本身。口头传统既是故事,也是作者。如果表演者以故事为代价去博得
受众的亲和,那就等于以作者自居,如此一来,他对传统的运用也不过
是为了推进其个人所构想的目标。讽刺,若要存在于口头传统,则必须
植入该传统本身当中去。它不会作为功能化的反讽性差距存在于“作
者”与其创造的叙述者之间,或存在于叙述者的关注与其故事的关注之
间。
当口头传统遭受书面文学这一主导力量的冲击而遁入“地下”时,它
会自然反映出那些维系其兴盛的参与者们在知识、审美及社会等诸方面
的经验。在现代时期,口头传统的处境如此艰难,歌谣和民间传说占据
了最佳口头文类的地位。令人遗憾的是,对于《贝奥武甫》和《诗体埃
达》的口头创作论,反对者们却常常从歌谣与民间传说当中寻找评判的
依据。曾有人断言,《贝奥武甫》并非纯粹意义上的歌谣,因而必定是
出自一位个体创作者之手。我们在讨论长篇叙事形式的时候,并未试图
将歌谣或民间传说视为书面文学的口头传统因素;因为它们是书面叙事的竞争对象而不是影响势力,这种情况至少持续到浪漫主义运动。
口头叙事的形式特点在歌谣及民间传说中多少都会发生一些变化。
对这些文类产生深刻影响的因素不仅包括书面文学理念,也包括固定文
本概念,即个体叙事实际上并非伴随每一次表演而重新进行创作。这些
文本无疑源自真正的口头传统,而且确切地说,它们也并非某一原始版
本的“变体”。不过,即便是最低程度地诉诸书写,它们所获得的固定性
(fixity)也会超越真正口头创作的程式化语汇。
然而,“同情化想象”不止在口头叙事中促使作者及修辞性反讽淡出
文本,同样也在掌控着歌谣的吟唱与民间传说的讲述。但是,我们所处
的文学世界却受制于另一种截然不同的反讽势力:一方面是保守派学者
力求为《贝奥武甫》留住作者,另一方面却是先锋派叙事艺术家们在摹
仿民间传说的讲述和歌谣的吟唱,对他们而言,让作者淡出文本是其孜
孜以求的完美境界。
(1) 柏拉图文艺对话录之一,通过苏格拉底的弟子斐德若的回忆转述了苏格拉底临刑前与朋
友、弟子及其追随者之间的对话。
(2) 米诺斯B类线性文字:古希腊克里特(Crete)文明时期,即米诺斯时期(Minoan
Period),公元前3000—公元前1100)的一种书写文字系统,出现于希腊字母的发明之前。
(3) 阿波罗尼奥斯(Apollonius Rhodius,生卒不详):又称“罗德人阿波罗尼奥
斯”(Apollonius of Rhodes),约公元前3世纪的亚历山大诗人,常在史诗中注入心理描述及传
奇特征,突出叙述者的权威性。
(4) 南斯拉夫常用于伴奏叙事歌曲的一弦小提琴。
(5) 《诗体埃达》:又称《老埃达》(The Elder Edda),关于北欧传说及神话的诗,由冰
岛历史学家塞蒙恩德(1056—1133)收集整理,故又称《塞蒙恩德的埃达》。
(6) 基涅武甫:兴起于公元9世纪的盎格鲁—撒克逊诗人。
(7) 如尼文:约公元200至1200年,北欧及不列颠等地区使用的书面文字系统。
(8) 《诗体埃达》中的第一首,也是最著名的一首,讲述了世界的创造及末日的降临;诗题原意为女祭司的预言。
(9) 爱奥尼语:古希腊的一种方言,早期希腊诗歌的创作语言。
(10) 阿卡狄亚—塞浦路斯语:伯罗奔尼撒半岛中部的阿卡狄亚及塞浦路斯岛使用的一种古
希腊方言。
(11) 阿提卡语:古代希腊阿提卡(Attica)地区的方言,约公元前5世纪至公元前4世纪成为
古典希腊文学的标准语言。
(12) 麦西亚:英国中世纪早期七国时代的国家之一,位于今英格兰中部。
(13) 半行诗程式:古代盎格鲁—撒克逊口头诗歌的特点之一,即一句分为两个半句。
(14) 哈弗洛克(Eric A.Havelock,1903—1988):英国古典学家,曾从教于哈佛和耶鲁等
北美高校,是著名的古希腊文化、历史研究专家。
(15) 恩斯特·罗伯特·库提乌斯(Ernst Robert Curtius,1886—1956):德国文学评论家及语
言学家。
(16) 此处的原文locus amoenus系拉丁文,意为快乐的地方。
(17) 此处的原文puer senex系拉丁文,意为年轻长者。
(18) 下降阴府:基督教神学中的概念,出现于《使徒信经》(Apostles'Creed)和《亚大纳
西信经》(Athanasian Creed)的信规当中,指耶稣殉难后降临阴间拯救正义之士的灵魂,使之
脱离罪恶与死亡的枷锁。从此意义上说,耶稣乃是战胜了地狱的黑暗。所以,耶稣“下降阴
府”不仅表述为“descended to the dead”,也在不少场合说成“the harrowing of hell”(字面义为“入
侵地狱”),原著在此处采用了后者。
(19) 伊萨卡(Ithaca):希腊西海岸的小岛,相传为奥德修斯的故乡。
(20) 墨兰提俄斯:《奥德赛》中的羊倌,羞辱以乞丐形象假扮的奥德修斯。
(21) 欧迈俄斯:《奥德赛》中的猪倌,奥德修斯的忠实追随者,当假扮乞丐的奥德修斯发
誓说奥德修斯必将归来时,欧迈俄斯指责其为骗取钱财而故意说谎。
(22) 安提诺俄斯、欧律马科斯及克忒西波斯:均为奥德修斯妻子的求婚者。
(23) 忒勒玛科斯:奥德修斯之子。
(24) 伊洛斯:《奥德赛》中的乞丐,与奥德修斯争夺乞讨地盘并为此进行决斗。
(25) 欧律克勒亚:奥德修斯的老仆人,她从前者腿上的伤疤认出其真实身份。
(26) “神话”这个词源自希腊文中的“mythos”,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常表示类似“情节”的概念。
(27) 西嘉:罗马帝国时期的非洲古城,在今天突尼斯境内。
(28) 优提齐乌斯·普罗克洛斯(Eutychius Proclus):公元2世纪语言学家,曾担任罗马帝国
皇帝马可·奥勒留(Marcus Aurelius)的老师。
(29) 弗提乌斯(Photius,生卒不详):公元9世纪君士坦丁堡大主教兼著名学者。(30) 卡累利阿:位于俄罗斯西北部、与芬兰接壤的地区,今有俄罗斯境内的卡累利阿自治
共和国,以及芬兰境内的北卡累利阿和南卡累利阿地区。
(31) 诺森比亚:中世纪不列颠的小王国。
(32) 圣比德(the Venerable Bede,约672—735):亦称比德,英国宗教史上著名的修士、学者及神学家,有“英国历史之父”的美誉。
(33) 凯德蒙(C?dmon,生卒不详):公元7世纪英国基督教诗人。相传其原为放牧者,后
于睡梦中偶然学会作诗,凡《圣经》中的段落,经他之手都能转化为美妙的宗教诗篇。
(34) 小F.P.马古恩(F.P.Magoun,Jr.,1895—1979):美国文学批评家,中世纪英语文
学研究专家。
(35) 希尔达(Hild of Whitby,约614—680):英国基督教女教士,曾创建著名的惠特比修
道院,死后被尊为圣徒。
(36) 马提亚·弗拉齐乌斯(Matthias Flacius,1520—1575):今南斯拉夫北部信义宗(即路
德教)神学家、新约圣经学家。
(37) 他提安(Tatian,约120—180):叙利亚基督徒,以叙利亚文写成《四部福音合参》
(Diatessaron,约160年),将四部福音的重要内容编为一整体性的故事,后被译为希腊文流
传,如今仅有一小部分存留下來。
(38) 拉巴努斯(Hrabanus Maurus,776—856):德国神学家、圣经诠释学家兼诗人。
(39) 古高地德语(Old High German):现代德语的原型,出现于5至11世纪中期。
(40) 《希尔德布兰特之歌》:现今仅存的一首用古德语写成的日耳曼英雄诗歌,讲述武士
希尔德布兰特与儿子疆场对决的故事。
(41) 《瓦尔迪尔》:古英语史诗,现只剩残卷,讲述英雄瓦尔迪尔与恋人逃离匈奴王的囚
禁、盗取宫廷财宝并对追缉者进行英勇反击的故事。
(42) 《戴欧》:古英语史诗,讲述诗人戴欧受贬之后,以自白的形式将自己的流亡生涯与
日耳曼神话及盎格鲁—撒克逊民间传说人物的相似经历进行类比。
(43) 《威德西斯》:古英语史诗,行吟诗人威德西斯(意为“远行”)自述其游历各地,并
介绍古代及当代著名君主和神话、传奇英雄。
(44) 《费恩堡之战》:古英语史诗,讲述丹麦王子赫纳甫(Hn?f)与其妹夫费恩(Finn)
之间的战斗。这个故事也作为一个片段穿插在《贝奥武甫》当中。
(45) 法罗群岛:今丹麦自治省,位于苏格兰与冰岛之间,其口传法罗语歌谣源自古代北欧
文明。
(46) 弗里斯兰人:古代位于现今荷兰及德国境内靠近北海南部的民族,属于日耳曼人的一
支。
(47) 希索巴特人:《贝奥武甫》当中与丹麦人进行战争的族裔,其名意为“战争须髯”(war-beards)。
(48) 《流浪者》:古英语诗歌,讲述一位年轻人在战争中失去战友与亲人,沦为流浪者的
辛酸历程。
(49) 耶阿特人:北欧日耳曼人的一支,活动于今瑞典南部,一说属于哥特族。
(50) 牡鹿厅:《贝奥武甫》中丹麦国王的宫殿。在这里,贝奥武甫保卫王室免遭食人怪戈
兰德尔的袭击,将之击败,并砍断其胳膊。
(51) 普罗旺斯语:中世纪法国南部奥克语(langue d'oc)的一种方言,通用于普罗旺斯;普
罗旺斯文学则起源于11、12世纪的行吟诗人,后带来整个中世纪欧洲方言文学的兴起。
(52) 11至14世纪流行于法国的一种长篇故事诗,以颂扬封建统治阶级的武功勋业为主要题
材,故称“武功歌”。
(53) 加斯顿·帕里斯(Gaston Paris,1839—1903):法国作家、学者,以研究中世纪法国文
学及传奇文学著称。
(54) 罗曼语:印欧语系的一支,起源于“通俗拉丁语”(Vulgar Latin),中世纪欧洲传奇文
学的创作语言,法语亦属于罗曼语族。
(55) 艾因哈德(Einhard,770-840),查理曼大帝的侍从秘书,法兰克王国史学家,“卡洛
林文艺复兴”的代表人物之一,曾为查理曼大帝立传。
(56) 图林根人:日耳曼人的一支,活动在位于德国中部的图林根,该地区于公元6世纪为法
兰克人所征服。
(57) 加斯科尼人:法国西南部比利牛斯地区(旧称加斯科尼省)的巴斯克语民族。
(58) 战斗教会:神学中指那些同邪恶及耶稣的敌人进行斗争的基督徒。
(59) 教父神学:基督教早期由所谓“教父”(Church Fathers)从事的神学研究。
(60) 《罗兰之歌》的版本众多,其中最古老的版本是12世纪的牛津手稿。
(61) 哥特兰:位于今瑞典南部,相传为贝奥武甫的故乡。
(62) 塔西佗(Tacitus,约55—120):古罗马杰出的历史学家。
(63) C.V.韦奇伍德(C.V.Wedgwood,1910—1997):英国历史学家及传记作家。
(64) 奥利西斯:埃及神话中的冥界之神及丰饶之神。
(65) 大卫·林赛(David Lindsay,约1486—1555):文艺复兴时期苏格兰诗人,其诗作《乡
绅梅尔德伦传》以历史人物梅尔德伦的功勋为基础,将中世纪晚期的传奇、纪事和讽刺融为一
体。
(66) 巴伯(John Barbour,约1320—1395):苏格兰诗人,著有诗篇《布鲁斯本纪》,讲述
苏格兰国王布鲁斯的丰功伟业。
(67) 布莱因·哈里(Blind Harry,约1440—1492):苏格兰诗人,所著诗体纪事《威廉·华莱士列传》,讲述苏格兰民族英雄威廉·华莱士抵抗英格兰入侵的功绩。
(68) 《玫瑰传奇》:13世纪法国寓言长诗,典雅情爱(courtly love)文学的典范之作,以
玫瑰作为贵族女性的象征,向世人宣讲情爱之道。前半部分由基洛姆·德·洛利思(Guillaume de
Lorris)所作,后半部分由让·德·梅恩(Jean de Meun)完成。
(69) 《农夫皮尔斯》:14世纪以中古英语创作的寓言体叙事诗歌,以数个梦境影射英国社
会现实与宗教。
(70) 斯诺里·斯特卢森(Snorri Sturluson,1179—1241):冰岛历史学家、诗人及法律演讲
人(lawspeaker),著有《散文埃达》(Prose Edda)及《天下或挪威列王纪》(Heimskringla
or the Lives of the Norse Kings)。
(71) 让·德·热安维尔(Jean de Joinville,1225—1317):中世纪法国著名编年史家。
(72) 萨迦:中世纪冰岛及挪威等北欧民族的口头叙事,原意为故事、传奇或历史;家族萨
迦是其中的一类。
(73) 法律演讲人:斯堪的纳维亚诸国(如瑞典、冰岛和挪威)的政府职位,起源于日耳曼
口头传统,但只在北欧演化为独特的政府职能。
(74) 《斯特龙戈萨迦》:古代冰岛萨迦,讲述颇具名望的斯特龙戈家族(the Sturlungs)的
历史。
(75) 《伏尔松萨迦》(V?lsunga Saga):古代冰岛萨迦,讲述伏尔松家族围绕宝藏、权力
与情爱等主题经历的兴与衰。
(76) 《霍尔夫斯·克拉卡萨迦》(Hrólfs Saga kraka):古代冰岛萨迦,讲述传说中的丹麦国
王霍尔夫斯·克拉卡及其族人的历险。
(77) “智者阿里”(Ari the Wise,1067—1148):冰岛杰出的编年史家,第一位用古斯堪的
纳维亚语创作历史的学者。
(78) 吟游诗歌:与埃达诗歌齐名的另一种古代斯堪的纳维亚诗歌形式,其主题多歌颂君王
的丰功伟业。
(79) 奥丁:古代北欧神话中的一位主神,掌管战争、死亡、智慧、诗歌等。
(80) 圣·奥拉夫(St.Olaf,995—1030):中世纪的一位挪威国王。
(81) 斯特拉·索尔达森(Sturla Thórdarson,1214—1284):冰岛政治家、萨迦作家及历史学
家。
(82) 《尼雅尔萨迦》:13世纪最著名的“冰岛人萨迦”之一,讲述了几个家族之间的世仇,以及争端的解决。当中包括武功盖世的古恩纳尔(Gunnar)和足智多谋的尼雅尔(Njal)。
(83) 哈尔盖德:《尼雅尔萨迦》中古恩纳尔的妻子,生性跋扈、喜好争斗。
(84) 布伦希尔德:古代北欧神话中的女勇士,英雄西格尔德的追随者,但因为一场爱情阴
谋而嫁给了古恩纳尔,后为此对西格尔德实施报复并将其杀死,但在后者的火葬现场,跳入柴堆自焚殉葬。
(85) 《格雷蒂尔萨迦》:“冰岛人萨迦”之一,讲述古代冰岛绿林好汉格雷蒂尔充满传奇色
彩的一生。
(86) “联想节奏”指的是那种深受韵律诗影响的常规语言节奏,它有助于实现自由诗及散文
语言当中的意义被唤起。
(87) 《卡勒瓦拉》:芬兰民族神话史诗,根据芬兰及卡累利阿民间故事编撰于19世纪,标
题意为“卡勒瓦(Kaleva)的领地”。
(88) 这段引文出自乔伊斯的小说《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主人公斯蒂芬 ......
您现在查看是摘要介绍页, 详见PDF附件(3524KB,50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