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人心底印绿色
那一年,春天来得早。德国的春天柔和,没有北京的风沙,到处风和日丽,令人春心萌动,欲有所吃。
有位在柏林工大进修的罗女士来访。罗女士是南方人,在与我太太闲聊时,忽然说起:“你家楼外的草地上,有好多荠菜耶。”
两人当下跑了出去,挖了一大抱草回来。
我看那草,是一种塌地的植物,绿色的叶子,羽状的叶片,带了分叉,有点儿像是荠菜。但心里不敢确定,就说:“荠菜不是长在中国的吗,洋人这儿会有野生的?”
罗女士态度很坚决,说:“我觉得它就是荠菜。我们小时候去野地常挖的。”
我说:“那这儿怎么没人采、没人吃呢?好像根本没人认得这东西似的。”
罗女士撇撇嘴,说:“洋人根本就不懂吃。”
, 百拇医药
几个人争议很久,终是口馋,决定不管三七二十一,学神农不要命,尝了再说。
大家认真动起手来,把那菜掐根洗净剁碎拌馅儿,和面压皮儿包馄饨。罗女士是个烹调老手,说,荠菜吃油才香。我拿了油瓶,倒了半瓶油到菜馅里,用筷子去搅,那油竟一下子消失得了无踪影。心中不由得大喜,素菜能这等吃油,其味必佳!
馄饨煮好盛到大碗里,大家都伸了头去看。清汤里面,馄饨一个个大馅宽边儿。包着馅儿的皮皱缩成一朵,透出玉绿色,甚是可爱。夹起一个馄饨来,咬下去满口的鲜香,真好吃。果然是上品荠菜!
太太后来走路只看地面。最后有了心得,说是发现以柏林工大学生宿舍C楼前一片草地上的荠菜最为肥大。她找了空闲时间,拿了小篮去挖。回来后又精心将荠菜洗净,装食品袋,放冰箱,打电话通知各处朋友。如此兴奋忙碌,并不觉劳苦。
有一天,我请大学里的一对德国夫妇来吃这荠菜馄饨。他们齐声大赞菜馅的清香鲜美,说是从未吃过,每人吃了两大碗,兀自不肯罢手,都问馅是什么菜做的。
, 百拇医药
我答:“一种可吃的蔬菜。”
又问在哪儿买的,中国商店吗?
我笑答:“路边挖来的。”
他们都大惊失色,把我吓了一跳。我忽然意识到问题严重。洋人只懂得吃的东西要从店里买,敢对路旁脚边的东西下手,还把它们煮到锅里,做菜下饭,拿来宴宾待客,这行为是有毛病的。
他们跑进厨房,拿了荠菜仔细端详,还央求我们一起去了趟实地现场。隔几天,这对吃了荠菜的德国夫妇背了个大背包,兴冲冲地专门跑来找我。他们从背包里费劲地往外掏东西。我一看,都是些厚本大书,有德英百科、拉丁文辞典,还有营养学、植物学的典籍。
他们兴奋地说,那天吃了好吃的植物,不知道是什么,这怎么可以,应该把它搞清楚,现在全部有关的信息已经查明。
, http://www.100md.com
于是先翻开植物图册,认图画、辨照片,验明那草的正身。然后翻开植物学辞典,说那草乃什么科、什么属,搞清那草的来路。又翻开拉丁文辞典,说那草拉丁文应叫什么什么。再翻开药典学,告诉我那草含有这个素那个素。
“有一种降压药,叫什么什么,有它的成分。”那位年轻的太太认真地强调补充。
我笑着看德国人的傻劲儿,吃荠菜不就是吃荠菜嘛!
为查荠菜的知识,夫妇两人在柏林国立图书馆里泡了一天,然后借出来这一大堆书,又跑到我这儿来。那些荠菜的知识,我如今只剩了一个在脑子里,好像是在什么营养书里,他们查出来,这种草“可吃”。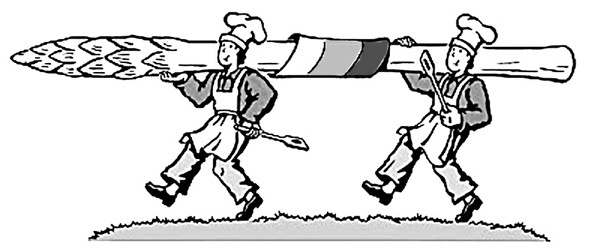
后来,这对德国夫妇逢人便说,中国人是最敢吃、爱吃、会吃的人民:“您能想象吗?中国人走路时会去看地上的草,会想到挖起来煮到锅里做菜吃!”
, 百拇医药
我却发现荠菜在德国到处都是。我同样也搞不懂德国人,把这么鲜、这么美的菜扔在地里头,几百年的德国历史中,竟然没一个人试着去尝一尝!他们不是也有过饥荒吗?
我想起年轻时在陕北。那儿穷山恶水,吃糠、吃菜、吃草、吃根,还是不能把肚子填饱,人人对山对水怀着一种吃的感情。中国上千年战乱饥荒不断,使我们对吃有着一种特殊的情结。甚至汪曾祺到美国,见了地上的草,会说:“这种草的嫩头是可以炒了吃的。”“多放油,武火急炒,少滴一点高粱酒,很好吃。美国人不知道这能吃。”有时我想,世上只有我们有这种气魄,能把大自然吃得那么彻底。
德国人和美国人一样,都没有“吃”的眼神儿。他们只是喜欢大自然,简单直接,发自内心,没什么道理。
很早,我就有过这种感受,记得还诌过什么句子。抽屉里找出旧本子,见记下来的是:
他们把每一片绿色/都印到了心底;
我们带了汁水/把每一片绿色煮到了锅里。
这不同的文化差别,真是奇妙啊。, 百拇医药(谢候之)
有位在柏林工大进修的罗女士来访。罗女士是南方人,在与我太太闲聊时,忽然说起:“你家楼外的草地上,有好多荠菜耶。”
两人当下跑了出去,挖了一大抱草回来。
我看那草,是一种塌地的植物,绿色的叶子,羽状的叶片,带了分叉,有点儿像是荠菜。但心里不敢确定,就说:“荠菜不是长在中国的吗,洋人这儿会有野生的?”
罗女士态度很坚决,说:“我觉得它就是荠菜。我们小时候去野地常挖的。”
我说:“那这儿怎么没人采、没人吃呢?好像根本没人认得这东西似的。”
罗女士撇撇嘴,说:“洋人根本就不懂吃。”
, 百拇医药
几个人争议很久,终是口馋,决定不管三七二十一,学神农不要命,尝了再说。
大家认真动起手来,把那菜掐根洗净剁碎拌馅儿,和面压皮儿包馄饨。罗女士是个烹调老手,说,荠菜吃油才香。我拿了油瓶,倒了半瓶油到菜馅里,用筷子去搅,那油竟一下子消失得了无踪影。心中不由得大喜,素菜能这等吃油,其味必佳!
馄饨煮好盛到大碗里,大家都伸了头去看。清汤里面,馄饨一个个大馅宽边儿。包着馅儿的皮皱缩成一朵,透出玉绿色,甚是可爱。夹起一个馄饨来,咬下去满口的鲜香,真好吃。果然是上品荠菜!
太太后来走路只看地面。最后有了心得,说是发现以柏林工大学生宿舍C楼前一片草地上的荠菜最为肥大。她找了空闲时间,拿了小篮去挖。回来后又精心将荠菜洗净,装食品袋,放冰箱,打电话通知各处朋友。如此兴奋忙碌,并不觉劳苦。
有一天,我请大学里的一对德国夫妇来吃这荠菜馄饨。他们齐声大赞菜馅的清香鲜美,说是从未吃过,每人吃了两大碗,兀自不肯罢手,都问馅是什么菜做的。
, 百拇医药
我答:“一种可吃的蔬菜。”
又问在哪儿买的,中国商店吗?
我笑答:“路边挖来的。”
他们都大惊失色,把我吓了一跳。我忽然意识到问题严重。洋人只懂得吃的东西要从店里买,敢对路旁脚边的东西下手,还把它们煮到锅里,做菜下饭,拿来宴宾待客,这行为是有毛病的。
他们跑进厨房,拿了荠菜仔细端详,还央求我们一起去了趟实地现场。隔几天,这对吃了荠菜的德国夫妇背了个大背包,兴冲冲地专门跑来找我。他们从背包里费劲地往外掏东西。我一看,都是些厚本大书,有德英百科、拉丁文辞典,还有营养学、植物学的典籍。
他们兴奋地说,那天吃了好吃的植物,不知道是什么,这怎么可以,应该把它搞清楚,现在全部有关的信息已经查明。
, http://www.100md.com
于是先翻开植物图册,认图画、辨照片,验明那草的正身。然后翻开植物学辞典,说那草乃什么科、什么属,搞清那草的来路。又翻开拉丁文辞典,说那草拉丁文应叫什么什么。再翻开药典学,告诉我那草含有这个素那个素。
“有一种降压药,叫什么什么,有它的成分。”那位年轻的太太认真地强调补充。
我笑着看德国人的傻劲儿,吃荠菜不就是吃荠菜嘛!
为查荠菜的知识,夫妇两人在柏林国立图书馆里泡了一天,然后借出来这一大堆书,又跑到我这儿来。那些荠菜的知识,我如今只剩了一个在脑子里,好像是在什么营养书里,他们查出来,这种草“可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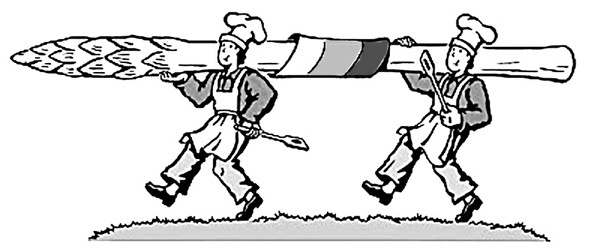
后来,这对德国夫妇逢人便说,中国人是最敢吃、爱吃、会吃的人民:“您能想象吗?中国人走路时会去看地上的草,会想到挖起来煮到锅里做菜吃!”
, 百拇医药
我却发现荠菜在德国到处都是。我同样也搞不懂德国人,把这么鲜、这么美的菜扔在地里头,几百年的德国历史中,竟然没一个人试着去尝一尝!他们不是也有过饥荒吗?
我想起年轻时在陕北。那儿穷山恶水,吃糠、吃菜、吃草、吃根,还是不能把肚子填饱,人人对山对水怀着一种吃的感情。中国上千年战乱饥荒不断,使我们对吃有着一种特殊的情结。甚至汪曾祺到美国,见了地上的草,会说:“这种草的嫩头是可以炒了吃的。”“多放油,武火急炒,少滴一点高粱酒,很好吃。美国人不知道这能吃。”有时我想,世上只有我们有这种气魄,能把大自然吃得那么彻底。
德国人和美国人一样,都没有“吃”的眼神儿。他们只是喜欢大自然,简单直接,发自内心,没什么道理。
很早,我就有过这种感受,记得还诌过什么句子。抽屉里找出旧本子,见记下来的是:
他们把每一片绿色/都印到了心底;
我们带了汁水/把每一片绿色煮到了锅里。
这不同的文化差别,真是奇妙啊。, 百拇医药(谢候之)